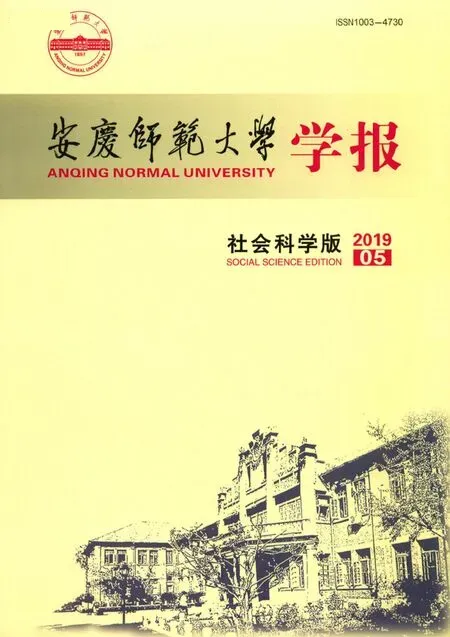清遗民复辟活动论略
2019-03-16程太红
程太红
(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所谓遗民,指朝代更替之际出现的不仕新朝、守贫节志以报故国旧主之恩的特殊群体。民国初年的逊清遗民,在文化上强调赓续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在政治上反对共和政体,图谋复辟专制。“时清室遗老,方以拥戴故君为职志”[1]1,“大清皇帝之中兴,盖无日不默祝暗祷”[2]644。从清帝退位(1912年)至伪满洲国成立(1932年),逊清遗民图谋复辟的活动持续不断,“可以说从颁布退位诏起到‘满洲帝国’成立止,没有一天停顿过”[3]84。正如时人所道:“然则于复辟之乱,独不惜精血,秉毛椎、钻故纸,恒至丙夜,矻矻不休,搜索枯肠,忘食废寝,几如光武之读书,乐此不疲。”[2]583
整个民国年间的遗民复辟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2年溥仪退位至1917年张勋复辟,为遗民复辟的亢奋期,复辟活动频频发生,至丁巳复辟达到高潮;第二阶段,从1918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为复辟活动的消沉期,遗民复辟势力衰退,几无复辟活动爆发,仅剩以溥仪为首的前清王室与若干遗臣仍在四处活动;第三阶段,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至1938年“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病故,为遗民复辟的异化期,遗民主观上的复辟活动被日本侵华所利用,溥仪、郑孝胥等遗民也沦为举国唾骂的汉奸。
一、遗民复辟活动亢奋期:“宵光熠熠星争出,妄想圆成日再中”
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各地遗民蠢蠢欲动,欲恢复清王朝统治,遗民复辟活动进入亢奋期,“宵光熠熠星争出,妄想圆成日再中”[4]。1912—1913年间,以溥伟、良弼、善耆、铁良为首的王室宗亲领导宗社党人在全国各地发动复辟活动。逮至袁世凯称帝前后,隐逸于京津、青岛、上海等地的逊清遗臣强烈要求“还政于清”,并且秘密聚集起来筹划复辟。在宗社党人与各地遗民的推动下,至1917年张勋复辟,已然进入复辟高潮。
这一时期,遗民复辟活动的核心力量是宗社党势力与隐逸于京津、青岛以及上海的遗臣。
辛亥革命爆发后,前清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贝勒载涛、军咨府军咨使良弼以及江宁将军铁良等宗室王公建“宗社党”。该党初为清室对抗与绞杀革命党、破坏革命的御用机关。参加者大都是京师满清宗室与各地的八旗子弟。溥仪退位后,宗社党成为复辟最活跃势力。
民初宗社党势力分布广泛,活动频繁。“直隶、东三省、湖北三地最为频繁”,“其他从沿海到内地,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皆有党人的活动痕迹[5]4。在宗社复辟势力中,青岛的溥伟、善耆与西北的升允是最大的两股力量。
1912年春,溥伟等青岛遗民欲联合日本川岛浪速等人,策划满蒙独立,建“北清帝国”,但因袁世凯政府的阻止而中断[6]。同年夏,溥伟联合青岛遗民刘廷琛、陈毅、于式枚等人策划“癸丑复辟”。据温肃记载:癸丑(民国二年)二月,赴青岛,转赴充州访张绍轩于军次。时王怡山(王宝田)在张幕府,因王介见张,述近日宫中事,谈及时局,引为同志。复返青岛,恭邸(恭亲王)与张绍帅密谋讨贼,期以三月一日举义,旋改初三袭济南,但事情败露,亦宣告失败[7]。
1912—1913年,升允与蒙古王公贵族、沙俄侵略势力相勾结,企图组织武装发动复辟,并策动地方军阀官僚等封建势力共同响应[8]。尽管宗社党的复辟活动十分频繁,但大都以失败而告终,一方面由于宗社人员分散,缺乏严密的组织与有效的联系,另一方面,党员驳杂,素质亦落后,“自是难以成事”[5]4。
袁世凯上台后,大力鼓吹尊孔复辟思想,引起了各地遗民的注意。初始,遗老不明袁世凯称帝的真相,纷纷要求袁世凯政府“还政于清”,“当袁氏盛时,力足控制一切,诸人虽怀兴复之志,苦于无隙可乘。及称帝议起,其腹心爪牙颇有携贰,复辟之机,遂动于此矣。”[9]42
1914年,寓居青岛的劳乃宣连作《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君主民主平议》《书陈东塾先生说长白山篇后》等文,要求袁世凯“还政于清”。他提出:“定国名曰中华国,不称民国”;“定纪年曰中华国共和,几年不称民国几年,以共和纪年,乃周召共和旧制”;“总统任期原定五年可以联任,今定为联两任,共十年,预为规定以免临时周折也。今年为共和三年,至总统十年任期满,为共和十二年,其时宣统皇帝年已十八,可以亲裁大政,预定是年,还政于皇帝,依周之共和十四年,周召公还政于宣王故也”;“还政之后,大清皇帝封项城为王爵,世袭罔替,所以报项城之勋劳,亦以保项城之身家也”[10]150-151。随后,劳氏又致书赵尔巽、徐世昌、周馥等人请他们劝诫袁世凯采纳其建议。
在劳乃宣的影响下,刘廷琛亦撰写《复礼制馆书》《君主共和评议》等文章,大谈大清二百年厚德载物,而民主制实不适中国。若袁世凯自为帝,必为举国所不服,外国亦所不承认,因而只有返大政于大清皇室,复还袁氏内阁总理之任才合理。时任职于民国国史馆的宋育仁亦联合史馆中的遗民,公开发表“还政于清”的演讲,并且上书请愿,公然要求袁世凯答应他们的请求[11]。与袁世凯私交甚好的前两江总督周馥,先后三次致函袁世凯,要求复辟清室。
逮至袁世凯政府垮台,青岛遗民与上海遗民更是往来不断,积极密谋复辟。据《郑孝胥日记》记载:他与沈曾植、李瑞清等人就多次约见青岛遗民刘廷琛、章梫等人,共谋复辟事宜[12]1602-1603。沈曾植还数次致书升允,提议寻找奉系军阀的支持,“大局非无机会,利用督军团亦可不折一矢”[13]85。此法得到升允、章梫以及金梁等遗民的认可,他们纷纷远行东北,游说张作霖[13]768。
在京津地区,康有为、梁鼎芬等遗民策反冯国璋复辟。据《恽毓鼎澄斋日记》记载:“近日‘复辟’二字,忽喧传于中外。康南海唱之,冯华帅和之,闻梁星老颇奔走于其间。民国以来,横征暴敛,纲纪不修,于是人心日思旧朝,加以项城失威信于北,民军争权利于南,土匪横行,生民蹙蹙靡聘,急谋救济之策,不得不出此一途矣。”[14]郑孝胥亦云:“过姚赋秋,闻梁星海自南京归,云冯等已一致举龙旗复辟,十五六日可宣布。”[12]1614
与此同时,一直心系大清的张勋及其“辫子军”加入了复辟阵营。“张勋者,素号粗鲁顽鈍之人也,其脑筋中常有一大清宣统皇帝存在,所谓受恩深重,不可忘也。”[1]9张勋及“辫子军”的加入,为遗民“推翻”民国政权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与军事实力,将复辟活动推至最高点。
1916年至1917年间,张勋在其幕僚万绳栻、刘廷琛、陈毅等遗民的策划下,不断扩张自身实力,为复辟作准备。他先后多次聚集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安徽等各省代表在徐州召开会议,利用会议的“合法性”,转而变为“十三省之盟主”。时人评价云:“其盘踞徐州,广招兵队,固时时以复辟为怀而彼辈之所谓研究阴谋派者,即利用之,以为尝试之具,而彼又何知,居然为十三省之盟主矣。”国民党议员孙毓筠亦认定张勋召开徐州会议,“其黑幕中实为筹备清室复辟”[1]9。
如此以来,“清唱班成矣”[13]86。1917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争端,以“调停人”的身份带兵北上。入京后,他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开始实施复辟。张氏认为北上复辟是各派军阀赞同与默许的,以力证自己复辟的“合法性”:“勋此次到津,徐东海朱省长均极端赞助,其余各督军亦无违言。芝老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谓只须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勋又密电各方面征求同意,亦皆许可。”[1]17
复辟活动正式提上日程之后,张勋力邀请各地遗民北上商讨复辟事宜。张氏之“谋臣”万绳栻、刘廷琛等人就致电升允、沈曾植、郑孝胥、陈曾寿等人,邀请他们共谋复辟事宜[12]1667。陈曾寿、胡嗣瑗二人接电后携沈曾植拟定的《复位奏稿》《第一月行政大略》《第一诏书》率先北上[9]50。 随即“(张勋)复函约沈公子培、王公聘三及郑苏龛、李季高、沈爱苍等北上,共同商办”[9]46。康有为、沈曾植、王乃征三人随即到达北京。“文武圣人”顺利会师,复辟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917年7月1日,张勋、康有为等人以武力相胁进入紫禁城,拥戴仍在睡梦中的溥仪复辟,改元为“宣统九年”。至此,遗民筹划了近六年的复辟终于实现,“六年四乱不堪悲,明主中兴万物熙;鸡犬不惊金鼓静,驰驱九陌看龙旗”[15]。
但是,张勋复辟之举招致社会各界的唾骂与讨伐。“民国而谋复辟是叛逆也。民国为国民之国,国民为保全自己之国计,群起而讨逆宜也。”[16]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出兵讨伐张勋。讨逆军势如破竹,12日即攻入紫禁城。复辟宣告失败,张勋、康有为等主谋弃主而逃,“此军再挫清再亡”[17]。
1912—1917年是清遗民复辟活动的亢奋期。时值清朝覆灭不久,民国政局混沌,遗民思恋故国故君的情结强烈,在主观意愿都上极力赞成复辟。再者,以溥伟、升允、张勋为首的前清遗臣仍保留了一定的政治军事势力,为他们对抗民国的复辟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但是,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复辟运动的失败亦是必然的,遗民复辟之举无异蜉蝣撼大树。在丁巳之殇之后,复辟势力被大大削弱,辫子军的解散致使他们丧失了唯一的正规武装力量。曾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张勋等人亦退出政界。遗民结束了依靠自身实力进行复辟的可能,该群体亦沦为民国政治文化舞台上的边缘势力。自此,遗民复辟活动进入消沉期。
二、遗民复辟活动消沉期:“旧庐萧瑟空流叹,大陆疮痍正费才”
张勋复辟失败后,遗民复辟活动逐渐进入消沉期。复辟势力衰退,仅余溥仪周边“近臣”郑孝胥、罗振玉、金梁、陈曾寿、胡嗣瑗、陈宝琛等人仍汲汲谋划起事。但在此阶段,遗民苦于“旧庐萧瑟空流叹”,并且认识到“大陆疮痍正费才”[18],溥仪与王室的安危以及复辟运动的开展必须需要助手与外援。故而积聚复辟力量与寻找复辟外援成为消沉期遗民的主要活动,但其拉拢外援的策略亦以失败而告终。
丁巳之殇后,遗民复辟力量大为减弱。曾参与谋划复辟的政治遗民大多选择闭门不出,著述自娱,不问世事。如张勋在复辟失败后,归隐天津,“此数年间,尘事不婴,闭门多暇,日辄流览通鉴,或习为大字,不复与世相闻。自念少起寒微,中更军旅,讫与事变终始,今行年六十有八,内省多疚,奚足语人者。”[19]刘廷琛则隐逸于青岛,“以书法自娱”[20]。沈曾植亦退隐上海,“垂翅而归,亲友畏避,廉公门馆,不异曲池”,“顾南中集矢,北乃溃然,此中因果,殊非思议。病不堪忧,置勿复道可已。”[21]至20世纪20年代,遗老大多已年事已高,病弱不堪,复辟要人皆先后逝世。遗民已经很难依靠自身势力进行大规模的复辟运动。
在复辟人才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溥仪“近臣”金梁就明确表示筹划复辟之事必须寻求外援,“求贤才、收人心、联友邦”实为重中之重,“心腹之臣运筹于内,忠贞之士效命于外”[22],极力要求发展复辟人才。1924年4月10日,金梁上《列举贤才折》,向溥仪推举复辟中兴可用之人才三十位。金梁荐举的“有可用其心者”与“有可用其人者”皆为遗民,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积极的复辟分子,如升允、刘廷琛、铁良、万绳栻、胡嗣瑗等人。而金氏所提及的“有可用其名者”并非都是遗民,其中尚有民国政客与新式知识分子。如熊希龄,“勤敏有为,颇负物望,前虽有不谨之处,仅用其名无损于我”。再如蔡元培,“异说惊人,似有魔力,实则化之以德,未尝不可援”。如梁启超,“著书立说,文采动人,后生学子靡然从之,实能左右舆论”等等[23]。由此可见,在金梁看来,无论政见是否一致,凡是能为复辟所用之人的皆可拉拢。金梁“贤才折”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了以他为首的部分遗民强烈要求复辟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一阶段复辟势力的衰弱,遗民单纯依靠自身实力是无法发动复辟活动的。
金梁的《列举贤才折》是在1924年提出,故而时人有“甲子复辟”之说。但是金氏的发展复辟人才的计划,还未实施即被冯玉祥政变中断。冯氏个人对于溥仪小朝廷的存在早已不满,“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患”,“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24]1924年11月,冯玉祥在取代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后,将溥仪驱逐出宫,囚禁于醇亲王府。
冯玉祥的举动,引起了全国各界对于溥仪以及王室待遇问题处理的讨论,金梁就说道:“有主张原订条件一字不动者,有主必还宫复号者,有主改号逊帝者,有主岁费可减,必有外人保证者,有主移住颐和园者,有主在东城购屋者。实则主权在人,无异梦想,皆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遗民听闻后,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为溥仪安危以及王室待遇的保留积极奔走。郑孝胥曾多方拜访段祺瑞,庄士敦亦密切与张作霖联系,但是皆未果,“盖自段、张到京后,皆空言示好,实无办法。”[3]176-177
为了摆脱民国政府的控制,确保溥仪安危,遗民决定将溥仪偷送至外国使馆,以寻求政治庇护。11月29日,溥仪以治病为由,在陈宝琛、庄士敦的陪同下,逃到了德国人的医院。随即庄士敦赶往英国、荷兰公使馆,寻求“避难”。但是去往领事馆的庄士敦迟迟不归。郑孝胥在得知此事之后,随陈宝琛赶往德国医院,将溥仪送到了日本大使馆。
经此事变后,溥仪与其身边遗民深刻地认识到王室的安危以及复辟的开展都需要外部势力的支持。此后,他们极力拉拢本国的军阀势力与外国政治军事势力。溥仪就曾表示“我在天津的七年间(1925—1931),拉拢过一切我想拉拢的军阀,他们都给过我或多或少的幻想。”
溥仪曾寄厚望于奉系军阀,但以失败而告终。“给过我幻想最大的,也是我拉拢最力、力时最长的则是奉系将领们。”[3]2091926年6月,溥仪拜访了张作霖行馆曹家花园。席间,张作霖“恭敬”的态度与“效忠”的言语极大地鼓舞了溥仪复辟的信心。自此,他公然开始了与奉系军阀的酬酢往来,多次接见张学良、张宗昌、楮玉璞、徐源泉、李景林等奉系将领。在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之后,溥仪又寄希望于“矢清室之志”的张宗昌,为其提供了大量的金钱资助。
除此之外,陈宝琛与康有为亦四处拉拢其他军阀势力。1926年,冯玉祥失势后,张作霖、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权。陈宝琛曾亲自到北京,找其旧友、新任内阁总理杜锡珪援助复辟。康有为则直接致函吴佩孚,以“中华之民国,以清朝让之,非民国自得之也”等语进言,劝其还政于清。吴佩孚则以“金石不渝,曲高无和必亦”之言拒之[3]204-205。
20年代是各派军阀争权夺利最为激烈时期,他们根本无意于复辟王室。尽管溥仪提过:“吴佩孚曾上书向我称臣,张作霖曾向我磕过头,段祺瑞主动地请我和他见过面”[3]209,但这些只是军阀们的是敷衍之语,更甚至正如溥仪自己所说,这些遗民刻意的亲近,“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向我要钱”[3]217。
郑孝胥、罗振玉等人则不断寻找外国势力支援复辟。他们前后联络过沙俄的谢米诺夫、奥地利的阿克第以及英国的罗斯等人。这些人都是本国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被本国政府驱除出境,他们在政治军事上已无实力可言,不可能替遗民办成任何实事。他们鼓吹复辟,不过是迷惑遗民,骗取钱财罢了。
在消沉期,溥仪与遗民拉拢国内与各方势力支援的方案,都以失败而告终。除了金梁曾有甲子复辟之议,遗民也未有提出新的复辟计划。清遗民真正意义上的复辟活动也已经在此阶段完全落幕。
三、遗民复辟活动异化期:“欲资才狼助,终乃作傀儡”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扶持溥仪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尽管溥仪是“满洲国”的执政与“皇帝”,但是实际上的统治权完全被日本控制。“满洲国”并不是清朝的复辟,而是日本“以华制华”政策的产物。溥仪、郑孝胥等遗民主观上的复辟活动被日本侵略者所利用,最终“欲资才狼助,终乃作傀儡”[25]5701,遗民复辟活动完全异化。
“满洲国”的建立虽是日本蓄谋己久的计划,但与遗民无意识地推动有一定的关系。1924年冯玉祥政变爆发后,郑孝胥、陈宝琛将溥仪送至日本使馆,为“满洲国”的建立埋下了祸根。自此溥仪与遗民的言行与活动完全被日本所监控。在日本人的“保护”与“殷情照料”下,遗民不仅未能清楚地认识到日本行为的目的,更甚者对日本充满了感激,“他们从使馆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王国维就曾说:“(日本)非徒以皇上往日之余尊,亦且视为中国将来之共主,凡在臣僚,谁不庆幸?”[3]189遗民的这种认识造成了他们对日本的错误判断。故而在日本提出“满洲国”计划时,深得部分遗民的赞同。
在遗民复辟活动异化期,溥仪是“复辟”的核心人物之一。一方面,作为亡国之君的溥仪强烈要求恢复其自身的“皇帝”之位;另一面,日本正是利用溥仪的“皇帝”身份与复辟的心理,以达到它“以华治华”的目的。
1924年,溥仪得到日本的“帮助”与“优待”后,始终认为日本将会是其复辟的重要助力:“自从进了北府,得到了日本人的‘关怀’以来,就对日本人有了某些信赖。我在日本公使馆里住了些日子,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3]234
1926年,“皇姑屯事变”后,有人曾劝诫溥仪,切勿盲目相信日人,避免走张作霖的老路。但是,溥仪与遗老认为日本需要他们的帮助。而他们可利用日本与中国的矛盾,以达到复辟的目的:
张是个带兵的头目,这样的人除了他还可以另外找得到。而我是个皇帝,这是日本人从中国人里再找不出第二个来的。那时在我身边的人就有这样一个论点:“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关东与党军(指张学良与国民党)协和,力足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3]218-219。
溥仪对日本的依赖的心理为其走上汉奸之路作了准备。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急需在东北扶持一个傀儡政权。日方即向溥仪与遗民提出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并要求溥仪立即东渡。陈宝琛、胡嗣瑗、陈曾寿等遗民则劝告溥仪东渡一事,不可鲁莽行动。“东北的局势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以及‘民心’的趋向等等,目前还未见分晓,至少要等刘骧业探得真像之后,才能决定行止。”[3]269陈曾寿更是上奏稿:“密规近日情势,宜慎赴机宜,免误本谋”,“所当暗中着着进行,不动声色,使人无从窥其际。待机会成熟,然后一举而起。故不动则已,动则必期于成。若事未实末稳,己显露于外,使风声四播,成为众矢之的,未有不败者也。”[26]175
但是,溥仪心意已绝,坚持东渡。1931年11月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土肥原贤二“拜见”溥仪,表示军部将扶持溥仪建立“满蒙独立国”,“与日本为攻守同盟”[12]2350。溥仪在得到日方保证之后,随即东渡至旅顺。初到东北的溥仪就发觉事与愿违,日本并不是为了帮助其复辟,而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尽管他坚持复辟大清,但是在日本的淫威之下,他亦无任何反抗之力,只有不断妥协与退让,最终成为了完全意义上的傀儡。
溥仪的“皇帝”身份是日本建立“满洲国”的重要幌子,而郑孝胥则是日本能够顺利实施计划的核心人物。
辛亥革命后的郑孝胥,曾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局势,积极谋划复辟。在他看来,在“共和”“共产”之后,中国将会被国际“共管”,并且将恢复溥仪的皇统。“共和生子曰共产,共产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复昌。此图谶也。”[3]2072而在“共管”未有来临之前,日本将会是复辟的最佳助力,“日人以复辟为己任,其论甚正,华人必有能受其任者”[12]1601,“日人毋始于义而终于利”,日本“赞助复辟之举乃道德干涉,非权利干涉也”[12]1611。这种对国际国内局势的错误判断,致使郑孝胥走上了与日本合作之路。
1923年,隐逸十年的郑孝胥得到溥仪重用,开始出仕溥仪小朝廷内务总管一职。冯玉祥政变后,郑孝胥将溥仪送至日本使馆,是为羊入虎口第一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郑孝胥认为是大清复辟的最佳时机,“久悬之文章可交卷矣”[26]174。他极力怂恿溥仪东渡。
溥仪一行到达东北后,日本就对郑孝胥予以“重任”,以“总理”之位许之,让他一手包揽“满洲国”的建立事宜。郑孝胥沉醉于位高权重的迷梦中不可自拔,企图依靠传统儒家治国理念建立一个“王道乐土”的世界。
郑孝胥对“王道”理想的追求使他不自觉地充当了日本的工具。郑氏对内不断向溥仪与诸遗老施压,迫使他们听从日本的要求;对外则与日本达成各项协议,出卖中国主权。在溥仪与诸遗老不赞成“满洲国”的政体是共和国时,他告知溥仪:“共和,则谢以未达;如议君主立宪,则告以事体繁杂,须研究讨论,果无流弊,乃试行预备,以三年为期”,“复辟必须依赖日本,眼前与日本反目,将来的希望也完了。将来复辟不是没有希望呵”[3]303,“现在答应了日本军部,将来把实力培植起来,不愁没有办法按着咱的意思去办”[3]308。日本更是借助郑孝胥“满洲国”总理身份与其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控制了整个东北的政治经济命脉。
溥仪的复国梦想与郑孝胥的“王道”理念终究不过是黄粱一梦。“满洲国”是傀儡政权。政务上,日本实行“内部指导”与“总务厅中心主义”策略,日方的“总务厅”是最高权力机构。中央各部门的总长虽是中国人,但是每个部门都配备由日藉“次长”,并由次长控制实权。郑孝胥名义下的“内阁制”与“国务会议”毫无实权。经济上,日本借郑孝胥之手,与其签订《日满协定书》等协议,完全控制了整个东北的经济运输命脉。思想文化上,日本将郑孝胥的“王道”理念转变为奴化思想。他们将郑氏的“消除种族之见”思想掺以“白种人食肉,残忍之性不同于黄种人之食谷者”观念,为其发动战争寻找缘由[12]2403。除此之外,日方还宣传郑氏的“博爱”思想,以磨灭汉族与大和民族之间的种族区别,消除东北人民的反抗与爱国情怀[27]。郑孝胥的施政策略与其“王道”理念完全沦落为汉奸理论,成为他“汉奸”身份的罪证。
溥仪、郑孝胥与日方数次交手之后,逐渐认识到日本侵略的本质,但无力改变。“仓皇任国事,倐忽岁再易。空拳冒白刃,非主反为客,拙棋受机子,此局难对弈。何能贪天功,潜转岂人力”[28]。“满洲国”完全傀儡化后,郑孝胥亦被日本人抛弃。1935年,郑孝胥在《大同报新年献词》中抱怨说:“满洲国初为幼儿,故需日本扶持之。今已由童稚而成人,足以自立,不需人扶持,而日本仍以幼儿视之,则乖于理矣。”[25]6343此方言论引发了日方不满,遂以大字不识的张景惠取而代之。随着郑孝胥的逝世,也宣告中国传统士大夫企图依靠传统文化治世方案的彻底失败。
历史证明,遗民复辟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对于遗民而言,复辟的失败未尝不是好事,大多遗民在灰心意冷之后,都选择以诗书度余生,保全名节。“满洲国”虽然“成功”了,但是溥仪、郑孝胥等人却丧失了民族气节,沦为了举国唾骂的汉奸,这种“成功”的代价,无论对于他们个人而言,还是整个民族国家而言,都是得不偿失的。究其根源,遗民“不识世界大势,不明政治正轨”[2]617,锢守道统与政统,这种保守、落后乃至反动的政治文化观念导致了他们的失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时代在前进,旧式的传统道德与学识已经无力逆转中国社会、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清遗民最终被历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