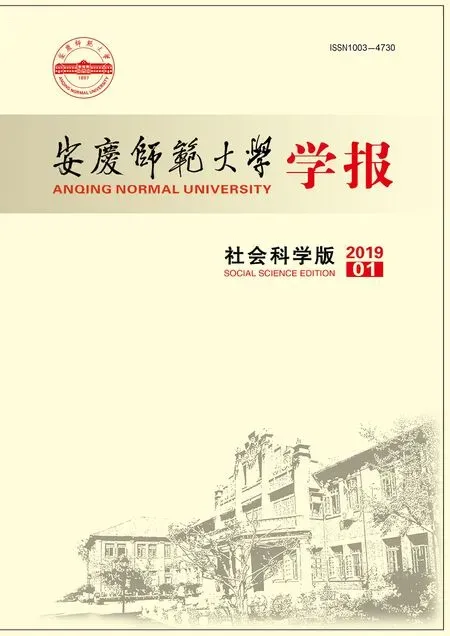《南山集》案前后的方苞
2019-03-15陈昌志
陈昌志
(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一、人物生平与南山集案本原
前人论述方苞“其叙天伦悲苦处,怅触生平,时为泫然废卷。痛莫切于伤心鲜民之谓矣。”[1]用“悲苦”二字概括方苞的生平,可以称得上是方苞的异代知音。又论及“望溪立朝,议论亦多如此,泥古而不彻,强人以难行,当时皆厌苦之。”方苞为古文大家,一生精研儒家经典,先贤行迹学说当对他产生极大影响,反面的评价则“文过饰说,似是而非”可以说刻薄到极点[2],我们认为方苞是一个标准化的儒家知识分子,纵观其生平以及思想,南山集案无疑成为考察的一个重点。
南山集案是清代统治者发动的几次大型文字冤狱之一,其本来目的是为了钳制读书人思想,扫清统治中国这一政治过程中的文化障碍。很不幸的是,方苞在这场灾祸中被牵连下狱,成为其人生履历中最难以磨灭的记忆。事情起源于方苞为同乡文人戴名世集作序,其序文:“吾闻古之著书者,必以穷愁。然其所为穷愁者,或肥遁而不出,仕宦而中跌,名尊身泰,一无所累其心,故得从容著书以自适也。”[3]
“戴名世字田有,号褐夫,又号南山,桐城人。才隽辩逸,不事生产,家落,授徒自给。以制义名,刊本流布,自曰:‘此非吾之文也’……都御使赵申乔劾其所著南山集狂悖,逮治伏法。其被祸也,由于有志于明史,闻桂王旧阉有为僧者,欲访求之。又得乡人方学士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书中沿用永历年号,坐大逆,论极刑……望溪亦因作南山集序,同罹其难。”[4]
方苞下狱,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如果说这段序文有问题,仅仅在于他不应该为戴名世的文集作序,大体上他所言的都是旧式文人那一套著书立说的缘由与经过,与政治无涉。戴名世的问题在于不顾现实的语境,固执地选择一种杀身成仁的态度,以“故国人民有所思”的身姿去眷顾早已远去的历史图景,想通过不朽的“立言”寄托人文情怀。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将“犯罪”与“惩罚”转换为符号系统之后,这样描述:“君主及其权威、社会共同体、管理机构;标志、符号、痕迹;仪式、表象、操作;被消灭的敌人,处于恢复资格过程中的权利主体、受到直接强制的个人;受折磨的肉体、具有被操纵的表象的灵魂、被训练的肉体。”[5]147我们可以将方苞置于这样的关系中加以讨论。“惩罚场面在公众心目中确立或加强了这种成对观念(犯罪——惩罚);一种话语使一套符号传播开,使之每时每刻都发生作用。”[5]143反观方苞,其心迹可以证明。
细读方苞文章,发现其一生明显分裂为两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行文中都蕴含着特定的无可奈何与不可言说的痛苦,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精神分裂错乱症患者才可能有的表现。
二、案发后的方苞
康熙辛卯(公元1771)年,方苞的内心一定蕴藏着无限的痛苦。
作为儒家的饱学之士,对于“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而成仁”一定有深刻的体认,生活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辛卯年冬十月,余以南山集牵连被逮”[6]713这是故事的结果,又“五十一年,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这是故事的曲折过程,“五十二年,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峄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免罪入旗。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未几,改直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7]事情的最后,看来一切皆成定局,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更大的波澜在方苞的心里早已翻江倒海。他所面临的最切实的问题:采取怎样的态度面对这个可以令他生亦可以令他死的政权。
如果将方苞在“南山集案”前后的文字做一番比对,会发现一些令人惊喜的细节,透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反观这样一位满心矛盾的文人做过一番怎样的苦痛挣扎,而最终走向这个对他而言曾经是无法逃避的压迫力量的行迹。
那年,方苞作《狱中杂记》,“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同于往圣,每质狱辞,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傥仁人君子为上昌言:‘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别置一所以羁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数计哉!”意外的是,方苞一方面在揭露狱中魑魅,另一方面却又写出这样的“谀辞”,此时的他,思想中仿佛植入了一台矛盾的螺旋桨,以一种无罪的姿态默默抵抗加在他身上的一切有罪推定,既想保住传统儒家士子的高洁品行,又害怕随之而来更加可怕的政治打压。所以他说“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引孟子“术不可以不慎”以求心灵解脱。
方苞详细记叙了在陷狱这一年所遇到的生命中的“贵人”,从陌生人到知己朋友,仅仅是因为“先生大名,上深知”,方苞作《结感录》,文中可见其内心情感的波动——他感激的是这一群陌路知己,却又不得不将这种感激之情外化出来,变成那个“一言定生死”的人物。“结感录者,志辛卯在理时诸公为余德者也。余羸老蹇拙,虽报德不敢自誓也,惟感结于心而已。其故交如同里刘捷古塘......盖感者以为其道未可以得之也,若诸君子,则与吾为友时,早见其然矣。今感而录焉,是轻诸君子之义。”[6]713深于礼学的方氏甚至搬引经义来为自己立论做支撑,同时也是为这些他在狱中认识的朋友做现实的注解,但这些文字无疑早已从某种程度上窥破了他内心深处的隐秘[8],这一显性的矛盾好比是自己挖的陷阱,接下来的他不得不引身向前往那陷阱中奋不顾身地一跳。
壬辰年,作《大理卿高公墓碣》,方氏在追述恩师生平时,终于不能忘掉年前的那场大灾难,此种文字,时见笔端。“又六年冬十二月,以乡人戴名世文集牵连被逮”又“余所犯尚未决,虽天子明圣,而吏议余罪至重,死生未敢自卜,恐公之仁孝,余独闻知者,遂就湮灭,而心气瘀伤,不能营度为人。”[6]403将自己尚未判决之罪归功于天子明圣、吏议所归,这种言论不能不令人觉得他的胸襟气度不复从前了。
癸巳年,多亏他颇负时望的古文拯救了他,在李光地的善为说辞下,得到了康熙帝的朱谕“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如此一来不但赦免其罪,而且对他的学问给出很高的评价,他自身也得到安置“以白衣入直南书房”开始了他的三十年仕宦生涯,经历了康、雍、乾三朝。有《与白玟玉书》,当初方氏罹祸,白玟玉曾经给予襄助,“足下微服,冒众隶相调护;既就逮,为纪家事,拮据药物,以供老母,逾年如一日;二君子始以仆为知人。”[6]661早在《结感录》里,作者就再三表达了这种感激之情,彼时尚有一种心高气傲的迹象,盖既抱定一种无望的心态,无意徘徊他顾,自然朋友之间情谊纯洁不容玷污,可有趣的是随之附带一笔“今赖天子仁恩及于宽政,二君子及众戚党做计御老母而北,已于二月下旬抵京。”此时已经是“以白衣入直南书房”的皇帝近臣,言必称圣上皇恩,想来方苞是深知由士进入仕这一角色转换之间的堂奥的。在这封书信里,他说“仆少诵书史,窃慕古豪杰贤人,求之乡里间,惟刘君古塘……然尝惜其规模过隘,长游四方,所见当世名士不少,未有如古所云者,而二君子且倜乎远矣。及与足下相见至再三……”方氏此时的说法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在之前写给杜老先生等人的书信、墓表中可全然不是这样说的呢?如果说言必称尧舜是儒家知识分子致仕精神所必由,那么言必称圣上皇恩则无疑标示着此种知识分子向某种力量低下了高贵的头颅,身体的打压或许已经恢复,但精神的臣服从此开始显现,无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笔者无意刻薄古人,仅就罗列的事实而言,方氏似乎将之前种种傲骨精神丢失殆尽,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丢失,已然可视为一种无从捡拾的遗憾了。
为朋友代作《弦歌台记》,细读这篇文章,只会令读者感到方苞言不由衷与不知所云。“余思之经旬,而未得所以为言之义焉。将陈夫子之德与道欤?则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不可绘画;且语之至者,已备于前贤矣。将谓兹台为邑人所瞻仰欤?则今天下郡县州学皆有夫子庙堂,过者不戒而肃恭,亦不系之兹台之存毁。至于山原林麓之观,又不足道也。”[6]410他不知道要如何表达经历生死劫难后的情绪,这种语焉不详的背后是怎样的“淡乎寡味”与“空洞无物”呢?这实在是方氏文中的败笔。
在《泉井乡祭田记》一文中,从作者的追述中恍然可以一窥其惨淡往事“吾生而存,若辈无饥且寒”苦厄之中的坚守似乎更能够激发其内心的柔弱,身体神经层层传递,终于使手中的笔记录下凄惨的时光“又五年辛卯冬十有一月,余以南山集牵连被逮,将至京,守吏防夫伺甚严。或曰:‘入则不可以生矣。’余惧余姊言之终弃也,乃于逆旅夜煹灯作书寄兄子道希,使以兹田归冯氏。”[6]416透过文字,我们不难想象当时方苞惶惶如丧家犬的凄苦样子,他不得不散尽家财,而他自己亦将这种恐惧之情变现在纸上,这一番情景究竟可怜,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蒙皇帝赦免的方苞在罹祸之后的诸多文字里充斥着如“会逢天子仁圣,不遽用吏议,而不肖之躯延于狱中者又逾年。”在噤若寒蝉的姿态下小心翼翼地诉说着别样动人的话语。值得注意的是此文的落款“时康熙壬辰十一月望后六日,在狱思愆斋”这“思愆”二字好似在玩弄一种无罪的阴谋,显然不至于到屈节的地步,或许在方氏的逻辑深处,既然已经无法选择一种“成仁”的姿态去俯仰天地,那又何妨在这冰冷浊臭的刑部大狱里冷静思考自己的“罪愆”呢?至于皇帝的朱谕赦免是否与这一番前程的“思愆”密切相关呢?便不得而知了。
作《许昌祯妻吴氏墓志铭》,自述遭遇“余既许诺,逾月而被逮,又二年出狱。”[6]327有《宣左人哀辞》语“而是冬十月,以南山集牵连被逮”“及余宽法出狱,隶汉军”[6]456,有《阮以南哀辞》语“及先君子殁,而余及于难”[6]459,从以上种种来看,方苞对于这场牢狱之祸难以忘怀,他并不够达观。苞在狱中治三礼之学,作《礼记析疑序》有言“壬辰、癸巳间,余在狱,箧中惟此本,因悉心焉。”[6]810这一时期,凡著文总是若有若无地映带一笔,其中似乎有某种深意——近乎刻薄的怨愤之辞,只不过在文人天生的善于保护的笔下,流露出的便成了“哀而不伤”。究其大概,凡经历过伤痛苦楚的人对于往事总念念不忘,这是人的自然属性,这是一方面;方苞到底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一生都在成圣为贤的追求中,这使他如何能真正向一个非汉人的政权低头心折呢,在那些时常提及往事的文字中,少了一种更加激进猛烈的批判姿态,这种批判精神的缺失,是否可以看作是他内心矛盾挣扎中作一种“卧薪尝胆”式的积蓄力量的过程呢?
康熙五十三年,岁在甲午,方氏有《记梦》一篇,“杨君老而穷,走四方,而余祸发于不虞,以辛卯冬十月赴狱”;又“余既编籍旗下,上哀矜,使以白衣厕馆阁校勘。自痛丘墓无主,故虽病且衰,而黾勉从事。盖以天子仁圣,犹万一冀幸焉。记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6]522他一方面近乎婉曲地表达了自身不得不隐藏的无奈情绪,另一方面则又不断地表示自己的诚挚心意,由离心转向向心的过程中[9],当是五味杂陈、无法言说的,只不过圣上皇恩浩荡,竟然可以使一个儒家弟子不断违背自己的初衷,最终面折心服。同年,方苞作《长宁县令刘君墓志铭》中给出了注解“及君就选,余难后志气益索,老母沉屙,君主余家凡数月,而未得一听君琴。君顾余促促,每悄然不乐。”[6]735此一时期,“志气益索”“促促”“愀然不乐”皆是真实写照。
丙申之后诸作,这种经作者刻意经营的文字渐渐减少,此时的方苞,正式完成了他的自我救赎,已然走上一条坦途——在外力的束缚下,走向另外一条他自己从来不曾想过的道路。倘若我们站在今人的立场,方苞此举或当受到谴责:政治的驯服,早已经磨灭了文人心中那点残存的焰火,行文看起来颤颤巍巍、风烛残年,我们心中所构想的方苞不该是这样一幅噤若寒蝉的形象,似乎他已经把内心的信仰丢弃一旁,做些不痛不痒的歌颂文字。然事实上却是身处权力压迫风暴中心的文人实在是有许多无奈,方苞不过是选择了一种极尽委婉曲折的言说方式,他的内心依然痛苦而火热,依然愿意选择一种乐观放达的生活态度。试看其在《游潭拓记》中的那段议论:“余生山水之间,昔之日,谁为羁绁者?乃自牵于俗,以桎梏其身心,而负此时物,悔岂可追邪?夫古之达人,岩居川观,陆沉而不悔者,彼诚有见于功在天壤,名施罔极,终不以易吾性命之情也。况敝精神于蹇浅,而蹙蹙以终世乎?”[6]423日本文艺家厨川白村说:“人唯在游玩的时候才是完全的人。”[10]要之,方苞内心自然是苦闷而后悔的,可是后悔归后悔,人生终究得向未来看,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才是正确的态度。可是,这种态度便会陷入老庄的世界里,而对于儒家饱学的方氏而言真的有效吗?这正如厨川氏所言:“于是我们的生命力,便宛如给磐石挡着的奔流一般,不得不成渊、成溪,取一种迂回曲折的行路。或则不能不尝那立马阵头,一面杀退几百几千的敌手,一面勇往猛进的战士一样的酸辛。”比较之下,我们便能直观地发现这构成一个有趣的隐喻,方苞的内心实在是痛苦到极致。
三、案前方苞
梳理方苞南山集案发生之前的文字,我们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番情形。这与前文构成明显的矛盾,这就让人感到困惑,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能使一个人前后产生这么大的变化。
甲申年,苞作《吴宥函文稿序》,行文之间,这位“年三十二始举江南乡试第一,逾七年,为康熙四十五年,中试进士第四”[11]的得志青年对腐败的科举制度下失意的友人表达了无限的同情,并且猛烈地批判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故余序其文而有感于教人与取之得失如此”又“夫教化既行,其取之也,求以可据之实行,而论之以少长相习之人,犹未必其皆得焉。乃用章句无补之学,试于卒然,而决以一人无凭之见,欲其无失也,能乎哉?”[6]893青年时代的方苞一开始就选择用一种独特傲岸的身姿面对他的这个时代与社会,这无疑是凌厉痛快的质问,然“久困场屋”才是这一时代的习见,宽解朋友的同时也无非是抒发自己内心对这一应试方式的早已不满的喟叹。
这年,妻蔡氏琬卒,作《亡妻祭氏哀词》,从行文来看,这位“性木强,然稍知大义”的妻子与苞之情感稍嫌寡淡,在苞则给出其解释“余少读中庸,见圣人反求者四,而妻不与焉,谓其又无贵于过昵也。乃余竟以执义之过而致悔焉。甚矣!治性与情之难也。”[6]503其铭:“惟在生而常捐,乃既死而弥怜。羌灵魂其有知,倂悲喜于无言。”释悔追悼之情现于笔底,此可为苞“少不更事”的确证,也是天真心性的显现。作《教授胡君墓志铭》,用心细致地刻画胡公这一位贤者形象,又“余每见与君同时人,其形貌辞气必笃于后生,遭遇多坦夷康乐。”对这样的现象给予解释:“盖方是时,明运虽衰,而太祖立国之规模远迹三代,其教化之通平阴阳而凝聚于万物者厚矣。董子所谓陶冶而成之者是也。”[6]290可见对于朝代鼎革,作者已抱定一种朴素的阴阳相生观念,或者说此时作者确乎一个安时处顺的文人。基于此,对于前朝先辈,承接他们的人生经验教训,臻至溶于自我体系,铭曰“谓俗盖陂,而遇君则甚平。谓天不可知,而赋君者独贞。先民有躅,于君犹微。”
戊子年,时方苞四十一,这年作《左仁传》,“呜呼!当明将亡而逆阉之炽也,如遘恶疾,近者必染焉。忠毅与同难诸君子皆明知为身灾,独不忍君父之寒而甘为燠足者也。世多以仁之类为愚,此振古以来,国之所以有瘳者,鲜矣![6]221”以传主左仁为中心,成就一篇史论,传主事迹鲜明,读书人头脑中“忠君体国”的思想激荡开来,虽为陈迹,不无慨叹之意,惩戒之情,此是儒家思想体系下文人自然生发的思想,然其于新朝发此宏论,可见其正直敢言的精神气象。
作《刘北固哀辞》,好友殁去,忽奄不返。心有所悲戚而无所凭吊,他细数与好友订交数十年间点滴故实,悲怆怀人之情尽现。辞曰:“谓子之归兮,终吾生以后先。痛一言之未接兮,遂闭影于重泉。宦与学其交悔兮,命忽奄而不返。吾语子非不早兮,胡因循而致然?”[6]455在拳拳追问中,依稀可见壮年文人胸中那份语淡情深,哀而不伤。
戊寅年,苞作《灌婴论》,通过对灌婴的功劳翻案“由是观之,定天下安刘氏者婴也,审矣!”他得出结论“岂人心之变,随世以降,而终不可返于古邪?此有国家者所宜长虑也。”[6]69这是一篇献给当政者的策论,可以看出方苞本人的政治态度。读书人安邦定国的理想似可以从中窥见倒影,此时的方苞,身体是自由的,言论亦相对自由,这并不是说他言论悖逆,而是从中可以想见其为人、为学与处世的面貌。身处升平盛世的文人,尽可以从故纸堆中寻找治世方略要术而不用考虑其他,文人的入世精神淋漓毕现,心忧天下建言献策,成为他此时思想的主流。
又作《鲍氏女球圹铭》,在写给外甥女的圹志中,实际传达出方苞的礼法观念。言及“金陵俗浮惰,而女教尤不修,甘食美服嬉游而外,为女为妇之道胥无闻焉。其富女以此相高,贫者不得,则以怼其父母,贱其夫而外其舅姑。余每侍老母侧,见内外宗女,为陈古女妇仪法,群女往往心病余言,稍稍自隐去,独球承听,久而益恭。”[6]406与其说方苞是在作文悼念他的这位未字的外甥女,不如说他是在为自己所治礼学张本。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产生价值观念不同的群体,在礼学大家方苞看来,恢弘古礼无疑是相当重要的,而鲍球便是亲身践行古礼的代表,为其彰表后世更可见其崇礼意志,亦可见其儒家士大夫心性,即构建秩序分明,安定有序社会的愿景。
作《何景桓遗文序》,在满腹遗憾中,方苞对科举取士制度再次发起猛烈的抨击,语言峻切深厉,为前作诸篇中尤为杰出。“余尝谓害教化败人材者无过于科举,而制艺则又甚焉。盖自科举兴,而出入于其间,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6]609在当时的语境下,此等议论不啻石破天惊了,甚可以说到了狂悖的程度。此时方氏身上那种激进的精神,令人感动。
《方苞集》中录作者年三十至四十间所作诸文,从文体论的角度分析[12],有序十篇、论二篇、书札共计十一篇,墓表哀辞共六篇、传一篇、散文五篇。可以看出,作为应酬之用的文章并非这一时期的主要构成,而作为抒发一己之见、叹、感的文章则占据了大半,有对科举制度限人作无尽的口诛笔伐,有对治国之术的发问,有对礼学理想的追求,有对时文的主张,这些方面大概可以说明壮年时期方苞的思想构成,更能表明这一时期其思想激进言辞的峻切,分明是以一个王朝的叛逆者与挑战者的形象出现在那个时代的,只是方苞何以敢发出这诸多激进逾矩的言论呢?这与他既可以居庙堂之高,又可处江湖之远的身份特征不无关联。
四、余 论
因为一场“无妄之灾”而陷入矛盾心理的方苞,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人格与文字中流露出的态度判若云泥。应该如何对其进行批评呢?我们给予方苞一个参照——南山集案的主角,戴名世。戴名世仅仅是对清王朝的离异,而不是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离异[13]。在《南山集》中,找不到对封建思想体系和封建制度的任何批判。“《南山集》案”则标志着汉族士人反清斗争的基本结束,促成了正统知识分子对清王朝态度的转变,方苞则是这个转变的典型代表。
从方苞文集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转变时期方苞的思想矛盾。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苞的民族意识还间有流露,表现出他对新朝的同志在内心深处并不那么诚服。方苞在青少年时期,他的父亲就常对他讲“诸前辈志节之盛”,这对他不无影响。在《田间先生墓表》《孙征君传》等文中,方苞对坚持民族大义的钱澄之、孙奇逢、杜岕等人的景仰之意,总是溢于言表。当然,在这些文章中,反清的内容已经被抹得淡而又淡了。另一方面,在方苞文集中,还可以读到不少指摘时弊的文章。如《狱中杂记》揭露当局治狱的黑暗,《陈驭虚墓志铭》指斥权势家“有害于人”,《记开海口始末》《浑河改归故道议》等文揭露权臣结党营私、巧取豪夺,《逆旅小子》指责官吏漠视人民疾苦等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方面揭露了“盛世”外表下的黑暗,对人民也有一定的同情,都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但在方集中,大量的还是出自“助流政教之本志”的文章,表现了他根深蒂固的理学思想体系。为此,他甚至谩骂反理学的黄宗羲,而不顾黄也是一个坚定的反清志士。他写的一些揭露现实黑暗的文章,其出发点也不过是为了达到“官耻贪欺,士敦志行,民安礼教,吏禀法程”以整肃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
如果将方苞看作一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显然他是一个“圆形人物”[14],这在于他的心路历程永远处于一种漂泊不定的状态,他似乎永远在追求着一种完美的精神,但是在时代的潮流下,又多少显得有些迷茫彷徨,一代知识分子的苦苦求索,在政治与内心之间难以却达成一种平衡。于是,我们看到的方苞,是这样的形象:善于韬光养晦,使得我们想批评他却又苦于找不到切入点,以为那或多或少的错误只不过是时代的不幸罢了。知识分子在这一“规训与惩罚”的过程中,要完成其自我救赎的使命,必然形成两种走向:或选择继续反抗,用良知呼唤正义,在极端的情况下则选择逃避这个社会,但实际上这种办法会使他们陷入一种“不餐周粟”的矛盾而略显尴尬的境地;另一种做法则是选择一种“暂时的”缄默不言,在此群体看来,韬光养晦,避开风口浪尖无疑是明智的,等到社会清明,政治压力减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点微弱的呐喊,产生出“反动的”言论来。方苞属于后者。
方苞是不幸的,他承受着时代带给他的无法避免的灾难,其心态亦从激进敢言走向曲折迂回,这自然可以说是人生的成熟,却是个体精神不无遗憾的溃败,这种溃败再无复盘的可能;但方苞又是幸运的,身负大才成为拯救他的救命稻草,从溺水状态登上河岸的方苞,从此臣服这种不可摆脱的命运。但方苞毕竟不是普通人,在归顺的同时依然在抗争,他只是暂时的服从,或者说只是身体的服从,而非心灵深处的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