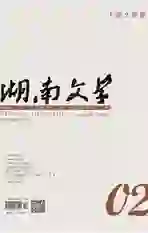飞得更高
2019-03-13苏鹏云
苏鹏云
一
早上改改骑着摩托去园林上班。那摩托前杠锈渍斑斑、周身是污糟糟的红,被改改骑在胯下就像一个受了气的小媳妇一样,沮丧得很。小区的水泥路面破损了很多处,坑坑洼洼的裸露出黄土层来。改改摩托开得弹子球一样左支右绌,到底没能避开一处洼坑,摩托颠簸了一下就熄火了。改改就懊恼得不行,满脸的愠怒。她扔下摩托急唠唠地朝公交车站走去。这时候纳音的电话打了进来。他的声音浮浮的带了一丝不安和犹豫,语音里还夹了点尴尬。纳音说,改改,律师让我把和包工头债权形成的经过写个材料说明,可你知道……
改改淡淡地说,没关系,我下班帮你写。
纳音又期期艾艾地说,改——改,——离婚的事能不能再想想?
改改说,纳音,这事别再说了。我已经想好了!我着急上班,先挂了啊。
不等纳音说完改改就把电话挂了。纳音再打进来,改改就不接了。
改改现在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改改的家在“新欣家园”。是十多年前政府为失地农民建的。在这之前,改改一家和小区的其他人家一样,有十几亩耕地,有好几间砖房和一个大院子。后来,他们一家分到了好几百万的征地款,还有两套单元房。这和从前务农的日子,相差甚远,有九重天那么远。蓦然间的暴富,就像突然从云罅间挤出的光令人头晕目眩。有几年,钱多得像光阴似的从指缝间向外溢。小区里的人们也不遑细虑,只顾欢天喜地忙着过自己的日子。他们打牌、养宠物、洗桑拿、买摩托……(那时候还没有私家车)纳音也照着别人的样子亦步亦趋地描摹,仿佛稍有差池就会落伍似的。他踌躇满志地对改改说,城里人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现在,别人有的我们都有。改改却不以为然,眼前的日子让她有一种迷惘和局促的感觉。
纳音沉溺于赌博。改改劝他别赌了,他瞪着眼睛说,城里人就这么打发日子的,风不吹日不晒的,多好!劝了几次,见纳音还不收手,改改蛰伏的冬虫一样噤了声。
陆陆续续地,新欣家园里有了私家车。纳音看着眼馋,也想买车。盘点家底却发现积蓄所剩无几。纳音心里就恐慌得很。有人劝纳音说,你可以再出外打份工啊,我们的光阴都是这么过的。你整日打牌,输多赢少,家底造完你后半辈子喝西北风啊?坐吃山空的道理你懂不懂!
纳音听着有道理,就想出去试试。
改改说,好啊。电视上一直说南方出现用工荒,你就去南方吧!
纳音去了不到两月就回来了。一进门,改改差点没认出来:纳音像电视剧里的特种兵一样,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的;多少天没有梳洗过的头发烂鸟窝一样蟠结着;饥肠辘辘的斑鬣狗一样的眼睛闪着幽幽的蓝光。在狼吞虎咽地吃下改改为他做的三大碗手擀面后,他告诉一脸纳罕的改改说,南方缺的是技术工人,不是缺人。全中国哪儿都不缺人,缺的是有文化懂技术的人。
改改的娘家在几百公里之外县城的乡下,闭塞又贫困。在那个村子里,改改是唯一上过高中的女孩子。那一年,她还想参加高考,却被爹像拽一叶风筝一样地拽回了家,爹说,一个丫头家,认得几个字,会写自己名字,识得几个数码点得清票子就行了。家里劳力不足,你回家种地吧。
没过多久,爹托人给改改说了门亲事,对方就是纳音。改改心里喜欢洪生,喜欢得整个胸腔里面万紫千红,草长莺飞,蜻蜓乱舞,蜜蜂叫个不停,改改知道,洪生也喜欢她。可那又怎么样呢?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婚姻靠的还是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口口相传下来的规矩。
那洪生不喜欢务农,瞒着父母和村人到新疆摘棉花去了。他像一只仓促间出走的兔子,连一句话都没有留给改改。
很快,爹置办了两桌酒席,请亲戚朋友们坐过之后,就让纳音把改改带走了。那年改改十八岁。由于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纳旭东两岁时需要上户口她和纳音才补办了结婚证。办证的时候,需要填登记表。纳音不识字,不会填。
改改瞠目问纳音,你一個字都不会写?
纳音说,嗯。
改改喃喃自语道,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文盲!
纳音咸鱼一样地翻着白眼说,这有什么好稀奇的?我们村像我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夜里纳音牤牛一样不惜力,贪婪、粗鄙,甚至带着男人排遣内心的原始性猥亵。时间一长改改对房事就怠惰得很。
二
当地政府决定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大型园林。园林里有乔木、灌木、柏树林、溪水、花卉、亭台、假山、花鸟鱼虫,园艺景物一应俱全。就需要有一大批工人去侍弄这些景物。当地的劳动就业部门和建设单位签订合同,劳务用工全是新欣家园的失地农民,官方把大批量地安排劳动就业称为“劳务输出”。改改被社区委派为“劳务输出带领人”。社区主任说,改改你高中毕业,有文化,脑子活络,知道怎么带领人。
改改急赤白脸地说,可我没有专业知识呀?
主任睒着眼睛不容置喙地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改改每天挤时间在电脑前查看园艺布局、花鸟的养护、乔木的剪枝、灌木的修葺、植物的习性和喜好,几个月下来,不知不觉也记了两大本笔记。她就照本宣科地将这些知识口授给干活的工人,竟和园艺师讲得相差无几。主任眼里的改改就有了木秀于林的感觉。他咂巴着嘴感叹道,这有文化到底是不一样啊!
改改劝纳音说,你也到园林上班吧,活也不重。
纳音如一只树懒一样伸着懒腰说,钱挣不多,还早出晚归的,我累着了。
小区棋牌室在某栋楼的一楼,是一户八十平米的住房,生意红火得很。推牌九、掷骰子比大小或摇单双、打麻将的,分别坐在几个自然间里,叽叽喳喳聒噪得很。由于楼群间距窄、光照不足,加上在烟雾和苍蝇屎的熏渍下,原本就有限的空间显得更加逼仄兼黯暗,即使是开着灯。
那天晌午,陕北来的“油耗子”提了半麻袋钱到小区棋牌室找人耍赌。这是个五短身材的中年男人:微胖,黝黑、秃顶,小臂上文着一条腾飞的青龙。他将半麻袋钱掼在地上,拍着手上的灰尘叮囑老板说要找一个牌技和财力旗鼓相当的人耍;他说,藏獒PK藏獒,叫棋逢对手;藏獒咬鹿犬嘛,他摇头接着说,那叫倚强凌弱!
他的声音炸雷一样打着忽闪在屋子里訇訇滚动。像接到指令一样,打牌的人都停了手;说话的人也噤了声,他们都静静地集结到了“油耗子”周围,他脖子上手指粗的金链子、地上的钱袋子、质地考究的白绸衫裤、霸气的口吻都令他们着迷。他们脸上更迭着的是仰慕和自卑。也许,还有巴结吧。
老板满脸堆笑地拉开抽屉,拆开一包“软中华”递给“油耗子”一支,凑近,点上。然后自己也点了一支说,怎么着?耍大的?
“油耗子”吐着烟圈点了一下头。
老板撇着京腔道,没问题,您就好吧!
“油耗子”是个富得流油的主儿,只要让他满意,服务费还不是他随性给?老板这样想着的时候,脸上就笑出了一脸的牙花子。他把纳音引荐给了“油耗子”,说,这个纳音深谙赌道,还讲义气,从不耍赖。“油耗子”拿脚搓着被自己扔在地上的半截烟蒂说,好,就纳音吧!
双方在桌子的两头摆开了阵势,摇骰子比大小。纳音手气那叫一个旺啊,只摇了三把,就把半麻袋钱赢了过来。
“油耗子”一脸的水波不兴。他把车钥匙扔给马仔,淡淡地说,去,再去提钱。
纳音说,不耍了。
正在兴头上的“油耗子”脸就暗了下来,可又不在陕北的地界上,也不好发作。就怏怏地招呼马仔准备离开。他刚一捩转身体,却碰到了迎面走来的改改。
改改是那种漂亮得落套的女人:猫脸圆中带尖、大眼睛、刀鼻儿。那天她穿了一条黑色小脚裤,白吊带上罩了件宝蓝色的中袖外搭,姣美之中带着点狂悍。年轻的改改颠动着碎步走得很快,被吊带束着的胸脯随着她的走动也微微颠动。“油耗子”禁不住心旌摇曳,他迎上前去在改改胸部捏了一把。“呕——”改改受了惊的母鹿一般,尖叫一声,屋里一片阒然。人们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油耗子”脸上已挨了改改一巴掌。
改改才从社区开会回来,落了钥匙,是来找纳音要钥匙的。一进门就碰到了这个武大一样的矮子对她动手动脚。她气急败坏嚷道,你要干什么?
咋了?旁边有人一边问一边拉开了改改。
这一切都被送“油耗子”出门的老板看在了眼里。他心想,这还了得?这不是挡我的财神、断我的财路吗?也是有意替“油耗子”遮丑,他冲改改瞪眼睛说,人家也没把你咋地呀,不就碰了你一下吗?
改改叱问老板道,你把你婆姨弄来让他碰啊?她清秀的脸庞涨得如朱鹮鸟一般通红,尖着声音吼道,去叫啊——
少顷。人众里发出一片此起彼落的埋怨声,一个女人咋那么厉害;没事让人家走呗;你又没有损失啥,还喊啥呢?
又有人挂着一脸促狭的笑,打诨道,就是损失了也没啥,女人本来就是资源,又用不坏!
哈哈哈——一阵荤笑,声振屋瓦。
忽然,“哗啦”一声脆响,紧跟着是一些玻璃碴子在瓷砖地面上跳跃着,发出一阵细若游丝的尾音之后,受到惊扰的蟑螂一般,瞬间往四下里逃窜开去。
说笑声戛然而止,一切又归于寂然。
那“油耗子”受到某种鼓励似的,他满脸怒容地将一只玻璃烟缸摔在了地上。悻悻地说,老子把半袋子钱扔下了,摸你一下怎么了?就是老子想睡你,他又提高音调说,谁敢放个屁?
财大气粗的“油耗子”走到哪里都是中心人物,哪受过这样的气?耍钱耍了个夹生,本就堵心,又挨了改改一巴掌,觉得憋屈得很。他指着改改扭头问纳音,你的女人?怎么这么没规矩啊?有眼不打送钱的爷,你懂吗?你说怎么办吧!今儿不给个说法,我就不走了。说着,打开马仔递上来的一把折扇,沉沉地坐在了椅子上。
纳音堆着一张笑脸说,你说的是。这女人啊,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说着劈手一巴掌,一小股殷红顺着改改的嘴角汩汩地流了下来;接着又是一下,改改的鼻子又出血了。改改哭着骂道,纳音,你个龟孙子,婆姨都让人欺负了……
那个正午,改改的号哭声尖厉又悠长,半个小区都被吵醒了。后来哭不动了,就一声接一声地抽噎。她的身子也跟着抽噎一下接一下地抽搐,仿佛正在遭受西伯利亚强冷空气侵袭的植物一般,寒噤连连的。
花大姐从前也是新欣家园里拿征地款的“富婆”。有一天,花大姐在建筑工地做监理的男人从脚手架上掉了下来,当场殒命。那花大姐本来就是个颟顸之人,又受了刺激,就变得乖张得很。穿得绿黄红紫、周身都是烂醉的颜色,把自己骰子一样掷在赌桌上。结果越赌越大,越输越不服输!没几年就把家产输了个精光,最后连男人的赔偿都搭了进去。为了生计她和那些赌徒们维持着很低级的关系,她陪他们睡觉、喝酒、赌博,他们为她提供最基础的衣食。
纳音说,这花大姐看着蔫儿,其实床上功夫了得!像一只下山的猛虎。不像改改是个中看不中用的。
这话传来传去就传到改改的耳朵里了。改改想,纳旭东太小了,他得有个家。纳旭东是她死灰一般生活里一星微红的炭火,他应该开心。便无心把话说破,就借故说复习功课考园艺师,要搬出去住。纳音数着改改拿回来的一沓工资,忙不迭地点头说,行啊,我支持你。
三
有时候改改会想起从前:她和洪生是同乡又是同学。上高中时功课紧,为了节省时间两人爱抄近路。在经过一道浅宽的溪流时,没有桥,他们就踩着裸露在水面上的石头蹚过去。有好几次涨水,溪水漫过了石头,他们索性脱了鞋、手拉着手一起从水里走过去。那一年,领高中毕业证的那一天,也是涨水的季节。两人拉着手过了溪,都走上了溪畔的沙滩,洪生还没有撒手的意思,改改就要挣脱,哪知洪生的手攥得越发的紧。改改抬头,就看见洪生正盯着她笑呢,露出一口干净、整齐的牙齿,星星点灯似的。改改心里抽了一下,又抽了一下。洪生小声说,改改我想一直拉着你这样走下去!
她的脸红到了脖颈子,不知所措地将散落在侧刘海处的一绺碎发别在耳后,定了定神,低声说,放开呀,让别人看见了多不好。
那时候改改多年轻呀,清晨豆蔻上挂着的一抹水氲似的,清澈、新鲜、芳香四溢。
洪生的媳妇死于一场疾病。“三七”那天,改改去吊唁,看洪生颓唐得如一只折了翅子的鱼鹰。改改就劝导洪生说,孩子还小,你应该振作起来啊。改改在洪生媳妇的遗像前点了三炷香,小声念叨了几句。就挨着洪生在三人沙发上坐了下来,掏出一个准备好的装有现金的信封递给洪生,洪生半推半就着接了过来,和改改两个人一递一声地哭诉。到后来不知怎么洪生就孩子一样地把头埋在改改的前胸,又是一阵嘤嘤悲泣。改改一只手抚着洪生的脊背,一只手插进了洪生茂密的头发里,陪着洪生流了很多眼泪。
都是苦命的人儿!改改想。
改改的娘家也搞“城镇化”,大批的失地农民候鸟迁徙一样地离开了村子。洪生没有像众多的壮年男人那样去更远的地方打工,而是选择和儿子待在一起。洪生在县城买了房。他是那种闲不住的人,闲了就会浑身不自在。他手里攥着上百万的征地补偿款,又找了一份“特快专递”的活,收、送一件邮包,可得一块钱的利。这样下来,每个月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他就做得很卖力。洪生从丧妻的伤痛中走出来是几年以后的事。有一次,改改在长途车站和洪生邂逅。远远看见改改,洪生就笑,说,改改你啥时候回来的?洪生笑的时候,依旧露出一口干净、整齐的牙齿来,时光隧道的灯盏似的,一下子照亮了从前的岁月。改改心里抽了一下,又抽了一下。
改改也笑,说我回来好几天了,该回去了。
洪生要送改改母子去车站,改改也不推辞。洪生蹲下身子要背着纳旭东走。改改说,不用了洪生,他都十岁的人了,这半截路还对付不了!洪生执意要背,改改就不好再说什么。三四里的路程,两人慢腾腾地走了好久。
改改带人侍弄的这个占地一万亩的园林,前身是改改家从前的自然村。那时候,这里全是良田!种优质水稻,也种小麦。村里的人们家家忙着种田,自家地里的农活永远也干不完似的。从前,天很蓝、白云很柔软;而天空下面,是秧苗在亮汪汪的水田里像小姑娘一样稚气、明亮和羞涩;是叮叮咚咚的溪流,它们一路如歌向远方欢快地奔跑;是遍地开着的野花,苦菜花、野菊花、车前草花、马兰花,就像歌里唱的,“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还有,远处起伏的山峦;稀稀拉拉的民居,水墨画似的恬静、浪漫、旖旎。
纳音迷恋农事,是个种庄稼的好把式。他肌肉如鼓的肩头常常扛着一把雪亮的铁锹或别的什么农具,汗水一颗颗珍珠似的从他黧黑而年轻的胸膛滚落下来,渗进到自家的庄稼地里。那时候纳音生机勃勃目光如炬,它像一匹精力充沛的骡子一样,在黄绿斑斓的庄稼地里劳作得酣畅淋漓。全村的庄稼,就数纳音的长势好,没有一根杂草。肥施得也足,理所当然的,产量是最高的。有一年,纳音在田间干活的图片还上了G省的报纸。图片上的纳音穿了件绛红色的跨栏背心,头戴一顶晒得发黄的麦秸草帽,咧嘴笑着,笑得踏实、憨厚、心无旁骛。身后是一望无际的滚滚麦浪。下面是一句话的简讯——丰收在望,产粮大户纳音守望在自家的麦田里。那时候改改和纳音的日子过得安静得像初夏的天空一样,和煦少云。
日子脚跟脚地往前奔,转眼,纳旭东都职高毕业了。
四
一场大风从凌晨刮起,不时发出哨音一样的鸣叫。因缺少人气儿,远离尘寰,那风的鸣叫显得格外凄厉。园子里的灌木啦、花卉啦、乔木啦,剧烈地摇撼着身姿,一个个迷失了方向的生灵一样不知所措。围绕着园林的几十栋高矮不一的商住楼以一种犬牙交错、刀光剑影般的金属色泽指向苍穹。看着眼前的一切,改改想起社区主任几天前说的一句话,禁不住哑然失笑。主任说,没人住的房子就像没人睡的寡妇一样,恓惶得很。
改改想给自己买瓶水,就踅身走进一家小超市。门框上挂着的笼子里的鹩哥开口说话了,鹩哥说,早晨好!欢迎光临,恭喜发财。
改改仰头笑着逗鹩哥,你还会说啥呀?
店主人是个少妇,正坐在收银台前划手机呢,听见改改说话,就扬起笑脸来。画过的眉毛又粗又黑,像两只写意的小虾。她起身,翕动着两片红艳艳的嘴唇笑盈盈地和改改搭讪,怕失商机似的。她说,它今天心情不坏!有一天不高兴了,会使劲儿用头撞竹笼子。想出去。
是吗?改改的心里软了一下,又软了一下。
你这鸟卖吗?改改话问得突兀。
女人愕然。稍顷,她说,你准备掏多少钱买?
改改说,你说个数。
女人伸出了一只手掌,翻了一下。
改改提着鸟笼子爬到假山山顶。改改喜欢登上山顶的感觉:登高望远。
她打开笼门说,你自由了,飞吧!
鹩哥在高空盘旋了一圈,一个俯冲,落到改改近前的树杈上说,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然后张开翅子,一挫身,箭一样地飞走了。
改改笑嘻嘻地冲着半空里高喊,借你吉言。也祝你飞得更高!
社区主任又通知改改到看守所交罚款“领人”。
这是纳音四十多天里第二次“犯事”,起因是為讨薪。债务人是社区一家建筑公司,当事人是满嘴金牙的包工头。
纳音买了一辆卡车,伙着几个人开车给建筑工地拉沙子、水泥。干了有多半年的光景,按合同规定到了结薪的日子,那包工头说,没钱。
纳音几个找人写了诉状,把包工头告上了法庭。
这起劳务纠纷案以建筑公司账上没钱,无法执行而休庭。说择日再审,却再没开过庭。
那天,庭审结束走出法庭的那一刻,包工头乜了一眼纳音,然后脸上就浮出了讥诮的笑。那笑容就像钉子一样楔进了纳音的脑子里。
后来,纳音对另外两个合伙人说,大金牙肯定有钱!纳音几个又找法官说,他公司的生意好得很,怎么能没钱呢?
法官说,我们调查了,他账上的确没钱,法官两手一摊,耸着肩膀表示无能为力。
后来纳音开着卡车载着十几号人,将建筑公司的大门围住。只许进不许出,逼着包工头付钱。包工头打报警电话,纳音几个以“扰乱社会治安罪”被关了一周,交完罚款才被放出来。
改改对纳音说,我已经帮你打听过了,外面有人还欠那包工头几百万的工程款呢。你先别急,我再看看相关法律怎么规定的再说。
纳音头一次上法庭就碰了一鼻子灰,正窝憋呢,听了改改的话,就呵斥改改道,你夹住(闭嘴的意思)!
等你把法律条文吃透了,还不得猴年马月?
那改改和纳音在见识、思想方面是寸木岑楼,早已无话可说。她一看纳音这态度,就不再吭气了。
有一天,纳音几个把包工头堵在建筑工地上一顿拳打脚踢。末了,纳音摆出一副豁出去不过的架势说,我们已经揭不开锅了,今儿你走哪儿我们跟着,哥儿几个饿了,你就得管饭。
包工头满嘴流血,也顾不得擦。一张嘴,镶金牙的嘴里和着血丝又红又黄的。他将头点得鸡啄米一样做小伏低说,好说,好说!哥儿几个肯赏光那是我的福分!
那天,包工头请纳音几个吃完烤全羊,又去了社区一家洗浴中心,一人叫了一个越南“鸡雏”。刚上床,还正在吊兴致呢,被突然闯入的便衣给逮了个正着。纳音几个以“聚众淫乱”、“打架斗殴”两项罪名,又被关了两周。
“领”纳音的时候,改改把两个事先准备好的装有衣裤、鞋袜的纸袋递给他说,你去洗个澡吧!
那些衣物上还带有标签。
她吩咐纳音说,穿新鞋走新路,有这个讲究的。你一定把鞋换上!
纳音眼睛里一热,就有些泪眼迷蒙的样子。改改也不看纳音,说,洗完澡回家吃饭,我有话对你说。
纳音点头答应。
三个凉盘,三个热菜,荤素搭配,都是纳音平素喜欢吃的。改改倒了两杯红酒,也不说话,和纳音碰了一下。碰完了,改改忽然觉着这杯碰得谬误,是欢迎纳音载誉归来么?她咬了一下嘴唇,把脸上的笑全部咬回到肚里去了。纳音先前脸上是讪讪的表情,几杯酒下肚后,脸也红了,话也多了。
他说,“大金牙”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警察一问他全招了,欠钱不还,还说我们打他。等着,我非找机会再教训他一顿不可!
改改平静地说,纳音,你这样冤冤相报啥时候是个完?
纳音一脸的茫然,眨着一双空洞的眼睛,诧异地说,改改,你的意思是钱不要了?又提高声音说,那可是十几万啊,辛苦钱!
改改说,要!通过法律解决。
改改说,他欠你的,外面有人还欠他的,这叫“三角债”。你可以行使 “代位权”追偿。具体怎么做,我已经给你请了律师,到时候他会告诉你的。
纳音孩子似的,深深呼了一口气,脸上是一副醍醐灌顶般的轻松。
收拾完碗筷,改改拿了换洗的衣服准备回到租住的屋子去。纳音说,改改,你还不在家住吗?
改改说,不了!
一时哑场。
改改嘴唇嚅动了一下,终于开口说,纳音,我们协议离婚吧!
纳音错愕,愣怔了一会儿,他说,我不同意。
改改冷着脸说,纳音,这样过日子你觉着有意思没?你是纳旭东的爹,我不愿意把你诉上法庭!
纳音没有为难改改。他起身倒了杯酒,坐在桌前呷一口;吃菜,再呷一口……忽然,嘤嘤地哭了起来。他冲着改改摆了摆手说,改改你走吧,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离婚的事太突然了,你让我想想。
改改洗了把臉,走出门去。
五
改改是在假山上给洪生打的电话,她说,洪生前几天我在园子里放飞了一只鹩哥。
是吗?
我明天要回县城去,你来接我吧?
好。你几点到?我去车站接你。
赶早上的第一班车,晌午就到了。
嗯,知道了!
放下电话改改想,明天先去看看上学时常走的那条小路,这个季节溪水该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