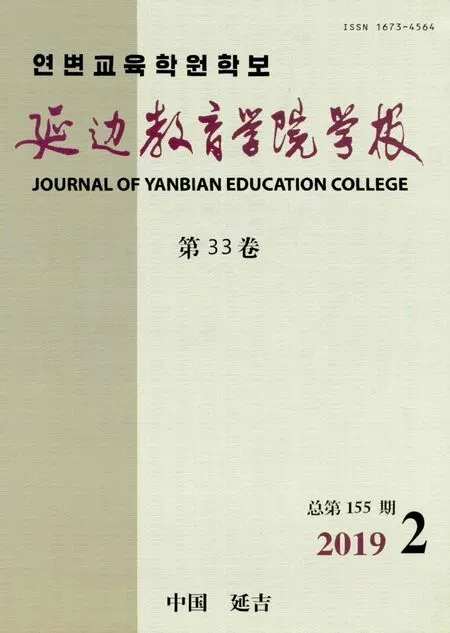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中国想象——以《小径分叉的花园》为例
2019-03-05边萌萌
边萌萌
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中国想象——以《小径分叉的花园》为例
边萌萌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2)
博尔赫斯是一位有着深厚中国情结的作家,他小说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既有意将中国表现为一种可以被他们自己的思维理解的存在,视为一种与其有相同特质的文化现象,又塑造出一个非我族类的“他者”形象。二者殊途同归,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旨在表达中国文化有其优异的特质去参与全球化情形下的国际对话,消除自我的边缘性。
赫尔博斯;中国想象;文化尊重;对话意识
《小径分叉的花园》是博尔赫斯以中国为背景的经典之作,博尔赫斯将中国元素与他一直热衷于探讨的迷宫、梦幻和时空等玄学主题完美无缺地结合起来。
一、中国花园——构成中国想象的基础
比较文学的形象学主要是在词汇、等级关系、故事情节三个层面展开,词汇是构成他者形象的基本单位。在《小径分叉的花园》中,“花园”是最主要的中国意象。随着十三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的流行,很多欧洲人开始欣赏中国园林之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法国画家王致诚对中国园林的介绍使欧洲人对其了解更加深入。18世纪是欧洲对中国最钦慕的时代,英法各国进入了所谓的“园林时代”,“园林”成为中国的典型代表。在中国花园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一方面,中国的神秘性构建了纷繁复杂的叙事空间;另一方面,花园在博尔赫斯的理解中始终与迷宫联系,充满各种未知的可能。小说的标题作为一个迷宫意象指的是阿尔贝的家,俞琛为了找到这里必须按照孩子们的指示:“走左边这条路,遇到每个十字路口都向左拐。”逆时针的走向与《死于自己迷宫的阿本哈坎·艾尔·波哈里》所说的“一直顺左手拐弯,一个多小时后就可以走到迷宫的中心”的迷宫走法相同,俞琛认识到这就是到达迷宫中心院子的做法,阿尔贝的家就在迷宫的中心。花园里的楼阁、曲折小径、凉亭、中国音乐、月白色鼓形灯笼恰巧反映了17至18世纪“中国潮”[1]时代欧洲尤其是英国对中国园林艺术的讨论,是博尔赫斯强烈的主观色彩的展现。博尔赫斯主观构想的中国花园给他叙述的“中国故事”提供了一个相对“真实”的布景。在他对弯弯曲曲的小径,优雅的凉亭的描绘之中,一种神秘、奇幻的气息弥漫开来,引领着读者一步步迈入他的迷宫花园,同时在花园之中博尔赫斯仍然不忘用“黄绢装订的手抄本”“青铜凤凰”“红瓷花瓶”“泛黑的金色柜子”等不断地提醒花园的“中国属性”,对中国花园这种奇幻、神秘的属性的反复描绘的过程使想象的中国转化为具象的中国,获得了艺术上的真实,有力地支持了博尔赫斯的中国叙事。而博尔赫斯正是在东方情调的幻想中,用中国花园给他的小说背景提供了一个奇幻东方的色彩。
二、自我的形象与文化他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使西方陷入了精神危机,欧洲人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叔本华、卡夫卡等作家开始接受东方的道家哲学“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理念,博尔赫斯在广泛的阅读中受到了这些作家的影响。再者,博尔赫斯本身就处在一个动乱、变革的时代,他创作的顶峰时期正是西方政治、思想遭遇最大危机的时刻,以欧美为代表的拉美先锋派文学是在欧美先锋派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欧美先锋派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阿根廷作为拉美先锋派文学的中心,博尔赫斯的作品也表现出对人生和宇宙的困惑和怀疑以及对拉美社会的迷惘和无奈。双重的精神打击让他受到道家思想的吸引,引庄子为知己,在作品中描绘一种形而上的玄虚美学,在“迷宫”中渗透对人生和宇宙的怀疑。汉学家史景迁在《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一书中写到:“我所谈到的大多数作家是在他们感到自己所处的文化前途未卜的时候开始研究中国的,对于那些深怀不安全感和焦虑感的西方人来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一条出路或退路。”[2]
除了所处的时代因素,博尔赫斯自身的神秘主义倾向也是他为了得到更好的艺术效果使用具有神秘色彩的中国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的原因。距离上遥远的中国能够消解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小说中对中国的描写也停留在明代,而且在明代中国给世界的印象还是美好的。时空的距离更能美化对象,巴尔加斯·略萨在《博尔赫斯的虚构》中论述道:“异国情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追求:事情总是发生在遥远的地方,因为远距离可以使得时间和空间更加美妙、生动。”[3]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的神秘以及模糊现实与怪诞的强调愈加突出了中国文化作为他视野之外的遥远疆土的神秘存在,并且极大地契合了博尔赫斯本人对异质文化中有关幻想美学的元素的需要,这正体现了个体需要的文化选择。
博尔赫斯对于中国异域性的想象是基于将中国归化、纳入西方文化的立场,在这种立场下形成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的历史与文化的投影。博尔赫斯的中国迷宫事实上就是一个自我的迷宫,“中国”作为一个被注视的对象,这个对象的形象也就传递了作为“自我”的西方世界的形象。
另一方面,博尔赫斯又将中国当成一个“文化他者”,“文学作品中,遥远的异国往往作为一种与自我相对立的‘他者’而存在。凡自我所渴求的、所构想的以及在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都会幻化为一种‘他性’投射于对方。这种投影大部分属于作者主观,并不能真正反映客体,但从中仍能反映某些信息。”[4]
《小径分叉的花园》中的奇幻色彩仍然是作家政治潜意识的表现,要求作者对已知形象作出夸张,塑造的“文化他者”身份不可避免地落入迷宫叙事的窠臼之中。迷宫叙事的背后,中国是一个超越时间性的形而上存在。因为帝国的永久性、人民的忠诚与自足感、对于秩序与等级的推崇停滞成为一种美德。沉醉于驾轻就熟的花园迷宫意象之中,当博尔赫斯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时候,发现了二者之间一种隐蔽的联系,他将中国的形象与迷宫叙事结合起来,这也是博尔赫斯的开创性所在。通过把中国放到迷宫的中心,只构成了文化上的一团混沌,地理上的一个边缘性他者。这一团混沌是无法用理性来表述的,也是西方无法触及的。博尔赫斯笔下的“中国”基本停留在西方的大规模殖民行动涉足中国之前,也就是殖民主义对中国进行“去神秘化”之前。《小径分叉的花园》所叙述的故事背景也在清代,远离历史发展的中国显然是一个更凝滞、封闭的形象,因而也就是一个更有用的“符码”;正是对于—个陌生而庞大的帝国、—个存在时间比《圣经》还要悠久的文明的一种既好奇又拒斥,既想接触又害怕受到威胁的复杂感受更容易产生文本的奇幻效果。
中国成为了—个失去时间存在与自我身份、对于西方来说是“绝对他者”的存在,一个萨特式的创造性想象物。在博尔赫斯的文本中,“中国”事实上是缺席的,它远离西方的知识系统,与它进行接触与沟通是不可能的,相互之间的理解也是不可能的,它只能作为—个陌生而超验,怪异而未知的“异己”形象出现在西方读者面前。通过异化而将中国塑造成—个神秘而怪诞的空间意象、一个完全无法理解的语义空无,正是博尔赫斯对中国这一“文化他者”进行表述的主要结果;通过解构中国的传统形象,博尔赫斯达到了用自己的方式重构中国的目的。“中国……似乎想接近他而不触及自身是不可能的,鲜有作家能在处理中国题材时不流露内心的幻觉……谈论中国的人讲的其实都是自己。”[5]
三、想象的背后——尊重的文明观与现代中国有待提升的对话意识
博尔赫斯穷尽一生都在追寻中国,根据以上叙述,博尔赫斯笔下的中国,一种是肯定性的、乌托邦式的中国想象,一种是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性的中国描绘。但是二者没有构成内在的张力,都是他身为一个作家的睿智与社会关照意识的流露。
博尔赫斯这位通古博今的世界性作家,有着自己成熟的文化观和文明观,由衷地尊重中国文明,在“道”的制高点上将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如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比肩而论,比如他说:“在日本,你始终能感受到守护神一般的中国的阴影……在日本,人们感受中国就像我们感受希腊。”[6]
《在小径分叉的花园》中,他借汉学家艾伯特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艾伯特一生的意义在于他身为中国文化的探究者和叙述者,当他讲清楚了彭阚花园的秘密之后他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艾伯特是中国文化的工作者与传承者,小说的结尾俞琛懊悔的心情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却为了西方服务杀死了一个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小说的内容是俞琛的供词,也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单就一篇法律供词而言,作案者只需要说清楚自己作案的时间、过程以及动机等,俞琛和艾伯特之间的完整清晰的对话存在于供词之中是没有必要的,俞琛有意将这个有关中国文化的奥秘流传下来。从文化诗学的角度看,“叙述策略不仅属于小说的艺术结构范畴,而且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折射出现实中的权力关系。一定的权力关系必定要在叙述中得到反映,给予某人以叙述话语,就是给予他或她一种话语权力。”[7]博尔赫斯在小说中给予中国的话语权力正是他对中国文明的向往与尊重,他一生向往中国,他曾对中国学者黄志良说“不去访问中国,我死不瞑目。长城我一定要去。我已经失明,但是能感受到。我要用手抚摸那些宏伟的砖石。”
小说文本中的中国又往往是处于“失语”的状态下的,最典型的中国意象“花园”只是一个符号,是博尔赫斯对于空间和时间思考的对象化。在这个小说中最重要的符号就是汉学家艾伯特,他在小说中替俞琛祖父说话,艾伯特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从他口中说出的关于《交叉小径的花园》的解读,是整个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的理解。艾伯特一步步引导着俞琛去理解祖父的意图,向他解释为什么俞琛祖父深谙创作的秘密,俞琛变成了被动的倾听者。在这里,中国文化的秘密似乎只有像阿尔伯特这样的汉学家才能破解,象征中国传统的符号也在阿尔伯特的家里出现。显然,中国的文明与传统需要他者的展示才能获得长生,中国处在文化边缘的地位。传统的世界体系认为,国际秩序是按照劳动分工来划分的,所以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分别处在了中心位置和边缘地位。20 世纪进入了全球化发展时期,这时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两难境地: 参与全球化还是把固步自封, 博尔赫斯看得很透彻,只有参与全球化才能实现自我认同。
博尔赫斯是拉美作家,他所处的阿根廷在当时也处于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代表的世界的边缘,博尔赫斯是一个智者,他选择了世界性的写作。他笔下的中国故事遮蔽了某些历史的实质,历史事件成了脱离情境的素材,但这种虚构却实实在在地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他是一个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作家,他想摆脱西方模式为自己说话,主流的强大一定会湮没他的声音,他只能选择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文化策略来缓解中心文化的唯一性,目的是反边缘化。一方面中华文化中自由无为的观念与西方严谨的秩序和逻辑形成互补;另一方面,中国与阿根廷都属于殖民地,他通过小说道出阿根廷以至整个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全球化的情形下面临失去自我的窘境,为了实现“自我”的文化认同,还有什么方法比塑造中国形象更能表现“自我”呢。
综上,博尔赫斯是希望中国能积极参与到国际对话之中代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发言。我们处在全球化的阶段,认同自我,建立自信,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的发展,建立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这样才能避免进一步被边缘化。
[1]周宁.异想天开——西洋镜里看中国[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1—122.
[2][4]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45,167.
[3]巴尔加斯·略萨.博尔赫斯的虚构[J].世界文学,1997(3):158.
[5]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62.
[6]黄灿然.博尔赫斯遗作新译[J].天涯,1996(9).
[7]张德明.流散群族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42.
2019—02—02
边萌萌(1996— ),女,汉族,湖北宜昌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I106
A
1673-4564(2019)02-0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