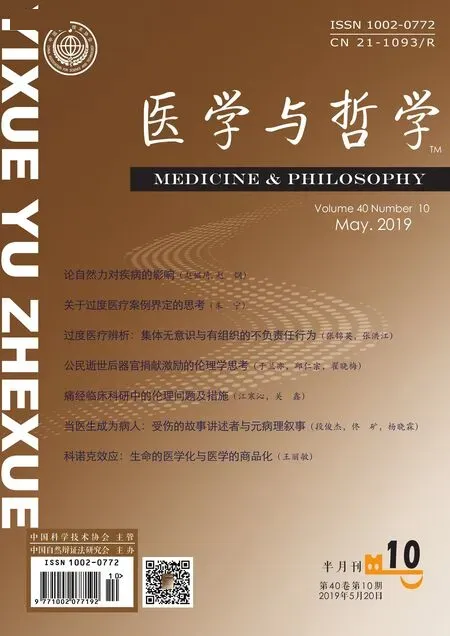技术与文化:器官捐献中的文化困境及其历史渊源*
2019-02-28蒋继贫
彭 博 蒋继贫
在今天,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技术科学之间的隔阂是有史以来最深最大的。
2014年,在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OPO)联盟研讨会上,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宣布自2015年起我国人体器官来源只能采用公民逝世后尸体器官捐献,即自此死囚器官被禁止私下分配,这意味着我国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不足更加严峻[1]。面对这一问题,笔者且从当今中国器官移植技术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文化隔阂谈起。当前中国器官移植技术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便是器官短缺,而导致器官短缺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民众的捐献意愿不高。关于器官捐献,其背后是存在几个理性假设的:人死后,器官如果不捐献的话,也会浪费,每个公民都应该为移植事业做出贡献;器官就是人体的一个零件,没有象征和情感意义;当获取器官时,家属应该暂停他们的悼念活动;脑死亡应该成为最直接的科学的判断死亡的方法[2]14。然而在中国本土实践中器官捐献工作的开展却困境重重,与上述假设所预想的状况大相径庭。关于这背后的原因学术界过去多从医学、法学、伦理学等角度进行探讨,却较少从医学历史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来探究。
当前人体器官捐献大致经历八个步骤——报名登记、捐献评估、捐献确认、器官获取、人道救助、缅怀纪念、遗体处理及器官分配,笔者且以这一主线串起器官捐献背后的历史文化困境。
1 身体的决策:生命价值的沟通
器官捐献中报名登记、捐献评估直至捐献确认这三个环节深刻反映了人们对于生命价值的认知。当前在这一方面我们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民众的实际捐献意愿不高。过去较多研究在大量对普通人群和特殊人群(如大学生、医务工作者)进行定量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宣传、转变观念、通力协作、强化激励等多维的促进器官捐献的策略[2]14。然而上述对策提出的一个大的假定前提是人性是自私的,我们是不愿意捐献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文化中的生命价值认知去探究,或许会疑惑,我们是真的自私,真的不愿意捐吗?亦或我们压根应该从别的环节探寻原因。
对于生命价值的哲思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文化中都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生命价值的观念最早源于种植经济时代人们对生命的理性认知,早至西方古希腊早期的哲学思想中,普罗泰戈拉就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3]毕达哥拉斯也曾主张:“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能结束自己或别人的生命。”[4]在中国古代同样有着类似的生命价值观念,在《孝经·圣治章》中孔子曾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中国医学的奠基之作 《黄帝内经》 中也有记载:“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这些思想都说明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对生命价值认知的原点是对生命的敬畏,以及生命价值的至高无上性。所以我们在此就要反思,在器官捐献中我们究竟是应该转变民众的生命价值理念?还是应该让民众更理解器官捐献的生命价值?如果说器官捐献背后所蕴藏的生命价值与民众的生命价值理念是一致的,那么或许我们应该做的是消除两者之间的互通障碍,架起沟通的桥梁,如果说器官捐献背后所蕴藏的生命价值与民众的生命价值理念是背道而驰的,那么或许做什么都是无用功了。
器官移植技术追求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命价值观呢?这一价值观是否符合我们普遍的生命价值观念呢?
其实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古代,早有对器官移植所蕴含的生命价值观的神话隐喻。《列子·汤问》中载:“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谓公扈曰:‘汝志强而气若,故足于谋而寡于断,齐婴至弱而气强,故少于虑而伤于专。若换汝之心,则均于善矣’。扁鹊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治之,投以神药,即悟,如初,二人辞归。”在这段描述中不仅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生命平等、生命至上、生命优先的诠释,更潜在蕴含了一种生理康复向社会、心理、康复模式转变的思想萌芽。与此同时,在西方,一个耳熟能详、老少妇孺皆知的神话故事就是《圣经》里关于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的传说,上帝用泥土造出始祖亚当,并以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就其妻夏娃。公元前12世纪的印度神话中的象头神就是利用象头复活的雪山神女的儿子。这些虽是神话,但却反映出器官移植最原始的价值理念便是生命的延续,同样也表达了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以及生命价值至高无上的观念。
由此可见,器官移植技术所追求的生命价值观其实与我们普世的生命价值观是一致的,我们在用一个逝去的生命来挽救另一个生命,这是一种生命的延续。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他们能真正理解器官移植技术背后的这种生命价值观,他们是愿意用自己已经逝去的生命来挽救另一个生命的,所以关于器官移植技术面临的器官捐献紧缺背后的历史文化反思应走向让更多的人真正去理解器官捐献背后这种生命接力的生命价值观,而并非一味斥责人性的自私,亦或一味强调转变思想观念,因为我们只有首先弄明白了普通民众的观念是什么,才能真正明白怎么做,面对器官捐献,或许我们正确的方向应首先是沟通器官移植技术背后的生命价值观与普通民众普遍的生命价值观,而并非执着于改变民众的生命价值观。
2 不完整的身体:对生命去向的追问
器官捐献中器官获取、遗体处理及器官分配这三个环节涉及到捐献者及其家属等如何面对生命逝去后生命去向的哲学思考。
在中国传统的生命价值观中,我们注重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意义,同时也关注生命的终结也即生命的去向。生命的去向包括形体的去向和灵魂的去向。从生命形体的去向来说,在《庄子》看来,万物都遵循着从生到死的生命规律,死后回归原初的物质世界,重新分解为基本物质,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其他的生命形体。至于具体转化为何种生命,却是不可知的。从生命灵魂的去向来说,则多主张灵魂不灭。正是基于有灵魂不灭这样的观念,所以为了防止生命灵魂的载体也即生命形体的消逝,人类创制了一系列的丧葬仪制与丧葬文化。传统的丧葬礼仪,充分表现了中国人“事死如事生”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就是把逝去的亲人当成还活着的人来处理,本质上就是生者为死者办一场盛大、隆重、哀荣的告别仪式。按照古礼,就是逝者在出丧阶段的礼仪,包括招魂、讣告、沐浴、饭含等礼俗程序,仿佛是送一个人远行,其中蕴含着浓郁的生命信仰因素[5]。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器官捐献过程中,许多家属要求能为捐献者举办一场类似的仪式以告慰亡灵。有学者做过相关访谈,记录过这样一段内容。
从手术室回到急诊室外的路上,X的婶婶提出了要给他烧一些香蜡纸的请求……我们开始为烧纸钱寻找地点,最后是定在一个人行天桥上。捐赠者的另一个表哥提着两大包香蜡纸来到了附近的天桥。他抱怨说:“依不到家乡的习俗的,家乡习俗可麻烦了。”他还提出要将烧剩的纸灰装起来带回老家,但是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在烧纸的过程中,死者的姑爷以及另一名亲属也过来了,全程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2]86。
由此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器官捐献过程中,我们是否做到了对捐献者及其家属生命价值的尊重以及满足捐献者及其家属对生命去向的追问。
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笔者认为过去我们在对丧葬仪礼的理解上有一定的误读,即丧葬仪礼虽包含有仪式和精神两方面的内容,但随着传统土葬方式以及各类繁琐仪制的逐渐弱化和消逝,或许我们应将重点转向丧葬仪制背后的文化及其所凝聚的对生命的思考。从器官捐献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尊重捐献者及其家属的生命价值,在捐献过程中充分考虑捐献者及其家属的丧葬风俗习惯。这种充分考虑并非要有多么隆重的仪式,而是要能让捐献者及其家属以他们过往所熟悉的经验方式来表达对死者的敬意以及对生命的告慰。目前,在器官捐献实践操作中主要有三方面措施来表达对捐献者的敬意:一是在器官获取前通过集体默哀的方式表达对捐献者的崇高敬意;二是在技术上,主要是通过先进的缝合技术尽量保持身体的完整;三是从遗体处理来看,当前许多地方都建有专门的捐赠者公墓,并且每年都会有固定的纪念日来缅怀这些捐赠者。但是,我们也可发现仅仅上述三种途径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捐献仪式上或许还可以做得更好。
对于生命去向的追问,主要体现在器官分配的环节,根据当前器官分配机制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捐献者及其家属是无法知道被捐献者的身份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捐献者家属真正面临了对生命形体去向的未知。现实采访中,也有不少捐献者家属表达了其实非常想知道被捐献者的身份,或者说特别想知道捐献者的生命的一部分是如何在另一个生命上延续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我们进一步需要去思考的便是如何在不影响被捐献者的情况下让捐献者家属能够了解那个他们最亲的“人”究竟去了哪里。
一位器官捐献志愿者这样说道。
你看有人就是那个眼角膜嘛,捐献给别人能够给别人带来光明对不对?我就看了,哎呀,可以呀。反正我呢,人呢,现在呢,反正就是讲人老了反正死了也不知道了,反正能够有东西,自己身上的东西能够给别人可以用上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呢?……或者是和我玩得好的朋友,或者是我女儿有那么一天发现她妈妈的眼睛能够带来光明的话,那不错啊,两个人多走动走动,变成好朋友了。就像她妈妈还在世上一样[2]94。
另外还有一位捐献者的父亲说道。
小孩很孝顺,如果不这样,如果脑子还管用,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现在脑子没用了,捐出去还能帮助有需要的人。感觉他还活着。所以我的要求是,假如接受者能联系我,我就想到孩子的器官还活着。假如实在不愿意联系,也就算了[2]95。
由此可见,器官捐献中面对生命去向的追问,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如何做到对器官捐献者的尊重以及对其自身及其家属生命的尊重;另一方面就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在捐赠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从人文关怀上让捐献者及其家属明了生命的去向。在传统社会中甚至直至今日,我们对丧葬仪式一直存在一个误读,即随着岁月的变迁我们似乎越来越只关注到仪式本身而忘却了仪式产生的根本意义和目的,过于重视丧葬仪式的形式,实则丧葬仪式是通过一系列可操作的程序来帮助一个生命与其家庭关系及社会关系进行脱离和告别的过程,其核心意义应在于对逝去生命的悼念以及对其原先所在的社会关系关系的调整,因此我们追求的应不是仪式的形式而是仪式的意义,我们应将重心放在仪式对于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家庭的意义。而对于生命延续的去向,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如何站在捐献者及其家属的角度让其更好地了解身体究竟去了哪里。
3 身体的意义:对生命“无偿”的误读
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在研究“库拉”交换圈现象时提出:“一个人之所以给予是因为他期待报偿,而一个人之所以回报是因为他害怕伙伴中止这种交换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馈赠—接受原则’(the principle of give-and-take),它既可以满足个人的心理需要,更是整个社会维系、整合和团结的管道,是美拉尼西亚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6]12与此同时,莫斯[7]在《礼物》中阐述到:“在后进社会或古代社会中,是什么样的权利与利益规则,导致接受了馈赠就有义务回报?礼物中究竟有什么力量使得受赠者必须回礼?”他提出了一种所谓“hau”(礼物之灵)的魔力,即礼物携带了捐赠者本性、精神、生命力,这种力量神秘而危险,总是迫使礼物回到它原初出发的位置。“hau”(礼物之灵)这一概念说明了礼物交换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人与人之间精神层面交流的过程,礼物交换的过程打破了原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初的隔绝状态,该过程既完成了人与人之间精神和情感方面的交流,也完成了社会关系的互动。由此可见在器官捐献中,所捐献的器官,至少在捐献者亲属和接受者看来,是携带了其主人的性情和人格。且器官捐献中的“无偿”并非绝对的无偿,器官捐献中的“互惠”实则是捐献者本人或家人与“社会”这个匿名但真实存在的整体进行交换。
当前我国器官捐献的基本原则是自愿无偿,我国对于器官捐献中自愿无偿原则的确定来源于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为此制定的原则,其中第五条原则表述为:细胞、组织和器官应仅可自由捐献,不得伴有任何金钱支付或其他货币价值的报酬。购买或提出购买供移植的细胞、组织或器官,或者由活人或者死者近亲出售,都应予以禁止。禁止出售或购买细胞、组织和器官,不排除补偿捐献人产生的合理和可证实的费用,包括收入损失,或支付获取、处理、保存和提供用于移植的人体细胞、组织或器官的费用。这项原则可谓非常清晰地解释了什么是器官捐献中的“无偿”,明确规定为保证器官获取的无偿性,禁止为器官定价和金钱支付。虽然当前我国器官捐献属于无偿捐献,但以下几种例外情况也被视为无偿的范畴:一是象征性地对捐献者(家庭)的感谢;二是该原则允许补偿因捐献而发生的费用。据笔者了解J市主要通过仪式纪念和人道关怀的方式来回报捐献者(家庭)捐献“生命礼物”的行为。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无论是仪式纪念还是人道关怀的“回赠”方式都面临着如何与中国乡土文化融合的问题。以纪念仪式来说,毋庸置疑这一回赠方式为捐赠者家属提供了一个缅怀纪念的空间和机会,也可理解为是对捐献者的一种“礼物回赠”。但是我们是否真正理解这种纪念仪式背后的意义呢?亦或说这一纪念仪式我们又如何可以做到更好呢?纪念仪式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将其理解为是对捐献者进行的一种祭祀行为,在这个特殊的祭祀活动中有其独特的对象与空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祀所要表达的文化内涵莫过于“追思先人,勿忘生者”这八个字,而这简短的八个字却反映了中国人豁达的生死观。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庄子“齐生死”,《周易·系辞》“生生之谓易”,把生与死看得等量齐观,把生命看成是一种呈“抛物线”型的自然过程,对生存和死亡都抱有一种顺应自然的态度。“追思先人”强调对先人的缅怀,是因为他们是自己的来源;“勿忘生者”则强调对生活的依旧热爱,是因为生者是未来。这也是为何历史上有关于清明时节人潮汹涌的诗歌描述,“著处繁华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正是“勿忘生者”淋漓尽致的展现。落脚到器官捐献中的纪念仪式,以J市为例,每年参与纪念仪式的有捐献者亲人、朋友、接受者、志愿者、移植医生、当地医学生等,且当地为捐献者建有专门的公墓,每一次的纪念仪式通过当地这样一种公共活动的形式,将由器官捐献这一行为所关联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了一起,让死者得以获得缅怀和纪念,让生者懂得感激和回报。曾有器官接受者代表在纪念仪式上说道:“我可能会忘了我的生日,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了你给我第二次生命的那一天。”[2]120这句话可谓触动了器官捐献的真正内涵和生命意义,是对生命礼物的切身体会,也是中国传统生死观念的现实诠释。
从人道关怀的角度来说,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关怀什么,怎么关怀,谁来关怀。对于关怀什么及怎么关怀这个问题,核心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让器官捐献中的关怀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也即让捐献者及其亲属感受到这种关怀是对它们“大义”行为的一种回报,而非通过身体获“利”的行为。传统文化的“义利观”大致可包涵七个方面的内容:(1)“义以生利”,义利统一;(2)“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行义言义,“功贤耕织”;(4)“何必曰利”;(5)好义欲利,人之两有;(6)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7)“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8]。由此可见,“义利”的差异往往是十分微妙的,如何把握器官捐献中人道关怀的度在实践中显得尤为重要。
由此可见,在器官捐献中我们需面对“生命礼物流动”的问题,毋庸置疑器官这一特殊的“礼物”不同于人类学民族志中传统的礼物,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实践中去了解器官捐献究竟意味着一种怎样的流动机制,这种流动机制中又隐含着怎样的互惠原则,在明确了互惠原则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做到用符合中国人传统文化的形式来表达这种互惠。
4 器官捐献文化困境的历史渊源及其现实意义:从中国古代医患互动谈起
那我们是否曾去反思过器官捐献文化困扰背后最根本的历史渊源及其现实意义呢?
在中国古代,医学并未被隔离于类似现代化医院的特殊场域(场所)当中,医者与其他社会成员(如农民、工匠、买卖人等)一样都处在最朴实的社会交往活动当中,在这种社会互动当中医者极有可能就在家中开起了诊所,而他们的邻居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木匠,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与相互熟悉的互动过程中,无论是医者也好还是木匠也罢,他们形成的都是最具社会普遍性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而不会因其职业的差异而有较大的隔阂。因此,中国古代医者社会互动的特点可谓是整个传统社会互动特点的缩影,我们不妨从中去探索器官捐献背后医学技术与大众文化之间渐行渐远的历史渊源及其现实意义。
4.1 在差序格局关系中的社会互动
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9]认为,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的社会,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就像一捆一捆扎在一起的柴,柴与柴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中国社会结构和西方不同,我们的社会结构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是差序格局的社会,其社会关系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范围的大小根据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
中国古代医者与患者的社会互动就是建立在这种差序格局当中的一种社会互动。以医者与患者之间的互动为例,我们且从以下两个方面一窥医者在差序格局中的社会互动样态。
其一,病家的择医而治。在中国古代,除了宫廷御医(也即官医)有着明确的官位品级的评价体系外,在民间缺乏对医家统一的评价机制,因此民众在择医之时,既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传统信条,也有经熟人介绍基于情谊的信任而择医的情况,更有“病笃乱投医”的悲剧。然此种种背后,都反映出病家在最终作出选择之前会考虑纷繁复杂的社会因素,都有一种极强的自我参与度在里面。在如此基础上建立的医患关系包含了复杂的个人情感及社会因素,而非仅仅只是医疗技术上的单纯关系。而现代医疗当中,我们的医院等级制度、医生的职称评价等帮患者在做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往往会有一种心理,认为既然是三甲医院、既然是教授,是不是就应该治愈我的疾病呢,因为患者在当代医疗中,在择医这件事上越来越缺乏参与感,那么当然对基于级别和职称帮助之下做出的选择会寄予唯一厚望,然而医生却非常清楚,再先进的医学针对不同情况的患者其都是有风险存在的。以器官捐献为例,医学享有绝对的权威,家属往往在一面刚刚遭遇亲属的死亡,另一面马上就要做出一个医学上的重大决定,在这个过程中有时连其他医学专业的医生都有所犹豫,更何况是普通民众,可以说在器官捐献中移植医学享有了绝对权威。有学者曾记载J医院器官获取组织L医生谈到其他医生对器官捐献的看法。
ICU科室的医生对捐献非常重要。因为(病人及家属)对捐献的认识,很大一部分来自ICU的医生,如果医生根本不接受这事,不积极或者不当一回事,那就对捐献的影响很大了。我分析,大概的困难在于三点。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科室主要负责其他的病种,与移植关联性不大,让他们参与没有动力;二是,因为医生的主要职责是尽最大努力挽救患者的生命,假如医生提出器官捐献,会让家属以为他不积极治疗;三是,我国的器官捐献还刚刚起步,还存在一些争议,现在医患关系这么紧张,无论是医生,还是医院领导,都不想掺合进来[2]103。
另外笔者了解到J市协调员P先生在其协调笔记中写到这样一段内容。
协调员、志愿者、医生在与家属沟通过程中要十分注意方式方法,毕竟涉及生死,稍有不慎不但不利于捐献工作的开展还有可能会导致医患矛盾的产生。
由此可见,当前我们的器官捐献工作一方面应该首先获得相关其他医学的理解,另一方面应该思考如何在中国人的差序格局中让我们的医学与民众重拾相互的信任和理解,让民众真正参与到医学的决定当中。
其二,医家的察情而医。中国古代著名医家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不失人情论》中载:“所谓病人之情者,五脏各有所偏,七情各有所胜。阳脏者宜凉,阴脏者宜热,耐毒者缓剂无功,不耐毒者峻剂有害。此脏气之不同也。动静各有欣厌,饮食各有爱憎。性好吉者,危言见非;意多忧者,慰安云伪。”[10]李中梓用其切身经验告诫医家,医家应能在诊疗当中对病人心理进行揣摩分析,以便采取相应的行为疗法以取信于病家(而不仅仅是病人本身),一方面求得更好的疗效,另一方面避免纠纷。在现代医疗环境中,越来越现代化的就诊环境、纷繁复杂的就医程序、医疗合同中的法律专业术语、手术室门栏上亮起的“手术中”的警示等,都在有意无意中削弱了医患之间的社会互动。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冲破现代化的种种、如何冲破医学的专业化让患者,让患者家属等体会到医生的一颗仁爱之心。以器官捐献为例,当捐献者被推进手术室后,家属往往只能在冰冷的走廊上等待,对于他们而言死亡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情,却是在他们全然“无知”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捐献工作,除了关注医学的救命天职,也不该忽视对捐献者及其家属的人文关怀。器官捐献有其特殊性,虽然移植医生面对的是已经逝去的生命,但其不应忘记对捐献者家属的察情。
4.2 以多元信息交流为基础的社会互动
中国古代的医者主要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医,众所周知中医诊疗讲究望、闻、问、切,其中的问诊蕴含了医患之间丰富的社会互动。中医问诊的信息不仅包含着病人的基本病情,还囊括了病人的生活喜好、社会关系、心理状况等众多内容。《难经·六十一难》载:“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11]。《丹溪心法》载:“凡治病,必先问平日饮食起居何如。”[11]《医学准绳六要》载:“凡诊病,必先问所看何人……次问得病之日,受病之原,及饮食胃气如何,曾服何药,夜寐何如,膈间有无胀闷痛处……诊病必问所欲何味,所嗜何物,或纵酒,或斋素,喜酸则知肝虚,喜甘则知脾弱。”[11]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当代的医生就不问了呢,问的内容就单一了呢?其实不然,或许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医生如何摆脱医学术语的束缚,用普通患者能够理解的方式来“问”,来沟通,来互动。在这一点上,或许古代温情脉脉、穿着大褂长衫的医者更能给我们以古老的智慧启迪。而在当代,以器官移植中的捐献为例,如果器官捐献中的协调员在与死者家属沟通过程中一味只谈献赠问题,其他问题毫不涉及的时候会让死者家属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正如上文中提到的,许多ICU医生不愿意涉及到器官捐献工作,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担心患者还在治疗过程中,跟患者谈捐献问题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猜忌。据笔者了解到在J市医院有通过设立器官捐献宣传栏的方式使家属主动来咨询捐献相关事宜的情况。由此可见,如何避免刻意只谈捐献问题,如何在一种多元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家属意愿,让家属享有绝对的尊重和自主权十分重要。
4.3 以“较单一”媒介交往为基础的社会互动
中国古代医者与患者间的沟通媒介受历史的局限性往往表现出比较单一的情形,通常以面对面的交往为主。这样的社会互动方式,医患之间互动的时空范围相对有限,互动的对象也是相对固定和熟悉的,其优势是医患之间往往十分相熟,处于共同的或交互的社会关系格局当中,从而为医患间便利的沟通互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在当今社会,现代医疗面临着跨时空信息传播的无限可能,大大拓展了医患互动的时空范围和方式,但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都离不开医患之间的相互理解,只有相互理解了才能有效互动。在古代单一的媒介交往为我们创造了较易相互理解的大环境,因为我们彼此熟悉。而未来世界,或许会因为科学技术而使医患相距千里毫不了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无论是医生亦或患者即便相隔千里毫不知情,但是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我们有着共同的人伦价值理念,我们有着共同的生死疾病观念,这就是我们互动的基础,不会因媒介而改变的人文基础。以器官捐献为例,捐献者及其家属要面对器官获取医院、移植医院、红十字会等数家机构,与此同时还要面对OPO负责人、移植医生、志愿者、协调员等不同的人员,而这些人员不同的身份、不同的隶属都有可能给家属带来紧张感,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们面对的是谁,以及不同的机构在捐献这件事情上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起着怎样的作用。由此可见,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在器官捐献工作中应如何做好分工,而当前我们最欠缺的则是在移植技术与普通民众医学文化观念之间架起沟通桥梁的这一角色扮演者,在器官移植的紧张过程中我们当然无法苛求移植医生如传统中医问诊那般,所以在当前实践中有了协调员、志愿者等新的角色参与,但接下来的工作应是结合地域特色明确协调员、志愿者及相关人员的角色和功能,以不至于在捐献过程中因身份角色的混乱而给捐献者及其家属造成误导与紧张感。
4.4 以中国传统礼法规范为共同基础的社会互动模式
社会学家李安宅[12]在《〈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中写道:“中国的‘礼’字,好像包括‘民风’(folkways)、‘民仪’(mores)、‘制度’(institution)、‘仪式’和‘政令’等等……既包括日常所需要的物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超自然等关系的节文),又包括制度与态度。”在古代社会中,社会分工程度还不高,医者所遵循的诊疗规范以及医疗习俗往往也是符合人们日常所遵循的一套仪礼法律规范的。
以诊金的支付为例,《红楼梦》中提到的一个关于医疗的细节或许可以作为考察古代医患互动的一个参照。贾宝玉的丫鬟晴雯病了,请来一位大夫胡君荣诊治,尽管贾宝玉对他开的药方并不认可,但既然请来了,诊金还是要付的。给多少呢?按照当时的行情,老嬷嬷建议:“少了不好,看来得一两银子,才是我们这样门户的礼。”宝玉道:“王大夫来了,给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大夫和张大夫每常来了,也并没个给钱的,不过每年四节一个趸儿送礼,那是一定的年例。”[13]又如康熙辛卯(1711年),李光地门人陈汝楫忽患重疾,群医束手,最后被青浦何氏始祖何王模之父、何氏奉贤支名医何炫治愈。陈汝楫感激之余,认为“赠人以金,不若赠人以言”,遂请其师李光地撰文表示感谢。李光地以前在维扬的时候,也曾找何炫看过病,因此爽快地答应,撰《赠自宗何子序》,回顾了自己和弟子请何炫诊病的经历,并以“良医良相”之说来赞誉何炫的高明医术和高尚医德[14]。
由此可见无论是诊金的支付也好,还是病家对医家表达感激的礼物馈赠,这一互动关系互动规则都遵循了中国人最传统的人情文化,风俗习惯。阎云翔[6]7在《礼物的流动》中写道:“礼物馈赠是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社会交换方式之一……研究礼物交换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和诠释既定社会中不同文化规则及社会关系结构的途径。”以诊金的支付以及礼物的馈赠来看,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仅仅只包含一种类似契约关系的互动,而更深层次的是包含了中国人的金钱观、人情观、交往礼节等等复杂的情感。这也就是为何在处理器官捐赠当中,如未能合理处理好人道关怀的问题会让病患或病患家属有一种“买卖”了器官的情感体验,而并非是基于人情、人道主义关爱的情怀。怎样去拿捏器官移植中涉及的“无偿”、“补偿”、“买卖”这三者之间微妙而敏感的差异,或许医学本身并不能给出答案,而需要对中国本体之中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了解才能拿捏到位,做到合法、合情、合礼。
总之,中国古代医患之间也可以说是医学与文化之间,为何不存在较大的隔阂,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医患的文化价值观念是相似的,他们处在相同社会文化、社会观念以及社会规范当中,因此医学与文化并不存在较大的矛盾之处。而自近代医学技术迅猛发展以来,医学的标准与文化的标准越走越远,于是医学与文化的矛盾开始日益凸显。当前我们急需要做的是如何通过医患之间的互动来减少医学与文化上的鸿沟,如何寻求当代医学与普通民众互动中共同的文化理念。落脚到器官捐献问题则是如何寻求移植技术与本体民众医疗观念、生命观的沟通与互融。正如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克劳福德(P.Craw-ford)所提出的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更加开放和更面向应用的学科,以包括那些被医学人文边缘化的贡献”[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