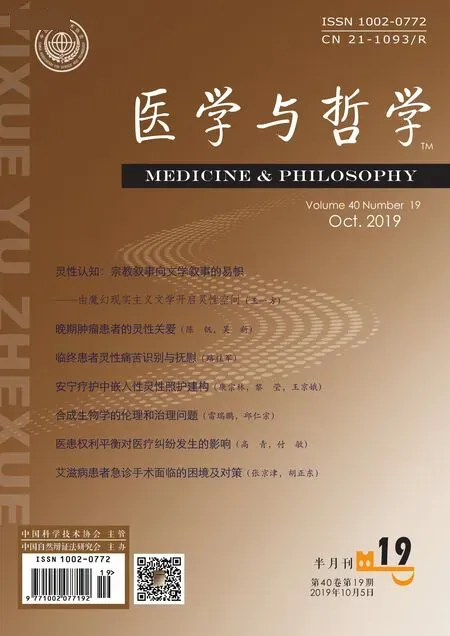对医学高新科技伦理争议的思考*
2019-02-25曹宪姣贺青卿
曹宪姣 朱 见 贺青卿
医学的发展同所有其他科学的发展一样充满矛盾冲突,医学改革和医学高新科技要求医学界不仅仅只是简单地支持高新科技发展,更要重视发扬人类价值[1]。医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对医学伦理道德提出更高标准,伦理的高标准会指引医学向着有利于医患双方的方向发展。医学科学发展倘若没有伦理学的约束,一些医学技术可能会适得其反,出现诸多道德风险,因此对医学高新科技的伦理进行深入思考具有重要意义。
1 医学高新科技的伦理争议
1.1 大数据处理——隐私与归置问题
医学的每一个领域都离不开数据的处理,医学信息化、数字化要求医生熟悉分析数据的方法、掌握分析数据的医学工具。目前,数据分析算法广泛应用于医学图像等检查分析上,另外还有无线电波和自动病理分析领域[2]。例如,最近Zhu等[3]提出了一个新的图像重建模式——流形逼近自动变换(automated transform by manifold approximation,AUTOMAP),该数据重建算法可减少传感器噪声和伪影对图像的不良影响,这为未来CT扫描技术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准确、高效地分析患者信息是对医生的挑战,但临床医学信息数据的处理不同于常规数据处理,最主要涉及患者数据隐私和数据归置问题。处理医学数据时应当考虑是否该赋予固定医务人员获取信息的权利,患者是否有权利掌握自身的全部生物信息,以及如何处理个体生物信息与总体信息之间的关系[4];与潜在的受试者接触和搜集信息的时候,其他人是否需要在场;如何搜集患者身份的信息,受试者在获得信息的过程中是否感到舒适;确定的个人信息以何种方式储存,储存多长时间以及跟谁分享。虽然医疗大数据能帮助医院改善医疗保健行为,但是会面临如何阻止公司和政府使用这些医疗数据的困难。医疗健康系统中构建的数据处理方法可能反映不一样的、有冲突的利益,过早地将特定诊断或实践方法纳入该处理方法可能意味着数据的不真实性,从而最终影响患者的利益[2]。
1.2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过度诊疗与负面效应
AI被称作是第四次技术革命,其辅助医学诊断和治疗已经有相应法律法规可循。机器学习是系统智能化的重要标志,AI的学习能力强大,医疗影像辅助诊断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Gulshan等[5]报道了一种用于检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深度学习算法(deep learning),结果显示基于深度学习系统(deep learning system,DLS)对检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具有高灵敏度和特异性。Ribli等[6]提出了一种改进的计算机辅助检测(computer aided detection,CAD)系统,它比传统CAD法协助放射科医生诊断出更多乳腺癌 。
AI的成本高昂导致高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如此间接拉大社会贫富差距,可能使一部分人对医学AI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AI所存储的信息往往来自于大规模医疗临床试验数据,不顾及人体间的异质差别将该数据应用于不同的个体,容易倡导非必要的医学测试和手术,出现扩大病情、过度诊治的情况,即便AI按照规范化诊治标准也可能常常难以达到良好治疗效果。AI带来的过度医疗问题忽略了人文关怀在疾病恢复时的作用,也可能会忽略替代医学如生物反馈、针灸、中药以及意象等诸多替代疗法的作用。AI大数据处理和影像识别能力远超人类,医务人员因此可能会因对其产生过度依赖而降低自身医学专业水平;当医疗行为出现错误决策时,责任的归属问题可能会受到利益的影响;另外,异常的AI诊疗结果会对接受诊治的患者及其家人造成额外情绪困扰,对疾病的诊治和恢复会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1.3 精准医学和靶向治疗——缺少临床证据与经验
精准医学是以基因测序技术、蛋白质分析技术、靶向药物研发和其他高精尖医学技术为背景的个体化诊疗方法,而靶向治疗针对体内的致癌位点如某个蛋白分子或者基因片段利用药物或者其他方法使肿瘤细胞特异性死亡,可称为“精准肿瘤学”[7]。精准医学以每个病人的分子研究和临床数据为基础,为对某一特定疾病具有易感性或对某一治疗具有不同反应的亚群而非群体制定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案。
目前精准医学研究的临床干预措施相对较少,且很少用于新的诊断测试,并缺乏可为基因组学等技术提供相对可信的数据,因此,精准医学首要的伦理挑战是拥有确定足够可信的证据和如何将临床证据纳入临床的问题。精准医学中个人参与程度很大,基于人群数据搜集和研究面临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该如何权衡[8],即便被大多数人证明有益的治疗方案或药品效果一般,患者可能不会轻易尝试这种具有更大个人风险的个体化诊疗。精准医学和靶向治疗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健康差异,个体化治疗方案是否优先提供给经济条件优越或拥有高端保险的人士?有些疾病的基因种族或家族倾向是否会增加对种族或家族的歧视?个体化医学是否会因为改变了医疗护理系统的标准而成为医疗过失诉讼的把柄?对于靶向治疗,无法解释的耐药性、肿瘤的基因组异质性、监测反应和肿瘤复发的手段不足,以及对药物组合的使用知识有限均需要考虑[7]。
1.4 手术机器人——手术技术更迭的短板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系统是目前最先进的微创外科技术平台,它具有放大的三维高清视频系统和手术视野,其具有仿真手腕关节(Endo-Wrist)功能的四个机械手臂均可进行7个自由度的灵活操作,并能够有效滤除外科医生手术颤动。手术时医生利用操纵杆来操纵机器人,实现复杂手术的精准微创、脏器保护及美容效果[9-10]。
机器人系统使用和维护成本高昂,患者需要支付更高的医疗费用[11],这对收入较低患者有失社会公平公正。机器人在精准性和持久性方面均优于人工,这对外科医生的手术技术提出更高要求;医生在机器人手术操作初期如果技术不够娴熟,或者操作过程中出现疲惫状态,则手术时间和手术效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若术中出现严重手术并发症,由于手术切口范围和可操作范围小,且距离手术部位远,可能难以及时有效处理术中紧急情况;另外,机器人操作臂的人机交互安全性如事前预防主动控制等方面有待提高[12]。当与床边的外科医生比较时不难发现,及时照看患者的伦理问题至关重要,除了术中助手和护士,机器人手术操作者难以第一时间照顾患者并查看患者生命体征。手术机器人在术中出现故障或者线路问题,需要有应急方案,否则可能会危及患者生命安全。机器人系统确切的并发症和死亡率一直难以准确量化,这对预后评估造成一定困难,故需要一个可靠的跟踪系统或者开放的报告系统来报告这些不良事件[13]。鉴于目前手术机器人属于辅助医疗系统,手术的主体依然是医生,未来随着机器人的自主性和参与度的提升,责任主体所承担的责任比重会发生变化。一旦机器人手术大量用于临床手术,医生的专业技能可能会逐渐被机器所代替,出现技能低效化,这对于医生的临床技能培养又提出了新的挑战。
1.5 基因测序和治疗——专业性与隐私保护
2000年6月26日,白宫发布了关于人类基因组测序的第一份草案,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完成是医学领域巨大的飞跃,基因测序根据血液或唾液测定基因全序列,能够提前锁定个人病变基因、预测患病风险的大小,正在广泛应用于临床疾病尤其是肿瘤的预防、诊断、治疗和监测[14]。
基因测序和治疗是一种信息技术,测试结果对于预测患病风险与临床诊断的价值的高低,需要制定统一标准。基因测序应该在确定知情同意并尽到告知义务的伦理原则下进行,这对获取参与者的配合和信任是至关重要的[15]。人体患病与环境、心理因素关系密切,基因测试只是单纯分析患病几率,但忽略了环境、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作用,会出现基因阳性率与患病率不对等的矛盾。遗传信息特别容易遭到泄露隐私的风险,基因检测不仅涉及到个人,亦涉及到该人的血亲,这些基因数据是否会被泄露给制药公司,基因公司破产后如何处理这些基因信息,警方是否可以通过家谱服务共享的基因数据库来识别嫌犯的亲属等[16-17]。基因治疗可适用于某些基因缺陷且没有其他更佳疗法的遗传病,但其治疗同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对人体带来潜在的损害。基因数据的披露需要进行遗传咨询、症状前筛查、基因诊断,在咨询和解释数据方面,临床医生的培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些遗传结果专业性普遍较高[18]。改变基因功能、替换细胞及再生医学均具有伦理挑战性,利用基因纠正有害突变是否会改变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感,例如,中枢神经系统细胞中的基因一旦被修饰,可能影响患者心理状态或情感的功能[19]。
1.6 干细胞研究——道德与尊严
干细胞分为全能干细胞和多能干细胞,后者主要来源为胚胎干细胞和胚胎生殖细胞,患者干细胞培养出所需组织能够克服移植排斥,具有重大临床意义,另外在癌症、基因治疗和新药开发等方面潜力巨大。干细胞研究在胚胎干细胞的多能性使其被誉为“万能细胞”,干细胞研究伦理主要在于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上。
1994年,美国发布有关人类胚胎研究禁令,禁止几经反复,最终支持已有干细胞的研究。获取胚胎干细胞需破坏人类胚胎,这几近于剥夺一个未来生命,有人认为胚胎克隆是生殖性克隆人的第一步,子宫外植入前的人类胚胎应该获得与完全发育胚胎相同的道德地位。胚胎是用来自多个个体的遗传物质产生的,那么谁应该提供研究同意书[20]?自然或自愿选择流产的胎儿细胞亦是胚胎干细胞来源,大量研究是否会招致堕胎的泛滥或者胎儿买卖商业化?胚胎干细胞与堕胎争论一样涉及宗教、道德和人类尊严问题。也许可以使用普通细胞进行基因编辑重排,令其具有干细胞功能属性,如此避免破坏原始胚胎[21]。甚至,有些疾病使用非胚胎干细胞系显示出更大的治疗优势,这为干细胞治疗提供更多可能性[22]。
1.7 深部脑刺激——难控的副作用
深部脑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是通过长期将单侧或双侧电极植入大脑特定的皮质下结构来实现电刺激,是一种可调节的、可逆的、非破坏性的神经外科干预。目前DBS已用于不同的治疗或替代药物应用,如神经病学障碍、帕金森综合征、肌张力障碍、重度强迫症、严重抑郁症、抽动秽语综合征,可缓解慢性疼痛和持续性震颤等。
DBS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电极插入大脑后会出现伤口感染、构音障碍、感觉异常、电极错位和迁移,且会有异常癫痫发作、脑出血、偏瘫、脑梗死等风险[23]。DBS需要对单个患者刺激参数进行微调并改变施加的电场,但目前尚缺乏对“有效剂量”的严格定义,临床医生很难短期内完全探索出DBS的最佳参数和刺激量[24]。目前还没有前瞻性数据,也没有有效的预测个体治疗反应的指标,临床研究分析并未讨论出DBS和神经调节药物治疗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面对致病区域扩大或病变活动的迅速蔓延,DBS方法的疗效可能有限[25]。过度报告DBS积极结果可能会掩盖它的劣势,严重抑郁症、强迫症或成瘾症的迅速缓解将以比个人环境改变更为剧烈的方式改变以往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例如,有报道显示严重神经疾病患者在DBS治疗后出现了明显的性格障碍,故DBS研究设计和后续评估需要更全面的结果报告,并应将更广泛的生物、心理、社会结果指标纳入评估标准。另外,DBS技术在知识产权领域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判断,技术的不成熟和过度、模糊或明显索赔的风险会导致专利申请的泛滥和不规范[26]。
1.8 无线传感器——芯片植入有风险
临床医生根据片面化的生命体征和实验室诊断推测它们之间的联系并判断疾病,难免出现信息不完整、不连续的情况,传感器可跟踪代谢状态并提供连续的医学数据。可穿戴生物化学传感器可收集生化或电生理信号,这种新兴医学电子产品使实时发现、诊断疾病成为可能[27];有科学家在研究设计提高医学精确度范围在几毫米到几微米的医学微型体内装置,能够安全地侵入人体以实时监测或诊断疾病,甚至直接向肿瘤提供靶向治疗[28]。
无线传感器可能会面临复杂的批准使用程序,因为植入体内的装置需要考虑感染或者设备故障诱发潜在并发症,另外存在永久植入装置是否有实用性、患者对它的费用接受程度以及获取芯片信息的合法化等问题。这种装置忽略了人体对自身调节的作用,加大了对生命监测的依赖性。使用智能芯片的患者还会面临被黑客攻击的风险,如人工耳蜗器、心脏起搏器、胰岛素泵等。将来如果这些智能芯片被有经济条件的人植入大脑中,就可能会造成他们的大脑在某些方面超越常人,有碍社会公正和稳定。
1.9 肿瘤免疫治疗——临床试验谨慎乐观
癌细胞的免疫逃逸是癌症治疗中的关键,免疫疗法从最初的免疫增强剂和肿瘤疫苗,到嵌合抗原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AR-T)治疗、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immune checkpoint therapy)[如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 antigen 4,CTLA-4),为肿瘤的治疗提供多元化治疗方案。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布给开创“抑制免疫负调控从而激发免疫系统对抗肿瘤”疗法的两位免疫学家,以表彰他们在CTLA-4和PD-1蛋白研究的贡献。目前免疫疗法已经应用于黑色素瘤、肺癌、膀胱癌、肝癌等。
免疫治疗的个体差异较大,这增加了严重并发症的潜在风险,免疫疗法过度激活免疫系统会导致自身免疫反应,虽然部分可控但严重者出现生命危险,如PD-1免疫疗法对正常细胞有较大毒性作用,且缺乏长期临床观察和验证;CAR-T免疫疗法运用了基因转导技术,会有“细胞因子风暴”、神经毒性、感染等副作用,该技术路线涉及取细胞、嵌合、体外增殖、回输等步骤,长周期和高成本无疑增加患者负担。免疫药物上市后的临床研究数据大多需要补充且真实性有待考量,严格的安全协议和产品定价有待建立[29]。免疫检测方法的不统一如检测手段、抗体灵敏度等不同,可影响最后数据的可信度,国内医疗环境容易过度夸大疗效而出现免疫治疗乱象。2016年7月7日,美国一项免疫疗法临床试验被叫停,因为试验方案中期被修改,导致三名患者意外死于脑水肿[30]。临床研究的应用和临床研究的监管尚无国际标准化原则,应当在保障人身安全的同时促进药品的创新研发。另外,免疫治疗研究单位是否达到招募受试者的能力,对入选患者的标准制定是否合理[31]?免疫治疗设备是否达到免疫治疗技术要求?研究者的道德水平决定他们是否会一味追求研究结果而忽视患者利益?在临床试验中,受试者是否能区分临床治疗还是医学研究,是否能充分了解科学研究的性质并正确看待可能面临的风险?由于缺乏相应免疫细胞治疗标准和技术标准,完善临床免疫试验和治疗标准、免疫细胞的制备和质量控制、有效性评价等机制迫在眉睫[32],伦理审查委员会对免疫临床研究的审查应包括研究者资质审查、研究方案的科学性审查、受试者的权益保护等[33]。
2 结语
医学高新科技的探索发展是一种双向伦理问题,医学科技的安全保密性、医院部署应用新技术原则、影响医生判断的利益冲突、应用新技术的培训和认证等需要考虑;对于患者,面临接受医学新技术之前的告知、新技术应用结果的跟踪报告、治疗伤害与受益的风险、医患之间有效沟通、患者个人和社会责任平衡等问题[34]。新技术的成本、结果、有效性和安全性在使用前后均要经过伦理委员会的评估,并在监督、授权和限制过程中使医疗高新科技发展与医学伦理并重,将科学性与伦理性并行。
国内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在学术界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对胚胎基因进行修饰以天然抵抗疾病严重违反医学伦理道德和科研法律法规,被编辑基因的胚胎在成长过程中面临成长变异、疾病治疗不公正等伦理风险,甚至其生命安全也会难以得到保障。医学伦理问题从来都是医学研究活动中的重要问题,抛开伦理的科学研究是没有实际社会意义的,违反医学伦理的医学科技也不会得到社会的公认。科学化管理是避免产生医学伦理问题的有效措施,要在建立健全成果共享机制的同时服从医学研究科学化管理,并严格遵守伦理准则,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