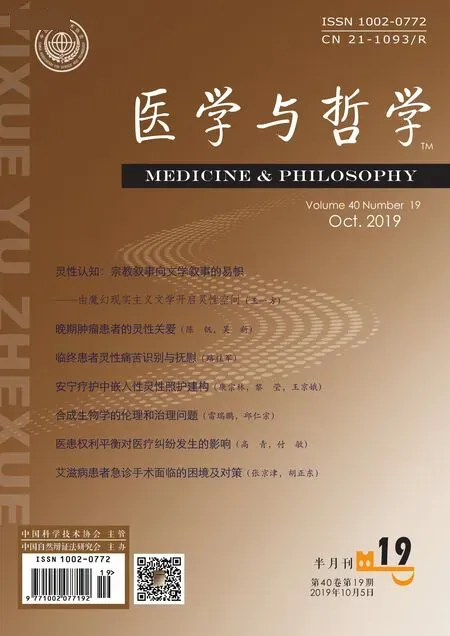论哲学之气与中医之气的分殊*
2019-02-25严家凤林家虎
严家凤 林家虎
如果说中国哲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那么中医则堪称是生命哲学的代表。而“赋予整个中国文化以生命的一个要素”[1]是“气”。从整体意义上看,中国哲学之气至少含有物理、生理、心理、伦理、哲理等几个层次的含义,可谓“一气涵五理”。就这五重含义的逻辑关系来看,“哲理意义的气,就是指作为世界万物之本原或元素的气,它可以化生万物, 其本身与物理意义的气相通, 而生理、心理、伦理乃至审美等意义的气都由此衍生而来。”[2]形成于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医学正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之气的理论基础上,从关注生命健康与疾病复杂关系的角度开启了对生命的关照。正是由于哲学之气与中医之气都与生命相关,人们往往将中医之气混同于哲学之气,如果不能厘清二者的区别与联系,既不利于人们认识中医,也不利于中医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1 以气论自然
困扰人类至今的三大问题皆是对生命的追问,对生命本质的追问必然引发关于生命本原的思考。我们的祖先在实践中观察体验,发现了与生命须臾不可离的气。气最初是指自然之存在物(物理之气),源于先民在日常生活中对云气、水气、雾气等自然现象的观察与体验,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归纳和总结,才逐渐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之气,用以解释宇宙的和生命的起源。从自然之气到哲学之气的转化是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复杂过程。作为哲学意义的气,首先被赋予宇宙本原的意义。《淮南子·天文训》有:“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对宇宙创生所进行的生动描述:道最初的状态是虚无,虚无演化出宇宙,宇宙产生出元气,有气而后才有天地。东汉哲学家王充认为天地万物皆由元气化生,《论衡·谈天》有:“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北宋哲学家张载直接将气理解为宇宙的本体,《正蒙·太和》有:“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主张元气化生万物:“太虚之为体,气也。”(《正蒙注·乾称》)至此,中国哲学对于气的认识达到了最高峰,后人无出其右。作为哲学意义的气也被称为元气,它既被视为宇宙本体,也被赋予了生命本原的意义,《鹖冠子·泰录》曰:“天地成于元气,万物成于天地。”《庄子》用“通天下一气”说明气对生命的重要作用,“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王充用阴阳之气阐述生命的形成以及生命之生长壮老已的盛衰过程,《论衡·论死》曰:“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至此可以看出,元气不仅是宇宙的唯一本体,也是万物生成变化的总根源。
中医吸收了古代元气论思想,将气看成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基础。《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 四时之法成。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难经·八难》曰:“气者, 人之根本也。”可见,人与天地自然中的任何其他物质一样,其生命都由气构成,人是天地之气合乎规律的产物。与元气概念联系最为紧密的是“精气”。《管子》把精气看成是“气”中最为精细者,“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凡人之生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即是说精气是人体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人的形体和生命是由精气构成的。中国哲学关于精气的概念被中医学吸收并用以阐释构成生命以及维持生理机能的先天之精气与后天之精气。精气是构成人体生命的生理基础,生命是禀受父母精卵结合而形成,人体诸脏腑各种机能皆由气推动和调控,可见,中医学在生命本原的认识上和中国古代哲学保持着高度一致。
但需要说明的是,哲学之气首先是宇宙观意义上的,气为宇宙间万物的本体而不仅仅是生命的本原。《荀子·王制》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由水、火、草木、禽兽皆是由气构成,进而归纳出宇宙间的万物皆是由气构成。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气是生命的条件, 但无生之物皆是气所构成的。”[3]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医学和哲学对于气的认识目的是不同的,“古代哲学研究气,目的在于探讨天地万物的生成和发展变化;中医学研究气,目的在于探讨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机理。”[4]二者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中医之气是哲学之气在医学领域的具体应用,二者不可一概而论。
2 以气论身心
中国哲学认为,气是生命的本原。那么,气有什么特质呢?《周易·系辞下》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万物包括生命都是从氤氲之气中“化生”而来,究其形成的内在机制而言,其核心是“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因而,气有有形与无形两种形态。相应地,万物在气的聚散中形成和消亡,生命的生长壮老已皆是气的运动变化的缘故。换言之,气具有运动不息、变化不止、连续不断的特性。
气不仅是生命形成和保存的生理基础,还是心理活动的基础。《论语·季氏》曰:“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矣,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段话从侧面诠释了生理之气的运动变化会引起人体生理机能与心理特征的变化,但就以气论身心而言,中医在这方面论述更多也更为全面。
中医有关气的理论最早最完整地呈现于《黄帝内经》之中,在《黄帝内经》中涉及气的表述很多,阴气、阳气、真气、天气、地气、风气、寒气、热气、燥气、暑气、湿气、火气、营气、卫气、宗气等等。医学之气有先天与后天之分,先天之气秉承父母的精卵结合而产生,医学上或称为“精气”、“元气”,先天之精气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诠释了生命的形成,“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灵枢·决气》)。先天之气形成后,受饮食水谷等精微物质的滋养,形成后天之精气,具有维持人体生命活动并抵御外邪入侵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有构成人体脏腑经络体系的这些物质所表现出来的生理功能,主要是指积于胸中、出于喉咙、贯注心脉而行呼吸的宗气,生于水谷、行于脉中的营气,生于水谷、行于脉外的卫气等。关于生理与心理之间的关系,中医表达了形体乃精神之基础的认识:“五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也”(《灵枢·卫气》),“气者,精神之根蒂也”(《脾胃论》)。中医学中除了涉及先天之气、后天之气以及脏腑经络之气以外,还有很多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气。仅就中医的五气而言,含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或指寒、暑、燥、湿、风的自然之气;或指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或指五脏化生的喜、怒、忧、悲、恐的情志之气;或指反映内脏变化的青气、白气、赤气、黑气、黄气的五色之气;或指臊气、焦气、香气、腥气、腐气之气味;或指酸、苦、甘、辛、咸五味所化之气;或指脏腑功能的五脏之气等等,这都是将人体生命之气具体化,并据此阐明机体疾病与健康的复杂关系以及生命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中国古代气功正是注意到身心贯通与气的紧密连接,进而通过调心、调息和调形来达到舒解疲劳、提高神智乃至延年益寿的目的。这些都清楚地说明身体与心理上的健康或疾病与气的正邪、逆顺、强弱息息相关。
哲学之气对医学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但哲学之气向医学之气的嬗变是一个从抽象的哲学范畴演化为具体的医学理论的过程,“当医学以气学理论观察生命、健康与疾病,发现人体内存在着实实在在、望之可见、触之可及的气。因此,医学从观察到思考,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气学理论。”[5]这意味着,哲学之气对医学的影响逐渐弱化,医学开始构筑自己的气学理论体系,用以解释人的生命本质、疾病的发生、临床的诊疗以及思维方式等,若至此仍以哲学之气捆绑束缚医学之气,则会阻碍医学的发展。
3 以气论情
不仅人的形体即生理活动离不开气,人的心理活动乃至情志活动也是以气为基础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所以要审慎地效法,适当地模仿,以制约“六志”。孔颖达在《正义》中说:“此六志,《周礼》谓之六情。”也即是说,喜怒哀乐等情感活动由气而“生”,对其进行调节而“不失”,才能合于天地。中国人用生气、喜气、怒气、唉声叹气等形容气与情志活动的关系,传神地表达了气对人的情感情绪的影响。
马王堆出土的竹简《性自命出》中也有关于气与情的关系的论述:“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这说明人的喜怒哀乐等情志活动本身即是气的具体外现,人的好恶喜怒哀乐之气“未发”为性,“及其见于外”则会受到外物的影响而转化为具体的喜怒哀乐之情。对于“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汤一介先生释义:“人道(做人的道理)是由于人们相互之间存在着情感才开始有的;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是由人性中发生出来的;人性是由天所给予人的(人性得之于天之所命), 天命是天所表现的必然性和目的性。”[6]这说明天、命、性、情之间的贯通性,但需要说明的是,情不等于欲,欲是指人过度的或基于生物本能的生理需求或欲望;情生于性,是性的外在表达,故而适宜的情志活动是身心健康的必要条件。
中国哲学尤其重视中庸思想。《论语·雍也》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儒家的中庸之道既是至上的品德,也是养生之道的精髓所在,《素问》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人的精神情志活动是内脏生理功能的产物,而内在生理功能则又有赖于气的推动。《内经》就人的情志活动偏胜对脏腑功能的影响做了详细阐释:“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中医七情变化反映了机体的精神状态,七种情志的偏胜会影响到脏腑气机,导致气血逆乱,甚至直接伤及内脏。中医将七情与阴阳五行五脏分别配属,并提出所划分的七情之间具有生克制化关系,为临床治疗因情志异常导致的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成为中医情志养生的重要理念。
中医自古即有以情胜情的疗法,利用五行生克制化的关系,以一种情志去克制另一种情志,从而有效地治疗由此产生的疾病。金代医家张从正深谙情志既可致病又可治病的道理,并运用于临床治疗:“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辱侮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忘此之言夺之。”(《儒门事亲·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而中国哲学也以气论情,却是从中庸适度的角度突出的人的情志表达要合度适宜,《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是君子、圣贤最看重的道德品质,应避免“过犹不及”,倡导执中致和。概言之,中国哲学将情志表达的适度视为君子品德,是德性修养的需要,而中医学要求情志表达的适度是为了防止情志致病,并用以临床治病。
4 以气论德
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核心,传统儒家哲学也叫道学、仁学、心学、理学,其中包含了深刻的伦理意蕴。气的哲学产生于先秦,是在自然之气的基础上归纳概括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先秦哲学论气主要是从宇宙本体和生命本原的角度加以论说,起初气与道德的联系并不紧密。但在儒家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气逐渐被赋予丰富的伦理内涵。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始于孔子的仁学,经由孟子逐渐构建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性善论。性善论强调善是人天生固有的本性,通过四端之心这一内在生命活动表现出来,“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赋予气以伦理的意义主要是通过浩然之气实现的。在儒家看来,浩然之气代表了君子的高尚品格,是中国人追求正直生活和人性圆满的体现。孟子正是以气作为道德修养的路径:“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作为充塞天地之间的气代表了一种道德无比高尚、俯仰无愧于心、至诚至坚的精神状态,“养气”的途径则是“配义与道”,透过心理道德活动而蓄发的勇气和力量,在日积月累中实现道德的日臻完善。孟子认为志为气的主帅:“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这就是说,志与气是可以相互作用的,唯有心志专一, 惟道义是从,才能涵养出浩然正气。由此可见,气在孟子已经被赋予了伦理的含义,气与人的品德修养由此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荀子和汉唐诸儒多“以气言性”,宋以后逐渐发展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两种含义。依据宋儒观点,天地之性无善恶,是天理在个体存在者身上的体现,而气质之性是形气结合(“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气禀清浊之性,是因人而异的实然之性。朱熹曾交代:“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朱子语类》卷四)也即是说,天地之性无善恶,而气质之性是有善恶之分的。
中国哲学“以气论性”赋予气以伦理的含义,但对中医的影响却很小。首先,中医谈医乃仁术,是从道德本性(天地之性)上说的,并未从气上说。先秦儒家认为,气是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本原,但随着性善论的建立,道德本体论思想逐渐成熟,自然万物包括生命都被赋予了道德的含义,而先秦形成的气本论却逐渐衰微,然而幸运的是,该理论被中医学吸收熔铸形成了逻辑严密的气-阴阳-五行理论体系,千年以来一直发挥指导医疗实践的作用。其次,中国哲学认为,气质之性是恶的来源。气质之性是万物包括人在“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气禀清浊之性,是个体的、分殊的实然人性。中医也说“气化”,即指气的运动及其所产生的各种变化,主要包括“天地阴阳之气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一切变化”,“自然气化所表现的时间节律与人体生命现象以及人体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无不对人体的生理机能、病理变化,以及对治疗措施产生的影响”和在“自然之气参与人体所发生的各种生化活动”[7]。总之,气的聚散、升降、出入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维系着脏腑经络的生理机能。因而,中医是从生理、病理的角度去认识人体之气,在养生方面,中医讲求养身、养心和养神,却并未直接涉及以气养德的伦理内涵。
5 结语
当前,中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期,正如何裕民教授所言:“当今是中医学发展的最好时代,也是难得的最后契机;需学术共同体认真发掘学科内生性动力机制,形成清晰新思维,做好顶层设计,融入时代发展大潮”[8]。而中医学的“内生性动力机制”无疑是“气”,只有立足于气的理论,考辨其历史源流,厘清其核心要义,才能从根本上阐明中医药学的“真正优势”。
本文通过以气论自然、以气论身心、以气论情乃至以气论德的辨析,充分展示了中医之气吸收融会哲学之气而建立自身气学理论的内在逻辑。中医学以当时天文历法、五运六气等自然科学为基础,创建了以天人相应、五藏六腑为核心理论的医学体系,它很好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文明成果[9],因而被誉为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气是最能彰显中国文化特质的一个概念,是赋予整个中国文化以生命的一个要素。但作为哲学意义之气与中医之气存在较大差异,只有将医学之气从哲学之气中剥离出来,厘清哲学之气与医学之气的复杂关系,认清医学之气在防病、治病、养生等方面的积极意义,才能为中医在当代的发展拨开“偏见”的迷雾、扫清“玄虚”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