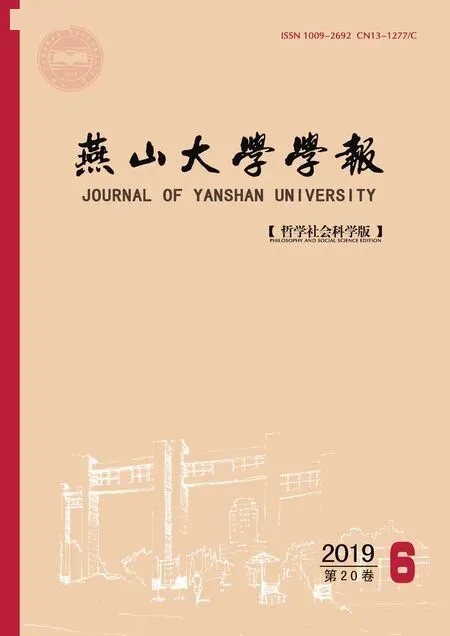从王宏印对“信达雅”的现代诠释看《易经》古歌英译
——以第十四卦“大有”为例
2019-02-24翟江月
石 英,翟江月
(1.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烟台264025;2.鲁东大学文学院,山东烟台264025)
一、引言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以下简称“中国传统译论”)是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建设的重要资源。要实现其基本论题、概念范畴和理论形态向现代翻译理论的转换,需要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历史评价、理论评判和创造转化。国内学者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王宏印著《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2003年初版;2017年修订版)。严复的“信达雅”译论,自其发表以来成为中国传统译论中最受翻译学界瞩目的译论,引起了广泛讨论甚至争论。王宏印在他2017年出版的修订版《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中,对百年来国内学者的“信达雅”研究史进行了梳理并对“信达雅”进行了现代诠释,受到翻译学界关注[1]125-137。中国的文化典籍之中,最古老的莫过于《易经》[2]。它与春秋时期成书的《易传》及随后形成的易学一起对我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易经》卦爻辞既有文字符号,又有非文字符号,而且有一些文字的含义尚不能确知。《易经》这种文本不稳定性是导致它难译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卦爻辞中又含有不同性质的文字,主要是商周古歌片段、隐含古史记录和哲理性的价值判断文字,即文史哲三类文字[3]4。因此,《易经》的语际翻译可谓是典籍外译中最为复杂的翻译现象。《易经》卦爻辞中不同性质的文字要求不同的翻译策略,其中古歌翻译要求较高的艺术性。鉴于尚未有从“信达雅”现代诠释角度针对《易经》英译进行研究的成果见诸报道,本文拟依据王宏印基于表现类文本对严复“信达雅”译论的现代诠释讨论《易经》古歌的英译问题,而历史和哲理文字的英译则待另文专论。本文选取的例证是《易经》第十四卦“大有”之中古歌的分析和英译。希望本研究有助于《易经》英译研究并有益于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翻译和传播。
二、王宏印对“信达雅”的现代诠释
按照王宏印的研究,中国传统译论从其自身的发展运演规律而言可分为四个发展时期,即肇始阶段、古典阶段、玄思阶段和直觉阶段[1]263。古典阶段的代表性译论是严复的“信达雅”译论。这个译论在百年来的翻译界所受到的关注超过其它任何一家传统译论。国内学者对“信达雅”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经典的研究和现代的研究[1]125。前者包括了梁启超、鲁迅、贺麟和钱锺书等人的研究,后者则更关注严复译论本身,尤其“信达雅”三字,有简单化和多样化并重的特点。相关研究者可大致分为赞成者和修正者两类,也有学者持否定态度。许钧认为,国内有关严复翻译思想特别是对“信达雅”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表明了“信达雅”思想的重要性,应继续深入挖掘,而国外翻译研究界对“信达雅”关注度很高,往往把它当作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典型代表,其理论价值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4]。
就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建设的要求而言,同其它传统译论一样,“信达雅”译论虽有一定的科学性、简明性和适用性,但也有其自身的问题,主要是未能对术语进行清晰界定,难以分析,缺少二级概念、不可操作等。王宏印认为,若要彻底超脱经典和现代阶段的研究路径及其局限,应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理论阐释和现代转换,而对传统译论进行现代转换是建立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必要理论准备[1]135。王宏印对严复“信达雅”译论的现代诠释和转换研究成果见诸他的多部论著,最新的论述则见于他的新版《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1]119-125。
王宏印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诠释思路是在翻译文本分类的基础上,重新用现代学术语言界定三个字的内涵,并增加二级概念,以提高在翻译批评和翻译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和可量化性。他借鉴中国传统文论的有关资源,从文本分类和创作标准的设定出发,对“信达雅”译论进行了现代诠释。从文本和世界的关系来说,一个文本可能是以再现世界为主的,也可能是以表现世界为主的。也就是说,文本可大致分为再现类和表现类。前者是以实用为文本构建的主要意图,要求更多的科学思维,例如应用文、科学论文、论说文以及新闻文本等,而后者则是以审美为文本构建的主要意图,需要更多的艺术思维、主观想象和艺术处理,例如各种文学文类以及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专业评论和研究的充满艺术性言语的文本[1]317。不同类别的文本在翻译时自然要求具有不同侧重的翻译标准。就翻译标准而言,“信达雅”之中,“信”是事理要求,“达”是语言要求,“雅”是风貌要求。从作品类别看,再现类文本的翻译要求在“信”的方面应客观、完整、缜密,在“达”的方面应准确、流畅、鲜明,在“雅”的方面应简约、匀称、统一;而表现类文本的翻译要求在“信”的方面应真实、充实、适度,在“达”的方面应形象、得体、新颖,在“雅”的方面应音美、形美、意美[5]246。在此基础上,王宏印挖掘民族译学遗产,借鉴国画艺术写实和写意技法的区分,在翻译技法层面创造性地提出了再现手法和表现手法,并专门就文学翻译表现手法进行了理论建构和应用分析,形成了他针对表现类文本的文学翻译标准和翻译手法系统。就表现类文本的翻译而言,“信”的真实、充实和适度即要求译作要表现原作内含的丰富思想、真挚的情感、深刻的哲理和高尚的道德,但并非机械的文字对应;“达”的形象、得体和新颖即要求译文要传达出原文的精妙、独特之处,所用语言应是文学语言,符合特定文体和文类的需要,同时注意吸收原作语言的表现方法或创造性地运用译入语;“雅”的音形意三美即要求译文正如鲁迅所说,写文章要“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意美,以感心”[5]248。若从文学翻译的表现手法而言,即是要承认两种语言文化间的差异,力求克服或利用这种差异造成的张力,允许翻译的“创造性悖谬”。三者之中,“达”必须基于“信”,而与“雅”相符合,在翻译实践中应力求三者兼备,辩证统一。
三、《易经》卦爻辞中的古歌片段
前文指出,《易经》文本的不稳定性是造成其翻译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易经》通行的版本主要有王弼本和朱熹本,而别本则有上世纪以来出土的多个简帛本。通行本虽经过后人整理,但在文字上仍保留了与许多上世纪出土的战国本完全相同的或意义相同的文字,说明今本仍是各种版本中最重要的版本,整体上今本更优,今本的权威性并未因许多别本的出土而削弱和动摇[6]。通过比较王弼本和朱熹本的经文可知,除了个别文字有差异,二者在文字上总体差别不大[3]258。因此,本研究仍以《易经》通行本为文本基础。
20世纪以来的易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明显异于传统易学的新成就,其中对《易经》文本的研究尤为不同。例如,根据王晓农的研究,上世纪初的古史学派如顾颉刚(1926)、胡朴安(1942)、李镜池(1981)、李大用(1992)、谢宝笙(1995)、黄凡(1995)等对《易经》文本的研究,虽然具体结论各不相同,但都倾向于认为《易经》主要是甚至全部是一部古史,经文中含有相当多的记录商周历史的文字,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历史文献[7]9-13。有些学者如高亨(1984)、傅道彬(1988)、黄玉顺(1995)、洪迪(2014)等认为,《易经》文字中有很多属于文学类,含有很多古歌,甚至认为是一部诗集[7]16-17。把《易经》视为哲学文献则是较为悠久的观点,认为经文表达了古人朴素的哲学观念。纵观这些研究,它们尚未能把文史哲三种《易经》卦爻辞研究路径统一起来。近年来,对《易经》卦爻辞进行文史哲打通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王晓农2016年出版的专著《〈易经〉英译的符号学研究》。他认为《易经》卦爻辞从其来源上看主要有三个,即商末周初周王室占筮活动的记录,构成卦爻辞主要的来源,包括了历史记录和占断用辞,其次是当时的古歌,再次是编者纳入其中的历史故事、格言和改编或创作的古歌等[3]262。他把卦爻辞逐条切分为问辞和占断辞,问辞又分为历史类、文学类和哲理类文字,而断辞则总体上具有哲理性质[3]263。作者从历史、诗歌和哲理三维入手解析《易经》文本,识别了其中的文史哲材料,其中在古史方面识别出的文字形成了一个连贯历史叙事框架,古歌方面以《诗经》诗歌为参照,整理出了多首古歌或片段。由此将《易经》64卦的卦爻辞切分为基本上各不重叠的三类文字,并确立了基于《易经》今本的64卦经文拟文本。
原则上,《易经》经文的文字中除了较易识别的占断专用辞之外,其它的文字不会同时是古史记录和古歌片段。这样,在识别出古史文字之后,其余的是否是古歌可根据其语言形式和内容加以判断。实际上,《易经》古歌研究的基本方法即“以《诗》观《易》”已经逐渐确立。因《易经》卦爻辞援引的古歌存在残章断句等复杂情况,要将每卦都敷演为具有完整意象的古歌,难免有所牵强,似也无必要[8]。就《易经》经文中的古歌而言,这些诗歌与《诗经》诗歌的主要不同,一是短小,二是没有叠章,但在艺术上,完全可跟《诗经》媲美[9]。当然,《易经》古歌与《诗经》诗歌相比,远不如后者那样普遍运用复沓回环、双声叠韵等修辞手法[3]222。《易经》卦爻辞中的诗歌还是比较原始的、朴素的,主要是写景状物抒情的。根据王晓农的研究,《易经》古歌片段有的可能是对早已流行的民歌的记录[3]221。这些古歌反映了远古的风俗习惯,由于它们长期反复出现,引起筮者注意,一些片段进入了筮辞,或被直接吸收进《易经》。而有些则可能是卦爻辞编撰者根据当时流行的民歌进行的创作。根据《易经》古歌所属卦爻辞的情况,从卦爻辞中大致可以识别出一卦之内的单条卦爻辞和多条卦爻辞,以及跨卦的卦爻辞三种古歌形式,其中主要是第二种,涉及到“乾”“坤”“屯”“蒙”“小畜”“贲”“大有”“大畜”“大过”“大壮”“明夷”“渐”等卦[3]239。以下主要以王晓农对第十四卦“大有”卦的古歌分析为例,说明《易经》古歌解读思路。该卦经文如下。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本卦的主题当与农业丰收有关。以上卦爻辞中,除“吉”“无咎”等占断专用辞之外,九三爻辞中“公用亨于天子”可判定为与周人史事有关[3]236;六五爻“厥孚交如,威如”描述的很可能是占筮所得兆示的外貌。其它文字从内容和形式上看都具有古歌的特征。初九爻的“害”指的当是影响农事的灾害。据《左传·桓公六年》,“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10]708初九爻和九二爻问辞有押尾韵,九四爻和上九爻问辞虽未押韵,但四行可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古歌的面貌。牛车在古代文献中也称为“大车”[11]。因此,九二爻的“大车”可理解为牛车。上九爻“自天佑之”之“天”即指周人信仰的“天”,与商人对“天”“帝”的概念都不同。关于九四爻的“彭”,隋唐之际陆德明的《周易释文》云:“彭,子夏作‘旁’。虞作‘尪’”。他将“彭”解为“尪”,该字本指跛足或脊背骨骼弯曲之人。古代巫觋多由此类人充当,这里当指求雨之巫尪。在形式上,初九爻和九二爻的问辞押尾韵。卦爻辞中的“佑”通“祐”,“载”和“祐”(或“之”)用古韵“之”部[12]。“自天佑之”也可能本是“自天之佑”,后来发生了文字顺序的变化。因此,“害”“载”“佑”三字原本都应是押韵的。在艺术手法上,初九爻和九二爻的问辞描写的都是现实景象,而九四爻与上九爻的问辞则都属于心理活动,二者交织在一起,与现代“意识流”创作路子很相近;其表现手法则类似“赋”的直陈,颇有“风”的味道[3]237。王晓农根据对“大有”整卦文字的韵律、主题意象和艺术手法的分析,认为有足够理由从本卦初九至上九爻辞中辑录出四句古歌片段,可合成一首古歌如下。
无交害,
大车以载。
匪其彭,
自天佑之[3]236-237。
这首古歌的主题是农业,描述了丰收的景象和人们的喜悦心情并由此感念“天”。全诗的大意是,没有频繁不断的灾害,丰收后用牛车来装载;这丰收不是求雨之巫的神通,而是来自上天的保佑。这四句诗整体读来语气轻快、意象生动、情感真挚、格调愉悦,诗意浓厚。如前所述,第四句的“天”是当时周人因其特殊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天”的概念,与商人对“天”的理解有所不同,也反映了周人对“巫觋”之术与“天”之间关系的认识。
四、“大有”卦中的古歌英译分析
就“大有”古歌的英译而言,现有《易经》主要英译本,如理雅各(J.Legge)[13]、贝恩斯(C.Bayens)[14]、蒲乐道(J. Blofeld)[15]、林理璋(R.Lynn)[16]、傅惠生[17]、闵福德(J.Minford)[18]等的英译文要么未将其视为古歌,因而译文未呈现明显的文学特征,要么即使指出某一卦爻辞有古歌片段,却未能从整卦来解读和翻译古歌,因而译文不能作为经文整体的一部分而自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因此,都有不尽如人意处。以下根据前文关于王宏印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现代诠释,着重在其二级概念层面,分析“大有”古歌英译的问题。
众所周知,作为中国最为古老的文化典籍,《易经》的文字至为简洁。从王宏印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现代诠释来看,《易经》古歌译文需在事理上与原文契合,语言上要反映出原文的语言特征,在音形意风貌上要具有古朴的诗歌面貌,并分别满足前述三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在“信”的方面,应力求译文真实、充实、适度。例如,根据基本语义,第一句的“害”译为 disaster;第二句的“大车”译为“ox wagon”,并将原文“载”之对象显化,增补“the rich harvest”,以充实之;第四句的“天”译为“Heaven”,大写首字母以体现其人格化特征,以符合周人“天”的概念之实。译文总体上应表现出原文古歌的农业主题,适度再现原文文字的简洁特征,避免过度的明晰化。在“达”的方面应力求语言形象、得体、新颖,如译文基本保留了原文的形象,而第三句的“彭”稍作变通译为“the power of witchcraft”以符合上下文对句长和音韵的要求。《易经》古歌的英译,由于原文的特殊性,译文的意旨也不应是一望便知、一览无余的,由此体现原文“体”的特征。在“雅”的方面力求译文音美、形美、意美。在形式上,本卦古歌前两行押韵,其表现手法类似“赋”的直陈,同时在艺术手法上,该诗呈现的现实景象(前两句)与描写的心理活动(心理活动)交织在一起,颇近似现代“意识流”的创作手法。译文应对此进行表现,各句译文尾词皆为清音“t”,虽属于准押韵,也能一定程度上呈现诗歌的基本面貌。在句式上,整个译文前两行中,第一行是短语(形容词“incessant”后置),第二行是带主语的不定式小句结构,后两行则分别采用了具有强调效果的结构,最后一句有词序调整,即“sent”后置。关于标题,从本卦的卦爻辞中析出的古歌本无标题。笔者认为,根据前文解读和全诗意蕴,可以采用该卦标题“大有”为标题,也可以采用最后一句的“天佑”二字作为诗题,即“天之庇荫、佑护”之意,相较而言,后者更胜。为了让一首古歌译文能够独立存在,译文不妨拟一标题,以“领袖风采”。综合全诗内容,可从最后一句中取“blessing of Heaven”作为诗题命名之。这样,全诗译文如下:
Blessing of Heaven
No disasters incessant.
Ox wagon to carry the rich harvest.
It is not the power of witchcraft,
But of the blessing Heaven us sent.
译文可谓在事理、语言和风貌三方面基本达到了前文所述翻译标准的要求,即“信”的真实、充实、适度,“达”的形象、得体、新颖,“雅”的音美、形美、意美。当然,由于存在多种语际差异,例如,汉英两种语言本身在各个层面存在系统差异,远古汉语和现代英语存在时间差异,与原文相比,译文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失”,而从翻译本体论上讲,它又具有“失”的本体属性,因此我们只能说,在上述三个方面,译文和原文在阅读效果上基本相当。
由本例分析可见,就表现类文体而言,王宏印对严复“信达雅”的现代诠释作为文学翻译标准在《易经》古歌英译中颇具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与一般诗歌翻译不同的是,《易经》古歌的译文首先要满足一卦的不同卦爻辞条对译文的整体要求。换言之,每行诗的译文应能单独而自然地置于一句卦爻辞的语境之内,同时不同卦爻辞中的古歌片段经析出后又可聚集在一起成为一首具有独立性的古歌译文。本例中,每句译文都可满足所属卦爻辞对译文的要求,同时不同卦爻辞中的古歌片段又可聚集在一起成为一首具有独立性的古歌译文,主题鲜明、意蕴古朴、诗味浓厚。总体而言,通过运用表现手法,可满足《易经》古歌英译在事理、语言和风貌三方面的要求。
五、结语
王宏印对严复“信达雅”译论的现代阐释,从构建中国现代译论的目的出发,厘清了其术语的基本概念,在再现类和表现类文本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二级概念,对各概念进行了详细论证和说明,旨在提高原作翻译标准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就表现类文本而言,它要求译文满足事理要求(真实、充实、适度)、语言要求(形象、得体、新颖)和风貌要求(音美、形美、意美)。根据《易经》文本研究的成果,卦爻辞中存在一定数量的古歌片段,有的可构成一首意蕴完整的古歌。这些古歌具有情感古朴而真挚,文字简约而意深的特点,它本身体现了汉语文化的表现性特征,其翻译属于表现类文字的翻译。笔者对《易经》“大有”卦古歌的英译分析表明,在原文古歌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王宏印就表现类文本针对严复“信达雅”的现代阐释而构建的翻译标准可较好地满足《易经》古歌英译在事理、语言和风貌三方面的要求,以弥补前人译文在这方面的不足,因此在《易经》古歌英译中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