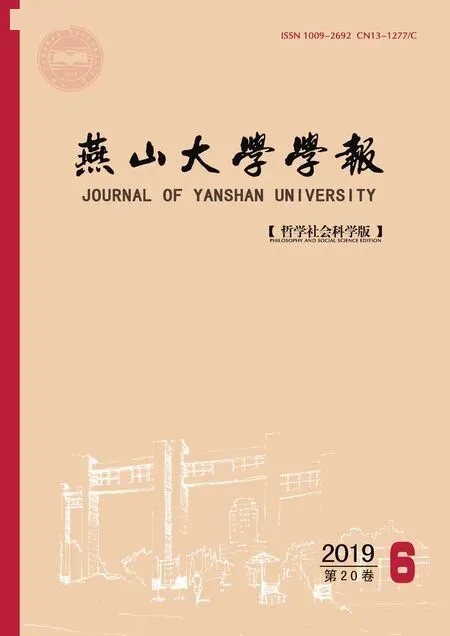张岱修养工夫论
2019-02-24范根生
范根生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张岱是明清易代之际代表人物之一,前半生生活于明朝,后半生生活于清朝,中年时期历经明清易代的大变革、大动荡、大转换。明朝覆亡、清军入关这一历史事件对他的生活和思想带来巨大的冲击:生活上,由往昔的豪华奢靡变得极为窘迫艰难;思想上,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痛苦抉择。断崖式的落差和转变使得张岱对明清之际社会、生活、学术和思想状况更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张岱作为晚明阳明后学,他虽没能建立起与同时代顾、黄、王等思想家齐肩的思想体系,但他对晚明心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工夫旷疏以及由此带来的师心自用、猖狂自大、认欲作理、掺杂情识等流弊之批判力度却一点也不逊色于顾、黄、王等人。张岱对修养工夫极为重视且有其自己的思考,颇有特色。
一、“悟”“修”并重
张岱修养工夫在根本处秉承心学“反身而诚”“逆觉体证”的基本路数,他说:“大抵圣贤教人,只在心上做工夫,不在外边讨求。”[1]265“家大父曰:心体中打叠得干净,圣贤学问工夫,自一了百当。张侗初曰:认得本心,一生更无余事。”[1]540工夫的关键在于觉悟和挺立人所固有之本心,认得本心,则一生无余事。“舜之学从精一入,惟其精一,是以灵虚之中,万善悉备,故一有感触,无不沛然。”[1]540每个人的道德本性都是完满自足的,在本原状态都可以直接相应于其所本具有的道德本性而发动为道德实践,但是,在现实之中,人作为感性的存在者,容易受到各种外在条件的限制而使其道德本性受到障蔽和陷溺,以致不能应事接物自然泛应曲当。
然而,后天的修养工夫对于道德本性本身并不能有所增损,所有具体的方法对于道德本性的体认都只是助缘工夫,只能最大程度地去促成人们对于道德本性的体认,且在最根本处这些方便法门,皆用不上力,故张岱说:“致中者,着想不得;致和者,着力不得。……博学、慎思、审问、笃行,都是方便法门。到得‘明’‘强’,方便都用不着。”[1]47而“吾人住世,一灵往来,半点帮贴不上。所谓戒慎恐惧,亦是这点独体,惺然透露,如剑芒里安身,铁轮顶上立命,无始光明,一齐迸露”[1]21,唯有对时时刻刻透露、呈现的道德本性保持警觉并当下认取之,然后操存涵养,不令之放失,使人本具有的道德本性充分朗现成为人之主宰。所以,张岱主张“舍”“逆”“减”和“诚”的修养工夫,他说:“学问时时进,便时时舍。……切磋琢磨俱是减法。”[1]79“《易》逆数也。故学者工夫,亦尽用逆。”[1]151“诚即性也。诚至而性浑然全矣,有何不尽?”[1]50
张岱认为一切外在的工夫在根本处都只是方便法门,皆用不上力。但是,他也极为重视后天积习、渐修等修养工夫,认为下学可以上达,格物穷理之后自可融会贯通,达至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地。他说:“致曲却须积渐,到得透露处,成功则一。……诚者不思不勉,自然能尽其性,何等直截!其次则必择善而固执之。要博学,要审问,要慎思、明辨、笃行,何等曲折!此等一不推致,即不能明善诚身矣。”[1]51“诚者”可以不思不勉自然尽其性,简易直截,但是对于在现实中绝大多数都是资禀不高的人来说却需要“致曲”的工夫,即需要择善而固执之,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等日常积习、渐修的方式来逐步推致。积习、渐修等“致曲”的活动同样具有道德实践的意味,“积渐”可以“到得透露处”,每一次的“致曲”活动都是在向本体逼近和回归的过程。而且“径而趋之与迂其道而至者,其所至则一也”[2]29,“径而趋之”与“迂其道”而至者并没有价值上的高低优劣之分,殊途而同归,这也即说“悟”与“修”是具同等效用的体道方式和途径。
王龙溪也曾说:“存乎根器之有利钝,及其成功一也。”[3]89但他又强调:“若在后天动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欲之杂。才落牵缠,便费斩截,致知工夫转觉繁难;欲复先天心体便有许多费力处。”[1]10龙溪认为从后天意念处下手则更为繁难,显然,他更倾向于先天顿教,认为先天工夫优于后天工夫。其实,不管是阳明本人还是其众多后学弟子都不否定“修”的工夫,但他们更多的是将“修”之工夫作为一种权法,因为只要是在“心即理”说的理论架构下,心学的修养工夫,不管是哪一派别,其修养工夫在最根本处必定都是指向良知心体的呈现和挺立。对此,牟宗三先生有十分精辟的见解,他说一切巧妙的办法,到紧要关头,皆无用,然后才逼出觉悟、顿悟之说,而所有助缘的功夫无非是在促成觉悟、顿悟[4]107-123,所以心学的修养工夫在最根本处只能是“悟”,一切具体方法皆助缘工夫。而由上分析可知,张岱认为修养工夫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不同的主体采取不同的方式,主张“悟”“修”并重,且他在坚持“心即理”说的理论架构下并不把“修”的工夫只看作是一种权法,而是将其提升到与“悟”的工夫等量齐观的地位,还更为凸显“修”的工夫。这似乎看到张岱在晚明“心即理”说受到极大动摇的情况下,通过对“修”的工夫地位的重视和提升来应对现实之流弊,并以此来捍卫“心即理”说所做的尝试和努力。下文在探讨张岱“格物”工夫时将对其“修”的工夫作进一步的论述。
二、本体与工夫的辩证
“现成良知”之辩是阳明后学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张岱对“现成良知”说也有一定程度的思考。“《论语》中‘之’字、‘斯’字、‘是’字,最当着眼,如‘是知也’,‘是丘也’,俱急切指认。一是不可当下埋没了这点真灵明;一是不可当前错过了这个真面目。”[1]92张岱认为良知不是静态的存有结构,而是时时刻刻都处于活动、发用的状态,作为先验的良知本体必定会在经验意识之中呈露、发用。“吹毛求疵,洗垢索瘢,何与人事?‘何所不至’,良心澌灭殆尽了。一见君子,忽然爆露,掩不善著善,俨然是恶恶臭、好好色的真光景。当下回头,就可立地成佛。正如石沉海底,火性千年不灭;斧声铮然,一触便现。照天耀地,也只是这点。”[1]11只是在现实之中,人易受到气禀物欲的障蔽而难以觉察,但是此良知并未澌灭殆尽,此状态下之良知犹如沉入海底的石头,石头由于受到海水的限制难以迸发出火花,但是它所本具有的火性却千年不灭,不会因海水的影响而丧失殆尽,且一触便现。人之良知也是如此,它不会因为气禀物欲的障蔽而有丝毫的减损,且时时刻刻都在经验之中呈露、发用,“一见君子,忽然爆露”,君子则能够当下肯认,当下即是,当下具足。“也只是这点”则表明呈现于感性经验中的良知与作为先验本体的良知在本质具有同一性,此当下呈现、发用之良知无圣、愚之分,其为人之道德实践的终极根据,并为人之道德践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每个人的良知在现实之中就都已经是完满自足的,都可以直接顺任良知而行,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闻之善作家者曰:人欲营利,必时时运动,则家业日长。若守定目前,毫不营运,天欲富女,亦无从而富女。”[1]170在现实之中,气禀物欲时时泛起,良知之呈露、发用总是处于理欲夹杂之中,如果一味固守良知现成而不做任何澄治、操存涵养工夫,则很容易冒认现成良知,将生物层面的感性知觉当作良知在经验意识之中的呈露、发用,导致工夫脱略,以纵情恣肆为率性而行,走向小人之无所忌惮,最终偏离圣贤之正道。故张岱借用诸理斋的话说“与知而自以为知,究成小人之无忌惮”。[1]35晚明社会对现成良知说的批判主要就集中在现成良知说容易将现成良知即良知在经验意识之中的呈露、发用与感性知觉相混淆,导致工夫旷疏、认欲作理等弊病。
由此,张岱认为良知虽现成,但此在经验意识之中呈现的良知与良知本体并不能完全等同。他在解释《孟子·良知章》时引用顾泾阳的话说:“孟子以‘不学而能’为‘良能’,‘不虑而知’为‘良知’。吾以为不能而学亦‘良能’也,不知而虑亦‘良知’也,何也?微良知良能,人亦安于不能不知已耳,孰牖之而使学?孰启之而使虑也?吾又以为学而能亦‘良能’也,虑而知亦‘良知’也,何也?知能之入处异,而知能之究竟处同,非学不学、虑不虑所得而歧也。”[1]539这里可以看出,张岱认为作为本体的“良知良能”是先验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但他又认为学而能亦“良能”,虑而至亦“良知”,因为有些人虽有“良知良能”,但在现实经验之中,由于受到障蔽而不能不知,故需要通过学与虑的活动来使人觉知此“良知良能”。而且,人之所以能通过学与虑来觉知此良知良能正是由于人本具有之良知良能作为根据,且此良知良能能够时时呈露、发用,否则,人将安于不知不能。故张岱特别重视道德修养工夫,“仁在乎熟之而已。”[1]520“人都做仁,熟不曾做,熟之,熟之,有多少工夫在。”[1]520认为需要不断地进行道德实践,即通过艰苦卓绝的道德实践活动使此经验意识层面的良知良能之用达至与良知良能之体同一而圆满的状态。
此外,晚明时期,现成良知之辩逐渐转换为对圣人是否现成的探讨。张岱对“圣者”与“圣人”进行了区分,他引用杨复所的话说:“圣者与圣人不同:圣人有定属之名;圣者无定属之名,亦在人为之耳。人倘能依乎中庸,遁世不悔,便是圣者矣,又何让哉?一字之异,其妙如此。”[1]34张岱认为圣人有定属之名,而圣者无定属之名,这是说圣人是在历史中盖棺定论,已经形成的特定的一类人,如孔子、孟子等圣人,而在现实中人可以选择依中庸之道而行,也可以选择不依中庸之道而行,当人能够选择依中庸之道而行,遁世不悔时,那么,他就是可以被称之为圣者,但还不能称之为圣人。因为只要人生在世就随时都具有犯错误的可能性,所以在现实中人只可能是一个圣者而不可能是一个圣人。这里可见,张岱虽认为“是世间孩提那一个不是尧舜?”[1]521-522但现实之中的人并非就是尧舜,对于圣人的追求是一无限靠近而又永无止境的过程。
张岱通过对道德实践工夫的高扬来疏堵晚明王学末流冒认现成良知、脱略工夫等现成良知说引发的非预期流弊,认为即使是圣人也需要时刻不断地做实践工夫,将工夫落到实处,他引用李见罗的话集中表达了他对于现成良知与工夫实践之间关系的辩证关系,他说:“论工夫,圣人亦无歇手;论本体,庸人亦是现成。”[1]466
三、道德严格主义
张岱特别重视道德实践工夫,他在具体实践工夫中则极为强调“忌惮”“戒慎”“恐惧”“惺惺”“小心”等工夫,“薛西原曰:情易失之过,不及者鲜。‘节’有止而不过之义。此中仍‘戒慎’,‘恐惧工夫’,不是空空便能中节。”[1]22“杨复所曰:“‘忌’即是‘戒惧’二字,‘惮’字即是‘恐惧’二字。‘无忌惮’者,无‘戒惧’‘恐惧’之心也。大抵异端只为大胆误了事。”[1]23“黄贞父曰:此病只是精神放肆,故曰:‘不敢不勉’,‘不敢尽’。‘不敢’二字最妙,即下‘顾’字精神,即首章‘戒慎’、‘恐惧’。”[1]37可见,张岱深切地意识到人性中潜存的幽暗面,体察到道德实践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虽然人人生而具有完满自足的良知本性,但在现实生活中能够真正做到完全地顺任良知而行却是异常困难和艰辛的,成圣成贤是一无限的过程,期间往往需要历经百死千难的工夫实践,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时刻还充满着各种诱惑,一着不慎即有误入歧途的危险,故“千古圣贤,惟有小心而已”[1]23,表现出张岱对于道德实践工夫的严苛要求。同时,他认为道德实践还要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和决心,“‘刻毒’两字甚好,比如我要作好,忽然起一恶念,这就是我的对头,却不肯下刻毒手与他讨个下落,不知何故?”[1]148良知本心挺立之时恰恰也是气禀物欲抬头和活跃之时,此时私心物欲十分容易掺杂、渗入良知本心之中,借着良知本心行善之名义来畅遂其欲,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有陆象山所说的“与血气争寨作主”的勇气和决心,战胜恶念。此外,张岱特别注重道德实践工夫的当下性,认为为善去恶的工夫刻不容缓,“‘一日’字最可味,舍此‘一日’不下手,永无下手之期矣。百事都始于‘一日’,况为仁乎?”[1]253-254生活中要做好任何事情都不能安于现状,“为仁”更是如此。在现实之中,人们十分容易受到外在不良习俗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积重难返,逐渐走向堕落,在这一过程中,人之心也将慢慢地养成根深蒂固的“习心”,使人陷溺于流俗之中而不自知,这是“为仁”过程中极易碰到的一大难题,对于此,张岱认为一定要知行合一,脚踏实地地去为善去恶。此“‘一日’最可玩味,舍此‘一日’不下手,永无下手之期”还表明张岱认为一定要抓住良知本心当下呈现、发用之时去为善去恶,因为此时是最为根本,也最为有效的工夫,如果不抓住此时从事修养工夫,那么人们将在习惯强大力量的作用下更加没有下手的机会。
张岱通过对“忌惮”“戒慎”“恐惧”“惺惺”“小心”等工夫的强调和高扬,企图以此来纠正和救治王学末流中狂妄之徒以现成良知为自然良知、认欲作理,师心自用等弊病。而对于“戒慎”“恐惧”与“慎独”,阳明认为只是一个工夫,“先生曰:非也,‘格物’即‘慎独’即‘戒惧’;至于‘集义’、‘博约’工夫只一般,不是那数件都做‘格物’底事。”[5]138他也明确地表明不能将这些工夫割裂,否则,工夫便陷入支离、有间断,“先生曰:‘只是一个工夫。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今若又分戒惧为己所不知。即工夫便支离,亦有间断’。”[5]39-40而张岱将“戒慎恐惧”与“慎独”工夫分开,他借艾千子的话说:“譬如防盗,‘戒惧’是平时保甲法,‘慎独’是关津紧要处搜盘法。将‘慎独’径作‘戒惧’者,亦非。”[1]21并借辛复元的话说:“‘戒惧’是静中主敬,‘慎独’是方动研几。静中主敬,私欲无端而起;方动研几,私欲无得而滋。”[1]22这里可以看出,张岱将工夫分为静和动,已发和未发两个层面,且认为这两个层面需要用不同的修养工夫,“戒惧”是平时保甲法,是静中涵养的工夫,“慎独”是关津紧要处搜盘法,是私欲发动时的克制工夫,而阳明则反对将工夫分为已发和未发,动与静两截,主张圆融一贯之工夫。对此,顾东桥就曾有疑惑,他写信向阳明请教道:“但恐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后生师传,影响谬误,未免坠于佛氏明心见性、定慧顿悟之机,无怪闻者见疑。”[5]46到了晚明时期,心学圆融一贯修养工夫的弊病进一步凸显,故张岱在具体修养工夫层面不断地细化、具体化,试图以此来应对工夫太圆融、高妙而使人无处下手或者使人陷入把玩文字忽视工夫中实修实证的一面,他说:“夫子目子路曰:‘由也,升堂矣,未入室也。’今曾目子张曰:‘堂堂’。‘堂’而又复曰‘堂’,则高明极矣;‘难与为仁’亦只少‘入室’工夫。”[1]363由上可知,张岱虽在根本工夫上秉承阳明修养工夫的路径,但在具体工夫层面已有所偏离阳明,而和程朱静中涵养、动中察识的修养工夫颇为接近。
彭国翔教授曾指出:“阳明之后理学工夫论发展所表现出的那种普遍趋向,恰恰与龙溪不谋而合,即要求将工夫的用力点落实于道德实践的终极根据上去,而不论对这终极根据的概念规定是如何因人而异。”[6]352心学一系的修养工夫论确实在不断地趋向内在化,阳明殁后,王门虽分化为诸多派别,但是他们在修养工夫上却都追求第一义的究竟工夫,从以上对于张岱修养工夫的考察发现,张岱的修养工夫在坚持心学的根本立场下出现由内而向外,即由偏重意识本体层面的工夫转向更为偏重日用伦常工夫的趋向。
四、格物致知
历来对“格物”的解释有很多,晚明学界对“格物”依然没有形成一个公论,而对“格物”不同的诠释也反映出学者不同的工夫路向。张岱说:“‘格物’二字,先儒于此,几成聚讼。”[1]4可见,张岱对历来“格物”说进行过一番考察,他对于“格物”也有其自己的思考。从根本处看,其“格物”思想与陆象山相一致。他引用徐子卿的话说:“零说可以,顿说可以,粗说可以,精说,吾心也是一物,若格得吾心了,此外有何物?”[1]2其“格物”即“格心”,故他极力反对朱子的“格物补传”,他说:“传分明以‘知本’当‘格物’,而宋儒以为阙文,得无多此一补传乎?‘物格’,‘知至’是一件事,故独曰‘在’。”[1]3张岱认为“物格”和“知至”是同一件事,最终目的都是“明明德”,不必将其分为两截,这也即表明“格物”和“致知”是实现此目的的两种不同方式。“格物是零星说,致知是顿悟说。”[1]2即“格物”是渐修的方式,“致知”是顿悟的方式。诚者不思不勉,自然尽性,直截爽快,这是接引上根之人的顿悟说,而对于很多初学者以及中下根之人,他们由于受到气禀物欲的障蔽不能如此直截了当地从本心道体直接切入,往往需要一个循序渐进,惟精惟一的过程,故张岱主张“致曲”,“要博学,要审问,要慎思、明辨、笃行,何等曲折!此等一不推致,即不能明善诚身矣。”[1]51这里可见,张岱虽基于心学的立场对朱子的“格物补传”进行了批判,但他并不完全否定朱子的“格物”思想。
张岱对朱子的“格物”说亦持有同情之理解,他说:“但患认朱子意差,真个于物上寻讨,饶君遍识博解,胸中只得一部《尔雅》,有白首而不得入古人之学,为可悲耳。要非可以病朱子也。”[1]2-3他认为朱子学与心学殊途而同归,在根本处是一致的,朱子并非要人去研究客观事物之理,后人误解朱子学的真精神而走上遍识博解、皓首穷经支离之路,这不能责怪朱子。
象山“格物”即“格心”,简易直捷,故他批评朱子“格物”说支离、不见道。然而,作为教法,象山这种简易直捷非分解的方式也带来诸多弊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后学弟子不知从何处无入手,象山高徒杨简曾屡次追问如何是本心而不得,《陆九渊集》中也频繁出现后学弟子“茫然不知所入”“无个下手处”的困惑;一个是后学弟子崇高好悟,徒知求取本心,忽视日常工夫实践,从而出现猖狂、悖慢、无礼甚至异端的行为,而象山学出现之问题也是心学一脉中的通病。朱子则采取分解的方式立说,他对象山非分解立说的方式不以为然,认为其学风空疏且将其学讥为禅学。相对于象山,朱子则更为强调日常工夫践履的笃实性,将修养工夫具体化、可操作化,使后学弟子在从事践履工夫时有轨可循、有阶可历而不会茫然无入手处。在这一方面,张岱极为赞同朱子,他认为“圣贤教人如老媪教孩子数浮图:一层层数上来,又一层层数下去。有这层,政见得有那层,先有这层,一毫参差不得。要人把全体精神,从脚跟下做起也。”[1]2身处明清之际的张岱深切地体会到心学之中无所依循的体道方式很容易造成工夫旷疏之弊,导致在实践中流为猖狂自大,以恣肆率情而为无所忌惮,给当时社会的学风、士风造成严重的危害,故张岱特别强调实践工夫要有所依循,须从脚跟下做起,一步一步,脚踏实地,下学上达,反对学者谈空说妙,不从具体的工夫条目入手而直接以体道为工夫。显然,这里张岱吸收了朱子的“格物”思想。
张岱虽认为工夫教法须有次第、顺序可依循,但他并不由此就认为在具体的工夫实践过程中不可躐等,必须严格依循教法逐节逐节地往上修。他说:“但得手处,自有次第耳,所谓逐节证,非逐节修也。”[1]82在具体的实践工夫过程中,需要“下学上达”,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下学”都可以“上达”,有些“下学”的工夫可能根本就不能“上达”,但我们又不知道哪些“下学”的工夫可以“上达”,哪些不可以,哪些“下达”的工夫适合,哪些不适合,所以,张岱虽然主张在具体的实践工夫中要有教法作为指引,但他也特别强调不能因循固守、亦步亦趋地按照教法修行,因为再圆融完满的工夫教法经由文字固定化之后,总是会有所限制和偏重,如果学者在修行的过程之中只停留在字面意思层面则往往很难把握住此教法之真实意涵。更为重要的是,教法代表的是一普遍工夫之法,每个人之气禀资质不同,同一教法的实施效果也不尽相同,如果人们不能根据自身特殊的气禀资质进行切实的践履体证,此教法也很有可能流为虚言妄说。有鉴于此,张岱认为修行者既要有教法来作为为学之入手处,但也要警惕此教法对人之限制,要结合自身的特殊情况进行修证,“根性个别,道体无方”,一定要懂得“权变”,即要根据你所选取的教法所达至的实际效果与圣贤之间的差距,不断地印证和调整工夫方法。同时,在逐步印证的过程中也不能畏葸不前,害怕或不敢向更高阶段的圣学迈进,结合实际的修证效果,一定要勇于向上提升和突破,不断超越现实、超越自我,努力向圣贤境地逼近。
张岱基于心学的立场积极吸收了朱子的“格物”思想,相较于朱子,张岱则更为强调“格物”之本,他特别突出“格物”的内向性,即确立伦理价值优先的立场,将“格物”的方向牢牢地指向成圣成贤这一根本目的,避免陷于“茫茫荡荡都无着落”。故张岱说:“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不可。须穷尽到十分。”[1]2天下事物无穷无尽,人之有限性注定不能将其格尽,所以,张岱不重视“格物”的普遍性,即关键不在于“格”了多少事物,而是有没有把事物“格”透,张岱认为“格物”一定要透彻,一定要至乎其极。
除此之外,张岱又说:“朱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也只是对初学下立手工夫。其实可以也那末处。任治,原不中用。薄处任厚,只是厚不得耳。《吕览》《月令》曾无秕政,山公吏部,何忧失人。究竟济事不济事?”[1]4可见,张岱认为“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下学渐修工夫不仅仅只是用来接引初学者的下手工夫,“其实可以也那末处”,这表明张岱认为此种下学渐修的方式也是格本、明心的一种途径,且不仅仅是一种权法,而是独立的“体道”途径。同时,他也特别强调此种下学渐修的方法其最终指向一定是为道德实践而非纯粹客观知识的探求,“参破此地,自透宗本,千蹊万迳,摄归一处,何物碍心?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1]8千蹊万径,最终都摄归一处,即要宗本,明心之全体大用,而且张岱认为这两种方式在成功处一也,没有价值上的高低优劣之分。这里也可以看出,张岱并不认为朱子的“格物”是“学不见道”,它也可以“下学上达”“豁然贯通”,故他说:“晦庵得力在格物,象山得力在致知,此皆论入门、不论究竟。朱陆似有殊途,及至到家,则共坐堂奥,不必论其徒从外入、徒内出也。”[7]77张岱认为朱子得力于“格物”,象山得力于“致知”,二者虽有极大的不同,但这只是圣学入门的途径,在根本处他们都是一致的,都是要“与道合一”,体证“太极流行”,入门之途径千蹊万径,不需要争论谁优谁劣,关键得看此途径方法是否适合个人,以及在实际践履中“济事不济事”,即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可见,工夫论发展到张岱这里,已不再那么突出要将工夫的作用点放在最根本的良知心体之上,修养工夫的关键不在于是第一义还是第二义,而是更加凸显此修养工夫到底有没有实效,能不能在现实中帮助人们达到成圣成贤的目的。
五、结语
本文从四个方面梳理了张岱的修养工夫论,在根本处张岱立足心学修养工夫的立场,强调“逆”“减”“舍”“诚”等工夫,但是,他又并不突出以良知心体为工夫对象的第一义工夫,而是更为凸显“修”的工夫,且将其提升至与“悟”的工夫同等的地位,将王学修养工夫由偏重内转为更加偏重外,不断将工夫细化、具体化,凸显其在日用伦常中落实的向度。此外,张岱试图跳出阳明后学关于修养工夫的争论,主张修养工夫应以“济事不济事”的实际效果来选取和衡量其价值,表现出效验主义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