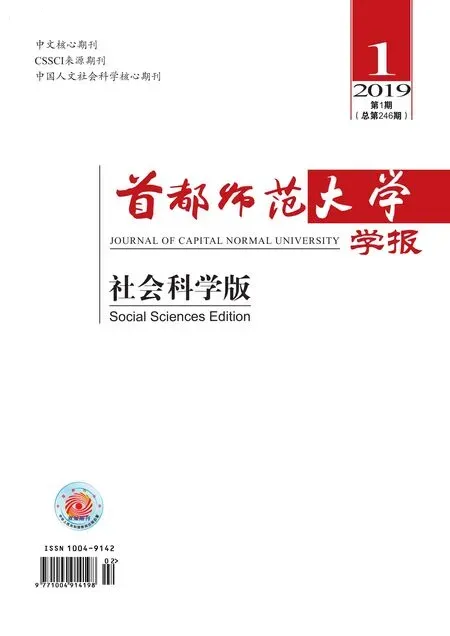“精理为文”与“理隐文贵”
——以《春秋》三传与《春秋纬》为例论汉代“经纬成文”
2019-02-22孙少华
孙少华
历来我们对《春秋》三传的研究,主要从经学、史学角度进行,然而脱离了经学崇尚的时代与具体的历史语境或文化背景,将我们对经学、史学的理解施于《春秋》三传,其中有多少合乎其成书时代的本意、合乎其解释时代的本意,我们不得而知。断章取义式阐释、循环式论证、假设性推论,或者给读者以启示,然究竟无法完全落实为可靠的结论。而从《春秋》三传对后世文学理论影响的角度看,有些说法却可以得以验证与落实。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赵简子与子大叔论“礼”,子大叔有“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之语,孔颖达疏云:“言礼之于天地,犹织之有经纬,得经纬相错乃成文,如天地得礼始成就。”[注]《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一《昭公二十五年》,《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8页。下同。此虽就“礼”而言,然其中“经纬相错乃成文”之语,抛开“经纬相错”之事实,却对后世文艺思想具有一定影响。若结合汉代经学与纬书之关系,此说亦可成立。然若深究,此语启发我们不得不想到一个问题:“经”与“纬”如何“相错成文”?
刘勰《文心雕龙》在其《原道》《征圣》《宗经》《正纬》篇中,多次论及“道”“圣”“经”“纬”与“文”之关系,尤其认为“圣人”能“精理为文,秀气成采”[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征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页。下同。,而“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注]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征圣》,《詹锳全集》卷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作“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改从唐写本,詹锳《义证》从之。笔者以为,原文文字究竟如何,已不可考,然其中“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思想当无误,为方便研究,姑从詹锳之说。、“《春秋》辨理,一字见义”[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宗经》,第22页。之说,亦可称“经”具“精理为文”之特征。刘勰又赞“纬”为“神宝藏用,理隐文贵”[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正纬》,第31页。,称“经”(《易》“四象”、《春秋》“五例”)为“隐义以藏用”[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征圣》,第16页。,可知“理”在“经”“纬”之间具有一定作用;而从具体的文本书写方法看,“藏用”属于“经”“纬”共同的文本特征。本文拟在推论“经纬为文”基础上,讨论二者隐含之“理”以及“藏用”特征对汉初文艺思想的意义。
一、 “精理为文”的实现方式与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称:“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圣训宜广,神教宜约。”[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正纬》,第30页。意思是“经”以“圣训”施教于社会,具有文辞“广博”之特点;“纬”以“神道设教”于天地[注]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正纬》,第78页注释1引饶宗颐等《文心雕龙集释稿》。,具有文辞“简约”之特点。另由此可见,“经显”宜为“文”,“纬隐”宜为“质”。如果根据扬雄“阴敛其质,阳散其文,文质班班,万物粲然”“天文地质,不易厥位”[注](北宋)司马光:《太玄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7、205页。,以及《春秋元命苞》“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天质而地文”[注]《春秋元命苞》,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93页。之说,刘勰此类说法,有其合理之处。综合各种说法,可知这应该是从二者的外部作用、内部材料体现出来的风格来说的。
刘勰又以为“圣人”能“精理为文”[注]《文心雕龙·征圣》:“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故《征圣》所言“精理为文”,亦可适用于“经”。,此类“圣训”多为“经文”,故知“经”之成“文”,在乎其所蕴含之“精深之义理”[注]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征圣》,第40页注释3。,而此又通过“一字以褒贬”体现出来。现以《春秋》三传为例,尝试分析。
三传对《春秋》记载事件的解释,多有不同,此一方面体现三传解释之差异,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三传对《春秋》之不同认识。《春秋》三传之“文”,由此亦可得以体现。
鲁隐公元年,《春秋》记载:“公子益师卒。”[注]《春秋左传正义》卷二《隐公元年》,《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715页。三传同时解释了为何此处不记录其卒日期的原因。《左传》以为:“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注]《春秋左传正义》卷二《隐公元年》,《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718页。即以为隐公未参与小敛之礼,故不书日。《公羊传》以为:“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注]《春秋左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元年》,《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00页。即以为年代久远,说法不一,无法记录。《穀梁传》则称:“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注]《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一《隐公元年》,《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366页。即以为公子益师有恶行,故不书其卒日。《春秋纬》则云:“孔子亲仕之定哀,故以定哀为己时。定哀既当于己,明知昭公为父时事,知昭定哀为所见,文宣成襄为所闻,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者。”[注]《春秋纬》,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下册,第648页。此处所言,显然是针对《公羊传》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进一步解释[注]后来何休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世”说,则是从义理层面做出的更进一步阐释。。在此,三传也是对《春秋》隐含的一个文本现象(“不书卒日”)的解释,《春秋纬》则是对《公羊传》提出的一个假设的阐发,进一步将“所见”“所闻”“所传闻”落实到某个具体的时代。这是三传与《春秋纬》在对《春秋》文本解释过程中发生的显、隐现象。如果从“经纬成文”的角度看,《春秋》及其三传为显豁之“文”,皆针对历史事实展开不同形式的记录或解说;《春秋纬》为隐晦之“质”,即指出历史事实的本质所在,二者“文”“质”交织,就形成为一个新的“文”。
鲁桓公三年,《春秋》记载:“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注]《春秋左传正义》卷六《桓公三年》,《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746页。这是一次有日食发生详细时间的记载(有“日”有“朔”)。《穀梁传》解释较为详细:“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尽也,有继之辞也。”范宁以为“既”的意思就是“尽而复生”[注]《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三《桓公三年》,《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373页。。《公羊传》解释了“既”的意思:“既者何?尽也。”[注]《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四《桓公三年》,《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214页。《左传》对本年日食无解释。然而对未记载详细日子的日食,《左传》则有解释,如桓公十七年的日食,《春秋》记载:“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左传》解释为:“不书日,官失之也。”即以为史官未记载,王充则以为史官重年月、不重具体日子,因遗忘而忽略了,故其称:“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注]黄晖:《论衡校释·正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册,第1140页。下同。由“官失之”分析,《左传》以《春秋》为史书。桓公三年的日食,《左传》未作解释,或以为史官记录已详,无解释之必要。
《公羊传》《穀梁传》对此类问题的认识,可从隐公三年的日食记载进行分析。本年日食,亦“不书日”,《公羊传》以为原因在于“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即以为鲁历不正,史官错记所致;《穀梁传》以为“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也是以为发生了错记。《隋书·律历志》以为《公羊传》《穀梁传》“皆臆说”。但抛开史料正讹之辩,是知三传皆以《春秋》为“史书”,其讹皆史官所致。综合《春秋》三传之言,其对《春秋》之解释,皆从正面解释经文大意,是对“圣训”较为明显的解释,其解释的意思也非常清楚,与刘勰所言“经显”吻合。
作为与“经”对立的“纬”,是如何解释的呢?我们看《春秋纬》的记载:“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其后,楚僭号称王,灭邓谷,政教陵迟。”[注]《春秋纬》,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下册,第655页。其中,“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为《春秋》之文,“其后,楚僭号称王,灭邓谷,政教陵迟”为《春秋纬》文。对于桓公三年这次日食背后的故事,从《春秋》及其三传之文,根本看不出《春秋纬》所说的“政教陵迟”云云,故可知《春秋纬》是从预言、警示或者反面教训的角度解释《春秋》此次日食,其意义是隐晦的,解释是反面的。这也与刘勰所言“纬隐”相合。王充曾云:“夫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注]黄晖:《论衡校释·正说》,第4册,第1141页。此实际上是针对三传与“纬书”而言。在对《春秋》的过度解释上,三传与《春秋纬》是一样的;但在对《春秋》内容的具体解释上,三传未脱离《春秋》本意,《春秋纬》已经结合后世文献进行了补充阐释。从内容及其功能上看,《春秋》三传为“文”,《春秋纬》为“质”;从其文本性质上看,《春秋》三传之“文”与《春秋纬》之“质”,皆属对《春秋》这一原始文本的综合解释,又“相错”成一个新的“文”。此处经、纬成文的基本方式,是就《春秋》文本记录方式而引发的阐释差异,从而造成的“相错成文”现象。
鲁僖公八年,《春秋》记载:“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按照王充的认识,这应该是一个对历史事件的原始记录,至《春秋》三传,对“致夫人”一词,则作了不同的解释。《左传》:“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以为告所至者为“哀姜”。《穀梁传》记载:“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辞也,非正也。”以为“致夫人”为“立妾之辞”。《左传》《穀梁传》的解释,开始将“夫人”坐实为哀姜与鲁僖公之母成风[注]王维堤、唐书文:《春秋公羊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07页。。另外,《穀梁传》解释“用”“致”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显然以为《春秋》具有褒贬之意。无论如何,此二传亦皆从正面解释《春秋》本文。《公羊传》的解释,则在《左传》《穀梁传》基础上有所推进:“其言以妾为妻奈何?盖胁于齐媵女之先至者也。”“胁于齐媵女之先至者”,从《春秋》文本无法得出此意义,此或《公羊传》据其他史料臆测之辞。从总体上看,《春秋》三传重在对“义理”的阐释。如果说《左传》《穀梁传》还重在对史实的解读,《公羊传》则有了“正统”之大义成分。但无论如何,《春秋》三传对《春秋》的解读,仍未完全脱离《春秋》文本,属于“正面的”“显明的”解读。相对于《春秋纬》而言,后者则隐含着“文本背后”的历史故事。如《春秋纬》记载:“僖公本聘楚女为嫡,齐女为媵。”[注]《春秋纬》,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下册,第655页。此“本”字,即体现出《春秋纬》的解释,重在文本背后的内涵。《春秋纬》此说见于《公羊传》何休解诂,知《春秋纬》是进一步解释《公羊传》“胁于齐媵女之先至者”而来。如此说来,《春秋纬》的解说,是较《公羊传》走得更远,距《春秋》文本原意亦更隐晦。然若从“文质”角度看,《春秋》《左传》《穀梁传》《公羊传》为“文”,《春秋纬》为“质”,经与纬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又呈现出在《春秋》文本统辖之下新的“文”。此处经、纬成文的方式,是就《春秋》文本内涵引发的阐释差异,从而造成的“成文”现象。
此处我们所说的“文”,是因为后世作为“经”的《春秋》及其三传,皆从正面记录、解说历史事实,具有“明”之“文”特征;《春秋纬》作为“纬书”,重视文本背后的意义解释,虽然有牵强附会、不符合文本本意之处,然皆委婉、隐晦,具有“隐”之“质”的特征。
鲁成公五年,《春秋》记载:“夏,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谷。梁山崩。”[注]《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六《成公五年》,《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01页。三传不约而同对“梁山崩”予以特别关注并详细解释。《公羊传》从“壅河三日不流”现象出发,以为“为天下记异”,突出“天灾异象”。《穀梁传》《左传》皆讲述了一个故事,以为“国主山川”,当祭告以禳灾。然而二书也有些微差异:《穀梁传》同《公羊传》,以为“梁山崩”出现了“壅河三日不流”(《穀梁传》作“壅遏河三日不流”),《穀梁传》祭告是为了使黄河流通;《左传》则云“山崩川竭”,国君应该礼祭山川之神。《穀梁传》《左传》叙述的故事都突出了“辇者”的智慧,只不过《穀梁传》又增加了“孔子闻之”之类的评价。在此,《春秋》仅仅记载“梁山崩”这一现象,然而《公羊传》以“异象”解释之,《左传》《穀梁传》详细解释如何消除此类灾异。无论如何,三传皆从文本正面解释《春秋》文意。《春秋纬》则云:“梁山崩,自是之后六十年之中,弒君十四,亡国三十二。”[注]《春秋纬》,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下册,第656页。即跳出了三传对《春秋》本文的阐释层面,从预言未来的角度,对“梁山崩”带来的人事灾害提出警示。这显然是一种属于《春秋》文本之外,且无法验证其真伪的预言。《春秋》三传以此为自然灾异(“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春秋纬》则以为此现象预示着后世有“弒君”“亡国”之祸。此类“解释当下”与“预言未来”的现象,是就《春秋》文本性质或功能的认识差异,从而造成的“成文”现象。
定公四年,对于吴、楚之战以及伍子胥鞭尸事件,《春秋》记载:“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楚囊瓦出奔郑。庚辰,吴入郢。”[注]柏举,《公羊传》录经文作“伯莒”,《穀梁传》作“伯举”。《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33页。《左传》详细记载了吴入郢事,有倒叙伍子胥发誓报复楚国、申包胥发誓复兴楚国事,并无伍子胥鞭尸事。[注]《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四《定公四年》,《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36—2137页。《公羊传》借伍子胥之口,解释“子为父复仇”的原则,在于“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注]《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五《定公四年》,《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337页。,重点在“复仇大义”上。《穀梁传》开始出现“坏宗庙,徙陈器,挞平王之墓”的记载,并且进一步解释“吴入楚”为“日入”的原因。[注]《春秋穀梁传注疏》卷十九《定公四年》,《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44页。《春秋纬》的记载则更具夸饰色彩:“时子胥因吴之众堕平王之墓,烧其宗庙。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注]《春秋纬》,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下册,第656页。除了“堕平王之墓,烧其宗庙”可见于《公羊传》注,“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明显属于《春秋纬》采录其他传闻而成。尤其是“血流至踝”,明显属于增饰之词。司马迁《史记》记载此事,主要采用《左传》的记载,然亦增加一句:“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注](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册,第2647页。此“鞭之三百”与《春秋纬》“血流至踝”写法类似[注]《史记》的材料来源较为复杂,在此我们不能因为《史记》与《左传》有相似材料,即断定《史记》的说法来源于《左传》,或者改造自《左传》。《春秋纬》的文献提醒我们,《春秋纬》可能成书较晚,但其说法可能早有来源。《史记》与《诗经》中的相似材料,也应该如此理解。,由此可知,《春秋纬》与《史记》更具文学性。然就《春秋》三传与《春秋纬》的关系而言,从叙事表现上分析,三传明显对《春秋》“吴入郢”事作了进一步发挥,《春秋纬》则对《穀梁传》的“挞平王之墓”做了进一步演绎,发生了由“挞墓”至“鞭尸”的变化。此处,如果说《春秋》及其三传的记载是基本客观的,《春秋纬》则具有“神异”色彩,属于《春秋》文本之外的内容。这本来属于两种不同的写法,即“历史实录”与“诗性叙事”[注]孙少华:《从“史诗”到“史实”——试论中国早期文本的两种书写思维及其演进》,《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第95-105页。,然至《史记》却实现了统一。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勰所言“经正纬奇”的特点特别显明。
刘勰称圣人能“精理为文”,其实对于《春秋》及其三传与《春秋纬》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并且,上文我们所说的“经纬成文”,正是“精理为文”的具体实现方式。
所谓“精理”,詹锳以为即“精神之义理”。综合以上论述可知,《春秋》之“义理”,是否如三传及《春秋纬》所阐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由三传与《春秋纬》所构建的《春秋》笔法阐释方式看,无论是《春秋》三传还是《春秋纬》,皆有其特定的“义理”存在。例如上文所言“伍子胥鞭尸”事,《春秋》侧重记“吴入郢”。春秋时期,一个诸侯国进入另一个诸侯国的都城,是较为罕见的事情。《春秋》记载此事,显然以为此事是当时的一件历史大事。《公羊传》侧重讲“复仇大义”,似乎是说伍子胥之举为“义举”。《穀梁传》侧重讲吴对楚郢都的破坏,似乎是以吴为“不义之师”。《左传》讲伍子胥“复仇”与申包胥“复国”事,一褒一贬自在其中。根据《春秋》的记载与三传、《春秋纬》的阐释,其中隐含的“精理”非常明显。所以说,“圣人”“精理为文”之后,后世阐释者在重新解读《春秋》,或者重新建构《春秋》的阐释方式的时候,仍然遵循了“精理为文”的要义,在经之传、经之纬一类的作品中,保存了“经”之“义理”。虽然这种“义理”,“传”与“纬”的侧重点可能会有差异,但基本上不偏离“经”之“义理”的主旨,从而使得后者也具有了“精理为文”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中国早期文本的主要书写方式,也是创造后世文化传统的基本原则。
二、“理隐文贵”与“经正纬奇”:《春秋纬》与《春秋》三传的文艺思想异同
从以上论述看,《春秋》及其三传作为“文”的一种体现,与《春秋纬》之“质”交互作用,呈现出一种新的“文”。而这种综合而成的“文”,除了具有文本书写上的“精理为文”特点,还具有刘勰所言“理隐文贵”与“经正纬奇”的特点。
就《春秋》而言,其意义本来是隐晦难明的。三传本欲对《春秋》的“微言大义”予以揭示,然由于新材料、新说法的出现,反而使得《春秋》的本意更加难以捉摸。《春秋纬》在三传基础上的进一步阐发,则使得《春秋》不仅具有了神秘色彩,而且使得其意义更加玄虚。由此可知,《春秋》与《春秋纬》其实皆具有意义隐晦的特点,然而二者也有区别:《春秋》意义之“隐”,属于记录者给后世阐释造成的一定解读困难所致;《春秋纬》之“隐”,则属于阐释者对《春秋》的神秘阐释所致。
刘勰《文心雕龙·正纬》曾称纬书“理隐文贵”,此说法对于《春秋》同样适合。那么,“理隐”何以“文贵”?兹以《春秋》与《春秋纬》为例,尝试说明。
“理隐文贵”,陆侃如、牟世金以为“内容深刻而文辞可贵”[注]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25页。。詹锳以为“图纬所讲的道理比较隐晦,而文辞可贵”,并引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以为有“象征暗示的隐喻”[注]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征圣》,第100页注释3。。就《春秋》而言之,我们不得而知孔子当初是否真的有特定的意义指涉或隐喻之意,但对于三传与《春秋纬》而言,这一点则是非常明显的。而从后世阐释者对《春秋》的理解来看,《春秋》之“微言大义”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从文献学角度看,《春秋》之“微言大义”存否是一个问题,然而从义理层面看,《春秋》及其三传与《春秋纬》皆有一定“理”存在,并且是隐晦的,具有象征、暗示的意义。
通过上文我们可知,如果将《春秋》及其三传作为“明”的一面,其“义理”也是明显的,且具有正面意义;《春秋纬》的“义理”则是隐晦的,且具有“负面”的“警示”意义。从文本写作方式上看,借用汉代辞赋“劝”与“讽”的说法,前者为“劝”,后者为“讽”。例如,上文“梁山崩”事,《春秋》三传皆视之为灾异,显然是从正面劝诫国君要礼祭山川之神以消除灾难。《春秋纬》则以神秘预测的方式,预言“六十年之中”将有“弒君十四,亡国三十二”的灾祸。如果说,《春秋》三传的劝诫属于一种“政之教”或“人之教”,《春秋纬》显然属于“神之教”,即借助“神之口”警示国君。这两种对“义理”的表达方式,无疑对后世文学或历史文本的书写具有直接影响。
另外,刘勰以为,“圣训宜广,神教宜约”,从上文可以看出,《春秋》三传之文无疑文辞繁富,而《春秋纬》之文一般只给出一种结论或者描述一种现象,没有具体的解释文字。
例如“梁山崩”事,《穀梁传》《左传》详细记录了伯尊(或伯宗)接受辇者(或绛人)的说法,并向晋侯建议礼祭山川之神。《穀梁传》还借孔子之口赞曰:“伯尊其无绩乎,攘善也!”《公羊传》虽无复杂的故事叙述,但也费尽笔墨去解释记录“梁山崩”的原因。《春秋纬》则不然,其在“梁山崩”后,直接下断语称:“自是之后,六十年之中,弒君十四,亡国三十二。”
再如《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详细解释了“元”“春”“正月”以及“不言即位”之意义;《穀梁传》解释了“正月谨始”与“不言即位”事。《春秋纬》以“黄帝受图有五始”(或“立五始”,见于《穀梁传》疏、《礼记·中庸》正义)概括之,非常简约,但内涵丰富。何休以“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解释之[注]《春秋元命苞》,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下册,第389页。,是知“五始”说之复杂。《春秋元命苞》中其他记载圣人异相、天地星辰、阴阳五行等文字,亦皆非常简约。
《春秋演孔图》《春秋合城图》记圣人异相、《春秋文耀钩》记地理山河或制度史官、《春秋运斗枢》记星宿帝德、《春秋感精符》记天变瑞应、《春秋考异邮》记灾异禳祸等等,皆如此类。即使具有叙事情节的文字,也是以简明扼要表达主旨大意为主,并不措意于故事情节的曲折展开。如《春秋合诚图》记载黄帝问太一事:“黄帝请问太一长生之道,太一曰:‘斋戒六丁,道乃可成’。”[注]《春秋合诚图》,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下册,第545页。这里只有“问”之内容与“答”之结果,至于黄帝如何问、太一如何答以及问答之后的事情,此处绝无涉及。按照陈望道的说法,这里应该属于“消极修辞”手法,即只关注意义的明确和题旨的表达。[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认为,修辞分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消极手法侧重在应合体旨,积极手法侧重在应合情境;消极手法侧重在理解,积极手法侧重在情感”。参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11页。鲁僖公祷请山川词也是如此。《春秋考异邮》记载:“僖公之时,雨泽不澍,至于九月,公大惊惧,率群臣祷山川,以六过自让,绌女谒,放下谗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诛领人之吏,受货赂赵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无生稼,寡人当死,百姓何谤,请以身塞无状也。’”[注]《春秋考异邮》,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下册,第566页。此又见于《穀梁传》成公七年疏,用于解释雩祭之礼。其中所言僖公“率群臣祷山川,以六过自让,绌女谒,放下谗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诛领人之吏,受货赂赵祝等九人”诸事,皆为“雨泽不澍”而设,并不涉及历史人物的褒贬或道德评价。这还是属于“主旨表达”而非“情感体验”。可以说,《春秋纬》的文献,皆欲通过“沟通天地之神”的方法,实现“神教”目的,进而达到文本的“政教”功能。这种文辞“简约”与“神教”功能,皆隐藏着特定的“义理”,纬书之“理隐”由此可见。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刘勰所言“经正纬奇”。毫无疑问,经文的正面表达,传达出明确的题旨与史实,其文辞之“广博”及其明显的“政教”功能,对战国秦汉儒家、法家、纵横家著作具有直接的影响。而纬书之隐晦表达,体现出深刻的义理、严密的思辨逻辑以及故事神奇、叙事委婉的风格,其文辞之“简约”以及“神教”功能,或者渊源于战国道家、墨家、名家思想,并与汉代著作保持着大体一致的文章风格。
三、“隐义藏用”与汉代文章之关系
按照姚永朴先生《文学研究法》的认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四部,主要分为说理、述情、叙事三类,而“经”三类皆备,乃子、史之源。同时,姚先生进一步认为,史书之叙事,即源于《尚书》《春秋》、三《礼》[注]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卷一《范围》,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23页。。此说有合理之处,然深入思考,则未必尽然。如《春秋》《左传》有叙事成分,然亦有说理成分;《公羊传》《穀梁传》《春秋纬》以说理为主,然亦有叙事成分。归结到一点,《春秋》三传与《春秋纬》,说理文献自不待问,叙事文献其实也以“说理”为主,但这种“理”,皆是隐藏在曲折的叙事之后。
从文本深层的角度分析,上文所言“经正纬奇”,有一个共同的深层文本特征,即二者皆蕴含着特定的义理,而这个“理”又皆是隐藏在特定的文字背后,隐而不彰的。所以,刘勰说:“《春秋》一字以褒贬……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又称图纬“神宝藏用”。[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征圣》《宗经》《正纬》,第16、22、31页。此处之“藏用”,属于经、纬之共同特征,也可说是当时“文章”之共同特征。[注]《易·系辞上》:“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周易正义》以为:“藏诸用者,谓潜藏功用,不使物知。”《诗经》中的“六义”,也有“藏用”的特征。按照詹锳等人的说法,所谓“藏用”,即“隐晦含蓄把作品的用意暗藏起来”[注]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第30页。。这一点,结合上文所谈《春秋》及其三传、《春秋纬》而言之,《春秋》之“大义微言”自不必说,三传对《春秋》之解读,实际上即暗含着特定的社会道德与秩序的构建,以及对政教功能的预设。虽然各书在表达上、文本写法上有差异,但其目的则是殊途同归。
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入汉以来,史家与诸子著书,皆自言上宗孔子之《春秋》”[注]孙少华:《〈孔丛子〈与秦汉子书学术传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页。。按照现代的话语来说,《春秋》三传与《春秋纬》甚至秦汉以后的其他著作,皆模仿孔子作《春秋》思想或笔法[注]汉代人著作,皆模仿孔子作《春秋》,司马迁《史记》、桓谭《新论》等皆有此类表述。《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0册,第4001页)王充《论衡·案书篇》称:“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可褒,则义以明其行善;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黄晖:《论衡校释》,第4册,第1172—1173页),大致采用含蓄、象征的手法,将文章“大义”及其功用隐藏起来。这就使得文章具备了“文”的意义,同时具有“质”的特征。另外,从“作者”或“述者”与作品内容的关系看,《春秋》及其三传与《春秋纬》中,“作者”的身影特别突出,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作者”在文本背后运用语言进行叙事、说理的影子,以及作者较为明显的文本动机(或称文章功能)。但某些时候,汉代文人大多会采用引经据典的方法,将文章意思委婉表达出来,其目的、作用和意义也隐藏在大量的叙述背后,“隐义藏用”的特征特别明显。这成为汉代文章书写的基本规范,同时也是汉代“文章”表达的主要方式。
关于《春秋纬》的成书,有人考证可能成书于汉平帝元始五年(5)之后,或者大体定于平莽之际(公元5-9年),由刘歆率“图谶之士”为之[注]徐栋梁:《〈春秋纬〉与汉代春秋学》,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这种说法,首先是将《春秋纬》中的“新五德终始说”定为出于刘歆原创,而非其继承自前人成说;其次,是确认《春秋纬》的文本在后世未被后人增窜。但无论《春秋纬》成书时代如何,它所具有的与《春秋》及其三传相同的文章“隐义藏用”的表现方式,则产生较早,并在先秦两汉一直存在。
从较为宽泛的层面说,汉代著作如与经有关的《韩诗外传》《焦氏易林》,与史书有关的司马迁《史记》,子书如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向《列女传》《新序》《说苑》、桓谭《新论》,以及汉赋、汉诗,以及司马相如、晁错、刘向、桓谭等人的奏疏、政论文等,皆具有“隐义藏用”特征。例如《新语》《新书》稍近《公羊》《穀梁》风格,《韩诗外传》借“子曰诗云”以阐理,《焦氏易林》借卦象变化以说理,《史记》借他人命运变化以藏“理”,《列女传》《新序》《说苑》《新论》借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以明理,汉赋、汉诗则将“理”隐藏在繁缛的文辞、委婉的表达之后。诸如此类,皆与“隐义藏用”有关。
在这一点上,汉赋的表现更为明显。汉赋对“藏用”方法的使用非常复杂。大致说来,主要有如下四种形式:
第一,使用铺采摛文、宏侈巨衍的方法,大量铺排文辞,将文章主旨隐藏在繁缛的叙述之后。例如枚乘《七发》,作品表面的意思,是从七个方面展开说理,“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为楚太子治疗疾病;隐含的主旨,则是意图借助他人之口,劝谏吴王刘濞“养生奉己,以求安康”。正如赵逵夫先生所言,此赋题名“七发”,实际上只有“六事”,最后的“要言妙道”只是提及,并未详细解释,“是一篇极含蓄的文字”[注]赵逵夫主编:《历代赋评注》(汉代卷),程度: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1、22页。。尤其是,《七发》中所列音乐、美味、良御、美景、校猎、交游六个方面,皆帝王享受之事,而太子竟对此熟视无睹。此赋隐含着希望太子珍惜所拥有的一切生活的主题,而枚乘骋辞以“藏用”的意图亦非常明显。可以说,在此赋中,“隐义藏用”的程度,较《春秋》及其三传、《春秋纬》更深。
第二,采用拟人化手法,将文章主旨隐藏在一个虚构的故事之后。贾谊的《鵩鸟赋》,更是借助鵩鸟之口,以拟人化形式,表达出“万物有终”以及“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的道理。江苏东海尹湾出土汉墓竹简《神乌赋》、赵壹《穷鸟赋》、祢衡《鹦鹉赋》,亦属此类。这种借助动物之口阐明道理的写法,与汉代纬书之“奇诡”的特征非常近似。
第三,以托物言志形式,传达特定的政治、社会道理。此类赋作如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王褒《洞箫赋》、马融《长笛赋》、蔡邕《青衣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以及班固《两都》、张衡《二京》诸赋,甚至扬雄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皆可归入此类。
第四,主客问答形式,将文章主旨隐藏在作品人物的问答之中。此类赋作,非常近似于《公羊传》中的自我设问、自我回答的形式,如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张衡《释诲》、包括后来崔骃《达旨》、郤正《释讥》等,皆属此类。
当然,汉赋“藏用”的种类不尽上述四种,但其中体现的文学特点已经非常明显:
第一,内容上扩大了描写的对象和范围。《春秋》及其三传、《春秋纬》基本上以社会政治为中心,说理、记事也是以此为主。汉赋则从社会政治衍生开去,从个人遭际、国家命运到日常生活、京都园囿、皇家校猎、自然风景,从题材上大大拓展了“文章”的书写内容。
第二,形式上更加注意修辞方法的使用。与《春秋》三传相比,汉赋说理的方式更为委婉。即使都是“作者”在作品中的声音较为突出的情况下,汉赋“讽谏”“劝诫”的表达方法,显示它已经比《春秋》三传更加注意修辞。这是“经”与“文”的一大区别。
第三,“情感”作用的介入。《春秋》及其三传、《春秋纬》主要以理、事为中心,而汉赋除了具备理、事之要素,还有“情感”作用的逐渐加强。这主要体现在汉赋通过铺排大量词句的方式,于叙述中蕴含着作者丰富、真实的情感,已实现作者说理的目的。理、情、事的综合使用与统一,是汉赋(甚至包括汉代诸子文章、汉诗、政论文、史书)作为“文章风格”的一大变化。如果说《春秋》及其三传与《春秋纬》一类的书籍属于“理隐事后”,此时汉赋之类的作品,已经变为“理隐情后”。
第四,内容、形式、情感的有机统一,是汉赋作品有别于经、纬的主要标志,也是判定优秀文学作品的基本标准。
综上所述,文章风格的变化,与政治需要的变化、时代思潮的变化紧密相关。如果说《春秋》及其三传产生在思想活跃的时期,其表达的方式会更直接、更清楚,说理、叙事的比重自然大一点。而当社会发生重要变化的时候,尤其是易代之际,大乱初定之时,文章的表达方式可能会更为委婉一点,“情感”的要素自然会介入进来。汉赋文学性质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可以说,从“经”之“精理为文”,到“纬”之“理隐文贵”,再到与经、纬具有共同文章特征的“隐义藏用”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先秦两汉“文章”内容、形式的演变轨迹,于此清晰可循。而先秦两汉“经纬成文”在文学演变中的意义,还有值得深入讨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