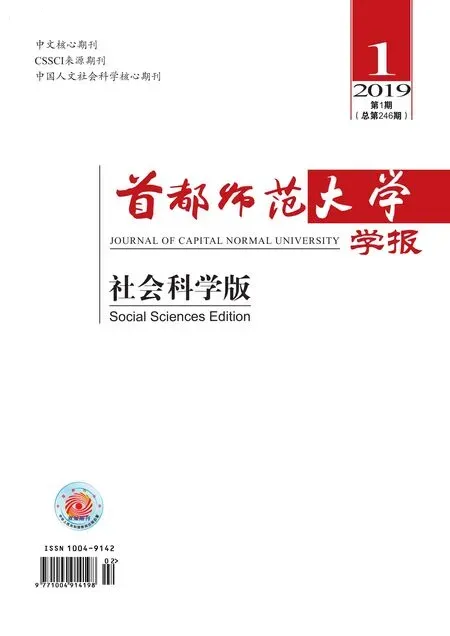边军与明中叶北部边镇的社会秩序
——以《赵全谳牍》为中心
2019-03-12邓庆平
邓庆平
一、引言
隆庆五年(1571),明蒙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许以互市,这就是著名的“俺答封贡”与“隆庆和议”。作为开放互市和交换俺答汗爱孙把汉那吉的条件,明廷也得到了俺答汗缚献的“中国叛逆”赵全、李自馨、王廷辅等九人。对于赵全等人的获擒,穆宗曾感慨:“叛逆元凶,频年纠虏入犯,荼毒生灵,罪恶滔天,仰赖上天锡佑,宗社垂庥,虏酋效顺,执缚来献,足洩神人之愤。”[注]《明穆宗实录》卷52,隆庆四年十二月丁酉,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版,第1293页。可见明廷对赵全等人忌恨之深。
上述事件在明代历史中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因而,对于隆庆和议及其前后的明蒙关系、互市贸易等重大问题,学界给予了充分的讨论[注]几乎所有关于明代蒙古史和明蒙关系史的论著中,都有涉及“隆庆和议”与明蒙互市贸易的相关论述。择其要者,如[日]和田清:《东亚史研究·蒙古篇》,日本东洋文库,1959年版,中译本《明代蒙古史论集》,潘世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美]Henry Serruys,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Ⅲ:Trade Relations:The Horse Fairs (1400-1600),Brussels:Institue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1975,中译本《明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王苗苗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第二、六、七章,台北:政治大学出版委员会,1977年版;[日]萩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日本同朋舍,1980年版;杨绍猷:《俺答汗评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黄丽生《由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归绥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14世纪中至20世纪初)》,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5年版;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于默颖:《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相关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计其数。。作为隆庆和议重要内容的赵全等叛逆被擒送朝廷一事,在上述各类研究成果中也多有提及,主要集中在概述丘富、赵全等自山西出边到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驻地,屡屡“纠虏犯边”,招徕汉民垦殖土地,逐渐聚居丰州滩一带,形成蒙汉聚居地“板升”的历史过程[注]除上述论著的相关章节外,徐凯曾撰写《赵全其人》(《北大史学》1999年00期,第233-239页)一文,也是集中讨论赵全出边后在俺答部中的活动,并评述其历史功过。。总体而言,赵全等人出边叛降的“后果”——经营板升、纠虏掠边、被俺答缚送明廷以及最终促成“隆庆和议”,明代史料记载丰富,学界也关注较多;而事件的“前因”——赵全众人出边前北部边镇的社会秩序、赵全等人的身份、为何以及如何出边,却鲜少有人论及。这当然是受史料所限[注]明代史料对于赵全等人出边后的活动情况记载较为详细,如高拱《伏戎纪事》、方逢时《云中处降录》、刘绍恤《云中降虏传》、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等,但对赵全等人的身份、叛逃经过却记载得非常简略。,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在于学者对于赵全等人叛降俺答部前因与后果的意义的重要性有不同认识。
赵全等人被缚送明朝后,宣大总督王崇古及明廷有关部院官员对各犯进行审问,将讯问结果汇集成一件完整的文献——《赵全谳牍》[注]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117页。看谳牍的行文,应是时任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会同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大理寺右少卿郜光先、兵部尚书郭乾、锦衣卫掌卫事后军都督府左都督朱希孝等一起审问。据《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编者考证,四库存目据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著录,今本卷末有顺德李文田手书题记,知抄自明抄本。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影印清光绪年间顺德李氏读五千卷室传抄明抄本,《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据该版本校点收录,本文使用该校点版。。谳牍全文虽仅有数千字,却记录了赵全及涉案多人的身份、家庭背景、叛降经过以及在俺答部中如何经营等详细情况。通过对这些叛人身份和出边经历的细致勾勒,可以考察明中叶,尤其是隆庆和议之前北部边镇社会的诸多面向。边镇地区复杂的军事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军人身份的多元性、流动性,在频繁边患中艰难求生而形成的诡谲人情和族群身份的不确定性,明蒙走私贸易的长期存在形成的商业传统,秘密宗教的民间传播及因此勾连起的社会网络,这些内容是解释赵全等人叛降蒙古事件的区域社会历史脉络或“地方性知识”。
赵全等人的叛降与被缚送回明廷以及最终促成明蒙关系的转变,是明中期被朝廷视为大患的“北虏”问题的组成部分。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学界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已有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前,如何还能对明中叶的“北虏”问题提出新的理解?赵世瑜师曾指出,同样被明廷视为大患的“南倭”问题,已被置于明中后期海上贸易发展的大背景下重新诠释,而“北虏”问题却仍在传统的游牧民族南侵与明蒙关系的解说框架内进行阐述。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可以从“内陆史视角”进行重新思考,使其成为16世纪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注]赵世瑜:《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收入氏著:《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154页。。此论确为卓见,提出了重新解释明代“北虏”问题的新角度,具有宏大的理论视野。赵师在讨论“隆庆和议”前长城内外的走私贸易传统时,已经注意到“明代的边军这一双边贸易的特殊媒介,他们与塞外汉人及与原籍商业网络的关系”,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可惜并未展开论述。笔者以为,这可能不仅仅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课题,在复杂的明代边镇军事体制下,边军的身份、生存境遇、谋生活动,构成了明中叶北部边镇社会秩序和结构性问题的主要内容,也因而成为考察明代“北虏”问题不可或缺的视角。《赵全谳牍》中所述之史实,恰好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生动的个案和讨论的起点。
二、边军身份与明中叶北部边镇的军事体制
对于赵全等人出边的经过及在俺答部中的作为,《明穆宗实录》有如下简略的交待:
虏执我叛人赵全、李自馨、王廷辅、赵龙、张彦文、刘天麒、马西川、吕西川、吕小老官等来献。初,赵全与丘富从山西妖人吕明镇习白莲教,事觉,明镇伏诛,丘富叛降虏。全惧,召其弟龙、王廷辅、李自馨,从富降俺答侄,边外古丰州地居田作,招集中国亡命,颇杂汉夷居之,众数万人,名曰“板升”。俺答授全等皆为酋长。丘富死,全等益用事,数引虏入犯,破城堡,杀吏卒,无岁不至,边境苦之。已而,试百户张彦文、游击家丁刘天麟(作者注:“麟”应为“麒”之误)、明镇子吕西川及边民马西川、吕小老等先后降虏,与全等皆居板升。[注]《明穆宗实录》卷52,隆庆四年十二月丁酉,第1292页。
相比实录中的记载,《赵全谳牍》所述各主要案犯的身份和出边经过更为详实,笔者将谳牍中涉及人物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整理,汇总为下表,以便后文的讨论。[注]表中的相关信息均据《赵全谳牍》整理得出,部分内容略有精简。

姓名身份出边情由周元湖广黄冈县人,因在本县书写,积年害民,问发大同威远卫充军,拨赴本边守墩。嘉靖二十四年(1545),叛投虏地。丘富大同左卫舍余①跟随吕明镇传习白莲教,事发,吕明镇被处决,丘富恐被缉拿,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投入俺答部下,用为头目。赵全山西行都司云川卫右所已故百户赵雄下余丁 与丘富一起跟随吕明镇传习白莲教,事发后,仍在左卫四峰山村居住。嘉靖三十四年(1555),有本村人声言要将白莲教禀官,赵全慌惧,遂领妾李氏、二子三女、弟赵龙等二十余口,由宁虏堡师家口出边,一同投顺俺答男铁背台吉部下为兵。 张彦文被掳走回,通晓夷语,投充大同正兵营通事,有功升大同后卫后所试百户。嘉靖三十二年(1553)六月初五日,大同总兵官岳懋领兵至灭虏堡巡边,偶遇大举达虏入境,张彦文卖阵媚虏,将军情泄与熟识虏酋,致岳懋并五百余名官军战死,张彦文仍回该营领兵,莫敢举发。嘉靖四十年(1561)十一月,张彦文跟随时任大同总兵刘汉前往平虏、汤西河等处,与贼对敌,见得贼众,又因素日卖阵媚虏得计,恐事败露,于是丢弃弓矢出边,投入俺答部下,升为头目。李自馨山西大同府应州山阴县富安坊民与赵全一同出边王廷辅山西大同府浑源州黎园里民与赵全一同出边刘天麒陕西延安府府谷县民,投老营堡游击李应禄作为家丁。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因李应禄剥削军粮及严行捆打,率犯陈世贤、王麒等,持刀杀伤李游击,各骑官马,带领一百三十余口于老营堡丫角山出边,投入俺答部下,送发板升住种。吕西川吕明镇子因父为白莲教首,惧罪不敢回籍,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率四十余人投赵全部下。杨一休陕西西安府民,因艰难投偏头关应军食粮,拨在高民墩哨备。隆庆三年(1569)二月,与虏交通,货换马尾,事发,由本墩出口叛投虏营。认吕西川为兄,号称吕小老。马西川阳和卫左所已故百户余丁马四子隆庆四年二月,因与榆次县人李孟阳出边货换马尾,投入赵全部下,往来传泄边情与贩货物图利。①关于丘富的身份,《赵全谳牍》缺载,《万历武功录》中有记,见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中三边·俺答列传中》,《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页。
从上表不难看出,除李自馨、王廷辅及吕西川外,其余诸人在出边前都具有军事身份,可细分为山西行都司辖各卫所军户、大同镇营兵、将帅家丁三类。[注]关于明代的家丁,学者多将之视为不同于卫所军、营兵、民兵之外的另一军种,如赵中男:《论明代军队中家丁的特点与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3期,第144-149页;赵中男:《论明代军事家丁制度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其发展》,《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2期,第86-90页;马楚坚:《明代的家丁》,收入氏著:《明清边政与治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162页。但也有学者将家丁与标兵、营兵、守城兵、瞭侦兵、通事一并归入“明代省镇营兵制下的军队”,见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2页。前者有大同威远卫军周元、大同左卫舍余丘富、云川卫右所余丁赵全、大同后卫后所试百户张彦文、阳和卫左所余丁马西川,第二类有大同正兵营通事张彦文、偏头关营兵杨一休,第三类则有老营堡游击李应禄的家丁刘天麒。这几种身份,在明朝军事制度中虽然各自属于不同的系统,但因其共同的军事身份则大体可以归入边军一类,他们的身份恰好可以反映明朝边镇军事体制的变化过程和复杂性,方逢时对这一变化过程表述得非常清楚:
洪、永以后,虏患日棘。大将之设,遂成常员。镇守权重,都统势轻。卫所精锐,悉从抽选。于是正、奇、参、守之官设,而卫所徒存老家之名。此边兵之初变,所繇以始弱也。历年既久,大将或不得其人,训练无法,纪律舛谬,士马之死亡者不补,逃散者不复。尺籍徒存,部曲虚耗。间有健将,急治目前,或扣官饷,或捐私财,召募勇壮,优加恩养,多者千人,少者数百,名为家丁。[注]方逢时:《审时宜酌群议陈要实疏》,《大隐楼集·补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页。
大致而言,明代军事体制可以分为卫所军制与营兵制两类,因而军人身份也就有了“军”与“兵”的区分。[注]吴晗:《明代的军兵》,收入氏著:《读史札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92-141页;王莉:《明代营兵制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第85-93页;方志远:《明朝军队的编制与领导体制》,《明史研究》第3辑,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35-44页;范中义:《论明朝军制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29-139页。对于营兵制,又可分为京营兵制与明中后期盛行于京师以外的省镇营兵制两类。[注]对于京师以外地区盛行的营兵制,学界有不同的称谓:或曰“镇戍制度”,见罗尔纲著:《绿营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页;或曰“镇戍营兵制”,见陈高华等总主编、刘昭祥分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军事组织体制编》,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86页;或曰“省镇营兵制”,见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第1页。卫所军为世兵制,营兵的来源则比较复杂,既有卫所军士,也有募兵。根据前辈时贤对于明代军制史的研究可知,洪武年间卫所制度广泛推行于全国,永乐以后卫所编制逐渐受到破坏,京营和省镇营的编制先后形成,并逐渐得以发展,但卫所军与营兵的双轨制一直持续到明朝结束,到清朝军制改革才发生彻底变化。在边镇地区,由于战乱频繁,将帅又往往私募家丁,作为自己的亲兵,并在历次战斗中发挥了奇效。
具体到大同地区,从军事建制来看,有山西行都司和大同镇的两套体系。大同一带的军卫原隶大同都卫,洪武八年(1375),大同都卫改为山西行都司,至清初始废。山西行都司下辖卫所“设废频繁”,至成化年间,其军事辖区稳定下来,统辖卫所有:大同左卫、大同右卫、大同前卫、大同后卫、朔州卫、镇虏卫、安东中屯卫、阳和卫、玉林卫、高山卫、云川卫、天城卫、威远卫、山阴所、马邑所、平虏卫、井坪所,共计14卫3所。[注]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275页。至于大同镇,虽然学界对大同成镇的时间还存在争议,但一般认为至永乐七年(1409), “置镇守总兵官,佩征西前将军印,驻大同,专总兵事,江阴侯吴高始专任。于是,大同称镇”[注]尹耕:《两镇三关志》卷9。(嘉靖)《山西通志》、(顺治)《云中郡志》也采用此说。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大同建镇于永乐十二年(1414),参见赵现海:《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上册,第300-302页。。作为九边之一的大同镇,其镇戍营兵体制下又分为标兵、营兵、守城兵、瞭侦兵、通事与家丁等多种类别。大同建镇,是依托山西行都司而设,各卫正军和舍余来自山西行都司,营兵则来自于招募普通民户或抽选自卫所军户。因而,山西行都司与大同镇的双重建置互有重叠,如万历《山西通志》所述:“国初,大同止设都司,以故军马属卫。至洪熙以后,始设总兵、副、游等官,粮虽系卫,而军马列伍易卫以营。”[注](万历)《山西通志》卷25,《武备下·将士·官军》,收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4册,第474页。
赵全案中有几位主犯是卫所军户,其中有三人,特别是本案的主要案犯赵全、丘富,均为军余,另有一人为谪发从军,一人为通事因有功擢升为试百户,他们分别来自于大同左卫、云川卫、阳和卫,皆为山西行都司统辖卫所。值得注意的是几位主犯的军余身份。按照明代制度,军户例不得分户,其户下人丁除正军以外均为余丁。他们不论是留居原籍、同居卫所或寄籍州县,都有帮贴军装、继补军役之责。有明一代,对于军余的管理方式也在不断调整,到明中期以后,改变明初的“原籍主义”原则,对于在卫所附近州县购置田产的军余,允许一人附籍纳粮,是即所谓的“附籍军户”,其余则在卫所当差,所谓“在卫立籍”。但州县对附籍军户的管理权极为有限,他们除纳粮外,只需承担极少的民差,甚至有各种方法逃避差役。而在卫余丁,虽按制度规定应尽数造入卫所军册,但明中后期的军册审编多因循守旧,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注]可参见于志嘉:《论明代的附籍军户与军户分户》,载《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0-104页;《帮丁听继:明代军户中余丁角色的分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4本第3分,2013年,第455-525页。。因而,不管是卫所还是州县,对于数量庞大的军余群体,都不容易进行实质有效的管理,相比起有军役任务的正军而言,军余有着更大的流动性。
具有边军身份的另外三人中,除一人是因生计艰难主动投军被派去守墩外,另外两人的身份值得注意,一人为通事,一人为家丁。通事为翻译,在边镇多充当向导和尖兵,他们大多是从蒙古驻地逃回的汉人,因其通晓“夷语”,了解“夷情”,成为明政府招徕和安置“走回人”的一大去向。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兵部题准“有自虏中逃回者……收作通事,给与月粮”[注]《嘉隆新例》卷4《兵例》,《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67册,第234页。。能够支领月粮,可见也被纳入正规的边军体系中。家丁则是将帅所领之亲兵,在边镇尤为常见,多为边将私募,如嘉靖年间的大同总兵梁震“素畜健儿五百人……前后百十战,未尝少挫”,梁震死后,其家丁编入营伍,“边将犹颇得其力”[注]《明史》卷211《列传第九十九·梁震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578页。。在嘉靖中期以前,家丁由将帅私人出饷供养,以后则由官府发放粮饷,成为募兵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仍有将帅以私财豢养忠勇之家丁者。
综上,《赵全谳牍》所涉及的多位案犯都是军人,他们的身份来源和入伍经历,反映出明中叶边镇多重的军事体制。在这多重体制下,无论是卫所正军、军余,还是普通民户,都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成为边军的一员。他们有些是世袭身份,有些则是因为各种原因主动投军。明中叶由于边患频仍,如大同一带的北部边镇也就大量增加各类军事人员。他们获得边军身份后,也就将自己的生活、生计与边镇多重的军事体制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
三、边军的生存境遇
如上文所述,《赵全谳牍》所涉案犯多为来自不同军事系统的边军,谳牍中对他们的出边缘由与经过又有较为详实的描述。因而,通过解读《赵全谳牍》,我们可以对明中叶边军的生活境遇有更多了解,本节仅从谳牍中涉及的内容,尝试做以下几个方面的讨论:
(一)边军与白莲教
据谳牍所记,主犯赵全、丘富二人皆曾跟随吕明镇传习白莲教,正是因为惧怕传教被政府缉捕才叛逃出边,而吕明镇之子吕西川则是因父传教之罪而叛投赵全部下。吕明镇是嘉靖时期活跃在大同一带的白莲教头目,大同巡抚方逢时在其《云中处降录》中记载:“嘉靖三十年(1524),妖人吕老祖(即吕明镇)以白莲教惑众,构祸于山西、大同之间,有司捕之急,叛投彼中。”[注]方逢时:《云中处降录》,《大隐楼集》卷16,第266页。白莲教徒因被政府缉捕或惧怕被捕而叛逃到蒙古部落,这是明中期出边汉人中比较常见的一类情况。
对于明朝白莲教的历史,已经有很多学者做过相关研究。[注]如[日]野口铁郎:《明代白莲教史の研究》,东京:雄山阁,1986年版;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黄景添:《白莲教与明代建国》,香港:中华书局,2007年版;[荷]田海著,刘平、王蕊译:《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等。另外,在各类中国民间宗教史的总论性论著中,也有大量涉及白莲教史的内容,如谭松林主编,连立昌、秦宝琦著:《中国秘密社会》第二卷《元明教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马西沙:《中国民间宗教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具体到明代中叶北边地区的白莲教活动,则有[美]卡尼T·费什著、张宪博译:《天花、商贾和白莲教——嘉靖年间明朝和蒙古的关系》,《明史研究》第4辑,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31-241页;董琦:《明代嘉隆时期白莲教活动研究——以明代北边大同地区为中心》,黑龙江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但是,主犯赵全、丘富所揭示的卫所军户参与白莲教活动的情形,恐怕不是个例,而现有研究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些参与白莲教活动的卫所军人,有些是因传习白莲教而被朝廷谪发充军,如正德年间山西太原府崞县人李福达就因传播白莲教,事发后被先后谪发山丹卫、山海卫永远充军,后因隐藏身份,发财致富,甚至纳银捐得了山西太原左卫指挥使职衔,且一直私下传教。[注]李福达案件始末,可参见不著辑者:《钦明大狱录》,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1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37-717页。有一些则是长期隐匿于卫所体系内的教徒,如嘉靖二十四年(1545),大同地区发生了明朝宗室成员朱充灼与白莲教首领罗廷玺联络蒙古小王子发动叛乱的事件,而罗廷玺的白莲教组织成员中就有许多卫所军余和各类逃兵。[注]参见董琦:《明代嘉隆时期白莲教活动研究——以明代北边大同地区为中心》,第19-22页。如果按照荷兰学者田海(Barend ter Haar)对于“白莲教”概念的解构,到明清时期,“白莲教”已经逐渐成为模式化的邪教与叛乱意义的标签,是官方和文人逐步建构的概念,那么明朝史料中的各类以“妖言惑众”的“妖僧”,大多在明中期以降的官方文件中被逐渐视为了白莲教徒。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将更多的各类“左道邪教”活动与卫所军户相关的事例纳入到考察范围中来。
早在宣德年间,山东文登县的“妖僧明本、法钟”等人,“皆栖霞县太平寺僧,以化缘至成山卫,依百户朱胜,因涂改旧领敕谕度牒,为妖言惑众,诈称转轮王出世”,后于宣德五年(1430)被擒获。[注]《明宣宗实录》卷61,宣德五年正月戊申,第1444页。英宗登基之初,就有“妖贼张普祥”自号“七佛祖师”作乱,张普祥本系“真定卫军,以妖书惑众, 潜居井陉县, 自号七佛祖师, 遣其党往河南、山东、山西、直隶等处度人”[注]《明英宗实录》卷12,宣德十年十二月己亥,第216页。。田海根据《宁夏新志》和胡适《跋〈销毁真空宝卷〉》等文献,认为明前期,在重兵防守的边境地区存在着活跃的民间佛教以及各种宗教团体,它们在军队中也有一定的信徒。[注][荷]田海著,刘平、王蕊译:《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第140-142页。当然,更为学者所熟知的明代民间教门——罗教,其创教始祖罗清,或曰罗梦鸿,其身份就是密云卫军,而传习罗教者也多数是承担漕运任务的运军。创教于明中叶,直到20世纪40年代被李世瑜先生“发现”后进入学者研究视野的黄天道教,在华北乡村有着相当广泛的传播和影响。该教的创始人李宾也是卫所军人,其墓志中说:“祖原籍万全左卫,后揆兑本堡。”[注]李世瑜:《现在华北秘密宗教》,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国立四川大学史学系联合印行,1948年版,第15页。“本堡”即宣府万全右卫的膳房堡,位于野狐岭长城脚下,是个军事堡寨,明朝在此堡居住的多为卫所军士及其家属,以及其他到此屯垦的戍卒、配犯。[注]相关研究可参见曹新宇:《明清民间教门的地方化:鲜为人知的黄天道历史》,《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25页。
从上述例子来看,从明初以来,由于从事秘密宗教传播而被发配卫所充军、因惧怕缉拿而避入军中或依附武将自保、又或因卫所军队组织为秘密宗教的传播提供了现成的社会网络等便利条件,在多重动因和不同路径的合力之下,包括边军在内的明朝军队系统中有不少民间教派的教首和信徒,应是不争的事实。
(二)边军的生存困境
谳牍中的另一案犯刘天麒,本为陕西延安府府谷县民,投老营堡游击李应禄为家丁,因遭李应禄剥削军粮并严行捆打,于是击伤李应禄后率众出边。虽文字极为简略,却可见明中叶边军的凄苦境遇之一斑。邱仲麟新近发表的论文,以丰富的史料展示了明代北边墩军的困苦生活,如军官私役、克扣军饷、军需物资不能如实领用等问题,揭示了明代中后期边军生存困境的普遍状况。[注]邱仲麟:《边缘的底层:明代北边守墩军士的生涯与待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第147-182页。
明初,全国普设卫所,每卫拨军屯种,屯田子粒用以养军,但军屯制度的颓坏也很快发生,前辈学者对此已有详尽研究,在此不予赘论。具体到边镇地区,边将占夺屯田和卫所以外的耕地、私役屯军的现象极为严重。正统以后,边镇将领“广置庄田,私役屯军……又纵下人占种膏腴屯田,是致军士怨嗟,兵政废弛”[注]《明英宗实录》卷103,正统八年四月丙戌,第2075页。;弘治年间,大同镇将官“役军士多至千人,侵屯地动以万计”[注]《明孝宗实录》卷145,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壬寅,第2534页。。这类记载在明中期史料中可谓俯拾皆是。[注]更多事例可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下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04-338页。
由于屯粮不能保障军士的供给,边军粮饷又仰赖民运粮、开中盐粮和京运年例银。但随着明代中期边患频仍,军费开支快速增长,国家财政危机严重,导致边储日虚,边军粮饷普遍不足。[注]可参见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308页。宣、大二镇甚至一度出现军饷“经年未支”的情形。[注]《明世宗实录》卷3,正德十六年六月丁酉,第126页。而将官还往往克扣军饷,如弘治十一年(1498)刑科给事中吴世忠题奏大同边情时说:“大同边境视他镇为尤重,大同边储视他镇为尤废……边粮折银,尽当给军,管粮郎中每石克银二钱以待他用……管粮者以多克为功。”[注]《明孝宗实录》卷145,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壬寅,第2533-2535页。魏焕在《皇明九边考》中这样论及宣府镇边军粮饷欠缺的情形:
按边军月饷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边者折银七钱,在内者折银六钱……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价腾踊,边臣苦于蓄积之未多也,则固与之折银……当其腾踊也,银一钱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银犹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饥而疲且至死也![注]魏焕:《皇明九边考》卷4《宣府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 齐鲁书社,1996年版,史部,第226 册,第59页。
所论虽是宣镇,但边镇情况大多类似,所谓“此诸边之通例也”。大同军士久受拖欠军粮、米价昂贵之苦,而大同守将又“抚驭失宜”,驱使军士修堡筑边,役重差繁,使得军中怨气沸腾,最终酿成嘉靖三年(1524)和嘉靖十二年(1533)的两次大规模兵变。[注]关于大同兵变的经过,可参见萩原淳平:《明代嘉靖朝の大同反乱とモンゴリア:农耕民と游牧民との接点》(上、下),《东洋史研究》,1972年,第30卷第4号,第30-54页,第31卷第1号,第64-81页;方弘仁:《明嘉靖朝五次兵变初探》,《明史研究专刊》第5期(1982年),第63-82页;赵立人:《嘉靖大同兵变述论》,《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30-34页,第40页。这两次兵变虽因大同巡抚张文锦、大同总兵李瑾先后役使军士修堡、浚濠且督工严苛直接引发,但也与边军久积之怨气有着紧密的关联。从史料记载来看,在嘉靖三年的第一次大同兵变发生之前,嘉靖元年(1522),由于“宣、大两镇连岁凶荒,军粮久缺,米价腾贵”,已经出现了宣府军士“鼓噪求粮,几至为变”的危局。[注]《明世宗实录》卷11,嘉靖元年二月甲午,第411页。同年七月,以张的祥为首的大同军士以粮饷未给,聚众鼓噪,嘉靖帝不顾兵部“抚处”的建议,下令将张的祥等为首五人于军前斩首示众,其余则调极边哨守,以为惩戒,使大同军士的积怨更深。[注]《明世宗实录》卷16,嘉靖元年七月甲子,第512-513页。最终,两次大规模的兵变相继发生。事后,参与兵变又未被明廷缉获的军士,多出边叛逃至俺答部中。
(三)汉、“虏”难辨
据谳牍所载,案犯张彦文曾被掳到蒙古部落,“走回”后因“通晓夷语”投充大同正兵营通事,有功升大同后卫后所试百户。在嘉靖三十二年大同总兵官岳懋领兵与蒙古人交战之时,因出卖军情给熟识的蒙古首领,致岳懋并五百余名官军战死。后因惧怕此事败露,于是再次出边,投入俺答部下。张彦文是明朝边镇社会存在的大量“走回人”之一,他的人生经历也显示出这一时期明蒙交界地区族群身份的流动性和复杂性。
大同地处明蒙交界的前沿地带,双方的人员流动非常频繁,既有蒙汉人民自发的双向流动,也有明朝政府的纵使和制度层面的原因。
蒙古人入塞多以劫掠为目的,除被明军俘虏外,也有蒙古人自愿来到内地归降者,所谓“不独华人接踵而来,夷种亦多举帐效顺。节据降人传报,虏中诸人节将臣招降牌谕密相传记,或相对感泣。故一岁之间,归降数逾二千有奇”[注]王崇古:《核功实更赏格以开归民向化疏》,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316,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51页。。 “降夷”是明代北边将帅家丁的重要来源,边将在历次边境战争中,逐渐召降了一大批骁勇善战的蒙古人,收为自己的私人武装,如王崇古所说:“各边纳真夷人之降,以充家丁冲战之用,行之已久。”当然,降明的蒙古人中也有诈降者,实为蒙古人派出的间谍情报人员,即“真虏每有诈降窥伺,旋即逸去,往往谂我虚实,为虏向导,反贻边患。各将领利其骁健,喜为招纳,而不虞其后”[注]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317,第3365页。。
汉人出边者,身份非常复杂,有被掳掠到蒙地者,也有贫民主动出边者,还有《赵全谳牍》中涉及的叛卒和白莲教徒。他们中不少人成为蒙古人掠边的向导或哨探、间谍,甚至因颇有才智受到蒙古贵族的器重,成为蒙古诸部对明朝战争的重要参与者,如赵全之流。所以胡宗宪才有“臣闻虏寇之入境也,鸱张乌合,动号十万,然其间真为彼之种类,劲悍难当者,才十之四五耳,余皆吾中国之赤子”的感慨。[注]胡宗宪:《题为陈愚见以裨边务事疏》,《明经世文编》卷265,第2801-2802页。但与此同时,出边汉人也有重新返回汉地的情况,按照万历年间御史沈涵的说法,可以分为“归正人”与“走回人”两类,即“内地人叛去复回,名为归正;被虏逃回,名为走回”[注]《明神宗实录》卷56,万历四年十一月己卯,第1283页。。如果宽泛一点理解,两者都可以视为“走回人”,明代的史籍中还有对于这类人员各种类似的称呼,如逃回人、回乡人、归乡人、脱归人、逸归人等等。[注]关于明代“走回人”的界定,可参见赵茜茜《明代“走回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3-14页。明廷对于这些“走回人”实行招徕政策,主要的安置方式是将之编入边军,特别是在边患严重的正德、嘉靖年间,更是大量起用走回人,充入军伍,与蒙古人作战。如正德四年(1509)四月,“令被虏走回男子,审无父母妻室,并不知乡贯者,听编入军伍,调用杀贼”[注]《明武宗实录》卷49,正德四年四月丙戌,第1127页。。甚至还将走回人用作明廷的间谍人员,遣回“虏地”,诱降出边的汉人或探听“虏情”。如嘉靖元年五月,兵部令各边镇巡官在那些出边日久、“谙晓虏情”的走回人中,审得“忠实有才略”者,“即留边效用,厚加慰劳,以备咨访,因而资为间谍,诱我汉人,使渐逃归,以孤虏势”[注]彭泽:《论待归正人疏》,《明经世文编》卷99,第869页。。所以王崇古才说:“此辈既能通虏,可为虏用,亦可为我用。此辈虽鲜忠勇,颇谙虏情,因用为间,亦可得力。”[注]王崇古:《禁通虏酌边哨以惩夙玩疏》,《明经世文编》卷316,第3348页。在出塞的汉人中,本也有被明廷派出常驻蒙古部落中的间谍,如“哨探”者,即“皆诈逃其地,俾与逃叛人民杂处”,寻机诱降出边军民并打探敌情虚实。[注]魏时亮:《题为圣明加意虏防恭陈大计一十八议疏》,《明经世文编》卷371,第4013页。
因此,明中期北部边镇明蒙之间的边界并非那么明晰和不可跨越,明蒙之间的人口流动异常频繁,而明廷招抚、纳降、行间等政策,使得这些不断流动、改变身份的人拥有了很多不同的身份标签,如“降卒”、“达官”、“达臣”、“虏”、“民”、“军”、“中国赤子”、“诸逆”、“奸细”、“归民”、“间谍”等,同时也给这批在边境流动的人提供了改变其身份的各种途径。
四、边军生计与边镇的商业传统
《赵全谳牍》中提及因生计艰难投军的杨一休与阳和卫左所余丁马西川,皆因“与虏交通”,出边“货换马尾”,事发后叛逃蒙古,投入赵全部下,并一直“传泄边情和贩货物图利”。这二人的出边缘由与牟利活动,揭示出边军参与到明蒙边境私市贸易的史实。
对于明朝北部边镇的明蒙贸易问题,学界已经有了非常多的研究,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可知,在整个有明一代,明蒙之间除时断时续的官方互市贸易外,还长期存在着民间的私市贸易。作为明蒙交界前沿地带的大同地区,北控边鄙,是拱卫京城安危的锁钥之地,又因“无山设险”,紧邻河套,易攻难守,成了蒙古人入掠塞内的“必窥之路”[注]魏焕:《皇明九边考》卷5《大同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6 册,第61 页。。所以,大同一带的明蒙私市现象一直非常严重,戍守边镇的武将、边军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早在正统年间,朝廷就发现瓦剌使臣大多带有兵甲、弓矢、铜铳等物,查询其原由,“皆大同、宣府一路贪利之徒私与交易者”,因此敕令大同、宣府总兵等官对这类事情严加禁约。[注]《明英宗实录》卷135,正统十年十一月庚寅,第2689页。能够拥有兵甲、弓矢、铜铳等军备物资,显然这些“贪利之徒”中相当一部分是宣、大地区的边军。明政府虽然一直严禁对蒙古走私武器的行为,但收效并不大。弘治十年(1497),大同“总兵神英、巡抚刘瓛、守臣孙振,贪和畏威,纵虏交易,锅、锹、箭、簇,悉入虏囊”[注]方孔炤:《全边略记》卷2《大同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38册,第250页。。弘治十一年(1498),大同前卫指挥佥事刘桂因私自卖给蒙古人武器而被枭首示众[注]《明孝宗实录》卷144,弘治十一年闰十一月丁丑,第2514页。。嘉靖二十一年(1542),“阳和卫前所百户李锦及总旗杨泽私与夷人贸易”[注]《明世宗实录》卷266,嘉靖二十一年九月壬子,第5266页。。
除武官外,还有大量普通的军士也加入到明蒙私市贸易中。如嘉靖年间大同总兵仇鸾所说:“各边虏患惟宣、大最急,盖由贼巢俱在大边之内,我之墩军、夜不收往往出入虏中与之交易,久遂结为腹心。”[注]《明世宗实录》卷364,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丁丑,第6483页。甚至到了“虏代军瞭望,军代虏牧马”的地步。[注]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中三边·俺答列传上》,《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6册,第426页。家丁也在其主帅的纵容下卷入边境的私市贸易。在嘉靖后期家丁改由政府出饷供养之前,家丁是由将帅私人出饷供养。为了稳定家丁的忠诚,将帅往往给予家丁高于普通士卒的粮饷和装备待遇,甚至“过额兵十倍”[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3“家丁”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71页。。同时,将帅还纵容家丁出塞劫马,或者从事走私贸易获利。嘉靖年间的大同总兵梁震“在边专练家丁,时时出塞劫虏营……得虏营马,尽与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趋利”[注]李贽:《续藏书》卷14《太保梁武壮公》,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84-285页。。其后继任的大同总兵周尚文也豢养家丁,且“私使其部与虏市”[注]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中三边·俺答列传上》,《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6册,第426页。。
边军长期从事明蒙私市交易,经年累月,甚至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交易传统。据王崇古的记载:
照得大同各路,逼近虏巢,向缘将士怯懦,虏酋贪狡;索贿买和,苟延岁月。甚至沿边各堡,有月钱之科派;大边墩哨,有分帐之买卖……访得大边哨军每二人贴一,全不坐哨,专事交通,时以粮银私买货物,深入分定虏帐,交结酋妇,展转图利。间得虏情,匿不实报,凡我兵动定,预为虏传。[注]王崇古:《禁通虏酌边哨以惩夙玩疏》,《明经世文编》卷316,第3348页。
所谓“月钱之科派”,是指边军按月收缴一定数额的钱银,交予蒙古人以防其来犯,即“索贿买和”。以至于未能按时缴纳,蒙古人还会催要,“大同各堡纳虏月钱,凡有月钱违限者,虏即行票催取,未委虚的”[注]魏时亮:《题为圣明加意虏防恭陈大计一十八议疏》,《明经世文编》卷371,第4013页。。而“分帐之买卖”则是指边军划分与蒙古人交易的区域,三人一组,二人贴一人,即以一人的折银军饷作为资本,购买蒙民所需货物,前往分定的蒙古部落营帐进行交易。据估算,当时大同墩哨军大约有五千人,每人每月行粮二石,按当时价格共合折银万两,以“每二人贴一”计算,光是大同墩哨军每月同牧民的交易额,就至少可达三千两银。若以此银两购买布匹前往牧区交易,则有二万余梭布出口到塞外,同时可进口牛三千头或羊万余只。[注]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编写组:《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356页。
按明制,作为明初山西行都司军饷主要来源的屯粮、民运粮,都征本色,后相继改为折银征收,大概到正统年间开始实行全面的以银币为中心的边饷政策。边军月粮折银,一方面如上节所述,由于折兑失宜和克扣饷银,加之明中期边镇米价持续居高不下,造成了边军的生活困境并因此激发了多次兵变;另一方面,以屯粮、民运粮折银和京运年例银为主体的军饷,也成为了边军从事与蒙古人的私市贸易的主要资金来源。通过军饷购买的塞外物资,并不仅仅在边镇一带流动,而是流向了更远的地区,如谳牍中的案犯杨一休与马西川,向蒙古人购买的马尾,就是边镇走私贸易的大宗货物之一,这与明代中叶以马尾作为衣帽装饰的时尚有关,这些马尾主要流向京城和江南地区。[注]具体内容可参见赵世瑜:《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第151-154页。同时,边饷折银使得边军的口粮只能通过购买获得,这使得北部边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米粮市场,加之其它商品的需求,使得“沿长城向东西延伸的明王朝的边境地区,不仅成了国防的第一线,而且成了一大经济消费区”[注][日]寺田隆信著、张正明等译:《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商品流通和商人活动的频繁,使得边镇的商业传统和商业网络不断发展,并最终推动了边镇的商业化进程。
五、 结论
《赵全谳牍》所展现出来的明代边军身份、生存境遇与生计活动,可以作为讨论边镇军事体制、人口流动、民间宗教、商业传统等社会秩序问题的一个切入点。这些问题都分别被学者们从明代军制史、明蒙关系史、秘密宗教史等角度进行过论述,但都没有将之纳入到明中叶边军的日常生活史这个整体框架内加以考察。关于明中叶九边建置、明蒙关系、互市贸易等史实,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同质性的研究很多。如何在这么丰富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新见,除赵世瑜师提出的“内陆史视角”外,循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从具体人群的活动出发看待明中叶的“北虏”问题,仍然会有很多新的启示。
本文正是尝试以大同地区的边军群体为例,讨论明中叶北部边镇的社会秩序问题。明中叶边镇的军事体制日趋复杂,这种复杂不仅体现在多重军事建制的重叠上,更体现在边军身份的多元性和流动性。卫所军户和普通民户都可以投军,成为营兵或边将的家丁;由于明廷对于秘密宗教教徒的谪发充军政策,或教徒避入军中的主动选择,导致军队中有相当数量的秘密宗教的教首和信徒;明蒙双方对于敌方人员的诱降、互派间谍“诈降”、明廷对于“走回人”的招徕和安置为军,都使得边境地带居民的族群身份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可变性。这种多元的流动身份使得边军与边将、边军与朝廷之间都难以建立长期的稳定的效忠关系,加之边饷折银政策在实施中的弊政、边镇粮饷数额激增导致的欠饷、米价昂贵、边将的欺压等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兵变一触即发。因而,出于各种事由的边军叛逃出边也就屡屡发生。而长期以来边镇社会存在的明蒙人民私市贸易的传统,使得在官方互市停罢之时,长城内外的商品流通也从未停止。边军是主要的贸易者,这既有边镇官军逐利的诉求,也因为其军人身份及承担戍守、哨探、与虏交战等军事任务时可以获得的军备物资与便利条件。明政府的边军粮饷折银的做法,不仅刺激了边镇的商业化,也为边军的私市贸易提供了资金来源,带动了从长城内外到江南商业最繁盛之地的白银与商品流动,将边地的“走私贸易”卷入到一个更大的全国性市场网络中。
于是,在区域社会史的视角下考察明代的“北虏”问题,要提出的问题可能就变成了:明开国以来延续了一两百年的“北虏”问题究竟给北部边疆的地方社会打上了怎样的烙印?或者是,北部边镇及邻近的蒙古部落的地方社会秩序和边民的日常生活,怎样构成了令明廷头疼不已的“北虏”问题?这样的提问方式及相应的解释,相信在这个传统选题上,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新的讨论空间,这也是笔者将要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