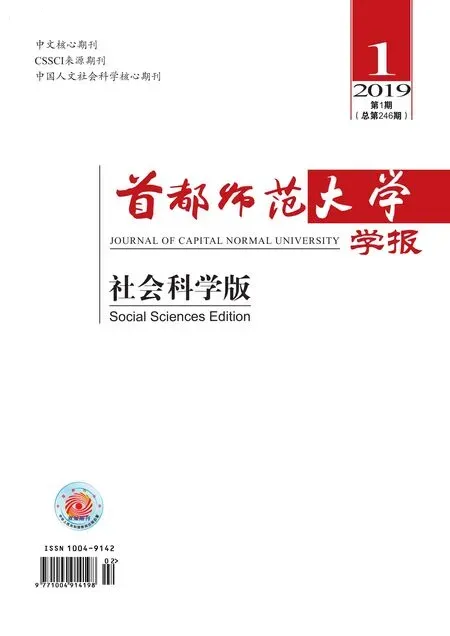戏在台下
——鲁迅《社戏》重读
2019-02-22郜元宝
郜元宝
一、《社戏》作为《呐喊》最后一篇的意义
1930年1月,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作者将此前十二次印刷时一直放在最后的《不周山》删去,后来更名为《补天》,就是《故事新编》第一篇。这样第十三次印刷的《呐喊》在版本上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鲁迅自己称之为“第二版”从这一版开始,通行的《呐喊》最后一篇就不再是《不周山》,而是原来排在《不周山》前面的《社戏》了。中小学语文课本经常选到《社戏》,所以在中国,《社戏》可谓家喻户晓。
《社戏》主要写一群小孩子,写他们幸福的童年。鲁迅很喜欢写小孩,这在中国小说史上也可说是一个创举。过去中国小说并不是不写小孩子,但从来没有谁像鲁迅这样,集中、正面、大量地写到小孩子。这当然和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有关,鲁迅正是五四时期“发现”儿童也是“人”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的始作俑者。
通行版本的《呐喊》一共收了14部短篇小说,至少11部写到小孩。但鲁迅笔下的小孩一般又都很悲惨。《狂人日记》《风波》里的小孩被父母打骂得很凶。《孔乙己》里的学徒“我”被“掌柜的”欺负得很厉害。《明天》里的小孩“宝儿”病死了。《阿Q正传》里的小孩当了假洋鬼子的替罪羊,被阿Q骂作“秃驴”。《故乡》里的孩子们饱受小伙伴分离之苦。闰土的几个孩子更是可怜。
面对这么多不幸的小孩,难怪《狂人日记》最后要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
但《呐喊》最后这篇《社戏》画风大变,大写特写童年的幸福。这大概就是鲁迅本人对“救救孩子”这声呐喊的回应吧。
一部《呐喊》,以《狂人日记》“救救孩子——”的呼喊开篇,以《社戏》中一大群孩子的欢声笑语结束。鲁迅笔下的中国故事,因为《社戏》,就有了一条光明的尾巴。
《呐喊》最后,紧挨着《社戏》,还有《兔和猫》《鸭的喜剧》两篇,也是写小孩,也是写快乐的童年。这三篇显然是一个整体,而且鲁迅所署的写作日期,也都是1922年10月。
1922年鲁迅日记丢失了,只有许寿裳的抄稿。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鲁迅的老同学许寿裳很崇拜鲁迅,连鲁迅的日记都要抄。可惜他只抄到片段,因此看不出这三篇小说的写作时间究竟谁先谁后。
但不管怎样,总之《社戏》被排在了通行版的《呐喊》最后。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社戏》的艺术成就在最后这三篇中也算是出类拔萃,而且《社戏》中孩子们的幸福指数也最高,所以不管《社戏》的具体写作时间是否最靠后,用它来做《呐喊》的收宫之作,也是最恰当不过了。
二、《社戏》之“戏”并非“好戏”
但《社戏》也有问题。这问题就出在最后一句话里——
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所谓“那夜似的好豆”,是说《社戏》里的孩子们那天晚上看完戏,回来的路上偷吃了村子里“六一公公”的罗汉豆。大家吃得不亦乐乎,所以豆是好豆,确凿无疑。
但戏是不是好戏,就值得商榷了。不信就请看小说提供的几个细节。
细节一,看戏的孩子们最喜欢“有名的铁头老生”,但他那一夜并没有“连翻八十四个筋斗”。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最想看到的“蛇精”和“黄布衣跳老虎”也未上台。唯一激动孩子们的是一个穿红衫的小丑被绑在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人用马鞭打。仅此而已。所以孩子们最后哈欠连天,一边“骂着老旦”,一边离开戏台。这样的戏,能说是好戏吗?
细节二,“我”的母亲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得多,一年能看几回。”
所以就戏论戏,那个晚上“我”在赵庄看到的,绝不可能是一生当中最好的一出戏。
三、“好戏”在台下
既然如此,为何小说结尾,“我”偏要说,他后来再也没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呢?
这就要看我们如何理解,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到底什么是“好戏”。
对大人们来说,评价一出戏好不好,只能看这出戏本身的质量。
但孩子们就不同了。他们关心的“戏”不在台上,或主要不在台上,而在看戏的全过程。
从听到演戏的消息开始,那些根本还不知道名目和内容的戏,就已经在孩子们的心里上演了。这是孩子们看戏特有的前奏。
《社戏》的戏台不在“我”的外祖母家,而是五里之外“赵庄”。因此“赵庄”人如何商量着请戏班子,如何搭戏台,戏班子来了如何排练,如何轰动全村,这些内容全省略了。其实这也都能给孩子们带来极大的兴奋与满足。
对“我”来说,看过戏的小伙伴们“高高兴兴来讲戏”,已经令“我”无限神往。这当然不是神往于具体的戏文,而是似乎已经从远处飘来的“锣鼓的声音”,以及“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的热闹场面。
最令人心花怒放的,还是好事多磨,却又终归得遂所愿。
原来那天晚上,船,这水乡唯一的交通工具,因为大家都要去看戏,突然变得紧俏。外祖母家没雇上船,眼看去不了,几乎绝了望,最后却发生大逆转:村里早出晚归唯一的“航船”居然提前回来了,而经过小伙伴们“写保票”,外祖母和母亲居然很快就同意由他们带“我”去看夜戏了。
这种幸福实在难以言喻,鲁迅先生居然把它给形容出来: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
接下来就是读者熟悉的一去一回的沿路风光,特别是回来的路上,大家在月光底下煮罗汉豆吃,以及多少年后仍然无限深长的回味。
这才是“社戏”真正的内容。这才是“社戏”的主体和高潮所在。
所以孩子们的赏心乐事,跟大人们张罗的戏台上那出不知名、也并不精彩的戏文,其实关系不大。并不是大人们张罗的那台戏给孩子们带来了怎样的快乐,相反是孩子们的快乐,是孩子们自己在台下不知不觉演出的童年喜剧,赋予台上那出戏以某种出乎意料的意义和美感。总之孩子们有自己的世界。他们在天地大舞台演出自己的人生戏剧。至于看大人们张罗的简陋的戏文,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四、三个值得感谢的大人
但要说大人们毫无功劳,也不完全对。大人们张罗的戏剧固然简陋,却毕竟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由头。孩子们可以借助这个由头,来上演他们自己的人生戏剧。这是《社戏》所描写的“戏”与“人生”的关系。
但大人们的功劳也就到此为止。如果因为提供了这么一个由头,就说自己给孩子们创造了莫大的幸福,那就太夸张,太“贪天功以为己力”了。
尽管如此,孩子们还是应该特别感谢三位大人。
首先是“六一公公”,孩子们回来的路上偷吃了他的罗汉豆,但他非但不生气,反而问孩子们“豆可中吃吗?”这就很了不起。《社戏》之所以脍炙人口,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像“六一公公”身上所表现的这种淳朴善良的乡风民情,他不仅对孩子们偷他的罗汉豆毫不气恼,还要把豆子摘下来,特地送给“我”的母亲——从本村嫁出去的姑娘、现在回娘家探亲、“六一公公”称她为“我们的姑奶奶”——品尝品尝。
更了不起的是,这位好心肠的“六一公公”居然还关心“昨天的戏可好吗?”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许多父母对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完全不了解,只晓得忙忙碌碌,怨气冲天,他们是决计提不出“六一公公”这个问题的。
“六一公公”的两个问题,一个关乎“豆”,一个关乎“戏”,恰好是孩子们最关心的,所以非常有助于孩子们重温和确认刚刚过去的那些赏心乐事。
其次是外祖母,她看见“我”因为没有船去看戏而焦急失望,就非常“气恼”,怪家里人为何不早点把船给雇下。外祖母一直为此絮叨个不停。晚饭时看到“我”还在生气,她的安慰也非常到位:“说我应当不高兴,他们太怠慢,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所没有的。”
如此关注并且理解小孩的心理状态,就不是一般的外祖母了。
最后是“我”的母亲。表面上,母亲对“我”去外庄看戏并不热衷,对“我”的生气更不以为然,甚至还叫“我”不要“装模做样”,“急得要哭”,免得招外祖母生气。
其实这也并不完全是母亲的真心。母亲这是在娘家,作为嫁出去的女儿,她也是客人的身份,必须处处小心,不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轻易满足孩子的要求。事实上母亲很想让“我”去看戏。一旦得到机会,稍稍犹豫一番,她就同意了孩子们的计划,在没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下,允许人生地疏的孩子自己坐航船,跟小伙伴们去五里之外的赵庄看夜戏。
这可不是一般的母亲所愿意做、所敢做的决定。
可以想象,母亲在孩子们出发之后,肯定一直担惊受怕。航船刚回平桥村,“我”首先看见的就是母亲一个人站在桥上,等着自己的儿子归来。已经三更了,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开始站在桥上。母亲虽然“颇有些生气”,但孩子们既然平安回来,她也就没再说什么,还“笑着邀大家去吃炒米”。如果换一个母亲,黑暗中在村口桥头独自等到三更,接到孩子时,第一反应大概就是抱怨、怪罪、训斥甚至辱骂吧?但小说中“我”的母亲并不这样。
母亲还有一个值得感谢之处,就是她既没有请别的某位大人跟孩子们一起去,也没有亲自陪着孩子去。她宁可自己担惊受怕,也要顺着孩子们合理的心愿。她没有自以为是地介入孩子们的世界。她尊重孩子们的自主权。
试想如果那天“我”的母亲自己去了,或着请了某个大人帮助照看孩子们,还会有孩子们那么多的开心之事吗?还会有这篇温暖而美好的小说《社戏》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五、《社戏》的主题及其他
鲁迅杂文中的一句话很有名,“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在五四前后,根据进化论思想,主张“幼者本位”,而要奉行“幼者本位”的新道德,就必须首先让老年人和成年人为少年人和儿童做出牺牲,因为“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同一篇文章中,鲁迅还具体地给老年人和成年人指出如何牺牲于儿童和少年的三个步骤:第一是理解,特别是理解孩子既非“成人的预备”,亦非“缩小的成人”,一定要知道并且承认“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其次“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第三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注]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页,第140-141页。这些有关“幼者本位”的想法,应该就是小说《社戏》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之一吧?
为了孩子们的独立,为了孩子们的幸福(独立和幸福往往是一回事),有时候大人们真的不能事事都冲在前面去。再怎么担惊受怕,再怎么不信任孩子们,父母也必须有所克制,必须退居幕后,必须作出必要的让步,乃至自我的牺牲。这样,孩子们才会有自己的天地,才能逐渐养成独立的品格和能力,也才会享受到他们自己的天地中那份独有的欢乐。他们的生命应该“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和鲁迅主张的“幼者本位的道德”截然相反的小说人物,比如张爱玲小说《金锁记》塑造的寡妇曹七巧。
曹七巧把她的一儿一女完全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生怕他们独立。儿女一独立,她就觉得要远离她而去,不再受她控制,不再是她的私有财产,她辛苦一生的目的也就落空了。因此曹七巧不惜以种种骇人听闻的办法,千方百计控制儿女,直到让他们跟自己一起在“黑暗的闸门”里沉沦下去。
曹七巧是个寡妇,《社戏》中“我”的母亲是否寡妇,未作交代。但我们知道,鲁迅的母亲很早守寡,《社戏》也只写到母亲,只字未提“我”的父亲。至少在小说情节中,“我”只是跟着母亲来外婆家“归省”,身边没有父亲。“我”的母亲和曹七巧在身份上非常接近,但道德观念、处理跟儿女关系的方法,真不啻有天壤之别。
最后还必须指出,中国的中小学语文课本选《社戏》,通常都是一种“斩首行动”,即删去《社戏》开头写作者“我”在北京室内的剧场两次极不愉快的看戏经历。尤其第二次,直接导致“我”跟中国戏“告了别”,“此后再没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经过戏院,我们也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说完这两次经历,作为对比,才想到“远哉遥遥”的十一二岁那次看戏经历,于是进入正文。
这是极平常的“将欲扬之必先抑之”的为文之道,不知缘何非要删去而后快。
或许,鲁迅反对中国旧戏或旧式剧场的言论有损“国粹”尊严?
或许,这一段包含许多“初期白话文”的“不规范”而有损鲁迅先生的尊严?
这都不敢妄猜,因为并没有哪一位中学语文教学的权威站出来解释过。
但不管如何,恰恰因为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才更应该保存鲁迅文章的本来面目,供师生们在课上或课后展开讨论。这不正是促进和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学不可多得的良机吗?我们究竟担心什么呢?面对鲁迅先生的作品,难道我们也要像曹七巧那样,对孩子们进行过度“保护”?我们其实应该学习《社戏》中的“八一公公”、“我”的外祖母和母亲,他们在将近一百年之前,就已经无师自通,懂得尊重孩子们的独立性,大胆而无私地“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了。如果向曹七巧学习,那么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就只能“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注]张爱玲:《金锁记》,《传奇》增订本,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版,第149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