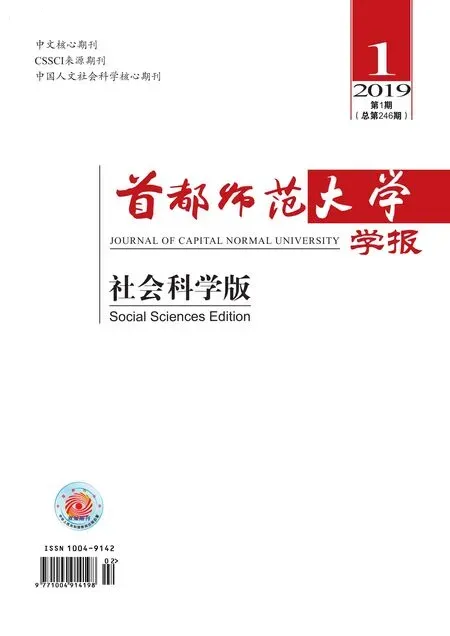《中庸大义》与唐蔚芝汉宋兼采之学
2019-02-22吴飞
吴 飞
唐蔚芝先生师从晚清经学大师定海黄元同先生,是南菁弟子中少有的理学家。黄先生以经学和礼学名家,与俞曲园、孙仲容被称为晚清经学三大家,也都被当做乾嘉汉学在晚清的延续,因而其门下也多以经学和礼学见长。唯独唐蔚芝先生,却主要是位理学家。这当然与唐先生早年从学于王紫翔先生有莫大关系,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他在南菁书院受的教育。 我们不能认为其理学均得自王先生,即使是唐先生的理学思想,仍然与强调汉宋兼采的黄先生有关,或者说,南菁书院的学习使唐先生获得了研究理学的新视角。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唐先生对汉宋兼采的理解,甚至可以更宏观地理解元同师生乃至清末民初汉宋兼采的形态。
一、蔚芝先生与元同先生
从日记、书信和年谱中都可以看到,元同先生与蔚芝先生之间师生情谊甚笃,交往密切,而唐先生所作《黄元同先生学案》,比章太炎之学案远为详细深入,也胜于其后徐菊人《清儒学案》中的《儆居学案》中的元同部分,不仅在民国时期算得上研究元同先生学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即便今日读来,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此《学案》中分别谈到了黄先生的主要著作,并给出相当系统的评价。在其中,唐先生对于元同先生辨性理之学的《经训比义》尤其推崇,说:“是书一出,而经学、理学始会归于一。”[注]唐文治:《黄元同先生学案》,《茹经堂文集初编》卷二,页18b,《民国丛书》第五编影印本,上海书店1996年版。言下之意,清初亭林先生所倡经学即理学之说,至元同先生而始成。唐先生还引刘芷人的评价:“以此说经,经由是明,以此应世,庶不执臆见为理义,败坏天下事矣。”[注]唐文治:《黄元同先生学案》,《茹经堂文集初编》卷二,页18b。以意见为理,乃是戴东原对理学,特别是王学的批评,唐先生当然知道,而此处引刘氏此说,自有呼应东原、修正理学之意。他在他处也记录过黄先生的话:“戴东原先生《孟子字义疏证》立说俱是,而近于毁骂。”[注]唐文治:《南菁日记》,光绪乙酉年(1885)三月初六日,转引自赵统:《南菁书院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页。唐先生虽然服膺程朱,到了晚年甚至推崇王学,但对于戴东原至黄氏父子对理学的修正,并未忽视。[注]关于定海黄氏父子与戴东原思想的关系,参看吴飞:《礼学即理学:定海黄氏父子的义理学》,《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4期。
对黄先生《子思子辑解》一书,蔚芝也非常重视。黄先生晚年辑解《子思子》,意在“由孟子以求孔子、曾子之学,必以子思为枢纽”,并且说:“加我数年,《子思子辑解》成,斯无遗憾。”显然很看重是书。故蔚芝以为,是书卒成,“先生之志彰,先生之学亦愈精矣”[注]唐文治:《黄元同先生学案》,《茹经堂文集初编》卷二,页19a。。蔚芝并不把元同先生目为汉学家,而是看作合经学、理学为一的儒者,故称:“盖先生之学,精于穷理,故其研求训故,辨析是非,细之入毫芒,大之充宙合。”[注]唐文治:《黄元同先生学案》,《茹经堂文集初编》卷二,页22a。而即便以考据文字、辨章制度为主的礼学,也仍未失去此一主旨:“礼根诸心,发诸性,受诸命,秩诸天,体之者圣,履之者贤。”[注]唐文治:《黄元同先生学案》,《茹经堂文集初编》卷二,页15b。
唐先生对元同先生学问的概括与评价,与近世学者大多不同,却是他亲炙师门多年的深切体会,亦是他从学所得之精华。因而,他这样界定黄先生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国朝讲学之风,倡自顾亭林、黄梨洲诸先生。亭林先生尝谓经学即理学,经学外之理学为禅学,故经学、理学宜合于一,不宜歧之为二。乃体郑君、朱子之训,上追孔门之经学,博文约礼,实事求是。其所得于心而诏后学者,务在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盖江慎修、王白田先生以后一人而已矣。[注]唐文治:《黄元同先生学案》,《茹经堂文集初编》卷二,页11a。
此论对黄先生评价极高,却也非常耐人寻味。顾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说,既是清代整个学术传统的宗旨,也是黄先生的学术圭臬,此不必论,而唐先生却说黄先生为江慎修、王白田这两位在宋学领域很有成就的学者的传承者,可谓发前人所未发。江慎修为乾嘉学者戴东原、程易畴、金辅之等人的授业师,下开乾嘉学术之皖派传统,然其人却不仅有《礼书纲目》《乡党图考》等经学著作,又尊奉朱子之学,撰《近思录集解》,且其《礼书纲目》亦有承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之义,属于清代前期汉宋兼采的代表人物。而王白田更是清代程朱学派最重要的人物,其巨著《朱子年谱》可以算作清代宋学研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但白田先生与慎修不同,除了其朱子学研究亦大量运用考据之法外,与其后的乾嘉学统并无大的关系。而蔚芝将元同先生与此二人并列,认为传承了顾亭林经学即理学之风,自然应该是为了表彰其在性理之学上的贡献,特别是《经训比义》与《子思子辑解》二书,似乎继承了《近思录集解》与《朱子年谱》的学统。
唐先生高度肯定元同先生的性理之学,并非出于尊奉理学的立场为尊者讳,他对很多问题的研究确实受到了黄先生的深刻影响。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他的《中庸大义》,因为《中庸》是黄、唐二先生均曾注释的经书。对《中庸》的诠释不仅是元同先生《子思子辑解》的最重要部分,也贯穿了他的《经训比义》,而此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也正是其父薇香先生的许多文章中率先提出的。唐先生《中庸大义》并非完全遵从黄注,但引《子思子辑解》之处甚多,我们对比二书,可以约略窥见唐先生受元同先生影响之大概。
黄元同先生《子思子辑解》一书之体例,每条经文之后必先列郑注,再下按语,按语中多有反驳朱子之说者。《中庸》为其首篇,黄先生按语尤详,且多引用其父之说,亦与《经训比义》有相互发明之处。全篇分为十四章,与朱子分三十三章之法颇不同。
据唐先生自定义年谱,自民国二年至六年间,先后编订《论语大义》《孟子大义》《大学大义》《中庸大义》,为授课所用教材。此书体例,分章依照朱子,而不从黄先生,每条经文下,朱注最多,间或亦有郑注列于朱注前,其后亦多有“先师黄氏元同云”,再以“愚按”下以己说。此后或引近人如陆桴亭、李二曲,乃至其弟子陈柱尊等人之说以发明其义。朱、黄二注应为唐先生作此书最主要的参考,故要把握《中庸大义》之旨,第一个关键在于观其在二家之间的取舍。
二、《中庸》前三章中的性理之学
唐先生《中庸》既按朱子分章,且尽可能纳朱注于内,其尊朱之意应无疑义;且不仅对朱子,即便对清儒批评甚多的阳明良知学,唐先生亦颇推崇。然若细究其对理学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蔚芝与朱子却相差甚多,反而更近于元同先生。《中庸》起首三章(本文中所言章数,均按朱子、唐先生所划分者),不仅是此书中确立基本框架与概念的部分,更是朱子阐释其天理人欲、已发未发、性命之学的关键段落。以下即主要以对这一部分的诠释看唐先生之性理学。
对于篇名“中庸”二字的理解,郑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朱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黄云:“中者,无过不及之名。民所受天地以生,是性之体也。其用之在人,谓之庸。庸,常也,用也。”其说既采郑君“用”之训,又不废朱子“平常”之意,汉宋兼采色彩已然非常明显。唐则全录黄先生之文,而取其训用之说,“训庸为用,最为精实,盖中庸乃最有用之学”,其实接受的是郑注。在这个问题上,他似乎比黄先生还要尊郑。[注]郑注孔疏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礼记正义》(2008年版),朱注用中华书局版《四书章句集注》(2012年版),元同之说用上海古籍出版社《黄式三黄以周合集》(2014年版)第十四册,蔚芝之说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四书大义》(2016年版)上册,不逐条出注。
对于《中庸》第一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郑强调“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重“人”,朱注兼人与物言,黄注认为朱子兼人、物之说非,而唐书对朱注与黄注均大段引用,并下按语云:“《春秋穀梁传》曰:‘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也。(若,顺也。)’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天以生物为心,故人各得其生生之理以为性。率性非任性之谓也。率其固有之善而行之,使人人各得,若其生生之性,是乃所谓道也。因一人之道,推而至于天下共喻其道,而学校立焉,所谓教也。性、道、教三字,专属诸人,朱注兼人、物说,恐非。”此处是黄先生与朱子一个相当重要的不同,而唐先生与黄先生则完全相同,甚至自己找文本依据反驳朱子之说。
朱子兼人、物说,于其性理学有莫大干系。他说:“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理为万物所赋,性亦万物之德,非仅就人论而已。朱子所讲,乃是一个相当宏观的宇宙论。黄先生并不接受朱子的宇宙论,而有自己的一个经学和礼学体系,因而不从其说;唐先生也不从其说,受黄先生的影响很大。但他和黄先生的关怀亦稍有区别,即他并不想建构另外一个经学体系,而是试图强调教育的意义,因而特别强调学校之立。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赌,恐惧乎其所不闻。”朱子于此处断句,黄先生则于下文“故君子慎其独也”后断句,唐从朱断句。此处是朱子发明其说的紧要处,因而注云:“道者,日用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岂率性之谓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倾也。”按照朱子的理解,此处说的“不可离”指的是人、物之理,即道体,人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偏离,之所以要戒慎恐惧,是要体会那个不可离的道是什么,其所不睹不闻的即为道体。但黄先生并不同意此说,下按语云:“此承上‘率性之谓道’言之。道出于性,人物智愚贤不肖皆具此性。性不可离,亦安可离道?‘不可’者,警戒之词,非言道体。‘可离非道’,又反复申明率性之谓道之意。君子于不睹不闻之地,犹戒慎焉,恐惧焉,是道无须臾离之实功。”黄先生认为这不是在说道体,道当然可能偏离,此处就在警戒人们不要偏离了道,所戒慎恐惧的亦非所谓道体,而是在日用生活中的细微之处。虽然黄先生不同意朱子,但在最后不忘了说,朱子之说虽近于支离破碎,却“别有深意,未可厚非”。唐先生全引郑、朱、黄三家之说,而下按语云:“师说至警切,道,所以率吾性而存天命也,须臾离道,即戕贼其性而悖天命也。故又曰:可离非道也。”随后引《左传》《孟子》之说,最后总结道:“戒惧慎独,所以养神而事天也。然则君子之功,岂偏于静乎?曰:不然,此特言其体尔。曰戒慎乎其所不睹,则其所可睹者,戒慎更可知也。曰恐惧乎其所不闻,则其所可闻者,恐惧更可知也。”由于最关心的是对人的教育,而黄先生之说与教育问题更加接近,所以无论对不可离道的理解,还是对戒慎恐惧的理解,唐先生都遵从黄先生之说,而与朱子不同。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一句,也是黄与朱的理解有微妙差异的地方。朱子云:“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显明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在朱子看来,慎独所针对的,主要不是别人不知道的事,而是别人不知道的想法,即自己的欲望。这种人欲的萌动对他人而言是不可见的,对自己而言却是非常显著的,因而慎独就是遏制人欲之几。黄先生对慎独的理解更朴素直观,认为就是别人不知道、唯有自己独处时的事,因而说:“凡人祗知不睹不闻隐耳微耳,不知此隐微中,人属尔垣,鬼瞰尔室,其为显见莫是过焉。”虽然黄先生也认为隐微之地其实是显见的,但他仍然批评朱子将慎独当做遏制人欲的说法。唐先生在抄录了朱、黄二家之说后,并未给出明确的判断,而是引《周易》消息之义,说:“消者,正所以为息也,故隐者正所以为见也,微者正所以为显也……盖圣人者,诚而神者也,君子者,善审几者也。几者,当念虑初起之时,善者则扩充之,恶者则遏而绝之,故《易传》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随后以此阐释《中庸》与《大学》中的慎独之意。在《中庸》开篇至关重要的这几句话中,这是唐先生第一次没有明确表示同意黄说,而大量吸收了朱注关于几微和念虑的理解。但是,朱子那里非常重要的人欲概念,在唐注中却付之阙如。唐先生虽然从念虑之微、善恶之几的角度理解慎独,却不把遏人欲当做最根本的理论问题。唐先生对易学颇有独到的理解,有《周易消息大义》等书传世,因而以《易》释诸经,也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此处,唐先生吸纳了朱、黄两家之说,以《易》解《庸》,而形成了自己的解释。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此句言未发已发,是朱子思想成熟的关键所在和宋明理学的要害,而黄先生也给出了与朱子相当不同的解释。朱注:“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性也。无所偏倚,则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地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道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其言不多,然所包甚广,关键在区分未发与已发两个层次:所谓未发,是无喜怒哀乐的中,是天地之性,是涵摄天下之理的道体;所谓已发,是有了喜怒哀乐,是情,发而皆中节,即喜怒哀乐皆恰到好处,是道之用。此与郑注“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相当不同。黄元同先生综合了郑君和朱子的理解,说:“此承上‘修道之谓教’言之。教施诸人,道先修诸己。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时,情涵于性。性者,民所受天地之中,故谓之中。用其中自无乖戾,故谓之和。下文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注云:‘达者常行,百王所不变也。’则达道犹庸道也。和为天下之庸道,此中庸所以谓之中和也。夫圣人自诚明,容有不待思索自合乎中和者。其下率性而行于道,必有过不及,则未发已发,时时求其中节而修之,不能不用思索。所谓自明诚之教,必先修乎在我者也,又以此道推而广之于人。”朱子认为前文言慎独与此文言已发未发,皆就天理人欲、道体性情上言,而黄先生却认为,前文的慎独一节讲的是“率性之谓道”,重在自修,此一节讲的是“修道之谓教”,重在教人。他认为性即“民所受天地之中”,用之则为和,这里说的 “达道”就是下文的“五达道”,即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即五伦,因而所谓“中和”,并不是执着于喜怒哀乐而言的,而是五伦关系是否处理得恰到好处。自诚明的圣人与凡人的差别在于,可以不必思索就做得恰到好处,但凡人必须自明诚,才能把五伦处理好,否则就要么过,要么不及,于是就特别需要思索和纠正,也就是需要“修道之谓教”,因而只有自明诚者才需要在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思索,从而达到发而皆中节。
如同对上一条的理解,唐先生此处的诠释综合了朱、黄二家之说,却又和他们都有不同。在这一条,他并没有引元同先生,反而引了薇香先生的两句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其未与物接之时乎?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其既与物接之时乎?”黄氏父子的解释实为一脉相承,都放弃了朱子关于道体的理解,而是将未发和已发都放在日常交往当中看待。在自己的按语中,唐先生首先谈到了朱子中和学说的发展,然后谈到自己的看法。此后在《紫阳学术发微》中,唐先生也大段引述夏韬甫对朱子中和之说发展的考证,可见唐先生对朱子之说非常重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同意朱子之说。在后面具体的阐释中,我们已经完全看不到朱子的道体之学。他说:“所谓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也。故曰: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众人纵其欲而汩其情,则平旦之好恶,有梏亡之矣。”其后引用自己的书《易微言》,以易之吉凶悔吝释之,云:“《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未发之性,卦画之未成爻者也。画而成爻,是为已发之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归于既济定,所谓发而皆中节者也。天下之大本,不外乎阴阳刚柔之性,天下之达道,不外乎阴阳刚柔之情。悉得其当,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盖取诸乾坤之消息也。”与前条类似,唐先生最终转向了自己的周易学,以此来解释他对未发已发的理解,因而无论未发之中还是已发之和,都在于阴阳刚柔之间的关系。此说自是唐先生独到之解,而与朱子中和之说已相当不同,就其精神实质上而言,还是与黄氏父子的说法更接近。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子的理解,先是讲“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随后说“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焉”。黄先生仍承前说,强调:“未发时无思索,惟自诚明者能之……未发之中,未有不由思索而能得者。若谓一思索便是已发,则未发时无所喜怒哀乐也,何以见无过不及之中乎?已发时方思索,则喜怒哀乐自此才有主张,何以见中为大本乎?”唐先生引了朱、黄注后下按语云:“圣人尽性之学,祗在致中和,王者之刑赏庆罚、制礼作乐,皆本于喜怒哀乐,因一人之中和,而使万物各得其所。中和之时义,大矣哉!”唐先生并未区分中与和,而是泛论中和。他也强调此句是在讲“教”,其说更近于黄,而重在发明教育之大旨。随后,他谈了自己对朱子“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的理解,认为这是“指为人上者而言”,其实与朱子之意颇有不同。
唐先生从朱子,认为此上是第一章,并全引朱子之论,然而自下按语时却又与朱说关系不大:“此章言性情教育,推原天命,实即人道教育也,人道以性情为本……故明王治天下,必先致中和,而致中和之功,必先慎独,一二人知慎独,则一二人之心术正,千万人知慎独,则天下人之心术正,然则天下之学,固莫大乎慎独,而言人道教育者,必以性情为本,言性情教育者,必以此章为首务也。”此一段按语虽然非常重视性情问题,但并不像程朱那样区分性、情的概念,因为其重点并不是对性理结构的分梳,而是对教育的诠释,因而与黄先生解“修道之谓教”更加契合。
综观唐先生对《中庸》第一章的诠释,虽然分章采用朱子,但对于朱子区分天理和人欲,未发已发、性与情、中与和等概念,并未接受,而对于元同先生不同意朱注之处,反而多从黄说。而其要旨,在于倡导教育,以正人心,如此取舍,应该是激于时事而发。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此段朱子分两句读,自“小人反中庸”后断,并以命、理详解之。唐先生依次分段,却未列朱注,谨列郑注:“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为中庸也。”随后进入后面一句。朱注从王肃、程子之说,以为“小人之中庸也”当为“小人之反中庸也”,释之云:“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黄先生则不从王肃增“反”字之说。唐先生按语云:“小人惟自以为中庸,故无忌惮。‘小人之中庸’句,自不当增‘反’字。”唐先生对这一条的解释,完全是从郑、黄之说而来的。
黄先生以为,至此为第一章,朱子则以为这是第二章。唐先生录朱子之言,而未下按语。
“子曰:中庸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各家差别在对“鲜能久矣”的理解。郑注:“鲜,罕也。言中庸为道至美,顾人罕能久行。”朱注:“世教衰,民不兴行,故鲜能之,谨已久矣。”郑以“能久”连读,朱以“鲜能”连读,而与久断开。黄注看到了这个区别,未作判断,但指出:“注以‘能久’连读,即下‘不能期月守’之意。”二说虽皆可通,而郑注与下文呼应,似较朱注为长。而于此处,唐先生具列三家之说,下按语云:“依近读为是。盖天下过者为横民,不及者为懦民,世必多能中庸之国民,而后天下客望其平,故教育国民,必以中庸为主。”此处是唐先生明确从朱违师的一个地方,但其用意也非常明显。无论朱子还是唐先生,都认为此处是在批评世风。
按照朱注,是为第三章,唐亦从之。
三、时中之教育思想
由对前三章的诠释,已可约略看出,唐先生虽然尊朱尊王,也颇重视性理,但对于宋明理学中对性理诸概念的辨析并不甚措意,故于朱子思想中最核心的天理、人欲之分,已发、未发之分,性、情之别,均未详言。甚至可以说,唐先生凡言及性情之处,几乎都是笼统地把这两个字当做一个词来看待。他这个时期对理学的重视,不在于对性情之辨,而在于对言性情。
在《中庸大义》中的前数章,唐先生对黄元同先生的引述非常多,但到后面就越来越少;可是在关键的地方,比如“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一条(朱注二十七章,黄注第十二章),黄氏父子均认为,“礼仪”当为“礼义”,这是他们礼学思想体系的关键之处,而唐先生也录下元同之说,认为“此说最精核”。即使在完全不引黄注的地方,唐书也经常是黄非朱。可见,黄氏父子的性理学对唐先生的思想有相当实质的影响,这种影响最重要的方面,即在于唐先生的教育思想。
朱子之学,特别重视学礼,教育本已为一重要方面,降至有清,由于对训诂考据的重视,教育更是非常重要,这在黄先生的学术和实践中都可以看到。唐先生继承并发展了朱子以来重视学习与教育的传统,他最重要的贡献在教育上面,他的经学和理学研究,都是围绕教育事业展开的。但比起前辈来,他的教育思想是针对当下而发的。民国时期面对巨大的文化转型,兴办教育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聚焦所在。唐先生既曾执掌交通大学,又曾兴办无锡国专,前者重在现代实业,后者重在文化传承。虽然是两所截然不同的学校,唐先生却秉承着一贯的教育理念,这在他对《中庸》和其他经书的诠释中都体现得非常明显。
唐先生并非顽固的保守派,和当时兴办教育的各界人士一样,他能够勇于面对现实。故而在《中庸》的诠释中,他不仅特别强调礼时为大的意义,反对盲目泥古僵化的迂腐态度,而且也将很多现代观念纳入其中。比如在第二十章对“百工”的诠释中,身为交通大学校长的唐先生就特别强调“工业”,说:“古者官有试,士有试,而不知百工亦有省而有试。《周官》不曰纪工、劝工,而曰考工,其义可见。秦汉而后,此职既废,士不能勤其手指,或薄工艺而不屑为,于是自一丝一粟一针一黹,以至建筑营造诸事,皆须仰给于人,吁可慨也!”
二十四章“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无论郑、朱、黄,皆不曾怀疑占卜、吉凶之验,而唐先生却强调:“子思子非矜言前知也,特明至诚之效,而勉人以为善耳……是从兴亡分妖祥,非以妖祥卜兴亡也。”唐先生时时注意使中庸之说与当时流行的现代观念不冲突,从而能够为学习现代科学的学生所接受。
但唐先生并不是无原则地向现代观念妥协,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他是坚守传统的。如《中庸》第九章“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唐先生明确反对朱子训“均”为“平治”之说,而是针对当时非常流行的平等之论,指出:
此言天下国家可均者,盖谓均贫富之产业也。强均贫富,则必均职业。夫人之职业可均乎?欲均职业,则必均聪明才智。夫人之聪明才智可均乎?斯议一兴,愤激不平之徒出,不夺不厌,天下将大乱矣,悲夫!诗云:“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孟子云:“勇士不忘丧其元。”辞爵禄、蹈白刃,岂非天下至难之事?然须知人人皆以辞爵禄为心,则事业谁复担任之者?人人皆以蹈白刃为心,则激烈之徒连踵,游侠多而天下亦乱矣。故惟得其中,而后均天下国家、辞爵禄、蹈白刃,于义斯无亏缺,于情斯无所偏着。茍失其中,则均天下国家、辞爵禄、蹈白刃,非为名即为利,非为利即为意气,虽为一时无识者所推许,而流弊无穷,深可惜也。
倡导自由平等之说、革命牺牲精神,均为当时非常流行的言论,很少人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反对。唐先生却既不同意无原则的平等,也不赞成盲目的牺牲。这些行为固然精神可嘉,甚至《诗经》和《孟子》中都有赞赏之言,却往往不足以救世,更不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行为准则。在民国初年讲出这番言论,实为难能可贵;而面对如此崇尚极端的社会风气,又该怎样呢?唐先生教育思想的主旨,正表现在这个地方:“虽然,圣人云中庸不可能,未尝云终不可能。中庸者,秉于生初者也,自在教育国民者,涵养熏陶,盖剂其偏,庶几中庸之士出,而彼之均天下国家、辞爵禄、蹈白刃者,亦皆流于范围,而不至流于偏僻矣。《礼记·礼运》云: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其中庸之世乎?”其后又引李二曲之言,云:“事功节义,人若能一一出之于性,率自平常,而胸中绝无事功节义之见,方是真事功,真节义,真中庸。谁谓中庸必离事功节义而后见耶!”
通过教育国民,涵养性情,培养中正平和之气,方可事事做得恰到好处,达到真正的中庸,平均天下、辞爵禄、蹈白刃等等平等牺牲精神,才有其应有的位置,才能达到古代圣人所说的大同之世。唐先生的教育,真可谓时中之教育,既不是单纯地发展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强国富民,也不是盲目地顽固守旧、对抗新思想,而是以涵育心性为基础,培养出足以强国富民的时代人才。
正是出于这样的教育目的,唐先生并不怎么关心理气之辨的细节,他的诠释核心是“修道之谓教”。他之所以重视性理之学,是因为在他看来,教育必本乎人心,必须由培养人的性情出发。
比如在第三十二章“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唐先生按语云:“此言至诚之性情,学问度量,最为精至,学圣根基,实在于此,不可不深味而曲体之也。肫肫,仁之本也,非肫肫无以成仁也;渊渊,渊之本也,非渊渊无以成渊也;浩浩,天之表也,非浩浩无以配天也。”此前之郑、朱、黄对这一条的注释里均未如此强调教育的主题;而唐先生将“性情”连在一起说,不区别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也是朱子和黄先生都不大可能的。
《中庸大义》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对伦常的强调。清代礼学昌明,尤其关注对伦常的分梳,定海黄氏以礼学名家,南菁弟子多为礼学专家。唐先生虽然不专长于礼学,却也对伦常问题非常关注,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之际,新思想全面检讨传统伦常、自由平等学说大兴之时,唐先生反而特别强调伦常的价值。
《中庸》第十二章“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郑、朱、黄三家皆以为同于前文“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之义,而唐先生却引《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故《周易》下经首咸恒,咸恒者,夫妇之大义也。上经首乾坤,乾坤者,天地之大义也。”唐先生认为这一段讲的与《序卦传》中相同,指的是夫妇为人伦之始。下一句中的“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唐先生按语云:“道者,人性也,人伦也,未有悖人性、外人伦而可以为道者也。”朱子虽亦重视人伦,但仍不可能将人伦提升到如此高的程度。而对待人伦的这种态度,在南菁弟子张闻远、曹叔彦等先生当中却非常常见,唐先生除了治易有得之外,亦屡屡引《孝经》,应该既是与曹叔彦相交流切磋的结果,亦是南菁礼学熏染所致。故于其后“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一段,唐先生便在引了元同先生的解释后,分别以《易传·文言》和《孝经·卿大夫章》来诠释对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人伦之道。
第十五章之“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以及所引《常棣》之诗,朱注甚简,未讲其人伦之义。而郑注、黄注都强调人伦的远近次序。唐先生则云:
此以孝道通天下,道必始自家庭之际也。本经下篇云:“立天下之大本。”郑君彼注云:“大本,《孝经》也。”盖孝者,发于天性,为人道所最先,仁民爱物,基于亲亲,推恩四海,始于老老。下篇言不顺乎亲则不信乎友,不获乎上,又言,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尽其性者,尽孝道也,所谓自迩也,自卑也,尽人性,尽物性,至于参赞化育,所谓远也,高也。孝之道大矣哉!
郑注此一章时,以为妻子为近者,兄弟父母为远者,孔疏从郑注,但又添“先使室家和顺,乃能和顺于外”的含义。黄注以为难通,孔疏更是支词,故改解为妻子为卑者,兄弟、父母为高者。如此,则卑高有解,而远近无着落矣,似亦有难通之处。唐注则取孔疏之意而发挥之,以为卑、近均指室家,高、远则均为外物天地,与《中庸》全经之旨似更能融贯,此处应为唐先生之一重要创获,而其对人伦次序的重视,则由郑、孔、黄之学术传统而来。由于第十五章讲人伦问题特别重要,所以唐先生在全章之末再下按语,云:
此章言和顺以孝其亲,以立人伦之本,《孝经》所谓“生则亲安之”是也;下章言祭祀之尽孝,《孝经》所谓“祭则鬼享之”是也。“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皆和气之所感召也;又下三章举大舜、文王、武王、周公以为标准,四圣皆大孝人也。自宗庙飨之,推而及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自继志述事,推而至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其端皆自和顺始,所谓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也,义理文法,特为邃密,朱子以为承上章“费而隐”而言,失之拘矣。
在唐先生看来,“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一句,统领随后五章,又与《孝经·孝治章》中的主旨相合,并且以《孝经》架构来诠释《中庸》的结构,层层推进,逻辑严整。因而他对远近、高卑的阐释,其实是对《中庸》一大主题即人伦之本的阐释。他的这一解释自然与朱子偏于性理的解释非常不同,所以明确批评朱子的理解失之于拘。此处也是唐先生《中庸大义》一书的创获。
这一部分至十九章而止。唐先生于第十九章之末又下按语以结之,以为由仁孝之源,推及神道设教,实为孔子之宗教思想,所以批评说:“近儒乃以孔子为非宗教,不读书而愚陋至此,可慨也。”
不仅这五章,唐先生对《中庸》结构诠释之巨大创获,还体现在他对最后一章即第三十三章的解释上。在他看来,这一章谈的是诚的六个境界,分别对应于《孟子》中的六种说法。
第一,引《诗经》“衣锦褧衣”,谈的是闇然而日章之君子,有羞恶之心,以外有文而内无文为耻辱,即孟子所谓“可欲之谓善”;第二,引《诗经》“潜虽伏矣,亦孔之昭”,谈的是内省不疚之君子,可以做到慎独,即孟子所谓“有诸己之谓信”,并指出,时人都谈思想自由,但如果都是邪恶和违法的思想,又该怎么办?第三,引《诗经》“相在而室,尚不愧于屋漏”,讲不动而敬之君子,良知能对越上帝,即孟子所谓“充实之谓美”;第四,引《诗经》“奏假无言,时靡有争”,已经由修己之功推其效于民,即孟子所谓“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第五,引《诗经》“不显惟德,百辟其刑”,是文王平天下的教育精神,即孟子所谓“大而化之之谓圣”;第六,引《诗经》“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和“德輶如毛”,是与天地合德的最高境界,即孟子所谓“圣而不可知之谓神”,而朱子以为形容不显之德,则觉太泥。
黄元同先生对这一章的诠释中已经尝试分析出不同的德性,唐先生的思路应该由此而来;然而如此细密地分出六种境界,既与十五至十九章的远近高卑相呼应,更与全书的教育主题相配合,则是唐先生自己的发明。
此章为《中庸》末章,唐先生以薇香先生《诚说》以及自己所作《陈氏柱尊〈中庸通义〉序》作结,以发明“诚”与“慎独”之义,认为世界之坏,中国之衰落,都在于违慎独之旨。唐先生最后还是归本师说,聚焦于人心的教育问题。
小 结
清代是中国学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经过乾嘉之际的汉宋相争,晚清的汉宋兼采渐成主流,而陈东塾与黄元同分别为汉宋兼采的两大代表,既有相当深厚的经学根底,又非常关心宋明的义理问题。定海黄氏父子在相关问题上更有相当深的思考,他们的汉宋兼采并不是机械地鸠合汉宋,而是经过乾嘉的检讨之后更深入地研究义理问题,故而接受了戴东原等人的许多思考。
唐蔚芝先生亲炙元同门下多年,承元同先生之衣钵。在他眼中,黄先生并不是一个以训诂考据见长的经学家,而是一个有着深刻思考与扎实学问的理学家,因而对黄先生的《经训比义》和《子思子辑解》都非常推崇,且认为他属于清代理学的正统。
正是由于对清代理学与自己师门的独特体认,唐先生虽然以治理学为主,汉宋兼采的倾向已经非常圆融地化入他的研究、思考乃至教育事业当中。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三点:
第一,对学礼和教育的重视,是宋明理学的一大特点。朱子尤其重视心性的培养,因而宋明学术的最大贡献是培养出一大批崇尚气节的儒者。唐先生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不仅将教育当做自己的毕生事业,而且在对经书的诠释中处处体现出这一点。而因为对人的教育的重视,他反而看轻了朱子学术中的性理之辨,不甚措意朱子的宇宙论与本体论,因而在对性理之学的辨析上,他反而自觉不自觉地承接了戴东原至黄氏父子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看,哪怕清代对朱子思想的批评者,都深深受到了朱子问题意识和学问构架的影响。
第二,和清代的主要经学家一样,唐先生非常推尊郑学,因而在《中庸大义》中也经常引用郑注。而清代经学的重要成果是礼学的繁荣,南菁学派尤其注重人伦的核心意义,这是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方面。和其他的南菁弟子一样,唐先生也非常重视人伦和孝德,不仅把它当做治国平天下之本,更将它当做人性的根基,无论在《中庸大义》还是其他著作中,对此都有大段的讨论。他也曾专治《孝经》之学,在《中庸大义》中屡屡引用《孝经》中的文字。因此,唐先生的学问重心虽然不在礼学,但对人伦的思考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三,在古今之交的晚清民国,西方现代文化纷纷涌入,中国的教育也面对很多新的挑战。唐先生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勇于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海外的经历也使他对现代文明有更多的体认。无论在教育实践还是经典阐释中,他都贯彻了《中庸》时中和《周易》变易的思想。虽然本文并未过多涉及这一点,但以易解庸是《中庸大义》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也是唐先生学问体系的重要支撑点,却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