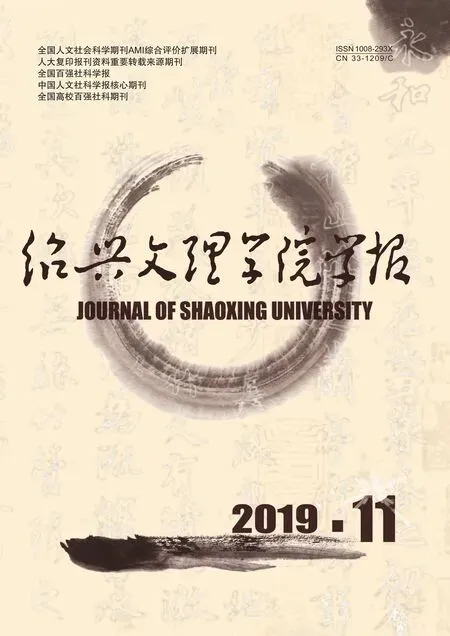基于认知图式映射的译文建构
2019-02-20孟庆亮
孟庆亮
(嘉兴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浙江 嘉兴 314200)
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思维活动。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是将一种语言符号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符号的行为。从语码学角度来说,是解码和编码的过程。从信息学角度来说,是将一种语言的信息转换为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从解构主义角度来说,是对源语文本的解构与目标语文本的建构过程。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翻译其实就是理解与表达的过程。但如何理解,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以及如何表达,表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其实就是翻译的过程。
在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被应用到翻译研究之前,研究者主要基于译者经验,分析看得到的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但是在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的条件下,几乎无法洞悉译语文本构建的过程,即翻译过程中大脑“黑匣子”的内部运作机制。认知科学的发展为翻译实证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发端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认知科学,在六七十年代得到了较快发展,并于八十年代被翻译研究人员应用到翻译过程实证研究中。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逐渐借助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以及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审视翻译过程。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图式理论与概念映射理论,结合翻译实践,讨论了基于认知图式映射理论的翻译过程,尤其是译文即目标语文本的建构过程。
一、有声思维(TAPs)与翻译过程
(一)有声思维简介
为了了解人在执行某项任务过程中的所思所想,以便分析不足之处,改进完成任务的流程,所以在无法直接观察大脑内部运行的情况下,让被试在解决任务过程中尽可能描述自己的思维活动,也就是“要求受试者尽可能说出在执行特定实验任务时大脑的一切所想”[1]。这就是有声思维法的基本内容,又被称为“心理学口语报告法”。
作为心理学中收集思维过程数据的一种方法,“有声思维法”最初由以格式塔心理学著称的德国心理及语言学家Karl Bühler和瑞士神经及儿童心理学家Édouard Claparède提出并应用到其研究之中。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有声思维作为实证方法之一被应用到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Gerloff,Krings以及Lorscher等人开始运用有声思维法对翻译过程进行探究性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进展。早期的有声思维研究使用的是由Ericsson和Simon所提出的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
(二)有声思维对翻译过程研究的应用意义
翻译是复杂且艰苦的脑力劳动,将源语文本翻译成为目标语文本的过程是在译者大脑中进行的,人们无法像观察机器的流水线那样了解翻译过程中思维的运行情况,所以,长期以来,翻译研究者只能通过研究原材料(源语文本)和成品(目标语文本)分析判断译文的好坏、译者使用的方法和策略等。
在将有声思维法引入到翻译过程研究后,人们可以在译文建构的过程中,窥视到原本被视为“黑匣子”的译者大脑中的思维活动[2]。而且,还可以“探索翻译规律、翻译策略、翻译步骤、发现译者解决问题的方法、存在的问题,从而研究翻译的内在过程,并启示于翻译教学”[3]。通过被试在翻译过程中对信息加工活动的口头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译者对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的认知,所掌握的语言文化信息和知识,所具备的翻译技巧及策略等多种要素在大脑这一思维系统中进行复杂的整合与互动,从而构建出在他能力范围内最为理想的译文。因此,与以往只通过分析翻译结果推测译者翻译策略、翻译决策等活动相比,有声思维实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译者采取某些策略或做出某个决策的认知根源,找出共性和个性问题,从而在翻译教学和培训中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培养出更为优秀的译员,翻译出质量更高的文本。
(三)有声思维对翻译过程研究的局限性
翻译是以结果为评价导向的活动,也就是说,译文的好坏并不取决于译者背景因素,诸如性别、年龄、专业、学历、阅历等,尽管这些方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译者的翻译水平和译文质量。如上文所述,通过有声思维方法可以管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语义取舍、译文的建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有声思维实验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大约十年前笔者曾以职业译员的身份作为被试参加过有声思维实验,对此有较深的体会。
跟其他科学理论一样,有声思维实验方法对翻译过程研究的作用和意义从一开始就伴随各种质疑。早在1991年,Toury就对利用有声思维法研究翻译过程提出疑问,认为这一方法干扰翻译过程,从而影响译文质量;而这一实验方法的开创者Ericsson & Simon则坚持认为,除了稍微减慢速度以外,其实并没有其他影响[4]。基于两者实验内容不同,Jääskeläinen并未表示明确赞成或反对,而是通过自己的实验,认为Toury的观点在词汇层面成立,但在句法层次不成立,因为被试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口语报告会令他们不愿做大的词汇变动,并因此提议就有声思维对翻译结果的影响进行系统的研究,从而提出了有声思维实验方法对翻译过程研究的有效性问题(validity of TAPs)[4]。Kring在研究中发现,口语报告的做法使翻译过程减缓了大约30%;而Jakobsen也指出,口语报告大大减缓了职业译员的信息加工过程,而且有些职业译员会出现尴尬等情况[5]。在对该方法进行大量研究后,Jääskeläinen认为在设计该类研究项目时应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1.被试的选择;2.任务分析;3.翻译任务的类型[5]。
在笔者看来,国外这些学者的质疑并非都有道理。就实验而言,口语报告肯定会影响翻译过程的顺畅性和连贯性,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实验的目的就是为了揭示翻译过程中译者大脑的内部运作机制。但是译者在自己的翻译过程中通常不会使用有声思维。
国内学者也对诸如“有声思维”等翻译研究的实证方法进行了评析,如姜秋霞、杨平认为,翻译活动个体性很强,被调查者言辞表述不尽完整,受试对象多为大学生,并不能充分代表和反映真正的翻译特性和规律[6]。李德凤在分析了十五个通过“有声思维”研究翻译过程的报告的基础上指出,问题并不在该研究方法本身,而是研究人员在实验的设计及实施程序方面不够严格,影响了结果的可靠性[7]。
(四)小结
语言既是思维的载体,同时又反映了思维的状况。但语言的表述远远跟不上瞬间变化万千的思维,也无法较为完备精确地反映思维的真实情况。因此,在有声思维实验中,译者所口述的,只是其翻译过程中大脑内部思维活动的很小一部分,就像是冰山的一角,无法完全呈现冰山的全貌。
从国内学者所进行的有声思维实验来看,大多采用国外的理论和框架,并没有太多的创新,在被试的选择上并没有科学细致的区分。在任务的选择方面,有的采用诗歌作为翻译任务。鉴于诗歌翻译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利用诗歌这一特殊的文学形式作为翻译任务进行有声思维实验,其实验结果也是值得商榷的。
鉴于TAPs的局限性以及翻译过程的复杂性,我们可否借助其他认知理论,从另外一个角度窥探译文生成过程中大脑的运作机制呢?接下来,笔者尝试从认知图式映射角度,初步探讨翻译过程中译文的建构。
二、图式理论与概念映射
(一)图式理论及其应用
据维基百科,早在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之前,康德(Immanuel Kant)就提出“图式”(Schema)这一概念。1926年皮亚杰(Jean Piaget)将这一概念引入心理学,随后又被剑桥大学实验心理学鼻祖、认知心理学先驱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Frederic Bartlett)引入到教育领域。后来教育心理学家R.C.安德森(Richard C.Anderson)将这一概念发展成为图式理论。
在心理学及认知科学中,“图式”指的是将各种知识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按一定规则排列组合起来的思想或行为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先前获取的知识的框架(frame)。
基于图式理论的特点,其被广泛应用在英语教学研究中,主要是对于阅读及听力理解、写作与词汇习得的教学指导。教师利用理论指导自己的教学任务,反思自己的教学效果,无疑会进一步提升英语教学的水平。另一方面,从发表的与图式理论相关的文献也看到,论文总体的同质化比较严重,研究的重复性比较多,说明我们对该理论的认知还不够深刻,应用还比较单调,创新性不够强。当然,有些文章视角独特,对研究者有良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如唐伟胜提出运用图式结构“探索叙事理解的认知过程”[8]。
除了外语教学领域外,将图式理论应用到翻译研究的论文数量相对较少。王立弟认为,“各种场景和文体的知识图式在阅读理解和信息的记忆与再现方面所起的作用对于认识翻译过程中的信息加工处理、记忆储存和译文生成等重要环节都很有启发”[9]。赵颖、杨俊峰则用图式理论探讨商务英语口译能力的培养[10]。
(二)概念映射理论及其应用
概念图(concept map)是描述不同概念、词汇或图像之间关系的图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康奈尔大学教授Joseph D.Novak教授根据David Ausubel的理论提出了概念映射(concept mapping)。Ausubel认为,先前的知识对于学习新概念非常重要。Novak总结说,“Meaningful learning involves the assimilation of new concepts and propositions into existing cognitive structures”[11].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吸收新的概念融入现有的认知框架,这才是有意义的学习。概念映射理论源于建构主义,该理论认为学习者会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概念映射主要有以下目的:
产生想法;设计复杂的构造,比如长文本等;交流复杂的思想;整合新旧知识对学习提供辅助;对理解的内容进行评估或者对误解做出诊断[11]。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Lakoff和Johnson在1980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对隐喻进行了系统的详细分析,并明确提出,除了传统的修辞功能之外,隐喻还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他们认为“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one kind of thing or experience in terms of another.”(Lakoff and Johnson,1980:23)。就其本质而言,“Metaphor is the main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we comprehend abstract concepts and perform abstract reasoning.”[12]。
他们将隐喻分为三种类型: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物质隐喻(physical metaphor)和方向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前两种隐喻都涉及用一个域的概念来建构另外一个域的概念,就是用已知熟悉的域建构未知新的域,即用已知域建构未知域。比如,人们借助完全不同的经验、旅行之域来理解经验和爱情之域,从更专业性的角度来说,隐喻就是从源域(source domain)到目标域(source domain)的映射(mapping)。映射的特点和原理如下:
映射是局部非对称性的,每个映射都是源域与目标域的多个实体之间的固定对应,当固定对应被激活后,该映射能够将源域的推论模式投射到目标域的推论模式上去。隐喻映射遵循恒定原则,即源域中的形象图式结构投射到目标域上的方式与目标域的内在结构是一致的,映射不是任意的,而且基于我们的身体以及日常的知识和经验,不论是概念映射还是图像映射,都遵循恒定原则[12]。
因此,作为对未知世界的认知方式,隐喻就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是利用现有的概念体系了解全新的概念体系,也就是借助既有的知识和经验来探究并学习新的知识。伴随认知语言学的发展,隐喻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被广泛地应用在语言教学、篇章分析、意义解读等方面。
三、认知图式映射与译文建构
奈达提出翻译的基本过程所包含的四个步骤:1.分析源语文本;2.源语文本转换为目标语文本;3.目标语文本的重构;4.读者对译文进行检验[13]146。
在他看来,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就是思维转换的过程;而重构过程涉及词汇、句法及话语特征的重组,以便使读者最大程度理解并欣赏译文[13]152。该阐述主要基于译者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运用有声思维研究翻译过程在当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似乎奈达没有关注或在该书中没有借鉴。
从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来看,奈达对上述翻译过程的阐述已经有些简单化。而且就其第四步来说,笔者认为读者的参与已然是在翻译过程结束之后,不应是翻译过程的步骤之一。接下来,本文尝试借助认知图式与概念映射理论管窥译文的建构过程。
(一)源语图式建构
翻译首先要读懂和理解原文,而原文的信息对译者而言则是全新的知识。根据图式理论,人们在接触新信息的时候,会尝试利用自己既有的认知体系或框架进行解读,并将其纳入该体系或框架用以解读吸纳更新的知识,如此层层递进,不断丰富和深化自己的认知体系。
因此,阅读原文的过程也就是利用自己的语法、语言、文化及专业知识在大脑中建构源语图式的过程。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水仙花》中第一段: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That floats on high o'er vales and hills,
When all at once I saw a crowd,
A host,of golden daffodils;
Beside the lake,beneath the trees,
Fluttering and dancing in the breeze.
我们根据已掌握的词汇知识了解到,这一段诗歌包含一系列表述人称和事物的名词:I,cloud,vales,hills,daffodils,breeze;动词:wander,float,see,flutter,dance;有修饰动词的副词lonely;修饰名词的量词crowd,host;修饰名词的形容词high,golden;表示位置的介词beside,beneath等。从结构上,运用语法知识,我们可以看到各名词之间以及名词与动词、动词与副词、名词与量词、名词与介词、名词与形容词之间的关系。
这样,我们利用既有的认知体系实现对诗歌中新信息的解读,并在大脑中形象地建构出对源语的认知图式。
(二)译文图式建构
根据前面Lakoff和Johnson对隐喻类型的分类,隐喻有物质隐喻、结构隐喻和方向隐喻。在建构了源语的认知图式之后,我们根据既有的认知结构对这些静态及动态现象进行解读,藉此将源语认知图式映射到目标语域中,从而构建出下面的信息及关系图式:
有个人(作者)在独自漫步;天上的云在飘荡;有金黄的水仙花;有湖泊、树木;微风习习;花在摇曳跳舞;等等。
这是物理现象的映射。随后,根据结构隐喻,我们了解到各物理现象之间的关系,人即作者将自己比作在山川幽谷上方徘徊漂浮的云彩,在独自漫步的过程中看到湖边和树下有大片水仙花,在微风中摇曳多姿,构成一幅浪漫优美的画面。
但只有画面是远远不够的。译者要通过翻译活动将在大脑中构建的图式用语言符号传递给目的语读者,同时还要尽量保持原文的音、形、意,使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够在头脑中形成与译者头脑中相近的图式,这就要求译文表达忠实地道、准确流畅、节奏优美。因此,译文图式建构既包括具体物理现象的映射,也包括具体物理现象之间关系的结构映射,还包括抽象意义的映射。当然,图式建构的正确完善与否,与译者既有认知框架及认知能力有很大关系。
Ungerer和Schmid用“An argument is a building”隐喻为例。“Building”作为源域,具有地基、墙体、窗户、房顶等各种特征,其功能在于提供保护;但如果建造不结实的话,整个建筑就会倒塌,这种带有各种属性的有形的格式塔被映射到目标域,有助于我们将“argument”这一抽象说法概念化[14],从而在大脑中形成图式,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和解读。而在寻求“对应”或“匹配”的过程中,译者总是面临各种抉择,并依赖他对两种语言及两种文化的把握,包括经验、知识、感悟以及个人的兴趣和偏好做出决策[15]。
(三)认知图式映射的特点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翻译就是基于认知图式映射的建构,是通过目标语言符号在目标语读者大脑中建构起尽可能接近源语读者在阅读源语文本时所构建起来的认知图式,从而让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信息和近似的感受。当然在建构过程中,既有操纵,也有补偿,有时基于宣传之目的,还可能会违背原作的意图。译文图式建构有以下特点:
(1)双向而非单向
根据Lakoff和Johnson的分析,概念隐喻映射发生在源域和目标域之间,是将源域概念投射到目标域,实现对目标域的认知,基本是单向映射。章宜华认为,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来看,翻译实际上是一种由源语文本向目的语文本进行语言和概念图式映射和整合的过程,具体反映为两个输入认知域之间的某种关联或联系[16]。本文认为,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图式映射并非单向映射,而是双向映射,既有源语到目标语的映射,也有目标语向源语的映射。
(2)多次循环往复
鉴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译文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反复的思考和推敲,有时一个词的使用都会“旬月踟蹰”。通过语义建构、语法建构、文化建构等等多角度多维度建构,对原文解读次数越多,对内容的理解就越深刻,从而译文的表述就越准确;反过来,在建构译文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加深和促进对原文的理解。
(3)动态而非静态
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图式映射是动态而非静态映射。由于对源语文本的认知由浅入深,因此大脑中构建的源语图式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不断从大体轮廓到细枝末节。在译稿杀青之前,译语图式也相应地不断调整和改进,以期达到音形意的最佳结合。而且,在翻译过程中要对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对有的文化要素进行移植,从而使译文真正达到与原文的对等[17]。
(四)小结
从认知图式映射角度来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借助自己既有的知识和经验,通过阅读构建源语图式,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认知越是全面深刻,则所构建的图式越详尽逼真,映射到目标语的图式也越全面准确,然后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隐喻认知加工,建构出忠实生动、贴切得体的译文,从而使目标语读者获得与源语读者近似的感受。
四、结语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翻译作为复杂的脑力活动,译文的生成或建构也是极其复杂的思维过程。尽管运用有声思维等实证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译者翻译过程中的思维状况,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做出某个决策的理由和依据,但它只是译者思维活动的冰山一角,远非“黑匣子”的全部内容。
认知图式映射从认知心理学及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了译者对原文的阅读和理解过程,以及在运用图式理论所提出的认知框架对源语文本解读和加工后形成图式映射到目标语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了解译文建构的过程,从而分析产生不同译本的译者主体原因,为翻译培训及译者提升自我修养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