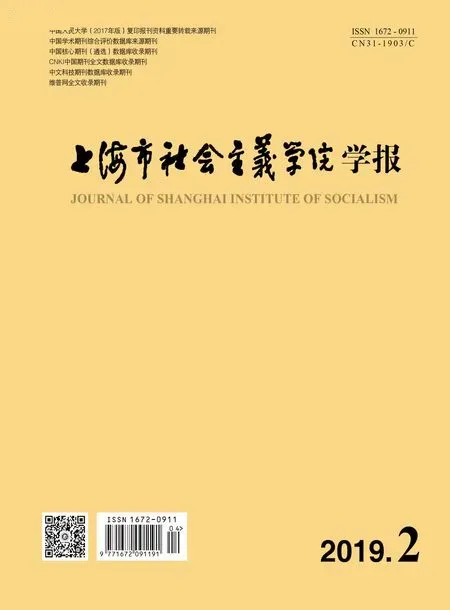艰难曲折的中文弥撒路
2019-02-19张化
张 化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研究上海研究基地,上海200083)
弥撒是天主教对圣体圣事礼仪的称谓,源于拉丁文Missa。弥撒是天主教最重要、举行得最多的礼仪,教会的主要信仰活动都围绕着弥撒进行。1963年以前,世界各国的天主教会均用拉丁文做弥撒。拉丁文在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起过巨大作用,但在社会生活中,作为一种被人们日常使用的口语,公元10世纪左右在欧洲已经死亡。18世纪,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就曾抱怨过拉丁文的难学。中国人学习拉丁文尤其困难。在拉丁弥撒年代,学习并使用拉丁文,成为中国人晋升神父的拦路虎。修生想成为神父,需花大量精力用于学习拉丁文。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修生用于学拉丁文的时间是:备修院3年,每周2节课;小修院3年,每周8节课[1];大修院7年,除了上拉丁文专业课,不少课程直接用拉丁文讲授。教徒望弥撒时听不懂拉丁文,不明白弥撒的内涵,望弥撒成为履行宗教义务的一种仪式。从晚明天主教再传中国起,用中文做弥撒一直是中国信徒和在华传教士难圆、未圆的梦。
1584年,罗明坚①编写的 《圣教天主实录》在广州出版。此书采用中、西方两人对话的形式,简要阐释天主教教义,实际上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第一本中文 “要理问答”。此书极受欢迎,广为传播[2]26-27。 1595年②, 利玛窦③编写的 《天学实义》在南昌出版。此书后名 《天主实义》,是一本比较详细的 “要理问答”[2]41。1602年, 经龙华民④、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编译,在韶州出版了 《圣教日课》。这是一本信徒每日念诵的祈祷经文。为适应中国文化,该书大量使用四六骈偶句,讲究对仗,简明、华丽而庄重。1665年,南怀仁⑤和利类思⑥修订后称为 “定本”。事实上,此后仍然不时修订和重印,延用到20世纪90年代。
1610年,利玛窦去世,龙华民接任耶稣会中国区会长。为保障教会在遇到教难时能够延续,他准备大力培养本地神父。但当时的中国候选人大多是三四十岁,或者更年长的成年人,如果一定要他们学会拉丁文后再晋升神父,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1613年,龙华民派金尼阁⑦回罗马商请几个在中国传教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614年,金尼阁抵达罗马,向当时行将离任的耶稣会总会长C.Aquaviva呈上 《五十 “建议”》,内容包括仿效希腊和斯拉夫教会,准许以本国语言翻译经典,让神父用中文举行圣祭、圣事,念诵日课。金尼阁还特地征询了利玛窦的老师R.Bellarmine枢机的意见。枢机指出,历史上有过先例,此事有可行性。1615年1月15日和3月26日,教廷召开了2次会议,教宗保禄五世参与了会议[3]。会议特准耶稣会士在中国以高雅的中文翻译圣经、举行弥撒及所有圣事及圣仪、日课祈祷;但须符合罗马礼规,并得到主教同意。同年6月27日,保禄五世以最高权力颁布以上特准,文件名称为:Letter Romanae Sedis Antistes,规定中国人可以担任神职,可以用文言文翻译所有礼仪经典,包括 《圣经》《弥撒经本》《礼书》《大日课经》,神父可用中文举行弥撒圣祭、圣事、诵念日课[4]180。这是让中国人更快掌握经典,主持宗教活动,促进神职人员本地化的重要举措。但此时,耶稣会总会发生人事变化,T.Vitelleschi接任总会长。他提议由特派视察员决定是否要执行这一特准文件。特派视察员由葡萄牙传教士卫方济⑧担任。这时,列强之间正激烈争夺对华传教权,形势对葡萄牙非常不利:1608年,教廷宣布托钵修士前往远东可自由选择路线,不必经葡萄牙的里斯本。当时在亚洲活动的托钵修士以西班牙为依托。另外,法国崛起,强力影响教廷。此后不久的1622年,教廷即接受法国教士的建议,推行宗座代牧制,规定在传教区设立代牧区,隶属教廷传信部,由宗座代牧代教宗管理。这些都是架空葡萄牙保教权的举措。如果允许用中文做弥撒,就会有大量中国人担任神职,将大大推进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这对葡萄牙保教权将构成致命打击[5]。卫方济视察的结果是不能执行这一特准,中国人不宜担任神职。
但是,在华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合作翻译礼仪经典的步伐并未停止。约1620年,费奇观⑨在南京出版 《诵念珠规程》,解释何谓 《玫瑰经》和如何念诵,配以15幅杂有中国传统绘画风格的木版画。该书和 《圣教日课》成为中国信徒日常、特别是望弥撒前后主要诵念的内容,开启了中国天主教徒念经的传统[6]。
要将礼仪经典译成中文,首先要解决 “Deus”的译名问题。1627年12月至1628年1月,在华传教士在上海的嘉定讨论礼仪问题,包括祀孔祭祖和 “Deus”的译名等问题,史称嘉定会议。这是一次空前盛会,除有11位传教士参加⑩,还有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孙元化列席[4]237。几乎包括了在华著名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为示郑重,会后还将决议案送到北京,征询因任职钦天监不能到会的邓玉函⑪、汤若望⑫的意见。会中争论非常激烈。1621年回到中国、精通儒学的金尼阁因竭力主张己说,竟过劳得病,同年去世。讨论的决议是:祀孔祭祖问题,沿用 “利玛窦规矩”;“Deus”译名采纳龙华民意见,译为 “天主”,不再用 “上帝”“天”[7]。译名问题解决后,1628年,被称为 “西来孔子”的艾儒略⑬编写的 《万物原真》在北京出版,这是一本简明的基督教哲理书。1629年,他编撰的 《弥撒祭义》(2卷)在福州刊印。这是第一本用中文阐述弥撒礼仪的书,包括弥撒的意义、祭祀的概念、教堂和祭坛如何布置、祭衣的样式、弥撒礼仪的规范和应达效果、辅祭方法等。1635-1637年间,他编印的 《天主降生言行纪略》(8卷)在福州出版,这是 《圣经》四福音书的节译本,主要介绍耶稣生平。他还编写了 《涤罪正规》(4卷)、《性学觕述》(8卷)、《领圣体要理》(2卷)等 30 多种书籍[2]152-157。1636 年, 阳玛诺⑭在北京出版译著 《圣经直解》(14卷),这是一年中各主日、节庆日规定诵念圣经章节的解释,附有对教规的思考。此书附有索引,开了中文书籍附索引之先河。1642年,他在北京出版了 《天主圣教十诫直诠》2卷。他还出版了 《圣若瑟祷文》《天神祷文》等十多种天主教著作[2]125-128。 他们的努力,为中文弥撒打下了最初的文献基础。
1659年,在福建传教的法国籍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陆方济⑮等人再次请求教廷批准行中文礼仪,选拔中国神父。这时,保禄五世1615年的特准竟被遗忘,教廷专设审查委员会进行讨论。同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⑯颁令⑰,仍要求晋升神父者必须掌握拉丁文;但降低了要求,只需勉强用拉丁文背诵经文。1660年,审查委员会发现了1615年的特准,但仍建议先调查中国的信徒人数、可能晋升神父的人数等情况,并试行教他们学习拉丁文。1664年,全体在华传教士再次申请执行1615年的特准,祝圣数十位年长的中国儒者为神父,让教会在受到迫害时得以保存,但遭到多明我会士闵明我⑱的反对。1671年,殷铎泽⑲受派抵罗马,再次提出申辩和申请。1672年2月15日,教廷信理部质疑翻译中文礼仪经书的需要及可能性,驳回其申请。
尽管罗马的意见不确定,在华传教士并未停止译著礼仪经书的步伐。1650年,在上海传教的潘国光⑲所著 《十诫劝论圣迹》(1册)在河南刊印。这是一本用简洁易懂的文字讲述十诫的书。潘国光有10多种著作,包括 《圣体规仪》(1册),论述圣体圣事的信条和领圣体的仪式,并附图加以说明;《圣教四规》(1册),解释各项礼仪规定;《瞻礼口铎》,注解各主日和大瞻礼日用的福音经。利类思被称为17世纪中文修养最好的传教士。从1654年起的20多年中,他由安文思协助㉑,选译了多玛斯的 Summa Theotogica㉒,题名 《超性学要》(30册),陆续出版。他按照南怀仁的指示和准许,加紧翻译、出版中文经典。1670年,他把整本弥撒经书译成 《弥撒经典》(5卷),订为2册,书名分别为 《中文日课经》《中文弥撒经》,封面上大字烫印由教宗保禄五世钦准。1675年,他翻译了 《七圣事礼典》(1册),介绍如何施行7件圣事、为亡者作 “安所”,以及各种驱魔、降福仪式,附有相关经文。他编译的 《司铎㉓课典》(1册),是神父通用的日课经本,收录全年所用瞻礼经文和一般礼规。1675年,他在北京出版 《司铎典要》(2卷),是神父使用的神工书,分别论述神父的地位、职务、弥撒日课、圣事、超性三德、十诫和教规。他的译著共有20多种,包括 《善终瘞茔礼典》(1册),这是一本对临终者用的祈祷词和用于葬礼的经文;《圣教要旨》(1册),这是一本对教理的简要说明。1675年,柏应理㉔出版 《永年瞻礼》(3卷),这是一本瞻礼日历。南怀仁也译著了 《教要序论》《告解原义》《圣体答疑》等书籍。总之,经艾儒略、阳玛诺、潘国光、利类思等人大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至1675年,已成功汉译全部需用的经典㉕。
1676年,南怀仁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区会长[8]。第二年,他致函耶稣会总会长,告之 《弥撒经典》《圣事礼典》《司铎课典》及礼仪所需用的神学书籍已译成,希望能执行1615年的教宗颁令、祝圣中国神父。非常不幸,遭到视察员S.de Almeida的反对,明令中国人晋升神父必须学习拉丁文,只能行拉丁文礼仪。1680年,南怀仁派柏应理携带全套3400余册中文译本赴罗马,申请即时执行1615年的特准。1684年,柏应理抵达罗马。1685年,教宗依利诺十一世大致同意,授意传信部讨论。但传信部、圣部、审查委员会再次不准。同年,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上书教廷,请求引用1615年特准,祝圣12位不谙拉丁文却愿意传教的中国教徒为神父。1688年8月1日,罗文藻祝圣了3位神父。3人中,吴渔山57岁,曾2次结婚;刘蕴德60岁,曾2次结婚;万其渊54岁,单身。他们能勉强用拉丁文背诵一些经文,却不懂意思。罗文藻宽免他们每日应该诵念的 《大日课》经,而以别种经文替代[9]。其实,这年的3月29日,教廷审查委员会已经拒绝了罗文藻的请求,且质问罗文藻是否祝圣过不懂拉丁文的人,如果祝圣了,要暂停使用职权,直到学会拉丁文为止,并表示:拒绝再受理同类申请[3]。因交通和信息传递困难,3人已然受了祝圣。1704年,教宗下令禁行祀孔祭祖礼仪。清政府随即禁教。1715年,教宗克雷芒十一世公布 《自登基之日》通谕,重申这一禁令。此后100多年中,中国对天主教的查禁越来越严,传教士被驱逐,只有极少数人躲在民间秘密传教。当然,华人神父更易藏匿。此后,在华传教士至少在1724、1752、1753、1789年反复以各种名义向教廷提议执行1615年的特准,均遭驳回。教廷还组织力量,按照 《自登基之日》通谕的精神复核中文 《弥撒经典》,认为该书内容大多有误,终被弃用。用中文做弥撒和人才本地化的进程被中止。
事实上,在清朝政府严禁天主教、传教极为困难、中国信徒又迫切需要的背景下,中文经典的译著、出版和使用还是有所进展。1689年,穆迪我㉖在武昌出版 《圣洗规仪》(2卷),解说洗礼及施洗仪规。冯秉正㉗是18世纪的重要译著者。1738年,他在北京刊印 《圣年广益》(4卷),是全年每日所敬诸圣的列传。他的译著有十几种,包括:《圣心规条》,是敬礼耶稣圣心的简要经文和祷文;《圣经广益》(2册),是每日弥撒福音经的诠释;《避静汇钞》,是神父的避静手册,包括避静的注意事项、规则及每日指定阅读的材料等。坚持隐藏在江南秘密传教的奥地利籍传教士南怀仁㉘也编著了一些实用的礼仪用书。1778年,他颁行 《圣母领报会规程》,面对耶稣会解散后的形势,重新规范教会团体。他还颁布 《昭事堂规》18条,规范教徒生活,包括堂内礼规和教徒应守的准则。这些译著从发布起至19世纪早期,一直被中国信徒广泛使用。
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告诉我们:“1948年我在罗马读书时,经常去拜望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驻梵蒂冈公使吴经熊博士,成为朋友,他私下告诉我,教宗庇护十二世亲自交给他个任务:把拉丁文的弥撒经文译成中文,教宗说拉丁文难,对中国人来说特别难,为了中国教徒便于理解弥撒,参与弥撒,应采用中文。”[10]3671949年3月10日,教宗批准使用中文举行礼仪。因政局骤变,未能推进。
1963年12月4日,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公布 《礼仪宪章》㉙后,各国均开始用本地语言做弥撒。中国大陆教会因与梵蒂冈沟通不畅,未能施行。1967年,台港澳教会开始用中文做弥撒。1988年,金鲁贤主教掌管上海教区后,即着手进行弥撒礼仪改革。他请了香港教区教礼仪专家罗国辉神父等人来介绍、教授新的礼仪。1989年9月30日,在佘山修院举行了第一台中文弥撒,随后在上海教区内逐步推广。使用的弥撒经本以台湾经本为基础,加以适当修改[10]368。佘山修院不再开设拉丁文课程。1992年9月,全国主教代表大会决定各教区可按情况推行中文礼仪。上海教区主动帮助推进:印了大量礼仪经书,送给各地,包括30万套弥撒经书、几千套台湾版中文大日课经、比较简单的日课经、施行圣事手册等;佘山修院开设礼仪训练课程,培训各地神父[11]。中文弥撒在各地迅速推广,为天主教中国化奠定了礼仪基础。目前,中国天主教会中会做拉丁弥撒的老一代神父绝大多数已经离世,中青年主教中只有极少数人会做拉丁弥撒,中文弥撒将不可逆转地成为通用的礼仪形式。
注释:
①即 P.Michel Ruggieri,字复初,1543-1607,意大利人,耶稣会士,1579年来华。
②此书出版年份有不同记载,笔者引用费赖之所著,梅乘骐,梅乘骏译,由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出版的《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一文第41页之说。
③即 Matthieu Ricci,字西泰,1552-1610,意大利人,耶稣会中国区首任会长。
④即 Nicolas Longobardi,字精华,1559-1654,意大利人,耶稣会士,1597年来华。
⑤即 Ferdinand Verbiest,字敦伯,一字勋卿,谥勤敏,1623-1688,比利时人,1659年来华,耶稣会中国区会长,清朝钦天监监正。
⑥即Louis Buglio,字再可,1606-1682,意大利人,耶稣会士,1637年来华。
⑦即 Nicolas Trigault,字四表,1577-1628,比利时(今法国)人,耶稣会士,1610年来华。
⑧即F.Vieira。
⑨即 P.Gaspard Ferreira,字揆一,1571-1649,葡萄牙人,耶稣会士,1604年来华。又,该书作者是费奇观或罗如望学界未定。参曲艺:《诵念珠规程——17世纪初第一本含插图的中国基督教书籍》,载袁熙旸主编 《设计学论坛·第2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页。
⑩这11人中有8个会议代表:龙华民、郭居静、金尼阁、高一志、费奇观、艾儒略、毕方济、曾德昭,3名观察员:李玛诺、阳玛诺、黎勃劳。见康志杰《明末嘉定天主教开教考述》,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编:《嘉定文化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⑪即 Jean Terrenzou Terentio,字涵璞,1576-1630,日尔曼人,耶稣会士,1621年来华,会9种语言,以名医生、哲学家和数学家蜚声德意志。
⑫即 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字道未,1591-1666, 德 国人,耶稣会士,1622年来华,著名科学家。
⑬即 Jules Aleni,字思及,1582-1649,意大利人,耶稣会士,1613年来华。
⑭即 Emmanuel Diaz Junior,字演西,1574-1659,葡萄牙人,耶稣会士,1610年来华。
⑮即 Mgr Francois Pallu,又作巴吕、巴録等,1626-1684,法国人,巴黎外方传教会创始人之一。
⑯即 Alexander VII。
⑰即 Super Cathedram。
⑱即 D.Navarratte,1610-1689,西班牙人,多明我会士,1655-1669年在华,后任多明我会总主教。
⑲即 Prosper Intorcetta,字觉斯,1625-1696,意大利人,耶稣会士,1659年来华。
⑳即 Franciscus Brancati,字用观,1607-1671,意大利人,耶稣会士,1637年来华。
㉑即 Gabriel de Magalhaens,字景明,1609-1677,葡萄牙人,耶稣会士,1640年来华。
㉒即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
㉓司铎即神父。
㉔即 Philippe Couplet,字信末,1624-1692,比利时人,耶稣会士,1659年来华。
㉕这一判断引自刘嘉祥编著:《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北,天主教主徒会,1992年版,第290页。
㉖即 Jacques Motel,字惠吉,1618-1692,法国人,耶稣会士,1657年来华。
㉗即 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字端友,1669-1748,法国人,耶稣会士,1703年来华。
㉘即 Godefroid-Xivier de Laimbeckhoven,字莪德,1707-1787,奥地利籍原耶稣会士、南京教区主教。
㉙即 Sacrum Concil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