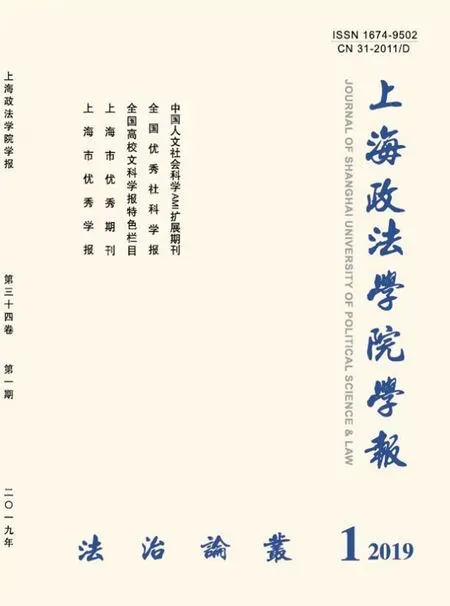法律解释的认知逻辑进路
2019-02-19宋保振
宋保振
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法律解释的价值必须要通过其运用来实现。从当下司法实践来看,法律解释的运用难题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解释权限模糊导致“不敢”解释;第二,裁判后果导向“不想”解释;第三,运用标准欠缺“不会”解释。如果说前两者更多涉及解释体制和司法理念等宏观内容,那么解释标准欠缺就直观体现了裁判实践中法律解释方法“运用难”,这也被称为“法律解释的困境”。①参见桑本谦:《法律解释的困境》,《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在我国法治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很难完全把握和运用法律解释这样一种抽象方法,另一方面也和当下法律解释研究过于“重理论”和“重西方”不无关系。当前,尽管越来越多的法律人开始秉持法律解释的智识性理解,但是考虑到各种解释方法运用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判断,法律的整体性和融贯性、裁判的逻辑标准与政策标准以及解释结论的可接受性,都成为解释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相对于恪守解释理论可能引发的“风险”,现实促使法官必须立足中国语境,从一种发展、多样和开放的视角来把握法律解释。其实裁判者也深知,无论法律解释理论建构的多么完善,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褶皱”都不可能被“完全客观”地填平,它仍是人的主观活动。至多就是依靠一些抽象的解释标准,证成法律渊源与法律决定之间的大前提,并以之作为“转换规则”弥补法律论证或推理中的“跳跃”。因此,如若想现实客观地掌握和运用法律解释,除了必要的教义学研究之外,还离不开一种社会科学上的认知研究。借助认知科学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准确性,真实反映法官解释法律的思维过程,进而归纳和总结此过程中的逻辑性思维规则,并将此运用于后案裁判。这不仅完善了传统法律解释教义学研究,更是对法律解释“理论指导实践”目标的实现。
一、法学视角下的认知逻辑界定
认知科学作为21世纪最大的新兴交叉学科,主要有两方面使命:一是揭开人类心智的奥秘,如心理学和神经学的相关研究,二是促进某些学科的发展,认知逻辑就是其中之一。认知逻辑(cognitive logic)是将现代逻辑应用于人的认知活动而形成的一个专门逻辑领域,也可视为现代逻辑和认知科学交叉所形成的新的逻辑领域和学科群体,是借用认知科学的分析框架对逻辑体系的再建构和再认识。从当前研究来看,认知科学的六大支撑学科——哲学、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人类学、神经科学,都可与逻辑学相互交织产生新的逻辑学科类型,它们都是认知逻辑的重要内容。如哲学逻辑、心理逻辑、语言逻辑、人工智能逻辑、文化与进化逻辑和神经网络逻辑。这些学科有的早已存在,如哲学逻辑、人工智能逻辑;有的正在发展,如心理逻辑;有的仍处萌芽,如文化与进化逻辑。①参见蔡曙山:《认知科学框架下心理学、逻辑学的交叉融合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由于认知科学的经验性质,认知逻辑能够更好地实现人类认知过程中心理过程与逻辑过程的统一,并因此具有经验性和非形式性两个基本特征。
在法学领域,认知逻辑作为对传统法律逻辑的拓展,构成新型法律逻辑的重要内容,并同时借助认知科学对法学研究的两方面影响发挥作用:在理论方面,认知研究解释了公平、正义等基本概念的心理机制和神经基础,展示出认知偏见对涉法思维的影响、冤假错案的产生在认知层面的原因;在工具方面,通过控制实验等研究方法,为理解涉法行为的心理——神经过程、司法判断等带来可能。②参见秦裕林、葛岩、林喜芬:《认知科学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述评》,《法律与社会科学》2017年第2辑。法学与逻辑学的密切关系是在法学领域开展认知逻辑研究的内在机理。一直以来,法律与逻辑就不可分离。从法律方法论的角度看,逻辑规则在解释法律、论证法律的时候有固定法律意义的功能。法律学人必须认真地对待逻辑尤其是形式逻辑,这对法律思维方式的形成、法治建设、法学教育等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此过程中我们也认识到,哲学的、逻辑的、语言的、修辞的和解释的方法都对法律判断有着重要的影响,法律方法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这些学科的支持。体现在当前,在国外法律逻辑学的不断刺激下,近年来我国迅速形成了借助语用学、言语行为理论、论辩学、商谈理论、修辞学、非形式逻辑、人工智能、对话理论等新兴理论研究法律逻辑的新进路。其中就充斥着大量的认知逻辑内容。在此过程中,法律解释作为人类理解和运用法律的主观活动,必须立足中国语境才能切实实现解释的确定性和妥当性目标。在传统的形式逻辑之外,为保证道德、政策、社会效果等“法律外因素”以合理的方式融入裁判,认知逻辑研究就成为一条必要进路。
二、法律解释中的认知逻辑要素
法律解释的认知研究拓宽了原有的解释研究进路,力图实现法律解释“理论指导实践”的学科目的。此研究以认知逻辑为指导,通过还原现实解释过程,探讨指引裁判者行为的逻辑思维规则,并进一步将这些规则性内容总结提炼为法律解释规则。
(一)法律解释的认知研究仍以法律逻辑为支撑
认知模式是在一定逻辑指引下,学习主体基于实践对信息进行获取、处理的模式。在该模式下,所有的“个体性”判断都不是完全主观性的反映,而是可以从一般性事件中归纳概括得出。不同主体的情感和行为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身认识世界、处世的方式和方法决定的,也即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了他内心的体验和反应。在此之下,法律逻辑就成为裁判者的行为规范,并通过在学科交叉背景下所衍生的新形式——认知逻辑得以运用。该认知逻辑作为一种知识推理,以认知语言为基础,是一种关乎认知过程及其规律的逻辑系统。③参见蔡曙山:《认知逻辑的对象、方法和体系》,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体现在法律解释过程中,法律解释的认知模式就是在法律认知逻辑指引下,建构体系性的法律解释规则,从而对裁判者的活动进行思维指引。这些内容主要包括:哪些因素影响到法官的解释活动?以及在哪些因素考量下进行自由裁量?法官如何对待疑难案件?当不同解释方法之间出现冲突时又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等。
因此,在法律解释的认知研究中,正确把握法学与逻辑的关系就成为一项重点内容。自笛卡尔以来,以几何学为范式的公理化思考就逐渐渗透到法学研究之中;之后,以德国的概念法学和法国的注释法学为代表的法律解释观认为,法律适用只是逻辑三段论推论过程,即使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也只不过是通过对概念的分析,再构成新的法律概念;自19世纪下半叶,此种思维范式受到了强烈的批判,“理解——解释——运用”三位一体的本体论解释学相继而生;20世纪之后,伴随法律解释理论的实践运用,学者逐渐认识到解释的复杂性,为了在解释活动中充分关注价值要素,社会科学就成为理解法律解释的一条重要进路,以及为了探索解释过程中所运用的思维规律,学界开始从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角度来研究法官对法律的运用和解释。此时裁判者所主要运用的逻辑已不仅仅是三段论基础上的形式逻辑,还有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用逻辑演算的方法来研究含有诸如知道、相信、断定、认为、怀疑等认识模态词的认知逻辑。法律解释也就不再被认为是“机械司法”,而是一种规则性的法官思维活动。
(二)指引解释者行为的逻辑思维规则
在法学领域,逻辑一直具有一种“固法”功能。①参见陈金钊:《逻辑固法:对法律逻辑作用的感悟》,《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7期。在接受了新修辞学、语用学、心理学、诠释学的影响后,对于法律逻辑的运用除了经典逻辑之外,开始重视具有价值要素考量的多主体认知逻辑。法律逻辑本质是法律思维准则,而理性的法律方法的运用,必须要遵循一定的思维规则。“逻辑从来都不是格式化的符号,而是特定思维规律的呈现。”在形式逻辑中有许多对思维规律的揭示,这些规律构成了一般的思维模式,并指导裁判者思维。很多时候,法官虽然不能直接依据逻辑规律来衡量法官断案得出的结论是不是正确答案,但我们却可以用逻辑规律作为标准,衡量其裁判的合理与可接受性。逻辑本身就是思维规律的总结。
这种建立在认知性法律逻辑基础上的法律解释同传统“依法办事”思维下的法律解释具有重大区别。传统“依法办事”思维下的法律解释在逻辑上主要是依据无主体的、主客二分的、无价值承载的、静态封闭的道义逻辑,忽视了法律解释的开放性必须要求一种承载诸多利益或价值主体,并由多主体参与和博弈的动态法律逻辑。除此之外,在研究方式上,之前的法律逻辑研究多采用逻辑加案例的方式,没有切实深入到裁判的解释过程中把握逻辑思维规则,割裂了解释与逻辑之间的关系。这种抽象研究的直接结果就是难以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解释逻辑或认知模式,所谓“逻辑固法”的功能并未能有效发挥。认知逻辑和传统经典逻辑与非形式逻辑都密切相关,其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单主体到多主体、从单模态到多模态、从不活跃的主体到活跃的主体的过程。如果从解释规则角度来审视,规范法律解释和实质法律解释共同构成法律解释的认知内容,也是建构法律解释认知模式的重要素材。一种开放性的法律解释必须建立在能够指导法律解释活动的法律逻辑基础之上,而这种逻辑又必须包含反映人脑认知规律的论证和推理规则。因为,只有通过建立可废止性的论证规则,才能一方面保障在法律解释活动中充分发挥法律逻辑的“固法”功能,确保法的安定性和可预见性;另一方面通过运用特殊情形下的非形式性逻辑规则,避免形式性法律逻辑规则的僵化,引入实质性论证以保障法律解释和适用的合理性。根据对现实案例的分析亦可得知,在认知模式下这些逻辑思维规则也通常以解释方法运用标准的形式呈现,进而发挥规范或指引裁判者思维的作用。此时,基于实践的解释方法的认知研究也就主要集中于探讨解释规则的运用。
三、法律解释认知研究的具体方式
既然明确了认知研究是弥补传统法律解释规范研究之不足的重要路径,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寻找此研究的恰当方式,以使之既能反映当下的法律解释实践,又符合法律解释的逻辑要求。根据当下所取得的相应研究成果,此研究方式可归纳为如下3类。
(一)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研究解释者的思维规律
在当下的法学与认知科学交叉研究中,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出发探究法官的思维规律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诸多学者也从此角度出发展开了相关研究,如李安、杨彪、陈林林、李学尧、郭春镇等教授。此时的认知心理学已经超越狭义心理学的范畴,而是强调整个认识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创造性、问题解决、言语和思维等。具体到法学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有关司法决策的非条件因素及认知偏差的研究,如司法假定、锚定效应、框架效应、经验法则等,特别是在裁判疑难案件时尤为典型。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基于案例的实证分析和模拟实验是两种主要的研究方式,成果主要集中于诉讼程序方面。然而,司法裁判毕竟不是科学实验。无论法官在裁判时进行了何种科学性思考,裁判结果都必须得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此时,隐藏在裁判文书背后的司法认知就必须通过恰当的法律方法表达出来,法律解释就是一种最常用的方式。这也正是在法治建设新时代,法律解释之所以必须要将传统教义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此时引导裁判者解释的除了形式逻辑之外还有一种认知逻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研究解释者的思维规律。对此正如有学者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出发对法律发现的再认识:法的发现是一个心理的过程,它必然遵循人的心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发现”实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心理的过程”。法律心理学研究表明,法官判断心理即导致做出决定的内在过程和法律中的公开求证过程有着本质的区别。①参见陈增宝:《认知心理学视野中的法律发现》,《人民法院报》2016年3月18日。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法官心理判断过程中的逻辑思维规则清晰明了地展现出来。
(二)结合具体裁判实践完善解释方法运用标准
如上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所研究的解释者思维规律正是解释方法运用的实践标准。一直以来,研究者并未放弃对解释方法运用标准的追求,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是有关“解释方法位序”的探讨。②自萨维尼提出法律解释“四要素”以来,绝大多数法律解释研究者都将解释方法运用标准聚焦于“解释方法位序”,而该位序存在与否也成为学者们支持或反对法律解释作为“一种方法”的理论焦点。对其表现形式,有研究者坚持一种严格的“效力位阶表”,但更多学者认为各解释方法之间要么是相对独立的,其运用是社会需求的反映,如苏力教授、梁治平教授和桑本谦教授等;要么认为各解释方法运用只是具有“文义—体系—目的”的大体顺位,如梁慧星教授、张志铭教授、葛洪义教授、陈金钊教授等。但是从其所做的“法律解释方法运用实证调研”结果来看,该“解释方法位序”理论的司法实效远未达到建构者们的预期。③参见曹磊、宋保振:《法官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的实证分析》,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20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解释的客观性追求而言,不同解释方法的运用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但也并非表明罗列在此“方法清单”上的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都天然地具有一种制度性、格式化、所有案件都必须符合的程序性指令。而且从法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属性及实践面向来看,试图建构一种“计算机程序”或“化学元素周期表”式的位序模式也是徒劳和不现实的;第二,法律解释方法运用标准作为一种“实践技艺”,必须立足中国语境并反映新时代要求。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完善和案例指导工作全面开展,当下司法中,法源体系不断开放,道德、政策、社会效果等“法律外因素”逐渐以合理的方式融入裁判,解释标准已不单单是传统的法教义学规范,而是必须要契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科技背景来把握。
也即,忽视真实的“法官思考过程”最终导致法律解释在描述层面上归于失败。法律解释首先是法官对法律意义的认知过程,然后才是语言组织和逻辑论证。偏见、启发式等认知要素对解释方法选择的影响丝毫不逊于规范的教义学说教。①参见王云清:《法律解释的去理论化与立场转换——认知心理学的启示》,《法律科学》2014年第3期。此时如何从认知角度出发,现实把握法律解释的多元化标准就具有重大意义。人类认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认知科学更是一个包括哲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等复杂交叉的学科体系,我们很难从其中直接获得指引法官进行法律解释的方法。但不容否认的是,法官运用和解释法律本身就是一个包含诸多逻辑标准和思维规则的认知过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这种认知模式的研究,发掘出具有实践上可操作性的逻辑思维规则,以此规则指引正确的解释方向,避免解释中的认知谬误,进而解决法律解释的运用难题。这也是在理论层面上认知科学对法学的影响。法律解释为了满足其实践要求,必然要融入大量的法官裁判经验、司法规律等内容作为裁判的规则或“潜规则”。即在面对部分疑难案件时,当法的渊源与待裁决案件的大前提之间出现推理空隙时要准确、恰当地予以填补,从而使得从法律规范到裁判结果的转换构成一个合法亦合理的演绎推理,如司法决策形成中的贝叶斯定理运用。此时,为了对法官的活动进行指引,同时约束解释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主观恣意,法官就必然转向对特定思维规则和标准的依赖,进而明确不确定概念的范围,减少选择的可能性,并同时增强法律对其活动的约束力。②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页。
(三)基于法律推理建构法律解释的认知模型
从操作角度来看,法律解释认知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借助认知科学的分析框架,将法官解释过程中所考量的因素进行量化,进而建构一个相对完整的法律解释认知模型。比如,在当前的证据分析问题上,贝叶斯推理已逐渐得到认可和适用,通过可量化的客观标准,成功避免了经典统计推理中的主观因素问题以及先验回避问题。③参见任晓明、黄闪闪:《贝叶斯推理的逻辑与认知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此时,面对法律规范中的不确定概念或法律漏洞,裁判者所依据的就不仅仅是目的解释、漏洞补充和利益衡量等方法,还有他们作为判断时真实的思维逻辑。这种通常作为神经科学之内容的思维逻辑若想真正实现对裁判的指引作用,必须要在专业化的分析模式中,将价值等主观要素以可认知的方式进行考量,并使之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构建一种推理模式。如麦考密克和萨默斯针对法律解释使用的不同方法或准则,提炼出11类法律解释论证。此解释论证过程通过认知逻辑将影响法官判断的价值因素规范化考量,避免无标准所引发的解释恣意。此认知模式既符合一般的解释论证要求,即有完备的大前提(解释保证)、小前提和结论,还与具体司法中的认知性法律解释活动相结合并抽象出形式化的规则,从而更好地协调法律解释确定性与妥当性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