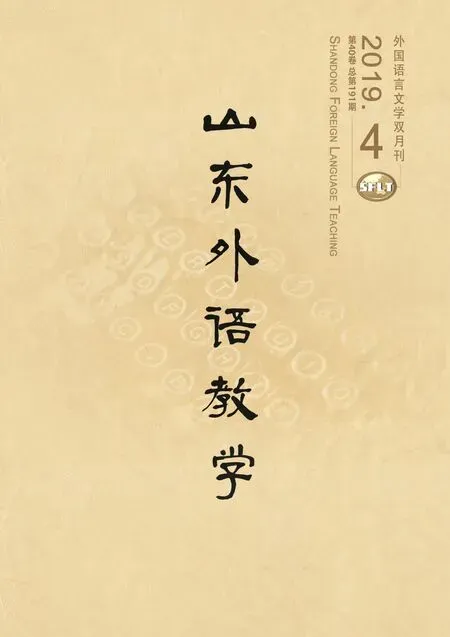基于容器隐喻的认知文化霸权
——从《黑孩子》中姥姥的身份谈起
2019-02-19蒋展
蒋展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杭州 浙江 310058)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社会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在《狱中札记》(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ofAntonioGramsci,1971)中将文化霸权定义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Gramsci,1971:57),称其包含了“一种大众对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群体施加于社会生活的普遍指令的自发性服从”,并认为这样的服从“来自统治群体因其地位与对生产世界的作用而产生的权威(及随之而来的自信)” (Gramsci,1971:12)。这样的定义从统治阶级的角度强调了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的思想文化上的统治。顺着这个思路,对于文化霸权的研究,便多是探讨统治群体所采取的手段,从外在的角度考察对被压迫群体所施加的影响。英国学者约翰·霍夫曼(John Hoffman)编写的《政治理论术语汇编》(AGlossaryofPoliticalTheory,2007)中便将“阶级文化霸权”定义为“某个阶级所采取的措施,使其有能力控制受其控制的群体的‘心灵与头脑’”(Hoffman,2007:73)。对于文化霸权的探究习惯性地形成了一种由外到内的套路,但受领导的群体自身有没有一定的机制,使其潜移默化地倾向于接受这样的文化领导?欲触及文化霸权最本质的内核,需站在被压迫者身体的角度,从认知角度出发寻找意识形态入侵的模式,发现文化霸权得以施行的认知机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布鲁斯·麦克纳奇(Bruce McConachie,1944-)将文化霸权与认知科学相结合,提出了“认知文化霸权”的概念(McConachie,2010:134),认为外在的文化与内在的认知密不可分。本文将在此基础上立足于白人种族与黑人种族之间的文化霸权,从美国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1908-1960)的著作《黑孩子》(BlackBoy,1945)中姥姥所代表的混血族群视角出发,并结合其他作品中的典型例子,来解读基于容器隐喻的认知模型是怎样对黑人种族的认知产生影响并使其易于接受文化霸权。本文通过发掘外在文化与内在认知之间的联系,揭示头脑中的认知模型对于整个群体接受“知识与道德领导权”所产生的影响。
1.0 基于容器隐喻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寻求立足点的基础,也是其心理上对自身的根本认知。一个人的身份具有多重性。美国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1949-)对“身份的混合性”(Bhabha,1994:5)进行了论证。美国文学认知研究学者帕特里克·卡姆·霍根(Patrick Colm Hogan)则进一步指出,“一个人的‘实际身份’与‘类别身份’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Hogan,2015:335)。身份的确立“并非由于实际身份的不同,而是由于类别身份的对立”(Hogan,2015:335)。在种族关系中,一个人属于黑人种族还是白人种族,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个体的“实际身份”,而是一种“类别身份”。后者是“一种根据最微不足道的定义而形成的标签”,将目标群体定义为“内群体与外群体”(Hogan,2015:335)。这种内与外的划分决定了群体中的个体进行自我与他人的身份定位。种族关系下的文化霸权,便是通过认知模型,使这样任意而武断的划分得到被划分群体的认同。
借由美国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1941-)与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1949-)的“容器隐喻”可说明认知模型的形成机制。“容器隐喻”是他们在其经典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WeLiveBy,1980)中提出的(Lakoff & Johnson,2003:26)。他们认为以容器的模式进行认知是人的思维的基本方式之一。“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容器,有一个边界面与内—外两个方位。我们将自己的内—外方位投射于其他被表面所包围的物体,由此我们也能够将其看作是有着内部与外部的容器”(Lakoff & Johnson,2003:26)。容器隐喻内在于人的认知,“甚至,当没有能够定义容器的自然的、物质的边界时,我们也会强行加上边界——划出分界线从而使其有一个内部与边界面”(Lakoff & Johnson,2003:26)。容器隐喻便是“类别身份”划分的认知基础。在对种族关系进行认知时,人会不自觉地将容器隐喻投射于种族关系中,将一个种族视为有着边界的容器,内—外方位被投射于种族关系上,形成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划分。这样的认知模型应用得极为广泛,却又不易察觉。当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1868-1963)提出其著名论断“二十世纪的问题便是肤色界限(color-line)的问题”(Du Bois,2007:3)时,暗含的便是容器隐喻认知模型中的边界。这是人的天性所在,“几乎没有人类天性比领域感更为基本”(Lakoff & Johnson,2003:26),这样的认知方式使个体自然而然地将群体加上边界。由此,无论是白人种族还是黑人种族,都将自己的种族视为内群体,而对方种族视为外群体,以基于容器隐喻的认知模型来看待己方与彼方的关系,不知不觉便接受这样既定的“类别身份”。
美国非裔文学中混血群体的“类别身份”与“实际身份”之间差异最为突出,因此,对于其“类别身份”的认同心理尤为值得考究。这个群体拥有白人的外貌特征,“实际身份”给予了他们“越界”的可能,即“越过肤色界线,从黑人一方到白人一方”(Sollors,1997:247)。但他们却认同被划分的“类别身份”,以黑人种族的身份自居。《黑孩子》中姥姥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从言谈举止中,便能够窥见容器隐喻对其思维的影响。姥姥有着白人的肤色,却认同于黑人身份。“我姥姥几乎是黑人能够达到的白人的那种白,只是身份上不是白人”(Wright,1998:39)。这里的“白人的那种白”便是“实际身份”,而后半句中的“身份”则是“类别身份”,小说中的姥姥始终以黑人身份自居。从文中姥姥的言语,可看出这样的身份认同与内在于认知的容器隐喻密不可分。根据莱考夫与约翰逊的理论,当我们“将方位附加于我们的自然环境”(Lakoff & Johnson,2003:26),例如“上”(up)、“下”(down)、“内”(in)、“外”(out)等,便是在运用容器隐喻。小说中,姥姥对赖特的信仰彻底失望后,称“在这个世界上(in the world)的血亲对她来说都死掉了” (Wright,1998:122);在赖特声辩她不需要为他的灵魂负责时,称“我[赖特]的灵魂在她[姥姥]的手中(in her hands),所以我[赖特]在这个问题上(in the matter)没有话语权”(Wright, 1998:126);在拒绝赖特所提出的安息日兼职的请求时,称“只要我[赖特]还睡在她的屋檐下(under her roof),就绝不允许在星期六工作”(Wright,1998:125-126)。从这些言语的细微处可看出,在姥姥的思维中,将世界、手、问题、家视作容器,在进行认知时运用了容器隐喻,而这样的认知模型对于其对种族身份的认同也会产生影响。当她将种族视为容器,便会不自觉地引入内/外边界,将己方种族与对方种族划分为内群体与外群体,从而将自己与白人群体划分开。
姥姥的类别身份被划分为黑人种族,基于容器隐喻的认知模型,她便会将这一群体视为内群体,将白人种族为外群体,而不会考虑到肤色的不同而产生的内外交融的可能性,更不会对内外界限存在的合理性进行挑战。而白人种族正是利用这样的认知机制推行文化霸权。“从认知角度解释,身份首先便是将种族主义理解为一种外群体定义”(Hogan,2015:338)。种族关系下的文化霸权,便是通过认知模型,使这样任意而武断的划分得到被划分群体的认同,使强加于群体的整体态度融入个体态度之中。这样的界定成为整个社会墨守成规的准则,在认知中成为定式,界限的合理性也不会再得到质疑。
基于容器隐喻进行内外划分的认知方式,在对待种族关系时具有普遍性。除了《黑孩子》中的姥姥角色,在其他作品中类似的人物心理上也有所体现。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威尔登·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1871-1938)在其自传体小说《一个前有色人的自传》(TheAutobiographyofanEx-coloredMan,1912)中,讲述了其越界的心理过程与身份的自我探寻。同样是一名混血,比《黑孩子》中的姥姥更进一步的是,他确实进行了“越界”。然而,即便他声称“我下定决心,既不否定黑人身份,也不声称是白人身份……而是让这个世界把我当作什么便是什么”(J. Johnson,1995:90),他在内心深处仍认同于自己的黑人身份。因此,在以白人身份与一名女子相爱后,他陷入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挣扎:是在错误的肤色下向她求婚,还是告诉她全部真相”(J. Johnson,1995:94)。从行文中,可以看出容器隐喻的认知模型在詹姆斯对种族关系的认知中产生的影响。在詹姆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黑人身份,而不是一直以来所以为的白人身份时,他将那一刻描述为“我魔法般地从一个世界进入了(into)另一个世界,因为我的确进入了(pass into)了另一个世界”(J. Johnson,1995: 9)。他将白人与黑人的身份视为容器,从一个身份转变为另一个身份便是从一个容器进入另一个容器,人为地在心理层面制造了种族边界。对于“越界”的詹姆斯来说,实际身份已将其与白人的界限消抹掉,但容器隐喻的认知模型使他始终以内与外来看待自己所在群体与白人群体。他从未思考过这种界限的合理性,更没有想过,在身体上所表现出的相似性说明根本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内外对立。所以,即使他跨越了肤色的界限,也并未因身体特征的相似性而对类别身份的人为划分产生质疑,在心理层面上,对种族关系的认知仍然没有跳出内与外的思维框架,从而将自己永远固定于黑人的类别身份。
种族身份的划分即一种文化霸权,因为划分的本身带有强烈的人为色彩与目的性,其必然结果便是借此产生进一步的隔离。但基于容器隐喻的认知模型使人易于接受划分类别身份的做法,由此产生内与外的界限,以此看待自身身份与其他种族的关系。内在于思维的容器隐喻使人在看待世界时不自觉地进行内外的划分,而种族身份的界定符合这样的认知习惯,所以被划分的种族不会在根本上对界限提出质疑与反对。
2.0 基于容器隐喻的限制作用
文化霸权的运作并不只限于利用人为的方式将两个种族进行划界,更进一步的是将思想与行为规范于一个可接受的范畴,这一切也与内在于思维的认知模型相关。容器隐喻对思维的影响也并不仅仅止步于通过内与外来看待己方与对方种族,其中所蕴含的制约性意义更为深远。马克·约翰逊在其另一著作《头脑里的身体:意义、想象与理性的身体基础》(TheBodyintheMind:TheBodilyBasisofMeaning,Imagination,andReason,1987)中总结的容器隐喻的内蕴时,称“容器同样也限制及约束了容器内的力……因为这种力的限制,被包含的事物有相对固定的位置”(M. Johnson,1987:94)。这样的隐喻内涵同样也能够推及到种族关系的范畴。容器内的事物会受到界限的制约,而基于容器思维的认知模型所产生的限制,便是这种内涵的投射。以容器认知种族关系,便会潜移默化地将位置固定在容器之内,在心理上产生壁垒约束举止言行,对自身乃至所在群体的各个方面做出限制。
基于容器的认知模型使一个群体在心理上构造了自己的固定位置,迫使自己在既定身份范围内思考行事,将个人的态度限定在一个对外呈现的整体态度之内。种族与阶级的界限逐渐被固定与僵化,文化霸权不断强化的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的整体态度被个体所接受。白人阶层所强调的“肤色界线(line)”、“伟大的、不可跨越的鸿沟(gulf)”(J. Johnson,1995:94),实际上也是通过容器隐喻强化一种界限感,使种族间的差异与隔离不断深入人心。正如霍根所说,“人的特性第一个重要的区别便是我们与他们,即内群体与外群体”(Hogan,2013:37)。一旦人们认可并接受了自己的“类别身份”,便会对内群体与外群体呈现出一种“应该怎样”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来自于个人好恶,而是来自整个群体所施加的影响。“对于他人的行为或经历,我们所做出的这种或那种情绪的反应,通常与我们是否将其分类为我们或他们密切相关”(Hogan,2013:44)。文化霸权利用这样的一种限制感,将个人行为固化于群体规约之中,使这样的方式在基于容器隐喻的思维之下得到默认。
基于容器隐喻的认知模型,在更广的层面是使人将自我限制扩展到家庭的范围内,强化家庭作为一种容器的限制力。《黑孩子》中白人对黑人的思想是严格控制的,宗教是用于控制思想的有效利器。姥姥是一名虔诚的宗教信徒,将自己的言行限制在宗教之内,实际上便是限制在种族关系所允许的范畴之内。她将家视为一个容器,保持着内与外的绝对界限,自动地承担起维护家庭内纯净的宗教氛围的责任。在发现寄宿的家庭女教师艾拉在家中向赖特朗读通俗小说时,叫嚷“你这个邪恶的丫头!我不许我家里(in my house)有任何魔鬼的东西”(Wright,1998:39),将这一事件视作外部的世俗邪恶对内部的一次入侵;认为赖特对上帝不敬时,称“如果你再随便提上帝的名字,你必须从这个家出去(out of the house)”(Wright,1998:167),以捍卫内部环境的绝对纯正性。她将整个家族的思想教育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严格地进行内与外的划分,将言行思维都限制在种族关系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这便是基于容器隐喻所衍生的限制内涵,将容器的界限投射为家的壁垒,更成为认知的壁垒。容器隐喻的限制内涵深入认知后,种族内部实行了思想上的自我限制,这样的认知方式成为文化霸权的内在推手。
另一方面,享受“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群体同样也会强化容器隐喻所带有的限制性内涵,阻止界限的突破,为己方群体的利益诉求减少障碍。美国黑人女作家洛林·汉斯贝利(Lorraine Hansberry,1930-1965)在剧作《阳光下的葡萄干》(ARaisinintheSun,1959)中,描述了一个非裔美国家庭不断与贫穷、与歧视抗争,以寻求自我价值与社会地位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情节,这个黑人家庭计划搬至一个白人社区,但遭到了白人社区的阻挠与抵抗。白人派来代表进行谈判,威逼利诱地劝导:“我相信,你们一定清楚当黑人搬进(move into)某些区域时,这个城市的各个地方发生的一些骚乱”(Hansberry,1994:116),以向黑人家庭强调界限的限制性;在听到这家人一定会搬去的最终决定时,又说道:“我真心希望,你们明白你们即将步入什么(get into)”(Hansberry,1994:149),暗示黑人家庭突破界限所带来的危险性。“在一定的社会形态里,社会空间结构通常会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运作原则,突出社会空间的公共性和排斥性”(庞好农,2017:74)。白人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生活领域的纯正性与优越性,籍由容器隐喻,在自己所居住的社区与黑人社区之间划分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通过言语之间不断强调的界限感,使黑人家庭意识到他们已逾越了容器所限制的范围,使其能够自觉地约束自己,保持两个种族之间的距离。由此可见,基于容器隐喻的认知模型具有普遍性,不仅存在于被领导阶层的思维中,领导阶层同样也可以使这样的隐喻为其所用,以达到潜移默化地推行自我限制意识的目的。
由于容器本身带有限制性内涵,基于容器隐喻的认知模型将使群体习惯于把自己的位置固定于容器之内,而不超过容器的边界。将这样的内涵投射于种族关系上,便会在心理上形成无形的壁垒,对自己的思想言行进行约束,从而使自己不能逾越种族关系所允许的界限,在所属群体遵守的整体意识形态下思考行事。一旦人为地对种族身份进行划分,使被划分的个体意识到自己在所属群体之内,便会基于容器的限制性将自己的个人言行举止从属于整体性。由此,在文化霸权的影响下个体倾向于接受对外一致的整体态度,将强加的条条框框内化为自我约束,据此逐渐磨灭个人的独立思考与行动方式。
3.0 文化霸权的认知基础
以容器为基础的认知模型使黑人种族接受了文化霸权框架下的既定规则,显示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下的身份认同与自我限制。文化霸权下的认知模型之所能够被投射于现实经验中,是因为将头脑中习以为常的空间、身体及生活体验作为模型投射到两个种族的关系上,从认知这一根本层面使黑人群体更易于接受日常生活中的设定。人们在认知隐喻的框架下形成与人的身体和生活经验相关的认知模型,从而在认知的层面使被压迫阶层接受社会现状与既定规则。
在对外在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中,人的本能便是从自身出发,从已知到未知,认知模型成为可能的原因也在于此。容器隐喻的最初来源便是人的身体,“我们都是物质存在体,以皮肤表层为界限与外在世界相隔绝,将外在世界视为我们身体以外”(Lakoff & Johnson, 2003:26)。身体是概念形成的基础,“有意识的思维的形成是一种附属现象,与身体所提供的现象基础相呼应”(Hayles,1993:161)。基于容器隐喻的认知模型便是莱考夫与约翰逊所称的“使我们的各方面经验概念化的隐形之操纵手”(Lakoff & Johnson,1999:10),它从身体出发,延伸到对外在的世界,形成认知概念。文化霸权借用的认知模型是建立在直接来自个体自身的生活体验上,将身体体验投射于外部世界,符合认知规律,因而能够潜移默化地控制人的思维。这种认知模型“决定了我们怎样自动地、无意识地对我们的经历进行理解,形成了我们不会加以反思的常识”(Lakoff & Johnson,1999:10)。通过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可解释为,在有意识的层面人们能够掌控自己的言行,认为自己的一切思维都是在掌控之中,而实际上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无意识。认知模型便是一种无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完成了大多数的思维活动。基于容器隐喻的认知模型也可看作伪装的一种形式,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思维遭到意识的抵制而无法直接进入意识的情况下,利用人们所熟知的直接经验进行伪装,使人无意识地利用这种经验进行认知,从而接受文化霸权下的身份归类与思想指导。
更进一步地讲,这样的模型不仅仅是现实经验的一种反映,还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构建现实,这是认知实现的一个从内化到外化的过程,也是使文化霸权得以进一步巩固的原因。当我们以认知模型来理解这个世界时,实际上也在创造新的现实。“隐喻为我们创造现实,尤其是社会现实。隐喻会因此成为未来行动的导向”(Lakoff & Johnson,2003:115)。当人们以容器内与容器外来看待自身所在种族与对方种族时,便会在实际行动上使外在世界符合头脑中的认知模型,使头脑中的构建成为自然存在的客观现实。例如,当基于容器隐喻,在头脑中为两个种族之间想象出一条界线时,便会在现实中实实在在地构造界限。在《黑孩子》中,幼小的孩子们便将界限变为了现实。“那个圆形的房子便是附近居住区的种族界线,白孩子与黑孩子心照不宣地默认他们白孩子在圆形房子遥远的那边,我们黑孩子保持在这边”(Wright,1998:83)。他们通过认知模型形成概念,同时也将概念变为现实。这种相互隔离的局面不是在强权政治的高压下所被迫保持的形势,而是在头脑中的认知模型指导下自发构建的现实。“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开始通过隐喻来理解我们的经历时,而当我们根据隐喻而行动时,现实变为了更深层次的现实”(Lakoff & Johnson,2003:106)。孩子们在幼年时对世界的认知还未完全被塑造成型,但已经不自觉地按照这样的模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说明这样一种无意识已经开始操纵着他们的世界观。认知模型所指导的现实成为一种共识,“白孩子与黑孩子都开始扮演起我们传统的种族角色,就好像这是与生俱来的,融入我们的血液,天性在指导我们这么做”(Wright,1998:83)。以容器隐喻的认知模型来看待种族关系,这样的关系模式在现实的实践中得到巩固,为文化霸权所欲达成的控制与监管创造了前提与条件。
文化霸权下的认知模型所具有的蒙蔽性,在于它选择性地突出了某些事实,而使另一些具有同样重要性的事实淡出人们的视线与思考范畴。“隐喻通过其内涵使我们经验中的某些方面被突出、变得清晰”(Lakoff & Johnson,2003:114)。当人们以容器隐喻为基准来看待世界时,内与外的界限以及容器所具有的限制作用被无限大地强调,使人们所欲认识的世界呈现出符合容器隐喻的特征,而忽视掉世界本身所拥有的多样性。在这样的种族关系中,每个种群的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在心中划分出内群体与外群体,而忽视掉种族的融合性,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将个人的言行举止限制在种群整体性的范围内,而忽视掉个体的独特性。“对隐喻的接受,迫使我们只关注自身经验中它所突出的方面,导致我们将隐喻所包含的蕴意视作真理”(Lakoff & Johnson,2003:115)。文化霸权正是抓住这一点对黑人种族与白人种族进行隔离,借助其自身的认知机制,强化肤色所形成的界限以及界限的限制作用,使黑人种族从内在的认知出发接受这样的规则。在对人为的界限进行突出的同时,文化霸权致力于消除种族间所存在的相似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融合的可能。例如,赖特描述了在打工的医院所看到的景象:两列不同肤色的护士一前一后地行走,保持着绝对严格的界限。赖特对此表示质疑,“我奇怪宇宙间什么法律阻止他们相互融合?阳光不会因为第一列里面有几个黑人女孩而停止闪耀,地球也不会因为第二列里出现白人女孩而停止自转”(Wright,1998:329)。这是医院当局做出的规定,这样的规定借助于认知模型,突出了基于容器隐喻而产生的限制作用,强化个体心理上的内外划分,使人心照不宣地接受了两个种族之间不可突破的界限。文化霸权借助认知模型的蒙蔽性,突出其中能为其所用的方面,从而使更多的现实遮蔽于黑暗中为人们所忽略。
借助于认知模型的文化霸权之所以能够不动声色地产生思想上的领导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借助于人脑的认知,将思想与行为的控制建立在人本身的认知机制之上,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阻力。基于容器隐喻的认知模型与文化霸权相互交融,一方面文化霸权需要借助这样的认知机制来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认知模型也在文化霸权的刻意突出下外化为现实。与认知模式相结合使人不易于质疑既定界限与规则的合理性,因符合认知习惯而潜移默化地全盘接收,这便是文化霸权的认知基础。
4.0 结语
将人的内在认知机制与文化霸权相结合,便是认知文化霸权的本质。文化霸权因其隐秘性与感染力在统治中被广泛应用,而所谓的“道德和精神的领导”之所以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并不仅仅因为掌握统治权的群体从外部施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与被统治群体的内在认知机制相结合。个体的思维并不是凭空形成的,在人的头脑中有固定的认知模型,而容器隐喻恰恰是最为基本的模型之一。基于容器隐喻的认知模型内在于人的思维,是对外在世界进行认知的基础。将容器的内外之分投射于现实中,黑人种族将自身所在群体与白人群体严格区分开来,视作内群体与外群体,接受指定的种族身份。而另一方面,容器暗含的限制意义使其在心理上将自身限制在种族整体性之内,使个人言行服从于整体态度,进行自我约束。如此,黑人种族受制于认知习惯,更易于将文化霸权所实施的精神领导融入自己的言行举止与思维方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