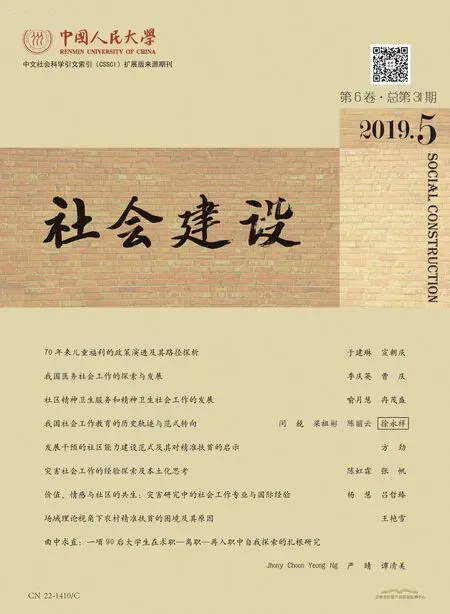灾害社会工作的经验探索及本土化思考
2019-02-18陈虹霖
陈虹霖 张 帆
一、灾害社会工作概述
(一)灾害及社会工作应对
王思斌曾提出“大灾害”的概念来说明灾害对人们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不仅强调灾害的广度和强度,尤为关注灾害破坏性的立体影响,即关注灾害所造成的多方面危害和长远影响,涉及人员伤亡、家庭缺失、财产损失、心理创伤、社会关系破坏、社区结构瓦解、生活质量下降等多方面。①王思斌:《灾后重建中社会工作的介入重点》,《社会工作》,2008(11)。文军、吴越菲在《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与反思》中细致阐述了灾害的多维后果:“灾害并不是与社会文化系统相脱离的事件,而恰恰是一种与‘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机制相联系的危机事件,因为灾害一旦发生,就会与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过程产生相互作用。”②文军、吴越菲:《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及反思——以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社工整合服务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5(9)。同时,灾后介入面临特殊场境,在有限服务时间内,社会工作者面对的是服务对象的多重创伤以及因灾害而集中爆发和勾连的诸多复杂问题,既要服务于个人、家庭、群体、组织、社区乃至更大的社会主体,又要有效回应多重需求。③吴越菲、文军:《从社区导向到社区为本:重构灾害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对灾害的破坏性、复杂性、时限性的认识,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问题为本、割裂的、修修补补的社会工作实务既不能回应灾难的恶性循环也无法满足社区群众可持续生活的需求。④张和清:《灾难的社会根源与灾害社会工作》,《开放时代》,2011(10)。在这一背景下,很多学者提出要用系统的、整合的视角来看待灾后重建工作。灾害的时限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如果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便会造成交互影响和恶性循环。系统视角下的灾后重建以“人在情境中”的视角来审视案主的社会性问题而非个体性问题,由此要求社会工作者在关注案主多元需求的同时,协助案主链接外部资源及保持资源递送路径输送网络的畅通。①杨慧:《社会脆弱性分析:灾难社会工作的重要面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5)。灾害社会工作因其特殊性,采用普通的服务模式和单一的处置方法难以满足救灾需求,迫切需要采取多向度、多层次的整合服务。②彭小兵、涂君如、吴莹婵:《社会工作介入地震灾区的社会秩序重建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积累的视角》,《社会工作》,2015(3)。社会工作介入灾害应对,应该采用整合策略,从微观层面的改变推动宏观社会政策、社会结构的转变。③张粉霞:《合作与冲突:灾难服务中的政社合作机制研究——以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为例》,《晋阳学刊》,2015(1)。
(二)社会工作介入灾害的必要性
从“大灾害”的角度来看,救灾和灾后重建需要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更加深远地评估灾害的影响。④王思斌:《灾后重建中社会工作的介入重点》,《社会工作》,2008(11)。作为专业的助人职业,社会工作在西方社会有长期参与应对自然灾害的经验。社会工作者在灾难管理的各个阶段——备灾、减灾和恢复重建中都发挥重要的作用,⑤Zakour, Michael. Geographic and Social Distance during Emergencies: A Path Model of Interorganizational Links. Social Work Research,1996, 20(1): 19-30.在处理灾后应激障碍,提供情绪支持并服务于弱势群体上尤为有效,⑥Galambos, C.M. Natural Disasters: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Considerations. Health and Social Work, 2005, 30(2): 83-86.也在制定系统性的服务计划⑦Banetrjee, M.M. & Gillespie, D.F.Linking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Community Practice,1994, 1(3): 129-142.、社区组织、动员和倡导⑧Pyles, L.Community Organizing for Post-disaster Social Development: Location Social Work.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007, 50(3): 321-333.、重建社会关系并重塑社会功能⑨Hobfoll, S.E.etal.Five Essential Elements of Immediate and Mid-term Mass Trauma Intervention: Empirical Evidence. Psychiatry, 2007,70(4): 283-315.等各个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社会工作介入灾害管理是专业使命的必然选择。了解和发现不同灾情背景下(包括灾害发生、救援及灾后重建的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灾民的需求,安抚灾民情绪并鼓励灾民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能力,重塑灾区的社会结构(包括家庭结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权责结构),尽快恢复、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协助不同类型的受害者善用各种优势配套资源,特别是对严重受损灾民(尤其是孤儿、孤老、孤残人员)的救助,从而尽可能快速提高其生活质量。这些问题都亟待社会工作者在灾后重建规划中予以认真考虑,并在持续的灾后重建中实现。
(三)灾害社会工作研究
2008年被国内学者称为“中国灾变社会工作元年”,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对于我国社会工作力量的发展壮大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团队参与灾后社会重建和社会发展为抗震救灾注入了新鲜力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灾害、参与灾害救助,随后鲁甸地震服务、11·15火灾善后服务、12·31踩踏事件应急服务都有社会工作者的一线奔劳;中国社会救灾史、中国社会救灾思想、救灾政治、应急管理、灾害社会工作、灾害心理干预、灾害经济学等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一时风生水起,灾害研究的中国声音正在积聚。
随着灾难多样性、复杂性和反复性的增强,灾前预防、灾难风险分析的必要性以及对灾难社会性内涵的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社会脆弱性分析、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在近年的研究中日益凸显,如张和清的《灾害的社会根源与灾害社会工作》、周利敏的《从自然脆弱性到社会脆弱性:灾害研究的范式转型》、文军和何威的《灾区重建过程中的社会记忆修复与重构》等。分析这些社会工作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不同程度的体现了针对具体灾难事件的功能主义导向。当时当下理清灾害研究的学术脉络,分析中国的本土化实境,借鉴国外灾害研究的智力结晶,对于灾害频仍的中国社会具有切实的实践价值。
二、国内外经验研究回顾
(一)灾害管理周期及社会工作功能
根据台湾地区“9·21”大地震的经验,冯燕将灾后社会工作分为三大阶段:紧急救援、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第一阶段是灾难发生后的一个月内,主要工作目标是维护生命安全,包括“生命救援、临时安置、危机处理以及需求评估”等。第二个阶段约在一至六个月之间,以“安置服务、情绪安抚、赈灾措施、资源协调”等为主。第三个阶段约在半年到三年之间,重点在于“生活重建、关怀弱势、心理重建以及建立制度”等。①冯燕:《9·21灾后重建:社工的功能与角色》,《中国社会导刊》,2008(12)。谭祖雪则认为具体的时间段安排有地区差异性。在紧急救援、过渡安置阶段,灾区更多呈现为“危机干预”的需求,需要社会工作者开展危机创伤干预、灾民情绪安抚、灾区秩序维护、灾民心理疏导等工作。在灾后重建阶段,灾区的需求更多呈现为受灾群众的心理康复、社区关系的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的恢复。当重建转入“常态化”阶段时,需求则转向“发展与预防”,更多呈现为能力建设的需要、生计发展的需要、减灾防灾的需要、特殊群体照顾的需要及生活品质提高的需要等。②谭祖雪:《灾后重建社会工作的转变与升级》,《中国减灾》,2012(12)。
整合部分学者关于灾害管理周期的论述,张粉霞,张昱将社会工作介入灾害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灾害准备、紧急应对、临时安置以及恢复重建。其认为社会工作角色功能的发挥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由弱变强”的递增趋势。在短期安置和恢复重建阶段社会工作介入均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介入的主要内容则涵盖灾难事件的界定与了解、个人的心理社会治疗、家庭与社区的重建、灾难管理政策制定的参与等。③张粉霞、张昱:《化危机为转机:国际灾害社会工作研究综述》,《社会工作》,2014(1)。
总体来看,学者们对灾害管理的周期和社会工作功能的认识呈现出一定的动态性、整体性、系统性和持续性特征,通过了解灾害管理的动态周期过程,掌握不同阶段社会工作者被期待的角色和功能,以及每个阶段功能发挥的强弱趋势,有利于制定切实可行的服务计划。但相关研究仍存在不足,过于强调需求满足和弱势回应,社会工作的服务呈现响应性和应急性特征,关注重点在于灾难调试和应对能力,对灾害的社会根源、灾前的风险感知和预防、灾后社区营造与复原能力的重构关注不足。
(二)“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下社会工作介入模式
基于对政社合一的认识,国内学者们纷纷对在灾后援建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模式进行了探讨。柳拯认为社会工作队伍介入灾区开展服务的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主导、高校主导等三种模式,且政府主导模式是目前的主要模式。①柳拯:《对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几点思考》,《社会福利》,2009(1)。顾东辉则认为在行政层面上应以政府为主导,在实务层面社工与政府是动态互动的伙伴关系。②顾东辉:《都江堰市灾后安置点社会工作的专业解析》,《中国社会工作》,2009(2)。徐选国提出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之间的逻辑关系随时间变换有所变迁,经历了防备(低度社会认知与制度缺位)—试探(尝试性嵌入与边缘性发展)—互动(成效凸显与信任关系提升)—合作(常态阶段服务的可持续性)四个阶段,且目前正在向第四个阶段演进。③徐选国:《“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下灾害社会工作的生成机制研究——以四川社会工作实践为例》,《天府新论》,2014(2)。陈涛基于不同的分工与功能定位则认为社会工作组织参与可分为运作型、协调型与资助型,各具特点、各有优势。④陈涛:《环境史视野与灾害史研究——以宁夏中卫特大沙尘暴灾害为例》,《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9(10)。总体来看,根据学者们的研究,随着时间发展、基于不同层面、不同的功能定位、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工作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介入模式呈现多样化发展。
(三)灾后社会工作的实务技巧
根据Walsh和McGoldrick的论述,社工在灾后重建实务干预中应鼓励个人、家庭、社区积极参与以下内容:(1)分享对于创伤事件的感受,如厘清事实、情境、模糊的看法和感受;(2)分享资源流失和生存的经验,如积极参与追思仪式,分享对生命意义的看法,表达自我情绪;(3)计划家庭与社区的重建,如重列人际关系,分配角色功能,建构生活、家庭、亲属关系和社区;(4)树立追求方向,如创造希望与重燃梦想,重新规划未来生活,从不幸的失落中找到新的目标。⑤Walsh F. & McGoldrick M. Living Beyond Loss: Death in the Family. New York: Norton, 2004, p. 3-26.相比而言,Kayser Wind和Shanka更关注跨文化的情境脉络,主张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为基础来分析社会功能。集体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文化中,社工当协助案主分享社区资源,重建家庭结构,尽快恢复常态生活;社工更要鼓励案主表达,倾听悲伤情绪,从灾难的经验中发现能帮助案主尽早恢复的优势。⑥Kayser K., Wind L. & Shanker. Disaster Relief within a Collectivistic Context.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2008, 34(3): 87-98.
国内学者的实务干预的经验总结主要有:(1)需求评估应评估与服务同时进行。以持续访问形式进行的评估且未配合实质性服务,对受灾居民而言可能是一种“打扰”,甚至是“二次伤害”。在基本专业伦理规范下,社会工作的工作方式灵活多样,家访是常见的工作手段,在社区里与居民非正式的聊天也可以成为信息来源。⑦徐文艳、沙卫、高建秀:《“社区为本”的综合社会服务:灾后重建中的社会工作实务》,《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2)以优势视角看待案主。社工进行心理疏导时,应避免给受灾群众贴标签。社会工作者相信人具有自愈能力;⑧王曦影:《灾害社会工作的角色评估:“三个阶段”的理论维度与实践展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7)。相信受助者具有潜能;在对案主赋权的过程中,工作者应重视获取和运用受助者的意见、资源和强项,促使受助者建立正面自我形象和内在的控制感,帮助他们寻找到适切个人需要和适合他们生活处境的解决方法,以在专业关系中实现平等、尊重。⑨高建秀:《灾后哀伤辅导身心灵激励》,《社会工作》,2008(11)。(3)追求优质的专业技术和专业关系,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工作有利于帮助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庭重建社会支持网络,同时倡导社区心理支持有利于关注社区支持网络的重建,从社区层面疏导个人情绪,从多方支持灾区民众的心理重建。⑩张粉霞、张昱:《灾害社会工作的功能检视与专业能力提升》,《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4)扎根个体情境,积极发扬传统文化。在灾后临床社会工作实践中,恰当激活中国文化中积极乐观的信念对于帮助受灾群众建立进取的人生、从正面看待人生过程中的挫折和不幸,具有实际意义。如:在汶川灾后的哀伤辅导中,复旦社工服务队充分结合受灾民众当地特色改善“身-心-灵”状态。此外,对受灾居民个体经验独特性的关注至关重要,辨别受灾对象在灾害事件中的角色、承担的责任、受灾前的生活等要素,以每个家庭原有的生活情境为基点开展工作,有助案主将灾难的创伤常态化和情境化。(5)运用非语言及体验性的临床技术。对于不擅表达的受助者,可采用非语言临床实务技术,如绘画、音乐治疗等,使之收获体验和感悟。人们通常鼓励别人用理智去处理情绪的困难,事实上,当人们遭受挫折和灾难时,若情绪没有恰当疏导,便难以用理性的态度去面对问题。因此,工作者需要从内心接纳受助者,运用多种方法协助受助者释放负面情绪,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
(四)灾后介入的现存问题及反思
结合我国近几年灾害社会工作中的实践经验和国外实务的经典案例,当前社工介入灾后重建主要面临以下困难:(1)身份问题。与制度设计相关,社会工作并未纳入国家灾后紧急救援条例和重建规划,因而介入的制度空间有限,介入的身份不明,进而影响服务绩效。①谭祖雪、杨世箐、张江龙:《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救援机制研究——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天府新论》,2011(2)。(2)服务内容。本土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目前存在“服务过度”以及“习得性无助”等问题,主要因为大部分服务内容都停留在对受灾对象的需求满足和弱势回应,存在忽略受灾对象本身的优势和复原力的问题。(3)服务方式。本土灾害社会工作呈现应急式服务和响应性救助的特点,这“结果导向”的服务模式易导致忽略灾害情境中的个体独特性,漠视社会不平等、压迫和权益损失等现象②韦克难、黄玉浓、张琼文:《汶川地震灾后社会工作介入模式探讨》,《社会工作》,2013(1)。。此外,“结果导向”在推动经济(基础设施和GDP)跨越式增长的同时,在社区生计、生态和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重建面临结构性困境,出现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外出务工增多)、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灾区变为景区)、社会关系和精神异化(居民间成为陌生人、消费主义盛行)等“三重异化”问题。③张和清、古学斌、杨锡聪:《中国灾后社区重建的结构性困境及其出路思考——以绿耕灾害社会工作实践为例》,《新西部》,2018(13)。(4)可持续性。由于社会工作力量大多都以项目为基本形式开展工作,服务经费不稳定,服务时间受限,服务队伍临时抽调、匆忙介入、各自为政且参与社会工作服务人员多为外地志愿者,无法在灾区长期坚守,导致持续效果大打折扣。④杨慧:《灾后社区回迁老人的需求评估与社会工作介入效果评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1)。(5)预防性问题。当前的灾害社会工作对灾害的社会根源认识并不充分,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许多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不可持续发展的恶性循环、更造成灾难的恶性循环,导致脆弱的现代生活。⑤陈映芳:《异常性揭示与正常性赋予:社会学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课题》,《江海学刊》,2011(9)。
承上所述,未来的灾害社会工作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1)建立和完善政府部门与社工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政府有关部门要团结社工组织,社工组织也要主动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汶川地震后,各方合作已广泛存在,而这种合作还需在更大范围内展开才可为社会工作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参与灾后重建。⑥王思斌:《灾后重建中社会工作的介入重点》,《社会工作》,2008(11)。(2)灾区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建立具备社会工作岗位的服务机构和人才队伍十分关键。唯有发展当地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培养当地社会工作人才,广泛吸引当地志愿者,才能形成对接居民需求的,良性、敏锐的回应机制,才可能使己有成果得以保持,已有项目得以深化。⑦徐选国、周小燕:《国内外灾害社会工作:实践、经验与启示》,《社会福利(理论版)》,2013(11)。同时,在综合性的支持灾区重建的机构中,社会工作者和其他方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合作,有利于服务的开展和形成对灾区、灾民的及时持续的支持。(3)采用整合的复原视角,以“社区关系重建”为核心建立社会工作整合服务。灾难服务应注重不同系统之间资源的流动性,社会工作者应意识到资源存在于个人、家庭和社区机制不同的系统中,且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不同系统之间流动。(4)加强对预防的重视。灾害社会工作者应加强对灾难的社会根源的认识;致力于把那些所有让灾难发生的结构根源彻底解除;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同时,以优势视角看待“富希望的社会工作”,产出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并付诸实践,提升社区民众意识并增权。①张和清:《灾害的社会根源与灾害社会工作》,《开放时代》,2011(7)。
三、灾害社会工作本土化
秉持“人在情境”中的社会工作在进入灾区开展工作过程中也应以“社工在环境”的恰当领悟为基础。②顾东辉:《都江堰市灾后安置点社会工作的专业解析》,《中国社会工作》,2009(2)。当参考并运用西方的社会文化价值理念和人文科学知识与技能发展下的灾害社会工作经验时,中国传统文化及价值取向会对救灾和灾后建设有哪些积极影响?又会面临哪些困境呢?中国社会工作者又将如何整合及发展本土化的灾害社会工作实务技术呢?学者高建秀、徐文艳、顾东辉、张和清等在此方面做了积极的反思,总结而言中国灾害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主要把握以下三方面:
(一)政社合一,公私协作
在“行政与社会合一”的中国,政府是社会资源的最大拥有者和分配者,也是大型危机的核心应对者。不同于西方国家社会工作从民间到政府的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中国社会工作受益于政府的大力推进。因此,就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救助而言,政府主导的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的介入无疑是最具有公信力的。“灾后重建中社会工作开展得最好的都江堰市、汶川县和理县,因为得到上海、广东和湖南等地民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将社会工作服务纳入了对口援助计划,从而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认同和大力支持。”③边慧敏、林胜冰、邓湘树:《灾害社会工作: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社会工作服务开展情况的调查》,《中国行政管理》,2011(12)。
可见,社会工作专业和政府的协作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而建立公私协力机制和社会工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几乎成为学术共识。社会工作服务不仅需在当地政府的工作框架内展开,服务方案在基本方向上也须与当地政府的总体工作规划保持一致;同时社工开展工作所依托的社区通常设有管委会和居委会等不同层级的社区事务主管机构,对这些机构的充分尊重和与之保持良好沟通,不仅可以避免服务不偏离政府工作规划的总体方向,而且可以为日后工作的开展构建必要的支持平台和积极的资源系统。④徐文艳、沙卫、高建秀:《“社区为本”的综合社会服务:灾后重建中的社会工作实务》,《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二)借力传统,文化重建
社会工作的主体是人,而人与其所在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传统文化对社会工作临床实务有积极启示,同时其中的消极因素也会给临床社会工作带来冲突。每个地域的居民都有各自喜欢与擅长的生活休闲方式,如东北好秧歌,广东喜粤曲。这些深植民心的活动对于个体的感染力不可忽略。以都江堰地区为例,援建社工在以“身-心-灵”模式开展哀伤辅导的小组中结合了该地民众多有习武传统(如:太极、八段锦),有利借助了当地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取得良好效果。①高建秀:《文化、心理与临床技术:灾后临床社会工作探索》,《社会》,2009(3)。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价值取向有消极的面向,如,过分强调社会性,表现为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及他人取向。②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这种社会性导致受灾群众在寻求外界专业辅导时会感到羞愧或内疚;受助者有时会以给工作者送礼和摆宴的方式希望与工作者建立“拟血缘”关系;受助者有自我决定的困难,工作者则常需扮演“权威者”或“专家”的角色;干预时受助者较倾向于任务达成,比较少关注个人感受。由此看来,临床社会工作实务技术的社会文化因素应当引起社会工作者的重视,工作的方式方法要保持充分灵活性以适应当地情境的需要,这是社区重建中的社会工作服务的基本要求。③顾东辉:《都江堰市灾后安置点社会工作的专业解析》,《中国社会工作》,2009(2)。
(三)全民参与,结果导向
汶川地震后的半年之内,中央政府出台了88条扶持灾后重建的政策,数量之多、密度之大,实属罕见。④谢登科、邹声文、刘羊旸、侯大伟:《在洒满阳光和爱的大地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心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纪实》,《中国应急管理》,2011(5)。同时,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党中央、国务院安排3000亿元中央财政灾后恢复重建基金,决定建立对口支援机制,安排19个对口支援省市全力以赴投入灾后恢复重建。在震后3年之内,党中央和国务院共投入恢复重建资金10205亿元,19个援建省市共投入825亿元,灾区累计接受社会捐赠资金和物资797亿元。⑤中国网,http://news.cntv.cn/china/20110510/104557.shtml,2010年5月10日。以汶川地震为代表,中国的灾后重建在资源投入上是超大的,在运作的制度安排上是“特事特办”、“全民参与”。
为确保灾后重建的成果最终被中央政府接受,同时为了更好地彰显重建效果和治理的有效性,地方政府可能采取“发信号”的机制,倾于集中资源和力量,打造重建的“示范工程”或“样本工程”。⑥卢阳旭:《灾害干预与国家角色——汶川地震灾区农村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结果导向”的中国式救灾模式在资本投资和硬件设施建设上取得突飞猛进的佳绩,GDP有跨越式增长,人们看到灾区越来越多漂亮的安居房建成、各种新旧基础设施重新投入使用,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社区民众生计、精神文化生活和生态环境等涉及到非物质损失方面的补救和重建工作仍然举步维艰,甚至诱发更深层次的发展问题和灾害隐患。⑦张和清、古学斌、杨锡聪:《中国灾后社区重建的结构性困境及其出路思考——以绿耕灾害社会工作实践为例》,《新西部》,2018(13)。
可见,“全民参与”“结果导向”既为社会工作参与灾后重建带来了机遇、赢得了资源,同时也为社会工作的灾后介入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
四、总结与评论
我国灾害社会工作在过去十年中得到较多关注和发展。从理论层面看,国内相关研究在以“人”为本、以“社区”为基本单位、“赋权”视角、“公私协力”、“整合化和系统化”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社会资本”、灾后“复原力”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内相关研究呈现从经典灾难社会学向社会脆弱性分析过渡的趋势。从实务层面看,国内学者们对灾害管理周期、社会工作者的基本功能与液态角色基本达成共识,也充分认识到社会工作在需求评估、哀伤辅导、专业关系建立等一系列专业服务中需讲究一定的实务技巧,比如将需求评估与服务提供同时进行、优势视角的运用、社区心理支持、扎根个体情境、积极利用传统文化、运用非语言及体验性的临床技术等。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应认识到,虽然汶川地震后国内灾害社会工作实务得到了飞跃发展,但仍然面临着身份合法性、发展不可持续、方式方法更注重单项输出而忽略服务对象的赋能,以及“结果导向”引致异化、对社会结构因素关注不足等问题。这需要学者们结合国外经验,立足于中国“政社合一”、“传统文化”以及“全民参与救灾、运动式治理”的背景继续探索。总体看来,国内相关研究对灾害的社会性、个体需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需求关注越来越多,研究领域也越来越细化。但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主要表现在:(1)功能主义导向、“应急式”研究为主。对灾害社会工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紧急救援阶段,而对灾后重建的追踪式研究关注较少,这与灾后社工介入以项目制为主、短期化介入有关。(2)对灾害的“结构”性因素关注不足,社会建构主义主张由外而内地聚焦社会利益集团对灾难产生的原因和灾难影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分析,①Tierney, K. J. From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 ? Disaster Research at the Crossroads. Th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7, 33(1): 503-525.因而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去看待灾害社会工作,应该关注灾害本身社会内部利益的建构下灾害产生的原因、防灾减灾的新型话语体系的建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来回答。(3)因政府以结果导向、全民参与、运动式治理为主要方向,因此社会工作在此背景下也多以结果导向为主,对过程关注不足,且对灾后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缺乏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