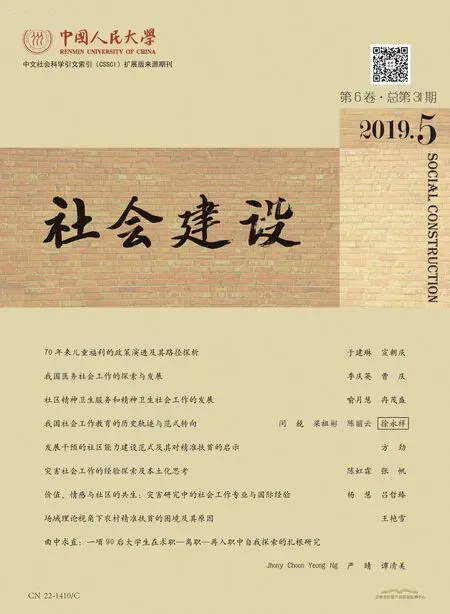发展干预的社区能力建设范式及其对精准扶贫的启示
2019-02-18方劲
方 劲
在发展研究学术议题与国际发展潮流彼此结合的知识体系下,当前社区发展的方向与主题讨论不再主要聚焦于由上而下的政府政策层面,而是更多地转移到“社区能力建设”(community capacity-building,CCB)的行动实践层面。以“能力”为基础的思考,反映出社区发展开始跳脱政策依附,回归到社区及社区成员等发展的主体。以英美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世界社区发展逐渐迈向反对居高临下的和消极的福利国家倾向和权威主义的社会干预。尽管很多社区发展是以所谓的“能力建设”为前提,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能力建设才真正加入社区发展的“词典”和国家的政策议程。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能力建设逐渐成为发展干预的一个核心原则。当前,社区能力建设已经成为西方发展研究领域成熟的学术概念和国家治理领域重要的政策话语,尤其在城市政策、社区更新和社会发展等公共议题领域影响广泛,被喻为国家治理的“新圣杯”(the New Holy Grail)。①Pete Duncan, Sally Thomas. Neighbourhood Regeneration: Resourcing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istol: Policy Press, 2000, p.15.本文将系统梳理社区能力建设范式的发展缘起、概念争论、实践操作以及实践效应,分析其面临的实践挑战与理论反思,并深入探讨其对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现实价值。
一、社区发展的理念变迁:从外源发展到融合发展
国际范围内,社区发展经历了从外源发展到内源发展,再到融合发展的理念变迁。外源发展(exogenous development)假设落后地区在技术、社会、经济和文化上远离中心或发达地区是发展受限的关键,落后地区要想实现赶超发展,中心区域的资本、技术、产业以及人口等生产要素必须向落后地区大规模转移,以此克服发展的外围性和边缘性,落后地区的“回水河汊”(back-waters)才能汇入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主河道”。①Philip Lowe, Christopher Ray, Neil Ward, David Wood & Rachel Woodward. Participation in Rural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European Experience. Newcastl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1998, p.7.基于发展的外源性视角,社区发展的主流政策回应基本是鼓励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并向落后地区大规模输入资源。于是,国家主导落后地区社会变迁的“技术-现代化”逻辑顺理成章成为二战后社区重建与发展干预的基本表征。但实践表明,这些措施并没有如规划者预想的那样取得理想的干预效果,落后地区依然徘徊于中心区域发展的干流之外。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社区发展的外源模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频频遭遇危机。
基于外源发展理念的社区发展途径主要受到以下几方面的质疑。首先,依附性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尽管外源发展策略可能为地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提供更多的机会以塑造发展过程,但由于社区发展过度依赖于外部机构干预和持续的资源输入,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必然受到牵制。其次,扭曲性发展(distorted development)。从发展干预的对象上看,外源发展模式相对容易激发出定居和商业类型的“进步”民众的发展动力和潜力,从而遮蔽了迁移、流动等其他类型的“落后”民众的发展诉求,社区发展的文化、社会等非经济层面被忽视,呈现出推动单一领域扭曲性发展的格局。第三,破坏性发展(destructive development)。社区发展的外源模式通常缺乏文化敏感性,对落后地区的文化多元和环境差异缺少足够关注,容易形成对地方生态和多元文化的“破坏”和“入侵”。最后,支配性发展(dictated development)。外源性发展是由地方社区之外的专家和规划者设计并推动的发展,从而不利于社区和民众自主发展能力的生成与培育。②Neil Ward.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Working Paper. Centre for Rural Research,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rondhein, Norway, 2003, p.6.
社区发展的外源性途径的实践困境激励了理论界和实践领域对内源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的探索。内源发展的基础是地方民众自身的变革标准及其生计的物质、社会和精神方面的福祉愿景,但与外部行动者及其周围世界保持着持续和动态的联系。内源发展旨在使地方民众的世界观和谋生战略成为发展的起点,超越了将地方传统知识整合进主流现代知识体系的外源发展观的范畴,并寻求建立起源于地方民众的世界观及其与地球关系的生物-文化途径。发展干预过程中,可以通过支持和加强社区内已经存在的内源发展因子,促进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有效勾连,在此过程中,除了生态、社会和经济层面之外,内源发展还格外强调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元素。内源性社区发展通常基于这样的逻辑,地方或区域的自然生态、文化禀赋和人口结构等独特的资源形态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计福祉改善应当由基于地方的资源和潜能的综合发展行动予以驱动。由此,社区发展呈现出从外源性资源推动向内源性能力构建的范式转换的趋势。①刘宝:《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式转换与实践路径——基于社区能力建设的视角》,《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想方设法建设地方或地区的自主能力,以抵御发展过程中广泛存在的全球竞争力、财政危机和社会排斥,在学术文献中已经得到了普遍讨论。②Christopher Ray. Cultu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rritorial Rural Development. Sociologia Ruralis, 1998, 38(1): 3-20.
内源发展话语强调能力建设并非“个人”层面,而是将“社区”作为能力建设的对象范畴,于是“社区能力建设”成为一个流行的学术与实践概念。当前,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已经走向政策前台,运用这种方法提供公共服务以及解决贫困人口的需求,旨在促进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这些实践努力主要体现为一系列注重建设社区能力、促进和维持积极的社区变迁的综合性社区行动(comprehensive community initiatives, CCIs)。③Rebecca Stone, Benjamin Butler. Core Issues in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Building Initiatives. Chicago: Chapin Hall Center for Children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6.综合性社区行动强调全面规划和资产建设的积极价值;强调培育社区服务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外部支持和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强调发展过程中有意义的居民参与的中心地位,以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可持续社区变迁的条件的重要意义。
由于内源发展模式保证了地方经济体制转型过程的自主权,内生增长的思想受到了许多农村发展工作者的青睐,它强调地方社会行动者决策过程的中心地位,以及他们控制和内化外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并普遍假定自我维持发展过程的特征。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内源发展对于提升边缘地区的自主发展能力,改善贫困社区的福利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然而,它并不能完全取代国家发展模式和区域发展模式等传统发展战略,因为从发展干预的实践效应来看,其经济和社会影响力还是相对有限。在没有明确考虑空间环境和相应区域的给定内部结构的情况下,片面强调区域内源性潜力的方法显得过于简单化。一方面,非地方性因素可能决定内源增长的前景,而另一方面,过度支持地方自主性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但无论如何,内源发展的实践价值和现实功能都不能被遮蔽,有效的地方动员和社区倡导能够显著增强社区意识与社区认同,从而促进地方赋权和解放的进程。这有助于受到排斥的外围地区和贫困社区更好地表达和捍卫自身的利益和愿景,并从传统的外部干预政策和实践中获得更大的益处,同时也能尽量降低外部干预的负面影响。然而,必须强调的是,从分支机构战略到地方企业支持、从单一机构行动到综合行动、从传统的官僚支持结构到创建具有网络功能的社会机制,都不会改变发展的基本特征,即外部力量往往是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内在力量通常可能会影响发展过程的性质。事实上,西方农村发展模式并不是从外源发展直接过渡到内源发展的线性变迁过程,而是经历了从早期注重自上而下的外源路径到后来强调自下而上的内源路径,再到如今逐渐突出以地方主导的“混合内源-外源动力”为特征的融合发展路径。对于地方社区而言,内源发展应被视为一种在社区内部以及社区和外部参与者之间的交流、沟通、互动、协作的动态调整过程。事实上,由于借鉴和吸收了区域发展战略等思想传统,内源发展和外源发展的简单划分更多地体现为理想类型式的二元方法论思维,并不是作为一种非此即彼的、相互排斥的实践性二分法,因为发展实践中二者很难完全分离,反而呈现为某种“融合发展”的格局。更为核心的实践议题是,应当努力探索实现二者彼此融合以达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切实有效的操作性路径。社区能力建设范式的理论拓展和实践运用即是在此种背景下的操作性尝试。
二、社区能力建设的概念内涵及其多维性特征
(一)社区能力建设:从修辞性概念到实践性概念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广泛使用社区能力建设这一术语,表征与地方社会合作的发展干预活动,促进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充分参与。然而,正如“社区”一词的多样化使用一样,社区能力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运用并不十分清晰,也没有厘清它为何应该如此强烈地出现在政策话语之中。最早提到能力建设的文献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21世纪议程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中均有所涉及。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建议,能力建设应包括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等方面的能力。然而,正如麦金蒂(McGinty)所言,联合国确认的“能力”必须与社区发生接触,这就要求能力建设的讨论转向更具参与性的模式,并与社区发展紧密联系起来。①Sue McGinty. Community Capacity-building, Paper presented at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conference, Brisbane,Australia, 2003, p.5.将能力建设放在社区层面,而不是过于广大的社会层面或过于细微的个体层面,符合以社区为联系纽带和经济单位的生活实际,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恢复那些对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社区关系和支持网络。②钱宁:《农村发展中的新贫困与社区能力建设:社会工作的视角》,《思想战线》,2007(1)。于是,“能力建设”在政策文本和实践话语中逐渐被具体化为“社区能力建设”。然而,尽管能力建设在发展话语和实践中占据了显著位置,但在社区层面上的能力建设过程却相对较少受到关注。③Juan M. Moreno, Lori M. Noguchi & Marie K. Harder.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Capacity-building: A Case Study of Two Program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2017, 97(4): 122-137.
要厘清社区能力建设的概念内涵,首先必须了解何谓“能力”与“社区能力”。能力来源于英文“Capacity”一词,既有容纳(containing)、持有(holding)、储存(storing)的涵义,也有思想和行动的能力(ability)之意。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那里,能力指能够执行的一些基本功能,是一个人有能力去做和正在做的事情,包括充足的营养、舒适的衣物、免于疾病、可预防的死亡、生活没有耻辱等不同方面。④Amartya Se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8.能力是人的综合素质在现实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效驾驭某项活动和行为的实际技能和本事,是实现个体价值的一种重要工具,是个体生命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力量。⑤韩庆祥、雷鸣:《能力建设与当代中国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5(1)。应用于社区层面,能力意味着一个社区能够以特定的方式行事,具备特定的能力和权力来做某些事情。这些能力可能涉及到社区功能的许多方面,关注帮助提升或者维持社区的福祉及个体、非正式团体、组织、社会网络和物理环境等构成要素。
社区能力蕴含着什么使社区正常运转以及什么使社区功能运行良好的基本假设。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的研究发现,社区能力涉及到社区的承诺、资源和技能的综合影响,它们能够被用来建立社区优势,解决社区问题,抓住社区机遇。⑥Aspen Institute-Rural Economic Policy Program. Measuring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A Workbook-in-progress for Rural Communities.Washington: Aspen Institute, 1996.社区能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人能够获得和使用的基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资源,包括人们之间的网络和人际关系,以及社区内存在的信任和凝聚力水平,社会资本是采取集体行动的关键要素,而集体行动又是社区能力的核心。①Andrew Woodhouse.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gional Australia: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6, 22:83-94.Chaskin指出,社区能力是人力资本、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本在一个特定社区中的互动,能够用来解决集体问题,维护和改善社区福利。②Robert J. Chaskin. Building Community Capacity: A Definitional Framework and Case Studies from a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Initiative.Urban Affairs Review, 2001, 36(3): 291-323.
鉴于对能力与社区能力的多元化理解,社区能力建设这一术语的界定也体现出不同的面向。社区能力建设可以界定为增加社区团体对健康或其他任何对社区成员重要的关注进行定义、评估、分析和采取行动的能力。③Ronald Labonte, Glenn Laverack. Capacity Building in Health Promotion, Part 1: For Whom ? And for What Purpose? Critical Public Health, 2001, 11(2): 111-127.社区能力建设也被视为一个增加社区能够利用的资产的过程。④Robert M. Goodman et al. Identifying and Defining the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Capacity to Provide a Base for Measurement. Health Education and Behavior, 1998, 25(3): 258-278.社区能力建设不是针对特定的地区,也不是其中的个人或群体,而是针对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采取介入行动。社区赋权和社区能力建设与旨在解决人们生活不平等的社会组织和动员形式密切重叠,⑤Glenn Laverack. Health Promotion Practice: Building Empowered Communities. Lond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9.通常是实现增强社区赋权的有效手段,旨在通过在地方层面系统地建立知识、技能和能力实现其实践目标。
(二)社区能力建设的多维性特征
上述关于社区能力与能力建设概念的界定反映出社区能力建设的多维性特征,社区能力建设并不能被某个单一角度所完全涵盖。总体而言,一些界定重点放在组织层面,一些集中于关注个人,一些侧重于情感联结和价值共享,也有一些强调参与过程。不过,界定社区能力建设的学术努力至少在以下几方面达成了一致:第一,资源链接的重要价值,从个人的技能到组织的力量,再到金融资本的获得;第二,关系网络的核心作用,有时强调情感,有时强调工具性方面;第三,社区领袖的关键意义,注重社区骨干和社区志愿力量的培育;第四,参与机制的整合力量,注重社区成员在集体行动和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有效参与。
在所有关于社区能力的界定中,两个关键理念是相通的:第一,社区能力是关于社区自身的集体知识和能力;第二,这种集体知识和能力是用来定义社区内的问题的,因此,社区能力是任何其他活动的先决条件。莫斯卡尔多(Moscardo)综合相关文献,概括出社区能力的八个主要元素:定义和解决问题的知识和能力;审慎评估项目与活动的能力;地方领导和企业家;特殊技术和管理技能;网络和社区凝聚力;与外部组织的平等伙伴关系;资源和基础设施;动机和信心。⑥Gianna Moscardo (ed.). Building Community Capacity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Oxfordshire: CABI, 2008.弗兰克(Frank)等人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社区能力包括九大元素:愿意参与的人;技能、知识和能力;福利与社区卫生;识别和获取机会的能力;执行计划的动机和资金;基础设施、支持性机构和物质资源;领导和参与的结构;经济和金融资源;扶持政策和制度。⑦Flo Frank, Anne Smith.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Handbook: A Tool to Build Community Capacity,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anada, 1999.
基于相关文献对社区能力关键信息的阐释,凯斯金(Chaskin)概括出社区能力的四个基本特征:社区意识;社区成员之间的承诺;问题解决能力;资源获取。①Robert J. Chaskin. Building Community Capacity: A Definitional Framework and Case Studies from a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Initiative.Urban Affairs Review, 2001, 36(3): 291-323.虽然这些特征在每个社区可能都一定程度地存在,但是如果一个社区要实现特定的目的,它们必须达到相应的阈值水平(指特定目的实现过程中社区能力诸种特征所需要的最小刺激强度)。社区意识主要包括集体性的价值观和规范的阈值水平,反映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结程度和彼此关系的认可程度。社区成员之间的承诺水平特指个人、团体或组织对社区公共事务的责任和义务,一方面强调社区成员将自身作为社区集体福祉的利益相关者;另一方面认为社区成员应当具有积极参与这种角色的主观意愿。问题解决能力意味着将主观承诺转化为事实行动,是几乎所有与社区相关的能力界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区能力元素中最经常强调的关键信息。资源获取强调获得社区内外的经济、人力、政治和物质资源,具备充足能力的社区拥有直接影响政策的能力,能够争取支持其发展的各种资源和条件。
三、社区能力建设的操作化及其实践效应
(一)社区能力建设的操作化
一般而言,社区能力建设通过个体(individuals)、组织(organizations)以及网络(networks)三个层面的社会中介的组合模式进行运作,从个人、群体、社区、社会政策等多维度整合性地思考介入策略。②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社会学研究》,2008(6)。
首先,个体层面主要关注社区的人力资本和领导能力。尤其注重社区居民个体的技能、知识和资源,以及社区改善和提升行动中的个体参与。增加个体人力资本投资能显著影响其获取资源和提升经济福利的能力。社区居民的人力资本既可以作为一种集体资源发挥有效性,也可以通过具体的、个体的贡献有助于社区能力的建构。领导能力实质上是人力资本的特定方面,例如社区成员个体作为领导者和变迁行动者动员他人和催化行动的能力。
其次,组织层面的关注点主要是为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目的而建立组织形式。社区变革战略需要创建和维持其所必需的组织基础,③Robert J. Chaskin, Prudence Brown, Sudhir Venkatesh & Avid Vidal. Building Community Capac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7.包括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CBOs);服务提供商、地方企业、发展干预组织、大型机构的地方分支;银行、学校、零售场所。组织层面的社区能力反映在这些组织作为更大行动体系的一部分,有效地履行职能以及与社区内外相联系的社会过程。某种程度上,组织可以被视为建设社区能力的组件和机制,其有效性的判断标准可能超越简单的产品输出结果的核算,而更加注重考量长远的综合性发展目标。
第三,网络层面涉及到个体与组织或者其他集体形式之间关系模式的社会结构。个体层面之间积极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提供了信任和支持的环境,能够有效获取资源,这通常被称为社会资本。社团群体如街区、社交俱乐部、邻里组织以及租户协会,很大程度上是为一个特定的群体进行集体代言或采取行动的平台。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可以扩展到关注诸如社团组织和更多正式组织之间的关系,每个组织作为结构空间里的一个“节点”而运作,与此同时,组织之间的工具性关系的基础机构能够为个体和组织提供更多的资源。
(二)社区能力建设的实践效应
美国西北大学“以资产为基础的社区发展协会”(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stitute,ABCD Institute)认为,个体如果能够充分使用自身的能力,社区就会更加强大,同时个体也将更加强大,这就是为什么强大的社区基本上都是地方居民的能力被识别、评价和利用的地方,而弱小的社区通常都是调动当地居民或社会成员的技能、能力和才能失败的地方。ABCD Institute的社区发展计划与首先确定社区的需求、不足和问题的传统方法完全不同,相反,它开始于对社区人力资本详细清单的统计与绘制。社区人力资本清单的详细信息包括个体的技能、工作经验、教育和培训、创业的经验等。此外,社区资产清单还包括地方组织和协会,可利用的物质资源和金融资源等。同时,社区之外的其他资源也是需要的,但主要强调的是依靠社区的发展。第一,以资产为基础(asset-based),以社区“拥有什么”作为开始,而不是“什么是不存在的或是有问题的”作为开始。第二,以内部为焦点(internally focused),强调地方知识、投资、创造力和控制的首要地位。第三,关系驱动(relationship-driven),建立或重建地方民众、地方协会和地方机构之间的关系,①Alan Black, Philip Hughes.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Indicators of Community Strength and Outcomes. Occasional Paper No.3.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 Canberra, 2001, p.19-20.并根据社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调整改变社区的内部结构,增强社区的适应力和自我发展能力。②袁小平、熊茜:《社会动员视角下的农村社区能力建设》,《山东社会科学》,2011(11)。
如果社区能力建设获得成功实施,将对社区发展形成重要的积极效应。根据Aspen Institute的研究,社区能力建设主要能够产生八个方面的实践成效。③Aspen Institute-Rural Economic Policy Program. Measuring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A Workbook-in-progress for Rural Communities.Washington: Aspen Institute, 1996.第一,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公民参与。一个正在进行能力建设的社区中,越来越多的且源自不同成员结构的民众参与到不同类型的活动和决策之中,这表征了公民参与的多样性。第二,扩大领导基础。“新人”参与决策能够增强社区领导的基础,社区成员获得技能以及实践与学习领导能力的机会同样也是领导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增强个人技能。社区通过利用各种资源创造发展个人技能的机会是建设社区能力的重要途径。随着个人发展出新的技能和专业知识,社区志愿服务的水平也会得到相应提高。第四,广泛的共识和愿景。创造一个美好的社区未来的愿景是社区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社区能力建设实践过程中,重点是如何广泛地达成愿景的共识。第五,战略性的社区议程。当社区成员和组织考虑未来并计划一起变革,有利于形成一个战略性的社区议程。通过广泛的社区参与对未来作出反应,是理解和管理社区变迁的一种有效方式。第六,朝向一致的进步目标。社区能力建设通过个体、组织和网络层面的干预行动,能够将计划转化为发展干预的实践成果。第七,有效的社区组织和机构。所有类型的公民结社和传统组织都是社区能力建设的主体,如果组织和机构运转良好和有效,社区就会变得更加强大。第八,社区更好地利用资源。理想情况下,社区应该如同聪明理性的消费者进行交易一样选择和利用资源,通过平衡地方自力更生与外部资源的利用,社区能够拥有面对未来的坚定信心。
四、精准扶贫的“在地化”困境与社区能力建设范式的启示
中国当前的精准扶贫实践本质上是一项国家外部干预贫困地区的社会工程,基本逻辑是精准识别出贫困人口并提供精准帮扶,最终实现可持续性的精准脱贫。不过,在瞄准机制逐渐定位于作为具体个人的贫困者的同时,诸多扶贫工程却使贫困者日益成为悬浮于国家政策过程之外的抽象存在,扶贫项目呈现出脱嵌于乡村社区的现象,地方民众的主体性被系统性地忽视或遮蔽,于是,“在地化”(localization)困境成为精准扶贫实践必须要面对的一项重要议题。实际上,任何持续有效的发展干预都是“外来范畴”与“本地范畴”充分互动、转译和再创造的过程。①窦学伟:《社区如何动起来?》,《读书》,2015(9)。如果精准扶贫不能通过有效的制度性规划实现外部干预的“在地化”转变,反而因其自上而下的行动介入遮蔽了基层社区的自主意识,那么作为行动者的贫困人群将无法通过自身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摆脱贫困,虽然短期内作为“社会分类”的贫困人口可能有所减少,但“昙花一现”的静态结果并不意味着动态发展过程和真正意义上的彻底脱贫。②荀丽丽:《悬置的“贫困”:扶贫资金资本化运作的逻辑与问题》,《文化纵横》,2016(6)。
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激活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促进扶贫对象实现自身造血功能是根本。要实现精准脱贫的干预目标,除了依靠外部力量和资源的自上而下的介入,还要注重贫困地区内源发展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本土与外来相互融合的发展干预模式是脱贫效应可持续发挥的关键。虽然社区能力建设范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依然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但作为发展领域里一个颇具操作性的实践范式和较强政策实践意义的概念③徐延辉、黄云凌:《社区能力建设与反贫困实践——以英国“社区复兴运动”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13(4)。,其在回应和弥补并不总是尽如人意的基于外源发展理念和“技术-现代化”逻辑的发展干预的负面效应过程中,依然具有相当大的理论吸引力和操作可能性。一定程度上,社区能力建设是被放置在与传统自上而下的社会工程、结构性的调整方案或者基于福利的发展模式相对立的位置,对于弥补外源干预的结构性困境和“在地化”难题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社区发展固然离不开政府、发展机构等外部力量的援助与干预,但社区要想获得可持续性的长远发展,社区自身潜能的挖掘必不可少。社区能力建设可以帮助社区从外部干预过程中获得最大化的发展机会。④Zahed Ghaderi, Gelareh Abooali & Joan Henderson.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for Tourism in a Heritage Village: The Case of Hawraman Takht in Iran.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7, 26(4), 537-550.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可综合运用社区能力建设的手段与方法,将外部资源和国家政策转变为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力,形成“内外融合”的扶贫格局,使贫困者迈上自我发展的轨道。
(一)个体能力建设:提升地方民众和家庭的人力资本与可行能力
精准扶贫强调扶贫“到户”、“到人”,但如果仅仅是“资源到人”、“政策到人”,扶贫对象自身没有与这些外部资源和国家政策相匹配的“接受能力”,缺乏主动参与尤其是不具备可行能力的参与过程,这种扶贫工程的实践效应将是暂时性和形式化的,并且可能助推扶贫对象的依赖心理,陷入到“久扶不脱贫”的循环之中。社区能力建设范式假设,增加个体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显著影响其获取资源和提升经济福利的能力,能力建设项目往往承诺给那些被排除在社会参与之外的人们赋权增能。⑤Sue Kenny, Matthew Clarke. Challenging Capacity Building: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3-20.精准脱贫的根本着力点离不开地方民众自身能力的提升与营造,只有具备了能够执行一些基本功能的可行能力,贫困人群才能应对压力和冲击,才能找到和利用新的条件和资源。这种能力不是反应性的,而是对不利变化和环境的主动响应,是一种积极的和动态的适应过程。为此,精准扶贫过程中应当避免经济资源单向输入的简单化操作倾向,将提升地方民众自我发展的实质机会作为根本发力点,重点确保贫困人口能够获得公平、良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培育信息获取与利用以及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鼓励和引导贫困人口建立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主体意识。
(二)社区组织培育:培育以社区为基础的能够“融合内外”的组织架构
社区能力建设是以社区组织为载体进行发展干预的实践过程,因为代表贫困人口的组织形式具有彼此支持、提升自信、互动学习、问题研讨、政治参与、利益争取、联络政府等诸多重要功能。①艾德:《能力建设:通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之路》,应维云、刘国翰译,北京:九州图书出版公司,1999,第131页。社区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对于精准扶贫和社区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架构能够作为更大行动体系的组成部分履行职能,能够以社区为单位和载体对资源、人力以及其他要素进行自我传递、自我复制、自我整合和自我推动,为实现“内外融合”的发展模式提供组织基础。精准扶贫工程应特别重视协助贫困地区培育和发展社区草根组织,通过组织化的社区行动,为社区成员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和机会。当然,社区组织培育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持续性地提供组织支持必不可少,否则容易半途而废。更为重要的是,当社区组织的培育工作是由外部力量发起时,如何使组织培育演变为社区内部的自组织过程,并非被动地服从和依附于社区的外部机构,才是真正体现其自力更生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标志。
(三)社会网络构建:构建地方民众和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与信任支持环境
贫困人口具有风险规避能力弱、脆弱性强等特点,这种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依靠行动主体自身的努力和外界网络的支持。具体而言,贫困人口应对风险和降低脆弱性除了依靠自身主体和家庭的内部努力之外,还需要依赖于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区等外部主体的关联性整合作用。在个体之间、组织之间以及个体和组织之间,积极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构建了彼此信任的环境,并提供了可感知的和实际的工具性或表达性支持,由此能够获取更为广泛的资源。社区能力建设所强调的社会支持网络是以贫困人口个体、家庭和社区组织为行动主体,关注与这些行动主体彼此关联的社会成员或组织结构对行动主体的现实影响,关注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行为过程所建构的网络系统。②胡洁怡、岳经纶:《农村贫困脆弱性及其社会支持网络研究》,《行政论坛》,2016(3)。精准扶贫工程应当重视贫困人口和社区组织的社会网络构建及其获得社会支持的程度,从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两个层面协助个体和组织发展并维持社会支持系统,为贫困群体建立一种守望相助、彼此扶持的社会支持机制。
(四)社区资源拓展:平衡地方自力更生与外部资源利用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精准扶贫实践中,在国家强大动员能力的支撑下,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部支持。不过,外部资源往往具有周期性和项目化特征,当扶贫周期和项目运作结束,贫困地区仍将可能面临资源和政策短缺的风险,从而影响发展的可持续性。社区能力建设强调资源的外部输入与内部动员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强调外源性因素与内源性因素的有机结合,强调外源性因素通过内源性因素发挥作用,这可能是避免单向的外部干预所带来的资源持续性困境的有效手段。因此,精准扶贫工程一方面需要有效调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各界主体的共同参与,做好项目、技术、人才和政策的配套协调工作,以提升贫困人口应对生活压力事件的资源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同时,也要因地制宜,重点挖掘地方社区蕴藏的各种本土资源。通过系统性的社会治理工程,特别是制度和政策的合理设计与有效实施,改善贫困地区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内源性能力建设加强地方民众和社区的自主发展意识与能力,充分挖掘可资利用的本土资源,增强发展的内生能力,可能是贫困地区摆脱“久扶不脱贫”发展局面的治本之路。①方劲:《乡村发展干预中的内源性能力建设——一项西南贫困村庄的行动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