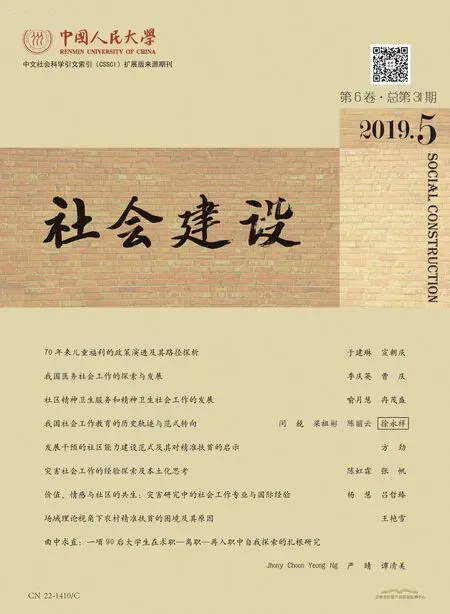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历史轨迹与范式转向
2019-02-18梁祖彬陈丽云徐永祥
闵 兢 梁祖彬 陈丽云 徐永祥
我国社会工作教育至今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变迁和历史轨迹,既是观察社会总体时代性与结构性特征的窗口,也是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社会工作发展不同范式的产物。基于此,我们尝试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置于结构转型与社会建设的宏大背景中,并结合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阶段性范式特征,采用“社会史”的方法,将其划分为三个主要历史发展阶段,从1917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1987年到2005年为第二阶段,2006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挖掘社会工作发展的中国土壤,也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未来走向,对于建构新时代社会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一、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下社会工作教育的专业性强调
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对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轨迹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形塑作用。学术界对于社会工作本质的探讨,大致可以概括为两大主导分析范式: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和社会建构主义范式。其中,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强调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助人性和科学性,而社会建构主义范式强调社会工作的政治性、本土性和情境性。①徐选国:《从专业性、本土性迈向社区公共性:理解社会工作本质的新线索》,《社会科学战线》,2016(8)。19世纪末,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在西方国家的快速发展,以解决贫困问题为主旨的慈善事业开始向以解决社会问题导向的专业社会工作转变。1917年,美国社会工作的先驱者玛丽·埃伦·里士满(Mary E. Richmond)《社会诊断》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作为一门科学和艺术的“社会工作学”的正式诞生。近50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社会工作经历了非专业化、初步专业化、高度专业化等蜕变过程而具备了专业价值、伦理操守、系统理论、实践技巧等一系列专业性要素①卫小将:《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之阐述》,《学习与实践》,2012(5)。,而这一时段也正是结构功能主义逐渐占据西方社会学界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结构功能主义重点考察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平衡机制,强调维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对维持系统稳定所发挥的作用。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的助人活动,在个体层面发挥着人格塑造、情绪调节及行为转化功能,在群体层面发挥着目标指向、规范约束和价值整合的功能,在宏观层面发挥着社会整合和社会导进的功能,从而成为维持社会结构稳定和社会秩序平衡的重要力量。②陈成文、孙嘉悦:《论社会工作的功能: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2)。随着二战后社会问题的加剧和社会需求的增加,以专业性作为其主要功能色彩的社会工作也成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技术。
在中国,这一时期的社会工作教育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其最初是经由作为西方文化殖民载体的教会传教慈善事业引入的,因为“通过社会服务的方式培养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年轻人进度缓慢,于是开始倡导对年轻人进行现代教育,而最接近基督教的高等教育是社会工作教育”③王思斌、阮曾媛琪、史柏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90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通过社会学项目将一批美国教师引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也随之引进。基督教青年会(1895年成立于中国)在其秘书长约翰·伯吉斯(John Burgees)的领导下,于1912年在北京创办了学生社会服务组织——社会进步俱乐部。1914年,在美国传教士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Daniel H. Kulp)的带领下,上海沪江大学建立社会学系,并设立了中国首家社区服务机构——沪东公社。沪江大学的师生以此为基地,通过社会教育与社会实践的方式服务地方。1918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北京协和医院成立了宗教和社会服务部。1922年,基督教青年会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其他传教士一起,在燕京大学创立了社会学系,并于1925年改称为“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开设了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会行政等一系列社会工作专业课程,协和医院则为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基地。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有12所教会大学在社会学系内开展社会工作教育。在这一历史阶段,社会工作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为西方传教士发起的以大学为基地的社会项目提供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为了保证专业性与科学性,大学内的社会工作课程最初由来自美国的传教士教授,后来则由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当地教师教授,其课程体系、理论基础和知识内容基本都仿效西方而来,也体现了当时中国教育界的专业理想主义倾向。有学者批评说:面对西方庞大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过于照搬国际标准,其课程设置与设计基本采用全盘模仿的手法,未经“本土化”过程便直接植入中国社会。④Leung, Joe C.B.An International Definition on Social Work for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Welfare, 2007, 16 (4): 391-397.
二、建构主义范式下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探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制社会制度消解了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生存发展的土壤,国家以“全能政府”的面貌承担了几乎所有的社会事务和社会服务,社会工作教育也随之中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社会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契机。1983年,民政部成立全国干部培训学院,组织学员到海外特别是到香港学习社会福利服务的设计和运作。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实施,为社会工作教育的恢复重建提供了机遇,民政部成为社会工作教育的开拓者和领军者。1987年,民政部在北京市马甸桥旁的北京对外经济交流中心大厦举办了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论证会(史称“马甸会议”),这次会议重新确认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地位,促成了社会工作专业的重建。
20世纪60年代末期,随着西方国家稳定和进步的社会局面遭到冲击,以整合和秩序为研究旨向、对社会变革缺乏足够解释力的结构功能主义开始走向衰落。1966年,皮特·伯杰(P. Berger)和托马斯·鲁克曼(T. Luckman)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建构主义进入了理论殿堂。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某些领域的知识并非实证主义所坚持的那样具有统一性,而是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产物,在实践中,社会工作更加需要用到的是地方性、族群性的知识。①何雪松:《社会工作的认识论之争:实证主义对社会建构主义》,《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因此,立足中国本土,挖掘和建构本土性社会工作,成为社会建构主义范式下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的必经之路。作为社会工作教育的发源地,社会工作植根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之中,西方国家几乎不存在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问题,因此,如何在中国情境下建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道路成为必须自主探索的重要议题。所谓本土化,主要是指社会工作教育从西方输入至中国后,面对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特征,不断适应、变化、调整,逐渐落地生根的过程。改革开放后,民政部、教育部等政府部门和社会工作专家成为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进程中重要的探索主体和建设推动力。1988年,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民政部的支持下率先建立“社会工作与管理”本科专业,这也标志着社会工作教育在我国的全面恢复和重新启动。同年,亚太社会工作教育协会(APASWE)与北京大学合作举办了社会工作教育国际会议,参会者包括来自妇联、共青团、工会等干部培训学院的教授和其他对社会工作感兴趣的高校社会学系教师。此次会议也被描绘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与西方同行的一次破冰式接触。1991年,在民政部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并于次年加入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成为正式会员。1994年,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CASWE)成立,这是一个以推进社会工作教育和专业社会工作发展为目的的非营利组织。在香港凯瑟琳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负责举办社会工作会议、海外考察学习、教科书出版及师资培训工作。在这一阶段,社会工作教育界与民政部门的携手探索,将以干部培训为主体的教育性质转变为以普通高等教育为主的学院化教育,培养生源也从职工群体转向大学生群体。社工专业教育、社工教育课程设置、社工教材编写、社工教学方法与实习等议题相继出现。②王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院社会工作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原则初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4(3)。在雷洁琼、袁方、王思斌等社会工作专家的推动下,截至1999年,开展社会工作教育的高校增至39所。
与西方国家自下而上由社会需求催生的渐进式发展不同,自上而下的顶层推动与政策吸引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探索的独特路径。1998年,教育部重新颁布《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社会工作专业从“控制发展”专业调整为“非控制发展”专业。伴随着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和教育部对本科专业审批权的下放,设置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数量迅猛增加,从1999年的30余所迅速增至2005年的100余所,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大中型城市。2004年,《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出台,并在上海试点。上海的先锋作用渐渐辐射到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带动了社会工作教育由点及面的全方位发展。社会工作的教育目标与本土化发展道路成为教育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如何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情境下探索解决西方经验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在社会建构主义范式的框架下,师资队伍的本土化建设、教材专著的本土化生产和社工机构的本土化孕育成为这一阶段的解决方案。
社会工作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带来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师资匮乏问题。虽然从国外、港台地区也引进了部分专业教师,但相对于中国蓬勃发展的社会工作教育的旺盛需求来说仅可谓是杯水车薪。为了弥补师资数量的缺口,中国众多高校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调配了相当数量的师资,通过短期培训、学术交流、“自学成才”、“边学边教”等方式进行学缘结构再造和专业背景重构。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语言方式的便利,很多教师前往香港攻读社会工作博士学位,同时,这一阶段香港高校与大陆合作开展的交流培训活动在师资队伍的本土化建设领域发挥了重要功能。如香港理工大学于1993年和1995年分别举办了两次“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人员培训计划”,培训了来自北京大学、民政管理干部学院、青年政治学院及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的十余名教师。2000年,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开办了全国第一个专业社会工作硕士课程(MSW),培养了一批对发展中国社会工作有承担的领军人才,并藉此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及实践模式。①阮曾媛琪:《我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一起走过的30年》,《中国民政》,2018(23)。2001年,香港大学和复旦大学合作,开设了社会工作及社会服务与管理两门硕士课程,这也是第一个在教育部注册的由中国大陆以外的机构实施的社会工作培训项目。
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西方、港台的经验成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重要借鉴对象,这一方面帮助我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通晓“国际通则”,另一方面也遭遇到水土不服、问题集中凸显等挑战。周永新教授带领香港社工老师和社会服务人员在80年代开始不断地提供培训和交流。由于缺乏中文教材和本地案例,早期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所用参考书大多来自香港和国外。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专家便提醒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要“摸索适合中国国情、可解决中国社会当下实际问题的本土化方案”②阮曾媛琪:《我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一起走过的30年》,《中国民政》,2018(23)。。2000年,中国社会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阶段,转变政府职能与社会管理体制,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成为社会主要需求。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工作与社区建设相结合的社会实验初步展开,社区服务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实践最早的领域之一。与此相应地,以社区发展为主题的教科书开始陆续出版,其中,以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永祥编著的《社区发展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社区工作与社会工作干预领域的教科书体现了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相结合的初始尝试。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发展的时期,社会工作教育的先行发展具有“先知先觉”的作用,为单位制的瓦解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也预先储备了一批专业人才。然而,由于缺乏公众认可的社会基础和系统明确的职业载体,“教育先行”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和社会组织孕育的重要特征。上海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孤独领跑者”。2003年,我国第一家非政府性质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上海乐群社会工作服务社在浦东成立。同年,我国第一家区级社会工作行业协会——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也在上海成立。在国家社会工作相关政策法规的不断推动下,社会组织和社区建设愈发蓬勃发展,社工教师领办社会服务机构成为社会组织本土化孕育的独特尝试。2003年,上海一些高校教师率先开始了领办社会工作机构的探索。紧随其后,深圳、东莞、广州、北京、南京、郑州、武汉等地的高校也相继开办了社会工作机构。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一书中呈现的数据来看,42.9%的高校开办了社会工作机构,①王思斌、阮曾媛琪、史柏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这也是在建构主义范式下教育先行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本土化表征。
三、结构-建构主义范式下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的双向推动
如前所述,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助人性和科学性,体现了社会工作教育对社会发展所发挥的结构性功能,强调了社会工作教育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的共通性和普适性特征;而社会建构主义范式强调社会工作的政治性、本土性和情境性,彰显的是社会工作教育对于不同社会情境的适应性和建构性功能,强调了社会工作教育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的特殊性和塑造性特征。2006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转折性之年。从经济的单向度发展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使得我们现代化建设模式及其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转变,也为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实务之间、社会工作理论与社会建设实践之间注入了内在的互动机制和动力。由于社会体制的转型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及社会工作在社会建设中所发挥的能动实践性的增强,单一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对专业性的注重或是社会建构主义范式下对本土性的强调都将对新时期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有所制约,只有将两种范式融合起来,注重专业社会工作教育与中国社会建设实践之间的双向推动力量,才能在新的社会历史阶段实现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理性发展。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同年,人事部、民政部联合发布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者作为一种职业类别正式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制度确认。②闵兢、徐永祥:《从“角色规制”到“身份认同”:青年社工的流失与留驻》,《青年探索》,2018(4)。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列入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人才队伍之一。2011年,中组部和民政部等十八部委《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发布,这是中央第一个关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专门文件,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也成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最佳的历史机遇和战略机遇。目前,全国共有348所大学开设了社会工作本科专业,155所大学和教育单位开设了MSW专业,20多所高校开展了社会工作博士点教育,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突破120万人。社会工作教育由此不仅在规模上继续获得大踏步发展,而且在教育层次、质量方面有了明显的提升,对社会建设实践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从实务层面来看,社会工作已经从社区逐渐推广到医务、司法、卫生、灾害等各个领域。社会工作教育界多次参与国家重大事件的干预,特别是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救灾中,上海、广东、四川、北京等地高校开展的灾后社会工作服务,有力地助推了党、政府及民众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仅中央两办所发的有关上海高校开展的社会工作服务的内参就达到了30多份。因而2008年也被称为我国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元年,自此,灾害社会工作开始系统化发展,专业队伍愈加壮大,实务经验愈加丰富,理论研究愈加深入,并进一步影响了宏观层面的制度推进与体制建设。2013年民政部发布《关于推进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制定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灾害的社会工作应急服务规程与预案;2016年,民政部印发《救灾应急工作规程》,启动“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社会工作服务计划”, 国务院发布《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6—2020年)》……一系列制度层面的推进均体现了社会工作实务在宏观结构层面的政策影响与社会建构功能。
一方面,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建设事业不断向纵深推进,另一方面,社会治理理念的确立和“政府购买服务”“三社联动”等社会治理实践的开拓也促进了社会工作教育在专业化、职业化和本土化层面的全面发展。在2010年之前,上海、深圳、广州等地陆续尝试在司法、残疾人服务、社区矫正、青少年服务等领域开展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并形成了“政府规划项目,出资委托社工机构运作”的“上海模式”、“政府出资购买社工岗位,社会工作机构聘用社工派驻相应单位开展服务”的“深圳模式”和“以从财政预算、政府采购、合约签订、资金拨付到财务审计一系列财政制度为支持,以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平台,对辖区居民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广州模式”。①唐钧:《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进展与前瞻》,《社会建设》,2015(4)。地方政府的探索和创新进一步促生了社会政策的出台。2012年民政部、财政部发布《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各级财政要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从而为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长效机制的确立提供了经费保障。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蓬勃发展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提供了鲜活的本土素材,也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开辟了大量对口岗位,从而极大地加速了社会工作教育的职业化进程。同样对社会工作教育专业化、职业化和本土化进程发挥催化作用的还有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举措——“三社联动”。“三社联动”是指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之间的联动,强调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的联动格局。②叶南客、陈金城:《我国“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与策略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0(12)。这也是将社会工作落地于社区,探索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有益尝试。在“三社联动”这一社会治理新机制中,社会工作者作为重要的专业力量提供专业服务、链接社会资源、进行政策倡导,充分展示了社会工作者作为新兴职业角色在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的适应性,也提升了社会层面对这一职业的知晓度与认可度。然而,由于在“三社”中相较于社区和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的主体性力量还比较薄弱,影响了三社联动的集体效能,因此,为了保证三者之间的均衡联动,必须大力增强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尤其是要加强在地化社会工作专业队伍的建设。在这一形势下,众多高校在社会工作教育的开展中自觉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更加注重与区域社会发展需求的对接和对学生实务技能的训练,并实施一系列的激励政策鼓励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参加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部分地方还专门成立了社会工作人才培训学院,为三社联动的良性运行培养、输送专业人才。
随着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快速发展和逐渐成熟,国际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频繁。本世纪以来,具有社会工作二级学科博士点或社会工作方向博士点的学校几乎每年都会举办各类主题的国际性会议,或到国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2010年,华东理工大学徐永祥教授作为中国国家代表当选为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的常务理事和执行委员。2016年,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理事会首次在中国上海举行。2017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CASWE)和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ASWE)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中美7+7五年合作总结交流会议……通过一系列的国际交流活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中国社会工作的影响力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四、社会工作教育的主要问题及未来走向
从西方知识输入背景下对社会工作教育的专业性强调,到恢复重建后对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探索,再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理念下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的双向推动,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的范式也经历了从结构功能主义到建构主义再到结构-建构主义相融合的转向。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社会工作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①向荣:《创新、共融、整合:突破当下社会工作教育困境的路径探索》,《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然而相较于如火如荼的社会工作实践,社会工作教育却面临着发展滞后、边缘和异化的困境。“后生快发”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总体特点。②颜翠芳:《从专业到职业:我国社会工作教育若干问题探讨》, 《社会工作》,2008(7)。从全国范围来看,社会工作教育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现象,东部沿海地区和发达省市发展较快,其他地区发展严重滞后;从教育过程来看,教育模式较为单一,缺乏层次性、特色性,导致培养的人才缺乏竞争性,难以适应社会的多样化需求;③李迎生、韩文瑞、黄建忠:《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社会科学》,2011(5)。从人才队伍来看,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数量距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提出的“到2020年,我国一线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145万人”的目标尚有一定差距;从人才稳定性角度考量,据全国各省的不完全统计,社会工作者的流失率均已普遍接近(部分已超过)20%的人才流失警戒线,青年社工作为社会工作发展推进的主力军,其流失问题却更为显著;从教育质量角度而言,专业认证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重要保障与督导机制。现阶段,我国主要实行政府主导型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认证的权威性得不到保障,认证标准不够科学系统,认证程序不够合理,阻碍了社会工作高质量职业教育的发展。④柴定红:《社会工作专业认证:美国经验及其在我国应用的反思》,《湖北社会科学》,2014(11)。从职业发展来看,现行的《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和《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更多地从技术等级发展方向为青年社工做出了粗线条的指引,而在个体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上还缺乏具体的规划,从而影响了社会工作者在可确定、可期待的职业发展路径下建构主体性与身份认同。⑤闵兢、徐永祥:《从“角色规制”到“身份认同”:青年社工的流失与留驻》,《青年探索》,2018(4)。
虽然面临着上述各种挑战,但我们相信这只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螺旋式上升途中的盘整,而这一盘整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工作教育与实务界的互动、本土化理论创新与社会工作实践的互动,对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的发展、新兴社会服务体系的建构以及民众福利水平的提升都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前景将会越来越广阔。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我国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及社会治理创新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并专门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其中既包含了对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需求,也蕴含了对了解本土情境、拥有创新思维、具备本土实践经验的高层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需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一步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服务创新、推动整个社会的团结、公平与正义、助力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将是社会工作教育界矢志不渝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