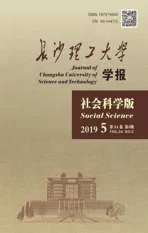当代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对立及融合
——基于“盖梯尔问题”视角
2019-02-16黄时进吴志豪
黄时进,吴志豪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认识论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对如下事实提供一个保证:对我们可以得到的每种知识,存在着一种机制使我们可以理解那种知识是何以可能的[1]。“盖梯尔问题”的提出,引发了对确证标准和认知信念不同的解读方式,建构了认识论的内在主义(internalism)和外在主义(externalism)。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分别以认识主体内部和外部为研究进路,通过解读确证标准和辩护信念试图解决“盖梯尔问题”,因而从认知辩护到认知评价形成对立。本文通过分析认知的确证和可靠的辩护,以及集体知识中的技能性知识,认为这种对立消解并走向融合将是必然趋势。
一、“盖梯尔问题”对知识传统“三元定义”的反驳
西方哲学界对于知识或知道(knowing)的界定,滥觞于古希腊的柏拉图:“伴随逻各斯的真实信念就是知识,未伴随逻各斯的信念则不属于知识的范围。”[2]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知识被等同于JTB(justified true belief,简称JTB),即“已经获得辩护的真信念”。JTB这种传统的“三元定义”(the tripartite definition)方法可以被描述为,S知道P,当且仅当:
1.P是真的;
2.S相信P;
3.S持有的信念P是受辩护的。
以上三个必要条件共同构成S知道P的充分条件,也被认为是知识成立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直到1963年,盖梯尔在《分析》(analysis)上发表了《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是知识吗?》(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一文中提出了两个反例,质疑JTB理论,下面的例子是其中之一[3]:假设史密斯和琼斯都申请到了某一份工作。又假定史密斯有强证据形成如下命题:琼斯是要获得那份工作的人,且琼斯口袋中有10个硬币(命题a)。命题a又可以推出此命题:将获得工作的那个人口袋里有10个硬币(命题b)。史密斯有充分的理由根据命题a而相信命题b,这样命题b既是真的,又得到辩护。如果按照JTB对知识的定义,命题b被视为知识。但盖梯尔假定的实际情况是:最终获得那份工作的人不是琼斯,而是史密斯,且史密斯的口袋里恰巧也有十枚硬币。根据这种结果,我们发现命题 a 是假的,但根据命题a推出的命题b 仍然是真的。对于史密斯而言,JTB 满足了命题b 的三个条件,但他实际上没有命题b的知识,因为史密斯口袋里有十枚硬币和获得那份工作是他本人不知道的。
因此,盖梯尔根据这两个反例对“经过辩护的真信念即为知识”的JTB知识观念提出质疑,形成“盖梯尔问题”,并很快引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持续的讨论,其中如何通过加强辩护条件来排除盖梯尔反例的研究进路,促使了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的产生。
二、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对立:从认知辩护到认知评价
盖梯尔的两个反例之所以能够成立,原因在于S相信P为真的辩护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缺陷,因此,要回答和解决“盖梯尔问题”,首先要克服S相信P为真的辩护缺陷。由于S的辩护发生在认识主体内部,所以,将认识主体内部确定为研究进路,探索解释知识条件的理论则被称之为内在主义理论。而与之相对的,是以认识主体的外部确定为研究进路,探索解释知识条件的理论被称之为外在主义理论。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以不同方式作为研究进路,通过解读确证标准和辩护信念来试图解决“盖梯尔问题”,在理论上也形成了争论。
对于知识的确证,是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在认知辩护上争论的主要分歧。内在主义认为,认识者内在的心灵活动产生确证,信念或理由是心灵的所有物,不存在外在环境的影响。正如费尔德曼(Richard Feldman)和柯尼(Earl Conee)所主张的,“对于认识主体S在时间T,有关命题P的信念态度D是确证的,当且仅当具有与命题P有关的信念态度D,与认识主体S在时间T具有的证据相符合。”[4]基于对“回溯问题”的解决,即避免反复无穷的对信念推论过程的“回溯论证”(regress argument),内在主义强调确证的内在可把握性(accessibility),同时以非推论的、自明的知识来界定基础知识,以及依赖于基础知识而推论出的非基础知识,对两者的区分及研究进路构建了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
内在主义的另外一个研究进路:融贯论,则反对基础主义的确证观点。融贯论认为,所有的确证都来自于相互依存的其他信念,这些信念相互为之辩护,这些相互循环的辩护也足够扩展解决了“回溯论证”的难题,信念和命题各部分之间构建了融贯关系。融贯被界定为:“区别于单纯的相容性(consistency),融贯必须是系统中信念之间的相互可导出性。”[5]
内在主义的关键在于是否直接判断某个信念是否受到认知辩护,即我们是否恰当地选择认知辩护的标准,而认知责任是衡量认知辩护标准的关键内涵。认知责任要求我们尽可能正确选择证据和信念之间的认知辩护,认知辩护内在于一个人的第一人称的认知视野,而信念者的内在心灵状态的主张却存在客观的不确定性。因此,“证据和认知工具的种类以及他或她可以获得的调查方法可能是如此可怕或贫困,而使其变得困难或不可能提出有关许多重要事项的有力证据或良好的理由,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接受信仰的证据或者理由不充分。其次,内在主义认为认知论证的主要目的是指导一个人决定相信什么……对认知指导的压力使得重点放在错误的地方,并引发关于实际上的自愿主义的反对意见。”[6](P235)
与内在主义截然不同,外在主义从信念与外部世界的有效联系来追求知识的确证。在认识论领域,“外在主义”(externalism)这一词可以追溯到美国哲学家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1973年出版的《信念、真理与知识》一书,阿姆斯特朗认为: “根据‘外在主义’对非推论知识的说明,使一个非推论的真信念成为一种知识的东西,在于信念状态、所相信的命题以及使信念为真的状况之间存在的某种自然联系。这是一种在相信者与世界之间有效的联系。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一点,与‘笛卡尔主义’和‘原始的可信性’不同,外在主义理论规范地发展了一种有关一般知识性质的理论,而不是单纯与非推论知识有关的理论。”[7]
引入外在确证标准成为外在主义解决知识确证的探索,也构建了两种研究进路:以贝叶斯(Thomas Bayes)为代表的概率主义(probabilism)和以阿尔文·戈德曼(Alvin I.Goldman)、马歇尔·施旺(Marshall Swain)和恩斯特·索萨(Ernest Sosa)为代表的可靠主义(reliabilism)。概率主义主张用概率演算来研究认知的确证,同时要求用某一信念及相关的其他信念确定的可能性来刻画确证的特征。而可靠主义将可靠过程设为确证信念的必要条件,认为当信念被联系到以正确方式,即用可靠过程或机制被确证为真时,才产生知识。外在主义除了这两种主要研究进路以外,阿尔文·普兰廷加(Alvin Plantinga)的“恰当功能理论”也是有影响的研究理论。普兰廷加将“恰当发挥功能”作为可靠信念的依据,来实现用保证来代替确证。
外在主义解决确证的标准和条件问题,也受到严峻挑战。贝叶斯的数学公式的数值演算是确定的概率,但实际生活中人的主观因素、自然条件以及生活生产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展现出来的不确定概率,以及单纯的数学概率推演不能确证人类社会复杂非线性系统的信念。
可靠主义也存在可靠性决定因素难以确定的问题,至少在三个主要方面被质疑:第一个就是笛卡尔恶魔世界,“想象一群生活在由邪恶的恶魔或笛卡尔想象的邪恶天才控制的世界的人。邪恶的恶魔小心翼翼地控制着他们的感官和内省体验,在他们身上产生他们所拥有的各种体验,如果他们居住在一个特定的物质世界中,其中包含各种特定的物体和过程,这些物体和过程以合法的方式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即使有问题的世界实际不存在。”[6](P246-250)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人们认为从外在得来的信念都是可靠的、真实的,但是实际事实是这些信念的事件都是假的。第二个就是在不依赖感官知觉或其他认知能力的情况下,通过一些不寻常的但是非常可靠的方式来认知信念,这样的信念又是否可靠?“假设某个人,诺曼,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美国总统地理下落的可靠透视者,他经常有自发的信仰或预感,他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关于总统在某一天的位置,事实上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他很少关注新闻和其他报道有关总统及其行踪的各种信息,并且从未作出任何努力来独立检查他的预感。”[6](P246-250)在这样的条件下,简单可靠性问题如何能够反驳诺曼关于总统位置的信念的真实性,他完全出于自身内在的确证来相信自己的信念。第三个就是关于可靠性的普遍性问题。外在主义者认为,如果在认知过程中的一般认知过程所指示的方式是可靠的,那么这种信念是合理的。问题就在于这种过程在何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即“在我的电脑桌上有一个白色的杯子,并考虑可能描述其结果的认知过程的一些不同方式:作为近距离良好照明下杯子的视觉感知,作为杯子的视觉感知,作为中型物理对象的视觉感知,作为一般的视觉感知”[6](P246-250)。那么作为不同视觉感知的对象,可靠性在不同情况下产生真实信念的变化就会极大,其中出现的错误信念也就无法保证。
三、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融合:从可靠辩护到集体知识
对“盖梯尔问题”的不同回应形成并且逐步发展出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争论焦点。内在主义把认知辩护归结为以负责的方式作为立论的基础,这种负责方式的判断与道德动机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正如Sosa运用“德性认识”,把德性作为理论基石来解决“盖梯尔问题”所内含的偶然性的运气知识,他认为“信念可以被评价为一种独立于所显示出来的胜任力之外的正确性。”[8]“德性认识”可以被界定为:信念的根源在于其智的德性,即能帮助人以认知的有效路径来处理问题的能力。针对外在主义的可靠主义反驳,内在主义形成可达及主义进行辩护,即认识主体凭借内在的主观因素,排除外界客观因素的介入就可以把握信念的理由。
齐硕姆(Chisholm U.)通过自我呈现和先验命题这两个来源以呈现确定的知识。自我呈现主要是当人通过感觉器官呈现事物的同时,也呈现了它们自身。例如,我们用眼睛看到一只花斑母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看到”的感觉,当我们具有这种感觉时,逻辑上可以推出我们在思考“花斑母鸡身体上有许多个斑点”之类的问题,自我呈现所蕴含的是思考的特征。先验命题即无需证明,只要我们理解就知道其必为真的命题,例如数学公理,先验的命题是不以人的认识程度为前提的客观地先验。齐硕姆认为,“必然存在着自明的基础信念,且通过一种先验的方式支持着其他信念”,并用“直接明证的(directly evident)和间接明证的(indirectly evident)”来区分证据的说明[9]。在齐硕姆看来,认知辩护以遵循道德原则为前提,在此前提基础上构建认知原则,通过认知原则,可靠性和责任之间的有机联系得以确立。齐硕姆判断“盖梯尔问题”是在“明显”概念上有缺陷的命题,因为包含“盖梯尔问题”例子的命题,并非从逻辑上进行严谨推理而明显,而都是通过其他命题的明显关系而归纳为明显,因此基于一个真实的命题,因为与一个虚假的命题有明显关系而推出此虚假命题为明显。
弗利(Richard Foley)则认为,“知识具有不必被认知主体所把握的信念,即具有一种认知合理性。”当然,前提是“在确定的情景下,足够好的选择就是合理的选择”[10]。即合理性与情境紧密相关。在弗利看来,受辩护与合理性的标准存在不同,因此受辩护的信念和合理的认知信念是不同的。一个合理的认知信念客观上是受辩护的,但是受辩护的认知信念并没有必要达到认知合理性的标准。对于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的对立,弗利是利用这样的进路进行消解的:在承认知识要求信念具有一种认知合理性的前提下,同时认为这种认知合理性不需要被认知主体所意识到;而认知辩护确实是一种认知责任,但这种认知责任却并不能完全保证认知主体获得知识。
戈德曼则探索用“强的或者弱的确证所做的区分路线”[11]来消除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在对确证性质的问题理解的对立,这为认知的确证和可靠的辩护融合内在主义因素和外在主义因素成为可能。戈德曼认为,笛卡尔的《指导心灵的规则》为认识论确定了一个传统目标,即知识的目的之一是指导我们的理智行为,那么我们的理智反过来负责通过行为维护受辩护的信念,即辩护概念的核心就是引领道义(道义论)。戈德曼将“引领”和“道义论”的结合预设了形成信念的条件:即要遵从恰当的规则作为认知责任。但遵从规则意味着这个所谓的“规则”本身只能为认识主体所具有的信念所塑造,也就是说,能够“引领”人们的只能是自身所能认识到的对象,而这恰恰又是受限的。
图梅勒(Raimo Tuomela)对集体知识(an account of group knowledge)的研究为消解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争,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图梅勒首先以我-模式(I-Mode)和我们-模式(We-Mode)两种模式来区分意向和行动。我-模式即我自身所具有的意向和行动,与他人无涉,而我们-模式则是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所具有的,我自身的意向和行动是与其他人发生关联的。在图梅勒看来,与我-模式相关联的是行动意向,只与个人的行动有关,而与我们-模式相关联的是目标意向,不仅与个人,而且与集体行动有关。图梅勒通过区分意向和行动,把作为单独的认知个体和作为集体中的认知个体区分开来,通过是否在集体中以及是否与他人发生关联作为区别的标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集体中的认知个体,其作为个体的个人意向与其作为集体一员的集体意向之间的关系。
图梅勒通过“清扫公园”的案例来诠释其集体意向:他设想有一群人,大家要一起清扫公园,必须要约定好大家都普遍接受的时间才能一起去清扫公园,因此其中有一个人就把自己建议的时间贴在所有人都能看得到的公告栏里。在这个倡议贴出来后,只有这群人的每一个成员都看到并且在倡议下留言表示同意这个时间,这个倡议才得以实现,即在约定的时间,这群人的所有成员都出现在公园并共同清扫公园。在这个案例中,图梅勒的集体意向和集体行动之所以得以实现,存在两个必要的前提:其一是清扫公园行动的计划得以公开,由其中的一位成员公示在公布栏中,大家都得知晓;其二是清扫公园行动得到每一位成员的认可,即大家对约定的时间一致认同并明确签名同意,这样才能确保大家在准确的时间同时到公园开展清扫行动,实现完成清扫的共同目标。
在“清扫公园”的案例中,清扫公园的集体行动由集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完成,单个的成员并不能完成,也不需要单个的成员自己完成所有的集体行动。每位行动者完成他的那部分行动的意向并非他自己的“私人意向”,而是与集体中其他成员紧密相关的集体意向,因为这与其他成员和集体行动直接相关。图梅勒认为,清扫公园集体中的每个成员在约定的时间一起来公园清扫,是因为每个成员都确信其他成员都会采取相同的行动,都具有共同的我们-模式的目标意向,才能实现共同清扫公园的集体目标。
在图梅勒看来:“一个集体作为认知者拥有两种信念:一是自然信念,即关于外部世界和一般性(非人为的,至少相当一部分是取决于外部世界的)事实的集体信念,二是关于社会性事实或非自然事实的集体信念。”[12]集体作为认知者,在进行集体辩护的进程中,一方面将原本认知个体承担的认知责任转换为认知集体所承认的认知责任,只有当认知集体的评价趋于一致时,认知集体的认知责任才得以凸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集体认知消解了内在主义在认知责任上的困境。另一方面,由于集体认知的理性程度在相当大的概率上超越认知个体,同时为信念辩护的“可靠性”在人类经验之内,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集体认知克服了外在主义在可靠主义上的难题。但集体知识的困难在于,在集体中各自的辩护的理由不一样时,如何产生一个集体接受的观点。
以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为基石,我们可以将集体辩护的知识区分为非技能性知识和技能性知识。非技能性知识即可以通过直觉、经验等不需要专业培训所能获取的,而技能性知识是“可以在科学家们的私人接触中传播,但却无法用文字、图表、语言或行为表述的知识或能力”[13]拓展到集体知识中,技能性知识可被认为是:“人们在认知实践或技术活动中知道如何去做并能对具体情况做出不假思索的灵活回应的知识。”同时,技能性知识将“关于知识问题的讨论带到了知识的原初状态,潜在地孕育了一种新的认识论——体知合一的认识论 (epistemology of embodiment)”[14]。技能性知识强调的是认知个体主动的身心投入,而不是被动的经验给予。“技能性知识的获得是一个从有意识的判断与决定到无意识的判断与决定的动态过程。”[14]因此,在集体知识的辩护中,在技能性知识方面占有优势的个体更容易成为意见领袖,在认知集体和认知评价标准相对稳定的情境前提下,意见领袖通过在集体认可的公布栏中发表倡议,基于以往辩护博弈经验的证实,集体中其他成员比较容易接受和认可,认知责任由意见领袖拓展到集体全体成员,集体逐步达成共同的我们-模式的目标意向,从而取得集体的一致意见。
四、结语
近代以来,认识论的研究兴起于笛卡尔和洛克,经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成为西方哲学的中心议题。当代“盖梯尔问题”的出现,又激发了对认识论研究新的热潮,当代认识论研究进路主要沿着如何逐步解决“盖梯尔问题”、客观分析知识条件、合理界定知识定义的方向进行探索。在此背景下,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间的争论源于对“盖梯尔问题”的回应,一方面通过认知的确证和可靠的辩护,以及集体知识中的技能性知识,逐步将两种对立消解并走向融合;另一方面在对信念的确证以及理论与观察事实的证实之间辩护研究进路中,又不断产生证据主义、语境主义、德性认识论等多种理论,将“何为知识”的认识论根本问题与实践的现实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有力地促进诸如“身体—心智—世界”交织关系的人工智能[15]等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