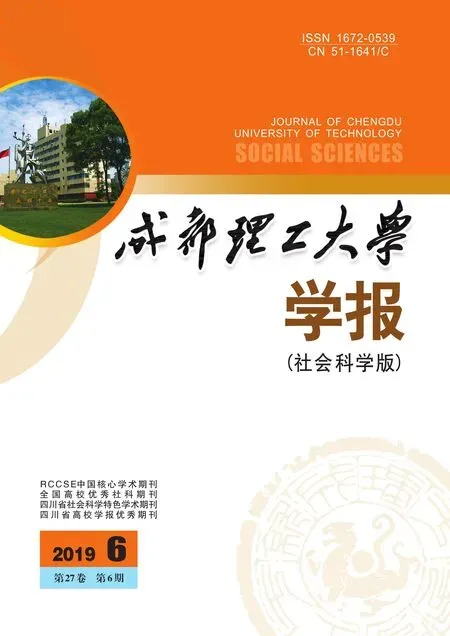京派的审美现代性反思
——以《受戒》为例
2019-02-16张少娇
张少娇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一、京派的审美现代性
从现代性的发生、发展及其在各个领域的波及和影响来看,一直有两种现代性相互交织并彼此影响。其中一个是资产阶级现代性,主要是指发生在社会领域的现代性,即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对科技的信仰,及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另一种现代性则更倾向于是对前者的一种反思,它对现代科技文明和理性崇拜持有一种质疑甚至是反对的态度。与此同时,其更为重视对人的情感和本能的强调,更注重挖掘人的感性生命力。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卡林内斯库曾经这样评述两种现代性:“无法确言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可以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剧烈冲突的现代性。可以肯定的是,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在作为西方文明史的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从此以后,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但在它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互影响。”[1]42
基于此,审美现代性是一种建立在现代性概念下的艺术思想特性,它更集中地在美学的领域发挥其效应。它将美视为第一原则和审美最高价值追求,当美成为审判和衡量一切的准绳时,其他的精神、主义和社会原则就让渡了自身权利。张辉在《审美现代性批判》中指出,“审美现代性通过强调科学、伦理相对的审美之唯,以生命与感性的原则在现代知识谱系中为主体性立法,从而达到反对理性绝对权威的……目的。”[2]8看得出,审美现代性也存在着对自身的反思。
当审美现代性随着欧风美雨进入中国的文学界后,自然而然地引发了诸多的思考与碰撞,审美现代性在中国迅速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都是值得反思的历史命题。最先激起对审美现代性关注的是文艺理论界。王国维作为其时文艺理论大师,提出了在无利害功利的审美之境中,艺术的超然忘我性。“有兹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3]40王国维将审美提升到了一种宗教的境地,将能够解决人生中的种种现实问题的寄托放在了审美上。这种观点在蔡元培处得到了回应,蔡氏提出了“美育代宗教”[4]1之说。基于美的信仰能够拯救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与苦恼,审美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一种人生哲学。而宗白华的“艺术的人生观”和周作人提出的“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为艺术”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京派的理论大纲和创作指南。尤其是在京派的文艺理论家朱光潜的《谈美》中提出了 “人生艺术化”的思想,以静穆的关照来实现人生的艺术化,以泛审美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这无疑为京派的创作指明了一个方向。
不难发现,在京派有意的选择中,其集体的倾向呈现一种无功利的、纯审美的创作态度。这种对于人生现实的刻意疏离与回避,对文学主旨追求的非现实性,对现代文明进程迅速发展使人性异化的思考,带着明显而深刻审美现代性的痕迹,审美现代性就在京派诸作家的文本中呈现出了别样的生机与活力。在与中国作家思想、文本的契合过程中,审美现代性也经历了不停被质疑、被思考的过程。
这个过程融贯其中,展现出了不同的锋芒。在京派领袖沈从文的观念里,美的追求达到一种极致状态,对于人性美的书写和讴歌,是他用以抗击病态的现代文明对人的冲击与异化的利器。他创作出了《边城》里那个善与美的化身——翠翠,《虎雏》里原始和野性美的代表——小兵,他相信这些淳朴而至真的人身上有着能够抵御金钱腐化的强大力量。为了着重表达对这种人性美之追求,沈从文创造了另一个都市人系列,他们孱弱而病态,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萎靡不振,以此来衬托他的田园牧歌理想。沈从文对理性追求的排斥、对文明进程的质疑、对人性健康的追求,都体现着审美现代性中两种现代性交织的思考。
沈从文在构建自己的湘西世界时,对于意境之美的承袭来自废名。废名用一只笔创造出了如文人水墨画一般悠远、宁静而笼罩着淡淡怅惘的氛围,他的小说最大程度地淡化了故事情节,读来如诗。废名在为文时表现出一种厌世的情绪,这种融合了西方的厌世观和中国“人生实苦”的观念,像一层薄薄的雾,将读者与这个世界隔绝开来。废名自觉地对文章中表现超然之美的追求,正是审美现代性的基本诉求。
二、汪曾祺对京派的承续
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将汪曾祺称为“京派最后一个作家”[5]211。回溯汪曾祺的生平,其在西南联大学习的那一段时光,大概是他人生中最为快意、平和的岁月了。战火纷飞中的西南联大是一片净土,培植着那个时代孱弱而倔强的一系学术之脉。而这个被誉为“京派文化大本营”的西南联大里,聚集着梅贻琦、刘文典、杨振声、朱自清、罗常培、冯友兰、闻一多、金岳霖、吴宓、唐兰等众多名家,他们以自身的学术、风度构建了40年代的一道文化奇景。这与汪曾祺深受传统士大夫家庭影响的教养,以及自身敏感纤细的气质禀赋无疑是极其契合的。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写作给予了耐心的指导和极高的评价,毫不吝惜对汪曾祺的赞扬,总是讲“他写的比我好”。汪曾祺从中学时代就很喜欢沈从文的文章,这种亲密的师生关系无疑对其文学创作乃至整个人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这个京派大师云集的地方,汪曾祺系统地学习了各家的优长思想,同时也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进行了深刻的思辨,这些都在他的文本里一一出现,其中自然不乏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
自然,汪曾祺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很大一部分承继了其师沈从文业已成熟的观点。所以,在汪曾祺的文章里看到沈从文的痕迹不足为怪。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扬名文坛,并且有着自己鲜明的文学主张和立场,在40年代这种立场吸引着有共同审美诉求的一些人,他们就是后来被称为京派的诸多名家。京派作家用文学来抵抗当时的政治高压环境;抵抗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支配;抵抗商业金钱对文学纯粹性的腐蚀。他们希冀建立文学的乌托邦来供奉文学的、人性的纯粹美。这些思考显然是审美现代性的一种追求。汪曾祺自然是认同京派的创作理念的,这种认同深深地根植于他的创作生涯。
刊登在《北京文学》上的《受戒》仿佛横空出世。在革命英雄主义的宏伟赞歌声中,在历史伤痛的悲观主义哀叹声中,《受戒》像一首轻快而透亮的江南小调,浅吟低喃出了一种格格不入的气质。看似出现得突兀,实际上,《受戒》非功利性的主旨、田园牧歌式的审美追求和健康完整的人性美的理想,无不透露出20世纪40年代京派文学理念中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与思考。
《受戒》的故事放置在了一个桃花源式的庵赵庄里,讲述的是小和尚明海和邻家女孩小英子懵懂纯真的爱情。这个设置不由让人想起了沈从文《边城》中故事发生的环境,一个充满爱与美的边城世界。《受戒》里更为诗意地书写了这种人性美,汪曾祺将人性冲突设置得更为激烈,但处理得却又十分恬淡。明海出家的荸荠庵是个和尚庙,但这个和尚庙里的和尚吃肉、打牌、结婚,在礼佛的大殿上杀猪,似乎没有森严的戒律。这些行为不仅违背了佛教的清规戒律,甚至与常人的认知都不相符。但这些作为人的日常,却是能够被庵赵庄的人理所当然的接受的。宗教和人性的冲突,在汪曾祺手里几乎淡化得没有了痕迹。人性之美遍布字里行间,使理性、规矩、戒律等准则纷纷让步,突出了人作为人应该有的天性,顺其自然的健康纯真的本性。
汪曾祺不仅承续了老师沈从文这种用人性美构建理想国的写作方式,更是融入了自己对人情世事的体悟认知,在淡化了故事情节的诗意笔触之下,将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打散在他的风俗画里。这也是汪曾祺和沈从文在审美取向上的不同之处,沈从文的人性之美往往带有一种神性的色泽。那些至纯至美至善之人仿佛不是人间之人,高蹈而不可企及,比如他描述翠翠时说她像“小兽”,似灵物而非人。但汪曾祺则给笔下那些人性美的化身以烟火气,在他笔下能看到人的日常生活,和尚们的日常和功课,小英子一家人的农村生活,能看到那个镇子里的一草一木,梳头的桂花油和小磨香油的香气扑鼻而来,打把势和耍蛇人的吆喝声近在耳畔。这样的描写刻意避开了人物性格的冲突与塑造,人物被放置在一个纯美、和谐的环境之中自由生长。这样的人,似乎就是身边的人,他们就近在咫尺,不难遇见。“穿了一件白夏布上衣,下边是黑洋纱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细草鞋,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一边插着一朵石榴花”[6]211的乡村少女就是走在路上随处可见的人,汪曾祺用这样的笔触写出的是他的一种审美取向,即每个人都有人性之美,不论到底贵贱。正是寻常人在寻常的日常生活里所展现出来的自然而然的天性最为诚挚而纯美,俗世生活里的一呼一吸都是人性美的体验,不应该违逆。
汪曾祺在对京派的承续过程中,不仅学习到了写作的技巧和能力,也吸收了京派的文艺理论思想。在《受戒》这个四十三年前的旧梦里,处处都激荡着京派的审美旨归,自然也就承续了一份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通过构建一个理想之地来彰显人性之美,来对抗理性、文明、金钱对人性的异化和腐蚀,来重新塑造唤起人对善良的向往,这无疑是审美现代性注入了其文本所散发的巨大魅力。
三、《受戒》之于京派的回响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后,汪曾祺拿出了《受戒》一篇,艳惊四座。这篇冲击着“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大潮的清新明丽之作,正是汪曾祺对京派创作理念的一种承续,一种致敬。特殊的岁月下对文学发展的桎梏也波及了汪曾祺,他的笔触收紧甚至干脆罢笔,只能在劳动中反思自己才华带来的惩罚。这样坎坷的时运对汪曾祺的创作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同时也极其深刻地考验着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这场浩劫中,沈从文一头扎进了文物考辨之中,但是汪曾祺依然拿起了笔,为80年代的文坛斟了一杯纯酿,滋补着后续的新人如苏童、余华、莫言以最初的灵气。
《受戒》一篇浑融的气象、温润的质地,在20世纪80年代以一种十分成熟的姿态出现。可见对于汪曾祺来说,这个时候的写作感觉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找到了自己的叙述方式,从容不迫的气度流溢在文字的每个间隙,彰显着他的智慧与禀赋。在《受戒》中,已经不见了汪曾祺在40年代对文学的思考和实验的痕迹。像《小学校的钟声》一篇就是采用意识流的手法来写,在40年代来说,对于国外的小说写法依旧是一种狂热崇拜和竭尽模仿的时候,汪曾祺也学习着这些经验。这篇小说的整个故事统摄在意识的流动之中,文笔颇有些拘谨,但是已经能够看出汪曾祺对于唯美风格的倾向与偏爱,甚至胡河清对其文章“满纸都是水”的评价已经初见端倪。这个时候的作品是汪曾祺写作的一个基调,虽然还在练习,但他练习的方向是在京派的审美指向中,即对纯美叙述的追求。
这种追求在他的《复仇》一篇中也能窥得一斑。在这篇中汪曾祺是在探讨存在主义与荒诞性的命题,但他巧妙地将中国的传统武侠小说元素融入进来,在他清丽的文笔之下勾勒了一幅意境深远的水墨画叙事背景。这一篇也颇能体现出汪曾祺对语言深审慎和自觉的追求。张学昕在《小说的气象——汪曾祺的短篇小说都是〈受戒〉》一文中这样描述:“汪曾祺的文字,你看不到丝毫的焦虑,生活在他的笔下也就不显得臃肿,形态飘逸、轻逸但却扎实牢靠,不折不扣。无论他叙述的是什么题材和人物,都非常干净,细致,自然。”[7]123显然,汪曾祺在40年代就在语言上下功夫,将语言的诗意性发挥到了极致,这就让他的文章具有了典型的散的特征。他着力于突破文体的限制,让诗的语言在小说中自然流淌。这种诗意美的追求在《受戒》中得到了升华,《受戒》对于散的追求不仅表现在语言上,更体现在情节里,汪曾祺将事件的发展都融化在了对风俗民情的绘饰里。
80年代,汪曾祺献出了一场美轮美奂的旧梦,这不单是对那个时代所有美好的追忆,也是经历了大是大非、大起大落之后人生的一种淡定与从容。显然,80年代的时代语境也再一次激起了汪曾祺对于文学和人性的思考。那是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后,工业化、城市化、科技化和现代化的工业文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人们的生活。整个时代都在被经济强力地拉扯,人们的思想还来不及从阶级斗争的纲领中扭头就被一把推进了经济建设的浪潮里,一切都迅速得来不及,世界在以秒为单位改变着、翻新着、冲刺着。这种工业化的激进发展和现代文明的席卷式冲击,都是一种资本主义式的现代性表现,这也就深刻地冲击着作家们对现代性审美的认知。
汪曾祺施施然地从工业化的大背景中抽身出来,隔绝了现代文明的冲击和金钱腐蚀的诱惑,在这一轮新的文明浪潮中固守着自己一方纯美的理想原地。他用《受戒》建立了这样一个清新明净的世界,和谐和质朴的人性之歌就是他的审美追求。这无疑是40年代的京派作家们一种集体的审美现代性追求与反思,汪曾祺用温婉的笔触批判工业都市想象,建立人性理想旨归,这也是《受戒》一篇出现时,能够冲决被禁锢的思想之魅力所在。
审美现代性建立在时间的线性不可逆维度之上,这就使得京派作家整体有一种强烈的时间意识,他们总是将美好寄托在过去的事物之上。汪曾祺也不例外,他延续了这种用原始的野性力量来批判现代文明,用人性做标尺来衡量现代文明对人的侵害与腐蚀,执着于一个供奉人性的乌托邦的建构传统。在这个层面来讲,汪曾祺站在80年代,回望并致敬着40年代的京派。他以唯美的诗性目光面对日常生活,这是属于京派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在审美层面的现代性反思。所以说,汪曾祺是京派的最后一缕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