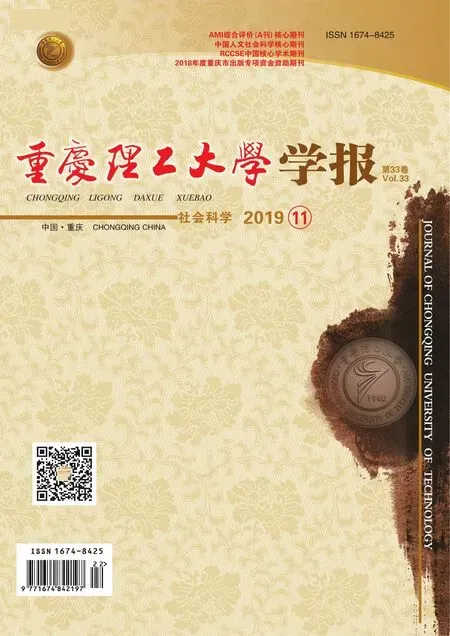超越自然与社会的分裂
——拉图尔的知识论研究
2019-02-15张意梵
张意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的争论由来已久,在拉图尔看来,它们之间的争论永远不会有结果,因为二者都陷入了自然-社会二元论哲学的陷阱当中。究其根本,科学实在论的解释体系,其实质就是以客体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知识论体系,主体的作用就是如实地表征客体。社会建构论的思路则是以主体为中心来解释客体,在主体认识客体的过程中,正是主体的认知能力决定了认识的结果。问题就在于,这两种解释模式,都以二元对立为前提,致使它们无法从根本上看到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正是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分裂,使得自然和社会二者变得很难沟通。那么,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究竟各自面临着什么问题呢?
一、对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的批判
主客二分这一预先设定,致使传统知识论只能把解释因素最终归结到自然界或社会界,导致它们根本无法很好地解释这两极“中间”(the Middle)产生的诸多“杂合体”(hybrids)(1)什么是“杂合体”(hybrids)?在“现代”观念当中,由于自然和社会是分裂的,杂合体似乎并不存在,因为现代人对事物的划分,总有明确的界限,要么属于自然界,要么属于社会界,这两个世界有着明显的区分,并且互不干涉。然而,在对科学技术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拉图尔发现科学技术的形成不可能完全归结为自然因素,也不可能完全归结为社会因素,而是多种因素结合和共同作用的结果,拉图尔把由各种因素共同联合而形成的集合体,称之为“杂合体”。科学技术与世界的联系,实际上既有社会因素的参与,也有自然因素的加入。所以,很难纯粹地把一种现象全部归之于自然或者社会,即社会与自然之间出现了杂合,而这种杂合普遍存在,或者说无处不在。然而,自然与社会的分离使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不得不尽力对各种杂合现象进行自然或者社会解读。。这样,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之间被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那道鸿沟所隔裂,而无法沟通。
杂合体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分裂与杂合,使得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双方的论证都显得很有道理而又相互矛盾。我们就不由得要问,“自然”和“社会”到底是什么呢?
(一)自然客体和社会主体
“自然”就是科学实在论概念下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客体”;“社会”就是在社会建构论的话语体系之下,对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进行建构的“主体”,这就是对“自然”和“社会”最直观和最根源性的定义[1]59-60。科学实在论的基本前提就是认为自然独立于我们而客观地存在着,外在于我们人类。因此,我们人类只能以“主体”的方式对自然进行“表象”,“自然”也就是科学实在论观点的“前提”。社会建构论则同科学实在论一样对人类“主体”进行了界定,认为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必然要以人类主体的“介入”才能形成,所以“主体”的地位至关重要,而“主体”就是通过“社会”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自然”也就是对“客体”的肯定,而“社会”则体现着与“客体”相对应的“主体”。所以说“自然”和“社会”争论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争论。这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问题的所在了,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之间的斗争根本分不出胜负,也不会有实质性的结果,因为“客体”和“主体”之间的争论在哲学史上可以说是旷日持久,且相持不下。可以说,“主体”和“客体”、“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传统一直伴随着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对“主体”和“客体”的划分,被许多哲学家所接受,同时它也被不少哲学家所批判和排斥。接下来让我们简单地探讨一下主客二分问题,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的争论。
(二)主客二分问题
哲学上的主客二分问题由来已久,发源于客观主义传统。客观主义思想早在古希腊就已基本形成,古希腊哲学以“本体论”为发展脉络,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秉持了这种客观主义观念。由于我们自身处在世界当中,直观的感受让我们很容易接受在我们之外有一个世界“客观”地存在着,这就是客观主义的直接来源。对于客观主义,胡塞尔认为这是以一种“预设”的方式对“外在世界”进行肯定,即“不言而喻地预先给定了一个世界”,并以此为基础再“追问这个世界的‘客观真理’”[2]。这种预先的给定,没有任何根基和理由,所以以客观主义为导向的科学哲学不能为科学奠基。
关于主观主义,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康德,以“哥白尼革命”的方式把“主体”抬到了决定性的地位,宣称“人为自然立法”。至此,人类以“主体”的地位处于世界的核心地位。从此“主观主义”思想也因康德的伟大而空前蔓延。拉图尔认为,社会建构论就深受康德思想的影响,这一说法公允而恰当[3]。请注意:主观主义视野下的“客体”的位置何在?“人为自然立法”中的“自然”,是“客体”意义上的“自然”吗?是“自然本身”吗?
最为关键的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究竟如何“有效”沟通且是否可以“有效”沟通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给出以下答案:客观主义者承认对客体的认识必须通过主体来完成,而主体又必然带有主观性,认识的结果必然带有“主观主义”色彩,这与其“客观主义”立场是相矛盾的。从主体性出发,沿着康德的路线前进,得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结论,这一结论中的自然,已经不是客体意义上的自然了,“自然本身”在康德这里已经沦为了“物自体”,“客体”已经不可知了。因此,不管是客观主义立场还是主观主义立场,都使对客体的客观认识无法成立,即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有效沟通是不能成立的。由此可知,正是主客二元对立思想之下“自然极(自在之物)和社会极或者主体极(人自身)之间日益加剧的分裂”[1]76,使得当今对科学技术的解释陷入了如此僵局的境地。
二、拉图尔的知识观念及方法
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已经无法对当前的科学技术做出充分的解释,拉图尔认为必须用一种新的方式才能合理地对科学技术进行解释。在此,先对拉图尔研究科学技术的基本原则做一简要介绍。
(一)“元”规则:追踪行动中的科学
不管是科学研究还是哲学思考,任何 “提前给出的结论”都必然会犯“预设”的错误,这将影响我们对事物考察的公正性。因此,为了可以对科学知识进行最公正的考察,拉图尔说,“我们将不再携带任何关于知识之构成的前观念(preconceptions)”[4]14。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不再携带知识之构成的前观念呢?
所谓知识的前观念,就是说当我们在考察科学知识之前,就对科学知识“应该是什么样子”所进行的预设,这种预设就是知识的前观念。拉图尔说:“科学有两张面孔,一副是关于我们已经知道的,一副是关于我们还不知道的。”[4]4前者就是已经形成的科学(ready made science),当我们直接接受这种已经形成的科学的时候,就接受了科学的现成观念;而后者就是形成中的科学(science in the making),这种科学则是还未呈现在公众面前的科学,是一种“非成熟”的科学,而不带有关于科学的现成观念。拉图尔这样说道:“我们研究的是行动中的科学,而不是已经形成的科学和技术。”[4]218因此,拉图尔把“探讨行动中的科学”作为他整个分析和论证的“元”规则。
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探究“行动中的科学”呢?拉图尔说探究行动中的科学的最好方式就是紧密地“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了能够如实地反映科学活动,并且避免先入之见,最好的方式就是采取描述的方式对科学活动进行研究,具体说来就是“田野调查”的方法,也可称为人类学的方法。
拉图尔说:“我的工作一直是从事‘经验哲学’的实践研究,也就是说,借用社会学中的实地考察(field work)的方法来解答哲学所提出的问题。”[3]拉图尔试图通过经验(既是哲学上的经验也是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经验)的方法,排除传统二元论主导下的理论优位立场,即以人类学的方法解决以传统科学哲学的方式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二)反哥白尼革命
传统的知识论以主客二分为前提,使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当中,如果想摆脱这种无结果的纷争,必须要跳出主体和客体对立的这种形而上学预设。因此,拉图尔便从对主体和客体分裂的批判入手,开启新的知识论研究。
1.回到中间王国(the Middle Kingdom)
前文的分析已说道,科学实在论以客观主义的立场,把各种杂合体通过传义者(intermediary)(2)传义和转译具有相同的内涵,只是使用的语境有所不同。的作用向“自然极”靠拢,使得物和事实都“纯化”为纯粹的自然形式,使得科学技术当中的诸多因素都围绕着“客体”而旋转。在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之后,这种情景正好出现了反转,康德提出的“人为自然立法”,使诸多行动者都围绕着“主体”旋转[5],社会建构论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展开立论,以“社会”为中心建构科学技术。
在传统知识论下,杂合体的存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以上两种纯化方式,都把杂合物纯化为“自然极”或“社会极”这样的纯形式,因此将所有的杂合体都视为这两种纯形式之间的混合物。纯化之后,他们又通过增加传义者来重构那些已经被其解构的杂合体。这样的解释模式是从自然和社会的两极开始,然后又走向中间,“这里既是当初的分割点又是相反资源的结合点,也就是康德的伟大叙述中现象发生的地方”[1]89。这样的解释模式,使得中间地带既被维持了,同时又被取消了;被确认的同时又被否认了。这样的矛盾是传统知识论面临的巨大难题。那么,我们怎么摆脱这种必然的矛盾呢?拉图尔说,那就必须要转换我们的解释模式回到中间王国,从中间王国开始。抛弃以往以客体极或主体极为取向的做法,转向以中间为取向的这种反向颠覆运动,“能够使客体和主体围绕拟客体和转译的实践而旋转”[1]90,这就是拉图尔所实施的一场反哥白尼革命。
反哥白尼革命让我们摆脱了对自然和社会进行二分的困境。从“拟客体和转译的实践”开始研究,我们会发现所谓自然和社会只不过是实践的一种结果。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和社会确实也在旋转,但它们不再作为旋转的中心,此时旋转的中心是中间王国——拟客体网络集体(由拟客体的相互关联而组成的网络集体)。那么,这种中间王国的主要组成者拟客体是什么呢?
2.拟客体(行动者)
拉图尔在批判传统科学技术解释模式和论述自身观点的时候,借用了米歇尔·塞尔斯(Michel Serres)的两个概念:拟客体(quasi-objects)和拟主体(quass-subject)。这一概念类似于其著名的观点——行动者网络理论里面的行动者(actant,actor),因此可以把拟客体等同于行动者。
行动者必须在非二元论模式下才能进行解释和理解。拉图尔取消了主体和客体,提出从中间王国走向传统的“主客两极”,而中间王国就是由众多的“行动者”组成的“集体”。以拟客体和拟主体来定义行动者,目的在于强调“行动者”要比“客体”更具有建构性,而比“主体”更具有实在性。拉图尔的人类学跟踪考察方式体现了其理论体系下的所有行动者具备了实践优位下的“参与性”而非理论优位的“旁观性”。因此,拟客体必然是以一种“生成的方式”而存在,而不是以一种“自在的方式”而存在。这一理论体现了强烈的“生成(becoming)决定存在(being)”的观点。拉图尔认为 “萨特(Sartre)对人类的评论,即实存先于本质也同样适用于行动者(actants)”[1]98。
反哥白尼的革命取消了主体和客体,否定了自然和社会的两极,让我们回到了中间王国,通过中间王国的行动者集体来解释两极。然而,充斥在中间王国的这些行动者或者说拟客体特点各异,互不相同。那么,它们之间是如何产生联系,以及知识是如何得出来的呢?
(三)知识的实质——指称之链(chains of reference)
当我们从自然和社会的纯粹两极回归到充满杂合体的中间王国之后,又该如何看待知识,知识又以什么方式而存在呢?
行动者通过转译的方式和其他行动者之间建立联系而形成一个网络集体,各自也都为网络联盟的存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不同的行动者具有不同的特性。在知识的表达方面,拉图尔把以文本、语言、表述等方式存在的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的转译,称之为指称(reference);所以,拉图尔把对其他行动者之间的一系列指称,称之为指称之链(chains of reference)。
文本、语言等符号对行动者的指称,就是知识之所以成为知识的基础。换言之,知识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指称的过程。例如,在对亚马逊森林的土质进行研究的案例当中,拉图尔就谈到“要想使世界变得可以认识,它必须要成为一个实验室;而如果一片未被开垦的森林要想被转化为一个实验室,那么这片森林就要必须做好被制成图表的准备”[6]。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对森林的土质进行认识,研究人员就要到森林当中进行采样,并且要对不同片区的土样进行标注和记录,形成文本对森林土样的一种指称;接下来,对通过化学和生物等方法对土质进行的实验,又是对土样进行了指称;进而,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而得出来的数据及进行评判,则是对实验的指称。这一系列过程都是不断进行指称的过程,而正是这种“一步一个脚印”式的链条保证了这种关联的可靠性。换言之,正是这种转译链条,才保证了指称和指称对象之间有着严格的关联要求,才使知识的成立得以可能。
三、知识客观性的形成:生成与辩护
客观性历来作为知识的首要美德(virtue)而备受重视,因此对知识客观性的考察是知识论的首要任务。对拉图尔知识论的研究,必然要追问其知识的客观性是如何达成的。
在传统知识论中,客观性被理解为知识对“客观存在”做出了如实而正确的表征(representation),在此我们借用这一传统概念,对拉图尔的知识观念进行评价。我们在以下意义上借用客观性这一概念,即当我们说某些知识具有客观性时,就意味着这些知识对其所指称的对象进行了准确而如实的表述。那么,知识的客观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一)弱强度的指称之链:文本层面的指称
科学知识对人类来讲,只能以语言的方式呈现出来,而自然现象只能是以无言的方式表达自己,只有把“人”作为中介来为自己代言。即如拉图尔所说,“就其自身而言,事实是不会说话的,自然力也仅仅是毫无情感的机制”[1]34。因此,这样说来,“自然”只有让“人”来充当自己的“代言人”,用拉图尔的理论可以说成:科学家在解释世界时,总会说他们是在为自然代言,是自然的代言人(spokesman/spokeswoman)。然而,代言人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自身“如实地”为自然代言了呢?
因此,科学家的有关陈述要想成为科学知识,就必然要经得住同行们的质疑、反驳等诸多考验,才可能得到同行们的认可。在科学论述被确定为科学知识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它们的主张者总是要极力捍卫他们的观点,通过各种手段去说服科学共同体里的其他成员,以证明其论断的科学性。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理论的反对者总是要尽力反驳甚至推翻主张者的理论。
当写作科学文本时,一旦预测到争论或正在面临争论,对文本做出技术性的处理就变得必不可少。“参考、引证和脚注的出现和缺失足以标示一个文件是否严肃,以至于你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引用而把一个事实转变成虚假之事,或者把一个虚假之事转变为事实。”[4]33通过引证则可以直接把自己的文章从孤立无援变得有许多同盟助友,如若有反对者不同意文本中的意见,那么他也要同时反驳与引证者有关的团体。这样一来,对别人的引证就相当于把别人拉入自己的联盟当中,使自己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
由于文本还没有经历深层次的考验,所以相对于能够经受住更深层次(比如建立反实验室等)、更多方面的考验来讲,这里的考验还只能称得上是弱考验,即还只是处于相对较弱的指称阶段。如果要想加强指称之链的强度,就要走出文本走到文本之下的科学现象中,即走到指称科学现象的科学仪器和由科学仪器组成的实验室当中去。
(二)指称之链的增强:实验层面的指称
自然科学讨论的毕竟是关于自然的知识,如果只把讨论停留在文本之上,似乎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你怀疑我写的东西?让我演示给你看。”“一位没有被科学文本说服,无论如何也不放过作者的十分罕见的、固执的持异议者,被从文本领进了据说文本由之而来的地方。我把这个地方叫做实验室。”[4]64现在我们已经从文本世界走向了仪器世界(实验室就是仪器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仪器是引导我们从论文走向那些支持论文的事物。“什么东西处于一部科学文本之后?记录。这些记录是如何得来的?通过设立仪器。”[4]69我们应当注意,仪器本身并不会说话,只有通过科学家的评论才能明白仪器到底想表达什么。拉图尔针对这种对仪器的评论说道,科学家在对仪器进行解释时,他们“并没有说出比记录下来更多的东西,然而若是没有他们的评论,记录则会说出很少的东西。这里有一个词语可以用来描述这种奇怪的情形,该词对接下来的所有讨论相当重要,这个词就是代言人(spokeman)。其作者的行为方式就好像他或她是在仪器窗处,被记录下来的东西的喉舌一样”[4]71。因为是仪器的喉舌,所以代言人在发表观点的时候,总是声称他或她的主张并不是其个人的观点,而是被指称者的观点。
持异议者总是存在的。反驳代言人的观点要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甚至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总有不畏困难的持异议者勇于反驳代言人。当通过文本不足以反驳代言人的时候,持异议者便设立新的仪器,组建新的实验室与代言者进行争辩,以期证明代言人并没有真正为被代言者代言,即想要说明,代言者所表达的观点与仪器本身所隐藏的道理是相违背的。
当对代言者的主张进行考验时,其结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代言者经受住了考验,一种是持异议者获得了成功。如果持异议者获得成功,代言人就变成了仅仅表达个人意愿或个人幻想的人。如果持异议者的反驳没有成功,那么代言者就被看成许多沉默者的合格喉舌。即“经过力量的考验,代言人就被变成主观的个人,或者变成客观的代表。‘客观的’意味着不论怀疑者花费多大的力气想要切断你与被言说对象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一直维持不变。‘主观的’意味着当你以人们或物的名义说话的时候,听众们理解为你只代表你自己”[4]78。由此,我们不得不说,当科学家们的实验室能够抵御各种力量考验(即质疑)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科学家已经“客观地”呈现了实验室的内在规则,也可以说科学家已经为实验室所研究的对象做出了“客观的”表述。
(三)经受住考验的指称之链:实在层面的指称
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实验室里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呢?拉图尔说:“在仪器的背后,还有其他的东西抵抗着力量的考验,这种东西我暂时地把其称为新客体(new object)。”[4]87拉图尔继续论述到,新客体在其生涯的开端并未被定义,它是在实验室里经历了种种磨砺之后才被命名的。例如,吉耶曼在研究“生长激素抑制激素”的初期,把该物质只叫成是“某种抑制生长激素释放的东西”,而生长激素抑制素是后来才被命名的。由此看来,新客体之所以获得了名称是因为其经受住了考验而具有了客观性;同时,它的名称本身也包含了它经受考验的具体过程。
根据以上情形,科学家为了获得对实验室的最后优势,必须把新客体转化成所谓的老客体,并且把这些客体返到他或她的实验室里面。这样,新客体就会逐渐转变成一个普通的名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非常明显地看到,新客体已经被具体化(reified)了。当理论经受住了考验之后,对这个理论所指向的对象的权威解释应该就是该理论本身了。这时黑箱便形成了,此时此刻,我们便可以说:为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提供依据的“实验室现在已经强大到足够定义实在(reality)了”[4]93。紧接着,拉图尔说:“正如res这个拉丁词所表示的那样,实在即是抵抗(resist)的东西。抵抗是什么呢?力量的考验。如果在一种限定的环境当中,没有持异议者可以修正一个新客体的形象,那么这即是‘实在’,这个新客体即是‘实在’,至少在力量的考验没有改变之前,它就是‘实在’。”[4]93
(四)知识“客观地”指称了“自然”
至此,最希望看到的唯一裁判者——自然,却迟迟没有出现。那么我们就试图找到自然,让自然评判到底我们认识到的实在是否真正客观地反映了自然。然而,在寻找自然的路途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所做的依然是以前的工作,来到的依然是同一个战场,那就是说“我们在更大的历史自然博物馆里找到的是更多而不是更少技术性文献和更大的集合体,我们得到了的是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争议”[4]96。换言之,自然并不为任何一个参与争论的阵营提供胜利的转折点。
文至此处,不得不承认,自然本身并没有对任何企图为其代言的人有所偏爱或嫌弃;而当我们最终确定自然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才发现自然不过就是在争论当中的胜出者对自然做出的定义。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自然原来是争论结束之后的结果,而不是使争论结束的原因。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讲,大致可以这样总结:最有资格为自然代言的人就是那个最“客观的”代表者,即“客观地”代表行动者(actant)集体的人。 “客观的”又是什么呢?“客观的”就是能够抵挡(resist)住考验的代名词。可以表述为:科学家做出了指称(reference)其他行动者的表述→抵挡(resist)住了力量的考验→定义了实在(res)→指称(the reference of)了自然。简言之,科学知识“客观地”指称了“自然”。
自然只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即“当科学家说,需要比联合体和数字更多的东西,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冲突和解释之外的东西,来解决争端的时候,科学家就为这些东西找到一个好的术语,而称其为自然”[4]96。如果一定要问自然究竟是什么,我们只能说自然就是知识最终所指称的对象。由此可以得出,通过一系列的严格指称而生成的知识,必然具有“客观性”。同时,可以看到拉图尔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提出的知识论体系,表明科学知识的生成过程和知识的辩护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它们之间不可分离,也可以说是同一个过程。
四、结语
拉图尔的知识论既看到了科学实在论所秉持的非人类因素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也兼顾了社会建构论强调的人类因素对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影响。可以说,拉图尔的知识论超越了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的立场,对科学技术现象、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给出了恰当而合理的解释,弥补了以往科学哲学的不足,这一点正是其理论的魅力所在。
然而,拉图尔知识论的成功之处也正是其理论需要批判的地方。拉图尔把知识的形成过程看成是行动者不断指称的过程。同时,行动者和行动者之间,通过指称建立起了行动者关系网络,所有的存在物都是在行动者网络之中存在,或者都是行动者网络指称的对象——比如“自然”(其实,拉图尔在他的整个知识体系当中,总是排斥“自然”这一概念,但是他最终不得不引出“自然”的概念,这就是他的理论的一个无奈)。结合上文论述,可以看出在拉图尔的知识论体系当中,“自然”只是在争论结束的地方才出现,也就是说“自然”只能被最强的指称之链所指称,而最强的指称之链并不是不可以被打破的,或者说在经常情况下也是可以被打破的。那么,“自然”到底是什么似乎并不能被确定,或者并不可以在终极意义上被认知。这里的“自然”不禁让人想到了康德的“自在之物”。是的,从康德的理论体系来看,这里的“自然”就沦为了康德意义上的“自在之物”,甚至可以说,拉图尔的整个理论就停留在康德的“现象”之中了,并没有超脱康德的理论体系。以康德的理论来评价拉图尔知识论的话,必然会得到上述观点;只是拉图尔会说:“康德是从‘人’和‘自然’这两极出发的,而我是从‘人’和‘自然’之间的存在物出发的,这是我的原则,也是我的真诚;至于自然到底是什么,我尊重康德。”
同时,关于拉图尔的知识论,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就是拉图尔并没有对 “行动者”的异质性进行区分。即拉图尔并没有对指称之链之中的行动者——既有“生物”也有“非生物”,既有“科学家”也有“非科学家”,既有“人”也有“非人”(或者说既有“理性的存在物”也有“非理性的存在物”)进行区分,而是把他们(它们)的地位和性质视为相同,这一点应该是违背常识的。简言之,把懂得修辞的科学家和一块根本没有任何生物属性的石头视为一致,是明显不妥的。也许,拉图尔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他是故意这样处理的,因为不这样处理,“自然”和“社会”的区分就会不可避免地形成,“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也就很难被跨越。然而,不同行动者之间存在的异质性问题是不能回避的,究竟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就有待拉图尔或者我们进一步探索了。最后不得不说,拉图尔的理论虽有所不足,但瑕不掩瑜,颇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