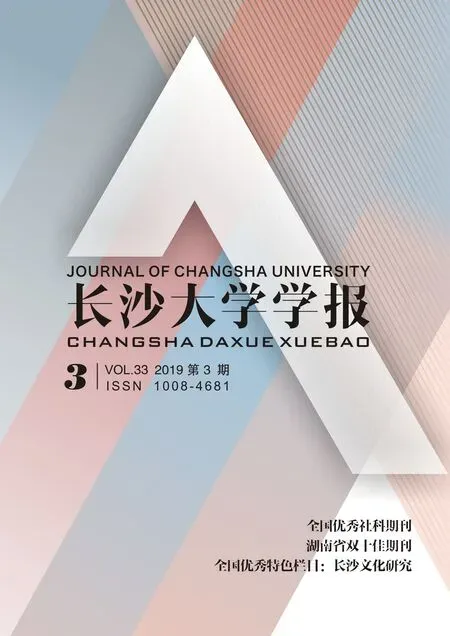民国初期长沙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仰
2019-02-15庞毅
庞 毅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民间信仰,均受到了历史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等不同学科的高度关注。在历史学研究领域,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对民国时期关注较少注相关代表性研究有:王健.明清江南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日常生活:以苏松为例[J].社会科学,2010(2);王振忠.华云进香:民间信仰、朝山习俗与明清以来徽州的日常生活[J].地方文化研究,2013(2);常建华.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史学集刊,2014(3);刘扬.信仰、群体与日常生活——清代以来东北民间信仰组织述评[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在长沙地方史研究中,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仰受到的关注亦不多,民国时期的日常生活多是被剪辫、放足、读报等新生活所占据,民间信仰则被放置到新生活的对立面“迷信”之中。透过尘封的报纸,我们发现,其实该时期民间信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长沙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娱乐等方方面面融为一体。
本文以湖南《大公报》为主要材料,通过截取三个历史片断,即节日庆典、庙会与醮祭,深描民国初期长沙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仰水乳交融的关系,从而加深我们对该时期历史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城市居民,主要是指居住和生活在长沙城区的人,并非西方社会中“市民”的概念。
一 节日庆典与民间信仰
民国时期长沙城市居民的节日庆典,仍是以传统的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为主导,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一抹亮色。每当传统佳节来临之际,每家每户都会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在这些节庆当中,民间信仰构成了活动的主要内容,尤以春节的香市、中元节的祭鬼、中秋节的祭月神最具代表性。
(一)春节香市
农历正月初一称春节,古称元旦。民国的月、日使用公历之后,改称公历一月一日为元旦,传统年节便称为春节。春节为农历一年之首,是湘俗中第一大节日[1]。每逢春节,长沙赴庙敬神烧香之人不绝于途,形成了集敬神、娱乐、商业等于一体的香市,俗称三大市之一(另有灯市、赌市)。
敬神烧香是许多长沙城市居民春节期间的第一件事。“湘人恒情,新年出行,必从庙始。故城中之玉泉山,城南之城隍庙、天庙,城北之龙王宫等处,从阴历元旦日起,无不车马游龙,炮声盈耳。”[2]“湘人迷信神道者极多,元旦日俱先赴庙观敬神,名曰出神。”[3]“新年向有出神方之习,故初一初三两日,玉泉山、龙王宫等庙,红男绿女,出方敬神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因此之故,造成春节期间,长沙各类庙宇可谓“人满为患”,其中,又以玉泉山为最。玉泉山香火之盛,为湖南省城第一。它是佛寺与神庙合一的宗教圣地,既祀观音大士,又祀陶、李二真人[4]。“初一日向玉泉山出行之男女成群结队,车水马龙,终日不辍,途为之塞。”[5]“定湘王庙、龙王宫、天妃宫、玉泉山各寺观行香敬神者,络绎不绝,而尤以初五日玉泉山为最盛,自朝至夕,红男绿女,前来上香者,不下万人”,该庙一日香资收入就可达“一千五百余串”,可见其盛况[6]。
除敬神烧香之外,长沙各城区的居民往往会以庙宇为单位,举行蚌壳舞、舞狮、舞龙灯等表演活动。舞狮与舞龙灯表演在各地比较常见,无须解释。长沙的蚌壳舞表演,即人们装扮成蚌壳等各类古怪精灵,活跃于长沙的大街小巷,表演各种神话故事、传说等。这些表演所到之处,不仅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欢声笑语,更蕴涵着神明的保佑。所以,无论是刮风下雨,这类活动都照常举行。1925年的春节,湖南《大公报》记载:“近日雨雪交加,闻蚌壳狮子稍稍敛迹,独城隍庙之城隍龙,大形骚动。昨日该龙在坡子街、八角亭一带游行,所到之处,家家户户,燃烛焚香,而城隍龙按户进出,围绕一周,其人民恭敬之诚,未有若此者。”[7]
新年敬神,人们除对神灵的信奉、崇敬之外,还有许多功利目的。如求财者,“还有一些大慈大悲,方便广开的少奶奶,趁头年初一,都到玉泉山烧香,祷祝今年‘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8];求子者,“出神还是在元旦,人人打扮最好看。许多绿女又红男,摇笺打卦向神龛。不求今年生贵子,便问今年的财喜”[9]。
从湖南《大公报》1915年到1927年的记载来看,每年的初一到十五,长沙城市居民赴庙烧香的盛况均是其报道的焦点,由此可知,该时期春节香市并未遭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二)中元节与盂兰胜会
中元节是长沙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在嘉庆《长沙县志》中记载,“七月初十至十五日,名中元,设羹饭酒食,盛列几筵,以祀其先,剪纸为衣,凿楮钱焚之,名曰荐祖。城市喧阗之处,或诵经献烛,施赈于孤魂甶子,谓之盂兰会”[10]。到了民国时期,中元节仍受到了长沙城市居民的隆重对待。“中元节届,家家都忙着接哑吧客——祖先之别名了,于是焚冥镪哪,烧包哪,办肴馔去祭哪,闹得个不亦乐乎。”[11]
一般来说,中元祭祖是每个家庭的主要活动。湘俗,“无论贫富,皆于初十夜,燃香楮于门外接祖,乃启龛陈所有之神主于堂上,有遗像亦悬之,朝夕治馔作供,五日而止”,“至十五夜,仍燃香楮送之门外焉”[12]。
不过,因中元节与佛教的关系,有时又会从家庭的祭祀活动变成社会公共的祭祀活动,谓之“盂兰胜会”。盂兰胜会的发起举办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由众人募捐举办,有系“各庙的和尚尼姑道人,四处募捐,设坛捣鬼”的,也有“戴着慈善头衔的人发起收捐,请一些和尚道士建水陆道场”[13]。如1925年长沙中元节,就由“戴着善士头衔的人”发起募捐,举办盂兰胜会。“东茅巷普天春内,近日有人发起举办什么盂兰胜会,发出□薄向人募款,预备于七月初四日设坛迎接所谓怪□神佛,办会七天。”[14]二是由某些社会组织、单位独立举办的。“值兹中元节届,正是捣鬼之时,昨二十九号晚,大西门外,□安公司,在门首高扎松□台三座,满挂红绿灯笼,缀以纸花,夹以电灯,天晚即有多数道士和尚,在台上捣鬼,河中河灯满放,岸上观者塞途。”[15]三是由地方社会官绅、名流发起举办。“田镇守使因思念旧将之情,而有中元超度幽魂之举,定自旧历七月十二日起十四日止,在考棚内请和尚为张前司令及兵弁等讽经超荐幽魂。”[16]
盂兰胜会期间各类活动不断上演,除上面提到的烧包、放河灯、做水陆道场外,还有叫夜、唱平安戏、放烟火等。1925年中元节,长沙就有唱平安戏。“请有各戏园角色扮演哥色鬼状,每词一章,出鬼一名,词上之鬼须与所出之鬼神情遍肖。”[14]至于举办盂兰胜会的原因,除追悼逝世者外,还有超度孤魂野鬼,祈求社会平安之目的。
(三)中秋节与祭月神
月神是中国民间流行的俗神之一,而对月神的祭拜主要在中秋节。月神又叫太阴星主、月姑、月宫娘娘、月娘、月光菩萨等。在古代的漫漫长夜中,月亮给人带来了光明,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自然受到人们的崇拜和喜爱[17]。
民国时期,长沙就有拜月祈福的信仰习俗。“本日为旧历中秋节,民间习惯,儿女罗菱芡瓜果于庭,拜月祈福。”[18]月亮由朔到望,由缺到圆,28天是一个变化周期,女性们发现,自己的经水也是28天为一周期。在人们无法正确认识人的生育生理时,误认为女性的月经和生殖直接相关。同时,月亮的圆缺变化,又使女性联想到自己怀胎后日渐鼓起、分娩后重修平复的肚子。所以,月神主生育的观念影响十分深远,受到人们尤其是女性的崇拜[17]。另外,中秋月圆,月亮又是团圆之神,吃月饼、喝团圆酒,拜月赏月,成为人们中秋节活动的主要内容。
传统节日庆典是长沙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其产生、发展又与民间信仰密不可分。除上述节庆之外,端午节、元宵节、清明节、七夕、腊八节等,都与民间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 庙会与日常生活
人们将神人格化以后,神祇和人一样有了生日,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庙会。相较于传统节日庆典,长沙的庙会更为密集。民国年间,每逢各类神祇诞辰,各类活动不断,形成了娱神娱人于一体的庙会。“长沙有县城隍庙、南岳行宫、陶公庙等50多座大小庙宇,各庙菩萨生日皆有固定日期。到了寿期,都要演戏三五日或十天半月不等。”[19]长沙一年四季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神灵诞辰庙会,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农历二月初二祀土地,二月十九观音诞,三月十五祀财神,四月初八祀如来佛及龙王,五月十三祀关公,六月六祀雷大将军,六月十九日祀观音,七月中元家家接祖,八月十七陶公生日,九月十九祀观音,九月二十六日为李公真人诞期,十一月十六日娘娘庙诞期,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灶神。”[20]在长沙各类庙会当中,最热闹的当属观音庙会。
(一)观音庙会
观音本为佛教中的神灵,但由于其救苦救难的形象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崇拜,由此观音逐渐世俗化,成为中国民间信仰中最广泛的神灵之一。观音诞辰说法有三,即二月十九为观音诞生日,六月十九为观音成道日,九月十九为观音出家日,民间有的将这三日并称为观音菩萨圣诞。在长沙城市居民的信仰世界中,观音信仰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长沙城内观音庙宇主要有玉泉山观音庙和西长街观音寺,每逢观音诞辰,二处香客如织。通过历年《大公报》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当年观音诞辰的盛况。“湘中愚夫愚妇有观世音之迷信,旧历九月十九为俗传观世音诞辰。记者昨过玉泉山,则见士女如云,香烟缭绕,加以梨园奏技,车水马龙,益复络绎不绝。”[21]“阴历十九日,俗传为观音大士得道之期,故省垣各业林庙祝预为挂灯结彩,烛火辉煌。一般善田信女不定期愿求福大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概玉泉山亦巨刹之一,当省垣中,□其香客较他处为多。”[22]“作为阴历二月十九,俗传系观音菩萨诞日,玉泉山庙,是日黎明起至晚,善男信女,前来敬香者,络绎不绝,黄泥瑕玉泉街,府东街息机园口,息息相关一带车轿塞途,终日拥挤不堪”,“庙内罗拜敬神男女,此去彼来,拥挤不通,香烛无处插放,乃堆放坪前钱鼎中烧化,烈焰气胜,有如火山。此一日中不知烧去若干金钱矣。且香烛触人,鞭声振耳,实极一时之热闹与纷扰”。[23]“昨八号乃夏历六月十九,相传为观音菩萨诞日,自黎明五时起至晚,善男信女,前往玉泉山进香者,车轿塞途,络绎不绝,文运街、玉泉街、万福街、黄泥街、府东街、息相街一带,香烛摊林立,附近各书店,亦临时售香烛,庙坪置大铁鼎三个,长条大香炉三个,俱烈焰飞腾,香烛堆烧成火山,无处插放,殿上香烟迷目,罗拜地下求签问卦之男女,恒二三百人,川流不已,热闹情形。”[24]从上述引用资料的时间看,整个民国初年,长沙城观音庙会始终香火不辍,人数众多,极为热闹。
庙会的举办也带动了消费市场,长沙香烛业便为之一振。“本日又称为观音生辰之期,黄泥段、玉泉街、府后街一带,香摊林立,以供求神者之需。”[25]“昨天是观音诞日”,“香市之嘈杂”,“环玉泉山之黄泥瑕、文运街、长康路、玉泉街一带,车水马龙,甚形拥挤,卖香烛者,大声疾呼,‘太太带幅香烛去’,而各女眷之呼朋觅伴声,及丐妇之‘太太小姐发慈悲讨个钱’的声音,亦洋洋不绝于耳。街途人力车,整整排列,其情形与剧团门首无异”[26]。因为供不应求,除香烛店卖香烛外,沿街设摊者有之,另外,许多商店也临时卖起了香烛,以此招揽生意。“有一般投机家,特设小摊,售卖是物,当街叫喊,一逢人过,即自为进香客呼之购买。”[27]“售卖香烛者,除遍街设摊叫卖外,其玉泉街一带各项商店,多临时改为香烛店,生涯(“意”误)甚佳。”[23]香市的繁荣景象,也从侧面证明观音在当时长沙人的信仰世界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长沙民众为何虔诚地信奉观音?无疑,民众朝拜观音心态各不相同,具体原因很难获知。但通过湖南《大公报》有关新闻或许能管中窥豹。第一,还愿酬神。“某营长于去岁奉上□令于役安乡,路经七星湖,值狂风暴雨,扁舟被覆,刘君漂流数里,几濒于危,得渔夫捞救,始免于难。其驱从十余人,均葬鱼腹之中,某君谓非神力决不再生,遂于是日斋戒淋浴,叩于大士之前,并捐洋十元以为香火之费。”[22]第二,求子嗣。“药十街商民樊某,行年七十,尚无后嗣。于去年娶姜姓女为妾,冀流传一□,不致抱□道之悲,特于是日祷告观音之前,并跪诵其求嗣之文词,旨极怆凄。”[22]第三,求平安。“某甲年约三十,在地虔心拜祷之间,眼泪涌出,人咸异之,问何故,悲云:老母病危,服药无灵,因泣求大士垂救耳。”[28]尽管上述三点无法反映出当时人信奉观音的全部原因,但仍可以判断,观音成为了民众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保护神,其职司范围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为我们理解民众虔诚信奉观音提供了一个窗口。
(二)城乡之链
长沙城区庙宇林立,以庙宇命名的街道就随处可见。据不完全统计,长沙市区以寺观命名的地名就有54个,占总数的9%[29]。司管各方面的神灵众多,乡民进城求神现象较为常见;同时,乡村地区也有因灵验的地方神而受到城市居民的“青睐”。城乡不同神灵的存在,为城乡之间的连接搭起了一座桥梁。
乡镇举行庙会,往往会吸引不少长沙城市居民下乡。长沙各乡镇有“陶公庙、灵官庙等20多座寺庙举行庙会。其中以梨陶真人庙会最负盛名”[30]。陶公庙,位于长沙县梨镇临湘山,距长沙市区15公里。据同治《长沙县志》记载,相传陶公庙建自“梁天监中,迄今千余年矣,历代屡经修葺”[31],奉祀东晋太尉长沙郡公陶侃之孙陶淡及其曾孙陶烜。传说二人在此“羽化升仙”,因“亢旱火灾,祈祷辄应”,受到官民的崇拜。每逢两位陶公真人生日农历正月十三和八月十七,便举办盛大庙会。民国初年,省城善男信女纷纷前往祭拜。1919年陶公神诞,“今年八月的诞期,又碰了中华民国国庆的日子,城里的学生,也有因当国庆假来行香的,城里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乡里的农夫农妇,看牛儿子村里姑娘,老的少的,美的丑的,形形状状的络绎不绝”[32];1924年,“榔梨市陶李真人生日,省中士女往朝拜者,至使小火轮特别增加生意,而乡城各处之慈善堂,乃触目皆是,男女趋拜,若饮狂药”[33]。
长沙北门外新河的龙王宫,也受到长沙城市居民的虔诚信奉。新河龙王宫,每逢四月初八龙王生日,举行庙会,不仅附近村民前往参加,城内居民也纷纷前往。1926年,新河龙王宫庙会,“新河地方,原有四团,各团分演几天,此外如光华电灯厂,华实纺纱厂,面灰公司,牛皮厂,也各送戏几天,和团上取一致的行动。附近乡村和城内的老幼男女,每日前来看戏的怕莫有几千人”[34]。
因为庙会的举办,为城乡贸易创造了条件。“清末和民国时期,庙会是长沙县物资交流的主要形式。”[30]陶公庙会,一般“每次时间长达10天左右”,“前来赶庙会、朝拜的香客成千上万”,“每次庙会,古戏楼上好戏连台,长沙城里的戏曲名角都登台演出,整天整夜连演连唱”,“庙会期间,商贾云集,买卖和交换商品的生意十分红火”。因为庙会的需要,人们结庐成市,形成了“三仙街”,有民谣唱道:“梨街上不作田,两个生期吃一年。”[35]可见庙会期间贸易的繁荣,民国《长沙县乡土志》也提到“市场庙会,贸易发达”[20]。
城市居民到乡村参加庙会,一般多是祭拜比较灵验的神灵,参加比较大型的庙会,时间上也比较固定,神灵诞辰或得道之期等。与城市居民不同,乡村居民进城拜神相对比较“随意”,没有固定的日期,什么时候进城就可能去进庙烧香。如1918年长沙戒严期间,一乡人进城可能是购买洋瓷壶和茶叶,后到玉泉山“求茶勅水”,并燃放爆竹,不知“戒严期间不准鸣放鞭爆”,因而受到警察讯究[36]。
自然灾害时期,长沙城乡居民也常常进城求神。1925年,长沙“天气亢阳,禾苗枯槁,长沙乡民晋城求雨者,日有所闻,但多为一乡一村之众,至昨日各都团联合为大队”,“约众千余,均青衣包头,各捧凳香,由浏阳门晋城,于午前十一时入省署,高宜□语,拜跪祈求”[37]。农民进城求晴求雨,与长沙的政治地位有关。长沙是湖南省会,省、市、县政府机关所在地,为确保安定等原因,官府一般会发放食物对进城农民进行安抚,农民因而会得到一些物质上的实惠。与之相对应的是,在神灵世界,地位高、法力大的神灵也多在城中,这也是民众进城的主要原因。
城市庙会不仅是城市居民精神寄托的场所,也推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特别是香市、交通等。与此同时,城市周边的乡村庙会,成为链接城乡之间的重要桥梁。城市居民参加乡村庙会,一方面当然是拜神祈愿,另一方面也给乡村带来了巨大的消费人群,促进了城乡之间的贸易交流。乡村居民前往城市拜神也有类似作用,但相对松散。
三 醮祭与“非常”生活
比之于节庆和庙会,醮祭没有固定日期,大多是在水旱虫灾和瘟疫等非常时期举办,但这并不妨碍其在长沙城市居民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民国年间,长沙经常举办醮祭活动。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长沙的醮祭至少包括消灾祈福醮、火醮、瘟醮、万人醮等。
消灾祈福醮,顾名思义即以消灾祈福为目的所建的醮,这类醮在长沙最为常见。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长沙消灾祈福醮名目繁多。1916年3月,湘西兵祸不断,人民死伤无数。长沙积善小补堂各巨绅,“特延僧道建七七四十九天大醮,为湘西难民死者超度,生者祈福”[38]。同年7月,长沙南门外贺家塘,“近高搭彩棚,横截道左,饶钹喧阗,□灵杂列,巫俗膜拜,士女环堵,更有仪仗车马亭障之属,额曰皇经福醮”[39]。1919年,商民潘华甲、王信和、蔡青珊、李桂荣等在社坛街举办经醮七日,“整洁斋修,禳灾祈福”[40]。1923年1月,长沙各粮栈及四乡发现一种小虫,食谷异常厉害,民众很以为奇怪,说“大劫将至”,“天降奇灾”等谣言四起,于是“群起窃议,以为非祀天建醮不足以俛天心,救此浩劫,于是祈神建醮之事,各处皆有”[41]。1923年8月,长沙绅商李达璋、许有庆等拟在经武门外老协操坪建天香大醮,以“超度阵亡将士”[42]。1925年6月,长沙南岳行宫与各善堂耆绅,“为救灾祈福起见,特建‘普天合一救灾圣醮’,定于本日(十六)在南门外魏家冲大烧三丈三之天香”[43]。同年8月,省垣士绅许有庆、李达璋等 “为救灾祈福起见”,在南岳行宫“修建九十天弥罗救劫大醮”[44]。
除消灾祈福醮之外,还有为辟邪禳灾、祈求解厄为目的的醮,主要有火醮、瘟醮、万人醮等。火醮,即以消除火患目的而建的醮。1926年6月,长沙青石街正假登陆街某庙建醮,即“为求神保火”[45]。瘟醮,即为消除瘟疫而建的醮。1925年8月,长沙“耆老信士以大旱之后,恐有大疫发生,特发起在南岳行宫大建弥陀醮典”[46]。“沅陵人民顽痼,风俗故陋,每每发现疫疠灾情,便求神建醮。”[47]万人醮,即向多户人家募捐而建的醮。同年,长沙“有袁迪□者,住北门佘家塘,因前年其妻胡氏抱病,医药罔效,听信卜筮者云,须建万人醮,病果痊愈”[48]。各式各样的醮祭反映出民国初年长沙等地民众的生存状况,同时也折射出醮祭在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要作用——消灾祈福,祛病减灾。
醮因种类不同,举办方式、规模等也不一样。通过各类醮祭时的情况,可以发现当时民众的参与程度。1916年,长沙贺家塘皇经福醮,“高搭彩棚”,“饶钹喧阗,□灵杂列,巫俗膜拜,士女环堵,更有仪仗车马亭障之属”[39]。1919年长沙大西门正街打醮,“人山人海,挤得不通”,各店铺门口摆着“纸糊篾札的东西,点得灯烛辉煌”,某典当铺里,“头门上大大的贴了天师府三个字”[49]。1923,长沙老协坪天香大醮,“虔修醮典三十六天”,“共焚百零八尺天香一架”,“用费将达一万”[42]。1925年长沙南门外建“普天合一救灾圣醮”,“定于本日(十六)在南门外魏家冲大烧三丈三之天香,届时用全付执事锣鼓□乐,由南岳行宫出发,遍游城厢后,再往魏家冲拜烧天香,捧香上路男女,闻准备有一二千人”[43]。
醮祭大多场面盛大、仪式隆重,参与人员众多。建醮一般由善堂等民间组织或团等地方基层组织来组织,民众积极参与其中,开展游街、捧香、舞龙灯等活动。从建醮的时间上看,基本没有一定规律可循。多数属于“突遭灾害而急需祈禳之时,或由于其他不得已事情,而随便择期举行者”[50]。
建醮花费甚巨,如何筹款?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长沙主要以按户科捐摊派进行募捐。“章醮之费,动需数百缗或数千缗。按房租业主七分,赁户三分抽之。”[12]1916年7月长沙贺家塘之醮,即“按房租抽收,主提三成,客加三成”[39]。1923年1月长沙清乡会建醮,“带同警察挨家募捐,多则三元五元,少则二角三角”[51]。1926年1月南岳行宫“弥罗救劫大醮”,“带着穿军服的人到街收捐,每家须捐洋五角”[52]。另外,也有由官绅等主动捐款者。如1922年11月,宝南街风化至善堂“紫霞胜醮”,便由“‘赵总司令捐洋八百元’,‘赵总司令捐香纸费洋二百元’。以下如宋师长、吴镇守使、谢镇守使……都捐了若干元”[53]。按户摊派,表明醮祭的正当性。人们对其举行并没有反对,则说明醮祭已经成为俗例,为日常生活所常见。尽管报纸多持批评态度,但上至高官,下至普通百姓参与其中,则表明醮祭在当时受认可的程度相当高。
捐款建醮,捐款者态度和目的各不相同。有真心祈福建醮的主动捐款者,但其中也有乘此机会敛钱收费的。“真心抽捐打醮的,固然不少。借此敛钱的,也狠多的”[54];“三数无赖者,按户科捐,扣其说则以此次汤督宵遁,该处保全,乃伊等预许福醮之力,故呼朋引类,硬派勒索”,“有表示反对者,即勒令迁徙,攘臂破口,必偿其愿而后已”[39]。也有碍于街坊情面而捐款者。“捐款多有不愿意出的,勉强出费的,都是碍看街邻的情面,不能推却。当这军兴的时候,街邻又如何能够得罪的呢。”[54]另外,还有被迫捐款者。建醮者借警察和军人收捐,民众怕得罪这些人,而被迫捐款。“有所谓‘慈善清乡会’的人,带同警察挨家募捐”,“虽贫穷人家不能担负,见有警察同行,莫可如何,只得勉强承认”[51];“有所谓‘弥罗救劫大醮事务所’的,带着穿军服的人到街收捐,每家须捐洋五角,口头虽是乐捐,但是带着穿军服的人,就有点不由人不乐捐的意思”[52]。显然,当时的醮祭有变质的味道,成为不少人敛财的藉口,且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批评,但醮祭依然大行其道。
醮祭作为民国初年长沙经常出现的民间信仰活动,虽然它没有固定的祭拜神灵对象,主要通过道士与天、神沟通,以达到消灾祈福、辟邪解厄等的目的,但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灾难、疾病等问题密切相关,在人们的信仰世界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当我们摒弃现代化语境中的“传统与现代”“迷信与科学”的话语,而是回归到历史的情境当中,民国初年的长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不同的历史画面。透过1915年到1927年间长沙城市居民的节日庆典、庙会与醮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历史并不是“传统”被“现代”取代,“迷信”被“科学”打倒,而是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仰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民间信仰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节日庆典、庙会,还是醮祭,都有相当多的城市人群卷入其中,形成了隆重的节庆活动、热闹非凡的庙会、大小不等的醮祭。而在这些活动当中,民间信仰是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比如春节香市、中元祭鬼、端午节拜月神,均是这些节庆不可缺少的内容,更不用说,神的生日庙会与消灾祈福的醮祭。并且,这些活动贯穿了长沙城市居民一年到头的日常生活。另外,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紧密的关系,不仅体现在精神生活层面,也体现在物质生活层面。在节日庆典与庙会活动当中,在敬神的同时,还会有演戏、舞狮、舞龙灯等精彩纷呈的表演活动,丰富了民众的娱乐生活。同时,由于活动的举办,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买卖贸易也繁盛起来,特别明显的就是城乡庙会,在一定意义上而言,这也是城乡的物资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