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伊朗高等教育成立阶段的话语性战略分析
2019-02-12卡西姆·扎艾力王诚
卡西姆·扎艾力 王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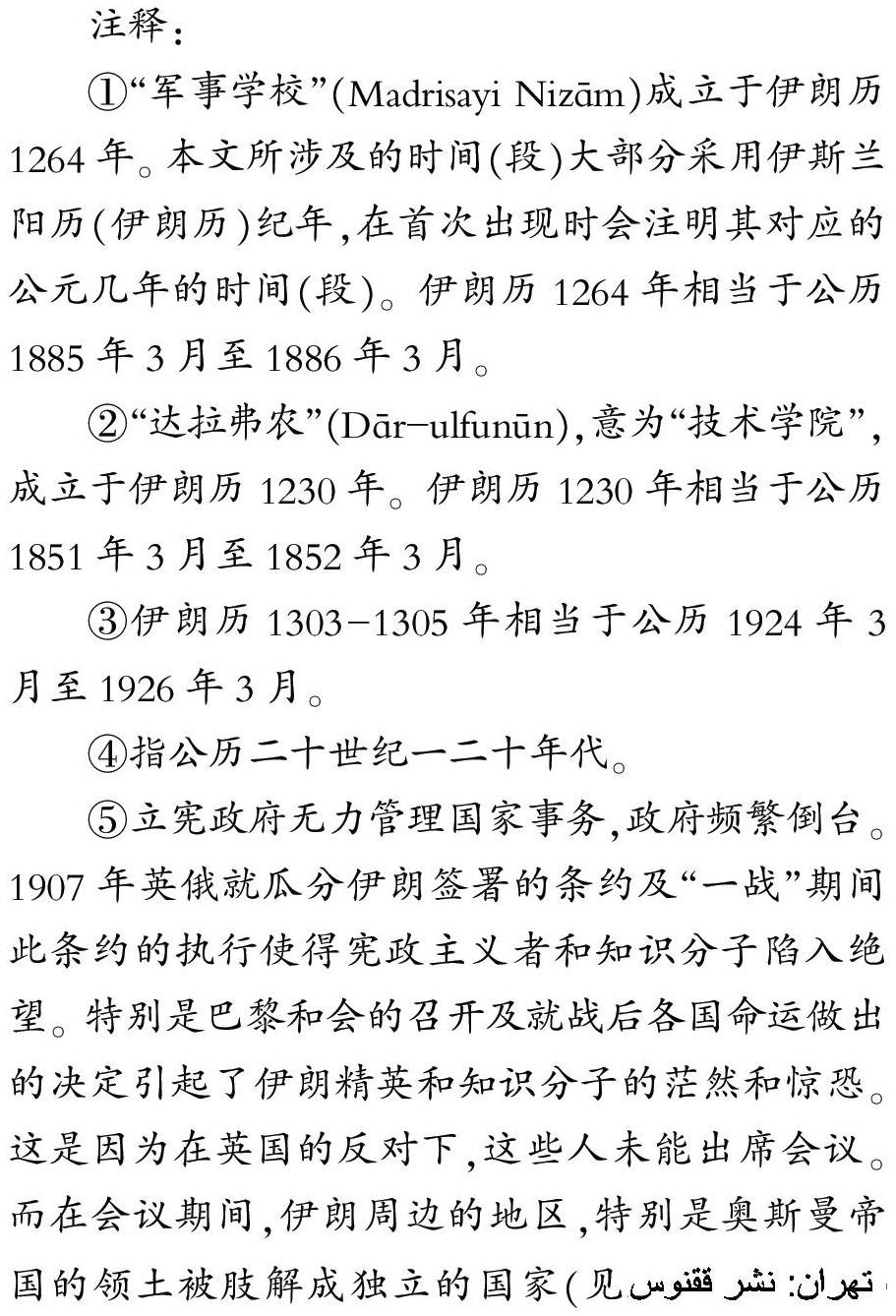

摘 要:文章以福柯分析历史现象的方法为研究方法,旨在探讨伊朗高等教育问题提出的缘起。尽管诸如“达拉-弗农”(Dār-ulfunūn)技术学院和“达拉-穆阿雷敏”(Dār-ulmualimīn)师范学院等新式教育机构已分别于伊朗历1230年(公历1851年)和1297年(公历1918年)建立,但是有关高等教育的议题却是在礼萨·汗执政初期,即从伊朗立宪革命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才得以提出。这一议题提出的背景因素包括政府现代化的需求,知识分子获得的新地位,“一战”结束后国际上的混乱关系以及立宪革命的失败。在上述条件下,《未来》杂志在伊朗历1303-1305年以《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为题发表了意见征询,收集了大量知识分子和官员的观点。此次征询有两个明显特点:其一是相对明确地提出了“新科学”的本质及其与传统知识的区别;其二是首次将“高等教育”同“初等教育”相区分,将其冠以“高校”之名,同时将其视为解决伊朗政府和社会问题的独立于“初等教育”的个体。此次征询中,知识分子为确立并解释“高等教育”的概念提出了四种方法,其中之一便是将传统学科和新式学科相结合,并藉此恢复穆斯林学者的“高等知识”和伊朗伊斯兰的文明传统,进而在伊朗建立高等教育。知识分子关于“高等教育”的言论也属于早期探讨“新思想本土化途径”的内容之一。
关键词:伊朗高等教育 知识分子 《未来》杂志 话语性战略分析
一、问题提出
在伊朗和其他一些伊斯兰国家面临现代化冲击之后,承担“大众”“公共”等初等教育责任的学堂(Madrisa)得以建立。随后,在受众和功能上都与其不同的高等教育理念问世。对于学堂,革新派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推广学堂,使民众“脱盲”,即拥有读、写,甚至更高水平的能力,进而使民众产生革新思想;而高等教育主要关注社会的专业化,并与现代生活秩序中的先进分工相关,革新派亦尽力推广,以使其引导伊朗社会。很明显,从“推广学堂”到推广新式的“高等教育”的转变需要社会学的解释:首先,政治家和革新派在伊朗社会需求问题上的观点出现了差异性;其次,社会内部各阶层中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对新式教育的需求;再次,在非现代的社会出现了现代化的历史发展新阶段。在恺加王朝(Qājāriya)时期,随着“军事学校”①和“达拉弗农”②等教育中心的建立,这一转变的意义以及探讨“伊朗高等教育议题产生背景”这一问题的必要性更为凸显。这些教育中心,有的明显超过了“小学”的内涵,其教学计划也与之有所不同,但高等教育的组织者和传播者——其绝大部分都是政治家或者这些教育中心的管理者——却并不将其视为“高等教育”机构,因此,尽管有上述教育存在,他们仍要求伊朗建立高等教育。
本文主要探讨伊朗高等教育议题提出的缘起,着重分析伊朗历1303-1305年间③在《未来》杂志围绕“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发表的意见征询。在此次意见征询中,一些重要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都发表了意见,并就高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本质,建设高等教育或初等教育的优先性及迫切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据此,本文将对“伊朗高等教育议题产生的可能历史条件”做出解释。
探讨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于,面对“新科学”和“大学”的问题是伊斯兰时期理解伊朗人特殊情况的最为迫切的需求之一。目前,关于“新科学”的替代物(如宗教学和本土科学)以及“塑造文明的大学”[1]、“国際大学”[2]、“伊斯兰式的大学”等议题均已得到探讨,但绝大部分探讨都没有涉及历史背景。本文通过探讨“高等教育”问题形成的历史条件,说明了关于“新科学”和“大学”的讨论的历史性。此外,考虑到知识分子对教育和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本文还将揭示伊朗知识分子对“政府”“民族”“国际关系”的关注。
二、研究综述
近几十年来,关于“新式教育”“新式学院”“高等教育”“大学”“新科学”的历史、本质、变化等问题的研究从未间断。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可分为如下两类。第一,一些研究者强调初等教育和普及教育,尤其关注“拉什迪耶”(Rashdiya) 和“达拉弗农”学校等“新式学校”[3]的兴起,而忽视对高等教育的讨论。第二,一些研究者将“高等教育”视同于“大学”,将探讨的领域局限在“大学”。这类研究者主要关注“高校建制史”相关的问题,其往往将德黑兰大学作为研究对象。此类研究者的代表包括法罗斯特霍赫[4](FarāstKhāh)、马赫卜比-阿尔德康尼[5](Mahbūbī Ardkānī)、塔里菲-侯赛尼(Tarīfī Hussaynī)和穆罕默迪[6](Muhammadī)。
上述两类学者在研究“伊朗高等教育史”这一议题时,均忽视了“新科学”和“伊朗新式高等教育”产生的独立的历史背景,而仅仅去讲述伊朗从古至今的高等教育史。实际上,“大学”是伴随现代制度诞生的新式教育机构;而在伊朗古代成立的教育科学中心,如“君迪沙普尔大学”(JundīShāpūr)、“内扎米耶学校”(Nizāmiya)、“智慧宫”(Bayt al-Hikma)等不能同近代意义的“大学”和“高等教育”划上等号。对于后者,应在其自身的文化框架和特点中进行理解。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概念,在伊朗和伊斯兰的学术传统中并不具备产生的条件,故应将其作为具有自身产生、发展历史的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而不应该将其同伊朗或伊斯兰文化框架下的学校和教育相关的议题混为一谈。与上述两种研究不同,本文的研究对象恰是与现代相关的伊朗“新科学”问题[7]。除此之外,就“高等教育议题在伊朗产生的时间”这一问题,本文的观点也不同于学界普遍认为的“始于恺加王朝的阿巴斯·米尔扎(Abbās Mīrzā)王储派遣留学生去欧洲”或“达拉弗农”建立的时间,而将这一问题在伊朗提出的时间界定在伊朗立宪革命失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段时间内。
三、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福柯(Paul-Michel Foucault)分析历史文化问题和现象的理论和方法。福柯通过批评传统史学,指出应出现这样一种方法或理论,其“能够给予研究者超越前人(学者、杰出人物)定见来对知识改变和断层(新知识范围的出现而非之前知识范围的延续)进行理解的可能”[8],而“系谱学”正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理论和方法。“系谱学”处于福柯思想体系的第二个阶段,是对其“考古学”方法的完善和深化。传统史学将确定的“原因”“概念”“力量”视为某一现象(如一场战争、一次饥荒、一个家族的兴起、一场骚乱、一次屠杀等)发生的因素。这种判定事物发生原点的方法符合这类史学与“总在寻找替罪者”的政治世界的联系。而根据福柯的系谱学理论,对事物或现象形成或发生改变的时间原点应进行仔细而深入的分析。对原点的分歧可以使我们“在某个特征或概念的统一的形式下,重新找到塑造这一特征或概念的大量事件”[9]。如今史学界所认为的“原点”,实际上是“原点”的重新架构的形式,而系谱学的责任便是揭示原点重新架构的形式。“原点”十分复杂,其包含了事故、细微的偏差、失误、评价错误与不正确的计算[10]。具有浅显外表的史学上的“原点”看起来安静、有序、静止且稳固,但实际上则是吵闹(如果我们仔细去听的话)、无序、破碎而易分解的。对“原点”的分析,体现了“被认为与自己同类的事物实为异类”[11]。历史现象没有统一的源头,其根源是众多的力量和元素,而现象本身包含了大量的残缺、裂痕和无法预测的因素。福柯“首先在档案和实验室研究中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努力以明确何人、何事以何目的对其他人说了什么”[12]。不同于基于个人或事件的伊朗高校及高等教育研究,本文试图探讨伊朗高等教育理念得以提出的历史条件间的随机的相互关联。
六、知识分子为解释高等教育地位所提出的话语性战略
在此次意见征询中,精英和知识分子提出了四种话语性战略以对在这一时期建设、发展高等教育的必要性做出解释。
(一)建设高等教育以服务政府现代化的战略
恺加王朝以来,伊朗逐步被卷入新的国际体制中。在此背景下,对政府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需求便一直是伊朗政治家的目标。成立新的机构、通过派遣留学人员到欧洲学习新的技术以对政府从业人员进行重组等措施是这一时期政治家们所做出的重要努力。在伊朗传统的体制内,政府结构依托的是传统的官僚制度,依靠的是神职人员、封建贵族、部落家族等传统势力,在知识分子看来,这种体制无法适应自己的改革计划。
为了消灭传统官僚制度,其一,要在司法领域引进新的法律和制度;其二,要用在欧洲或伊朗的新式教育机构中接受教育的新生力量取代传统官僚势力。这些新生力量不仅受过新的专业化的教育的培养,而且拥护新的政府,是巩固新政府根基的担保人。在这一进程中,教育不论是从其育人的本质属性还是从新政府的长期目标来说都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因此,教育应为新政府“确保新官僚(科层)势力提供服务以实现新政府的目标。在此次意见征询中,许多知识分子提到了高等教育与新官僚之间的密切关系”。萨迪克认为:“对政府下拨教育部的额外的预算用于派遣千名留学生到欧洲,令他们在那里学习对今天伊朗实现变革十分必要的新科技知识,如高级军事、农业工程、公路运输、教学管理、金融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理论和实践科学;回到伊朗后,他们可以用学位和人数上的优势消灭占领官僚系统重要席位的腐朽因素,进而掌控政府”[14]。再如,哈桑·穆沙拉夫-纳菲西(Hassan Musharraf Nafīsī)从官僚制扩展到“满足国家需求”的问题。其做了如下描述:“在一国之中,有学问和经验的执政者用于治国,专家和工程师配给工厂和技术机构,法院要有法学家,银行和经济机构的管理则需要经济学家,医生去消灭病原,军事家来发展新的军事技术,而教师则要培养知识分子和国民阶层。”他强调:“这些人都出于高等学校……国家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工程师、医生、法官和教师,若没有高等学校来培养他们,无能的庸才将会取代他们”[15]。他发问道:“这些人都出于高等学校,如果国家没有这些学校,如何培养这些人才?”
上述二人都拥有伊朗革新派的经验,他们都致力于建设新秩序:前者要求学习新世界的应用科技,后者则要求建立高效的新体制(科层制)以改善国家管理。从二者的主张来看,“新技术”和“科层制”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叠,由此可见,此二人都主张高等教育在建设秩序中发挥作用。
(二)建设高等教育以确保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战略
纳赛尔丁·沙(Nāsir al-Dīn Shāh)统治的中期以后,在伊朗逐渐形成了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一阶层了解在欧洲发生的变革,认为伊朗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低效且落后于欧洲[16]。尽管知识分子们的计划存有分歧,但大体都是要对伊朗的政府和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削弱甚至消灭守旧的传统势力。因此,对知识分子来说,教育机构具有其内在的重要性。其重要性可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知识分子对教育有着天然的依附。通过研究启蒙思想史可以发现:最初,知识分子意指“受过新式教育的人”——这些人去欧洲旅行,了解那里发生的变化,随后又在欧洲或伊朗接受了新式教育。在这里,“新式教育”指“在新式学校和学术中心接受的非宗教或传统学科知识的教育”。成立“教育协会”(Anjuman-i-Ma ārif)成为知识分子为了整顿、发展教育事业并确保自己社会地位做出的最重要的努力,而这一愿望最后以立宪政府批准成立“教育部”而实现[17]。从这点来说,教育领域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会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滑产生影响。在此期间,由于“现代化”与“科学”被视为同一物,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因此特殊化。因此,围绕教育发展,特别是关于教育等级划分的讨论,也会使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
其二,教育的差异化是确保社会等级划分的手段。由于“新式教育”这一象征性资本的存在。教育层级所发生的任何变化(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变化)将会导致社会、文化的等级划分发生变化。纳菲西持这一观点,其认为“高等教育”不仅可以为政府培养高效的专业人才,还可以成为社会等级划分的工具并确保政府对社会进行控制。他指出:“如果在某国所有人平等地获得初等(公共)教育,那么在这个国家没有人会成为杂货铺老板或卖甜菜的小贩;如果某一天,杂货铺老板的知识水平和部长的一样,并且他已经了解这一点后,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关掉自己的小铺而想要到部里工作,如此以往,这个国家一半的人都会想要到部里工作,那么社会生活也将不复存在”[18]。纳菲西认为,初等教育具有平等性,而高等教育进入人数的限制(接受此类教育的人需要具有更高的才智)天然成为社会阶层划分的重要因素。在其看来,社会的结构根据教育等级的标准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知识分子阶层,其认为,“在伊朗,应存在一个高于其他阶层的精英或知识分子阶层来管理社会要务”;二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国民阶层,其可以成为管理者的保障[19]。在纳菲西的社会等级划分中,“国民”可接受同等程度的初等或公共教育,但他们不应再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因为如前所述,建立秩序、管理社会需要教育的区别化,因此,对“接受高等教育”一事进行限制是必要的。在此社会结构中,首先应发展知识分子阶层,然后再培养其他阶层。因此,高等教育可以确保知识分子阶层相对其他社会团体在社会上的支配地位的延续。只有教育出现层级差异才有可能实现权力的运行、管理和控制。依上文所述,教育层级出现的变化应以确保知识分子的地位为准则。
(三)建设高等教育以服务领导国民的战略
教育首先服务于现代化,是伊朗现代化的战略之一;随着知识分子得到权力,这一战略也需要完善和提升。在立宪革命期间,教育是“觉醒”的渠道之一。显然在追求进步的道路上会有诸如传统迷信思想的精神阻碍、专制政府的客观阻碍阻止现代化进步思想的萌生与发展。若民众实现觉醒,则会渴望进步、追求幸福。“觉醒”一方面是指知识分子通过出版物、演讲等手段促使人民觉醒,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教育,使民众有文化,能够使其理解伊朗和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变化进程。因此,知識分子致力于发展“公共(大众)教育”(其标志便是成立“教育协会”和新式学堂),同时消除发展公共教育的阻碍。塔基扎德持此观点,他认为,教育部应将政府下拨的额外预算用于初等教育,而发展初等教育则是实现现代化、为知识分子成功提供保障的最为重要的手段。与其他强调高等教育优先发展的人相反,其既强调高等教育的必要性,也认为初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前提。塔基扎德指出,开明独裁者理念的成功以及知识分子管理阶层的产生离不开“国民的觉醒”的存在,“‘有识之士在一个缺乏教育的国家进行改革以及‘在一个没有发展的民族中出现有志有识之士的阶层是‘在理智上不现实且‘在数学上不可能的”[20]。塔基扎德的观点深受“一战”结束后的动荡局势以及知识分子在立宪革命后遭遇的失败境地的影响:首先,针对伊朗被“巨大的历史危险”⑦击败的情况,认为国民公共教育的发展是使伊朗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资本[21];其次,在对立宪革命最后失败的原因的分析中,其认为,立宪革命中所采用的成立政党、依赖教法学家和部族的支持等手段都是失败的;最后,立宪革命最终失败的原因正是仅仅将“治国要务寄托给受过教育的学者,而削减公众对国家、社会事务的干预”,因此,伊朗“不得不发展公共教育”[22]。当国民觉醒之时,他们可以给予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以支持。而塔基扎德的证据便是:绝大多数立宪党人都只接受过初等教育,但他们的确对立宪革命时期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给予了必要的帮助,在伊朗立宪运动和近代化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很明显,塔基扎德认为,教育的本质和目的不仅是实现政府现代化,还是实现社会现代化,帮助伊朗度过战后困境的主要途径。除去对“教育”的整体观点,塔基扎德同其他人一样注意到高等教育在政府近代化上的作用,并认为:如果伊朗在涉及治国理政方面的方法和技术上不能依靠外国人,而需要国内的学者,那么高等教育具有必要性。此外,塔基扎德相对于其他人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观点:“一国之中拥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仅仅是为了实现科层制政府的管理,更多地是为了引导国民”[23]。这恰与知识分子的要求相吻合。实际上,在塔基扎德眼中,相对于“技术和科层制”,引导民众的作用更为重要。当然,他也强调了实现高等教育及出现知识分子管理阶层的前提便是发展初等公共教育及产生觉醒的国民。
(四)对高等教育进行革新以使传统知识与新式知识相结合的战略
在“高等教育与引导国民与伊朗人对现代化的倾向性变化的关系”上,福鲁吉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其观点可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一是对“优先发展高等教育或初等教育”争论的批判。福鲁吉认为,塔基扎德对于“初等教育优先于高等教育”的争论是“不切实际的争论,仅仅为了显示自己是真理”[24]。他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对产生这种争论的原因做了解释——“认为‘初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前提的人忽视了这一点:在我国(伊朗),存在某种或某部分高等知识及其出现的必要前提。”他提到了法拉比(Fārābī)、拉齐(Muhammad-i-Zakariyā-yi Rāzī)、伊本·西拿(Abū Alī Sīnā)、比鲁尼(Abū Rayān-i-Bīrūnī)、纳西鲁丁·图西(Nasīr al-Dīn Tūsī)等伊朗中世纪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并指出:“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原因迫使我们遗忘他们”[25]。此处的“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是指欧洲人和东方学家的消极作用(对上述伊朗中世纪学者的批判及其对伊朗革新者的影响),以及敌视传统知识的国内革新派的观念——“我们处于起步阶段,故应该先发展初等教育”。这一观念阻碍传统科学与新科学发生任何形式的结合,也造成“从最低等级的教育开始”这一观点的形成,以及“教育部的工作被限制在初级学校的建设中”这一现象的发生。其认为,这种在伊朗教育领域占上风的“起步阶段”的观点,不仅否决了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实则也否认了对“初等教育”的需求。在此观点中,“对于深陷贫困的国家和民众来说,接受完整的初等教育仍是多余的;因为其会使得‘儿童的大脑受损而使他们不去从事工商行业,反而陷于‘不健康的思想”。由此可见,持这一观点的人强调“技能”,认为“最好满足于最低限度的文化水平以让儿童可以从事工业活动……技能教育可以使我们不需要完善教育系统”。福鲁吉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伊朗人还是“目不识丁的部落”,没有学生可以接受中高等教育[26],因此他们才会认为应优先发展初等教育。
二是高等教育是初等教育的前提。在探讨“初等教育优先于高等教育”这一争论的根源后,福鲁吉根据社会学家的观点强调了社会事务的本质:“对于任何事务的讨论若从个体性质转为整体性质,其整体情况也会改变。”其以社会的角度对教育问题和民族、社会与教育等级的关系做了探讨,并将这种关系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尚未开化的“野蛮”民族,这类民族的学生必然处于刚刚会识字的阶段,这样的民族必将永远是“他人的学徒”;第二类则是“在数个世纪中文明地生活”的民族,这类民族有著名的学者,他们不将公共教育托付给外族,而是自己承担起来。因此,他们“被迫要具备一定的高等知识以在有必要制定教学计划、编撰课本、培养教师的时候能够对公共教育进行有效管理”。他做出如下结论:“整体性特征与个体性特征相反。”这里是在讨论伊朗整个民族而非个人的教育问题,这意味着具备高等知识是公共初等教育的前提而非初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前提[27]。因此,与塔基扎德的观点相反,福鲁吉认为,在一个具有文明和学术传统的社会(如伊朗),高等教育是初等教育的前提条件。此外,福鲁吉继续对发展高等教育的目的做了更深一层的解释:“高等教育应通过我们充满雄辩和文采的作品使我们的‘国家意识得以觉醒……对作品的整体保存以及出版文選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的工作。”他强调,“高等教育对于我们来说是必需的,因为任何民族在缺乏国民勇气的情况下都无法生存”,而对于伊朗人来说,获得国民勇气最好的途径便是“通过展示古代文明和知识,将自身同新的灿烂文明相联结”[28]。他不仅强调“重述伊朗知识传统”“对伊朗知识的不断追寻”(特别是蒙古入侵之后的时期)在“重塑历史身份”上的作用,同时也指出“西方哲学界正重新回归伊斯兰哲学:在经历数百年对终极真理的探寻之后,欧洲的新哲学正在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回归神秘主义流派、照明学派,以及包括‘实体运动(Harkat-i-Jowharī)在内的新伊斯兰哲学家思想方式”。⑧[29]
福鲁吉认为,高等知识与“理想的完美程度”相关,仅在依靠高等知识的情况下才可实现理想的完美程度。当然,福鲁吉在这里并非是指伊朗,其关注的是文明的范畴,目的是消除现代文明出现的困难。他的战略是“古代知识与欧洲新式知识的结合”,为实现这一战略,他强调要关注、重视伊朗的文明和科学传统:“我们要从自身的悠久历史和知识传统中获得工作计划”[30]。他的方法将会促使“两个不同类型的文明相联结、两种思维相碰撞并擦出真理的火花”。这种方法对于世界文明来说是极其有益的,既可以实现“国家的愿望和国民所期待的幸福”[31],也可以在西方文明衰退之时“通过与东方进行结合而为人类世界的更新创造条件”。[32]
七、结语
本文对“高等教育”理念在伊朗提出的来龙去脉做了历史分析。在礼萨·汗发动政变后,伊朗知识分子再次获得权力,他们给予了礼萨·汗政权合法性,并活跃在其政府中——立宪革命的失败使得知识分子对民众感到绝望;而随着“一战”结束,动荡的局势使得精英对国家领土和主权是否保持完整和独立感到恐慌,而政府在建立国内秩序上表现出的无能也使得这份恐慌加剧。在此情况下,教育问题再次成为知识分子的重要议题,但是其内容已大不相同。实际上,在立宪革命之前,教育议题主要包括开化民众,使他们了解新世界的变化并培养现代意识。但是,在立宪革命失败后这段时间,由于政府的独立和权力问题的产生,知识分子地位的下降以及引导、教育国民的必要性的提升,知识分子对“教育”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并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议题——高等教育。该议题最终以大学的成立而得以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