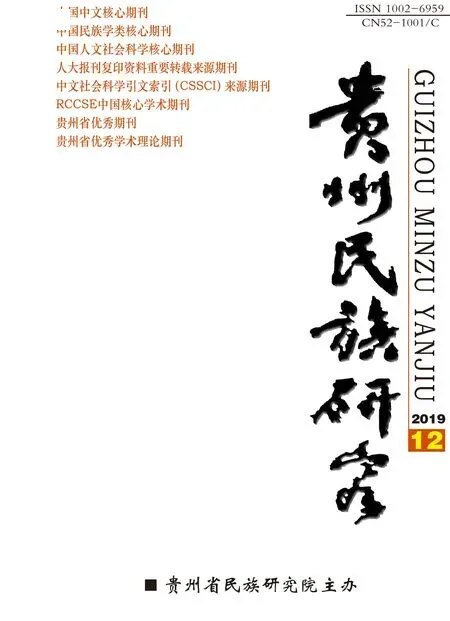文化视域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长诗比较研究
2019-02-10丛溆洋
丛溆洋
(西北民族大学 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30)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长诗是民间文学的一个门类,包括史诗、叙事长诗、抒情长诗。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长诗是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人们的精神需求也随着社会发展而提升。原有的神话、传说、短歌等旧的艺术形式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进而产生了民间长诗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新艺术形式的民间长诗在主题选择、艺术表达、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比先前的神话、传说等旧的艺术形式更加深刻、完美。如蒙古族的《格尔斯可汗》、傣族的《厘俸》、壮族的《莫一大王》等英雄史诗;傈僳族的的《逃婚调》、彝族的《妈妈的女儿》、苗族的《娘阿莎》等叙事抒情长诗。这些民间长诗在产生过程中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社会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使它们彼此间呈现出普遍共性的同时,又具有其独特的个性。
一、少数民族民间长诗中的共性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长诗大约产生于军事民主制时代,形成于奴隶制社会时期,其发展历程贯穿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纵观我国少数民族民间长诗的创作及传播,我们发现,它们在创作艺术程式、主题表达及艺术传播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共同之处。
(一)趋同的创作艺术程式
现实主义与浪漫理想主义并存的创作艺术程式是我国少数民族民间长诗共有的艺术特征,特别在英雄史诗中体现尤为突出。英雄史诗多产生于军事民主制时代,形成于奴隶制时代。该时期氏族部落逐渐走向阶级压迫,部落与部落之间战争频发,人们需要英雄来维护民族命运,保卫部落安宁。因此,出现了围绕民族命运大事来塑造推动民族历史前进的英雄形象的英雄史诗。在这一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民间长诗多数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理想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以英雄人物、部落战争为主题,在描绘残酷现实生活的同时,以塑造英雄形象来抒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如蒙古族的《江格尔》、壮族的《莫一大王》、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傣族的《厘俸》等英雄史诗均形成于该时期。它们都是人民在长期保卫战争和生产斗争中创作出的现实性和艺术性并存的英雄史诗。这些英雄史诗结构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它们用艺术的手法反映了各族人民长期生活在战火频发和斗争不断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各族人民期盼安宁生活的社会理想。如《江格尔》《格斯尔可汗》,它们是蒙古族两部结构宏伟,内容繁复,具有人民性和艺术性的长篇英雄史诗。两部史诗描绘了蒙古族从氏族制社会形态过渡到奴隶制社会形态的历史时期,尤其在11世纪至12世纪时期,蒙古族社会动荡不安,各部落之间相互攻掠。蒙古族人民为了能够生存和发展,他们与社会恶势力及自然灾害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江格尔》中是以“蟒古斯”的形象出现,在《格斯尔可汗》中是以“十二妖魔”的形象出现。这些被幻化出来的恶势力贪得无厌、残害众生,破坏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江格尔、格斯尔及他们所率领的诸多勇士都是作为镇压恶势力,保卫部落安宁的人民英雄而存在的。他们救护生灵,征服魔鬼,除暴安良,反对掠夺,浴血奋战,保卫乡土。这两部蒙古族英雄史诗均是采取了现实与神话交织的艺术形式,通过歌颂英雄,反映出蒙古族人民对部落征战,部落分裂的厌恶,对贤明君主和安定国家的渴望。
《江格尔》《格斯尔可汗》两部伟大史诗,在根据社会现实编写的同时,又继承了神话、传说的浪漫理想主义色彩。这种浪漫理想主义色彩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之中。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史诗的人物被神化,江格尔、格斯尔及他们的勇士们都有着非凡的本领,他们能变化万端,能未卜先知,能起死回生,能上天入地,能通晓动物语言,等等。这种超越人力所及的能力是蒙古族人民心中的幻想,以幻想来描绘英雄,崇拜英雄是蒙古族传统审美观念的反映。在故事情节中,这种理想色彩表现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在《江格尔》中人们塑造了“宝木巴”这个理想王国,把“宝木巴”描绘成:“没有死亡,人人长生。不知骚乱,处处安定。没有孤寡,老幼康宁。不知贫穷,家家富裕……”[1]。也表现在战场上征战的曲折离奇,变化多端。如《格斯尔可汗》中锡莱河大战的情节表现,包达齐在千钧一发之际用葫芦喷神火,格斯尔的妃子阿珠莫尔根可以恢复已经变成毛驴的格斯尔等。这些奇思妙想、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富有瑰丽的幻想色彩。
现实主义与浪漫理想主义交织的创作艺术程式不仅限于《江格尔》《格斯尔可汗》两部史诗,其他少数民族的英雄史诗在创作艺术程式上也如出一辙。又如壮族英雄史诗《莫一大王》。这是西南地区的一部英雄史诗。史诗的雏形大约产生于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壮族正处在军事民主制时代,西瓯、骆越统一岭西各部,正处于建立国家政权之际。在数百年里,壮族经历了蜀王南征、楚越之战、秦瓯之战,以及赵佗的近百年武力威边等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壮族产生了一批悍将,他们即是莫一的原型。莫一在作品中既是现实中的人物代表,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非凡能力的神话人物,他能赶山,能扎草成人,能把升起的太阳压下去,能头断而不倒地。莫一超越现实的形象塑造,为其赋予了至死不屈的浪漫理想主义精神。还有彝族的《支格阿龙》,其在艺术程式上也与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相似。
在这些史诗中,其时代背景、故事情节及人物塑造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
(二)相同的创作主题和价值取向
民间长诗从创作主题上大致可分为英雄史诗、抒情长诗和叙事长诗三大门类。英雄史诗的创作主题主要着眼于部落存亡、国家人民利益等宏观层面,通过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来描述关系民族命运的大事,塑造了一个个伟大而崇高的英雄形象。这类史诗有蒙古族的《江格尔》、壮族的《莫一大王》、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抑或是为了国家利益,人民安宁,毅然率部征战沙场,抵御外敌入侵的英雄。如土族的《祁家延西》、哈萨克族的《霍布兰德》《英雄塔尔根》等。这些充满伟大斗争精神的英雄人物以其粗犷、博大的感性姿态,雄伟、悲壮的气势,鼓舞和激发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产生敬仰和赞叹的情怀,从而提升和扩大了人们的精神境界。
叙事抒情长诗产生于奴隶制中后期及封建社会时期。该时期阶级矛盾尖锐,社会上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压迫等社会现实,文学创作也在逐步摆脱原始神话里的美妙幻想,走向自觉表现不幸人生的艺术道路。这个时期的民间长诗多以个人及家庭不幸等微观层面的弱小群体为内容:如以爱情悲剧、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民间长诗有傈僳族的《逃婚调》《重逢调》、彝族的《妈妈的女儿》、裕固族的《黄黛琛》、羌族的《木姐珠与斗安珠》、傣族的《娥并与桑洛》等;还有以叙述历史事件、习俗起源,调节民间纠纷,弘扬民族传统美德,规范民约民规等叙事长诗。如:维吾尔族的《安哥南霍》、裕固族的《尧熬尔来自西州哈卓》、满族的《尼山萨满》、彝族的《阿诗玛》、白族的《出门调》、壮族的《尞歌》,等等。
这些民间长诗虽然是出自不同的民族,但是,在创作主题和价值取向上却趋于相同。首先,就英雄史诗来说,其创作主题多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民族事件或传说。描述他们为了保卫家园,部落安宁,以大无畏的气魄与各种敌对势力殊死搏斗的英雄气概,塑造了各种高大英勇、推动民族历史前进的英雄形象,是各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写照。从价值取向上,各英雄史诗都表现出高度的思想性,它们歌颂人民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求得生存发展的积极进取精神,表现出深刻的反侵略,反战争的主题和价值取向。自我牺牲,敢于拼搏,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精神成为了各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主旋律。其次,就叙事抒情长诗来讲,叙事抒情长诗创作多以个人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为主旨,以个人的不幸和家庭的不幸为内容,以爱情悲剧,封建压迫为主题。反映各少数民族人民为了自由幸福的美好生活而不畏压迫,不畏困难,勇于与阶级压迫做斗争的反抗精神。各少数民族叙事抒情长诗的主人公多是为了争取婚姻自由与幸福同封建礼教及婚姻制度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甚至不惜殉情。各少数民族叙事抒情长诗成功地塑造了许许多多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在这些形象的身上,人们将自己内心的激情注入其中,通过他们的言行,表达了爱与恨、痛苦与欢乐、期待与追求等内心世界,进而成为鼓舞世代人们去追求,去斗争的强大力量。
(三)相似的说唱传播形式
民间长诗作为民间文学一个门类,其本质功能是审美功能,同时,还蕴含着娱乐功能、教育功能,等等。我国少数民族多数都地处边陲,传媒不畅,且有的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交流手段欠缺,因而,口头说唱就成为少数民族民间长诗传播的重要方式。口传需要有特殊的才能,包括理解力和记忆力,故不是人人可以为之。于是,在少数民族中,出现了一些具有特殊才能的艺人,这些艺人有着超出常人的超强记忆和演绎才能。如傣族的章哈歌手、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齐、蒙古族的好来宝艺人、哈萨克族的阿肯,等等。演唱和说唱是各少数民族民间艺人的主要表演形式。这些民间艺人或歌手将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艺术紧密结合在一起,使民间长诗成为一种通俗易懂、广泛流传的民间曲艺。也正是依靠他们世代承袭吟唱和表演才使各民族的民间长诗得以流传至今。我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都是以说唱的方式世代流传在人民中间。《格萨尔王传》是一部经过长期创作,篇幅宏大的藏族英雄史诗,这部英雄史诗以口耳相传的传播程式在藏族民间广为流传,由于其具有很强的历史性、普适性和艺术性而深入人心,进而逐渐艺术化,形成一种内容专一的口头性曲艺审美活动。《格萨尔王传》说唱,既是一个曲艺品种,同时还是一种艺术表演程式。在表演方式上采用藏语表演,牛角琴伴奏,演唱采用“一曲多变”,说唱穿插,有时还会配以图解。《格萨尔王传》的“说唱”表演方式不只是藏族所特有,蒙古族、柯尔克孜族、赫哲族、彝族等民族中也都存在着类似的表演,从而构成了长诗“说唱”类曲艺的一个模式性形式。
二、少数民族民间长诗中的个性特征
我国的民族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各民族在共生共荣的环境中又保持着一定的民族性及地域性。这些文化个性与自然环境、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审美意识等因素有着极为突出的关联。这些因素之间互有促进,彼此衍生,最终形成了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及民族性的审美特征。民间长诗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学艺术自然而然地成为承载民族文化记忆和民族精神内涵的载体。
(一)文化圈个性特征
“文化圈,是指具有相同文化因素的区域,区域内包含一个文化丛。丛内诸文化散布于这一区域,形成功能上互相关联的文化实体。”[2]中国在先秦时期形成四大文化圈:即由黄河中、下游文化区组成的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由东北、蒙古高原、西北三个文化区构建的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由青藏、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三个文化区组成的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由长江中、下游、华南、闽台等文化区组成的江南稻作文化圈。据《尚书·旅獒》载,西周时“四夷咸宾”,说明那时我国民族分布格局已定,四大文化圈已经形成。
就四大文化圈的生存环境优劣来分,自然环境最为优良的是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该文化圈范围为黄河中、下游,土地平旷肥沃,气候适宜,适合人类生存和作物生长,是中国主体民族汉民族的主要集居区域,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排在第二位的是江南稻作文化圈。该区域包括鄂、湘、苏、浙、赣、台、桂、粤、海南、港、澳等地区。[2]这里曾经是越人的天下,在文化圈的西南部有部分苗瑶语族民族,其地理特点是丘陵遍布,沟渠纵横,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适宜人类居住和水稻种植,以大米为主食,受汉文化影响严重,文化多元,是抒情叙事长诗的发达区。这两大区域自然环境优良,适宜人类居住和农耕生产,人们的生活相对较为舒适安逸。人们不用过多地为了生存与自然作斗争,也很少发生为了争夺物质资源而发生部落或民族战争。因此,该区域产生的民间长诗多以反映爱情、婚姻家庭及社会生活为内容,是叙事抒情长诗产生区。如侗族的《秦美娘》、壮族的《唱英台》、苗族的《仰阿莎》等。
排在第三位的是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该文化圈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及青海大部分区域。该区域地势海拔高,气候复杂,经济类型多样,民族众多,有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民族及孟高棉语族民族,是我国民族最多的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社会发展参差不齐,有地主制、奴隶制、农奴制,甚至有的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该区域的民间长诗类型多样,有史诗,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也有叙事抒情长诗,如彝族的《妈妈的女儿》、傈僳族的《逃婚调》等。
排在最后的为北方森林草原文化圈。该文化圈是四大文化圈中自然环境最为恶劣的文化圈,从东北三省、内蒙古、宁夏、甘肃绵延到新疆及青海的西北部。这里气候寒冷,自然环境多样,物质资源匮乏。森林、草原、沙漠、戈壁和沼泽等地理环境孕育了性格粗犷、彪悍、豪放的阿尔泰语系的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三个语族的民族。该文化圈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权最多的区域,在古代,各部落、各民族之间为了生存频发战争和冲突,为英雄史诗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形成了中国著名的英雄史诗带。在这条史诗带上产生了几百部英雄史诗,我国三大著名史诗中,其中两部就产生在此文化圈。这些英雄史诗结构宏伟,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塑造栩栩如生,语言优美动人,篇章繁富,具有突出的艺术魅力,是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维护部落安宁,推动社会发展的回声。如《江格尔》《格斯尔可汗》《智勇王子喜热图》等。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人类文化的形成与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很大的关联。不同的气候,不同的自然环境会造就不同的民族心理状态及不同的气质性格。不同的心理及性格又会产生不同的审美观念。从科学美学的视角来讲,人类审美活动的形成,或者说认知模块的构建是以事物的有利性为必要前提的。对于生活在不同文化圈的民族来说,他们所生活的文化圈是有利于他们的,他们从畏惧自然,崇拜自然到热爱自然是一个从生存到生活的拼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形成了固有的认知模式及审美知觉。这种来自社会现实的审美知觉带有很强的独特的地域性及民族性。
(二)创作思维模式的民族性特征
思维模式是人脑多种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的集合;是被客观世界已经模式化的思维定势。思维模式受制于思维主体所处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恩格斯说:“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的运动形式的反映。”[3]依据此理论,民间长诗的创作思维模式无论是思维的表层结构还是思维的深层结构,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的思维模式特征。首先,从思维模式的表层结构解析,构成各少数民族民间长诗的元素和母题的多是来自高山、河谷、森林、草原等的民族生活。但是,表现在长诗中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情结,是一个民族久远的历史经验和情怀铸就在人格和生命之中的那种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可以决定诗人一生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民间长诗是各少数民族在短歌、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以原始人自我情感、欲求为中心的心理过程;是在拟人化的比附中把握客观世界。“他的无意识心理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渴望,要把所有外界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的心理事件。”[4]神话思维的运演不是按照理性思维的分类分析,而是“按照主观印象、感觉把握客体”[4],是被卡西尔称之为‘最强烈最深刻的推动力之一’的神秘情感及相关信仰。”[5]如《江格尔》中的江格尔形象,他从小就具有超人的头脑和超强的武艺,长大后智慧过人,有正义感,胸怀广阔,知人善用,能呼风唤雨,能挟雷带电。这种尊崇义、勇、力的审美心理凸显出蒙古族民族传统神话中对英雄审美的思维定势。
影响思维方式的另一个方面是语言。思维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语言也可以窥知思维方式的特征。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符号性特征,它包含着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精神,凝聚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曾论断:“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6]思维与语言相互依存,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维是语言的内容。民间长诗是借助民族语言来表达的,表达者的思维轨迹受于语言的浇铸,语言能够构建文化精神,由此,在思维方式上会凸显出语言的民族性特征。
(三)个性化的民族审美意识
审美意识是一个由感觉、想象、表象、意志、情感等多种心理要素组成的复合体。普列汉诺夫曾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他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7]虽然在这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艺术心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是影响艺术心理的全部因素。艺术心理还受到个人心理发展状况的影响。影响个人心理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因素,即遗传与环境。二者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作用的。人是环境的产物,生存环境在人的审美心理行程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地貌、气候条件、地理位置等左右着人的发展。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对希腊早期文明研究所产生的观点,他认为常年生活在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的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环境中的民族,一定比别的民族发展得更幸福。那里没有严寒和酷暑,人们能够感受到“温和的自然界怎样使人的精神变得活泼、平衡、把机灵敏捷的头脑引导到思想与行动的路上。”[8]由此可见,由于特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又造就了特定的文化类型;特定的文化类型继而又塑造出特定的审美心理。
审美意识还要受到经济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哲学观和伦理道德观等影响,这些都给审美意识打上了民族特有的印迹。从经济生活方式上看,因各民族有渔猎、稻作、游牧等不同的生产方式,在审美意识上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如北方游牧经济生活方式的审美意识是根植于游牧生活的大地,带着草原的芬芳,蕴含着古老而豪迈的民族英雄气概;而江南稻作文化圈所表达的是在崇山峻岭中给人以希望。
三、少数民族民间长诗呈现“异同”的原因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和现象的产生与发展都处在一定的因果联系之中。少数民族民间长诗作为各民族思维活动的一种创作形式也同样有其因果联系。
(一)同:缘于相同的社会形态现实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包含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以及分配方式。所有制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精神生活。因此,少数民族民间长诗作为各民族人们的头脑对社会现实生活审美反映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尽管在形式上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个性,但是,在相同的生产方式下,创作主题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在奴隶制社会时期的英雄史诗中塑造了恶人、魔王、恶魔、好色的可汗等众多面目狰狞的反面形象。如《江格尔》中的“蟒古斯”、《格斯尔可汗》中“阿而嘎聪”、满族《尼山萨满传》中的阎王、国舅等,这些形象显然是现实社会中的穷凶极恶的奴隶主形象。他们剥削压榨,为富不仁,因此,对等级观念和为富不仁的谴责成为了史诗创作的动因。
又如农奴制广泛存在于我国西南地区,其基本形态是农奴处于人身依附地位,农奴以奴役性条件从农奴主处领取土地,世代耕种,被束缚在土地上。农奴主强迫农奴服劳役、交纳实物或货币等不同形态的地租,农奴没有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农奴主对其拥有任何形式的处置权。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当时的精神生活,也决定了民间长诗的内容、形式及风格。民间长诗作为人们对现实生活审美反映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反映农奴制的民间长诗,不管是哪个民族的,都有着激烈的抨击等级制度的不公,抨击农奴主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以及对没有人身自由的苦闷心情的共同点。如傈僳族的《重逢调》,这是一首揭露农奴制时期傈僳族不幸婚姻生活的长诗。长诗描述了一对青年恋人因男主人公凑不够聘礼,被迫背井离乡做苦工,不幸被奴隶主抓去做了奴隶,过着与牲畜一样的生活。他承受了10年的折磨与煎熬后逃了出去,带着用血汗换来的聘礼钱回到家乡去提亲,但是,心爱的姑娘已经被父母逼迫嫁给了别人,过着“白天饿着肚子淌汗水,夜晚忍着寒冷流泪水”的悲剧生活。又如藏族的《在不幸的擦瓦绒》。壮族的《唱英台》、裕固族的《黄黛琛》等。这些长诗,尽管存在于东南西北不同的区域,但因其都产生于同一社会形态的农奴制时期,所以,各区域的叙事抒情长诗在题材、主题等方面都趋于相同,只是在具体环境和情节上有所变化,以彰显民族特性。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即便各少数民族民间长诗出现的时间前后相差较远,但是只要是在同一社会形态下,它们在题材、主题及风格上都具有很大的共性特征。由此可见,相同的社会形态是形成各少数民族民间长诗存在共性的主要原因。
(二)异:始于文化的不可通约性
这里所要阐释的“不可通约性”是相对的不可通约性,而不是西方所强调的绝对“不可通约性”,更确切地说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差异性。
“不可通约性”概念是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SamuelKuh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他说:“在常态性的科学所经历的各个时期中,前后相继的理论和范式是不可通约的。”[9]库恩的“不可通约性”理论告诉我们相异的范式、语境、词汇、叙事以及历史讲述等差异在科学领域和伦理学领域都是存在的。不可通约性客观存在于科学本身之中,即内在科学的语言系统。它强调了科学发展中的质变,这种质变表现在心理学、文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诸多方面,即科学共同体的世界观变化。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不可通约性”既是异质差异性,也是世界观与世界观之间的差异。将“不可通约性”延伸到民族领域,就会发现,民族文化及文明有着明显的异质性,即文化的“不可通约性”。就民族语言来讲,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这种不同仅是词汇使用或词汇字面不同,就可使世界观出现差异。由于语言与语言之间,世界观与世界观之间都存在不可通约性,进而就形成一种文化观。语言作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符号性差异,其受到语境的制约,语境又是由生活世界凝聚而成,因而,语言表达是受生活世界所左右。民间长诗是从少数民族的生活世界中产生,其蕴含着民族独有的世界观、文化观,有自己的语言、体裁、风格和民族心态等。语言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不仅具有自己特有的音律特点,同时还构成了民族认识世界万物所特有的信息系统,是体现本民族生活、文化和信息的重要载体。正因这些独有的世界观与文化观,无论是从表象还是深层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从而彰显出本民族文学的话语权力,即不可通约性。正是这种文学的不可通约性,使得其拥有了民族气质,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美感。
文化传统是一种贯穿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类文化的核心精神[10]。文化传统有着一定的稳固性和延续性,以及历史性和现实性,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标志。民间长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形成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并继承了原始神话、传说、短歌等原始文学的核心精神。促使产生这种民族核心精神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文化类型。文学来源于现实生产、生活中不同生活方式所展现的精神美感。四大文化圈经济方式各有不同。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的经济生产方式主要是旱地农业,辅以家庭饲养。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的经济生产方式表现为东北文化区以渔猎采集;内蒙古草原文化区和西北文化区以畜牧业为主要生计。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的经济生产方式包含有以绿洲耕牧为主要经济类型的四川盆地文化区;以山地耕牧、山地耕猎及山林刀耕火种等为主要经济类型的云贵高原文化区和青藏高原文化区。南方稻作文化圈则以种植水稻为主,副业多与鱼桑有关。四大文化圈由于自然环境和生存方式的差异,使得各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心理性格等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地理单元性的文化特征或文化素质。这种地理单元性的文化特征或文化素质既是该地域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也是民间长诗创作的基础。
二是宗教信仰。宗教是一个多层次、多体系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一定历史阶段的民众的心声反映和观念体现。民间长诗是一门独特的语言艺术,是人民的生活、思想与感情的自发表露。二者共存于多样化的文化体系中,并相互融合渗透。从各少数民族民间长诗的产生可以看出,宗教是民间长诗创作的源泉之一。宗教对民间长诗影响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次是原始宗教,第二层次是原生型民间宗教,第三层次是创生型世界大教。这些宗教对民间长诗的形成具有普遍的影响,尤其是原始宗教在少数民族民间长诗中的体现更为突出,并广泛影响成为民众自然发出的内心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