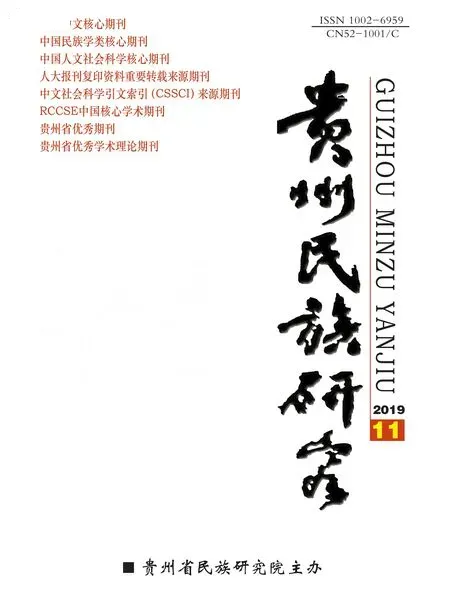清代贵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及动因
2019-02-09杨军
杨 军
(贵州民族大学 法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一、清代贵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的变迁
清代贵州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大体可分为基于中央王朝政治统治的行政型组织与基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的传统型基层社会组织,二者经历了一个由并存到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
(一)行政型基层社会组织在贵州民族地区的推行
1.里甲制的推行
明初,由于社会经济得到改善,人口和土地得到增加,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拥有土地且可以提供赋税的自耕农。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布政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里甲制。但在实行土流并治的贵州地区,广大土司区域内仍由土司对其属民进行直接管理、控制,里甲制多适用于流官管辖地区。
清代在贵州民族地区亦大力推行“里甲”制,其主要职能仍是以催征赋役为主要职能。如乾隆朝广顺州,“汉庄、苗寨编为十里、十枝……。(苗汉庄)共计一百一十有奇。”荔波县“辖十六里……征地丁银一千四百一十四两二钱二分,常平谷一万五千三百二十七石八斗八升五合二勺[1](P51、108)。可见,清代“里甲”这种赋役组织在贵州民族地区已经较为常见。
2.保甲制的深入
中国历史上国家政权在基层社会制度设置上是把役、政分离,而国家在保障其税赋征缴的同时,对于维护社会治安进而强化对当地的控制等繁琐事项亦无力完全独自承担。因此,在里甲制之外,为维护基层社会生活秩序,以“安靖地方”为要务的保甲制的地位便凸显出来。
清朝建立后,面对战后急需快速重建的社会秩序,顺治元年(1644年),首先在北方地区实行保甲制,同时康熙末年的“摊丁入亩”,也极大地削弱了里甲制存在的经济基础,保甲制度得以受到清王朝的重视。尤其在清代贵州民族地区,伴随着清廷对当地统治的逐步深入,乃至于其后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大力推行,都促使清王朝愈加重视在贵州民族地区统治秩序的稳定,使得保甲制得以在贵州民族地区大规模推行,如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向清廷奏疏:“至于清盗之源,莫善保甲。保甲之法,率以十户。云、贵土苗庞杂,户多畸零,保甲不行,多主此议。不知除生苗外,无论民夷,自三户以下皆可编甲,不及三户者,编附近甲,无许零住。逐村经理,逐户稽查,责在乡、保、甲长。一遇有事,罚先及之。十家被盗,一村牵连。保长甲长不能觉察,左邻右舍不能救护,各皆酌罚,无所逃罪。”[2]可见,相较于里甲制而言,清代在贵州民族地区推行的保甲制,由于其侧重于维护社会治安职能,更加利于稳定“改土归流”后贵州民族地区较为复杂的社会形势。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保甲制推行的范围主要是“熟苗熟僮”“绅衿之家[3],至于“生苗”之地,由于清廷统治尚未深入,仍保留其传统型基层社会组织。
“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又将保甲制推行至“新辟苗疆”,如雍正四年(1726年)夏,广顺州长寨“建参将营,分扼险要,易服剃发,立保甲,稽田户”[4](P284)。其后,就连以往清廷统治较为薄弱的“九股地方,请将苗疆界址清查,于旧有头目内择其良善老成者,按寨大小酌定乡约、保长、甲长令其管约稽查”[2](P248-249)。至道光朝,不仅位于贵阳府辖下的修文县,“通计四里共五百四十四寨,俱一例编入保甲”[1](P39)。黔南独山州亦“汉苗户口于道光六年(1826年)查清,苗寨汉户已编入保甲,共计汉人三千九百零九户,苗人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五户。”[1](P101)
(二)传统型基层社会组织的并存
历史上贵州各少数民族,由于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形成了不同形式的传统型基层社会组织,如水西彝族的则溪、侗族的侗款、瑶族的石牌、苗族的议榔等,大体可以分为血缘型与地缘型两种。尽管自元代始,中央王朝力图将内地行政型基层社会组织引入贵州民族地区,但是一方面由于国家政权对于广大民族地区力有不逮;另一方面,土司制度的实行,也使得国家政权的力量难以直接影响各民族的社会内部。因此,在相当的时期仍保留传统型基层社会组织,如乾隆十五年(1750年),贵州巡抚爱必达奏称:“查黔省旧疆熟苗与汉人比屋杂居,甚为恭顺,有土司、土舍、土目及苗乡约寨头管束;新疆生苗,与屯军错处,亦额设土弁、通事、寨长、百户分管,……俱交承办之土司、土舍及土目、土弁等,勒限拿缴”[5](P211)。从中可见,清代贵州民族地区不论是较早开发的“熟苗”地区,还是较晚开发的“生苗”地区,清廷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一些各民族传统基层组织形式,只是加以改造,赋予其维护当地社会治安的功能,成为国家认可的基层社会组织。
1.血缘型传统基层社会组织
清代贵州民族地区的血缘型传统基层社会组织,主要以水西彝族的则溪制和瑶族的石牌制为代表。
则溪制主要存在于贵州水西彝族中,则溪是对彝语的音译,原义为仓库。则溪制根源于彝族的家支,家支是彝族科会的一种血缘组织,源于原始社会的父系氏族,由同一男姓祖先所繁衍的子孙组成[6]。在家支的基础上又形成若干具有血缘关系的宗亲。为巩固水西政权的统治地位,安氏土司按照宗法关系从上至下分封血缘亲属,分割土地。其十二宗亲,每一宗亲占有一片土地,形成一个统治区域,加上安氏最高统治者苴穆所占本部土地,一共形成了十三个区域,这便是水西的十三则溪。《大定县志》载:“则溪之下,有四十八目。又其下,有百二十骂衣,千二百夜所。盖犹中国之乡里甲也。”[7](P123)在则溪制度下家族内的人们要缴纳钱粮,遇有战事还须服从调遣,共同抵御外敌。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水西土司安胜祖病故停袭,水西改土归流,但“四十八支司孙头目如故”,表明水西地区彝族社会的基层社会组织仍然存在。
在瑶族地区,其基层社会组织为以血缘为基础的石牌制。石牌由石牌组织和石牌条款组成,几个村寨联合起来,建立公认的石牌组织,称为“立石牌”。召开石牌会议,表决制定条款,写于石牌之上并埋进土中,称为“埋石牌”。石牌条款是集体协商产生的,对石牌内所有人员皆有强制力,违反条款的称为“犯石牌”,将受到相应惩罚。各石牌有自己的石牌头人,由日常生活中德高望重、办事妥当的自然领袖担当,他们没有明确的职责,处理纠纷的前提是当事人的请求,所以一旦失去威望和民众的信任,他们也就被自然免除。
2.地缘型传统基层社会组织
议榔是苗族历史上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基层社会组织,其规模大小不等,有一个村寨为一个议榔,也有几个或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村寨组成的议榔,议榔是以村寨或地域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形式,超越了血缘关系和宗支界限。清雍正朝镇远知府方显在招抚诸苗中曾“乃令各寨头人订期会集,宰款合榔。宰款合榔者,苗俗也,又曰合款,亦曰诂话。其会盟处曰款场,首事人曰头人,头人中之头人曰榔头。悔盟者有罚,曰赔榔。皆苗语也”[8](P146)。议榔有大小款首、榔头,管行政事务;有称作“硬手”和“老虎汉” (虎士)的军事首领;有“巫师”(即祭司)作宗教领袖;有“行头”“理老”主持司法,排解纠纷。榔、款首和军事领袖等一般由选举产生,“理老”“行头”一般是自然形成,条件是为人公正,能言善辩,熟习榔规款约。
款作为贵州侗族地区的基层社会组织,分为小款、大款。小款和大款以涵盖村寨的多少进行区分,但它们相互独立,不存在隶属关系,各款召开鼓楼会议,制定款约、选举款首、处理款内外各项事务。款首一般由德高望重,熟知习惯法的老人经推选产生。但与议榔制下的长老不同,款首在惩治违反款约的款众时享有的自由裁量权更小,不能擅自做主,需召集全款区的人,向大家讲明案件事实和社会危害,依据款约拟定的处理方法还需通过款民一致同意方可强制执行。
(三)清代国家政权对传统型基层社会组织的重构
清代为加强对贵州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控制,将内地行政型社会组织在贵州民族地区逐步引入,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清廷以末代水西宣慰使安胜祖无嗣为由改土归流,水西之地归大定、平远、黔西三府流官管辖,在当地设立里甲制。如大定府所属木胯、火著、架勒、化各四则溪编为八里;黔西府所属则窝、以著、雄所三则溪编为八里;平远府所属的独、朵泥、要架、陇胯四则溪编为九里;威宁府所属编为十里,每里各有十甲[9](P214)。然而,在长期土司统治影响下,原先的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在民间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里甲首多由原先的土目担任。如平定里有镇西、阿市、杨柳湾、大比肇、斯栗堡、大屯、家戛、湾溪八大土目,里甲中的甲首仍由土目等各头目继续充任,具体管理各土目区的赋役职能。相对于“保甲”制而言,“里甲”主要负责催征赋役,并不直接干预各民族内部事务,更容易得到各民族的接受,在推行中较为顺利,当然也出现了一些为适应当地民族传统的变化,如归化通判,“所属地方,曰羊场枝、板当枝、驼鲁枝、鲁可枝、黑则枝、薛家枝、生苗枝、红播技、干家枝、猪场枝、洛河枝,共十二枝,……现在成熟田一万六千一百八十—亩有奇,额征正米一千三百一十五石有奇,征银九百二十四两有奇”[1]。这里与前文广顺州的记载较为类似,出现了“枝”这种赋役组织形式,应该是“里甲”制在少数民族地区施行后,对当地传统基层社会组织改造后形成的一种变种。
相较于里甲制,偏重于社会治安职能的保甲制更加受到清王朝的青睐,除顺治元年(1644年)顺治帝便颁行编制户口保甲之法,康熙朝清廷又重申保甲之法,雍正四年(1726年),再次严申保甲之法,规定:“查定例,保甲编排,不许容留面生可疑之人,熟苗熟僮一体编排保甲。”改土归流后,为了更加深入地控制贵州民族地区,保甲制度得以在以往的“生苗”地区大规模推行。但是,由于贵州民族地区复杂的历史、民族传统,清廷对于内地行政型基层社会组织的推行不得不做出某些妥协或变通,以求适应当地实际情况。具体而言,主要有两种形式:
其一,保甲制引入当地社会,取代原有传统型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但保甲长仍由当地民族原有首领充任。此种情形多适用于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受内地影响较深的“熟苗”地区。鄂尔泰在《议复苗疆四款》中向朝廷建议:“若尽收熟苗之器械,或转受生苗之摧残,则外侮之来,反无以抵御,……凡白昼出门者,概不许携带;其有万不得已事,必欲夜行携带兵器者,先通知乡保头人,告以欲往某处,携带何器,何时回家,乡约给以图书号票。所过共几塘汛,则给以几号票,每一塘汛盘验放行,收票登薄。”[2](P199)可见,保甲制在大力主张改土归流的鄂尔泰看来,具有“安靖地方”的治安职能,而将其引入苗疆“熟苗”地区。担任保甲长的一般为“乡保头人”,即当地少数民族旧有首领。一方面因为这些人“熟稔苗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助他们在当地群众中的影响力,以减少保甲制推行中的阻力。
其二,将保甲制植入贵州民族地区传统型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中,并加以改造,以实现国家对当地基层社会的控制。这种方式多适用于那些较为偏僻受内地影响较少的“生苗”地区。在雍正朝改土归流后,对于如何控制新辟苗疆地区,有人主张在“生苗”地区推行保甲制,彻底取代各民族原先传统型社会组织。如雍正五年(1727年),四川副将张瑛主张:“宜令剃发易服,尽献兵器,分设里长甲首,而迁土目于内地。”命鄂尔泰议之。鄂尔泰言:“冠发必其愿遵,若强之改薙,将悍苗反与齐民无别。其土目即可改为里长甲长,若必尽徙,恐两不相习,不若以夷治夷。”为了减少当地少数民族的抵触,清廷最终采纳了鄂尔泰的建议,在官府的主导下基本保留当地民族传统型社会组织,加以改造。如镇远知府方显在台拱农寨苗,“令诸苗合榔,公举榔头管理寨事”,便取得较好的效果,“苗罗拜泣,遂相率归寨。显宿台拱寨三日,谕以缚献施秉案犯,唯唯听命”[8](P156)。至乾隆朝后,贵州民族地区纷纷出现反清起义,迫使清王朝更加重视“以夷制夷”的治措,如嘉庆元年(1796年)四川总督和琳提出“苗疆百户寨长名目应酌量更定以专责成也”,具体是“查川黔楚三省,……从前均系土司,嗣后各土司等陆续呈请归流,始改设州县营分统,归文武管辖,苗寨内止设百户寨长,如内地之里正保甲而已。但该百户等人微权轻,苗众既不甚听约束,且向例汉人亦准承充”。基于上述原因,建议加强基层官员权力,“嗣后凡有苗民格斗窃盗等事,均著落此种土官缉拿办理”[10](P589-590)。从中可以看出,由各民族原先的基层社会组织首领仍担任经过改造后的百户、寨长,并被官府赋予了保甲组织的基层社会治安管理职能。
二、清代贵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的动因
(一)政治上由间接统治转向直接统治
清王朝统治贵州后,对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继续沿用元明以来的土司制度,实行“以夷制夷”的间接统治,随着国家权力的不断深入,土司制的种种弊端逐步凸显,如土司之间,因争抢土地或者世代积累的纠纷,频繁地发生掠杀战争,成为地方极不稳定的因素。而世享其民的土司对土民残酷剥削、横征暴敛,无视法律,对土民生杀任性,逼迫“土民不甘受土司毒虐,愿呈改土籍为汉民”[11]。因此,清朝统治者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间接统治,并非其本意,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权宜之计,一旦时机成熟,自然要将间接统治转变为流官制下的直接统治。
雍正朝,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改土归流的议疏得到了清廷的采纳,于是拉开了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序幕。清廷改土归流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削弱土司的势力;另一方面,是将尚未纳入国家行政建置的民族地区设官治理,并通过调整疆界“归并权势”,扩大流官的统治范围,实行“编户齐民,按亩升科”,从而实现国家政权对贵州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究其实质,改土归流并非简单地剥夺土司的官职,而是争夺对其治下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直接统治权。这一点清代较明代尤为明显,清雍正五年(1727年),鄂尔泰奏请清帝:“黔省边界生苗,不纳粮赋,不受管辖,随其自便,无所不为,由来久。……但户口必须编造,钱粮自应从轻。且夷民半无姓氏,名字雷同,应行更定姓名,汇册报部,酌为额赋,按年输租”。雍正帝诏曰:“自此,土司所属之夷民即我内地之编氓;土司所辖之头目,即我内地之黎献,民胞物与,一视同仁,所当加意抚绥安辑,使人人得所,共登衽席,而后可副朕怀也。”[5](P86、87)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朝改土归流,不仅是废除原有土司,而且在其地建立起传统官僚行政体制下的直接统治。如清朝在平定古州后,先后设置八寨、丹江、清江、古州、都江和台拱六厅,除以兵分扼险要外,善后事宜的要务便是在当地立保甲、稽田户。因此,改土归流不仅是清廷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统治形式上的变化,也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的内地化趋势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并非是“一刀切”,如鄂尔泰在《正疆界定流土疏》中认为,“改土归流原属正务。但有应改者,有不应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必不可不改者;有必应改而不得不缓改者;有可不改而不得已竟改者,审时度势,顺情得理,庶先无成心,而有济公事。”[12]仍保留一些皈服朝廷守土相安,并无过犯的小土司,但即便是在改土归流的少数民族地区,流官一般也仅设置于县一级,而在广大基层地区,仍保留了相当的传统型基层社会组织,这也为国家行政型基层社会组织的变通提供了迫切的驱动力。
(二)内地移民涌入与林业经济的繁荣
1.内地移民涌入
作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口而言,清朝时的贵州呈现较大变化。清初由于常期的战乱使得贵州人口较明末大为减少,而中原内地则出现急剧增长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之间的矛盾,雍正皇帝提出:“嗣后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鼓励人民自主开垦荒地,使得大量内地汉民进入贵州,也改善了贵州“不患无地,而患无人”的局面。至道光朝,外来移民在贵州民族地区已占据相当的数量,如黎平府,“其间客民之住居苗寨者,又较别地为多,……计府辖地典买苗产客民四百九十四户,贸易、手艺营生未典买苗产客民一千七百十六户,蓬户二百四十二户。府县两属屯所客民附居苗寨及未附居苗寨者共二千四百五十二户”[1](P322-323)。
大量外来移民,尤其是农业移民的涌入,一方面促进了贵州民族地区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客观上也造成了“客苗争地”,激化了社会矛盾。如乾隆六十年(1795年),苗民石柳邓反清起义,乾隆帝认为缘起于“今因日久懈弛,往来无禁,地方官吏暨该处土著及客民等,见弱易欺,恣行鱼肉,以致苗民不堪其虐,劫杀滋事,迨至酿成事端,又复张皇禀报”[5]。为控制外来移民大量涌入后的贵州民族地区,清王朝强化当地的保甲制,将外来移民也一并编入。如道光初年,由于当地“红”“黑”匪徒横行,贵州巡抚嵩溥建议朝廷,“民人应责成乡约保长,苗人即责成土弁寨头,实力稽查”[2](P447)。此后,清廷反复强调在客、苗混居的地区严查保甲,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谕“贵州附居苗寨客民,既经编入保甲,其分户另居者,自应一律编查。著该抚饬令各地方官,督率村寨保长人等,将客民旧户,迁徙若干,现存若干,其旧户内有子孙分户另居若干,逐一查明造报。毋得假手胥吏,致滋扰累。并令该管道府、直隶州,就近核实确查,不得日久生懈,致成具文”[5](P505)。
2.林业经济的繁荣
贵州地貌复杂,气候多样,雨量充沛,林业资源向来丰富。早在明代贵州的林业经济就得到发展,如明正德九年(1514年),为修缮乾清、坤宁二宫,便有从贵州采伐大木的记载。其后,相关史料缕缕不绝,至清代贵州仍是朝廷征收木材的主要来源地,如清代《皇木案稿》载:“桅断二木,近地难觅,须上沅州、靖州及黔省苗境内采取。”[13](P11)由于贵州林木广泛行销内地,自然带动了当地林木的种植与贸易。
乾隆五年(1740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向朝廷建议,鼓励贵州各地民人栽植林木,“种多者量加鼓励。”在官府的大力推动下,贵州民族地区的林木种植业得到快速发展,内地商民来此经营木材交易者趋之若鹜,如黎平府,“山多戴土,树宜杉。……商贾络绎于道,编巨筏放之大江,运于江淮间者产于此也”[1](P177)。繁荣的林业经济也改变着贵州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生活秩序,如盗伐林木、林木纠纷、因洪水暴涨,上游漂没的林木,下游群众捞获后的工价银纠纷等频发不穷,因此,也成为当地基层社会组织亟待解决的问题,如道光锦屏县王寨捞获木植工价碑规定:“如违,许该保长指名禀究。该保长若敢通同徇庇,或经访闻或被告发,立即签提,一并倍处”。[14](P31)
清代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在人口结构、分布以及林业等经济贸易的发展,不仅显著地改变了当地原有的社会及经济结构,成为内地文化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供给途径,也为清王朝对当地基层社会组织的重构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三)儒学与科举的兴盛
清代对贵州民族地区推行的“王化”过程中,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清王朝巩固其在贵州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后,开始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及科举考试,对于内地文化、制度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促进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心理上对国家的认同。
1.儒学、义学教育的发展
清代初期,清廷就对贵州民族地区的儒学教育非常重视。即在官府所举办的教育机构讲授儒家经义,各地分设府学、州学、县学等。
早在康熙三年(1664年),水西宣慰司改土归流后,新设黔西、平远、乌撒三府学。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贵州巡抚王燕奏请增设“将附学之清浪,设教授一员;附学之开州、广顺,未设学之永宁、麻哈、独山各学正一员;附学之普安、余庆、安化三县,未设学之普定、平越、都匀、镇远、铜仁、龙泉、永从七县,各设训导一员;照小学例,取文武附生各八名,廪、贡循例遵行”[2](P148-149)。此后,雍正年间增设永丰州学和荔波、锦屏二县学。乾隆年间增设仁怀厅学,嘉庆年间增设松桃厅学和兴义县学,道光年间增设郎岱、古州和八寨三厅学。至清末,贵州全省共有官学69所,其中,府学12所,直隶厅学3所,直隶州学l所,厅学6所,州学13所,县学34所。
在广设儒学的同时,清王朝还非常重视对贵州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土司子弟启蒙教育的义学。早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云贵总督赵廷臣建议:“今后土官应袭,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者,听补廪科贡,与汉民一体仕近,使明知礼义之为利”[2](P61)。通过这些措施,清廷不仅强化了对贵州少数民族土司政治上的控制,也加强了土司对朝廷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子弟的教育,清朝也给予特殊优惠的规定,雍正八年(1730年),贵州巡抚张广泗建议,“似应先就已安营汛之处,分别苗户多寡,各为设立义学,然后随地分设,庶资实效”。进而达到“俟数年之间有稍识文义者,……以风苗众,庶陶以文教,消其悍顽,于苗疆治理,不无裨补”[2](P229)。为督促少数民族子弟勤于读书,“令各该管官不时稽查,随予嘉赏,并将其父兄一体奖赉,以示鼓励”。
2.科举制度的兴盛
清代贵州科举考试始于顺治朝,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规定“贵州各属大学取进苗生五名、中学三名、小学二名,均附各学肄业;廪额:大学二名、中小学一名”。此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帝议准“其族属苗民俊秀子弟有愿学者,令入义学,府、州、县训导督教。文理通明者,由教官汇送学臣,一体考试应举,不许汉人阻抑”[2](P158)。雍正三年(1725年),清廷再次明确:“黔省苗人子弟情愿读书者,准其送入义学,一体训诲。每遇岁科两试,於该学定额外,取进一名,以示鼓励”[5](P76)。为鼓励“苗生”积极参与科举考试,清廷还采取了“苗疆加额进取之法”,为“苗生”单设进学名额,以致当时还出现了“汉生”冒充“苗生”进学、参加科举考试的现象。清代贵州民族地区科举盛行,一方面使得少数民族精英得以进入国家官僚队伍中,“入中原礼义之乡,睹文物之盛,观感兴起,必有大变其犷悍之习者”[2](P158);另一方面,科举制度本身又促进了贵州民族地区的“王化”进程。
清代十分重视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不论是针对培养贵州少数民族上层精英的官方儒学还是提高少数民族群体启蒙教育的义学教育,清王朝都能做到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在进学、考试、生活津贴等方面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这些举措一方面带动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效地强化了各少数民族在文化心理上的认同感。
三、结语
清朝对于贵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治理,相较于元明时期,在积极地将内地行政型基层社会组织形式引入当地的同时,并对传统型基层社会组织加以重构,以其对贵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广度与深度而言,可谓空前。这一时期,清王朝在贵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的设置上具有两个特点。
(一)较为重视以维护地方治安为主要职能的保甲制
中国古代传统上基层社会组织大体上可以分为催征赋役与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职能的两类基层社会组织,如清代的里甲制与保甲制。清代贵州民族地区特殊的民族、历史传统相交织,使得以维护地方治安,直接巩固清王朝政治统治权力的保甲制度更为得到清王朝的重视。早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云贵总督赵廷臣就建议:“其作硬衢路,宜仿保甲之规;其仇杀抄劫,宜立雕剿之法。又赏罚之条必信,馈送之陋必革”。[2](P61)尽管在清代前期,保甲制主要设置于“熟苗”、“熟僮”地区,但在雍正朝改土归流后,立即将保甲制推行于那些原本“王化”之外的地区。针对清代贵州民族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如清中期前明朝反清势力及各民族反清起义、清中期后的“民苗”纠纷,清王朝都是积极主动地以保甲制作为维护其封建统治的主要治措。
(二)基层社会组织设置上的灵活性
清代贵州民族地区各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传统社会组织和传统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清王朝在推行和重构各地基层社会组织时,往往会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变通。如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对于原先“王化”之外的苗疆,清朝一方面将侧重于地方治安职能的保甲制在当地广泛推行;另一方面,清廷也意识到,“若遽欲设立土司头目,以统率其众,不但苗众不肯服从,且恐滋事端”,而外来流官往往也是鞭长莫及,因此将各民族固有的传统型基层社会组织改造为保甲组织,并由其首领担任甲首,“查各苗寨内,向有所称头人者,系各本寨中稍明白、能言语、强有力者,众哲即呼为头人。应请各本寨择其良善守法者,仍其苗俗,听于本寨内将姓名公举报官。……是亦同内地设立乡约、保长之类[15](P241)。这些担任地方保甲长的原先各民族基层社会组织首领,一面由于其旧有的自然领袖权威,又凭借官府的威势,从而将两种不同文化特性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完美地结合为一体,进而有效地维护了贵州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生活秩序。
综上所述,由于清王朝意识到贵州民族地区复杂的民族、历史文化差异,在将内地行政型基层社会组织引入当地时,从中央到地方官府都能积极地做出一些本土化的变通,而当地各少数民族也在社会实践生活中主动或被动地将本民族传统基层社会组织与之相融合,从而重构出较为适合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活实践的基层社会组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