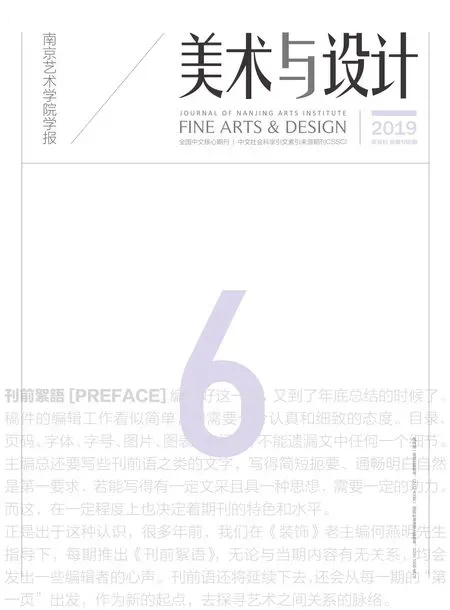“遍友历代,归宿晋唐”:祝允明仿书与明中期书学仿古模式的创立①
2019-01-10蒋志琴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24
蒋志琴(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24)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江苏长洲(今苏州)人。著有《怀星堂集》《祝子罪知录》等三十余种。他是明中期倡导复兴晋唐二王书学传统的代表人物,上承宋代米芾、元代赵孟頫以来的求古意风尚,下开董其昌、王铎以临导创之风,成为明代书学仿古模式发展过程中的开创性人物。
祝允明的书法被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誉为国朝第一。对于祝允明的书学,学界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②分别见薛龙春《乱而能整——祝允明书法摭论》,《中国书画》,2009年第5期;舒鸣《从艺术接受学视角看祝允明“兼善多体”现象》,《书法研究》,2016年第9期;黄惇《神会意得——从祝允明、文征明到董其昌的仿书研究》,《中国书法》,2015年第11期。,如指出祝允明“兼善多体”、其草书“乱而能整”等艺术特色,黄惇教授在《神会意得——从祝允明、文征明到董其昌的仿书研究》中,将祝允明、文征明和董其昌视为明代推崇古法以求雅,将临摹与创作紧密结合的代表性书家,认为三者的仿书创作直接推动了当时书坛的发展。受此启发,本文以祝允明为例,尝试对明中期书学仿古模式的成因、方法等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逼真”古人与反对奴书:祝允明仿书的评价标准
“逼真”古人,是以祝允明为首的一些吴门文人、书画家的文艺评价标准。王世贞以“似临模帖”[1]351评价李攀龙之诗时,也是就此标准而言的。黄姬水评价老师祝允明《草书李白诗卷》时说:
“逼真二王,深得书家三昧。”[2]46
哲学上,理解“真”有三个维度。其中,符合论之真,强调思维与事物之间的一致性。从《草书李白诗卷》看,黄姬水显然是就二王书风与祝允明仿作之间的一致性而言的。他所谓的“逼真二王”,是指祝允明书写此作时,通过历史性想象,最大程度还原了祝氏心目中二王传帖的字形、笔法、结体等书写特征。跋中“逼真二王”与“深得书家三昧”的因果关系,则揭示了以黄姬水为首的书家视“逼真”古人为书学评价标准的事实。当然,祝允明采用的是另外的说法,如称自己所临钟、王之作“仅存优孟衣冠”,[3]129-130称其《临米、赵千字文、清静经册》“亦颇得形似”,[2]52都有欲绝肖(逼真)的意思在内。也就是说,逼真临仿以得原帖笔法,是祝允明面对自宋以来晋唐笔法缺失问题的解决方案。他假设了如果临仿逼真,必然获得以笔法为主的原帖的正确书写方法。
祝允明以“逼真”古人为仿书的主要评价标准,在当时具有开创性意义。我们可以将明初书家胡正的仿作《行楷书临帖卷》(临王羲之《十七帖》、王献之《秋月帖》、赵孟頫书札、怀素草书帖等)与祝允明的同类仿作相比可以发现:以胡正为首的明初书家在临习古代书帖时,多以意临之,并不刻意追求仿作与原帖之间的高度相似性,书家自身的风格面貌贯穿临作始终,这也导致了胡正临仿的二王、赵孟頫等作品之间的差异很小。换句话说,以胡正为首的书家在临仿过程中,犹带本家笔法,时时流露自己的书写习惯,并未表现出刻意求真、存真的临帖态度,师法原帖之意、不类形模才是他们主要的追求目标。因此,逼真临仿标准彰显了以祝允明为首的文人对书坛时风的反叛和对新风的引领。
祝允明时代,沈周、文征明等吴门文人、书画家常以乱真标准评价文艺作品。如:
“(沈周)自其少时作画,已脱去家习,上师古人。有所模临,辄乱真迹。”[4]287
“老夫(沈周)惯与松传神,夹山倚涧将逼真。”[5]
跋文中“辄乱真迹”,指出了临作与原作之间的高度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主要体现在物象的造型、色彩、运笔以及造境方法等方面。综观中国古代绘画史,沈周是一位较早在画作跋文中挑明仿某家(如董源、巨然)笔意或笔法的画家。此外,他一生专仿黄庭坚,以能高度再现黄氏书法的字形、笔法、结体等为荣。从追求高度相似性上看,沈周的书法和绘画在思维方式上具有一致性。因此,此处乱真是逼真的另一种说法。
王世贞评价前辈祝允明的文艺成就时,说:
“书之古,无如京兆者;文之古,亦无如京兆者。古书似亦得,不似亦得;古文辞似亦不得,不似亦不得。”[1]41
王世贞认为,文学和书法之师古方法截然不同。就书学而言,“似”与“不似”都是重要的取法途径。综观书法史,祝允明以“似”(形神兼备)之法得书之古;米芾、董其昌、王铎等以“不似”(神似形不似)之法亦得书之古。从祝允明《跋米搨兰亭》中,我们可以看出,其遵循法(以似得之)和米芾不缚于律(不似亦得之)之间的异同:祝允明所谓“似”之法,是指临仿过程中,力求全面再现古人在书写过程中的方法、步骤和动作,大至神采,小至字的结体、用笔、大小;而“不似”之法,则是“以胸中气韵,稍步骤乃祖而法之耳。上下精神,相为流通”,[6]545由此得原帖的精神、气韵而神似之。前者重视法则内的规范性,后者追求超越法则后的多种可能性。两者都是重要的取法方法。关键在于,祝允明作为明中期书学仿古的主要倡导者,面对当时寡师二王、多从刻帖而非真迹入手等局面,将临仿之作的主要目标设定为恢复原帖的笔法、神韵(书帖在翻刻过程中已逐渐丧失),并视优秀的仿作为原帖的分支、补充。可以说,依据自己所处的时代、艺术理想等,祝允明选择了“似”之法。我们知道,如果临仿之作以“似”(形神兼备)求之,则临仿过程中,需要不断平衡天趣与法度、雅与俗之间的矛盾[7],难度较高。正因为如此,优秀的仿书作品才具有了书学示范的价值。正如张凤翼评祝允明六十七岁临《黄庭经》所言:
“设有好事儒者,摹勒登石,以嗣王、赵二帖,即以搨本一纸易一鹅,谁曰不可?”[8]268
从另一个角度看,“逼真”标准的模拟特性,容易导致蹈袭、剽窃等问题。为避免此病,祝允明一方面从理论上说明“蹈袭非剽窃”,[9]指出逼真仿作对书学经典的存真、阐释价值;另一方面强调书写者的学问和性情在书写过程中的主导性,以此反对奴书。在《书述》中,他解释说:
“元初……吴兴独振国手,遍友历代,归宿晋唐,良是独步。然亦不免奴书之眩,……太仆(李应祯)资力故高,乃特违众。既远群从宋人,并去根源。或从孙枝,翻出已性,离立筋骨,别安眉目。盖其所发‘奴书’之论,乃其胸怀自憙者也。”[6]512-513
从这段文字看,祝允明以“奴书”批评书家在仿书创作过程中的奴性、局限性:如有门户之见(格局小)、有模拟和剽贼之病(未能内化);不能流露书写者独特的个性、不能吐露其胸中的见解和学识。在他看来,仿书中的奴书之病,产生于后人拘泥于浅见、耳食,“未尝神访”,[6]274执着语言文字而忽视语言文字背后的深刻内涵,只是人云亦云,没有深入思考。祝允明的岳父李应祯也反对奴书,但两者的差异在于,李应祯并没有将“逼真”古人、“归宿晋唐”等与反对奴书紧密结合起来。换句话说,李氏虽然做到了取法宋人而非近人,能以宋人之书立己书之骨骼形貌,书写过程中也能注入自己真挚的感情,但因取法乎中,只能得其下。即能法宋而未能归宿晋唐,因此,其病在俗。
逼真标准的形成,还与祝允明的儒士定位[6]28、述而不作的经学思维方式等关系密切。如他在《怀星堂集》卷一开篇《大游赋》中,刻画了一个独立于天地之间,“要圣贤以为期”,[6]12尊贵无比的自我[6]64。我们知道,祝允明强调自我的独特性,必然反对奴书;而求古尚贤、述而不作[6]472的心态,又必然以逼真古人为贵。在《重刻鄂州小集后序》中,祝允明写道:
“圣人没,六经绝,而文章之法垂。春秋以还,述者孰不欲袭芳贻猷,……近世有唐、宋四家之号,遂令初学胶固耳评,他若罔闻知。愚尝以为不必然,诸子咸师孔氏,诚理至辞达,可名世也。”[6]516
按照文中这种经学存真、述而不作的思路,晋唐经典之书如书学之经,后世临仿时应以存真的态度,悉心揣摩,逼真临仿;而且,存真的仿作,宛如“理至辞达”的释经之文,它有助于赏析,可以视为晋唐经典法书的临习示范。更重要的是,随着晋唐书法真迹的减少,学习者不易获观,以及晋唐真迹在翻刻过程中日见失真、失神,在晋唐书家书写方法堙没——学习者在无法获得口诀手授笔法的情况下,逼真临仿是获得原帖笔法、章法等的最佳途径。
祝允明六十六岁时,在《写各体书与顾司勋后系》款识中,罗列了他心目中的书学经典。他说:“此……《黄庭》《兰亭》《急就章草》、二王、欧、颜、苏、黄、米、赵,追逐错离。”[6]565可以看出,祝允明心目中的书学经典,既有经典名帖,如王羲之《黄庭经》《兰亭序》,皇象《急就章》;也有具体的经典名家,如二王、欧、颜、苏、黄、米、赵。将二王与《黄庭经》《兰亭序》并列,显示了祝允明对书学经典的特殊理解,即某家风格之经典性与某家(或某件)经典作品之经典性。这种将经典作家与其经典作品分离现象的形成,与书学经典的流传方式有关,如受绢、纸等材质寿命的限制,以及古代手工复制、翻刻等技术的制约,一些保存良好的经典之作备受重视,脱颖而出(如冯承素《兰亭序》摹本),也与祝允明对一些书学经典之书家归属问题持有的审慎态度有关。
当然,古代法帖真迹藏品是逼真古人的物质基础,娴熟的临仿技巧则是重要的技法基础。祝允明酷爱收藏[10],以目见古法帖珍品为人生幸事。祝允明四十二岁跋传唐代书家怀素墨迹本《(小草)千字文》曰:“藏真(怀素)书,向独见妇翁太仆李公(李应祯)所藏一帖耳……谨志岁月以自幸耳。”[11]427与其他诸多传世古帖(或为刻本,或为拓本)相比,怀素小草《千字文》为墨迹本,尤为难得之物。正如他在《临王羲之帖册》中所言:“古今书家辄称钟、王,……故其尺牍相传,等若球璧。即石刻流播,亦奉为
楷模。”[3]129-130
总之,祝允明以“逼真”古人为仿书评价标准的形成,与其述而不作的经学思维方式、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尤其是欲从原帖中获得正确的书写方法、笔法等目标有关。这一标准假设了逼真临仿必能得原帖之笔法、神韵,并以真迹藏品为物质基础、以娴熟书写为技法基础。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然,这种做法也遭到了王世贞的讥讽,称祝允明之书“独于八法,形而下者。”[6]647
二、“书必异体”与书法教法示范:祝允明仿书的艺术特色
如果我们将元末明初苏州书家宋克(1327—1387)的《草书进学解卷》、明初河南书家宋广的《草书风入松轴》、浙江书家宋璲(1344—1380)的《草书敬覆帖页》、苏州书家谢缙(1355—1430)的《草书自书诗卷》、松江书家张弼(1425—1487)的《草书七律诗卷》 与祝允明的草书作品相比较,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异:除了与宋克一样更倾向于师法古人外[6]559,祝允明还有兼善诸体的特点。
“书必异体”是祝允明友人对其书法特征的概括。王锜在《祝希哲作文》中说:
“祝希哲作文,杂处众宾之间,哗笑谭辨,饮射博奕,未尝少异。操觚而求者,户外之履常满。不见其有沉思默搆之态,连挥数篇,书必异体。文出丰缛精洁,隐显抑扬,变化枢机,鬼神莫测,而卒皆归于正道,真高出古人者也。……所尊尚援引者,五经、孔氏;所喜者,左史、庄生、班、马数子而已。下视欧、曾诸公,蔑然也。……希哲方二十九岁,它日庸可量乎?”[12]
王锜认为,祝允明虽然年方二十九,但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有高出古人(如欧、曾诸公)之处。因为祝允明创作时,不见其有构思之态(宛如天成),常常是提笔一挥而就、连挥数篇,内容各不相同,书体亦各有异;而且无论是书写内容还是书体,虽极尽其变化,皆能归于正道。换句话说,祝允明面对求文之命题作文,能一挥而就:其文,多出于古之经、史,又能变化多端;其书,能入古帖,又能自出新裁,变化枢机,书必异体。综观中国古代书法史,祝允明之兼善多体、“书必异体”特征的形成,显示了当时文艺领域师法对象在专精与博取之间的取舍和转换,以及对欣赏者立场(或称欣赏者意识)的重视。文学上,这种博取态度在祝氏师友辈中很常见,如书画家沈周的兴趣十分广泛,凡经、史、子、集,下至传奇、浮屠,皆涉其要而掇其英华;唐寅之学,上究天文,下察地理,旁及“风鸟、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间”;[6]389祝允明自己则“自六经子史外,玄诠释典、稗官小说之类,无所不通”,[13]并声称博识以升艺。就艺术创作而言,创作者重视欣赏者的阅读期待、审美趣味,则显示了明中期以后文艺创作过程中逐渐增加的游戏心态、艺术的表演性倾向。
从祝允明的传世作品看,所谓“书必异体”之“体”,广义上是指书体间的差异,即楷书、行书、草书、篆书、隶书之不同(篆书、隶书为祝允明时代篆刻家常用书体,书法家涉略者较少);狭义上是指诸书家各自的风格特征,如王羲之风格、颜真卿风格等。祝允明应友人之邀杂临诸名家帖(“请举各家体貌为之”[14]),便是使用了这层意义。祝允明一生以得古帖之字形、笔法,能得其形神兼备为乐。文征明跋祝允明临宋拓智永《真草千字文》中指出了这一特点:
“余尝谓书法不同,有如人面。希哲独不然,晋唐则晋唐矣,宋元则宋元矣。彼其资力俱深,故能得心应手。此卷摹临智永禅师法帖,而雄姿劲气,更轶而上之,吾不知其为逸少、为智公、为希哲也。”[15]
从祝允明《真草千字文》款识可知,他之所以临摹这件作品,是因为宋本智永《真草千字文》拓本很精彩,以及友人的临摹邀请。结合文征明“吾不知其为逸少、为智公、为希哲也”可知,祝允明试图以墨迹临本恢复甚至超越宋拓本,才是更重要的原因。我们知道,宋拓本智永《真草千字文》虽然墨光萤腻,字画遒劲,但与其原墨迹本相比,缺失很多,如起止、转折处点画的力度、粗细、牵丝等的细腻变化。智永作为王羲之的后代,其《真草千字文》保存了大量的二王书写技巧、结体特征,被现代书家公认为学二王书的重要入门之阶。由此,关于智永、二王书系的书法史知识、书写技法等,就成为祝允明以历史性想象还原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本的重要辅助手段。这样一来,祝允明临帖时逼真原帖、仿书创作时书必异体等行为本身,就具有了参与文人书法史建构、传播的重要意义。
祝允明的“书必异体”,意味着书家能逼真地呈现古人或古法帖的字形、笔法、风格等特征。由此,书写技法和神采风韵的再现,成为一项重要的技能(学力)。就二王自身的书写技法而言,其口诀手授式的传承方式,至宋代已不易得,至祝允明时代,只能从晋唐原帖及历代晋唐原帖的仿书中探寻线索。正如清代书家翁方纲所言:“明贤晋法初谁得,但有枝山与雅宜(王宠)。”[2]46王宠跋祝允明《草书七绝诗卷》则曰:
“枝山此书点画狼藉,使转精神,得张颠(张旭)之雄壮、藏真(怀素)之飞动,所谓屋漏痕、折叉股、担夫争道、长年荡桨等佳意咸备。盖其晚年用意之书。”[2]56
在这段评价中,王宠关注祝允明草书中对古代书家风格特征的准确把握、对古代具体笔法特征的精确再现。欣赏过程中,他的兴趣点在“屋漏痕、折叉股、担夫争道、长年荡桨”等古代经典书写技法而非作品本身。这从侧面显示了当时以祝允明、王宠等为首的书家对掌握古代经典技法的强烈兴趣和执着追求。李应祯也很重视书写的技法问题,文征明在跋老师李应祯的书帖中,详细记载了老师重技法、反奴书的特点。他说:
“(李应祯)因极论书之要诀,累数百言。凡运指凝思,吮毫濡墨,与字之起落、转换、大小、向背、长短、疏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盖公虽潜心古法,而所自得为多,当为国朝第一。其尤妙能三指尖搦管,虚腕疾书,今人莫能为也。……自书学不讲,流习成弊。聪达者病于新巧,笃古者泥于规模。公既多阅古帖,又深诣三昧,遂自成家,而古法不亡。尝一日阅某书有涉玉局笔意,因大咤曰:‘破却工夫,何至随人脚踵?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16]
李应祯反对一味模仿古人的奴书,强调书写过程中自我心性的表达。他非常关注古帖的技法,尤其是握笔方式和运笔方法。其技法之得,全在自我悉心揣摩原帖,而非借鉴他人的探索成果。从这个角度看,学习者直接从古帖、原碑中探索笔法,是对耳提面命、口诀手授式传统书法教学法的脱离。而这种脱离,与中国文化的贵族化向平民化的转换有关①尹吉男教授《贵族、文官、平民与书画传承》中指出,晋唐书家年幼学习书法时,主要临仿真迹,由传承有序的书法老师为其指点笔法;宋以后学书,多始于临仿刻帖(或赝品),笔法问题主要靠暗中摸索而得。。李应祯、祝允明等明代书家,早年学书多以临仿刻帖入手,他们对于笔法的认识,多来自身边的师友(师今)。当他们转而师法晋唐时,晋唐笔法的原貌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疑问而变得重要,而临仿时逼真原帖,从帖中寻找答案,无疑是释疑的最佳方法。可以说,这种师学方法、态度的转变,无形中促成了一些新观念。如新的师徒观念、新的书法教学方式、新的书学评价标准。祝允明说:
“故尝谓自卯金当涂,底于典午,音容少殊,神骨一也。沿晋游唐,守而勿失。今人但见永兴匀圆,率更劲瘠,郎邪雄沈,诚悬强毅,与会稽分镳,而不察其为祖宗本貌,自粲如也(帖间固存)。……赵室四子,莆田恒守惟肖,襄阳不违典刑。眉、豫二豪,啮羁蹋靮,顾盼自得。观者昧其所宗:子瞻骨干平原,股肱北海,被服大令,以成完躯。鲁直自云得长沙三昧。诸师无常而具在,安得谓果非陪臣门舍耶?而后人泥习耳聆,未尝神访,无怪执其言而失其旨也。”[6]274
他以“帖间固存”为依据,将“泥习耳聆”与“神访”视为两种对立的学书方法。在晋唐笔法缺失、没有传承有序的书学老师指导笔法的情况下,通过逼真临仿以实现“神访”原帖,成为学书的根本大法。在祝允明的心目中,这一大法以晋唐二王笔法和风格为核心、晋唐二王仿书体系为补充,即书极乎二王,而底乎唐。由此,晋唐二王体系成为书学的核心,宋以后诸多书家则被视为不同阶段、不同角度阐释晋唐经典的阐释者。这就将古代书法史理解为何谓晋唐书、如何学晋唐的历史。这样一来,宋以后的书学发展史就变成了如何从各个角度取法晋唐而出新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仿书具有了书学示范的功能。
综上所述,祝允明的“书必异体”,是其无书不学、博学好古的证据,其中渗入了当时文人的游戏精神和欣赏者意识;其“书必异体”之仿书作品,因逼真原帖,尽可能地恢复了晋唐旧帖中的字形、笔法、章法、神采,成为学习晋唐书帖的重要参考,具有了书法教学示范的功能。
三、“想象宗祖”与“以意构之”:祝允明仿书的创新之法
祝允明曾以“想象宗祖”论及古人之诗,他说:
“古人为诗,趣识既卓,而齐量又充。其命题发思,类有所主。虽微篇短句,未尝无片意新特。今人之诗,自数大家外,能者甚众,佳篇亦未尝乏,而求其合作者,则殊鲜焉。……守分者多疲词腐韵,无天然之态,如东邻乞一裾,北舍觅一领,错杂装缀。识者可指而目之曰:‘此东家裾也,此北户领也。’是可谓之陋。狥质者多儇唇利口,无敦厚之气,如丹青涂花,伶人饰女,苟悦俗目,不胜研覈,是可谓之浮。陋也,浮也,皆非诗道,与古背驰,无惑乎其不合作也。……大抵生纽性情,趁人道路。况其摹仿师法,泄迩忘远,只知绳武云仍,不肯想象宗祖。”[11]546-547
文中“想象宗祖”与“绳武云仍”作为一组对立的诗歌学习方法,分别对应于师古与师今。“想象宗祖”之法意味着,作诗时与古为徒,随性情而动,想象力成为沟通古今的重要手段。从祝允明的文集看,古诗十九首、陶渊明诗等是祝允明心目中“趣识既卓而齐量又充”的诗作代表。因此,“想象宗祖”可以理解为,以古诗十九首等相关文化知识为基础,以性情为助力,以想象力为媒介,探寻原诗命意之所主者(主导因素),探索得诗歌天然之态的途径,从而领悟“何谓生命”(生命意义、生命真实)。
祝允明的想象宗祖与研想之法,都强调想象力在艺术思维过程中的核心地位。祝允明在《书鸱夷子皮遗像》中说:
“观册子上道古人志行,必以是入,研想求其容气如何,予辈之所同,如太史公论子房已然矣。……抑直以我精神,暗中摸索云尔也。”[11]562
其意思是,研想者之意(意识)[11]523,通过范蠡(即鸱夷子皮)的遗像(物质媒介),基于同情、同理之心(“予辈之所同”,共性),以“我精神”,不断综合想象(“暗中摸索”)流露在遗像中(已发之言)、隐含在遗像外(未发之言)的知识和信息,即“求其容气如何”。这是一个以想象、直觉联结遗像及其时代才性的相关知识,由此实现今人与古人感通的过程。它没有标准答案,是一个类似能“涤荡氛土,以清宁吾神气”[11]526的游戏。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共性,是研想之法得以实施的基础。在祝允明看来,从士之养成过程看,古人与今人的修养方法相同;今人若能志向卓尔不凡,能离俗求雅,则“我精神”自然能通过暗中摸索,领悟到古人的精神世界,实现“今人高会古人心”[6]200的理想状态。简而言之,基于共同的修养和同情、同理之心,古人与今人可以相通。
就书画取法而言,想象宗祖之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以金石复制方式流传的古代书画,通常仅存大概形貌,几经翻刻后,甚至出现“蹇裳濡足之苦,……甚多似,而多遗恨者”[6]542的情形。也就是说,在仿书创作过程中,想象宗祖作为理解古人的重要手法,是基础,还需要解决创新性表达的问题。为此,祝允明晚年提出了以意构之创新之法。他说:
“(仆)今效诸家裁制,皆临书,以意构之尔。”[6]565
综观祝允明传世临书及诗文可知,“以意构之”之意,有大意、心意等多重含义。
从临书与原帖的关系看,以意构之之意,主要指原帖形貌、神采之大意。从其“旧人笔虽有高下,必走法度中,其下者凡耳。今人纵佳者,多以脱略法度自为高。沈畦灭径,指作意外境,直愚耳。凡可也,愚不可也”[6]556由此可知,祝允明将古代书画中的精华主要归结为笔法和运用笔法的原理。如果论及原帖书写原理的形成,显然涉及原帖书写者的个性、才华、学养、艺术追求等诸多方面,它们不可能脱离时代环境。这样一来,书家的临仿行为,似乎是一次时空穿越之旅——穿越到古代书家的心灵、艺术世界中,完成一次代替(代言)书写。此时仿书者就像演员,代言书写也就具有了游戏精神、自由属性。在这个意义上,仿书也就有了创新性。
从仿书创作过程中模拟和运思角度看,以意构之之意即心意,是以心为器官的意识活动。它与才、理等相互作用,贯穿书写活动始终。祝允明说:
“学者,士之食也。质者,学之田也。才者,学之稷也。功者,学之耒也。文者,学之饎也。”[6]292
“身,舆也。世,途也。才,马也。心,御也。理,御之法度也。盖才出乎心,身乘之以临世。”[6]456
第一种说法着眼于士之才能的养成。祝允明认为,获得才能之多寡、高低,取决于先天资质、后天学习。第二种说法指出,“才”作为世俗“借倩之买名利官禄”[6]578的媒介,受控于心(控制主体)和理(控制法则)。也就是说,书家之心以理为法则,控制其才华的发挥和运用。由此,才(意)与理(法)的平衡问题,成为书家以意构之创新活动过程中的关键。
心,作为祝允明眼中的“士之机”[6]237(士人的三大文化武器之一),有爱憎,多变化;“圣哲用道养心”,[6]261凡俗可以通过取消古今、贵贱、人我等二元区分,养出蕴含“心腑之真”[6]86的“童心”。[6]131童心是未经后天熏染的先天之性。它受之于天(理气和而始生),本身不可见,有恒定性。这种恒定性使人类能心意相通[6]253。理,作为心意控制才能的法则,与欲相对,有“中节”[6]249之特征。书学之理,既存在于原帖之中,也存在于临帖者以想象为媒介的理解之中。原帖之理与临帖者理解之理之间的差异,如果能高明且独特,就有了仿书的创新基础,即因误读而产生新意。另一方面,因个人的才性、悟性等差异,临帖者所得原帖之理虽各有偏差,但亦各有所得,就像是“大成之圣为其徒者,具体一支,皆有益于后人”。[6]545也就是说,高妙的仿作作为原帖(母)所生之子、支流,可以视为整个系列(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心意的活动过程,是心御才以得书理的过程。因此,仿书创作过程中,书理之得,或偏或未得其时,但作为一个发展系列,有其自身存在的独特价值。
通过对祝允明“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命题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以意构之之“构”的具体内涵。祝允明说:
“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川岳盈怀,境之生乎事也。……若单行孤旅,骑岭峤而舟江湖者,其逸乐之味,充然而不穷也,情不自境出耶?情不自已,则丹青以张,宫商以宣,往往有俟于才。夫韵人之为者,是故以情之钟耳,抑其自得之处,其能以人之牙颊而尽哉?……(蔡)子华情生境,境生事,其为好游而有得,则予能言之矣;若其目之所视,足之所履,体之所止,意之所指,则岂他人之知旨乎?”[11]553
宽泛地看,目(视)、足(履)、体(止)、意(指)都属于“身”的范畴,是人与外在环境接触、沟通的媒介。“境”指游览过程中人融入自然的境况,即“川岳盈怀”。在这里,“事”指外出旅游,如“单行孤旅,骑岭峤而舟江湖”等事件。情,即人在游山玩水中的逸乐之情。“事表而情里”,[11]563情居于主导地位。因此,“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显示了一个由身、事与境相互触发,由境生到情生的体验过程。当这种个体的情感体验持续发生,以至于表达的欲望无法抑制时,彰显个性的书写、绘图、歌咏等艺术语言,作为想象、灵感的结晶,喷薄而出。此时,灵感、想象、直觉等作为艺术理解和表达的催化、粘接要素,将驱使“丹青以张,宫商以宣”之才。因此,祝允明的以意构之之“构”,是指仿书创作者以原帖为基础,以想象力和直觉为媒介,平衡才(意)与法(理)的构造和创造活动。这是一个身、情、境相互激发的过程。
以意构之作为仿书的创新之法,关键在于解决意与法的关系问题。书学上,祝允明极力推崇晋唐之书,以逼真临仿为方法,以守而勿失为目标;行为上,祝允明“为人简易佚荡,不耐龊龊守绳法,或任性自便”[6]644“惮近礼法之儒”。[6]647但因其天资极高,能“默而好深湛之思,濡豪展卷,游心玄间。宾杂众沓,凝神反视,川奔云烂,捷若宿构”。[6]644这种矛盾状态及其矛盾的解决,对晚明书家颇有启发。
此外,以意构之作为祝允明的实临创新之法,与文征明所谓的“探奇摘异”,[17]以及“泥于点画形似,钩环戈磔之间”[8]268之实临有很大的差异。祝允明天纵奇才,记忆力极佳,仿作能形神兼备,即不惟“点画惟肖,而结构疏密,转运遒逸,神韵俱足”。[8]268正如王穉登所言:
“枝指公(祝允明)独能于榘矱绳墨之中,而具豪纵奔逸之气,如丰肌妃子著霓裳羽衣在翠盘中舞,而驚鸿游龙,徊翔自若,信是书家绝技也。”[8]268
王氏以丰满美丽女子著霓裳在翠盘中跳舞的形象,比拟祝允明仿书的艺术特色。它指出了其书既能受制于法则、规范(晋唐经典),又能自出己意的书写表达特点。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正是祝允明以意构之创新之法所刻意追求的。
结 论
祝允明时代,书学取法,寡师二王。即使倡言师古,也不过“谈书则曰苏(苏轼)黄(黄庭坚)”,[11]784而忘二王之矩;或多师法近人,如明初二沈兄弟、姜立纲等,多有尘俗之气。因为帝王的推崇,二沈、姜氏书风占据了官方书坛主流。从明初传世仿二王体系作品看,仿书多以意临为主,不刻意追求仿作与原帖的高度相似性。这样一来,在书学领域,谁值得学、学什么、如何学等问题,成为祝允明时代面临的重要问题。
自身的经学修养、家学熏染,以及受吴地之士多师古文化传统的影响,祝允明将这些书学问题归结为:在传承有序、口诀手授式晋唐书写技法失传的情况下,如何得二王书风的笔法这一核心问题。在祝允明的心目中,何谓二王笔法以及如何得二王笔法的历史,就是文人的书学发展史。与晚明董其昌“妙在能合,神在能离”[18]之说相比,祝允明特别关注笔法问题,并将逼真临仿视为得二王笔法的重要途径。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与祝允明的经学思维方式、文学与书学相通观,以及沈周在画学领域倡导的师古方向、师古方法等关系密切。
在祝允明的思想中,五经乃文之本源,是古贤智慧的结晶,其后之文,不过羽翼五经者,或未得其整体性,或失其时代性,但皆有其独特的价值;治经当以汉贤注传为主,汉后及唐贤疏义、宋贤所传为辅,即“文极乎六经,而底乎唐。学文者,应自唐而求至乎经”。[11]778他将五经经文与羽翼五经的汉唐释经之文,以及宋贤所传之文分出了主次等级,提出“根本乎五经,平览乎十代”,[11]781将它们纳入经(母)与释经(子)的发展序列中,并以释经之文解释经文的存真程度为标准,判定其价值的高低。
与同代人相比,祝允明在文学、书学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他看来,书法与文法相通,“观古人文,可得书法;观书,可得文法”。[6]555文学领域的“根本乎五经,平览乎十代”和书学领域的“遍友历代、归宿晋唐”,体现了祝氏“踞中以揽边,握要以延博”[11]783思维方法在文艺领域的普遍运用。
祝允明能自然地将这些思维方式、理论成果迁移至书学领域:将二王之书视为书学之五经,唐代虞世南、欧阳询、颜真卿等诸书家被视为二王之书的阐释者(即书极乎二王,而底乎唐。学书者,应自唐而求至乎二王),宋后诸书家则被视为阐释继承者和发展者,并将它们视为一个文人书学发展的序列。据此,从如何得晋唐二王书系笔法的角度看,逼真临仿晋唐原帖(实临)、书必异体,成为仿书的方法、技能评价标准,以意构之则成为仿书创新大法。
在祝允明之前,吴门画家沈周追求逼真临仿古画、写生古桧,并较早在绘画作品的跋文中明确提出仿某画家,开启了一个绘画发展的新方向(复古)、新方法(逼真临仿某画家的具体风格)。在师学方向、方法上对祝允明有一定的启发。因此,祝允明书学仿古模式的形成,是解决时代问题的产物。它以得二王经典笔法为核心,以“遍友历代、归宿晋唐”为书学发展策略,并由此逐渐展开。
晋唐书学经典法则作为规范,可以指导前进的方向;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阻碍创新的形成。因此,书学仿古模式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是意与法(规则束缚与自由创造)的关系问题。如果书家受制于经典书写法则,则创造性受损,失之自然;一味师心自运,又易流入俗俚,有失雅正之体。为了平衡意与法,仿书创作过程中,书家需要考虑:书学宗祖晋唐二王书风的具体笔法如何?如何表现其字形、笔法、章法之美?诸如此类。总体而言,祝允明将仿书创作视为一个今人以笔墨与古人相沟通的过程。它包含创作者对古人书写行为的想象和还原,对古代书法史和文化史的认知,以及创作者自身的书写情感和欲望表达,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实践活动,它折射出创作者真实的生存状态。
可以说,祝允明的逼真临仿、书必异体、以意构之仿书创新法,既体现了祝允明时代的文化精神,也展现了书学学术方法的转变,即在人的生命存在状态中把握仿书创作活动。由此,以临仿书帖为媒介,古人与今人的关系,便从外在的关系逐渐向内在的关系转化。这种转化,使仿书创作行为具有越来越多的体验性特征。而这种学术转向和体验性,在明末董其昌、王铎等书家那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