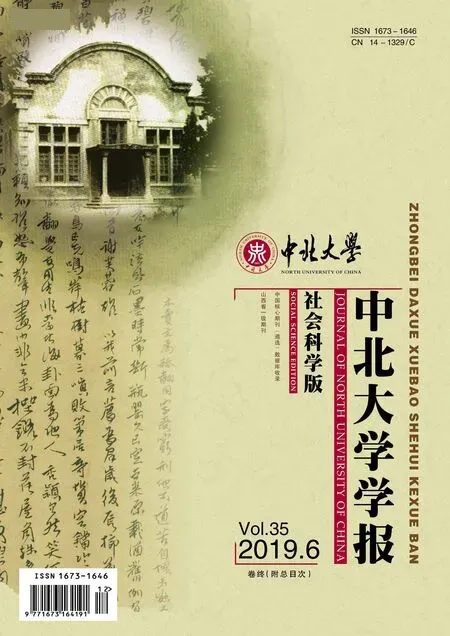论地理名胜作为文学资本与创作的关系
2019-01-03李欣玮
李欣玮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文化资本”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一个重要社会学概念。“从资本是积累的劳动角度上看,文化来源于人类的实践,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积累的结晶,它的传承是通过教育和学习把知识固化于头脑中的劳动,是一种积累或未被消费掉的劳动。”[1]作为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来源于文化生活。“作家对具体客体的选择总是或明或暗地受到当时社会生活的情势的规定和制约,包括政治的、 经济的、 文化的和社会心理、 社会意识等多种生活因素。”[2]119我们将文学理论与社会学概念结合起来,作家在创作时,会受到一种被积累下来的文化资本因素的影响,这种资本,不仅仅是作家所面对的客观存在物,更是一种已被前代作家的感性直观和情感体验所投射并固化下来的精神资本。同时,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以其所蕴含的精神力量,赋予客体新的文化内涵。故本文在布迪厄之“文化资本”的前提下,提出“文学资本”的子概念。“文学资本”特定于文学构思、 创作之中,是作家在创作时所受到的创作客体已具有的文学内涵。作家的创作往往在接受已有文学资本的基础上,并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建立在这样的资本之上,成为这一文学资本积累的推动者、 传承者、 发展者,在创作中与其形成双向互动。本文以特定地理名胜作为文学资本与作家创作关系的切入点进行讨论。
地理与文学的关系,学界多从地域文化、 风土人情对创作的影响来讨论,从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 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3]1730刘师培《南北文风不同论》、 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 钱建状《南渡词人的地理分布与南宋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地域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较大的地理区域和时间范围,即一段较长时间内,地域文化对作家群体及其创作的影响。事实上,地域文化不仅间接浸染着生长于斯的作家,还会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影响往来于此的文人。特定的地理要素,尤其是风景名胜,常常在许多发于一时的山水记游之作、 登临怀古之文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本身作为一种客观物质在一代代作家的创作中不断被意象化、 情感化,最终成为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双重产物。这些名胜已经建构起来的文化内涵,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成为了一种文学资本,对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文学资本,不仅是作家所面对的客观存在物,更是一种已被前代作家的感性直观和情感体验所投射并固化下来的精神资本。作家不由自主地被这种精神资本所吸引,无意识地模仿,强化着这里的固有内涵,并有选择地进行再创作,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文学资本积累与再生的重要资料。
目前,地理名胜与文学的联系更多出现在地理揽胜类的文本之中,用于辅助介绍其文化属性,并未将其文化意义提升到较高的地位。名胜古迹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不应被一笔带过,相反,作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桥梁,名胜古迹体现出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极有必要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而被进一步挖掘和展现。这也有助于使社会大众进一步体会到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存续作用,对于强调保护物质文化遗产、 树立精神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本文试图讨论特定地理名胜作为一种文学资本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或从文学角度揭示出历史文化遗产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唤起公众对名胜古迹文化内涵的重视,提升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感。
1 同一历史人物的不同文化性格:苏轼与湖州、 杭州
1.1 湖州与杭州:截然不同的文学资本
江浙地区气候宜人,风景优美,生活安逸,是历代文人向往之所。湖州与杭州恰属这一地区。杭州位于钱塘江下游,京杭大运河南部。湖州得名于湖,紧邻杭州,西靠天目山、 北濒太湖,与苏州、 无锡隔湖相望。依唐圭璋、 汪国垣先生按省份地域划分作家创作来看,两地同属江左之处。但深入研究,两地却具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资本:
“钱塘自古繁华”,杭州作为南宋政权的中心,是政治、 经济要地。自唐以来,其文化地位就在不断上升,这里有丰富的物产、 怡人的环境,更有在当时世界领先的城市建设,从作为一种文学资本走进文人墨客笔下之始,便形成了独有的文化特点。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琦,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4]25
(柳永《望海潮》)
这首《望海潮》,是表现杭州文化特色最鲜明的实例,不仅仅是柳永,历代文人都在杭州留下了昂扬入世的文字:唐代李白“诗成傲云月,佳趣满吴洲”[5]549; 孟浩然“今日观溪涨,垂绝学钓整”[6]755; 岑参“千家窥释肋,五马饮春湖”[7]255,不管是快意行走江湖,还是在杭州壮丽景致前的远大志向,抑或送别不作悲伤语,祝福友人能在杭州快意生活的话语。这样的文化资本传承至宋代,更因经济的南迁而愈发昂扬:宋初潘阆《酒泉子》:“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万家掩映翠微间,处处水潺潺”[8]8; 张先《破阵乐》:“郡美东南第一,望故苑、 楼台霏雾。垂柳池塘,流泉巷陌,吴歌处处。”[9]36“尽朋游,同民乐,芳菲有主。”[9]36他们都以一种积极用世的态度,写尽钱塘的繁华。
湖州自然景观清幽,少烟火气而多世外仙境之感。早在东晋时期,湖州便印上了“隐逸”的标签。“贤者乐游其地。自魏晋以后,仕者或志慕闲散,往往请乞于此。”[10]湖州成为文人隐居的佳地,北朝鲍照《从庚郎中园山石室》表现了湖州的幽静之景:“冈涧纷萦抱,林嶂杳重密。昏昏瞪路深,活活梁水疾,幽隅秉画烛,地墉窥朝日。”[11]81唐吴中四士之一的包融曾写下“坐令开心胸,渐觉落尘滓。北岩千余切,结庐谁家子。愿陪中峰游,朝暮白云里”[5]49的隐逸心境。大历年间,湖州文坛又出现了一大批隐逸诗人,如陆羽、 朱放、 李冶等,其中诗名最盛的是诗僧皎然“自从东溪住,始与人群隔”,自从来到湖州,诗人便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体味着这里美景,也感受着前人所遗留下来的放世之情。“放世与成名,两图在所择。吾高鸱夷子,身退无瑕摘。吾嘉鲁仲连,功成弃珪璧。”[12]19“舒卷意何穷,萦流复带空。有形不累物,无迹去随风。莫怪长期逐、 飘然与我同。”[13]508钱起作“谷口春残黄鸟稀,辛夷花尽杏花飞。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14]643亦表现湖州之清冷宜隐。总体看来,历代文人在湖州留下的多为放世之作。
1.2 苏轼在湖州、 杭州的创作
一代文豪苏轼在杭期间,大兴政事、 上访佛寺、 下采民风,创作多以积极的笔触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对杭州景民的热爱。如《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15]404
苏轼前后两次官任杭州,在经历了乌台诗案等政治创伤后,亦常有人生幻灭之感,但每至杭州,这里积极昂扬的气质便不自觉地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人生是空的幻灭之感被杭州自有的文化底蕴冲散,在这里,即使潦倒于政治,但苏轼仍心系民生,旷达入世。如《自普照游二庵》:
长松吟风晚雨细,东庵半掩西庵闭。
山行尽日不逢人,郁郁野梅香入袂。
居僧笑我恋清景,自厌山深出无计。
我虽爱山亦自笑,幽独神伤后难继。
不如西湖饮美酒,红杏碧桃香覆髻。
作诗寄谢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16]66
这首《自普照游二庵》直接表现出苏轼在入世与避世间的矛盾: 政治的纷扰使诗人常生隐居避祸之念,但望着西湖美景,又生出积极于生活的冲动。杭州正是这样用它独有的文学资本感染着作家、 影响着其文学创作。
同样位于江浙一带,同样是苏轼其人,在湖州的作品却常以逃离出世的“隐逸之心”为主题。[17]苏轼未曾长居湖州,但每每短暂停留,却受到湖州既已成型的文学气质影响,于湖之作往往旷然而生隐逸之心:“暖余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16]61此诗是苏轼第一次过湖州所作,字里行间都是政治的失意,心灰意冷间苏子企图“对青山谈世事”,归隐之心溢于言表。《将之湖州戏赠羊老》则明确地表示出苏轼在仕隐之间做出的选择。
余杭自是山水窟,久闻吴兴更清绝。
湖中橘林新着霜,溪上苕花正浮雪。
顾渚茶芽白于齿,梅溪木瓜红胜颊。
吴儿鲙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
亦知谢公到郡久,应恠杜牧寻春迟。
鬓丝只好对禅榻,湖亭不用张水嬉。[16]57
全诗未提及一句政事,也未表现出任何仕途的不畅带来的苦闷,有的只是对纵情于山水田园之乐的期待与享受。可以看出,湖州对于苏轼而言,是一个可以全然忘忧、 隐逸于自我精神世界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是苏轼未至湖州前的创作,“久闻吴兴更清绝”,还未亲身体验湖州之美,苏轼便早早把湖州描绘得如此惬意怡人,这种诗人在创作之前的心理预期,不可不谓是湖州自有的文学资本对其产生的影响。此处再对比苏轼于杭的作品《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一:
夏潦涨湖深更幽,西风落木芙蓉秋。
飞雪暗天云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
湖上四时看不足,惟有人生飘若浮。
解颜一笑岂易得,主人有酒君应留。
君不见钱塘宦游客,朝推囚,暮决狱,不因人唤何时休。[16]44
同样是对于美景的描写,相比在湖州的醉心山水、 渴望决然归隐的心情,苏轼于杭州之时却总是不自觉地将视线投注于景物之上的社会生活,以一种昂扬热血的态度关注政治民生。两相对比,湖、 杭两地的文学资本对创作的影响便十分明显了。
2 不同历史人物的相同文化选择:洞庭诗两首
如上所论,不同的地理文学资本会对同一作家的创作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甚至使其在同一段时间内做出不同的创作选择。同理,不同时代背景、 人生经历、 文学气质的作家,在某个特定的文学资本面前,却会受其影响,不由自主地向这一文学资本已有的风格、 内涵靠近,从而创作出意境内容上具有相似性的文学作品。
2.1 洞庭文学资本
位于湖南北部,长江中游荆江河段以南的洞庭湖,最早与沅水、 澧水、 辰水、 叙水、 渐水、 酉水、 资水、 湘水并称“九江”。《尚书·禹贡》云:“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18]52,最早记录了洞庭的地理位置,文学作品中最为人所知的洞庭文字应是《湘夫人》中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19]48,屈原心系国家与政治,其作品多有关乎洞庭的描述,如“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19]107,“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暗暗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19]182。屈子游经洞庭湖所发出的对于国家、 政治的绝望呐喊成为了洞庭文学创作的起点和精魂,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和文化资本,具有着阔大的胸襟与气派。
随着岳阳楼的兴建,“岳阳天下第一楼、 洞庭天下第一湖”便一代代为人传颂。延颜之《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气势开阔、 境界雄浑、 寄托遥深。“江汉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沦洞庭,七泽蔼荆牧。经途延旧轨,登闉访川陆。水国周地险,河山信重复。却倚云梦林,前瞻京台囿。清氛霁岳阳,曾晖薄澜澳。凄矣自远风,伤哉千里目。万古陈往还,百代劳起伏。存没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请从上世人,归来艺桑竹。”[20]280自此,无数文人骚客不断继承、 强化着洞庭湖、 岳阳楼这一文学资本,壮志满怀而来,而使其不断发展、 再生。
2.2 洞庭诗两首
孟浩然(689—740年),世人称之孟山人。“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21]155,其诗冲淡自然,意境清迥,韵致流溢。作为盛唐诗坛的先行者,孟多以“隐士”的形象、 “冲淡自然,平和清冷”的诗风而为研究者所关注。与孟浩然不同,杜甫(712—770年)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22]1的宏伟抱负。其创作往往密切关注现实生活,又因经历安史之乱的颠沛流离而多“沉郁顿挫”之气。杜甫和孟浩然,一位处在盛唐年间,一位经历由盛至衰的年代; 一位纵情山水,行隐逸之乐,一位投身社会,仕朝堂之忧。在时间、 空间、 性格、 经历上完全不同的两位诗人,其洞庭湖之作却有着相同的文学气质: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21]74
(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22]271
(杜甫《登岳阳楼》)
二诗均写洞庭山色,都表现出壮阔宏大的文学气象,为后世文人所乐道。方回于宋元之际编《瀛奎律髓》,此两首诗均入选,回在孟诗后批道:“予登岳阳楼,此诗大书左序球门壁间,右书杜诗,后人自不敢复题也。”[23]3胡仔亦云:“洞庭天下壮观,自昔骚人墨客题之者众矣……皆见称于世,然未若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则洞庭空旷无际,气象雄张,如在目前。至读子美诗,则又不然。‘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梦也。”[24]41清人黄叔灿《唐诗笺注》卷一:“二诗总好在上四句,开口即极形容洞庭之大。”[25]90可见由宋元直至清代,《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登岳阳楼》都被认为是表现洞庭湖光山色的登顶之作。同时,在创作手法和表现内容上,两诗也多有相似之处:开篇先言视角和背景,“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盛夏远观洞庭湖山水一色,“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则是登楼远眺。但不论视角高低,均为远望之景。第二联共同表现了洞庭的壮阔气象,怀抱日月,吞吐山河。“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水汽蔓延,波涛汹涌,其豪迈之势有撼动城池之力。“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洞庭水势浩瀚,可将吴楚两地东南分隔。日月、 星辰、 山川、 宇宙都包孕其间。三四联同述心事,联系上文已阐述的作者时代背景和文学风格,再细究子美、 浩然创作两诗的时间,我们发现,前两联对洞庭气象极为相似的表达,却是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下创作的:据《新编唐诗三百首》注,孟诗开元二十年作,字里行间都是与其平淡冲净的创作风格截然不同的踌躇满志和政治期待。杜甫《登岳阳楼》则创作于其57岁之时,即去世的前两年。依据后两联看也可得知,此时的杜甫已是年老多病,饱经沧桑。在这样“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时刻,杜甫却并未将心事移情至洞庭湖,在诗景中表现出凄凉衰飒之境,反而以一种难得的气魄描绘了声势浩大,极为壮丽的洞庭水景。
其实,洞庭—岳阳文学资本对创作的影响,在孟、 杜二人的诗歌中有鲜明的体现:依前文所记,孟浩然之《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创作于开元年间,而杜甫之《登岳阳楼》作于大历年间,前后相隔三十余年,在杜甫登高创作之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早已名冠天下。《唐诗纪事》记张说荐孟浩然,孟浩然为玄宗赋诗事,玄宗说:“卿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可见此诗当时已是天下传诵。杜甫之“昔闻洞庭水”“所闻”内容恐怕也有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所传递下来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即使我们将子美在艰难苦恨之时仍作旷达辽阔之景的矛盾现象理解为受到孟浩然诗的感召,也是说得通的。二位作家的诗歌创作与其本身的文学风格、 生活经历产生了极大的矛盾,究其原因,我们不妨猜测,是洞庭湖这一文学资本已经建构的文化内涵,感染着孟、 杜二人,使他们不自觉地靠近、 模仿、 强化着洞庭文学资本。
3 双向互动中获得超越:西塞山的文学地理流变
同一作家面对不同的文学资本,会做出不同的创作选择; 不同作家笔下的特定地理意象却受到文学资本的影响而有了相似的文学表达,这都是文学资本对创作的驱动作用。反之,作家创作是文学资本得以形成的前提,文学资本源自伟大的作家和极富影响力的作品。作家创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某些传统的地理名词的认知,通过文学世界里的表达与描写,模糊了其原本的含义,使其成为一种文学资本长久流传。地理文学资本与作品创作正是在这样的双向互动中获得了艺术上的超越。
论及西塞山,“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26]13的词句会首先进入文学爱好者的脑海中,“西塞山”作为一个文学意象,代表着清丽柔美的江南景象,更是文人悠然闲适、 远离尘嚣的心灵家园。但是,纵观文学史上“西塞山”入诗入词的情况,我们却发现,地理概念上的“西塞山”不只有一个:“壁立江心,横山锁水,危峰突兀,雄奇磅礴”等大相径庭的景致存在于对西塞山的描写之中。在张志和《渔父》之前,文学作品、 地理文献的记载往往将“西塞”与“西塞山”混同:“河水重源,又发于西塞之外,出于积石之山。”[27]462江淹《渡西塞望江上诸山诗》[28]13:“南国多异山,杂树共冬荣。……石林上参错,流沫下纵横。”“西塞无尘多玉筵,貔貅鸳鹭俨相连。……鲁儒纵使他时有,不似欢娱及少年。”[29]2452《全唐诗》中,涉及“西塞山”的诗歌共11首,其中孙元晏《吴·武昌》、 陶岘《西塞山下回舟作》、 韦应物《西塞山》、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等诗中描写的西塞山,也都明确指向湖北省黄石市的旧时古战场的遗址,这里厉风飒飒,黄土漫天,山势高耸险峻:“势从千里奔,直入江中断。岚横秋塞雄,地束惊流满。”[30]532“残日衔西塞,孤帆向北洲。”[29]6546此类对“黄石西塞山”的描写并不在少数,但为何最终却被“江南西塞山”所取代,不仅为后世文人反复引用、 吟唱,而且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精神家园,和极具力量的文学资本?张志和《渔父》在“江南西塞山”经典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春江细雨不须归。[29]278
《渔父》表现西塞山下悠然的隐逸生活,白鹭、 桃花、 蓑衣、 斜风细雨,从视觉、 触觉几个角度勾画出一幅美丽的江南山水图。一经创作,便广为传播,引来一众文人墨客的唱和与吟诵。《竹坡词话》载:“当时和《渔歌子》者无算。”“仿张体咏渔父者亡虑十数家。”[31]78“西塞山”的从容与安逸使它成为无数在宦海中浮沉的文人心之所向的精神净土,争先恐后将其作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原料。张羽《西塞晚渔》:“西塞山前日欲基,江树离离起烟雾。玄贞仙驭不可扳,时听渔歌隔溪渡。湾头酒贱级鱼肥,红尘不上绿获衣。投竿侍掉看新月,扰见双双白母飞。”化用《渔父》词境,并进一步扩充、 丰富。王琪《望江南》:“西塞山前渔唱远,洞庭波上雁行斜。征棹宿天涯。”将《渔父》中的意象化入诗中。甚至有苏轼《浣溪沙·渔父》:“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黄庭坚《鹧鸪天》:“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尚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 黄诗直接引原句至自己的诗中。吴绮《渔父家风过西塞山访张志和旧隐不得》:“鳜鱼春水旧迢迢,有客泛兰舠。而今事往无人问,花落大夫桥。” 吴诗更是访遍旧址,以求先人遗风。数不尽的文人墨客受到西塞山“隐逸”的精神感召,在不断的化用、 借引之中,西塞山成为了一种文学原料、 文学资本,让作家不自觉地靠近、 模仿、 丰富。西塞山也在文人墨客一代代的传承与发展中,逐渐经典化,成为湖州的一个标志性的地理文学坐标,作为一种文学资本,显示出了其独特的价值和影响力。
随着张志和《渔父》的流传,“西塞山”在文学创作中被重新选择与解构,成为诗词中江南鱼米之乡的代表,其地理指向也由湖北黄石移至浙江湖州。清代词人查慎行的《瑶华慢》:“……矶边小作迟留, 向香火荒祠, 笑问渔父。鳜鱼肥美,算只在苔霅, 溪山深处。生前好事, 多著了, 清吟几句。又分得, 西塞山前, 别派斜风细雨。”西塞山不再以湖北黄石高耸险峻之境而为人所知,人们印象中的西塞山,就在烟雨朦胧的江南。西塞山这个普通的地理名词,因为文学创作的变化而发生地理位置的流变,并最终成为一种文学资本而被广泛使用,这恰恰体现着地理名胜作为一种文学资本与创作之间双向互动。可以这么说,曾经概念模糊、 指向不清的西塞山成为文学资本而流传下来,依靠的是极具影响力的创作,而自从这一地理名词文学化、 资本化,便作为一种极具人文内涵的素材,不断丰富着后人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