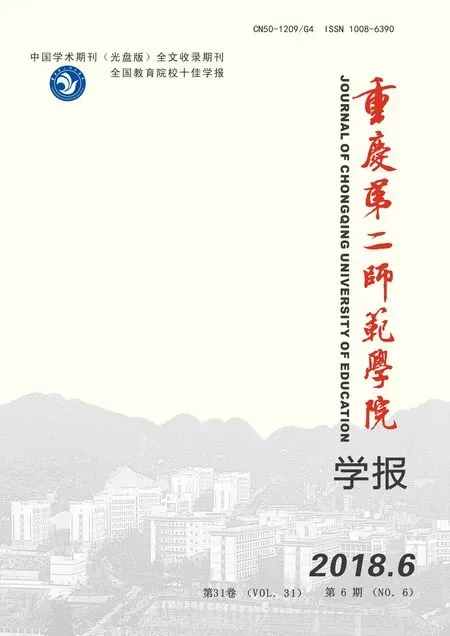明代笔记小说中梦的类型、特点及其思想内涵初探
2018-12-06付娜
付 娜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中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有关于梦的记载,《诗经·小雅》之《斯干》:“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1]546通过梦之对象“维熊维罴,维虺维蛇”来占卜推究吉凶情况。先秦时期人们对于梦象非常重视,故而设立占梦官之职。《尚书》明确记载了因梦来指导君王政治的实践活动,如《说命》:“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2]363-364孔颖达疏:“殷之贤王有高宗者,梦得贤相,其名曰说。群臣之内既无其人,使百官以所梦之形象经营求之于野外,得之于傅氏之岩,遂命以为相。”[2]364可见,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将梦与社会生活实践密切结合,且带有宗教的神秘色彩,甚至具有某种神启意义。而真正借助梦来构建颇具文学气质的寓言则是《庄子》的“庄周梦蝶”。傅正谷评价说,“庄周梦蝶”“表现了他的哲理性散文的独特风格,开创了中国古代梦文学的先河,从而使之成为中国梦文学的卓越先驱者”[3]24,并将庄子誉为“中国古代梦理论的奠基人”[3]14。自此之后,历朝历代以梦构建小说故事的作家作品很多,如唐传奇中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等便是典型的以梦为主体构架,阐发人生如梦思想内涵的作品。这类梦故事既与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又有文学作品的奇幻色彩,同时还寄托着世人的生活情思和人生愿望,颇受历代文人墨客青睐。因此,以梦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从未衰歇,一直延续到明清之后。本文以明代笔记小说为例,对其中的写梦作品进行裒类分析,揭示其特点,并对与之紧密相连的明代社会文化思想进行探析。
一、明代笔记小说中梦的类型及特点
(一)应举梦
明代是科举取士发展的鼎盛时期,明太祖建朝之初就曾发布诏令:“使有司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4]1695又于洪武三年发布诏令:“使中行文武,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毋得与官。”[4]1539至洪武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4]1696。明太祖下达诏令使科举成为永制,规定为官之路,只有科举一途。对于统治者来说,科举确是有效维护政治秩序与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政策,故君王对此也格外重视,应举之事也多有所梦及。《双槐岁钞》卷三《驾驭文武》:“文皇帝夜梦十三人共扶一殿柱,又一马遍身生麟。第二日引见举人,而麟居首,故有是命。”[5]143文皇帝梦中马身生“麟”与科举士人名“麟”相联,读来颇为奇异,从侧面可见统治者对于科举的关心。又如《双槐岁钞》卷二《国子试魁》:
先一夕,上梦殿前一铁钜钉掇白丝数缕,悠扬日下。觉以语左右,莫知其为何祥。及拆状元卷,乃花纶也。上嗛其不叶梦,取第二人为首。已而得丁显卷,姓名与梦相符,遂擢为状元,显时年二十八,子宁次之,纶又次之,三人皆拜修撰。[5]119
本来中状元的是花纶,皇帝为迎合梦境,却将丁显擢为状元。显然,小说显示出皇帝对于梦之神秘权威的服从,认为是冥冥天道的意旨,为了迎合天意,故而“取第二人为首”,可见其将科举士人的取用与天意进行联系。这也说明,对于君王而言,应举之梦带有某种神秘的天意启示,科举成为顺承天意并显现出来的现实承担。而对于应举的寒门士子来说,科举则是他们唯一的显达途径。
王玉超在《明清科举与小说》中说:“明清开科次数有限,取中的数额亦有限,但每次参加科举的人数却成千上万,故此,明清时人常常把科举比作‘独木桥’,足见其得以取中的难度和几率的低微。”[6]73正因为是“独木桥”,天下士人对应举一事便格外揪心,其梦中也多出现为官中举之事。《施槃应梦》:“己未殿试毕,夜梦一棺,己行其前,以手按之,后有百人随而号哭。”“时取进士止百名。其梦颇应。”[5]347通过梦中百人随而号哭,预示了自己是一百名,而当时恰好录取一百名进士。《酌中志》卷七《易水生》:“乙未春试前一夕,有举子梦见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之入试,试目一纸,有‘晋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飞不定。与易水生争逐之,为彼先得。及入会场,第一题是司马牛问仁章。”[5]3264通过梦预知了自己的考题。《客座赘语》卷十《卢玉田过湖续梦》[5]1455通过梦中的诗句预示了自己官居何位。《双槐岁钞》卷七《登科先兆》中“千户林兴”[5]207通过梦预兆了其应试名次。《庚巳编》卷二《柴驿丞》:“予昨夜梦一白须老人云:‘明日有五举人至此,中一绿衣者是汝异日恩人,慎毋慢之。’予是以不无少望耳。”[5]634《菽园杂记》卷六也写了孙状元会试途中借宿民家,其主人在前一夜“梦状元至,故治具以俟”[5]427。此外,《涌幢小品》卷二《讲书职分》[5]3154、卷七《名先状元卷》[5]3271等都是通过梦的形式,预先告知士人应举结果。
不难看出,士人的应举梦之所以如此丰富,正是其心系应举的具体事项,如名次、考题、贵人提携等。如果说君王之梦的特点是与神秘的天意相关,那么士人应举梦的特点则是更注重应举的具体内容,具有明显的功利性。
(二)感生梦
感生思想最早可见于《诗经·商颂·玄鸟》篇,其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1]1140带有隐约的感生思维。《大雅·生民》篇有“厥生初民,时纬姜嫄”,郑笺云:“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而生,于是遂有身体。”[1]800其感生思想格外明显。钟肇鹏在《谶纬论略》中说:“感生就是认为帝王和圣人都是自天而降,从天上来到人间进行统治和教化。一般人都是由父母所生的,帝王圣人则是感天(上帝)而生。”[7]99可见,感生是一种由上天降临人间并带有某种神秘的政治意蕴,被赋予了某种天然的权威。其实,感生思想在历代帝王将相的传记中并不少见,其目的无外乎神化某个人物,赋予其天命所归的神圣感。这种感生思想在明代笔记小说中也有充分体现,小说主人公往往感梦而生,通过梦中预示或灵异事迹显现而生,表现出统治者乃是“承天之命”。如《双槐岁钞》卷一《圣瑞火德》:“初,皇考仁祖淳皇帝居濠州之钟离东乡,皇妣淳皇后陈氏尝梦黄冠馈药一丸,烨烨有光,吞之,既觉,口尚异香,遂娠焉。及诞,有红光烛天,照映千里,观者异之,骇声如雷。”[5]99对此,作者在小说末尾评道:“帝王之生,必有圣瑞,章章如此。”[5]99显然,感生梦神化了帝王,赋予了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再如《涌幢小品》卷四《母后奉迎》:“生时母梦仙妃渡水,踏一鱼,乌金色,落其家,人以为瑞云。后尊为章圣皇太后。”[5]3221不难看出,这两则故事都记述了帝王感生的故事,无外乎神化其人,背后不过是“承天之命”的思维套路。这样的传统始自汉魏时期谶纬的流行,从汉武帝刘秀到王莽夺权,都用这样的伎俩以保证“江山稳固”。
明代笔记小说中的感生梦除了蕴含政治权威的因素外,还对感生之人进行了道德评判,这无疑赋予了感生思想新的特点。《庚巳编》卷三《梓潼神》:“是夜,梦神人告之曰:‘翁好善如此,当获福报。吾梓潼神也,将降生以大而门。吾在胥门线香桥人家楼上,其家不知奉事,翁今速往迎归尔。’既觉,语其妻,则妻梦亦如之。”“未几有姙,生僖敏,仕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累赠翁如其官,母为一品夫人云。”[5]644在这则笔记中,作者认为其感生入梦的原因是“陈僖敏公镒父孟玉,为人愿悫,乡闾称善士”。可见,神人感梦的标准是“善”,也就是仁义有德。再如《涌幢小品》卷十六《曾孟》:“孟子生时,其母梦神人乘云自泰山来,将止于峄。母凝视久之。忽片云坠而寤。时闾巷皆见有五色云覆孟氏之居焉。”[5]3474可见,明代笔记小说中的感生思想除了神化政治权威外,更有对民间道德修养的关注,其感生不再是帝王将相的专用套路,而是对百姓的道德嘉奖。这无疑也是士人在书写传奇小说时将塑造政治权威的天命所归思想转向对民众道德仁义的关注,实则也是将作者的道德情怀投射于人间民众。这些故事通过描述普通人降生时其母的梦境,体现其非凡天命。
通过明代笔记小说中的感生梦,我们发现,由帝王垄断的感生神话主题在明代已经出现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可见其世俗化的历史进程,也可看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道德因素评判。
(三)魂诉梦
《论衡·纪妖篇》“人之梦也,占者谓之魂行”[8]441,认为人做梦时是灵魂在游行即活人可以通过做梦的形式与阴间亡灵进行会通,故而阴间亡灵亦可通过梦这一通道来向人间提出诉求。明代笔记小说中的魂诉梦,就是叙述阴间亡灵以梦为媒介沟通人间,将自己的不平遭际诉诸人世。《涌幢小品》卷十二《冯小二》:
衡阳有少妇秦氏,孀居,有姿色。姑欲嫁之,不听。邻少年冯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间。因计毒其姑,佯为助丧,求与妇合。妇大怒,飞石中之。因讦妇有所私,为姑所禁,置鸩焉,陷于辟。有管思易者,鄞人,以恤刑至,疑之。夜梦老妇牵一马,泣诉曰:“马实杀我,非妇也。”遍求马姓者,不得。视邻右尺牍有冯小二,忽悟曰:“是矣。”遽呼询之,立承。妇遂得释。管后与尚书吴中争狱,不胜,愤而卒。[5]3388
在这篇笔记小说中,冯小二因贪图少妇秦氏美色而设计毒杀其姑,假意助丧而求其合,被秦氏拒绝,并以飞石击之。冯小二则怀恨诬陷秦氏鸩杀其姑。其姑托梦于管思易,告之杀人者乃冯小二。其中,秦氏之姑正是通过梦这一形式向刑狱者管思易倾诉其不白之冤,尽管其冤屈最终没能大白于世,然毕竟能将亡灵冤屈告诸人世。《双槐岁钞》卷五《冤魂入梦》:
戴谦为南京御史,梦骑马至清江厂,有朱衣引一人索命,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曰:“盍往观乎?”即前导,所过皆竹房。至一家,独瓦屋,入门,有男子卧地上,一妇人绿衣、红裳、簪花,处其傍,曰:“欲救之,奈气绝矣。”惊寤,出水西门,至清江厂,物色得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梦中所见,呼其家问之,乃因市肉与屠人斗而死。告以所梦,举家皆大哭。[5]179
李姓朱衣者因与屠人斗殴而死,心有不甘而入梦御史戴谦,申诉其遭际。文中虽没有写到御史戴谦为其主持公道,但可想见李姓朱衣者的不平遭际已得到世人关注,心中冤屈得以大白于世。此外,还有已死之人沦为动物而托梦于家人,借机表达其心中愤懑。如《双槐岁钞》卷十《沈阳鸡异》:
河间沈阳中屯卫前千户胡泰,母死已十年,父亦再娶。弘治己酉,明日,泰偶出,果有荷米食及鸡至者,即欲烹鸡饷之。鸡人言曰:“毋烹我,且待泰儿回。”家人大惊异。及泰回,绕身喃喃,叙及家事。泰告父以梦征,乃畜不杀。后益作孽,飞啄后妻面首。且自矜存时干创艰难,今家业日耗,皆夫纵后妻之故。诟詈不已,远近闻之,借观者众,泰拒不纳。无何,后妻逐入炕下,扑杀之。考诸《五行志》,近鸡祸也。[5]273
胡泰之母因愤恨丈夫后妻耗败家业,于是托梦于儿告之她已化为雌鸡,要求儿子收养之,以便她将心中愤懑发泄于后妻,“飞啄后妻面首”。另有鬼魂托梦有求于人之事,如《菽园杂记》卷九:
至元甲午,吉宜人将就馆,其姑施夫人疾病,叹曰:“吾妇至孝,天且赐之佳子,吾必及见之。”既而疾且亟,治后事,其大父卜地阳抱山之原,使穿圹以为藏。施夫人曰:“异哉!吾梦衣冠伟丈夫来告云:‘勿夺吾宅,吾且为夫人孙。’ ”既而役者治地深五尺,得石焉,封曰“太守陆君绩之墓”。别有刻石在旁,曰“此石烂,人来换” ,石果断矣。其祖命亟掩之,而更卜兆地。夫人又梦伟衣冠者复来曰:“感夫人盛德,真得为夫人孙矣。”德润生,其大父字之曰顺孙,而施夫人没。人以为孝感所致。[5]460
在这则梦故事中,施夫人梦见衣冠伟丈夫请求她不要将墓地建在他的墓地上,他作为报答将会降生为其孙子,记述了鬼魂有求于人,人满足其愿望后,报恩于人。
在这类笔记小说中,阴间亡灵可以通过梦沟通阴阳两界以申诉其不白之冤、不平遭际,并以某种方式作用于人世,其鬼魂形象亦全然没有惊悚之感,反倒如寻常人一般知恩图报。可以说,魂诉梦典型地体现了明代百姓对于鬼魂的知性态度。
二、明代笔记小说中梦的思想内涵
(一)宣扬劝善惩恶的伦理观
关于善恶的劝惩观念,最早可在儒家经典《尚书·汤诰》篇“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2]297中窥其源本。不过此时针对君王统治者,其中带有“敬天保民”的政治道德色彩。在道教典籍《太平经》中,颇具佛教善恶报应色彩的承负说也得以理论化构建:“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能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之功,来流及此人也。”[9]91《佛说未曾有缘经》言:“施善善报,施恶恶报。”[10]663可见,因果报应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其理论融合了儒释道三教,深入人心,广为传播。
善恶报应观念在明代笔记小说中有着诸多体现,人物的福祸遭际由其自身的善恶行为决定,并通过神人喻示获得福报或灾应。《庚巳编》卷三《梓潼神》讲述了因陈僖敏公的父亲孟玉为人朴实善良,生活极其节俭,故而在梦中得遇梓潼神,梓潼神感其善德,降生其门而为陈僖敏,仕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累赠翁如其官,母为一品夫人云。因陈家为人善良、朴实节俭受到神灵保佑,光耀门楣。《都公谈纂》卷上则记述了孝子苏叔瑜坐船送母亲骨灰回乡,“忽江涛怒激,舟欲覆”,于是下船行山路,“越三日,梦一叟语之曰:‘江行不危,无恐也。’”[5]548,也因为其孝心而梦得“叟语”,遂平安渡江。又如《涌幢小品》卷十七《与伞》记述了慈人冯景茂尝下乡督农,中途遇骤雨。有一妇哀求附伞。冯不忍妇女被雨打湿,委伞与之,自己跳入了民舍。其后他自己割田建设了一座避雨亭。夜梦神语之曰:“尔有阴德。与尔三银带。”[5]3509这三则笔记小说无疑都体现了善有善报的思想,表达了百姓朴素的道德报应观,具有强烈的劝善倾向。佛教为了拓展其在民间的影响力,往往制造各种报应以自神其教。如《都公谈纂》卷下记载了因为杀生而死的故事:
阊门人陆某,尝夜梦皂衣者四人至其家,再拜乞命。明旦,忽有人持四鳖来馈,陆笑曰:“昨宵之梦,其殆汝耶?然吾必欲食汝,不能释也。”竟烹食之。不二日,疽发于背,诸药莫疗而死。[5]576
佛教讲究“众生平等”,提倡素食,而陆氏为满足食欲而杀生,就遭到了“疽发于背”而死的报应。现在看来,此则小说粗暴地宣扬佛教报应,多有“自神其教”、恐吓世人的意味。毕竟吃荤就要置人于死地,实为更大的不道德。
由此可见,在明代笔记小说中,借助梦的形式将世俗的是非善恶进行展现,以某种神秘的报应来宣扬民间的伦理道德,一方面强化了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另一方面这种宣扬的方式难免带有粗暴的恐吓色彩。
(二)阐扬命皆前定的命运观
宫宝良在《术数与明清社会》中探讨民间命运观时曾说:“社会上普遍有着命定论的思想,并且深入人心,认为世间万物皆有‘定数’‘气数’,‘生死由命’‘成事在天’‘在劫难逃’。”[11]257明代笔记小说中就有很多篇目体现了这种“命皆前定”的命运观。《庚巳编》卷七,浦应祥经常梦乘肩舆行,而其前有一僧舁之。等他做了官,梦境居然在现实中出现,他禁不住感叹:“兆于三十余年前,人生得丧,岂偶然哉。人生福禄有限,神已在前梦中明示,而人不可知。”[5]674三十年前的梦境已然透露其今后的人生际遇,其命运定数在冥冥之中得以呈现。《都公谈纂》卷下“俞公易颔”一则,讲述了俞公士悦初生一月时颔患疳,脱去颔骨,母夫人甚忧之。一夕,梦神人谓曰:“儿后大贵,吾为易其颔骨耳。”俞公因得到神人易颔骨而得以“大贵”。俞公士悦儿时的“易颔骨”竟然注定了其后的“大贵”,可见小说透露出一种明显的“命定”思维,即一个人的显贵来源于某种神异的显现。再如前述《菽园杂记》卷六中记载了孙状元在会试途中,借宿民家,民家早已在梦中梦到有状元来借宿,所以一切都准备得很好。小说作者在其后评论道:“观此,则人之出处,信有前定,非偶然也。”[5]427又如《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八,方袁为长史时,一日昼寝,梦一美姬扶床。后世宗怜宗皋老,赐以宫婢六人,则有梦中之美姬。作者在其后评论道:“神已先示,则其福祚有限可知。”[5]2656《涌幢小品》卷十四记述了家父一晚三次做梦升官,作者在其后议论说:“神先兆之,想数有不可逃者,亦何用怼且悔也。”这些故事都体现出了命皆前定的命运观。

(三)展现人文至上的鬼神观
宫保利说:“明清社会上有着非常强烈的鬼神观念,整个社会普遍存在鬼神信仰。”[11]265即便如此,这也绝不是说人们处于对鬼神的虔诚膜拜状态,鬼神拥有对人间的绝对权威。事实上,由于梦这一特殊的沟通桥梁,鬼神与人拥有了平等的交流地位,人的自主独立意识与尊严也得以凸显,在明代笔记小说中,鬼神反倒处于弱势的状态。如《都公谈纂》卷下记载:“嘉兴焦通判,生子病疹,祷于城隍,不效,击败神鼻。”他的妹妹为王妃,夜梦城隍诉破鼻之事说:“此人凶恶,吾不敢犯。”故事中的神拥有人的性格,神竟然怕恶人。在故事后作者也嗔怪“鬼怕恶人”。再如《庚巳编》卷二中记述了鬼神以梦为媒介向人告状的故事:“昶自御史谪官福之古田,一日,私廨失所畜鸡,寻之乃在神前,舒翼伏地如被钉者。以问舆皂辈,皆言神以久不祭,故见谴耳。”于是,昶想要毁掉神祠,夜晚,梦见神来谢罪:“予血食于此者累年,不敢为过。昨日鸡被钉,乃鬼卒辈苦饥,故为之,非予敢然也。公幸怜之勿毁。”在这则笔记小说中,神害怕自己的神祠被毁反倒向人祈求。可见,明代人们对鬼神的敬畏程度降低,鬼神已不再让人恐惧,而其鬼神形象也颇具世俗人格特征。不仅如此,神灵甚至还入梦来帮助官员判案。如《涌幢小品》卷十九《断狱》:
归震川先生令长兴,好谭文,于听讼非所长。有乡豪与媳奸,为仆所见,挥刀杀之。知事不可掩,入室,取一婢杀之,提二首赴县。告以获之奸所,欲脱己罪。遇大雨沮城外。其夕,先生梦城隍神告以杀死本末,先生辰坐堂上。其人携二首奔入,未及言,先生大呼曰:“贼贼,汝杀人。”如是如是。遂伏罪,众咸以为神。自后无敢欺者。
再如《涌幢小品》卷十二《神断》:
伍典为柳州太守。州民钟钮,其叔自他所,贻书钮,携囊金市产,钮堕其计,至中途,叔与伙贼扑杀钮。携其囊金去,不可踪迹。妻讼之官,且祷于神,谓事必下,公始得决。已而南宁道果以属公,檄至,公得钮妻所上叔所贻书,方思为之计,神忽见梦。公因策梦中语,谓事当起于僧人。因于府治白石山结僧堂一区,令方僧至者率舍其中,各写经凡几。已而得一僧,所写经字与钟妻所上书适类。又因诘其祝发岁月,正与杀钮时合。乃令钟妻遣仆觇之。众僧中果一人如钮叔,指以示,即公顷所诘问僧也。杖之吐实,遂伏辜。
以上两则都是神灵通过梦告诉审案者事件的原委,从而解决现实问题。可见鬼神在明人思想观念中并未处于一种绝对的权威状态,人们对鬼神的信仰更多来源于百姓日用的人文世界,鬼神形象也颇具人格化特征。
无论是鬼神害怕人,抑或帮助人间处理案件,这种鬼神服从人间世界的思维,无疑反映了明人对鬼神观念神秘化的消解,而这种将鬼神在世俗中的平庸化,代表着明人“人文至上”的鬼神观。
三、结语
明代笔记小说所写之梦主要可分为应举梦、感生梦和魂诉梦。其中,应举梦包括君王之梦和士人之梦:君王之梦关联于冥冥天意,带有神秘性;士人之梦则更注重应举的具体内容,具有明显的功利性。感生梦除了蕴含政治权威的因素外,还对感生之人进行道德评判,这无疑赋予了感生思想新的特点。魂诉梦则以梦为媒介沟通阴阳两界,让鬼魂将自己的不平遭际和诉求告诸人世,并作用于人间。通过对这三类梦的思想内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其整体上宣扬了劝善惩恶的伦理观、命皆前定的命运观和人文至上的鬼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