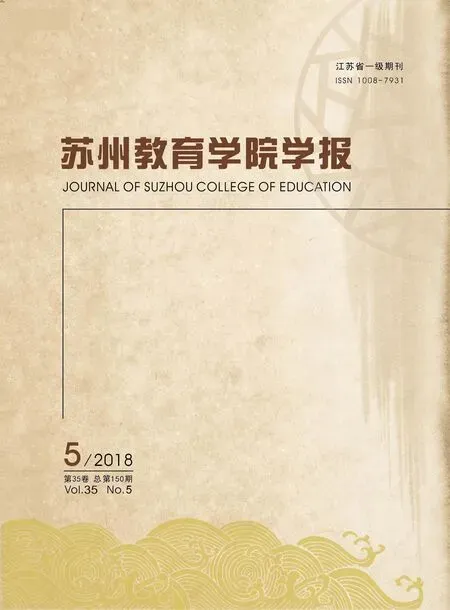栏目特邀主持人:龚 斌
2018-11-20龚斌

主持人语:本期刊出的四篇陶学研究论文,多涉及陶渊明接受史上出现的问题。
严明、周晓璇《明清陶诗争议之辩》一文评述和分析陶诗在明清诗坛引起的两次影响较大的争议。明“前七子”何景明说:“诗弱于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于谢。”提出所谓“诗弱于陶”的命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观点?本文以为这是明人以严羽为诗学圭臬,恪守辨体论诗的方法,将陶诗置于汉魏古诗的发展流变中加以考辨所致。明“前七子”的文学审美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崇尚雄伟刚健的美学风格。然文学审美风尚是时代性的,审美尺度随时代而变。中国诗歌自汉之后的流变,与时代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汉魏古诗与六朝诗风各有面目,思想与艺术的价值虽异,但其流变都有必然性,各有各的美学价值。本文以为“明代诗人并未能看到陶诗的独特价值,也没有认识到陶诗是晋朝文学中的一种独有表现,具有巨大的诗学价值”。这一看法是中肯的。稍嫌不足的是,何景明称“诗弱于陶”之“弱”究竟指什么?何以称陶诗“弱”?陶诗与汉魏诗的美感有何不同?所谓陶诗之“弱”,在魏晋诗歌流变史上究竟有何意义?如对上述这些问题加以分析辨明,则本文说理会更充分,更有价值。
刘中文《陶渊明“达道”之历史解读及辨议》一文,详细解读并评议陶渊明之“道”。陶渊明之“道”的内涵是陶学的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也是陶学史上持久争论的问题。本文全面梳理古今贤达对陶渊明所达之“道”的解读,并分别作理论辨析与评议。关于渊明“达道”或“不达道”之争,缘起于杜甫《遣兴》诗:“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必挂怀抱。”这本来是杜甫读渊明《责子》诗后的戏语,意思说渊明有五子,皆不好学,儿子的贤与愚,何必挂在心上?杜甫戏称的“达道”之“道”,显然属于道家之道。苏轼喜陶诗并推崇陶渊明之为人,深信渊明是达道之人。明人都穆《南濠诗话》说:“东坡尝拈出渊明谈理之诗有三,一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曰:‘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三曰:‘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皆以为知道之言。”苏轼举出的谈理之诗三首,一是表现自然之趣,二是享受得生之趣,三是说委运任化,不以生死挂怀。本文以为苏轼理解的陶渊明的“知道”,此“道”乃属于道家之道。这是正确的。关于陶渊明“达道”与否,以及“道”的具体涵义,正如本文所说,实际上是涉及陶渊明的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是陶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千余年来争论不已。概括言之,不外三种看法:一为道家,一为儒家,一为儒道释杂糅。其中,称道家者为多,儒家者次之,而称受佛教影响较少。事实上读陶诗及观渊明之为人,儒、道两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为纯是道家或纯是儒家,未免都是偏颇。至于葛立方称渊明为“第一达磨”,确实“应者寥寥”。近代论陶渊明思想,以梁启超、陈寅恪、朱光潜等人为最重要,其中尤以陈寅恪所论影响最大。他说渊明思想为“新自然说”,不同于旧自然说重养生,学神仙之术,而是委运任化,与自然合一。“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本文详细辨析关于渊明思想的各派观点,尤其重点辨析了陈寅恪的“新自然说”,认同朱光潜对陈寅恪的质疑。文章分析朱光潜论陶的用意:一是否定陈寅恪的研究方法,称陈氏把渊明看成“有意”皈依新自然说,这完全有悖于陶渊明“不求甚解”的任真、率性的性格。二是朱光潜认为陈氏说渊明“外儒内道”,其要旨在证明渊明“是道非儒”。称陈氏“不但过于系统化,而且把渊明的人格看得太单纯,不免歪曲事实”。朱光潜质疑陈寅恪是“是道非儒”,此点可以讨论。“外儒内道”之说,是儒、道有内外之用,似乎推论不出“是道非儒”的结论。关于陶渊明是否受到佛家的影响,也是研究者颇有分歧的问题。陶诗中词语有“冥报”“空无”,诚属佛家用语,有人将之作为渊明受佛教影响的证据。更重要的是渊明的诗有“禅趣”,这就成了渊明受佛教影响的最有力证据。其实,佛教的“禅”是六世纪才正式出现的。早在晋初的玄学家清谈(如乐广),以道家得意忘言说谈玄,与后世的禅机很相似了。但我们不能说他们的清谈即是佛教的禅机。东晋时代佛教广为流布,但它先前是依附玄学的,而不是相反。弄清这样的事实,也许对评价渊明是否受佛教的问题有所帮助。总之,本文详细梳理了陶渊明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渊明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儒、道、释的关系,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认为明末高僧紫柏大师与清人钟秀都强调从“心性”入手、消除哲学与宗教各派别的畛域来解读陶渊明的“道”的方法尤为可取。又以为“陶渊明的贡献就是用生命论证(或曰践行)了郭象‘儒道会通’的独化论玄学,亦即用生命论证了郭象‘儒道会通’理论的可操作性”。不过,如何用“心性”来解释渊明的“道”,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本文虽提出了但未进一步申论。
贺伟《〈文选补遗〉所录陶渊明诗文考论》介绍陈仁子《文选补遗》的增补陶渊明诗文的篇目、收录的来源、注释的参考等内容。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宋元易代之际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南宋遗民处于历史的巨变中,太需要陶渊明作为精神寄托。陈仁子编辑《文选补遗》,当受苏轼的影响。苏轼批评萧统《文选》“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陈仁子《文选补遗》大量收录陶渊明作品,正是南宋遗民暗怀故国之思,以隐居不仕,坚持民族气节的反映。本文经过比照,以为《文选补遗》中的陶渊明诗文,主要据元李公焕本,同时参考了绍兴本、汤汉注本。这是非常合乎事实的结论。又认为作为南宋遗民的陈仁子,在宋亡后隐居茶陵东山,不仕元朝,这种政治态度决定了他必然赞成汤汉对陶诗的解读。汤汉以“忠愤注陶”著称,《文选补遗》中引用不少汤汉注语,其原因还是在于陈仁子的遗民身份。又指出:陈仁子还对某些陶诗篇目加以阐释,进一步发挥陶渊明不事二姓的政治节操。这都与编者的政治态度有关。
李寅捷、李剑锋《试论龚鼎孳对陶渊明的接受》探讨明清之际著名诗人龚鼎孳对陶渊明人格的仰慕及其深层原因。自宋以后,陶渊明成为高尚道德和节士人格的高标,其文化价值超越时代。许多文化名人,大谈陶渊明的隐士风采,以及不仕异姓的高洁品格。知识者慕陶、效陶、和陶成为突出的文化现象,久盛不衰。苏轼不惟好陶诗,而且好陶渊明之为人,作和陶诗一百余首。后世文人踵武东坡,作和陶诗者不计其数。尤其在宋末元初及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归隐的人生选择以及后来不仕刘宋新朝的节操,获得广泛的仰慕和赞叹,成为许多遗民的精神寄托。本文论明清之交的龚鼎孳对陶诗的接受,解释一个“贰臣”,一个家财万贯的富翁,为何作诗赞扬陶渊明的归田,赞扬他不仕刘宋新朝的洁身自好?又为何和陶渊明的《咏贫士》诗?上述问题是值得探究的。本文作者认为:龚鼎孳趋同遗民群体,诚心帮助遗民,得到舆论的谅解;龚不可能走归隐之路,诗中流露的归隐之意只是“缓解尘世压力的方式”,“求得灵魂净化”。又认为龚作《和陶公咏贫士》诗,借以净化自我,“守贫精神却成为他精神栖所”。本文探讨龚鼎孳对陶诗的接受的时代原因及个人的心理因素,应该说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借此可以提供人性复杂的有力证据。毫无疑问,文学与人性的关系十分复杂。“文如其人”固有众多例证,但文不如其人,或为人为文正好相反,也不乏其例。大体而言,以文衡人,远不如以人衡文来得可靠。龚鼎孳二次作“贰臣”,与陶渊明的归隐不仕的高洁品格有泥霄之别。况且,杜浚曾屡劝龚鼎孳退隐,龚却依然作“贰臣”。如果龚果真把“陶渊明固穷守节的精神就成为他的精神依托”,则龚辞官归隐并非不能做到。所以,若以为龚鼎孳真把陶渊明的归隐或固穷守节作为“精神寄托”,“视作理想”,恐怕要细细斟酌了。另外,文中称陶渊明“任真”的“包容性”,如何界定“包容性”的边际,也是要严肃考虑的。自宋之后,随着陶渊明地位越来越崇高,作和陶诗者甚多,诗文中仰慕、赞美陶渊明者更多。各色人等仰慕陶渊明,写诗向往隐逸,向往闲适,似乎非如此不足显示自己的文采风雅,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非常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