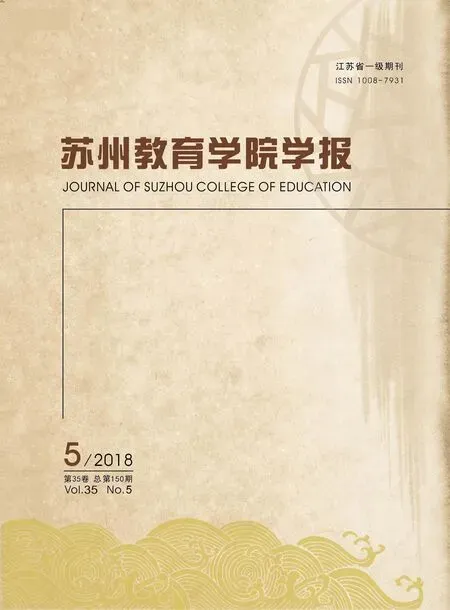世界主义语境下“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反思和探寻
2018-04-03杨丽莉
杨丽莉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何谓“他者”?从来源看,“他者”有着悠久的哲学渊源,在不同的哲学语境下有不同的内涵。围绕“自我”与“他者”这一核心主题,大致有如下几种内涵:胡塞尔的现象学中由“先验自我”建构的“他者”;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具有侵略性的、构成主体性的“他者”;福柯的权力话语建构下的从属性“他者”;列维纳斯的优先于自我的伦理学“他者”—这些哲学内涵都反映出“他者”的差异性特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单一地使用固有的“他者”内涵无法充分表达“自我”与“他者”之间日益复杂的关系,也难以满足世界主义对于“共同理性”的憧憬。随着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媒介形式的不断更新迭代,我们与“他者”的交往形式也发生了改变,在此全新的境遇下,挑战与机遇并存,我们需要从不断生成的“自我”与“他者”这个角度,重新审视自身的主体性身份。
一、陌生人社会
现代境遇下“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出现了哪些变化?从社会领域中人与人的关系角度看,伴随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张、人口流动速度的增快,陌生人社会的逐渐形成,成为我们与“他者”交往的新环境。涂尔干在研究现代人的生活境遇时指出:“个人主义、流动性和城市化的兴起创造了一个以匿名和失序为特征的陌生人社会。”[1]36无论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国际移民,还是旅游业的快速发展,都使我们与陌生人相遇的概率大大提高,以孤立的个体面对异己的“他者”。随着这种转型的推进,个人的疏离感、异化感随之而来。
大都市的街道是构成陌生人社会的一个独特空间,无论是纽约、伦敦,还是东京、上海,街道上人流涌动。无论是我们对于“他者”,还是“他者”对于我们,都是无名的、不可理解的。如托马斯•德•昆西在伦敦街道上体会到的感受:“他站在往来人流的中心,这些面孔穿梭不停,不与他交谈一词一句;无数双眼睛,瞳眸间却没有能读懂的东西;男男女女匆忙的身影交织在一起,于陌生人而言却是谜一般的存在。”[1]59我们与“他者”之间没有时间的羁绊,也没有记忆的勾连,只有此时此刻在此空间里的短暂相遇,与“他者”的疏离感在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空间中被强化。在世界主义视野下,地理上的边界日渐模糊,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将人类纳入全球共同体中。在此语境中,人类的关系似乎应该更加紧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陌生人社会中人们的疏离感与日俱增,出现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的两级分化,“家庭变得越来越私人化,而劳动组织世界则变得越来越‘公共化’了”[2]。
陌生人社会是如何在“公”“私”极化的过程中加剧人们的疏离感的呢?在“公”领域,首先,陌生人社会的形成是由于地理空间上的障碍不断被消除,全球性的社会公共空间不断扩大,在跨国旅游、国际性商务工作以及互联网社交媒介中,人们不断遭遇陌生人,疏离感不断滋生。其次,我们看似被社交软件、电视电影等全球流通的商品所整合,同时却付出了生活方式统一化、标准化的代价。不同于囿于地理空间而凝聚在一起的大家庭,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以渐趋单一化的生产、消费模式联系在一起,这种看似密切的抽象联系,反而加深了人们之间的隔阂。在“私”领域,我们在陌生人社会中与“他者”的交往显示出更强的目的性。因相遇的短暂、匿名,现代社会的交往更趋向于哈贝马斯所说的戏剧性交往,“就戏剧行为而言,我们把社会互动看作是一场遭遇,在遭遇的过程中,参与者构成了透明的公众,并且相互展示”[3]。在这种展示中,我们不自觉地会强化自我的意向。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维持生存的生产活动是与家族紧密相连的,交往圈稳定,因此人们在工作、生活各方面的表现都呈现出一致、稳定的人格。而在陌生人社会中,我们与“他者”的交往活动充满着偶然性与不确定性,频繁的短暂相遇激发了人们的“表演性”人格特征。
詹姆斯•弗农认为,“表演性”人格中有着极为强烈的自我塑造与自我表现的倾向,“风靡一时的化妆舞会就可以根据以上解释,被理解为在陌生人人群中完成自我表演的一方舞台。”[1]72在面具的遮掩下,人们可以尽情释放自己想要展示的一面。在以匿名、陌生、转瞬即逝为特征的现代交往形式中,人们更趋向于向他人展示、表演、投射自我。抽象的交往方式与“表演性”的自我投射使得“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疏离感不断增强。
二、新的媒介形式
新环境下媒介形式的变化对“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认知、理解“他者”的媒介形式不仅是交流的途径,更是交流本身的一部分。全球化带来的媒介形式的更新、信息传播速度的激增,使传统上依靠地理区分的共同体向价值认同的共同体转变。从报纸到电视再到网络,新的传播媒介使我们与“他者”的交流呈现出更多的自我选择性,将人们“联接在一起的是一组具有相似性的观念和一套具有整合力的价值”[4]。也就是说,人们从传统固化的阶层中脱离,逐渐以个体的视角来认知、理解他者,并主动选择认同与自我价值观相契合的文化,当前国内青少年对欧美、日韩文化的热衷充分说明了这种认同的主动选择性。美剧《国土安全》在国内的走红,与作品本身所传达的理念,为这种价值认同的趋向性转变提供了例证。剧集聚焦于士兵布罗迪在国家英雄和叛徒之间不断游离的身份,质疑美国中情局为打击恐怖分子而发动战争的合理性,揭露以国家名义牺牲个人生命的残酷政治。该剧对平凡个体生命的尊重,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不同民族、国家的观众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归属感与认同感。
新的传播媒介同样也存在扁平化的弊端,使我们对“他者”认知的抽象性加强。从报纸、杂志、广播到电视、电影、网络,新的传播方式通过概括和提炼不同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使人们通过想象认识到“他者”。如布希亚德所说:“人与世界因为有了媒体而‘远视’的同时,看的方式却因为媒介的作用而被限定。媒体具有‘敞开’(呈现)和‘遮蔽’(误导)的二重性……复制和再复制使得世界走向我们,变得主观而疏离。”[5]新媒介缩短了我们与“他者”之间的距离,但也削平了深度。在跨文化交流中,这种抽象化的认知会强化我们对自我的投射,而忽略“他者”文化中的独特性,从而固化了文化间的差异性。究其根本,是因为全球化带来了信息的激增,人们在处理大量新信息的时候,不免会采取抽象化的方式来提高处理效率,而这会使我们忽略他者文化的独特生成背景与立体鲜活的多样性。
詹明信认为西方的个人与力比多的视角,无法与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产生共振,他以《阿Q正传》为例进行了分析:鲁迅对怯懦、巧滑、自欺欺人的“瞒”和“骗”的精神胜利法的批判,是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生成并服务于特定历史阶段的革命效果。詹明信颇有洞见地指出,在分析“他者”文化时,孤立、抽象、缺乏个人经验的分析只不过是一堆缩减所观物的主体的幻象,是“文化染上的心理主义和个人主观的‘投射’,……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物质条件是不具备西方文化中的心理主义和主观投射”[6]的。
在信息传播愈加便利、快捷的条件下,人们从地理联结的共同体转向价值观凝聚的群体,对“他者”认知的方式有了更多的选择,但同时使我们更易于陷入对“他者”认知单一化、抽象化的误区。
三、“影响—接受”模式的变化
世界主义语境下多元文化得到充分的发展,但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不容忽视,从该角度来考察“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可以发现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他者”的困境。以萨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框架下的“他者”形象,揭露出殖民地的社会意识与文化知识被西方国家的权力、意志、利益、愿望和想象所渗透。西方国家依照自己的需求来描述、塑造东方的“他者”形象,这是外化其内在欲望、归化“他者”的表现,旨在自我表征与自我实践。虽然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民族、国家间的文化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是单向的“影响—接受”模式,被言说的弱势的“他者”开始反抗西方所建构的、内嵌着权力关系的知识系统、文化体系,转而将“西方”作为“他者”,在质疑与批判中实现自我主体性的确立。
《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一书关注殖民地的人们处理宗主国的话语表征问题,是屈从、挪用还是反驳?面对被现代文明割裂的土地,被殖民者们的自我变得混杂而破碎。书中提到殖民地的本土作家对宗主国的旅行游记的仿写和滥用:“阿格达斯提出并且用当地的归来者更换非土著旅行者以及它们对他者性的轻蔑言辞。他就这样将普基奥从目的地变成了家园。对于新殖民地的现代主义者来说,去殖民化要求人们不是绕过而是穿越宗主国生产主体的话语。”[7]殖民地的作家其实是被迫以戏谑模仿的方式使用殖民者们的话语体系,从而以反抗的姿态来确立自我本真性存在的价值。
但这种以反抗西方话语体系的方式来确立自身主体价值的内在逻辑理路,与西方将东方作为被言说、被控制的对象来实现其统治权的逻辑有着相似之处。以“反西方”为内在核心,对话语体系进行本土化重塑,往往仍摆脱不了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与控制。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在讨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时,试图建立“本土心理学”来与西方理论形成平等对话,但理论基点仅仅是历史悠久、对心理现象的分析早有先例等单薄的论据,在方法上也多是套用西方的现成理论来分析中国本土的现象。真正对中国主体性的确认,对大国荣誉的恢复,建立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才是问题的关键,但目前尚未达到该目标。
在全球化背景下,“影响—接受”模式虽然被打破,但无论是西方所展现出的文化霸权控制,还是东方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反抗,都仍然暗含着以二元对立为逻辑起点,对其他文化实施同化、归化的内在趋向。将“他者”作为对立面,依靠压抑、矮化、排斥其他文化来获得内在价值的确认,这是现代性发展到这个阶段不同文化之间的真实状况。
四、不断生成的自我与他者
全球化为我们与“他者”的接触提供了便利,但各种潜在的交流困境依然存在,在这种境遇下,“自我”与“他者”的紧张关系如何改变?首先,面对陌生人社会和新的媒介形式,我们在与“他者”的交往中,不仅要怀着理解、包容的心态,还要提防自我同化“他者”的欲望以及自我目的的过度投射,走出这种困境需要我们时刻意识到“他者”不是我们实现目的的工具,而是世界格局中独特的一份子。其次,避免以平面化、抽象化的简单方式认知“他者”,借助全球化带来的便利进行具体而深入的交流,而不是堕入现代媒介的操控之中。最后,克服以二元对立为逻辑起点的交流方式,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需要我们拥有坚实的自我主体性并重视交流中的互动,从而走向不断生成的“自我”与“他者”。
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大同世界》中,以卡斯特罗关于印第安人非现代本体论为例,向我们展示“自我”与“他者”的不断生成性。美洲印第安人并未将动物、其他非人物种与人类区别开。不以自己的观念将外物当成被控制、被统治的对象来进行分类、整合,而是以生命的形式与外物共在,并在与其相处的实践中不断生成新的自我。印第安人与美洲虎的这种关系,与马丁•布伯的“我—你”之间不分彼此、本真性、非功能性的关系相类似,“那里生存先于存在,与他者的关系不再只是确立身份的方式,同时也成了实践的过程:成为美洲虎,成为他者”[8]。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归根到底要落实在我们如何理解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如何理解我们自己。在世界主义的视野下,跨文化交流成本的降低并不意味着交流中的偏见与误解会减少,所以我们要克服自我表征、同化“他者”的倾向,以包容、尊重、开放的视野看待“自我”与“他者”,在具体而深入的交流实践活动中,不断跨越文化的鸿沟,与“他者”共同实现“自我”的不断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