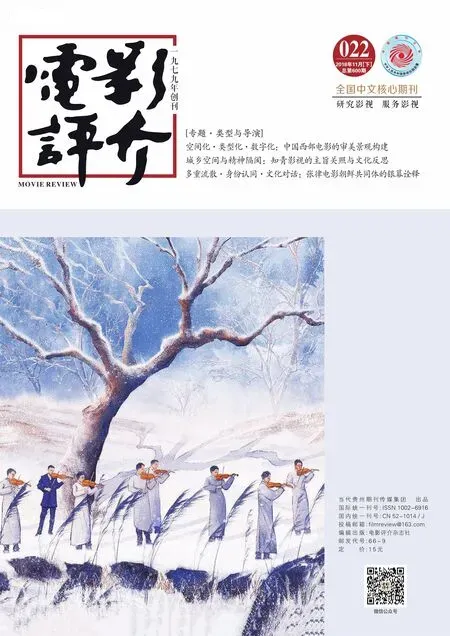空间化·类型化·数字化:中国西部电影的审美景观构建
2018-11-14
“西部”作为语境和空间,是西部电影的影像符号与文化内涵。“西部电影”从20世纪80年代命名发展至今,首先是以中国西部这一地域范畴作为界定,在电影创作层面,以“西部”的景观建构西部电影的空间美学和影像符码谱系,并基于此,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叙事和意义演变。“影像西部不是天然的、固定的,而是不同力量关系的意识形态场域、集结、表征;它不只是艺术家个人天才的创造,更是个体/群体、本土、民族、国家、世界等复杂关系在电影文本中的符号凝结,正是中国乃至全球复杂多样的关系,决定了近20年来中国电影西部审美空间建构的走向。”经历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尤其是当下媒介环境对电影艺术和技术影响,势必对电影空间表达和审美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在梳理西部电影历史演变的同时,将西部电影置于产业化和媒介化的语境中,从西部影像空间与西部电影类型化建构的关系,重新思考西部电影当下的发展策略。
一、西部空间的影像表达:从国族反思到武侠片类型实验
(一)西部空间的发现与西部电影的国族反思
对西部电影历史脉络的梳理,会发现中国电影对西部审美空间的呈现和影像表达经历了由极盛至衰的清晰轨迹。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和八个》(1983),是新时期开始最早发现并表达西部空间的影片,并因此成为中国当代电影具有转折意义的创作。影片《一个和八个》将摄影机游移于宁夏贫瘠的石砾场,用全景镜头把荒凉贫瘠、开阔苍茫的西部空间推向当代大银幕。《黄土地》(1984)将西部空间的影像化表达地更为极致,电影的故事讲述退居其次。陕北的黄土地在画面构图中成为主体,空间表达或者直接打断叙事,或者将人物挤压至边角,黄土地成为本片真正的主角,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崭新的西部审美空间将从此占据中国银幕。不过,究其根源而言,中国当代电影人对中国西部审美空间的发现与创造表达,是对此前“革命与拯救”的政治话语的反抗性实践。新时期电影人迫切思考和言说民族文化反思、民族身份认同的时代命题,他们找到了象征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起源的“西部”,创造性地以空间的影像表达开启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宏大叙事的发展脉络。《黄土地》的西部空间贫瘠干涸、阔大荒凉,仿佛“凝滞在‘前文明’时代,”以此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意图激发民族自省和国家富强的愿望,暗合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时代精神。在影片《红高粱》中,西部空间的影像表达与民族神话、时代精神的书写高度契合,极致张扬。一望无际的红高粱覆盖了贫瘠荒凉的土地,象征着生命野性的繁殖能力,一泡尿酿造一酒坊好酒的情节设置不仅模糊了历史背景,更为《红高粱》的民族神话增加了酒神般的迷醉和狂欢,与民族意识逐渐强大的现实高度一致。《红高粱》用通过对西部空间的影像建构和审美表达,建构起一则中国走向世界的寓言神话。
伴随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孕育中华历史与文明的西部土地与表征中国走向世界的西部空间意义之间,逐渐凸显出冲突与矛盾,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落后与文明西之间的冲突逐渐成为西部电影早期的主题。吴天明的《人生》(1984)正是在时代冲突命题中,以“黄土地”思考个体的突围与出路问题。《人生》在高加林与巧珍的爱情故事表层叙事中隐含着二人逃离黄土地/传统乡村的主题,高加林读过书、有文化,他要“合理”而公然地逃离贫穷、落后的乡村;巧珍作为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农村女性,她将对城市、现代、文明微弱而隐秘的渴望寄托在对高加林的爱中,巧珍那不宜声张的渴望显然更易被挫败,被高加林抛弃的巧珍最终嫁给马加,对巧珍而言古老贫瘠的黄土严厉冷漠又似乎包容宽厚。而作为突围的失败者和传统的叛逆者,高加林则在影片的结尾被永远地悬置于黑暗的银幕。在《人生》中,黄土地成为青年一辈试图逃离与突围甚至背弃的传统价值观、生活方式的符号表征,陕北的黄土高原在大银幕上以不同角度、变化的色彩被着力呈现,与主人公的命运和故事叙事紧密相关,深沉古老的西部空间成为震撼人心的影像审美空间。整部影片是在厚重贫瘠、苍凉包容的西北黄土高原的影像空间中思考个人与历史、文明、现代社会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影片《二嫫》继续了这种探索,然而也无情地诉说了一个更为惨重和残酷的事实,即使以生命为代价的乡村突围依然可能只是一场虚空。在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西部生存空间日益被挤压。与之相对的,则是西部空间影像表达的日益空洞。
(二)武侠片类型实验与西部空间的过度开发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部”成为中国电影竞相表达的影像空间,与此同时,西部逐渐从旷远厚重的意义空间变为空洞的奇观化叙事空间。这一开端实际上是由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开始的,影片刻意将原著小说的故事从江南陈家花园移至西部的王家大院。陈凯歌的《边走边唱》(1991)也将奇观化的场景设置在中国西北。正如学者姚新勇所综合论述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电影人在反思国家民族命题的影像创作中,发现了独具特质的西部审美空间,其艺术的探索和创新迅速获得世界认可,并将中国电影一跃引领进入世界优秀电影的行列,树立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某种典范。然而他们的艺术开拓在西方的眼光中却被诡异地解读为陌生、神秘的东方图景,成为符合西方主体视野中的荒蛮、他者“东方主义”想象的奇观。贫瘠的西部正在苦苦思索向现代与文明靠近的时候,却意外在电影国际资本生产制作、传播消费和评奖的体系中,成为西方话语霸权最为期待的东方奇观。雄心勃勃的中国电影人不可避免地、自觉不自觉地受制于西方话语操控,西方评委/观众成为不少中国影片的预设观众。
1991年何平导演的《双旗镇刀客》成为美国西部片的中国版本,20世纪90年代正值中国电影市场化发展,被视作神秘东方图景的西部空间开始成为商业类型电影开发的对象。在市场需求刺激和国际合作强化的时代背景下,以艺术探索和人文思考为开端的西部电影首先完成了与港台武打片的嫁接,中国西部成为港台武侠片/武打片最热衷取景的故事空间。《新龙门客栈》(1992)、《东邪西毒》(1994)中对西北黄沙、大漠、废墟的偏爱,甚至驱动曾经在宁夏下放劳动的作家张贤亮建造起中国最早的影视城之一——宁夏镇北堡中国西部影视城。西部影视城打出出售荒凉的口号,诸多这一时代的西部影像在这荒凉的西部空间拍摄完成。西部影视城门口题写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口号,这一理想似乎也终于在李安的《卧虎藏龙》(2000)中实现。集聚国际资本和好莱坞制作团队,并在奥斯卡备受关注的《卧虎藏龙》将“中国西部”的影像空间的国际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影片中的西部已不是贫瘠而身负历史厚重的黄土地,甚至不是武侠片中漫天黄沙的侠义西部世界,而是将中国西部最具视觉奇观的雅丹地貌、山谷、沙漠等西部符号剥离历史地影像化,与美国西部片中的西部符号和空间呈现几乎了无区别。紧随其后的《天脉传奇》(2002)、《英雄》(2002)对西部景观的开掘和视觉呈现达到极致,《天地英雄》(2003)中那个国家化的、遥远历史中的西部空间更加强化了西部奇观的视觉冲击。在国际资本的运作和国际团队的合作下,“西部”已经是一个地域和国别难辨的影像空间,也彻底改变了西部空间的意义指向。此后的《神话》(2005)等影片在西部取景,而西部空间的在影片中的视觉呈现和意义表达都走向式微。2000年前后的中国电影市场低迷,2001年“入世”后的中国电影又受到WTO协议的影响,面对重重困境,中国电影和西部电影该如何探索本土化发展路径和生存道路。
二、中国西部电影:类型化与本土化电影实践中西部空间的再发现与再表达
中国电影经过深化市场体制、文化体制发展,在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后,“类型化”成为电影创作者最重要的艺术方法和市场策略,也成为颇受研究者关注的电影课题。然而,中国电影产业化升级的步伐还没能有效带动西部电影的发展,在上一轮武侠大片中几乎将意义消磨殆尽的西部空间也明显失去了对资本和观众的吸引力。在中国的版图中,西部的电影生产创作地域空间和影像表达的审美空间越发失语和缺席。今天,当我们在新的媒介语境中重新审视2013年底上映的影片《无人区》,影片在类型创作上的探索对于打破西部电影的僵局与沉寂倒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无人区》经过反复修改、四次撤档,最终在贺岁档获得2.2亿票房,居当年票房第15位。本文关注和探讨在当代语境下《无人区》对“西部空间”的再发现,对“西部空间”意义的再表达。这个“西部空间”不是80年代西部电影纯粹的艺术探索和国族叙事,也不是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国际资本裹挟与过度开发的空洞符码,它是勾连起中国西部电影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的本土化实践,为中国电影类型化、本土化探索和中国西部电影发展提供了某种借鉴和思考。
第一,西部空间的再发现。“无人区”——一个专属于中国西部的地理概念,在片名上一目了然地把故事展开的叙事空间定位在中国西部。中国最著名的无人区基本都分布在青海、西藏和新疆等西部地区,无人区即“生命禁地”,是未开发的、危险而神秘的。此外,无人区也指新疆的一条长达500公里的沙漠公路,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沙漠公路。电影《无人区》在新疆哈密、吐鲁番、克拉玛依,甘肃敦煌等地的沙漠戈壁拍摄,故事就发生在一条人迹罕见并且没有手机信号的沙漠公路上。和“黄土地”一样,“无人区”是一个西部空间概念,在影片中因此可以看到雅丹地貌、山谷戈壁、沙漠石砾、废墟黄土和废墟般的加油站,这些构成了整部影片的主要场景。在构建“西部空间”的视觉符号和影像风格时,影片借鉴了美国西部片的某些摄影和造型技巧。例如,最常见的地平线与人物构图,全景镜头中的西部空间辽阔荒凉,特写镜头中的砂砾则凸显了西部空间的粗糙质感。公路和戈壁上的汽车、马匹的奔驰、追逐,人物的打斗形成影片的运动性和节奏感。在地理方位上比“黄土地”偏西的“无人区”更为开阔空寂,山脉、大漠、戈壁绵延不绝、一望无际。这里不是乡村亦不是城市,虽人迹罕至却可能蕴藏稀有的资源和生命,偶尔踏足的旅行者和探险者带着故事和欲望。西部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财富追求与法律约束,个人欲望与社会利益冲突的地域空间,并由此成为关照和思考人性的精神。《无人区》中违法分子捕猎鹰隼的行为来自境外的资本诱惑和支持,人们因此不惜铤而走险、甚至杀戮人命、以身试法,在全球资本发展、媒介和文化融合的今天,中国西部的广袤空间已经不是几个单一的视觉符号和影像空间所能表征和容纳的。从这个角度讲,具有当代意义的西部空间的再发现是中国西部电影类型创建的基本要素,它神秘、广袤、丰富有待被发现。
第二,西部空间意义的当代表达。《无人区》讲述由徐峥扮演的律师远赴新疆,为非法贩卖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猎隼的盗猎者辩护、洗脱罪名,潘肖在归途中独自穿越“无人区”沙漠公路反被盗猎者追杀灭口,由此建构了一个逃亡与追逐、杀戮与救赎的故事,“无人区”成为影片必不可少的叙事空间,它符合故事逻辑,不再是空洞的符码,无法与其他空间进行置换。故事地点包括进入无人区之前的戈壁“帝豪酒店”,“无人区”沙漠公路以及途经的“夜巴黎”加油站和交易猎隼的沙漠废墟。盗猎者派杀手(黄渤饰)追杀律师潘肖,卡车司机无理挡路、粗鲁向潘肖驾驶座椅撒尿,潘肖向卡车投掷打火机引发麦秸着火,潘肖误撞杀手无处救治试图毁尸灭迹,“夜巴黎”的天价油费和“捆绑销售”,傻子锤死杀手又被盗猎老大撞死,盗猎老大杀死傻子父亲并试图把他与舞女活埋等情节,只能虚构于“无人区”这个空旷孤寂的西部空间,一个短暂地处于法外之地的空间。对此,影片有足够的逻辑铺垫,以律师为职业的潘肖代表着法律及其所维系的社会秩序,然而潘肖为盗猎者洗脱罪名的行为消解了他代表秩序的可信度;与此同时,刚刚进入无人区时潘肖与卡车司机兄弟偶然发生的追逐和挑衅,表明潘肖的律师身份和他所谙熟的规则并不适用于无人区。因此,这个500公里没有手机信号的“无人区”,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叙事空间,潘肖在此孤立无援,需要独自面对失序的逃亡之路,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整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完成救赎与自我救赎。在此意义上,“无人区”不仅是故事展开的叙事空间,也是人性袒露、精神救赎的意义空间。
西部空间在频繁地沦为空洞影像符号之后,对其意义的再发现和当代表述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无人区”是救赎与自我救赎的空间。影片中的“无人区”与“黄土地”一样干涸、缺水;不同的是,无人区因为没有手机信号——现代文明与技术的象征——而人迹罕至、封闭隔绝,影片画面的黄色调处理,使整个无人区的空间仿佛回到盘古尚未开天辟地的混沌时空。故事的主要人物带着一己之欲闯入这个混沌而隔绝的荒芜空间。潘肖不辞辛苦乘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3个小时马车来小镇为盗猎者辩护,并用贿赂各路记者制造年轻律师远赴边陲小镇为无辜者洗脱罪名的新闻头条,唯一的目的是追逐名利。盗猎者杀人越货、违反法律盗猎鹰隼,同样唯利是图,盗猎者因此视潘肖是和自己一样的人。影片中有一段长达40分钟、占故事1/3的叙事时间发生在黑夜的无人区公路,黑暗的画面是伴随着潘肖的一段内心独白开始的——“人在陷入绝境的时候,什么都干得出来,正所谓动物本能”,此时,潘肖正打算把误撞的杀手毁尸灭迹。与白天的昏黄混沌相比,深夜的“无人区”仿佛彻底遁入漫无边际的黑暗,成为与媒介等现代因素隔绝的、生命个体不得不独自面对的心理绝境,是潘肖绝望、孤独的心理空间的视觉表征。潘肖的车灯在黑暗中模糊成一个忽明忽暗的亮点,除了无边的黑暗,看不到时空的边界。他冲着后视镜张开嘴巴露出沾满污血的牙齿,此时个体被象征性地掷入这孤立无援的生命原初的心理和欲望时空,并不得不看见自己或他人最黑暗的欲望与本性,在对人类名利欲望和生存本能挣扎的审视中,“无人区”成为意义阐释的空间。
在接下来的情节中,卡车司机的哥哥、杀手、傻子逐个被杀死,卡车司机、舞女、潘肖险遭杀戮,尾随而来的“夜巴黎”舞女使潘肖从逃亡开始救赎与自我救赎。潘肖大段背诵法律条文,试图证明和找回自己的律师身份。当昏黄转为黑暗,潘肖和舞女面临绝境,竟然毫无掩饰地互相诉说各自的欲望、绝望、谎言——几乎是现代人的普遍困境。潘肖在绝望中感到自己就像故事里的猴子,“置身在这猛兽横行的远古时代,可悲的是,并没有人在树下为我放哨”。当主人公被迫直视自己的欲望与孤独,黑暗的无人区不仅在意义上建构了一个欲望化的物理和心理空间,也在视觉上将焦点聚集在人物身上,使观众的视线无处可逃,直逼自私、孤独而又唯利是图的人性黑暗。当然,作为一部商业类型片,导演并不会停滞于对人性的拷问,而是设置了一个“夜巴黎”舞女的角色,使潘肖的逃亡和绝望转向拯救女孩和自我救赎。
所以,无人区是一个看似开阔无边际实则有起始、有边界的空间,它使现代人在远离城市和人群的、暂时失序的空间中审视自我的欲望、困境,并寻求救赎之路。在泛滥的城市影像、越来越不着边际的玄幻世界漂浮许久的中国电影,或许能够在“西部空间”中扎根大地,借助类型的商业叙事和娱乐元素重新审视人和人生存的当代世界。影片结尾处,潘肖为了救舞女,用打火机引爆了盗猎者的卡车,自己也葬身火海,如凤凰涅槃般获得自我救赎,欲望与金钱灰飞烟灭,人与世界又回到混沌的起点。与《英雄》中漫天飞舞的胡杨树叶不同,这一次腾空飞舞的是贩卖猎隼的人民币,没有了为奇观而奇观的生态威胁,取而代之的是对资本与欲望冷峻思考的定格。从胡杨树叶的视觉奇观到人民币的灰飞烟灭,《无人区》在中国的西部电影的类型化创制中真正落脚于西部。
遗憾的是,影片《无人区》对于西部空间的发掘及其与当代人类困境的意义表达似乎并没有在其他影片中获得持续的探索。2010年上映的动作片《西风烈》是有明确和自觉的商业类型化追求的影片,同样以封闭的“西部空间”作为故事空间,并试图以火爆的场面和动作满足观众的期待。导演高群书公开表达想要拍一部“传统的、纯粹的、精良的好看之作”的愿望,然而这依然是一部“景观大于叙事”的类型片。
三、数字化西部景观,中国西部电影发展的困境与路径
最后,面对西部空间的再发现和当代阐释建构中国西部电影的命题,也难以脱离数字化的媒介语境。20世纪末开始数字革命,数字技术正在颠覆传统的电影制作、传播方式,同时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表现功能。将西部电影的类型创作置于这一媒介语境中重新思考,困境与路径并存。
首先,正如《无人区》中封闭孤独的“无人区”,当代数字化和网络社会加重了人类的孤独感和隔绝,人们寄居在虚拟世界,原始欲望被激发或压抑,数字化媒体、新的媒介环境继全球资本和消费之后带来对人的新的压抑和奴役。西部空间在符号和意义层面都可能成为一个适宜于表达和思考人类匮乏、隔绝与孤独的精神空间的影像世界。
其次,数字技术在后期合成领域的能力对电影制作产生的影响和未来的空间引人关注。传统的胶片和样片的后期制作方式已经逐渐被取代,计算机可以将一切传统的媒介物质材料转为数字信号进行存储,通过电脑剪辑、修改,完成后期制作。依赖数字技术能够后期合成逼真的虚拟空间场景,不仅真假难辨,精湛的创造甚至在视觉观看的效果上甚至比真实更真实。特别是VR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正在为当前的电影制作、未来可能的电影互动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基础。在这场数字技术革命中,电影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奇观化的西部空间将完全可以通过数字合成技术与绿幕制作完成,作为单纯的景观,在西部取景也将不复优势。鉴于上一轮全球资本对西部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意义遮蔽,如果不重新思考数字化时代的西部影像制作,则可能面临西部影像在数字的虚拟技术中被湮灭的危险。
由此可见,观众不再需要一个空洞而陌生的神话西部和历史西部,西部空间与西部电影的类型化与本土化创作只有与当下的时代焦虑和普遍情感相联系,才可能获得生存路径,同时以当代意义的再阐释抵御某种数字革命的技术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