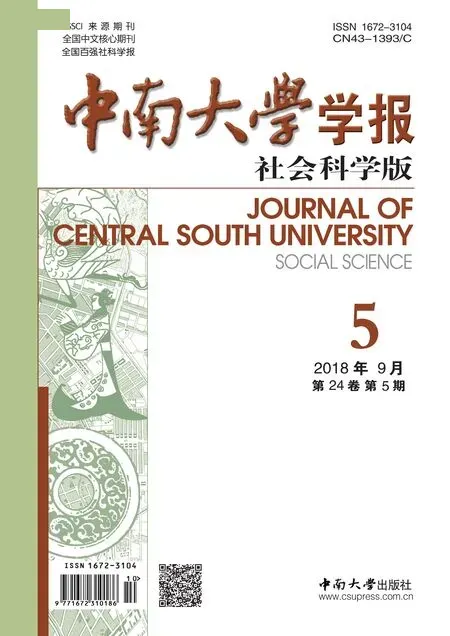论王世贞诗乐相合的文体观
2018-10-15涂育珍
涂育珍
论王世贞诗乐相合的文体观
涂育珍
(东华理工大学江西戏剧资源研究中心,江西南昌,330013)
王世贞的文学批评将“才、思、格、调”结合起来,通过辨体批评,确立文体典范,以文体“正变”为核心,贯通诗、词、曲诸多领域。王世贞论及诸文体的体性特征时,既强调复古、拟议古法,又主张通变、顺应性情;既强调骈俪、典雅,又主张从俗、近俗。后人常困惑于其矛盾之处,或各执一端,或以“剂”来解释其调和折中之意。王世贞论诗词曲之体制并非简单的叠加或折中,他认为诗词曲的体性于雅俗之间相通的基础在于诗乐相合。其文体批评的内在逻辑是以复古为导向,诗心与乐体结合,融通雅俗,探寻将“今乐”文人化的曲学尊体路径。
王世贞;词学;曲学;辨体;文人化
王世贞是晚明复古主义诗学流派“后七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博学多才,著述繁复,对诗、词、曲诸多领域皆有精到的批评论述。古人论及词曲的文体特质往往从诗性和乐体两方面切入,或认为“古之诗,今之词曲”,把“可歌”作为诗词的体制特征①;或以“今之乐,犹古之乐也”,视诗性之“真传”为复古乐之途径②。我们将王世贞的词学和曲学观点与复古主义的诗学背景结合起来考察,可以注意到他所探寻的一条诗乐相合的复古思路。他以复古主义为导向,确定文体典范,论词曲也以辨体为先,并据此展开其溯流别、明正变、审雅俗的具体阐述。
一、复古主义的诗学背景与诗乐离合的辨体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体”是比较复杂的概念,不仅仅指文体类别,还涵盖了对文体特征的整体把握,“既指向体裁或文体类别、又指向体性、体貌风格;既有具体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之义,又有文章或文学本体之义,是具体与抽象、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有机结合”[1]。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辨体批评也综合了以上“体”之概念的诸种内涵和外延,其中居于首位的当属本体之体。
从《尚书》“辞尚体要”、刘勰“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2](529)到杜甫的“别裁伪体”、皎然“辨体十九字”,再到宋代的黄庭坚、严羽,都提出了文学批评以“体制”为先的看法。由于语境的复杂和不断变化,“体”之文类、风貌等内涵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本体”的解读。如杜甫之“体”指诗歌创作的风雅传统,而皎然之“体”则更多是指创作风格;陈师道转引黄庭坚“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3](303)之语,黄庭坚则有“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4](175)的表述。“各有体”与“自有体”表述相似,但内在所指却有较大区别,陈师道转述之“体”指体式规范,为不同文类之体,黄庭坚自述之“体”则指创作精神和创作原则,为体要之体。
明清时期前后七子倡导的“格调”之说远接严羽的诗法,将《沧浪诗话》对诗之五法的解释“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凝练为“格”与“调”,并围绕“格”与“调”展开了大量关于诗歌的体式风格、字词句法、声韵音调等艺术技巧的讨论,从形式规范的角度寻求文体典范,由此强化了溯源探流、区别正变的辨体意识。明代“格调”说的辨体批评将严羽倡导的“兴趣”落实在艺术形式的体性辨析和法度规则之中,一定程度上虚化了其中蕴含的性情表达的追求,以致后人有意无意地将格调说与明代心学思潮、主张“性灵”的诗学理论区别开来。但如果深入讨论格调说因情及声、以调论乐、由乐观情的思路,则能清晰地看到“以声辨体”“别体得趣”与心学性情自达的诉求之间这条被遮蔽的关联线索。
心学与诗学之建构都以性情表达为根底。心学家陈献章《批答张廷实诗笺》曰:“欲学古人诗,先理会古人性情是如何,有此性情,方有此声口。”[5](74)《认真子集序》则曰:“言,心声也。形交乎物,动乎中,喜怒生焉,于是乎形之声,或急或徐、或洪或微,或为云飞,或为川驰。声之不一,情之变也,率吾情盎然出之,无适不可。”[5](5)通过吟诗方式表达性命自得的内心体验,是因情及声。诗学家李东阳则以声论诗,将诗律与乐教融通。《麓堂诗话》提出:“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乐始于诗,终于律,人声和则乐声和。又取其声之和者,以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俳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则古之教,何必以诗律为哉?”[6](1369)诗之体的本质在于通过“乐”来调和性情,强调诗歌与音乐的内在相通。作为明代格调说的先导者,李东阳最早将“格”与“调”并举,以声论诗,从诗乐离合来论诗歌体制的发展,而声调、体格与政教之道相通,从格调形式便可领会时代风气。李东阳论诗特别强调应该“具耳”:
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费侍郎廷言尝问诗,予曰:“试取所未见诗,即能识其时代格调,十不失一,乃为有得。”[6](1371)
受此影响,前后七子的诗学批评大多注重将“格调”与时代风气联系起来。王世贞的表述要显得复杂一些,他一方面指出文章格调一代不如一代,“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7](985);另一方面又能较宽容地对待“格之外”的优秀篇章,如他提出“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然而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盖不止前数公而已,此语于格之外者也”[8](549)。强调说明诗歌风气的发展变化与时代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六朝之末,衰飒甚矣。然其偶丽颇切,音响稍谐,一变而雄,遂为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机藏隙。盛者得衰而变之,功在创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趋下。又曰:‘胜国之败材,乃兴邦之隆干;熙朝之佚事,即衰世之危端’。此虽人力,自是天地间阴阳剥复之妙”[7](1008)。王世贞对于历史盛衰变迁的观点基于《易》阴阳消长、剥极复生的思维方式,具有通变灵活的特点,也体现在他对待“体以代变”“格以代降”③的现象并不拘泥于此固有定势,还能注意到在文体发展过程中消长生息的转机。王世贞形容诗之“体变”“代降”为:
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9](27)。
这段经常被征引的文字谈论了词曲发展与音乐的关系,其中论各文体缘起的先后顺序和承继关系常被人诟病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但事实上,王世贞所论的重点不在于文体形成的顺序,而在于论及音乐对诗词曲体制发展的重大影响,以及文体兴衰与时代审美趣尚之间的关系。王世贞诗学观的“格”与“调”关联的内在逻辑是以“诗乐”关系为基础的。四言本于风雅之谣,七言体的节奏受到楚歌的影响,而五言源于汉乐府之歌,诗歌的时代体式的演变根源于“乐”的变迁。再换个角度来看,先秦时期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开启了《诗经》风雅传统,古乐府格律化之后成就了唐诗之盛,隋唐时清乐杂胡部之声称为燕乐之后,文人介入的方式也从声诗入乐逐渐转变为倚声填词。音乐随时而变,虽可遵循韵律追古乐之踪迹,终不如推求今乐雅化之途径,实现复古乐之风雅传统。
王世贞对文体兴衰的叙述,说明了各文体尊体与雅化的发展过程,依据的是文人士大夫的诗教传统和礼乐文化④。“礼失而求诸野”,每一次诗与乐的遇合都是新的诗歌体式生长的契机,而文体融于诗教,俗乐定格于声律,诗与乐融合的典范得以确立,也意味着诗乐背离的再一次开始。
二、乐府之变与词学辨体的文体典范意识
在诗乐离合发展脉络的节点上,诗、骚之后是汉魏乐府。《艺苑卮言》《明诗评》及一些序文中有王世贞关于乐府诗的评论,其中关于李东阳拟乐府作品的评价前后不一,褒贬两端。王世贞在《书李西涯古乐府后》中解释了对李东阳的拟乐府态度变化的原因:
吾向者妄谓乐府发自性情,规沿风雅,大篇贵朴,天然浑成,小语虽巧,勿离本色,以故于李宾之拟古乐府,病其太渉论议,过尔抑剪,以为十不得一。自今观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创造,名语迭出,纵未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若使字字求谐于房中铙吹之调,取其声语断烂者而模仿之,以为乐府在是,毋亦西子之颦、邯郸之歩而已[10](54)。
王世贞早年不仅对李东阳的拟乐府下过“议论太过”的断语,而且在《明诗评》中将他列为评论的118位诗人的最后一位。如此苛评,显然有失公允。王世贞晚年“气渐平,志渐实”⑤之后,有一种少债老偿的愧悔弥补心态,但这种解释很难说明其批评态度变化下包含的文体观。抛开意气之争的变化,这段话的重点在于论述乐府诗的体制规范,表达了以下观点: ①李东阳拟乐府的特点有三:议论太过、不可披之管弦、奇旨名语;②乐府体当从声与辞两方面规范:其辞发自性情,规沿风雅,宜质朴本色;仅从声律模拟只能得乐府诗之皮相,乐府诗体制特点在于声之乐,而非声之律。王世贞早年完成的《艺苑卮言》中极力贬低李东阳的拟乐府,“李文正为古乐府,一史断耳,十不能得一”[7](1046),着眼点正在于议论太过而背离了文体规范。前后对比,王世贞非常热情地赞美了李东阳拟乐府的“奇旨”“名语”,肯定他的创作精神和语言表达的创新,但“一涉议论,便是鬼道”[7](959)的看法并未改变,而且进一步批评了李东阳拟乐府诗不能合乐以披管弦。
清初王士祯同样借用王世贞的评语赞美李东阳拟乐府,“夫西涯乐府虽变体,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弇州晚年尚尔服膺,遽斥之为‘野狐外道’可乎?”[11](20)这段批评话语的使用与王世贞论苏辛词为“词之变体”如出一辙,大抵王世贞也是将西涯乐府视为乐府诗之变体。王世贞称自己的乐府诗为《乐府变》,将词的文体特征概括为“词者,乐府之变也”。从二者的联系上可以看出王世贞树立文体典范的辨体意识。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曰:“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2](183)乐府诗体以汉乐府为典范,其声当合乐,其辞当合乎风雅之教的精神传统。
据此,王世贞评价杜甫乐府诗能“以时事创新题也。少陵自是卓识,惜不尽得本来面目耳”[3](1007)。何景明有相似的观点,“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并直陈“子美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一变体也”[12](123)。王世贞二十二首《乐府变》都是“舍意调而俱离之”[13](72),采用杜甫“即事命题”的拟作方式,直写当朝实事。乐府诗的价值通过采诗实现,“古乐府自郊庙、宴会外,不过一事之纪,一情之触,作而备太师之采云尔”[13]。《乐府变》“下以风风上”的创作精神正体现出乐府体的本质,而这组诗同样不能合乐,仍称为变体。王世贞没有直接描述过“乐府体”的体性特征,但曾引王僧虔《启》云:
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时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又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韦”“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由《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其语乐府体甚强,聊志之[7](960)。
他深表认同的这段关于乐府体的描述,与郭茂倩《乐府诗集》对乐府诗曲式结构的描述是一样的⑥,因此,他认为李东阳无法通过声韵格调的模拟或新变来创作出合乎典范的乐府体诗歌。如前所述,李东阳重视以声辨体,不过,西涯乐府所拟之声在韵,而非乐,因而带来乐府诗的古诗化,引起宋荦等人“要当作古诗读”[14](417)的非议。但问题是,今之乐,非古之乐,汉时乐曲已不复闻,明之乐府体又合什么乐呢?⑦
在诗乐离合发展脉络的节点上,乐府是诗之变,词乃乐府之变,这并非仅仅是指词起源于乐府,而是指词体与乐府体以同样的方式,将“今之乐”纳入风雅之教的序列中,“词兴而乐府亡矣,曲兴而词亡矣,非乐府与词之亡,其调亡也”[15](385)。此“调”便是乐,今之乐非古之乐,词之体也不同于乐府体⑧,诗为乐心,声为乐体,词体的正与变也当以传承风雅、合乎词乐为准。
王世贞论词体之正变:“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15](385)张綎等人提出词体有婉约与豪放之分,从词体风格来谈论正变也成为明代较为盛行的角度,因此,王世贞从词体风格将婉约词列为正宗,他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如徐釚的论述就来自王世贞的说法。他在《词苑丛谈》中转述:“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16](101)词体以“婉约”为正,与合乎词乐的标准相关,苏词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但不妨碍李清照曾斥之为句读不葺之诗,原因即是不协音律。因此,王世贞以其不合词乐之宛转近情⑨,将苏辛豪放词视为变体,其余包括王世贞列举的柳永、周邦彦等为正宗,而列黄庭坚等为变体。这些论断,非议者不多。但王世贞将南唐李氏的词置于正体之首,因温韦词“艳而促”的风格而视之为变体,这两点则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其中争议的焦点在于对温韦词的看法。
我们注意到这种以士大夫审美为词体确立文体典范的思路,其后很快又转向了以比兴论词体的主要路向。如明清之际云间词派的陈子龙,推尊南唐北宋词为正体。《幽兰草词序》认为花间词“意鲜深至”,而南唐北宋词“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他以花间词类比齐梁诗,尊南唐北宋则类比“文宗两汉,诗俪开 元”[20](726),随后进一步提出“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20](704),将词体小道提升为“大雅之谈”[20](705)。至于清代常州词派如张惠言等将温庭筠词置于词之正体,也需先将其解读为“深美弘约”[21](1617)的寄托之作,以合雅正,如果没有覆上这层比兴之法重新诠释,温词的绮艳柔婉是不能成为词之正体的。
士大夫文人对风雅传统的坚持与婉娈近情、柔靡近俗的词体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为消解这种距离,早在北宋时期的黄庭坚就有意提出“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借用比兴寄托的诗学传统来抵挡如法秀之“罪余以笔墨劝淫”的诘难[4](194)。自南宋以来,黄庭坚的“诗人句法”被以诗为词的趋势所掩盖,词越来越接近于诗,词体独立于诗体的特点渐渐消失。在王世贞的时代,主情任性的思潮日趋泛滥,婉媚旖旎的情词一时风行,王世贞也说“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柔婉多情的词体本色乃是在唐五代合乐可歌的环境中形成的,乃词体不同于诗的根本特征。为强调这点,王世贞不惜宣称“宁为大雅罪人”。这体现了保持词体特质与“风雅”传承之间的矛盾。王世贞意识到,消解“风雅”传统与词体本色的距离不等同于词变成诗,因此,王世贞标榜南唐北宋词的清雅风格作为词之正体,希望能在雅俗之间寻求平衡点,以同时保有词之诗心乐体。而事实上,后来清代词家以比兴寄托之法来推进词的诗化和雅化,虽完善了词的格律,但也已不能复现合乐可歌之词体特质。
时至晚明,王世贞所倡导的词之正体,其实也和李东阳的拟乐府一样,披之管弦已绝无可能,王世贞晚年与西涯乐府的和解乃至高度赞美西涯乐府之奇旨,也许有一种对古之乐不能复现的无奈?
三、融通雅俗与南曲的尊体意识
延续“词者,乐府之变”的理路,王世贞提出了“曲者,词之变”,合乎今之乐的南曲自然成为他关注的对象。如前所引,王世贞将“入乐”“入俗”“谐耳”与否视为文体转移的前提和动因,他从这几个方面深入辨析了“曲”的体性特征。王世贞的戏曲观点主要反映在《艺苑危言》中所附的一卷曲论,这些论曲文字在明代即被专门辑录付梓,是为《曲藻》。试摘录部分经常被征引的论述如下:
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而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宮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
但大江以北,渐染胡语,时时采入,而沈约四声遂阙其一。东南之士未尽顾曲之周郎,逢掖之间,又稀辨挝之王应。稍稍复变新体,号为“南曲”。高拭则成,遂掩前后,大抵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虽本才情,务谐俚俗[9](25)。
首先,“入乐”,时代新声给予了曲体形成的机遇和生长的环境。金元新声带来了元曲一代之盛,南曲新体成就了高明《琵琶记》的地位,南戏传奇遂大兴④。王世贞将“入乐”与“入俗”结合起来,文体之兴往往肇始于俗乐,世俗生活真挚的丰富的情感蕴蓄着源源不绝的创新力,切合了社会最真实的审美需求,又经由富有才情的文人之手,锻造出经典传世之作,即所谓“虽本才情,务谐俚俗”,以求达成诗心与乐体的融合。
王世贞这种融通雅俗的思想也受到时代风气的濡染。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士商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呈现十分明显的融合趋势。社会阶层秩序的崩塌与重组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切思考⑩,促使王世贞对时代变化的体察和思考,并影响到他的文体观,影响到他对情感表达和创作体式风格的选择。王世贞对俗文学的兴趣十分浓厚,他关注小说《金瓶梅》,甚至被列为可能的作者之一,又辑小说《剑侠传》及《艳异编》;他与吴中曲家往来密切,对吴中戏曲的创作情况也十分了解,《曲藻》中多有点评。关于《鸣凤记》,从汲古阁《六十种曲》及凌廷堪、冯梦龙等人的著录情况来看,这部时政题材的戏曲作品与他渊源颇深。清乾隆年间焦循的《剧说》载:“相传《鸣凤》传奇,弇州门人作,唯《法场》一折是弇州自填,词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报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乃终 宴。”[22](203)因罹“父难”,戏中表达的对严嵩的深恶痛绝、对现实政治的关怀,王世贞当有刻骨之感。深挚之痛通过戏曲来传播,时代格调也通过以曲写心的戏曲得以呈现。正如王世贞对《琵琶记》“体贴人情、委屈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的评价:
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惟其逐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屈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至于腔调微有未谐,譬如见钟、王迹,不得其合处,当精思以求诣,不当执末以议本也[9](33)。
其次,王世贞认为还有必要将“入俗”与“谐耳”结合起来,曲的体性特征依托于所合之乐的体性。“入俗”,体贴人情乃是曲体最根本的特征,“不当执末以议本”,但“腔调”有未谐处,不得其合处,仍需精思求诣。问题是“曲”的乐体形式多元,有散曲、剧曲,名称复杂如“乐府”“词”“小令”“套数”“传奇”“戏文”“南戏”等,不一而足。纵观《曲藻》中的41则曲论,其评论对象多为剧曲,从他所评论的吴中曲家来看,他对当下的南曲创作保持着热切的关注,表达了自己对南曲尤其是剧曲的重视。王世贞明辨南北曲的声情不同,如他“论曲三昧语”所言“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辨体的目的是为了强调遵体,他认为既作传奇,当遵依南曲音律,如建议李开先所作《宝剑记》等不合乐处应改妥,并且将《琵琶记》树立为南曲的文体典范。
(伯华)所为南剧《宝剑》《登坛记》……自负不浅,一日问余:“何如《琵琶记》乎?”余谓:“公辞之美不必言,第令吴中教师十人唱过,随腔字改妥,乃可传耳。”[9](36)
元朗谓(《拜月亭》)胜《琵琶》则大谬也,中间虽有一二佳曲,然无词家大学问,一短也;既无风情,又无裨风教,二短也;歌演终场,不能使人堕泪,三短 也[9](34)。
王世贞认为与《拜月亭》相比,《琵琶记》的典范之处在于融通雅俗,以雅正之风化关乎近俗之人情,合乎曲体之本;既有词家大学问的典雅,又能使人堕泪,合乎声情之美。在确立南曲文体典范的问题上,王世贞与何良俊、徐渭等曲家意见相左。何良俊认为《拜月亭》等早期经典南戏虽才藻不及,然不失本色,终是当行,而王世贞则认为《琵琶记》在体贴人情的同时,又具备“逐句之工,使事之美”。这种文人化的审美取向,与他在确立词体典范时尊南唐词而不是更早一些的花间词的思路是一致的。
最后,王世贞确立《琵琶记》的典范地位,推行南曲曲体的文人化,来源于他对当时曲坛的发展状态距离古老的诗乐相合理想尚远的忧虑。王世贞认为可以通过艺术形式的雅化和规范来达成这一理想,所谓“诗有常体,工自体中,文无定规,巧运规外……故法合者,必穷力而自运,法离者,必凝神而并归”[7](964),南曲正当盛时,是时代格调之体现,而在曲辞、声律等方面的创作表现未能达到尽善尽美,也没有形成审美规范,“郑所作《玉玦记》最佳,它未称是;《明珠记》即《无双传》,陆天池采所成者,乃兄浚明给事助之,亦未尽善;张伯起《红拂记》洁而俊,失在轻弱;梁伯龙《吴越春秋》,满而妥,间流冗长……”[9](37)。在曲体体制规范化上,王世贞主张将俗乐文人雅化的复古路径。时人多指摘南戏“声乐大乱……今遍满四方,辗转改易,又不如旧,而歌唱益缪,极厌观听。盖已略无音律、腔调。愚人蠢工,构意更变,妄名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变易喉舌,趁逐抑扬,杜撰百端,真胡说耳。若以被之管弦,必至失笑”[23](365)。一方面王世贞质疑以北曲音律为正体,指出北曲“渐染胡语”“四声遂阙其一”,应以南曲为正体;另一方面又因为缺少足够的创作体验的积累,无法提供明确的南曲曲律规范的实践图谱,他只能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曲辞的文人化上。
“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7](964),格调与才思密切相关,才思与性情互为表里。正如王世贞谈论梁辰鱼古乐府的特点,“或正言以明志,或婉语以引情,一切归之和平尔雅,庶几洋洋乎盈耳矣”[8](557),文人化审美的意义指向十分清晰,倡导雅正、委婉、有节制的抒情。王世贞在李攀龙之后主盟文坛,其文学观念影响甚巨,他的曲学主张以复古为导向,致力于融诗心于乐体,试图解决“今乐”文人化、雅化的内在逻辑,对当时及其后的曲体规范化、尊体的选择有十分深刻的影响。
注释:
① 如南宋郑樵云:“乐以诗为本,诗以乐为用…古之诗,今之词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理可乎?…奈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乐日微…今乐府之行于世者,章句虽存,声乐无用。”(《通志二十略·乐略第一·乐府总序》,王树民点校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83-884页)
② 如李开先《西野春游词序》所言:“音多字少为南词,音字相半为北词,字多音少为院本,诗余简于院本,唐诗简于诗余,汉乐府视诗余则又简而质矣,《三百篇》皆中声,而无文可被管弦者也。由南词而北,由北而诗余,由诗余而唐诗,而汉乐府,而《三百篇》,古乐庶几乎可兴。故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呜呼扩今词之真传,而复古乐之绝响,其在文明之世乎。”(引自吴毓华《中国古典戏曲序跋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
③ 王世贞之后,胡应麟诗学概括了诗歌“体以代变”“格以代 降”的观点,持悲观态度,指出:“四言变而《离騒》,《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三百篇》降而《离骚》,骚降而汉,汉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诗之格以代降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 页)
④ 李舜华认为:这样一种声辞统系的叙述,它所依据的并不是各文体实际发生的次序,而是各文体进入礼乐文化系统、或者说被尊体与被雅化的先后次序。(《“乐学与诗(曲) 学”专题主持人语》《文艺与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⑤ 钱谦益《列朝诗集》引《书西涯乐府后》有一段四库本删节的话:“余作《艺苑卮言》时,年未四十,方与于鳞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行世已久,不能复秘,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而已。”据魏宏远《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转变“三说”平议》(《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考证,出自《弇州山人续稿》明手抄本,颇为可信。
⑥ 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一》题解中解释乐府的音乐性结构:“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乐府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310页)
⑦ 清代贺贻孙提出:“近日李东阳复取汉、唐故事,自创乐府。余谓此特东阳咏史耳。若以为乐府,则今之乐,非古之乐矣,吾不知东阳之辞,古耶?今耶?以为古,则汉乐既不可闻;以为今,则不为南北调,又创此不可谱之曲。此岂无声之乐,无弦之琴哉?”(《诗筏》,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⑧ 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曾借何元朗《草堂诗余序》之语,形容乐府与词体风格之不同,“乐府以皦径扬厉为工,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6页)
⑨ 王世贞:“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 第385页)
⑩ 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中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王文成全书》卷二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65册,第688页。)余英时先生认为:16世纪以后的商业发展也逼使儒家不得不重新估价商人的社会地位。(《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1] 吴承学, 何诗海. 古代文体学研究漫议[J]. 古典文学知识, 2014(6): 116−122.
[2] 刘勰. 文心雕龙[M]. 杨明照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3] 陈师道. 后山诗话[C]//何文焕辑. 历代诗话.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4] 张惠民. 宋代词学资料汇编[G].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3.
[5] 陈献章. 陈献章集[M]. 孙通海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6] 李东阳. 麓堂诗话[C]//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7] 王世贞. 艺苑卮言[C]//丁福保辑. 历代诗话续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8] 王世贞. 弇州续稿[C]//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82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9] 王世贞. 曲藻[C]//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 北京: 中国戏曲出版社, 1959.
[10] 王世贞. 读书后[C]//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85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1] 王士禛. 香祖笔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12] 何景明. 大复集[C]//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67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3] 王世贞. 弇州四部稿[C]//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79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4] 宋荦. 漫堂说诗[C]//清诗话.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5] 王世贞. 艺苑卮言[C]//唐圭璋. 词话丛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6] 徐釚.词苑丛谈[M]. 王百里校笺.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17] 张綎. 诗余图谱[C]//徐釚. 王百里校笺. 词苑丛谈.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18] 魏庆之. 魏庆之词话[C]//唐圭璋. 词话丛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9] 王士禛. 花草蒙拾[C]//唐圭璋. 词话丛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0] 胡应麟. 诗薮·杂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21] 陈子龙. 安雅堂稿[C]//续修四库本第1387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22] 焦循. 剧说[C]//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八.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23] 祝允明. 猥谈[C]//陶宗仪《说郛续》续修四库本第1192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Wang Shizhen’s view of literary style: Combination of poetry and music
TU Yuzhen
(Research Center of Jiangxi Opera Resourc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13, China)
Wang Shizhen’s literary criticism combines “talent, thought, style and tone”, and establishes the stylistic model through style identification criticism which holds direct variation of stylistic model as the core and threads up such various fields as poetry, Ci and Qu. When he discusses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literary styles, Wang Shizhen emphasizes both returning to the ancient and traditional method, and advocating the doctrine of adaptability and conforming to the temperament. Meanwhile, he not only stresses the art of parallelism and elegance, but also advocates traditions and vernacularism. As a result, later generations are often so much confused about his contradictory opinion that they even insist on two extremes which are actually both of Wang’s version, or use “Ji” to explain its compromise. Wang’s poetry criticism system is not simply overlaying or compromising. Instead, it i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poetic music to link elegance and vulgarity. The internal logic of stylistic criticism is retro-oriented combining poetic heart and musical body, integrating elegance and vulgarity, and exploring the approach with opera theory and upgraded style, which reflects the scholar-writer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music.
Wang Shizhen; Ci theory; Qu theory; style identification; scholar-writer
2017−11−26;
2018−06−15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戏曲改编研究”(12CZW036);江西省社会规划课题“中国词学评点研究”(10WX70)
涂育珍(1974—),女,江西临川人,文学博士,东华理工大学江西戏剧资源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戏曲及古代戏曲批评,联系邮箱:253663413@qq.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5.020
I207.2
A
1672-3104(2018)05−0171−07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