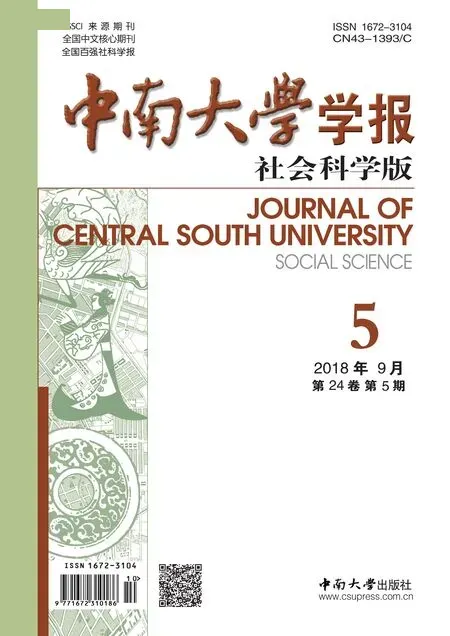全球气候政治的群体化:一项研究议程
2018-10-15赵斌
赵斌
全球气候政治的群体化:一项研究议程
赵斌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对全球气候政治进行理论解读,有助于全面认知该进程中存在的困难,并为寻求化解之道提供现实启迪。详细梳理并分析全球气候政治的参与主体之后,认为全球气候政治经由主权民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参与,逐步演化为群体化态势。在带有系统效应乱象的全球气候政治群 体化进程中,新兴大国群体有必要深化协调、协作与合作,共同推进全球气候政治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善治的 实现。
全球气候政治;全球气候治理;参与主体;群体化;新兴大国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历史自工业革命以来,对所谓理性和现代化的持续追求,一度成就了科学与技术领域的高歌猛进。与此同时,交通、通信等条件日新月异,不仅使“征服自然”不再显得遥不可及,而且各主要民族国家一再滑入彼此征伐的“霍布斯丛林”。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周期总在国家间政治或曰国际冲突的悲剧中循环往复,以工业化和全球化为时代界标,差异或许仅仅在于全球性自我毁灭规模是否扩大,抑或代价加重与否(从1904年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由于长期处在战争/冲突阴霾之下,传统安全/高级政治议题难免过于“强势”(甚至二战后至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而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保议题,则长期归于沉寂。
直到1972年,厄尔尼诺现象爆发、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问世、首次联合国人类 环境会议召开,人类才开始反思无限增长和扩张的代价,一度被长期遮蔽的气候环境问题,才开始提上议程。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气候变化议题因此上升至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高度。以IPCC报告为依据,气候变化议题更侧重于“人为气候变化”(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即包含两层意思:显著的全球升温系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所致;全球气候因人类活动所改变[1]。气候变化议题说到底仍是政治议题,并表现出自反性,即反映一种全球风险,对地球上的生命构成威胁,无所不在的风险超出了个人能力甚至国家的控制,且昭示着现代性本身的深刻危机[2]。从国际体系层面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之殇” (Cancer of Westphalia),到主权民族国家层面的“污染者敌意”(Malignancy of the Great Polluters),再到公民社会意义上的“现代性迷失”(Addictions of Modernity),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进程却似乎始终难逃倒退甚或失败厄运[3]。
鉴于此,文章分析的核心在于全球气候政治的群体化(grouping),即从现象来看,主权民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是全球气候政治的参与主体,但这不足以揭晓全球气候政治的变化现状及存在问题,而以“群体化”为特征的全球气候政治新动态,带有一定的复杂系统效应。作为一项新的研究议程,分析全球气候政治的群体化,有可能为全球气候的善治和全球气候政治发展找寻出路,或为中国气候外交提供理论与现实启迪。
二、全球气候政治的参与主体
由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共属性,一度囊括几乎所有的国际政治行为体,气候变化的政治因而也带有全球政治或曰世界政治的色彩,从参与广度和深度而言,相较传统的“高级政治”甚或国际政治本身,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①。可以说,“任何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都对他国产生了代价效应”,人们不得不在全球政治互动体系中给予气候政治一定的话语空间;关于气候变化的探讨促成了相互依赖的社会和政治网络,形成了以多边反馈为特征的全球复杂系统[4]。在这种全球气候政治的相互依赖网络当中,较为明晰的网格结点,则是大小不等的主权民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这两类行为体虽效能各异,却共同推动(或阻滞)全球气候政治变化的进程。
(一) 主权民族国家
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通过,成为全球气候政治进程的分水岭。在京都协议之下,民族国家利益应让位于政治经济合作,以促成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实现。如果说,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政治当中存在着一种可能路径,即兼顾不同文明的代际延续和公正发展,那么京都机制需为此而努力。《京都议定书》的原初目的在于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建构一种全球政治共识,只不过,这种气候政治共识由于主权民族国家的领土政治(territorial politics)特性,使得附件一国家强制实现减排目标必须寄希望于“考虑缔约方国内实施承诺的灵活性”[5]。
然而,为应对气候变化巨大挑战并通往理想彼岸,所需借重的主权民族国家经济和政治手段却给我们带来了麻烦②。这方面最恶名昭彰的“倒退”例证,莫过于2001年乔治·W·布什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并宣称退出京都协议的理由在于接受议定书会使美国经济付出太大代价,尤其不满诸如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免于强制减排目标设定[6]。无独有偶,2017年6月1日,特朗普政府又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该协定一度为2015年以来中美战略对话的一大阶段性成果,且作为全球气候政治制度的象征意义自2016年以来为国际社会所共同期许。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再次开历史倒车,无疑使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进程再遭重创。
中等强国如澳大利亚的气候变化国内适应政策,也强化了民族国家的领土政治色彩。“澳大利亚须谨防全球协议效果欠佳,并为此做好准备”,这意味着全球谈判在面对人为气候变化所带来迫切的社会、环境与发展需求时,刚性不足(not robust enough),京都协议只是“掩盖了澳大利亚碳排放的(国内政策层面上的)结构动因”,因而主权民族国家或领土政治仍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7]。
作为转型经济体同时又是当前主要新兴大国之一的俄罗斯,其国内政策同样印证了主权民族国家在气候政治中的中心地位。例如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内,俄罗斯其实具有明显的排放剩余空间优势,但考虑到美国退出京都机制可能会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俄罗斯还是拒绝批准议定书[8]。即使后来俄罗斯在2004年决定批准《京都议定书》,也宣称这仅仅是为加入WTO而与欧盟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
此外,就连以全球气候政治领导者自居的欧盟,其在国际气候建制上的所谓创新理念和开拓性实践,其实也都极大地仰仗各成员国的国内气候政策与行动,比如德国的二氧化碳减排计划、法国的环境协商会议(Grenelle Environnement)、英国的气候变化法案(Climate Change Act)等,这些成员国气候政治的“成功探索”其实不亚于欧盟层面的努力,且还能以国家间的外交形式更好地与美国进行互动交流[9]。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展现出新的趋势,即旧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元对立的旧秩序正让位于更引人关注的联盟(alliances)[10]。不过,就其中民族国家这一全球气候政治的参与主体而言,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对自身领土主权利益的关照,往往更甚于对国家间所谓集体的气候建制的需求[11]。换言之,当前的全球气候谈判之所以常常以失败告终,全球气候治理之所以失灵,其根本原因仍在于所谓的全球气候政治努力难以有效整合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或者说主权民族国家间难以就气候难题的解决而实现超越领土的接壤);有关气候变化应对方面的全球集体政治是无效的,因为这些所谓的“全球安排”仍然由地理界限的主权利益和实践所决定(如有关“规范”建构的实践,其载体仍为主权民族国家,规范的传播路径仍由国家主导);在气候变化议题中心的经济因素方面,主权民族国家也在占据先天优势③。
可见,全球气候政治的参与主体,仍为主权民族国家。文章对相关问题的讨论,难以避免这种“国家中心主义情结”。事实上,不论是国内政治层面的气候政策与实践,还是国际政治或世界政治意义上的全球气候制度建构,主权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至少在可见的将来仍难以被完全颠覆④。
(二) 非国家行为体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制度,构成了传统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研究的重要主题。我们不难想象,国际气候政治的研究与实践,主要围绕各国政府的气候政治行动和国际气候谈判行为而展开,因而带有国家中心主义色彩。然而,世界政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 NSA)也同样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政府授权非国家行为体,以促使后者参与国际气候政策进程,进而拓展全球气候政治;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参与气候政治协商、游说政府、准备(和提交)政策报告、接触大众传媒等途径,尽可能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可以说,非国家行为体及其广泛活动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政治中一道不容忽视的风景线。
所谓非国家行为体,指的是国际关系中除主权民族国家外的国际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可能并不从属于任何单一的国家制度,也可能没有国家所具备的那种正式和普遍的法律效力,但却可以影响国际政治进程。具体而言,非国家行为体大致包含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多数也被视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带有营利性质)、国际媒体(International Media)、暴力非国家组织(武装组织如基地组织或跨国犯罪组织)、宗教团体等。可见,非国家行为体的扩大,既冲击着传统主权民族国家赖以维系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又使得传统的冲突管理与解决路径变得更为复杂。简言之,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构成了双重挑战,需要尽可能发挥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国际政治的正向功能(如环境保护与社会服务等),同时管控和防止其可能存在的消极作用(如跨国犯罪与恐怖组织活动等)⑤。在非国家行为体当中,NGOs(包括私人的和自组织的利益团体)较为普遍和多见。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参与其中,而起源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这一全球气候制度结构的核心进程是由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经历多回合谈判而生成的,但非国家行为体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在此后的历次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非国家行为体,如NGOs的身影频繁出现,近年来尤其是2013年底的华沙气候谈判,NGOs对伞形国家群体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气候政治立场大倒退表示强烈不满,并以集体退场的形式对发达国家进行抗议。而且,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压力施加方,往往可能影响政府的气候政策和决策,进而推动一国的气候政治变化及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三、全球气候政治的群体化
群体作为一个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概念,指的是两个以上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集合。具体到全球气候政治,所指群体主要是不同的国家群体,如欧洲联盟、伞形国家、小岛国家联盟、七十七国集团(G77)、基础四国(BASIC)、金砖国家(BRICS)等等。这类群体内的国家关系,除欧盟例外,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联盟。从全球气候政治的参与主体来看,全球气候政治自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以来呈现出群体化的特征。所谓群体化,即单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如主权民族国家对某个群体的参与。根据符号互动论和社会心理学有关群体的认识,影响群体化的关键变量在于:a.群体化的背景或曰叙事情境,一种叙事情境直接为某个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活动舞台,比如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组织结构,为个体的社会化提供了行动场域或话语空间;b.行为体是否参与互动,即群体化还必须受到个体本身的身份选择和意愿的影响,现代的政治行为体多数并非政治社会化的囚徒,往往有选择之权利;c.互动本身可能对群体化产生过程动力,即群体的形成与群体化的维系,其动力来自该群体内部的行为体之间以及该群体与他群之间的持续互动。
也就是说,各个国际政治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政治中不得不表现出或多或少的“从众”行为,并尽可能“抱团”应对——客观上这与全球气候变化本身的全球公共问题属性紧密相关。但同时,具体到国家群体的重组,却耐人寻味,因为不得不承认,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论,与所有的环境议题一样,可以说是文化、世界观乃至思想意识形态之争[12]。具体到气候变化应对或曰气候治理,也同样存在典型争议:
其一,多边(multilateralism)与小众(minilateralism,或译作“小多边主义”)。有关全球气候治理的多边(主义),可以说直接源于国家间政治与外交互动中的多边主义情结。按照约翰·杰拉德·鲁杰(John Gerard Ruggie)较为理想的界定,多边主义指“一种制度的形式,以便三个(及以上)国家基于普遍行为原则而相互协调”。由于任何国家都不能被强制签署条约且随时都有退出之选择权,因而多边主义对制度化的程度要求极高——可以说多边主义的发生率并不会高于自助秩序(self-help order)[13]。显然,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议题领域,多边主义倾向于讲求平等、避免歧视,所生成的诸多环境机制也给发达国家增添了不少非对称义务,以确保对欠发达国家进行必要的扶持,进而尽可能发展/维系国际道义和公平。鉴于此,从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环境发展大会,到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再到1992年地球峰会,环境多边主义变得越来越复杂。从正能量效应和国际伦理来看,具体到全球气候治理,UNFCCC有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其相当于“国际平权行动”(international affirmative action)⑥般的实践,不仅仅归功于“G77+中国”这一群体化政治力量,且因联合国成员对诸如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安全等价值诉求的普遍认同而得到强化。
不难想象,按照多边主义的理想定义和我们在真实世界中外交辞令式的思维惯性,带有广泛包容性和战略选择弹性的多边主义更受欢迎——认为这至少可以无限趋近于全球气候政治公正的实现,并为迈向一个更具雄心的普遍协议增添了可能性。然而令人尴尬的两难境地是当前以联合国为主体的谈判,一方面可以说煞费苦心、无所不包,另一方面却终究难逃进展缓慢、举步维艰的窠臼,以至于在日渐临近的全球气候变化风险面前显得手足无措、惊慌无助[14]。鉴于此,多边主义的变体——“小众”(战略)应运而生,即在外交当中形成了小部分“志同道合”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应对当代严峻且重要的全球议程。这里提到的全球议程成了“小众”群体的共同关切:a.全球和跨国威胁(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战乱、贫困或流行性疾病),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b.某个议题(如气候变化)太过复杂而难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笼统应对,不得不拆解细分为若干个子议题(如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并以某种可操作的方式来应对;c.在多数成员国所组成的论坛中,促成问题解决的难度往往较大,因为这些成员国间的国家利益、管理方式和经济实力存在较大差异。应当承认,“小众”兴起的背后往往折射出对“大众化”的多边主义战略的“不满”,反映在全球气候政治互动进程当中,更多体现为对以UNFCCC为主导的多边主义的完善或补充。例如,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多边主义理应关注的核心利益之下,即使相关协定再精巧复杂,仍可能派生出仅关心自身实际好处(practical benefits)的小团体[15]。既然多边主义存在诸多瑕疵,便不能当作万能的济世良方,那么就有理由呼吁和期待某种更为精明、更具雄心的“小众”俱乐部,且该群体最好由“气候大国”(Climate Great Powers)组成,共同应对原多边主义框架下的顽疾,并为迈向一个全球方案而找寻新出路⑦。
事实上,不论多边抑或小众,所还原的无非一个共同的全球气候政治群体化图景。就实用主义的立场来看,从UNFCCC、京都机制为主体的全球气候制度,再到非正式国际机制下的气候政治互动,所谓的群体化气候外交体现出了灵活性。换言之,气候政治俱乐部(如基础四国的涌现)有助于克服庞杂而宽泛的多边主义难以避免的缺陷——负重累累、冗长的讨价还价过程、过多的投票权归属;无法为温室气体排放大户提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激励,或避免气候变化应对的搭便车行为;无法在全球气候政治体系当中维持权力的平衡;等等。因此,在迈向一个可能的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协议之时(2015年《巴黎协定》以降),群体化的全球气候政治或许在如何提高谈判/议事效率、协调(主要大国)俱乐部利益、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实践的国际合法性等方面显得更为窘迫。具体而言,小众方面,少数几个主要大国(如BASIC新兴大国之间)组建起来的谈判论坛可能推进对话和建立彼此间的信任机制,尽管这或许还难以从更为宽泛和根本的意义上解决深刻的利益分化或应对搭便车难题。毕竟,比起强有力的国际行动总难以避免遭遇国内政策优先偏好而言,减少游戏规则的核心参与者数量似乎无可厚非,从而有助于就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而尽可能达成一项协议。考虑到过往的气候政治俱乐部往往重在洽谈减缓行动,有关间接的/非气候目标如提高能源效率、技术革新乃至气候融资等,容易生成排他性的群体利益,这类利益反过来也将吸引成员加入并减少搭便车因素。换言之,在更为普适性的UNFCCC可能遭遇挫折的国际气候行动领域,小众群体大国被寄予厚望,从而达成关键性的协议——为高层次的政治对话创造机会,在可能的领域达成和解、建立互信。例如,历时九个月的双边对话,2014年11月宣告通过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就有关碳减排的关键议题,中美双方做出重要承诺,这一共同努力也一度被视作为2015巴黎大会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序曲或前奏⑧。
其二,新兴大国群体化与(传统)国家间政治。在群体化的全球气候政治当中,不得不提及的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群体的崛起⑨。可以说,后冷战时代以来,整个地缘政治版图极富戏剧性地发展,在于过往那些所谓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何以成长为替代往昔西方权力中心的新兴力量。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快速增长,这些新兴力量也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反映转变中的身份和利益诉求——从联合国改革到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再到对上文所述多边国际机制的重组,以期全球经济政治事务的现存主导模式能够发生对自身有利的转向(尽管这些新兴力量不见得都期望能颠覆现行秩序)。
这里,我们不妨仍以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为例,这几个新兴大国于2009年组成基础四国群体,该“准集体身份”的形成,反映了新兴大国群体崛起路径同传统国家间政治模式之间的交错重叠。当将目光聚焦在近似于上文提到的“小众”之时,基础四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乱象当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这不仅仅表现为该群体历次的首脑联合声明,抑或在全球气候政治协商当中尽可能“用一个声音说话”(从2009哥本哈根大会到2015年巴黎大会)。事实上,同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松散联合并“抱团打拼”的趋同行为让人联想起某种政治联合(coalition),哪怕这种联合或曰“共同努力”不过旨在达到“短期的、特定议题目标”[16]而已。理论上,从实用甚至功利的角度来说,少数几个具有“共同语言”的国家之间磋商相关议题的成功率毕竟也高于上述宽泛的多边互动⑩,更遑论这几个国家是后起的新兴大国。新兴大国“抱团打拼”,或曰群体化这一行为结果可能产生的国际政治效应暂且不论,在上文全球气候政治的制度结构形成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了诸多的(甚至有些僵化的)气候政治群体,如以全球气候政治领导者自居的欧盟(EU),以及JUSSCANNZ、俄罗斯和其他转型经济体国家、G77+中国、伞形国家(Umbrella Group)、“环境完整集团”(Environmental Integrity Group),等等。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以降,BASIC群体突现,且在气候政治诸多议题方面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这几个新兴大国表现出了相同或相似的立场(参见表1),为全球气候政治发展注入新活力,使全球气候治理呈现不同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元对立的“第三条路”——新兴大国协调作用突出、基础四国松散联合主导、多个群体之间相互重叠,进而为探寻集体行动难题的化解方法、重塑全球气候治理、争取全球气候政治公平正义等价值意蕴的实现而贡献力量[17]。可见,考虑到基础四国在全球气候政治竞争中寻求协调(coordination)、协作(collaboration)乃至合作(cooperation),群体化趋势也进一步凸显。这不仅表现为上述小众特定目标甚或个体需求所致小团体的日常会晤,而且还更缘于高度的可见性(high visibility)、有关重大议题表态时的相对一致性(relative consensus)(参见表1)、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渐趋明显的主导作用(leading role),BASIC未来甚至可被视作某种根基扎实的、真正的政治联合(a broad-based genuine coalition)。应当承认,《哥本哈根协议》多少反映了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集体行动难题时的尴尬,某种程度上“进一步退半步”也算是无奈之举。所幸的是,BASIC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以此为起点,气候政治领域的国家间关系亦得以局部重组,并在美欧相继受困于国际金融经济大危机、主权债务危机而对充当全球气候政治领导者“有心无力”的时机下,持续发挥更为深远的国际影响力;BASIC作为新兴大国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一种新联合,并非意味着削弱甚至脱离其原属发展中国家阵营(尤其“G77+中国”),相反还时常以诸如“BASIC+”的形式来邀请G77专家参与BASIC部长级例会,从而既提高了议事效率又增强了谈判能力和代表性。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以来,BASIC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仍将举足轻重,并在UNFCCC和KP机制为主体的制度结构变迁进程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表1 BASIC自哥本哈根大会(COP15)以来的主要谈判立场小结

表1 BASIC自哥本哈根大会(COP15)以来的主要谈判立场小结
谈判目标协议类型时间表资金机制防火墙 巴西力争KP第二承诺期强有力的减排目标KP有效期延长;为合法性议题赢得空间KP第二承诺期附件一国家承担历史责任 南非期待“双轨制”的法律约束力,但对法律的界定却语焉不详KP第二承诺期 印度附件一国家共同减排;超越KP而施行更为严格的举措协议形式应当由(谈判)内容来决定;合法性应置于UNFCCC框架之下KP第二承诺期绿色气候基金应基于公正并确保直接到位附件一国家承担历史责任 中国维护UNFCCC和KP的权威,增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团结合作附件一国家强制减排KP第二承诺期附件一国家承担历史责任
注:KP为《京都议定书》简称;表中空白部分意味着并非各国都对具体议题表达清晰立场,以资金机制为例,这多半为宽广的“G77+中国”群体所倡导(坚持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和技术支持等)而并不一定需要单个BASIC国家重申;有关时间表的同一参照,虽为BASIC群体共同偏好所在,成员国间却仍可能存在不同意见,比如巴西一贯以来纠结于推行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抑或更为温和的BASIC目标,往往表现出一种类似于“中间道路”(middle course)式的“骑墙”策略
其三,离心力、群体分化与重组。全球气候治理原本需要“同心协力”,但离心力的存在增强了集体行动难度,这种影响全球气候政治发展的惰力,存在于各个群体之中。从全球公民社会角度而言,离心力的克服,向心力或凝聚力的增强,或可能有助于全球气候政治难题的根本解决。相反,若缺乏稳定的内部秩序或互动关系,无谓的群体分化与重组,也可能堕入传统联盟政治和国家间关系的窠臼,甚或酿成大国政治的悲剧。近年来,美欧气候政治的分歧不断,美国特朗普政府更是退出全球气候政治《巴黎协定》,而欧盟自身也连续遭遇主权债务危机、英国退欧等“逆流”的侵袭,同样无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当然,发展中国家群体内部,不可避免也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如G77就存在分化的风险。
以G77为例,该群体创立于1964年的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反映了南方国家自独立以来共同应对发达国家挑战的联合立场。随着中国的加入,G77很快发展壮大,并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程序和制度,其主要目标在于代表南方世界的整体经济利益,增强成员国在联合国的谈判能力,促进南南合作。可见,其实单从历史回溯,所谓“G77+中国”早在UNFCCC框架构建之前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出于议题导向(如表1所涉及的协议类型/时间表/资金机制/防火墙),原本就在联合国各项议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发展中国家谈判群体,自身也在全球气候政治当中发生分化,即逐步裂变出至少四个子群体:除前述BASIC以外,还包括小岛国家联盟(AOSIS)、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最不发达国家(LDCs)。(其中,由44个小岛国家组成的AOSIS,由于气候变化带来海平面的持续上升进而可能招致灭顶之灾,要求国际社会强力应对全球变暖的呼声也最为强烈,尽管其自身的经济总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微不足道;由撒哈拉以南非洲及亚太地区49个低收入且经济脆弱的国家组成的LDCs,常被视作气候变化责任的豁免者以及资金援助的首要关照对象;OPEC由石油富国组成,其温室气体排放较高,倘若世界化石燃料消耗锐减,反倒可能对该群体造成冲击,因此OPEC在“G77+中国”中显得另类和特殊并且表现得相当活跃,利益关切亦同石油产业密不可分——由于掌握至关重要的石油资源,OPEC甚至被视作“谈判超级大国”(negotiating superpower)。正如我们从1995年第一届UNFCCC大会(COP1)以来所看到的,AOSIS始终表现得较为积极主动,甚至坚持要求尽快建立起强制减排的时间表。及至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AOSIS再次提议设立新的减排目标并赋予其法律性质,该提议第一时间得到来自LDCs的支持,然而这种支持之声较为微弱,甚至因招致OPEC和BASIC的共同反对而放弃;同样地,有关资金议题,虽说G77的整体立场保持高度一致(均要求更多的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但在具体的资金运行机制方面,四个子群体间又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可见,如同自然界的裂变一般,在UNFCCC框架下成长的G77难以达成绝对共识。
四、结语
全球气候政治的参与主体,包括主权民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且前者往往还占据着中心地位,“国家中心主义”一度也成为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进程的桎梏,使得全球气候政治仍徘徊、停留于国际气候政治。全球气候政治参与主体之间的频繁互动,形成了全球气候政治的制度结构,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进程为主导的国际气候变化机制复合体,辅之以非正式国际机制下的气候政治互动(如BRICS, G20, IBSA)。
就参与主体而言,全球气候政治呈现群体化的特征。与其说群体化是全球气候政治变化发展的某种“规律”运动,不如说是全球气候政治进路部分回归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之现实情境。群体化,既源于多边(以及小众)主义导向的国家行为体从众,又以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为时代特征(尤其反映巴西南非印度中国等新兴大国2009年以来形成的全球气候政治影响力),同时由主要大国个体行为趋同、群体崛起所引领的这种群体化进程,也同样面临着群体分化的风险(或重组之机遇——倘若1+1+1>3的话)。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的,“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8]。那么,对中国气候外交而言,群体化意味着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全球气候政治的群体化,为中国气候外交提供了广阔的行动空间——中国既属于“G77+中国”之“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世界,又是崛起中的新兴大国,而且还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国际机制同“全球北方”/发达国家世界频繁展开双边或多边互动;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群体化本身可能存在离心力和群体分化的风险——崛起的中国因此可能遭遇战略选择困境,由于快速增长和相对较强的综合实力,中国往往被动陷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伦理陷阱(ethic trap),成为发达国家群体甚至发展中国家群体的“众矢之的”,如此一来易遭遇“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可见,中国气候外交,需要有所侧重——坚持BASIC群体的主导地位,从而进一步增强新兴大国群体对全球气候变化风险的管控能力、提升新兴大国的国际话语权、提高气候政治对话和议事效率;利用时空上平行的BRICS和“G77+中国”,并结合中国在国内新能源研发、绿色经济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利益共同点,拓展发展中国家世界的气候政治合作空间。应当以BASIC为主导,同时以具体议题为导向(如适应、能力建设、低碳经济等)尽可能兼顾非正式国际机制的其他气候政治互动平台,以及对话与合作渠道,而不刻意追求一味迎合所有伙伴(反倒可能导致自己被孤立)。毕竟,全球气候政治群体化虽说客观上要求国家行为体更广泛深入地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体化毫无边界甚或以牺牲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的自身可持续发展为代价。否则,群体化也可能失去它本真的意义。
注释:
① 在全球化的意义上,“世界政治”与“国际政治”在政治权力主体、议题领域、结构特征等方面存在差异,参见David Held et a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9; 有关“气候变化的政治”的政治社会学反思,参见Anthony Gidde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② 参见David G. Victo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Warwick J. Mckibbin and Peter J. Wilcoxe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 16(2): 107−129; William D. Nordhau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2): 31−34.
③ Roderick P. Neumann, Political Ecology: Theorizing Scal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9, 33(3): 398−406; Sheila Jasanoff,,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0, 27(2−3): 239; Peter Newell and Matthew Pater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Bronislaw Szerszynski and John Urr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0, 27(2−3): 1−8.
④ 认为主权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仍难以撼动,参见Jean Gottman,,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75, 14(3−4): 29−47;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Robert D. Sack,,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3, 73(1): 55−74; 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3, 47(1): 139−174; Peter J. Taylor,,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4, 18(2): 151−162; John Agnew and Stuart Cordbridge,, London: Routledge, 1995;,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David Newman and Anssi Paasi,,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8, 22(2): 186−207; Anssi Paasi,, Geopolitics, 1998, 3(1): 69−88; Kevin R. Cox,, Oxford: Blackwell, 2002; Stuart Elden,,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Stuart Elde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0, 34(6): 799−817. 不过,有关主权民族国家“式微”的宏论亦汗牛充栋,较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参见Joseph A. Camilleri and Jim Falk,,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2; James N. 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Robert W. Co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tephen J. Kobrin,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8, 51(2): 361−386.
⑤ 参见Margaret E. Keck and Kathryn Sikkink,,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Craig Warkentin,,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Daniel Sobelman,, Strategic Assessment, 2001, 7(2): 30−38; A. Lawrence Chickering et al.,,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6.
⑥ “Affirmative Action”,又译作“平权法案”“肯定性行动”或“优惠性差别待遇”,最早起源于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为劳工就业市场的种族、宗教等问题而出台的非歧视政策,参见Judson MacLaury,, Federal History, 2010(2): 42−57, Available at: http://shfg.org/shfg/wp-content/uploads/2011/01/4-MacLaury-de sign4-new_Layout-1.pdf (accessed 01:00, 08/17/2018); 以“Affirmative Action”为视角来讨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参见Philippe Culle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9, 10(3): 555−558.
⑦ Moisés Naím,, Foreign Policy, 2009, 173: 135; Robyn Eckersley,?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12, 12(2): 24−42; Anthony Brenton,’, Climate Policy, 2013, 13(5): 541−546; William Nordhau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4): 1339−1370.
⑧ Suzanne Goldenberg,, The Guardian, 12 November,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 environment/2014/nov/12/how-us-china-climate-deal-was-done-secret-talks-personal-letter (accessed 01:30, 08/17/2018)
⑨ 尽管有关新兴经济体国家、新兴国家、新兴大国的界定可能存在不同的衡量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这些国家的综合实力持续快速增长,其对全球治理改革的需求也相应加大。参见Thomas Renard,, Europe, and the Coming Order, Brussels: Academia Press, 2009: 24−25;张宇燕、田丰:《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国际经济评论》,2010(4): 7−26;韦宗友:《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全球治理改革》,《国际论坛》,2011(2): 8−14;周鑫宇:《“新兴国家”研究相关概念辨析及其理论启示》,《国际论坛》,2013(2): 69;赵斌:《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形成机制——集体身份理论视角》,《当代亚太》,2013(5): 113。
⑩ Christer Jönsson,[A]//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London: Sage, 2002: 212−228; Pamela Chasek,,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005, 14(2): 125−137.
[1] IPCC. Climate Change 2001: Synthesis report[EB/OL]. [2001-09-29][2018-08-17]. An Assessmen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https://www. ipcc.ch/pdf/climate-changes-2001/synthesis-syr/english/question-1to9.pdf
[2] 严双伍, 赵斌. 自反性与气候政治: 一种批判理论的诠释[J]. 青海社会科学, 2013(2): 54−59.
[3] PAUL G. HARRIS. What’s wrong with climate politics and how to fix it[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4] ROBERT KEOHANE,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4th Edition[M]. New York: Longman, 2011: 30: 262.
[5] CLARE BREIDENICH, et al. The 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8, 92(2): 319.
[6] Q&A: The kyoto protocol[EB/OL]. [2005-02-16] [2018-08-17].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2/hi/science/nature/4269921. stm.
[7] NICHOLAS A. A. Howarth, Andrew Foxall. The veil of Kyoto and the politics of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 in Australia[J]. Political Geography, 2010, 29(3): 174.
[8] CARSTEN VOGT. Russia’s reluctance to ratify Kyoto: An economic analysis[J]. Intereconomics, 2003, 38(6): 346−349.
[9] JOHN VOGLER. The european contribution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5, 81(4): 835−850.
[10] EDWARD SAMUEL MILIBAND. The road from Copenhagen [EB/OL]. [2009-12-20] [2018-08-17] Guardian, http:// www. cfr.org/climate-change/guardian-road-copenhagen/p21030.
[11] ANDREW PAUL KYTHREOTIS. Progress in global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Reasserting national state territoriality in a “post-political” world[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2, 36(4): 458.
[12] ANDREW J. Hoffman. Climate science as culture war[J].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2012, 10(4): 32.
[13] JOHN GERARD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2, 46(3): 571−572.
[14] ROBYN ECKERSLEY. Moving forward in the climate negotiations: Multilateralism or Minilateralism[J].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12, 12(2): 34.
[15] DAVID VICTOR. Toward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Numbers,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J].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06, 6(3): 96.
[16] CHRISTOPHE DUPONT. Coalition theory: Using power to build cooperation[A]. // I. William Zartman, ed.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Approaches to the Management of Complexit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 1995: 148.
[17] 赵斌. 全球气候治理的“第三条路”?——以新兴大国群体为考察对象[J]. 教学与研究, 2016(4): 73−82.
[18]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人民出版社, 2017: 59.
Grouping in global climate politics: A research agenda
ZHAO Bin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Climate change is a hot issue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it is helpful to undertak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in order to fully recognize the puzzles and difficulty in the process itself, and to provide practical inspirations in seeking ways out. The present essay offer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articipants of global climate politics, believing that the global climate politics evolves gradually into grouping scenarios via widespread participations of sovereign nation-states and non-state agents. In the grouping process of world climate politics which carries with it systematic and chaotic effect, it is imperative for newly-emerging grouping powers to deepen coordination,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so as to promote together the development and good governance of global climate politics.
global climate politics;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participators; grouping
2018−04−20;
2018−07−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合作与中国气候外交研究”(15CGJ009)
赵斌(1985—),男,江西遂川人,法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英国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全球气候政治,联系邮箱:xjtuirzhao@163.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5.016
D829
A
1672-3104(2018)05−0138−09
[编辑: 谭晓萍,游玉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