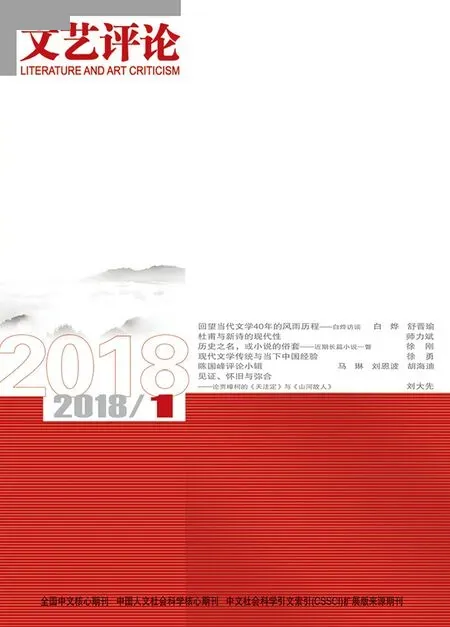论萧红短篇小说的时空叙事策略
2018-09-28楚金波
○楚金波
苏珊·斯坦福·弗莱德曼(S.S.Friedman)在1993年发表的论文《论空间化》中提出用“空间方式来理解叙事”的观点,即将叙事看作一幅坐标图,坐标图的横轴叙述单一的文本表层,遵从语言的线性特征,推动情节的由始至终发展,是“发生的事件序列”。纵轴则是被作者和读者占据的时空,在这样的时空中,他们通过赋意于文本,使文本可以和其他文学、历史文本和社会之间进行对话。这样,阅读叙事就“意味着阐释叙事坐标中横轴和纵轴之间的连绵不断的相互作用,包括文类规约、文学传统、对压制的政治校本的敏感度以及对符号及其象征意义的相互作用的认识等”①,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建构和理解文本的叙事极其重要。文本中事件发展在表层单一的横轴上,纵轴被外在强加层次众多的因素,且被反复书写。好的作家在具体的文学创造中,会采用很多策略加强横、纵轴间时空叙事的张力和粘合力,使叙事中的时间进程和空间拓展趋于复杂化,丰富文本的审美意蕴。萧红的短篇小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一、隐性情节的构筑
萧红小说,尤其是她的短篇小说擅于在横轴即单一故事情节发展中蕴涵隐性情节,这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弗莱德曼所认为的横轴只是单一推进故事情节表层的观点。其实横轴也可和纵轴一样复杂,萧红的短篇小说让表层情节和隐性情节两个横向分支相互交叉、相互影响,使小说的故事时空包孕得更为丰富。
《夜风》中,地主家以老祖母为首的兄弟七人一连几夜防卫马队的攻击为故事发展的表层情节,他们称马队为“贼东西”,当马队临近时,为了安抚和稳定地主家雇农的情绪,给每个雇农发枪,还骗不懂事实真相的长青之类的小雇农说马队的首领是万恶之极,专来杀小户人家,让雇农为保全自己小户人家而衷心效力于他。当长青和妈妈因为贫穷并且因为忠心地在严寒中为地主守护而生病危及到地主利益的时候,却被地主无情的辞退。单一的表层情节中包含着简单的人物(地主家的祖母、张二叔叔;雇农:长青、长青妈妈)、简单的事件,当故事发展到穷人无法生活下去,长青哭着哀求妈妈吊死在爹爹坟前的树上时,妈妈说了句:“孩子,不要胡说了,我们有办法的。”故事在此出现了转折,在文章结尾处被马队打死的地主张二叔叔“在一秒钟清明的时候,他看见了长青和他的妈妈也坐在爬犁上,挥动着拳头……”文本这时才显露出来隐性情节——穷人对地主的反抗浪潮,读者至此也豁然明了“马队”的含义,一场风起云涌的贫农反抗地主的斗争浪潮瞬间呈现于脑海之中。《看风筝》也是如此,情节简单,叙述老人在女儿惨死、儿子刘成失踪之后的生活遭遇和悲惨心境。小说中老人对儿子的追寻未果和儿子对老人的狠心丢弃形成故事的表层情节,当读到结尾“刘成不管他父亲,他怕他父亲,为的是把整个的心,整个的身体献给了众人……他为着农人,工人,为着这样的阶级而下过狱”②时才让读者一直费解的问题豁然开朗,简单的表层情节下交织着带领工人和贫农阶级的刘成及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从组织发动群众、与敌人斗争、到被捕的隐性情节。同样,《莲花池》中,作者也是把日本兵对中国发动战争——占有中国领土——蹂躏中国人民的故事情节隐含在对五六岁孩子小豆和爷爷相依为命的悲苦生活中,让日常生活的背后涌动着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挖掘出表层情节背后的隐性情节才使读者真正明了人们悲苦生活、麻木意识以及丧失自我状态的社会根源。萧红小说把时代风云变化的浪潮的隐性情节隐藏在具体平实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遭遇的表层情节发展中,让表层情节和隐性情节相互渗透,一方面可以更完整地理解表层情节进程中不能得到很好解释的某些因素,也丰富和拓宽了小说风云变化的时代背景。
萧红小说不仅善用隐性情节揭示时代特征,还能巧妙地利用其展现人物的心路历程和作家的主观意图。《牛车上》,小说以“我”为视点,叙述车夫舅父送“我”和去城里看儿子的女佣五云嫂的一件小事,表层情节单一。五云嫂诉说了她听到五云哥作为逃兵被军阀杀戮前后的生活变化,而听众就是曾经被征兵而后又叛逃的车夫舅父,文本通过两人的对话,把强硬被征兵、然后叛逃、最终被杀戮的无辜百姓遭遇的隐性情节暗含其中。而作为隐性情节的主角——车夫不经意的话语“我也有家小……”“都是想赚几个呀,才当逃兵去了!”鲜活地勾勒出了“逃兵”的心路历程。作家巧妙地以牛车的行进为主线,以五云嫂和车夫的对话为联结点,使表层和隐性情节相互交叉,形成内外两个富有张力的画面,一幅是牛车一路前行中优美的自然风景画,另一幅是蕴含其中的北中国军阀混战,劳动人民家破人忙、妻离子散的悲惨图景,两幅画面的纠结和对比鲜明地表达了创作者对当时社会控诉和无情揭露的主观意图。
萧红的短篇小说不仅以蕴涵隐性情节的方式丰富了横轴的情节发展,就在推进表层单一情节的发展中,也不仅是以时间顺序为主线,而是采用了多种叙事策略推进情节从“头”至“尾”发展。如《王四的故事》中把对王四的称呼的变化作为推进情节发展的主线,最开始的“四先生”,让王四体会到自己的重要性,这时的他精明、能干,因为别人的看重而更加负责,生活安然平静。而当他听到少主人称他为“王老四”时,他似乎一下子丧失了他原有的能力:懒惰、懈怠、没有了以前的精神,每天想着离开主人家能干什么,生活忐忑焦虑。河水上涨的那天,当他又被称回“四先生”的时候,他“好像又感觉自己变成和主人家的人一样了”,但是当他来来回回帮主人拿完东西的时候,他又回到被嘲笑的“王四”身份。文本中“四先生——王老四——四先生——王四”的称呼变化,展现了作品人物为主人家奉献的时间之长,自身内在心情的起伏变化对精神的摧残之大,地主压迫之下雇工命运之悲惨。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情节的发展对读者来说是一个心理渐进唤起的过程,情节由起始——展开——高潮——收尾,都隐约显示着作家和读者的审美心理轨迹。这里作家巧妙地利用了称呼的变化激发读者的审美心理变化,让读者慢慢深刻体味人物悲剧命运,也表达了创作者自身对社会和剥削阶级逐层深入的控诉。简短的故事结束了,但在读者心里却意味深长、回味良久。《桥》中,以桥头回荡的声音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主线,“黄良子——黄良——妈”的声音变化,叙述一个母亲因为贫穷而无法好好养育自己孩子的悲哀故事,读者也在这声声呼唤中达到审美情感喷涌的高潮状态。
由此可见作家的创作功力之强,她以多种方式推进故事表层情节发展,并在表层情节中蕴涵隐性情节这种独具匠心的叙事策略,使短小篇幅的单一故事中,蕴涵着宏大的时代背景和挣扎的人生百态。
二、隐喻功能的采用
苏珊·斯坦福·弗莱德曼(S.S.Friedman)在提出叙事的坐标图中,非常推崇纵轴的空间化叙事,认为纵轴可相对复杂,被作者和读者所占据,有很多外在强加的层次众多的因素,拓展了文本的叙事时空,萧红的短篇小说在空间化叙事上便采用多种策略完美地演绎了这种观点。首要策略便是采用了隐喻的方式。季广茂的《隐喻理论与文学传统》一书中认为,隐喻的涵义是指在彼事物的暗示之下把握此类事物的文化行为,重视文化学意义上宏隐喻(当然宏隐喻中包含了修辞学意义上的微隐喻)的作用。也就是说,隐喻具有揭示文化意义的功能。从这一角度来说,萧红是使用隐喻进行时空叙事的高手。
在短篇小说中,作家机智地运用隐喻来拓展故事的时空,使之蕴涵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桥》中,“桥”本身就是隐喻,“桥”是母亲与孩子联接的血脉,无桥时黄良子不得不每天早上绕道来到主人家,不得不每天翘首以盼看自己的孩子一眼,为不能给孩子擦鼻涕、送吃的而身心煎熬,时刻盼“桥”,而当“桥”真正出现的时候,因为阶级的差别,“桥”却成为母子相见的障碍,让母亲和孩子因“桥”而体味到切肤之痛,最后,当孩子因为不能过桥而被河水淹死时,“桥”成了剥夺穷人生命的匕首,彻底杀死母亲的孩子。在这里,萧红在设计隐喻的意象“桥”时,让其一直贯穿文本始终,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桥”隐喻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而正是这种变化,让其背后母亲对孩子的挚爱之情,阶级压迫对亲情的践踏和摧残,以及生命的高贵与卑微的对照才尽显其中。而另一部作品《看风筝》与此不同,萧红以朴实自然的笔触描述了老刘丧女后,穷苦无告时对儿子的追寻,而儿子刘成忍痛拒绝老父投身革命的故事。故事中具有隐喻意义的“风筝”意象只出现在文章的结尾:“一个初春正月的早晨,乡村里的土场上,小孩子们群集着,天空里飘起颜色鲜明的风筝来……刘成的父亲也在土场上依着拐杖同孩子们看风筝。”③这时,老人听到了刘成被捕的消息。春日的“风筝”隐喻为企盼和希望,是父亲对儿子的牵挂和思念,放飞的“风筝”投入蔚蓝的天空,也隐喻革命者刘成追求革命理想、无畏献身的英雄行为。作者让父亲在这样的情境中听到儿子被捕的消息有似鲁迅先生《药》的结尾,为父亲、儿子以及未来的革命留有一点明亮的色彩,是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象征。
对于隐喻现象最具实证主义色彩解释的“情感论”理论认为,“隐喻的基本功用不是把握外部客观世界,不是以一种语言单位替换另一种语言单位,而是激发情感,隐喻具有很强的情感冲击力”④。萧红作品《牛车上》,那贯穿文本的五云嫂戴的“头巾”,就很好地说明了隐喻的这一功用:下车采野花时,“她的头巾好像是在飘着”,当和车夫诉说丈夫当兵走了,“她的蓝布头巾已经盖过了眉头”,当我问五云哥阵亡她是否哭时,“她没有睬我,自己在整理着头巾”,当说到要抛弃儿子自杀又不舍时,“她用包头巾像是紧了紧她的喉咙”,当决定背孩子回家继续生活时,“那蓝色头巾的角部,也随着她的下颚颤抖了起来”,当听到车夫说自己也有家小时,她把“头巾放松了些”。文本中五云嫂“头巾”,既符合她的身份,也是不同情况下内心复杂情感的精当展现,否则任何对当时随情境变化的内心情感的语言描述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萧红短篇小说中,隐喻几乎处处都在,但每篇出现的方式都不尽相同,《王四的故事》中那个关乎王四命运的“手折”,《莲花池》中小豆向往的那个“莲花池”,《夜风》中地主家老祖母手中抖动的“小棉袄”,《离去》中那个黎文幻想着的“海洋”,都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也正是这些隐喻的使用,使萧红的短篇小说从有限的文本中挣脱出来,赋予其身临其境的语境、丰富复杂的情感、鲜明的主体意图以及宏观的文化背景等超语言因素的内涵,拓展了文本的空间。
萧红的短篇小说创作带有诗化和散文化的特征,因为除隐喻之外,明喻也是萧红在创作过程中擅长的修辞方式之一。明喻在萧红作品中出现的方式比较特别,除展现其本身的鲜明性和生动性之外,还有一定的语义上的丰富性、心理蕴涵性以及社会文化认知性,这种用法应和了学者季广茂的观点:明喻和微隐喻作为修辞手法,层次上并列,但都隶属于宏隐喻范畴,具有宏隐喻功能。《王阿嫂的死》中,死了丈夫、挺着怀孕大肚子每天给地主劳作的王阿嫂“瘦得像一条龙。她的手也正和爪子一样,为了拔苗割草而骨节突出”;而张地主则“手提着苍蝇拂,和一只阴毒的老鹰一样,振动着翅膀,眼睛突出,鼻子向里勾曲调着他那有尺寸的阶级的步调从前村走来,用他那压迫的口腔来劝说王阿嫂”⑤。这里运用明喻手法在揭示两个鲜活的人物特征时,背后的阶级特征和不同的阶级关系也一目了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当干活时谈论王阿嫂的人们看到张地主来时,“她们的头就和向日葵般在田庄上弯弯的垂下去”。向日葵本是向着太阳生长,而遇到地主的低垂生动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带给农民阶级的黑暗现实,表明农民阶级被压迫之重。当看到妈妈垂死挣扎时,小环“是一个被大风吹着的蝴蝶,不知方向,她惊恐的翅膀痉挛在振动”⑥,一只“蝴蝶”的形象把一个五六岁瘦弱小女孩的无助、惊恐表现得淋漓尽致,读来不免满心悲哀。《小六》中,当小六家搬家时,孩子顶着一块大锅盖,蹒蹒跚跚大蜘蛛一样从楼梯爬下来,形象的比喻勾起读者的好奇,为下文故事的展开定下情感基调。因为被主人逼迫搬家又不知搬往何处之事所折磨,所以女人(孩子的妈妈)每天“和患病的猪一般在露天的房子样哼哽的说话”⑦,女人坐在灰尘中“好像让她坐在着火的烟中,两眼快要流泪”,爹娘因为搬家“像两条狗似的打仗”,孩子在父母的吵架声中“像有火烧着她一般,暴跳起来”,明喻的使用活画出一家人被压迫到穷困至极时的非人生活,进而展现这种生活之下人的扭曲心理。五云嫂在诉说丈夫被征兵,之后杳无音信,再听说阵亡的故事时,她的说话,“好像落着小雨似的”(《五云嫂》),其实是五云嫂的心头在下雨,是因为生活不易和思念丈夫的内心哭泣;当李妈听说心中的爱人金立之要出发去前线打仗时,“她几乎不能站稳,就像有风的水池里走着的一张叶子”。(《朦胧的期诗》)悲戚心情尽现。此种手法的运用,是让读者和人物发生情感共鸣的时候,使背后的军阀混战给人们生活带来苦难的社会现实凸显出来,表明作家批判现实的主观意图。
在作为彼类事物的暗示下把握此类事物文化行为的隐喻被剥去其语义因素之后,会发现其内在是在彼类“感官”的暗示之下把握本应由此类“感官”来把握的事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通感”。通感,心理学上称作联觉(synaesthesia),“艺术通感实际上是由审美心理时空的整合作用所引起的各种感觉材料的相互联系,即时间感和空间感的彼此沟通。艺术通感中最常见的就是听觉向视觉和其他感觉的渗透。听觉具有流动性,是时间感的标志”⑧,视觉和其他感觉具有延展性,是空间感的标志,当具有迷茫性和朦胧性的听觉(时间感)向视觉和其他感觉(空间感)转换的时候,美感的真切性和具体性就会生成,审美心理时空的这种互渗与融合,除了促进人的审美体验和艺术感觉的丰富化外,还有利于读者以自己全面的本质力量(听、视、嗅、味、触觉)来把握审美对象之外的文化时空。
萧红的短篇小说中使用通感的地方虽然不多,但每个都很精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受限于时间的小说文本拓展了文化空间视域,深化了小说的主题。《莲花池》中,那个自幼丧父、母亲改嫁,与爷爷相依为命的瘦弱单薄的可怜的孩子小豆,日复一日地独自一个人蹲在窗口里,怕被其他孩子欺负不敢出门,对门口小莲花池里的花草充满着渴望。突然有一天被爷爷领上街,听到爷爷的嘴里吐出来一种带香味的声音:“你要吃点什么吗?这粽子,你喜欢吗?”这句话时,我们可以想见在每天吃不饱、孤独的孩子内心会激起怎样的美好感受,“香味”是孩子感知生活的角度,“带香味的声音”使孩子从类似动物的精神麻木的状态中转化为人,听觉和味觉的转换,是孩子心理时空的巨大跳跃,是孩子的纯真和人性的渴望复归,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描述和控诉。《朦胧期的诗》中,当作为佣人的李妈知道心爱的男人金立之要去前线,来到湖边听到因为金立之喜欢而自己才喜欢的军歌,也产生了厌恶的情绪,说那歌声“就像黄昏时成团在空中飞着的小虫子似的,使她不能躲避”,声音的不绝于耳的听觉朦胧感转化为无法躲避的小虫子叮咬的触感,使李妈此刻复杂的心情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看风筝》中,当父亲听到期盼已久、杳无音信的儿子就在眼前,在跑去相见的过程中,极大的喜悦调动了他所有感官:“三年前离家的儿子,在眼前飞转。他心里生了无数的蝴蝶,白色的空中翻着金色闪着光的翅膀在空中飘着飞。此刻凡是在他耳边的空气,都变成大的小的音波,他能看见这音波,又能听见这音波。”⑨这里各种审美感受的相互转化和融合,读者可以想见一个衰老父亲奔跑的速度,把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期盼、渴望相见,将要见到的狂喜等各种复杂心情表现出来,极大地丰富了创作者、作品人物和接受者的审美主体经验。《后花园》描写后花园一种花——大菽茨,“这些花从来不浇水,任着风吹,任着太阳晒,可是却越开越红,越开越旺盛,把园子煊耀得闪眼,把六月夸奖得和水滚着那么热”⑩,视觉和触觉的联通,使读者在审美心理上描绘出花开满园热情的盛景,展示大菽茨旺盛的生命力,也揭示出作者对后花园美好的回忆、对童年美好的体验和对当下生活的深入思考以及热烈追求的心境,这里通感的使用极大地拓展了创作者和接受者的审美心理时空。
三、声音叙事的设置
萧红以诗和散文的笔触在短篇小说中叙写小人物的人生,除巧妙运用隐喻来拓宽小说的空间画面和心理视域之外,声音叙事也被萧红用到极致。出于对苦难和悲情的展现目的,萧红的短篇小说从来不是静静的描述和诉说,总是有一种喧嚣的声音弥漫其中。她擅长在故事发展进程中设置声音效果,为读者营造一种新的感知方式,在声音的场域内使意义与声音合二为一,相辅相成,生成文本新的审美境界。
首先,声音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作品人物的情感表现空间。在叙事性的作品中,线性的文字叙事有时难以表达云雾状的心理空间,但如把声音的描写穿插其中,增强声音场的感染力,可以极大地彰显人物的心理活动空间和情感的表现。作品《小六》中,贫穷的小六一家被房主逼迫着搬家,又不知搬往何处,于是小六爹爹和妈妈之间因为走投无路而互相怨恨、吵架、寻死的场面陆续上演。在对如此喧闹生活的叙事中,作家一直把蟋蟀的叫声放进来,被逼迫搬家前的夜:蟋蟀在很厉害地吟鸣着,于是爹和娘在蟋蟀喧嚣的背景下开始因为生活琐事而争吵;在被逼迫搬家时,蟋蟀也是整夜整夜吟鸣,小六的全家就在蟋蟀吟鸣里向着天外的白月坐着或者被搬家逼得疯子似的娘和小六爹在蟋蟀的吟鸣中像两条狗似的厮打;当小六娘抱着小六去“跳湾”寻死时,蟋蟀依旧在墙根不停地鸣叫。萧红把自然蟋蟀音响和人事嘈杂的声音混在一起,既勾画出小六一家居住条件的恶劣(处处有蟋蟀叫,说明房屋何等简陋),也在叙说小六一家每个人的内心情感庞大郁结后的宣泄,那种对生活无奈、无助、崩溃的内心体验在蟋蟀的哀鸣中昭然若揭。
有时声音的设置是为了表达作家内心的情感体验。如《哑老人》,讲述了一个哑老人故事,生活贫苦,以乞讨为生,又不幸患了半身肢体不能运动的病,可怜的他每天只能睡在地板的草帘上,苦苦等待在工厂上班的孙女带点吃的回来,孙女因为照顾他而被女工厂头毒打致死,老人最后因无人照顾而被火烧死。作家以哑老人为视点进行描写,每个场景都配以破窗纸的叫声,当老人睡在地板的草帘上,苦苦等待孙女回来时“满窗碎纸都在鸣叫”、当老人吃了孙女买的包子后,点起他的烟管时“窗纸在自然的鸣叫”、当看到孙女因为感动和悲苦而哭,哑老人摇着枕上的头,胡须震荡着,这时“窗纸鸣的更响了”、当孙女几夜未归,虽然是怎样地饿,但老人仍然耐心地望着烟纹在等,“窗纸也像同情老人似的,耐心地鸣着”,当老人已预感不测,取出孙女的照片,把躯体偎作绝望一团的哭,然后又在抽烟,此刻是“窗纸不作鸣的时候”,最后,当老人在燃起的烟火中翻滚,而后被烧死,窗纸便不再鸣叫了,一切恢复到近乎悲哀的平静。“窗纸”鸣声既是哑老人悲苦心情和悲苦命运的写照,也是作家同情关注的眼眸。对哑祖父的描写勾起了作家深刻的童年体验——和祖父之间至深的情感,这种积淀在内心深处的情感使作家在描写文本中以乞讨为生的可怜的祖父形象时,配以窗纸的各种哀鸣,这里有思念、有不平、有控诉、有同情,也有对生活和现实的感伤和无奈。最后,不再鸣叫的窗纸既是老人生命的完结,也是作家情感达到制高点的体现。
其次,叙事采用声音的转借形式来传达女性的话语需求。热奈特认为:“叙事本身就是一种话语,”苏珊·S.兰瑟提出“个人的、集体的、作家的三种叙事模式”⑪。从这样的层面来讲,声音也是有意味的形式,通过它对声场的营造过程,传达出声音背后的人对话语权力的需求。《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不同时期的“嚎叫”演绎了她的一生。在拾起丈夫王大哥被地主烧焦的骨头时,用凄惨沁血的声音发出嚎天的哭声,这哭声越过草原,穿过整个树林中的老树,直到远处的山间,发出回响;当丈夫被烧死之后,王阿嫂天天痛哭,当王阿嫂遭受分娩之痛时,后山的虫子,不曾间断地在叫着,当小环捧着瓦盆爬上坡,去后山竹三爷借米的时候,听到山上的虫子憔悴的叫声,虫子的哀鸣也就是此刻王阿嫂的痛苦和哀鸣,最后,王阿嫂在炕上发出她最后的沉重的嚎声后死去。王阿嫂的嚎哭——流泪——不间断的叫——憔悴的叫——最后的沉重的嚎声,一方面推进王阿嫂的故事进展,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穷人,尤其是穷女人由“人”变成“虫豸”再到死亡的悲惨命运历程,王阿嫂的嚎叫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女性在男权制仍旧根深蒂固的农村里自己抗诉的声音,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作家对社会的强烈控诉。
其三,有时声音叙事本身被赋予双重意义,包孕了广阔的时代文化特征。如《夜风》中的“风声”:当远村狗吠的时候,像人马一般的自然界风声也吹上来了;当马蹄响声接近的时候,风声也更恶了;风声总是刮得更紧,刮得铿锵有声,以致整个树林都在呼啸;两天以后时代的风声更紧了,最后,地主张二叔叔在“不是夜,也没有风”的光明的朝阳下倒地。作家在构筑故事时插入的“风声”既是自然界的风声,是故事发生的时间交代和背景衬托,也是长青和妈妈因风感冒后被辞退等事件发生的条件;另一方面,“风声”也是当时穷人反抗地主的时代浪潮和社会环境,声音的插入极大地彰显了时代文化特征,使作品的描写和情感表达更有力量。
萧红在短篇小说时空叙事中,处处从小人物的平凡生活入手,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斗争、日本对中国领土的掠夺、国内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蕴涵其中,描写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贫民凄苦的生活状态,刻画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创伤,也是作家对自身人生体验的反刍。叙事中横轴采用表层情节和隐性情节的交叉互渗推进叙事进程,纵轴采用隐喻和声音延展叙事的时间和空间,把叙事话语同文本、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紧密结合起来,使短小的文本篇幅中包孕了广阔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意义。萧红时空叙事策略的采用拓展了中国乡土文学传统的诗性模式,深化了读者对乡土世界曾有的认知,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①唐伟胜《叙事》[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②③⑤⑥⑦⑨⑩萧红《离落残红》[M],武汉:崇文书局,2013年版,第21页,第21页,第7页,第8页,第29页,第20页,第118页。
④季广茂《隐喻理论与文学传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⑧童庆炳、成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页。
⑪[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