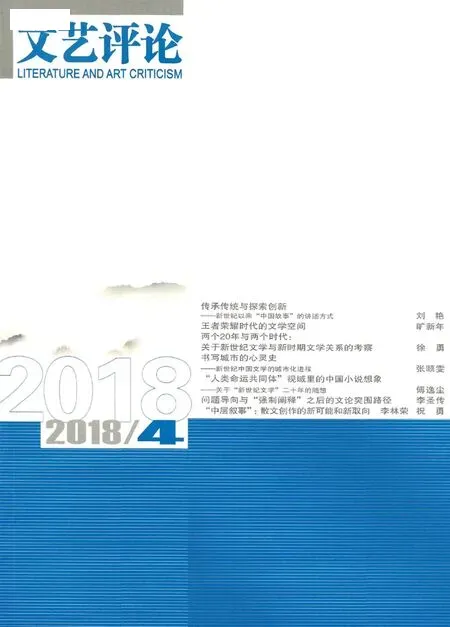传承传统与探索创新
——新世纪以来“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
2018-09-28○刘艳
○刘 艳
从2017年底文艺界对五年来的文学创作,从小说,到诗歌、散文等题材领域,作出全面回顾、总结和展望。其中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在累积中国经验和进行中国叙事的探索方面,是成绩斐然的。而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应该说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有意无意当中、却又几乎是殊途同归的一种创作指向。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其实是新世纪以来有艺术追求的小说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的艺术探索,“每位小说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勘测与这一问题的‘切线’,从而明确自己讲述‘中国故事’的路径和方法,在对能与不能、为与不为的思考中,寻找自身创作的伦理落位,为作品意义的生成提供一个稳定的价值支撑”①。比如,贾平凹对讲述“中国故事”、传达中国经验有长期和系统的思考,坚持将自己的思考贯彻于小说创作,并因此而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文学观念,探索小说文体和话语构型的独特方式。而借径研究作家如何累积中国经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也就是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如何还原和构建中国形象,等等,不仅可以助益我们考察和解析作品意义生成,还可发现有价值的叙事探索,厘清文本表层所容易引起的误读障蔽,达致文本深层和内部肌理;不仅可以发现作品的内容和意义生成方面的意义和价值,还可藉此探索小说在形式——也就是语言、结构、小说文体等方面的呈现形式。
传承和创新,可以说是讲好中国故事能够打开乃至双向打开的路径和方法维度。在有的研究者看来,在文本试验或者挑战既定的历史经验和文学经验方面,“50后”作家近年做得尤为突出,“他们不断地要越过界线,突破自我,穿透历史,挑战现实”,贾平凹在20世纪末力作《怀念狼》之后,新世纪以来《秦腔》《古炉》《老生》等,“也无不是在历史意识、现实感和文本结构、叙述方面不断越界”。“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蛙》都在极为大胆地探索,寻求把传统小说、戏剧经验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经验混合一体的方法。”所以研究者甚至说:“如今最保守的创作经验由20世纪50年代作家坚守,最激进的创作经验也是由20世纪50年代作家做出的。”②的确,“50后”作家既有挑战历史经验和文学经验的突破自我与越界探索精神,又在这探索创新里面,尝试传统小说、戏剧经验等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经验如何混合为一体的方法,这里面就同时涵蕴了创新和传承两个维度。探索创新中深蕴传承传统,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哲学、杂书杂著乃至戏曲等的影响,都可以落迹于小说当中,对小说语言、结构、叙事等小说文体方面,发生多方面的影响,即便羚羊挂角,却是有迹可循。在贾平凹、莫言等作家的创作当中,都可以发现他们在小说写作中的这方面的有意或者自觉探索,比如对戏曲经验的借鉴和化用,对古代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借鉴和化用,贾平凹《老生》即是生动的例证。创新,也就是作家在讲述中国故事时所作的叙事和小说文体探索方面的创新,从中可以发现1985左右开始的一段先锋文学经验在当下变异、转型和续航(吴俊语)的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两个维度上打开,一个是当年的先锋派作家在当下的转型或者说是续航,一个是非先锋派作家汲取先锋文学经验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在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等方面进行具有先锋精神的叙事探索。
接续传统,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即已发轫,可视作先锋文学在形式主义和叙事圈套的极致实验和体验之后的一种有意的回调,而近年来这条脉络也很清晰。2017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赵本夫《天漏邑》,堪称佳作,小说作了叙事上具有先锋精神的探索,但它对中国古典小说传奇文体资源和经验的成功借鉴,亦是毫无疑问的。金宇澄是《上海文学》有着三十多年资深经验的老编辑,以一部长篇《繁花》一举而红,大量沪上方言,旧日海上文坛的笔法,作家将近半个世纪的上海生活和家长里短方方面面俱娓娓道来,以一种老道的讲述体,让人重温古典话本小说的讲述体风格。小说借用说书人的形式,与读者——听书人彼此需要当中,产生了这样一个小说文本。作者自言:“话本的样式,一条旧辙,今日之轮滑落进去,仍旧顺达,新异。”《繁花》,有人从中读出了《繁花》是向《红楼梦》致敬的作品,有人从中读出了《海上花列传》的精神韵致——可以说它是对沪上文脉、古代文学文化传统的一种命脉传承。“70后”女作家付秀莹长篇处女作《陌上》,小说采用了古典小说散点透视的笔法,语言诗意、诗化,显示了抒情传统在当代的传承。又不失明清白话小说的韵致和古典的韵味,有人禁不住要去找寻它与《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传承与关联性。能够写出当今社会华北乡村的乡民日常生活的风俗画,能够将非震惊体验而是日常生活体验写得可圈可点,得益于古典写作手法及语言对她写作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她而言,是潜移默化的。
滑入旧辙的今日之轮,不止金宇澄等人。贾平凹可能是当代小说名家中对古代体悟最多最深的一位,他对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哲学、杂书杂著(天文、地理、古碑、星象、石刻、陶罐、中医、农林、兵法等)和戏曲,涉猎颇多,令传统如墨透纸背一般,浸润了他的文学创作。《带灯》后记他写道他由“喜欢着明清以至30年代的文学语言”,转而“却兴趣了中国西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无论哪种风格,都表明他对古代文学的偏好和文体风格的借用,《带灯》有对中国古典史传传统和传奇文体特征的参鉴。贾平凹2014年出版的《老生》,他把陕西南部山村的故事,从20世纪初一直写到今天,其实是现代中国的成长缩影。小说通过一个唱阴歌的、长生不死的唱师,来记录和见证几代人的命运辗转和时代变迁,通过老唱师念一句、我们念一句的方式,加进了《山海经》的许多篇章,更加意味着贾平凹在“我得有意地学学西汉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带灯》后记)。通过一个《山海经》,贾平凹几乎是将整个20世纪的历史接续起了中华民族的史前史。在贾平凹的读书札记里,可以知晓贾平凹是反复披览《山海经》的,甚至犹觉不足、还曾特地跑到秦岭山中去一一对照。这样来看,他化用《山海经》入小说,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极花》里,贾平凹如数家珍自己,细数自己“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阐发如何以水墨画呈现今天的文化、社会和审美精神动向,以一部《极花》写出了中国“最后”的农村。在最新长篇《山本》后记当中贾平凹写道:“几十年了,我是常翻老子和庄子的书,是疑惑过老庄本是一脉的,怎么《道德经》和《逍遥游》是那样的不同,但并没有究竟过它们的原因”;“突然醒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对了,我面对的是秦岭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我了吗,我与历史神遇而迹化,《山本》该是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随便进入秦岭走走,或深或浅,永远会惊喜从未见过的云、草木和动物,仍然能看到像《山海经》一样,一些兽长着似乎是人的某一部位,而不同于《山海经》的,也能看到一些人还长着似乎是兽的某一部位。这些我都写进了《山本》。”韩少功的《日夜书》以近十个主要传奇人物的叙事组合而成长篇,很得古典笔记体传奇小说的精髓,写出了后知青一代的精神史。接续传统,并不是一味滑入旧辙,从中,我们亦看出作家的一种艺术创新的意识,看到了作家不懈的艺术探索和创作追求。讲好中国故事,传达中国经验,“让世界读懂当代中国”,是像贾平凹一样的作家自身创作追求的具体践行。在接续传统当中,是作家创新的艺术探索之路的不断延伸,也是作家具有高远境界、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其实是中国的小说写作,在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化、古代文学与现代小说形式创新之间的一种有效平衡和融合。这种探索,也是一种创新。
传承传统还体现在对古代“传奇”文体资源的借鉴上,有学者对此作过周详而细致的论述。③兴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更加蔚为大观,并且在改编的影视剧中更加火爆的“新革命英雄传奇”,有都梁的《亮剑》、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石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等等。这些作品虽在创作理念和艺术特色等方面有所差异,但都是对明清古典英雄传奇的文体资源加以借鉴、继承和转化。古典传奇和野史杂传、为民间人物立传的书写传统,也同样影响着“新革命英雄传奇”之外的很多作家的写作,包括乡土小说和“50后”“60后”“70后”作家的写作。迟子建新世纪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等小说都可见传统的注入,《晚安玫瑰》等则有着对古代以来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赓续,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也是时有隐现的。在迟子建晚近的《群山之巅》,差不多是用一种野史杂传的笔法为龙盏镇的众多小人物画像立传,小说在辛开溜、辛七杂、辛欣来、安雪儿等人物的传奇组合结构当中,见出作家向中国古典小说史传与传奇传统借鉴的功力。而当下作家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传统,据说也是可以寻见的。石一枫则以《世间已无陈金芳》《营救麦克黄》《地球之眼》等中篇小说和最新长篇《心灵外史》,被认为是以创作接续了中国自新文学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条文学流脉——社会问题小说——这是近代和现代的传统,④也被认为是为讲述中国故事、积累文学的“中国经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继承先锋文学的经验,进行具有先锋精神的叙事探索方面,先锋文学的成名作家,凡是不能够突破自我的,近年创作多出现江郎才尽态势和面临创作方面的窘境。而凡是能够成功转型或曰“续航”的,其创作态势都非常可喜、不断有斩获。新世纪以来,当年的先锋作家,皆有新作问世,苏童的《黄雀记》、余华的《第七天》、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望春风》、北村的《安慰书》等,从中可见先锋作家艺术主张与写作实践的有意调整,昭示出先锋作家从先锋向常态化回调的一种努力,也在提示我们,先锋文学经验在今天是否还可能存在,并且以何种方式在继续生长和变异?其中,有的作家直接将现实事件乃至新闻事件“以一种‘景观’的方式植入或者置入小说叙事进程”,是值得警惕的,越来越依靠新闻事件和材料来写作,所滋生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生活在眼下,诗却在远方,生活积累和经验的匮乏,单纯靠闭门造车式“虚”构,可能是制约当下很多作家创作的一个瓶颈,亟需突破。
评论与创作是存在相关性的,并与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互相关联。2015年以来评论界在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先锋文学”作出回顾和反思、总结。当然,对于先锋文学精神,可不仅仅是停留在纪念层面,文学期刊和出版社,也仍然在以实际的举措,探索先锋文学精神与文学经验的当下可能性。像《花城》杂志一直被视为先锋派文学的重要阵地,花城杂志、花城出版社培育和形塑了北村、吕新等先锋文学作家。2016年,《花城》杂志刊发了吕新的《下弦月》和北村的《安慰书》,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并且重版了他们的代表作《抚摸》和《施洗的河》。近年来,《花城》杂志仍然一直在着力刊发像严歌苓《上海舞男》(2015年第6期)这样带有叙事先锋探索精神的作品。北村《安慰书》,小说在较好处理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之外,依然可见潜藏于其中的先锋精神和作家着意所作的叙事方面的先锋性探索,已经堪称先锋文学转型或者续航的佳作。近年来,非当年的先锋派作家,在写作中反而往往在叙事探索方面,颇具一种先锋探索精神。
新世纪以来,海外华文作家在“中国故事”讲述方式方面,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严歌苓、张翎、陈河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新世纪以来,严歌苓在《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和《陆犯焉识》等长篇小说中,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女性视阈当中历史与人性的双重书写,让她的作品溢出了以往宏大叙事所覆盖的主流历史的叙述法则。《寄居者》是“沪版的辛德勒名单”,《金陵十三钗》是女性视阈中日本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还原;《小姨多鹤》,可以视之为“抗战后叙事”,小说同时采用多鹤作为日本女性的“异族女性视角”与中国人的视角,来反观日本侵华战争给两国民众造成的伤害;《陆犯焉识》,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磨难史与家族史,更表达了“始终错过的矢志不渝的爱”的“归来”主题。严歌苓将“中国故事”在历史维度的打开和呈现,不是很多研究者所说的纯粹的“他者”叙述,而是叙述里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是可以和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叙述相兼容的;更可以给中国当代文学在历史层面的叙述,提供可参鉴的价值和意义。⑤而近几年的《妈阁是座城》《上海舞男》《芳华》,严歌苓已经把回溯性叙事的中国故事向中国当下的现实生活伸展和延伸,小说在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等方面的探索,为“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提供了宝贵经验。她的《妈阁是座城》在结构、叙事以及由之关涉的对人的情感、人性心理表达的种种暧昧繁复等方面的写作尝试,对于当代小说如何在形式方面,如何在结构叙事等方面获得成熟、圆融的现代小说经验,提供了不无裨益的思考并且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另一长篇《上海舞男》,小说故事核看似俗套——有钱女包养了舞男的故事,但小说的叙事方面的探索,是值得称道的。小说“套中套”叙事结构的彼此嵌套、绾合,突破我们生活的四度空间、直达五度空间的“绾合”式小说叙事,近年来的海外华文作家,像陈河、张翎、严歌苓等,他们通过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方面的先锋性探索,以其创作在构建一种中国叙事和中国形象。且不说陈河《甲骨时光》在多维时空交错、迷宫式的叙事结构等方面的卓异探索,就是严歌苓,令人叹佩的写作高产之余,也不断在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方面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毫无疑问显示出海外华文作家“中国叙事”所具有的先锋性。严歌苓最新长篇《芳华》则显示了另外的不一样的叙事探索,也是有意识的叙事创新精神。张翎的《流年物语》和最新长篇《劳燕》,在作“中国叙事”时也进行了诸方面的叙事探索,“物”或者“动物”的叙事视角,两个长篇里都有采用。《劳燕》还采用了三个灵魂——当年在美军月湖训练营是朋友的两个美国男人和一个中国男人在201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70年后相聚,每个人吐露自己所掌握的那一部分真相,以多声部的叙述和追述,还原和补缀出当年发生在月湖的全景历史。似乎是一种“鬼魂叙事”,其实已与海外华文写作中素有的“鬼魂”叙事传统——其惯常的魔幻现实主义意味、西方人的东方想象、某种后殖民文学的色彩或者兼而有之——有着根本的不同。也与有的作家以新闻素材拼贴入小说的“鬼魂”叙事,迥然有异。在素材和写作上,开启抗日战争叙事的新维度,是第一次将美军训练营作为题材入小说的尝试。
当然,海外华文作家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并不是只着意于先锋性的叙事探索,古典文化、文学的借鉴和化用,同样可见。陈河的《甲骨时光》就是典型的例证。陈河在《甲骨时光》中大量借用和援引古代典籍和纪实性材料。陈河凭藉《诗经》里的短诗《宛丘》“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就塑造出了与贞人大犬相爱的巫女形象,写出了一段最为伤感的爱情。相较而言,陈河对考古材料的倚重和借鉴,更加突出和明显。陈河仔细阅读了李济的《安阳》,上下册的邦岛男的《殷墟卜辞研究》、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杨宝成的《殷墟文化研究》、郭胜强的《董作宾传》,等等。⑥《甲骨时光》把大量的史料穿插在小说的诗性叙述中,诗性虚构出一个民国与殷商时期的中国故事。《甲骨时光》是通过杨鸣条对甲骨的寻找、甲骨之谜探寻发现的当下叙事以及与之对应的古代殷商的故事这两套叙事结构中完成对中国故事的构建的,杨鸣条一次又一次在与大犬的神交中返回商朝,两套叙事结构所构建的中国故事得以完整呈现,一个美学层面的中国形象也逐渐浮出水面。
近年的长篇小说写作,还在提示我们,文学创作在当下重新建构宏大叙事的可能性。中国文学,继承并创造性地转化当年的先锋文学的文学经验,是可以实现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历史主义思潮,以及由其催生或者陆续出现的其它“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小说,能够提供一种“复线的历史”(杜赞奇语),对于纠偏或者说补充“十七年文学”两种基本类型的小说“红旗谱”和“创业史”那种宏大的民族国家单线历史叙述的方式,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也带来了宏大叙事文学作品的弱化和被遮蔽。在这种情况下,重构兼具文学性的宏大叙事长篇小说的意义和价值,是让人心怀激动的。《麦河》(关仁山)、《祭语风中》(次仁罗布)、《己卯年雨雪》(熊育群)等小说,承接了“十七年”时期宏大叙事阐释社会现实和历史“本质”的传统,又“创造性地转换”了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了先锋文学的叙事经验,在叙事形式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求。
有研究者譬如陈晓明教授,近年来就一直对先锋文学经验的当下可能性和开辟汉语文学新的可能性作出一系列思考。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有一个恢复传统的趋势,但在他看来会离世界尤其西方的小说经验愈离愈远,他认为中国现代小说仍未获得现代形式,他认为当代中国小说应该对传统与创新有更深刻的认识:“汉语小说创作不只是要从旧传统里翻出新形式,也能在与世界文学的碰撞中获得自己的新存在,从而介入现代小说的经验”⑦。从中国的汉语小说还未真正获得现代形式层面而言,他的忧虑是不无道理的。所以说,传承传统并不是不讲原则地一味恢复传统,讲好中国故事,没有固定之路可循。但传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无疑是照亮作家艺术求索之路的一盏灯火,传承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而且从来也不可能有离开传承孤立存在的创新。小说家在传承与创新的钮结和绾合当中,一路前行。
①郭洪雷《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贾平凹新世纪小说话语构型的语义学分析》[J],《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
②陈晓明《先锋派的历史、常态化与当下的可能性——关于先锋文学30年的思考》[J],《文艺争鸣》,2015年第10期。
③参见李遇春《“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J],《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④参见孟繁华《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从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看当下文学的新变》[J],《文学评论》,2017年5期。
⑤参见刘艳《女性视阈中的历史与人性书写》[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⑥陈河《后记·梦境和叠影》[A],《甲骨时光》[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46-349页。
⑦陈晓明《我们为什么恐惧形式——传统、创新与现代小说经验》[J],《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