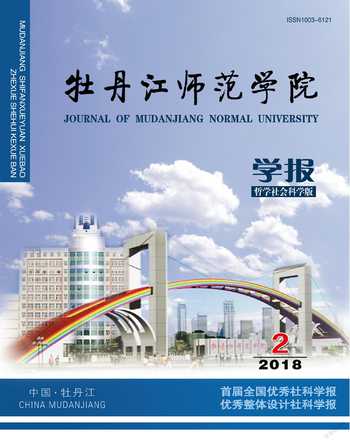道德风俗的嬗变与渤海民族的消亡
2018-09-10桑东辉
桑东辉
[摘要]作为一个民族,渤海族在中国唐代时期大祚荣建立渤海国时就开始显现出其民族特性。随着渤海国步入稳定和发展期,渤海族成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新民族。即便在渤海国被契丹人所灭之后,渤海遗民仍然保持了其民族特性。辽金时期,契丹人和女真人或武力镇压,或拉拢羁縻,想尽办法对渤海族进行同化。随着渤海人、契丹人、女真人等东北少数民族汉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各民族间融合的不断加深,渤海族的民族特性也逐渐被消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决定民族性中的诸要素逐渐淡化,特别是渤海民族独特的道德风俗逐渐湮灭。以婚姻家庭习俗为例,渤海族的婚姻家庭观念逐渐混同于汉人的儒家伦理观念。由此,构成渤海族独立存在要素的消失,决定了其在元代被作为“汉人八种”之一而失去了独立的民族性。
[关键词]渤海族;民族融合:道德风俗;婚姻家庭
[中图分类号]K246;B82[文献标志码]A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渤海国仅存国229年,但渤海民族作为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在辽金时期仍然保持着其独特的民族特性,直至元朝才被彻底融合入女真、契丹、汉族等周边民族族群中。考究渤海民族的消失,一个重要原因是渤海人民族要素的弱化,特别是固有的道德风俗的湮灭。
一
要讨论渤海民族道德风俗及渤海民族消亡原因,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渤海族在民族学意义上是不是一个独立民族。按照学界对民族构成要素的界定,一个民族的形成须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活习俗、共同的民族认同心理等要素。对照这些要素,不难发现,渤海人的民族特征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渤海人有其共同的地域。从民族来源上,渤海族是多元一体的,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融合了夫余、濊貊、高句丽、汉族等组成的新民族。据《辽史·地理志》所载,在渤海国强盛时,拥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号称“海东盛国”。其疆域包括现在吉林省的绝大部分,黑龙江省的大部分,辽宁省的一小部分,以及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和朝鲜的咸镜北道、咸镜南道、两江道等部分地区。即便是渤海国被契丹人灭亡,渤海遗民被大量迁徙至辽地插花安置后,其部族人民仍聚族群居。辽金时期,辽东、辽西、山东半岛等都是渤海人较为集中的聚居地。
第二,渤海人有共同使用的语言文字。据有关学者研究,作为多民族共同体所创立的渤海国,在大祚荣建立震国之初主要流行两种语音,一为粟末靺鞨所持的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靺鞨语;一为夫余、濊貊、沃沮、高句丽等古亚洲族语,后来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汉语成为渤海人公认的、约定俗成的官方语言和时尚语言。[1]
第三,渤海人具有共同的生活习俗。生活习俗涵盖很广,包括饮食、服饰、车马、居处、生养死葬、婚姻家庭等诸多方面。此处仅撷取几个方面简要说明。渤海民族在形成初期,其生活方式特别是衣食住行等方面仍具有明显的靺鞨等民族习惯。但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渤海人在服饰和饮食习惯上很快就汉化了。从考古发现来看,“渤海人的居室坐北朝南,一般建在夯土台基上,以木搭架,木柱下有石柱础,多用土坯砌墙,官府或大户人家偶尔也用砖、青瓦铺顶,或以草苫屋顶”。[2]从考古发掘的渤海墓葬看,在丧葬形式上既有木棺葬、火葬,也有合葬、二次葬。这不仅体现出靺鞨丧葬的特点,也包含了高句丽文化、汉文化的特点,反映了渤海民族构成的复杂和习俗演进的轨迹。由于渤海婚姻家庭习俗是本文讨论的核心,下文将具体加以分析。
第四,渤海人有很强烈的民族认同心理。特别是在渤海国灭亡后,渤海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反而表现得更加突出,民族意识也空前增强。如,契丹人曾两次大规模地将渤海遗民分割迁徙到辽地,进行插花式安置。但是,被迁徙分割后的渤海人仍“聚众而居,骄然自异,不与他族同俗”。特别是一些渤海遗民中的贵族豪俊更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渤海复国的活动,这可以从辽治下渤海人燕颇、大延琳、高永昌等组织的民族独立性质的起义得到较为可靠的证明。他们的起义大多具有民族复国性质,高永昌更是打出了“大渤海国”的旗号。进入金朝统治时期,尽管渤海人受到了同为靺鞨后裔、族源关系较为亲密的女真人的善待和怀柔,甚至与女真皇室保留了稳定的通婚关系,但是渤海右姓中的大氏、高氏、张氏、王氏等家族之间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同族联姻习俗,努力保持其民族特性和族群稳定性。此外,不仅渤海人自身认同其为一个与他族不同的民族群体,与之同时期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也都将渤海作为一个特殊的族群看待,唐宋时期称其为“渤海靺鞨”,辽金时期称其为“渤海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渤海是一个与其它族群不同的新族群。
基于上述因素,目前,学界就渤海作为独立民族存在过的这一事实基本已经形成共识。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渤海民族形成于何时的问题了。关于渤海族形成的时间段限和节点,学界也有不同说法。有学者认为,“渤海民族最早的形成是在七世纪末叶”。[3]151也有学者将渤海族的形成标志具体到某一时间节点,认为在唐肃宗至德元年,即公元756年,渤海大钦茂迁都上京“是渤海国和渤海族正式形成的标志”。[4]还有学者将渤海族的形成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隋末唐初。此时正值中原王朝北伐高句丽,其间,粟末靺鞨乞乞仲象、大祚荣父子率部徙居多民族杂居的营州,并率先汉化。此为渤海族形成的决定性开端。第二阶段是渤海国存在的二百余年间。其间,渤海族通过统一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作用而日臻固结。[1]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渤海国建立之初,并没有形成一个民族,渤海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应在其第三代王大钦茂执政时期,即公元八世紀中叶”。[5]关于渤海族的形成时间问题的讨论还有很多,本文仅摘取上述几种代表性观点。笔者认为,一个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很难将一个民族的形成精准地固化到某一点。应该说,从大祚荣建立震国就已经开始了渤海民族的构建,并逐渐具备了渤海族的雏形。而至于何时真正形成渤海族,按照民族形成所应具备的诸要素分析,本文认为,最迟在公元八世纪前后,渤海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应该已经基本形成了。
二
渤海人的婚姻家庭与同时期汉族和北方其他民族相比具有其自身的特点。据宋人洪皓的《松漠纪闻》载:
(渤海国)妇人皆悍妒,大氏与他姓相结为十姊妹,迭几察其夫,不容侧室及他游,闻则必谋置毒,死其所爱。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觉者,九人则群聚而诟之,争以忌嫉相夸,故契丹、女真诸国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妇、侍婢,唯渤海无之。[6]27922793
从上述记载可见,渤海人在婚姻家庭习俗上仍不乏古风遗存。在家庭内夫妻尊卑上,质朴的渤海人没有严格的夫尊妻卑,甚至于渤海女人在家庭中保持着比较强势的地位,如监视丈夫是否在外面置有侧室。洪皓作为儒家文化培养起来的中原士人,将渤海妇女在家庭中的这种强势归之于“悍妒”。但这种认识显然是囿于儒家礼教尊卑的狭隘觀念。事实上,渤海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正体现了渤海人由原始氏族部落向封建制迈进过程中,婚姻形式上仍保持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特点。即便是渤海人已经汉化到了一定程度,在婚姻家庭关系上,渤海妇女仍以不允许丈夫蓄妾、嫖娼的强势顽强地捍卫着渤海人严格意义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格局。关于渤海人固守严格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情况,在考古发现中也多有佐证。如,在黑龙江省海林市山咀子渤海墓葬发现的几例男女墓主并列合葬看,“当时似以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为基本形态”。[7]之所以一再强调渤海人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主要是从婚姻形式上看,蓄妾、置侧室的一男多女式家庭也是一夫一妻制的,只不过是蓄妾的一夫一妻制。比较而言,只能说渤海人是坚持不蓄妾条件下的一夫一妻制,而与汉人、女真、契丹贵族的妻妾并蓄条件下的一夫一妻制有着很大差别。而这体现出的恰恰是少数民族的传统民风。中原汉人之所以要实行妻妾并蓄条件下的一夫一妻制,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解决儒家所谓的孝道问题。诚如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蓄妾的一夫一妻制的确存在因妻子一方不孕而断绝家族血脉胤嗣的隐患和可能。因此,古人往往以纳妾、置侧室的方式解决因婚制和不孕而可能产生绝后不孝的隐忧。
应该说,渤海人的婚内家庭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较为原始的婚俗影响的。渤海人的婚俗颇类《诗经》《周易》《礼记》等古籍中记载的原始先民的婚俗,即所谓“期于桑中”“奔者不禁”“乘马班如,泣血涟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的劫掠婚、自媒婚等原始婚俗,而没有实行汉人的媒聘六礼的成婚形式。据《松漠纪闻》载,作为渤海遗民的一支——居住在混同江(松花江)边的嗢热(即兀惹)妇女,见有女真贵公子至其地携酒戏饮,则“多聚观之,间令侍坐,与之酒则饮,亦有起舞歌讴以侑殇者。邂逅相契,调谑往反,即载以归。不为所顾者,至追逐马足,不远数里;其携去者父母皆不问,留数岁有子,始具茶食酒数车归宁,谓之拜门,因执子婿之礼。其俗谓男女自媒,胜于纳币而昏者”。[6]2792类似记载也见于《契丹国志》《三朝北盟会编》等史籍。应该说,兀惹人这种自由放纵的自媒婚所展现出的正是渤海人婚姻习俗的孑遗。这种婚俗是由原始的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转变中的一种古风遗存。这在当时东北民族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上所述,既然兀惹妇女所追逐委身的是女真贵公子,说明女真人也是流行这一风俗的。如,女真习俗中的“放偷日”就体现了男女自由结合为婚的习俗。[8]尽管女真人也曾经有过这种古老的婚俗,但汉化后,金朝统治者很快就禁绝了这种落后的古风。而与此相反,汉化较早、较深的渤海人却仍流行这种婚俗,也就保留了渤海妇女的自由奔放的个性。这样,《松漠纪闻》中所记载的,渤海妇女“悍妒”“不容侧室”以及契丹、女真男子多蓄女倡、小妇、侍婢而渤海男人独无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到了金世宗时期,为了强化婚姻家庭中的礼教,针对渤海婚俗特意下诏明确,“以渤海旧俗男女婚多不以礼,必先攘窃以奔,诏禁绝之,犯者以奸论”。(卷七《世宗纪中》)[9]169
事实上,随着女真人对渤海人的怀柔政策,特别是女真皇族与渤海贵族女子的联姻,渤海人的婚俗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所谓的“坚持不蓄妾”的一夫一妻制也无法维系。至少在当时,作为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渤海女子无法再保持在家庭中的强势地位。具体而言,被动地与女真皇室联姻的贵族女子已经无法制约丈夫的蓄妾行为,因为连她们自己也不是作为正妻而是作为侧室被纳入女真皇室家族中的。据《金史·后妃传下》载:“天辅间,选东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卷六十四《后妃传下》)[9]1518也就是说,辽阳渤海贵族女子中德貌俱佳者被金廷选召充作金宗室储王的侧室。金皇室纳渤海女子为侧室的有很多,如金太祖诸子中,宗干纳渤海大氏女为次室,宗辅纳渤海李氏为次室;金世宗的妃子中渤海女子更多,主要有大氏女、张玄征女、李石女。尽管渤海贵族或主动或被动地与金宗室保持着联姻关系,但渤海贵族也极力强化族内通婚,努力保持其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意识。如,渤海贵族中,大氏、高氏、李氏、张氏、杨氏等彼此通婚,保持了较为密切的族内姻亲关系。以辽阳张氏为例,张浩高祖母为大氏,曾祖母为李氏,祖母为杨氏,母亲为高氏,张浩夫人也是高氏,其家族中的张玄征、张汝弼也皆娶妻高氏。由此可见,张浩家族历代姻亲皆为渤海人。到了辽金时期,渤海张氏与熊岳渤海王氏世代联姻。如,王遵古娶张浩女,其子王庭筠也娶了张浩的孙女。由上述例子不难看出,渤海贵族都是娶同族女为妻的,从中也可略窥其浓厚的民族认同心理。
三
渤海国是一个仿效中原政权而建立起的地方性民族政权,其突出特点是在意识形态、典章制度等上层建筑方面,大量移植、效仿汉文化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乃至政权构建模式。以中央政权的机构设置为例,渤海国仿效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设置了政堂省、宣诏省、中台省三个省;同时,设置了相当于唐代的吏、户、礼、兵、刑、工的六部。值得注意的是,渤海国的六部名称与唐朝不同,而是冠以儒家道德德目,即:忠、仁、义、智、礼、信六部,甚至决定国家政权运转的核心机构都以儒家道德伦理含义命名。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对渤海国的影响是极深的。应该说,渤海历代统治者皆是主动积极地进行汉化,坚持不懈地倡导儒学的。大钦茂时期,曾派使臣到唐朝求请唐礼和历代史书等文化典籍,并先后派出贵族子弟到唐都留学。一些优秀子弟,如乌炤度、乌光赞、高元固等都曾中过唐朝的进士。甚至于渤海人起名和封谥也多采用儒家道德语汇,如大仁秀、贞孝公主、贞惠公主等。由上可知,“盛行于内地、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的儒学,成了渤海学习、输入唐王朝封建文化的中心内容”。[10]188相对于东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渤海人的文化素养是较高的。即使渤海国灭亡后的辽金时期,渤海人较之契丹、女真而言,无论从伦理道德、文化修养,还是生活情趣、服饰饮食等方面都更胜一筹,即使与北地汉人和中原宋人相比,也不逊色。[11]113如,金代著名诗人王庭筠就是渤海人,史称其善诗文,工书法,号称金代书法之冠。在金代渤海人中,以张氏和王氏两个家族子弟的才学最高,张浩及其子张汝为、张汝霖及从侄张汝弼皆为进士出身;熊岳王遵古、王庭筠父子也均出身进士;王庭筠的养子万庆、侄子明伯、外甥高宪也都以文名世。
渤海人不仅在典章制度、意识形态、文化教养等方面加速汉化、儒化,在婚姻家庭习俗方面其汉化程度也不断加深,儒家伦理色彩日益浓重。尽管渤海女人在家庭中表现得比较强势,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渤海人在婚姻制度等方面逐渐认同儒家的伦理道德,特别是妇女的贞洁观念日益强化。一些渤海贵族妇女不仅逐渐放弃原有的严格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而认同于妻妾兼蓄下的一夫一妻制,而且开始自觉地抵制一些婚嫁陋习。如,对东北少数民族盛行的收继婚,有的渤海女人就表示不认同并加以抵制。作为肃慎——挹娄——勿吉——靺鞨一脉相承下来的渤海人,历史上应该也是有过“父死子烝后母,兄死弟妻其妻”的收继婚传统的。然而,到了金代,渤海妇女中已经有人放弃了原有的婚俗传统,而认同儒家的婚姻伦理。史载金世宗的母亲渤海李氏在其夫宗辅死后,拒绝按照女真人收继婚的传统改嫁宗辅之弟而出家为尼。可以说,到了金代,渤海人的婚姻家庭习俗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由原始的民族婚俗开始转向儒家的婚姻伦理。
四
特定的民族习俗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基础。渤海民族的消亡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因于其特定民族习俗的湮灭。
渤海人较为强势的不蓄妾的一夫一妻制,因与女真皇族的联姻而在渤海贵族集团中率先受到冲击。尽管其族群中的下层民众是否仍保持不蓄妾的民族婚姻家庭习俗史料阙如,但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剧,到了金朝后期已经很难再见到渤海家庭不蓄妾、妇妒的记载。到了元代,渤海人已经变为“汉人八种”之一,其独立的民族性消磨殆尽。然而,有关这一时期的史料中,仍有记载一些偏远民族有关妇女悍妒,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渤海妇女强势悍妒的民族特征逐渐消减了。
除了婚姻家庭习俗的变化,在服饰、饮食、民居和建筑方式以及丧葬习俗上,渤海人也逐渐失去了其民族特色。如,他们的服饰、饮食早在唐代渤海国期间已基本汉化。渤海人的民居到了辽金时期也已经异化了。如,據《契丹国志》卷二四《王沂公行程录》记载,辽地的渤海人家其“所居室,皆就山墙开门”。这种房门开在东面山墙上的作法并不是渤海人的传统习俗,而是具有拜日传统的契丹和奚人的居俗。[2]而这也说明,渤海人在居俗上出现了改变,主动适应被移民地区的民风民俗。与此同时,渤海人的丧葬习俗更是多种民族形式并存,不具有其自身特点。
应该说,渤海人在主观上一直在努力保持其民族特性,特别在被契丹灭亡并被多次分割迁徙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新的移居地,坚持“聚众而居,骄然自异,不与他族同俗”。而且,渤海贵族之间坚持族内通婚,即使在金朝时期,女真统治者大量征召渤海贵族女子入宫为侧室的情况下,渤海贵族仍努力坚持娶同族的习惯。此点从渤海右姓张、王、高等家族联姻状况中不难看出。但是,这种保持独立民族特性的主观努力,与其民族从形成初始已有的兼容并包、积极汉化的民族特性正好背道而驰。
如前所述,渤海族的形成就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以粟末靺鞨为主体,融入了高句丽、夫余、濊貊、汉族等不同成分而构成。由于渤海民族构成的多元性决定了其民族习俗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其民族性中的兼容多元、开放包容的特点。本文认为,这种开放包容的民族特性是渤海族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其最终消亡的重要原因。因为开放包容、兼纳了多种民族文化和语言,所以,渤海国建立之初就没能对其独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加以重视和提炼。加之,在典章制度、道德文化、语言文字等方面多仿效、移植中原汉族王朝模式,导致了渤海族从形成之初,其民族特性就表现为包容各族特色,尤其吸纳汉文化的多元融合体。如果说,在文明程度上渤海人较契丹人、女真人汉化更早,因而与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有所区别,那么,随着契丹、女真的国家政权建立,汉化步伐不断加快,到了元朝,渤海与契丹、女真已无明显区别,此外与燕、鲁、晋等北地汉人也无太大区别。这也就是元人将他们都归入“汉人八种”的基本依据。对于渤海人来说,开放包容的民族特性是一把双刃剑。因其开放包容,渤海国才迅速融合了靺鞨、夫余、濊貊、高句丽、汉人等不同民族形成了新的渤海族。但反之,也正因此而导致其民族文化是杂糅的,并在民族进步中基于文明的进化而不断汉化,最终被契丹、女真、蒙古等“视同汉人”。由此认为,早在辽金时期,渤海人的民族特性已经不突出了,无论在文化修养方面,还是生活习惯上都已极大汉化,且程度之深远在同时期的契丹、高句丽、女真等民族之上。这也可以解释辽人和金人都对渤海人“一依汉法”管理的原因所在。
回到本文开篇所论及的民族形成要素,本文认为,渤海族的消亡也从这些要素不再显现而得到佐证。其一,是关于共同居住地域这一要素。在渤海国存在时无疑是具备的,即便被灭亡民族遭到迁徙,仍在新的移居地聚众而居。但是,随着辽人对渤海人的多次分割迁徙,加之金朝又将部分渤海人迁到山东、燕地等处,渤海人的共同居住地被分割、打破,呈碎片化、插花式的民族生存状态,民族独立的大片居住区域难以保持,保持民族独立性的空间受到冲击和抑制。其二,是关于民族认同心理。这是渤海族在辽金时期仍然顽强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渤海人在亡国后被分割迁徙到辽地后仍聚众而居,不与他族同俗。大延琳、高永昌等抗辽斗争中都以复兴渤海国为号召,无疑也是通过民族认同感号召渤海部众的一种手段。在金朝的怀柔羁縻下,张氏、王氏、高氏、李氏等渤海贵族仍努力保持其民族认同感,联姻通婚,在政治上彼此配合,努力保持其民族特性。然而,这些努力和民族认同心理在金朝统治期间已被销磨殆尽,有金一代再没有出现过类似辽代时期的渤海人复国运动。至元朝,渤海人的民族认同心理在现存史籍中已经难以寻踪觅影了。三是,关于共同的生活习俗。此点前文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在同时代东北民族中,渤海人的衣食住行汉化速度最快,汉化程度最深,同时,在衣食住行风俗上也吸纳了周边的女真、契丹、高丽等民族习惯。随着元朝的一统,渤海人作为“汉人八种”之一已经没有其独特的生活习俗了。四是,关于共同的语言文字。在渤海国成立之初,由于其民族构成成分的不同,曾在不同部族内、在下层民众中保持其不同的语言风格和方言用语,但从官方和时尚流行的角度来看,从渤海国建立后就一直是汉语、汉字的天下,也不具备独一无二的语言文字特色。
從民族构成要素考察,失去了民族特有的习俗支撑,加之民族共同生活区域的碎片化、语言文字的无差别化、民族认同心理的淡化,一个族群作为民族独立存在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这也是渤海族在元代初年最终消亡的根本原因。综合分析渤海族消亡的原因,固然有契丹人对渤海人的分割、迁徙等硬性同化和女真人对渤海人的联姻、怀柔等软性同化,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渤海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道德风俗的湮灭。而从渤海民族的基因看,渤海人的特有风俗习俗原本就不突出,这也与其民族构成的多元性和民族文化的开放性不无关系。概言之,正是渤海民族多元融合、开放包容的民族特性决定了其民族风俗和习俗缺乏明显特点,也决定了其在元朝一统天下时与汉化的契丹、女真等民族一道并入北地汉人的洪流。可以说,这种民族融合的特点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中华民族活力和持续力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孙秀仁,干志耿.论渤海族的形成与归向[J].学习与探索,1982(4):129134,120.
[2]程妮娜.辽金时期渤海族习俗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1(2):124129.
[3]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4]刘达科.金朝北方民族文学发微[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6570.
[5]都兴智,孙艳.关于渤海国及渤海遗民研究的几个问题[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13116.
[6][宋]洪皓.松漠纪闻[M].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孙秀仁,金太顺.黑龙江省海林市山咀子渤海墓葬[J].北方文物,2012(1):1126,2,113117.
[8]刘肃勇.从“放偷日”习俗看女真早期婚制与经济生活[J].满族研究,2009(1):8386.
[9][元]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王承礼.渤海简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11][日]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M].李东源,译.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李献英
The Evolution of Moral Custom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Bohai Nationality
——A Case Study of Marriage and Family Customs in Bohai
SANG Donghui
(Harb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Harbin,Heilongjiang 150010,China)
Abstract:As a nation established by the kingdom of Dazuorong in the Tang Dynasty, Bohai began to show it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Bohai, the Bohai had become completely a nationality different from other ethnic groups. Even after of the perdition, the descendants of Bohai still maintains it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iao and Jin Dynasties, Khitans and Jurchens try to assimilate the Bohai nationality .Along with the integration deepened, 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Bohai nationality have gradually been killed. It is essential for the disappearance of Bohai nationality that the people of Bohai unique moral customs especially the concept of marriage and family gradually fade.
Key words:Bohai nationality;national integration;moral customs;marriage and fam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