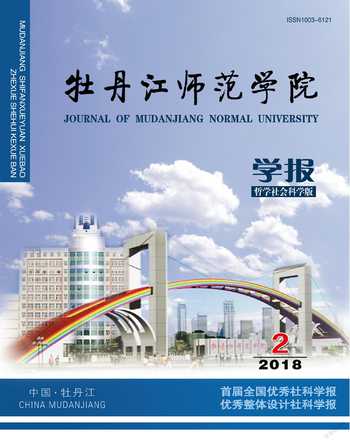20世纪前半期甲骨文、金文与《诗经》研究述略
2018-09-10陈斐斐陈良武
陈斐斐 陈良武
[摘要]《诗经》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诗歌总集,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诗经》的阐释和研究在学术史上始终处于显学的地位,历代学者都对其倍加关注。20世纪前半期,地下出土材料豐富,随着金石学、甲骨卜辞研究的推进,《诗经》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域。在继承前辈智慧的同时,借助于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以地下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互补的二重证据法,在《诗经》名物考释,作品年代的考释,文字、训诂和音韵研究领域,以及儒家《诗》论研究等方面往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些成果对厘清因文献不足而悬而未决的争议,开拓《诗经》研究的空间等方面都是大有裨益的。
[关键词]《诗经》研究;甲骨文;金文;考校释读;儒家《诗》论
[中图分类号]K207.8,I207.22[文献标志码]A
20世纪前半期,发掘、出土了不少新材料,在这些出土材料中有不少是具有很高文献价值的。其中,甲骨文、彝器铭文研究的推进对于《诗经》研究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如夏传才先生在《二十世纪诗经学》一书中所言:“广义来说,有关商周的考古发现都对《诗经》研究有参考价值,有助于了解《诗经》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有关名物制度。”[1]331可以这样说,作为相对接近《诗经》时代的文字符号,甲骨卜辞和彝器铭文保存了许多上古时代的文化,对于《诗经》的解读是有很大帮助的。
自19世纪末发现殷墟甲骨卜辞和彝器铭文以来,王国维先生主张并开始运用殷墟甲骨文字和金文来考释古书。1925年秋,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设《古史新证》课,在讲义的《总论》部分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241242接着,他罗列了《诗经》等十种纸上之史料,又谨举地下材料二种:甲骨文字、金文,称:“今兹所讲,乃就此二种材料中可以证明诸书,或补足纠正之者,一一述之。”[2]242243
利用甲骨文、金文作证,来对《诗经》进行研究,王国维先生可谓最早的学者之一。他运用“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观堂集林》蒋汝藻序)[3]1的方法,开古史研究的新风气,对《诗经》学具体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为后人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随着甲骨卜辞和彝器的不断出土,研究队伍及其影响也不断扩大,现代《诗经》学也开始关注利用出土材料做《诗经》新证研究。林义光、郭沫若、于省吾、杨树达、闻一多、傅斯年、陆侃如、冯沅君等人,或以注本(译注)的方式,或以论著论文的方式,或以讲义讲稿的方式,或以文学史书写的方式,在甲骨文、金文与《诗经》研究方面做了多种尝试和努力,颇多创见。20世纪前半期,学者依据甲骨卜辞、彝器铭文,在《诗经》研究领域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努力:一是《诗经》名物考释;二是《诗经》文字、训诂和音韵研究;三是《诗经》作品年代的考释;四是儒家《诗》论研究。
一、《诗经》名物考释
《诗经》名物驳杂且距今久远,里面有不少关于商周时代名物的记载,如果对这些名物一无所知,将成为认识《诗经》的一道屏障。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最早提出了“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诗经》的名物考释早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开启了后世考释《诗经》名物的风气。名物考释常可窥见于历代《诗经》注疏之中,到了考据之风盛行的清代,更是成为了专题性的研究。简言之,广义的“名物”,涉及事、物之“名”与“实”,非但不局限于鸟兽草木,还包括制度等范畴。如扬之水先生《诗经名物新证》所言:“草木鸟兽虫鱼,只是诗中名物之一端,举凡宫室、车服、宫制、祭祀,礼、乐、兵、农,等等,自古也都归于名物研究之列。”[4]320世纪前半期,王国维、闻一多等人承续乾嘉朴学的治学传统,利用甲骨卜辞、彝器铭文对《诗经》的名物方面做了细致的考释,成果主要集中于姓名、官职名、地名以及礼制等方面。
(一)《诗经》姓名、官职名、地名考
首先,考释《诗经》中的姓氏。如王国维先生《“女”字说》中,根据《南旁敦》金文“”与《诗经》“美孟弋矣”之“弋”互释,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将《杜伯鬲》金文“嫞”字与《诗》“美孟庸矣”之“庸”互释,借助金文解释《诗经》中的姓氏。指出,“凡女姓之字,金文皆从女作,而先秦以后所写经传,往往省去女旁”这一文字现象。[3]382其次,考释《诗经》中官名。在《观堂集林·释史》中,王氏结合《大雅·常武》“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以及《颂鼎》《寰盘》“尹氏受王命书”,《克鼎》“王呼尹命册命克”[3]177179等铭文来考释“作册尹”这一官职名。(《王国维全集》第14卷中《书作册诗尹氏说》一文亦有相关说明,参见151153页)第三,考订《诗经》中的地名及地理。《说殷》中,王国维先生就根据殷墟卜辞所祀帝王,称“商居殷最久,故称殷”,又“《诗》、《书》之文皆‘殷、‘商互言或兼称‘殷商”,两相印证,断定商起于地名之殷,殷地在河北不在河南。[3]P352又如,《散氏盘跋》由克鼎出土之地考订《大雅·崧高》“申伯信迈,王饯于郿”之“郿”地,当在今宝鸡县南方克之故墟附近。[3]450452《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中,王国维先生结合卜辞和古籍,认为卜辞“雇”字古书多作“扈”,并指出,《小雅·桑扈》亦借雇为扈,考订出其区域在今河南、北附近。[5]137138在《北伯鼎跋》中,依据河北出土的北伯彝器数种,结合古籍记载,考订鼎文“北”为古之邶国,以北伯彝器出土之地证邶为燕,鄘即鲁也,加上卫,三者均在殷墟境内。而且邶、鄘皆有目无诗。后人以卫诗独多,遂分隶之于《邶》《鄘》。[3]449450此说可供参详。
(二)《诗经》制度考
利用甲骨卜辞、彝器铭文考释《诗经》的名物,除了姓名、官职名、地名,还有对《诗经》中的典章礼仪、文物制度等方面的考释。
《诗经》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记录了很多有关上古社会的生活、文化习俗,对于研究商周时期的典章礼仪、文物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古人作诗,直纪当时制度风俗”[6]326,王国维先生在《东山札记》第十一篇中举了相关例子来说明此观点。如,“《小雅·瓠叶》一篇咏燕饮食,首章云‘酌言尝之,此泛言也。次章则云‘酌言献之,三章则云‘酌言酢之,四章云‘酌言酬之。古人饮酒之礼,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人酬宾,献、酢、酬,卒爵而礼成。《礼经》所纪,无不如是,此诗次序亦同。……《楚茨》序祀事,与《特牲馈食》、《少牢馈食礼》略同,惟尊卑有殊,而节目不异。”[6]326诚然,透过《诗经》所载可对其背后诸如宴食饮酒礼之类的古代礼仪文化制度有所了解。将甲骨卜辞和彝器铭文的有关记载与《诗经》文本内容相结合,不失为考证古代礼仪文化制度的一个有效途径。他还曾在《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中提到:“观殷墟卜辞所纪祀先王礼,大抵先(同“燎”字),次卯,次薶卯。或先后沈,或先后卯。”[3]14以此解释《诗·大雅》中,“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涉降,在帝左右”的关于“燔燎之礼”的礼仪制度。在《古诸侯称王说》一文,王国维用大量殷墟卜辞和彝器铭文出现称“王”的例子与《诗》《书》等古籍称“王”的现象相证,并推论“古时天泽之分为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我们不能一概以僭越视之。[5]139140这是关于周初“诸侯称王”社会制度沿袭的考释。郭沫若对王国维的这一结论也是非常认可的。他在《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引了王氏原文,亦称“古诸侯在国内既可称王,因而其臣下亦每自称其首长为‘天子”[7]15,并引《献簋》记载为证,可备参之。
郭沫若,甲骨“四堂”之一,对甲骨卜辞和彝器铭文非常重视,与《诗经》研究颇有关涉。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上海联合书店印行)借助甲骨卜辞、彝器铭文等最新成果,并结合《易》《诗》《书》《周礼》等先秦古籍,专注于中国古代社会名物制度和生活文化研究,且每有新见。比如,在《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一文,郭沫若先生根据周代彝器中锡臣仆的记录,推知“奴隶是家传世袭”的,并提出了《大雅·既醉》“君子万年,景命有仆;其仆维和,釐尔士女;釐尔士女,从以孙子”中的“仆”为奴隶的本字[8]252253,推知周代存在奴隶制度。然亦有不少穿凿附会之辞,如书中常以阶级论来分析上古社会社会制度和阶层,这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
由上可见,借助甲骨文、金文来考释《诗经》名物,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诗经》内容,把握其主旨,并给古史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
二、《诗经》文字校释、训诂和音韵研究
文字、音韵和训诂是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千多年来《诗经》研究绕不过去的课题。甲骨卜辞、彝器铭文的不断发现与研究的深入,对于《诗经》文字、音韵和训诂等方面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其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境界。
(一)甲骨文、金文与《诗经》文字研究
关于甲骨文、金文与《诗经》互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异文研究这方面。王国维先生对此做了不少研究,但比较零散,现主要收录于《王国维全集》。王国维在《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二》中指出:“其余《诗》、《书》中语,不经见于本书,而旁见彝器者,亦得比校而定其意义。”为了说明“古司、事通用”的问题,他征引古今史料互证。《小雅·十月之交》:择三有事。《毛公鼎》云:粤三有嗣。则“臬司”即“臬事”。[3]32又,《小雅·楚茨》云“先祖是皇,神保是飨”,云“神保是格”、“神保聿归”,《传》《笺》训“保”为“安”,不以“神保”为一语;他引《克鼎》“巠念阙圣保祖师桑父”,认为“神保”“圣保”皆祖考之异名,“非安飨、安归之谓也”。[3]34事实上,王国维先生在语词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也是沿着从甲骨文、彝器铭文与《诗经》的比校这条路径走的。如,《玉溪生年谱会笺序》一文,他借助《函皇父敦》铭考释《小雅·十月之交》之“艳妻”,《鲁诗》本作“阎妻”,皆此敦函之假借字。还因此称毛、郑是非乃决于百世之下。[3]615他还结合史料与鄂侯鼎铭文,说明古“佑、宥”二字与“右”同。在《观堂别集·释宥》一文,以彝器铭文材料补证王引之《经义述闻》和孙诒让关于“酢”与“佑”的说法,说明《诗》“钟鼓既没,一朝右之”的“右之”,当是“命之宥”。[5]169171
林义光先生较为关注晚近出土的三代器物铭文,其所著《诗经通解》(1920年衣好轩铅印本),博徵群书,兼及钟鼎铭文,音韵文字,每有胜意。林先生依据金文并结合古籍做了很多关于《诗经》音韵、训诂和文字研究方面的深入工作。如,在《诗经通解·考槃》中,他指出:“考当作老。考,金文或作,师敦‘祖考如此。作,毛公敦‘寿考如此。以形义求之,皆为老字。”[9]70认为考、老古相通。同样,他又在《诗经通解·蓼萧》中指出,“鞗革冲冲”之“鞗革”,金文作攸勒,石鼓文作鋚勒。[9]192值得一提的是,他非常关注文字的形、音、义的结合,这一点在《诗经通解》的体例中得到充分体现:诗句常有校字,入韵字用国际音标来标音;诗歌每个章节之后常引古今文献解释字词义;每篇都有诗歌的篇义(别义)的探讨;也非常重视诗歌异文现象。在异文这一块,他尤其关注石经残碑文字,常征引石鼓文、汉石经、唐石经等碑文材料说明异文现象。
于省吾先生的《泽螺居诗经新证》在材料使用上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引甲骨文、金文与诗文互证。如,《丝衣》“俾無訧兮”一句,于氏谓“甲骨文‘亡尤习见,大丰与献亦均作‘亡尤”。[10]10又如,《小星》“肃肃宵征”一句,于氏引员鼎“征月”即“正月”,毛公鼎“内外惷于小大政”或訓政为正长,言“肃肃小正”语例正同,同时结合《礼记》《尔雅》等古籍加以说明,认为“正、征、政古同用”。[10]9
傅斯年先生研究历史语言时也有不少关涉甲骨文、金文与《诗经》研究方面的成果。他在《〈诗经〉之“性”“命”字》一文,论述了《诗经》本无“性”字。对唯一出现“性”字的诗《大雅·卷阿》“俾尔弥尔性”,傅斯年先生认为,此即“俾尔弥尔之一生”,称“此处之性字必为生字明矣”,且引金文证之,认为《诗》中“弥尔性”在金文中正作“弥厥生”,弥生是长生,“其出现全在祈求寿考之吉语中”。[11]189190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大雅·卷阿》“俾尔弥尔性”问题,前面王国维先生在《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二》亦有相关阐述,他引齐子仲姜鎛“用求考命弥生”证“弥性”是“弥生”,谓:“犹言永命矣”。[3]34
(二)甲骨文、金文与《诗经》训诂研究
在《诗经》训诂方面,王国维也是颇有造诣的。他善于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彝器铭文,并结合各种古籍来训诂和考释《诗经》词语,拨正一些旧注的误释,并提出己见。如,《桧风·羔裘》“舍命不渝”一句,《笺》释为“是子处不变,谓死守善道,见危授命”。王国维在《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二》中,据《克鼎》《毛公鼎》驳之,“谓如晋解扬之致其君命,非处命之谓也。”[3]33《大雅·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的“配命”一词,《传》解释为“永,长;言,我也;我长配天命而行”。他根据《毛公鼎》谓“配命”“亦一成语,永言配命,犹言永我畀命,非我长配天命之谓也。”[3]34他还以《思齐》中“临”“保”二字,与《大明》《云汉》中“临”字的使用,与毛公鼎、师敦上的铭文进行比照,驳斥《笺》辞为“迂曲”之言。[3]34对《卷阿》《韩奕》《江汉》《商颂·殷武》中《传》或《笺》类的一些旧注,王国维都引彝器铭文材料一一驳正。其中,《商颂·殷武》“天命降监,下民有严”句,他连举宗周鼎、齐侯镈钟、虢叔旅钟上的多条铭文记录,说明“‘有严一语,古人多以之斥神祗、祖考”,指出《笺》以为“天乃下视下民有严明之君”的失误。[3]35
前文已经提到傅斯年先生做历史语言研究时也有关涉甲骨文、金文与《诗经》研究的成果,《性命古训辨证》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这本书的上卷中,傅斯年搜集卜辞、金文中有关性、命二字的资料有一万余条,通过比较说明其原训及其字义演变[12]111。他善于从语言学角度入手来考察思想史。在论述《诗经》之“令”“命”字一章节中,他认为,《诗经》之“令”字与“命令”一义并无关涉。同时,他指出:“所有郑笺以之训善之令字及其同类之令字,在《诗经》本书皆原作霝字,不作令字”,认为它是“一吉祝辞,履见于金文,皆作霝终,且有与令字同出一器者”,并以克鼎、颂鼎、微鼎等相关彝器上的铭文为证。他还以图解的方式探讨了今本《诗经》对金文书式大体之转变。而且,他还挑出《诗经》中所有与“命”字相关的诗句,将其分为动词类、名称类、形容词类等词性和用法,讨论了“命”之义项本义和引申义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诗经》中命字之字义,以关于天命者为最多,其命定一义,则后来儒墨争斗之对象也。”[11]190198傅斯年先生对《诗经》之“令”“命”字之字义考述可谓缜密详尽,可备参之。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初还有一批学者以注释的方式对《诗经》学做出了贡献。这一时期,涌现出不少“新证”派研究者,如林义光、闻一多、于省吾等先生利用古文字材料以明《诗》之训诂。林义光先生的《诗经通解》是综合文字的形、音、义的大著作。在《诗经》训诂方面,他征引铭文古籍考证“于”“乎”(呼)古相通。他认为,《六月》中的“王于出征”即“王呼出征”,根据《尔雅·释诂》训“于”为“曰”,称“曰”为“乎”之借字,又引“诸彝器记册命事每云王乎某某,乎读为呼”为证。[9]196郭沫若先生也留下关于《诗经》方面译注的成果。比如,《青铜时代》一书中《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部分,征引了不少甲骨卜辞和彝器铭文成果来释《诗》,并且大胆地做了古文翻译现代白话文的古文今译尝试,使《诗》变得通俗易懂。其中,也协和了不少民歌调子,主观再创作的意图难掩,结果难免失却《诗》之原味。闻一多先生以注释的方式在甲骨卜文、金文与《诗经》研究领域多有建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诗经新义》和《诗经通义》之中。经统计,《诗经新义》(原载1937年1月《清华学报》第12卷第1期)目录二十三条,考释二十三种语词。其中,征引了甲骨卜辞和彝器铭文来作考释的就有9处。以下试举几例作简要分析。《诗经新义》中,闻一多在考释“楚”字时,引述于省吾谓“梁乃荆之讹”的观点和彝器铭文材料证据,自己又补充了一些金文材料并加以考释。认为荆梁并从刃声,是二字古同音,古字假借情况时有,不得尽以误字目之。[13]263纠正了于氏之错漏。考释《行露》“谁谓雀无角”之“角”时,条列了五类证据,包括引文字画为证,引鼎文(《续殷文存上》四)证明古彝器铭识有大喙鸟,且其喙之形与卜辞角字逼肖,认为“是古人造字,喙与角不分二物也”。[13]167再加上其它古籍辅证,言之凿凿。《诗经通义》(原载1937年1月《清华学报》第12卷第1期)中,征引甲骨卜辞和彝器铭文来作考释的就更多了。
在20世纪前半期写出的《诗经》多种注本中,大多注意利用已考释出的甲骨文和金文资料。其中,成就最为突出、成果最为集中的著作当属于省吾先生《泽螺居诗经新证》(出版于1982年,《诗经新证》部分及相关论文主要是二三年代的研究成果)。于先生的《诗经》研究善于引甲骨文、金文与诗文互证,而且关注前人的这类研究成果。如前所述,王国维先生曾借助《函皇父敦》铭考释《小雅·十月之交》之“艳妻”,《鲁诗》本作“阎妻”。在此基础上,于先生结合古籍对“艳妻煽方处”做出更为详尽的考释。同时,他对王氏的一些表达提出质疑:“何以知历王之后必姓娟耶?”[10]3438《小戎》“蒙伐有苑”一句,《郑笺》释为“化杂羽之文于伐”,于氏举《玉篇》引作“蒙瞂有苑”例,又列金文盾之象形字,谓、干音通,解释了郭沫若释为干的原因。但是,他并不认同郭所称“《郑笺》画羽之说而非”的观点,他还是比较认可《传》训苑为文貌,谓画龙其盾之辞的解释。[10]19
(三)甲骨文、金文与《诗经》音韵研究
两千多年流传下来,《诗经》受到文字异形、言语异声的干扰,已经难以原其本貌。文字尚可以符号的形式保存,后世还能考释其形、义,但古声是最难保存的。这也给《诗经》的音韵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音韵问题历来是《诗经》研究问题的重灾区。宋人在研究《诗经》音韵时提出了“叶韵说”,看似能解决不少问题,却也不免于主观随意性,为后人所诟病。《诗经》的音韵研究在新材料的基础上,具有前人所不备的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王国维先生在《周代金石文韵读序》称:“余更搜其见金石刻者得四十余篇,其时代则自宗周以迄战国之初,其国别如杞、郐、邾、徐、许等,并出《国风》十五之外,然求其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3]256他拿十五《国风》之外的金石材料来与“诗三百”的用韵作比较,以证明清朝古韵之学精确。林义光先生著《诗经通解》,如前所述,依据金文并结合古籍做了大量多关于《诗经》音韵、训诂和文字校释方面的工作。在音韵方面,诗句常有校字,入韵字会用音標来标音。如,《七月》“以介(匄)眉寿sou”一句,他认为:“介读为匄,乞也。金文多言‘用祈匄眉寿,祈匄者祈乞也。”又,“朋酒(醜)斯饗kiong”,提出“酒,古文作酉,古金文凡酒字皆作酉”的观点。[9]164165显然,林义光先生擅长通过金文和诗文的比照考证文字通假或相通的原理,给入韵字注音。以今日学术观之,林先生拟音或有不足,然仍有一定意义和参考价值的。如前所述,傅斯年先生在《性命古训辨证》一文借助金文和音韵知识对“令”“命”字作出考释。他提出,“所有郑笺以之训善之令字及其同类之令字,在《诗经》本书皆原作霝字,不作令字”,认为它是“一吉祝辞,履见于金文,皆作霝终,且有与令字同出一器者”,并以克鼎、颂鼎、微鼎等相关彝器上的铭文为证。他还以图的形式探讨了今本《诗经》对金文书式大体之转变,指出,金文霝(平声)与今本《诗经》令(平声)相通,金文霝(去声)与今本《诗经》命(去声)字相通。[11]190193
闻一多先生对《诗经》词语的读音亦有所关注。在《诗经通义》甲本中,《邶风·日月》“俾也可忘”,《陈风·宛丘》“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小雅·都人士》“万民所望”,他认为,“‘忘读为‘望,‘望、‘忘古字通”。并以《县妃》之“望”字,《献鼎》《师望鼎》《召卣》《帅佳鼎》等相关彝器铭文之“”字,称“以上望、并借为忘。《诗》则借忘为望。”[13]353此外,作为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姜亮夫先生所著的《诗骚连绵字考》,是综合语音、文字、训诂,结合古文献与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成果而成的文字学著作。古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其古文字研究亦与《诗经》颇有关涉。运用甲骨文与《诗经》互证,也是杨树达《诗经》研究的一个特点。其论述主要收录于《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积微居甲文说》《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
实际上,20世纪前半期,古文字学家、历史语言研究专家在研究中大多注意运用甲骨文、金文与《诗经》互证。不过,他们的有些论述并非都以《诗经》研究专著的形式留存,而是散见于其他著述中,因而对于《诗经》研究的贡献容易被人忽视。所以说,虽未以《诗经》研究专著的形式留存,但这些研究的确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不应当被埋没。
三、《诗经》作品年代的考释
《诗经》作品年代的推考历来都是难度高,争议大的公案。利用出土材料有助于解决一些因文献不足而成为悬而未决、聚讼纷纭的公案。比如,陆侃如、冯沅君伉俪合写了一部《中國诗史》,其中,上卷《古代诗史》的《诗经》部分关注到当时最新的学术研究动态,吸收了王国维、郭沫若等人在甲骨卜辞、彝器铭文研究上的硕果,对《诗经》作品年代给出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考释。
(一)关于《颂》诗作品时代的考释
陆侃如、冯沅君伉俪在《中国诗史》称:“在《南》、《风》、《雅》、《颂》四种体裁中,《颂》的时代最早。”[14]19关于《商颂》的时代历来有二说:一是宋国;一是商代。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总论》部分称:“《诗》,自周初迄春秋初所作,《商颂》五篇,疑亦为宗周时宋人所作也。”[2]242另外,他在《说商颂》下还曾将殷墟卜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与《商颂》比照,发现“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并称:卜辞称国都曰“商”不曰“殷”,而《颂》则殷、商错出;并以地名和人名与《商颂》之异,提出《商颂》是宋人所作,为宋诗,不为商诗。[3]6263后人对此依然有争议。然而,有意思的是,傅斯年先生的《诗经》讲义十二篇(据作者《自叙》所言,大体写就于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也关注到出土材料与《诗经》作品年代的相关问题,在《商颂》断代问题上,他也比较倾向是宋诗。为此,他举《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谓“宋人自称商,金文中已有成例”[11]6870,并引王静安《说商颂》来进行论述。
关于《商颂》是宋诗还是商诗的问题,陆、冯二人的《中国诗史》中亦有专门讨论,也是主张宋诗说,并依据魏源《诗古微》、王国维的《说商颂》下来展开讨论。谓:“若依王国维的意思,正考父是戴公时人,故《商颂》大约作于西周末叶,公元前800年左右。魏源则以为《史记》之说不误,《商颂》的年代当在前650年前后。”至于王、魏二人关于《商颂》年代之说哪个可能更准确些的问题,陆、冯二人最终也没有举出更有力的证据给出定论。他们只是从内容与文学技巧方面将《商颂》分为近《颂》、近《雅》两类:前三篇(《那》《烈祖》《玄鸟》)一类,假定为前8世纪的诗;后二篇(《长发》《殷武》)一类,假定为前7世纪的诗。[14]2328
(二)关于《雅》诗作品年代的考释
王国维先生在《鬼方昆夷玁狁考》中,结合彝器铭文与古籍考证《出车》是宣王时诗。他认为,诗中人名如吉甫与南仲属宣王朝,而周用兵玁狁事,见于书器者,大抵宣王之世,并引“诗”为证,解释玁狁后裔之别名及所处地域。[3]377392
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也尝试对《诗经》作品年代进行系统考证,多引经据典,并借用了当时甲骨卜辞、彝器铭文的研究成果。他们对“二雅”(105篇)中的《常棣》等21篇作品年代进行了推考。其中,在推考《采薇》《出车》《六月》“三篇均叙征玁狁事,似为宣王时的作品”[14]32的过程中,就征引了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的相关考述。推考《江汉》“叙召虎征淮夷之事,作于宣王时”,也借助了彝器铭文的研究成果,谓:“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六)、吴式芬《攗古录金文》(卷三之二)、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四)等书,均著录《召伯虎敦》,首云‘隹六年,知为前822年事。铭文与《江汉》最相近,故此诗年代亦可借以推定。”[14]3738
(三)关于《风》诗作品年代的考释
闻一多先生在《诗经新义》考释“素丝”时,结合彝器铭文与古籍,认为《诗》之“素丝”即为金文之束丝。根据仅《守宫尊》《鼎》和《羔羊》《干旄》二诗言及赠丝内容,而且郭沫若定《守宫尊》和《鼎》分别为懿王和孝王时器,故而闻一多推测《羔羊》《干旄》二诗有可能是西周末叶,懿、孝前后所作。[13]268271他在《诗经通义》甲本也讨论了这个问题。然而,他修改了一些说法,采用陈梦家“《守宫尊》、《鼎》皆为懿王时器”的说法,同时附上郭沫若之说,更为肯定地推断二诗作于西周末叶。[13]321323从他补充材料,修改说辞的做法来看,他做学问还是比较严谨审慎,且考虑到时代要求的。
前文已经提及,王国维先生在《北伯鼎跋》中,根据北伯彝器出土地考述了邶、鄘、卫之地,创《邶》《鄘》皆有目无诗之说。他此番论述后来为陆侃如、冯沅君二人所用。他们在考述《国风》时征引了《北伯鼎跋》,在“二南独立”的基调上,称“《国风》实存十一”[14]46。然而,“二南独立”还是存疑的,《国风》实存十一之论实际上是缺乏说服力的。不过,他们在考述《卫风》时,提到许穆夫人的诗时,称:“吕大临《考古图》(卷七)及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六)中有《许子钟》的铭文一篇;有韵,风格近雅,惜时代无考。”[14]53,显然,他们注意到了《诗经》内容与《许子钟》铭文材料的比对,虽未考释出具体年代,这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思路。考述《豳风》时,讨论了钱穆《周初地理考》、徐中舒《豳风说》,以及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的相关成果,肯定徐中舒论《豳风》的时代,“赞成他把这几首诗的时代从周出移至春秋”,但又“不同意他把地点从陕西移至山东”[14]5760。
在上述论说中,虽然有些推论不太准确,亦有存疑,但不得不说,关注当时最新的学术研究动态,吸收时人的研究成果,这是陆侃如、冯沅君夫妇《诗经》研究的一个亮点。也难怪陆、冯二人的《中国诗史》于20世纪30年代一问世,便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了。需要说明的是,像他们这样利用出土材料的研究成果,从学术史的角度系统地做《诗经》研究的并不多。
四、儒家《詩》论研究
在20世纪前半期,也有一些人利用甲骨卜辞、彝器铭文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做儒家《诗》论方面的研究。
(一)《诗经》的分类:“三体说”与“四体说”
关于《诗经》的分类,历来是以“六义”“四始”说为主。《毛诗序》始用“六义”说概之:“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是为四始,诗之至也。”[15]11孔颖达《毛诗正义·毛诗注疏卷第一》云:“诗有各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意。《周南》为王者之风,《召南》为诸侯之风,是听声而知之也。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15]1213实际上,从体制而言,孔颖达主张的是“诗分三体”:风、雅、颂。之后,历代基本延续“诗分风、雅、颂三体”之说。然而,存在争议的是“二南”的归置问题。到底是归为“三体”之中的《国风》,还是可以当作独立的体裁?对此,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就集中讨论了此问题。
陆、冯二人在《中国诗史》明确指出:“《二南》独立问题发端是由于《小雅·鼓钟》第四章末两句的解释:以雅以南,以籥不僭。”[14]10籥,在《诗经》不少作品中都出现过。如,《小雅·宾之初筵》“籥舞笙鼓,乐既和奏”,《邶风·简兮》“左手执籥,右手秉翟”,历来注疏释为笛子类的乐器。(注:关于“籥”的解释,《周礼》“籥师掌教国子舞与吹籥。”《郑笺》“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此为籥舞也。”王夫之《诗经稗疏·邶风》认可这个解释,认为,籥者,郑玄、郭璞皆云是三孔笛,吹之易成声,不用按撅,故且吹且舞,无碍于右手之秉翟,今小儿所吹闷笛近之。朱熹《诗集传》以为六孔,则管也,非籥也。王夫之以实物证之,解释籥是像闷笛一样的三孔乐器。)陆、冯二人根据苏辙《诗集传》把“以雅以南”之“南”指向《二南》、王质《诗总闻》把《南》当作乐歌名,以及程大昌《考古编》以《南》《雅》《颂》为乐名等相关解释。认为,“他们承认《南》当与《风》分开”,称:“《二南》的独立是可以成定论的。”[14]12继而断言:“《诗经》内分为南、风、雅、颂四类。”[14]12二人结合“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上册《释南》)里以为南是钟铃一类的乐器”[14]18,继续讨论“二南独立”的问题,提出:“南字由乐器而成为方向,郭沫若以为‘因古人陈钟镈于最南,但也可说南为长江流域盛行的乐器,故用以代表南方。如再参以崔述之说,我们可以假定:《二南》之诗作于‘南方,歌时亦用‘南器,故名。”[14]18之前,在讨论“雅”的时候,他们二人也认为“雅为乐器”,还称“美中不足者,在尚未能证明颂与风亦为乐器。”[14]18很显然,陆、冯夫妇倾向于从乐器归属的角度讨论“诗分四体”的问题。
关于郭沫若释“南”为乐器,此观点又可见于郭沫若《卜辞通纂》对于第159片“于祖辛八南。九南于祖辛”的考释:“‘南当是献于祖庙之物,乃钟镈之类。”[16]288不过,据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的《卜辞通纂》出版说明:《卜辞通纂》初版本1933年在日本东京印行。在1958年作为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稿,郭沫若加了一些校语和注释。那么他在第159片卜辞释例上面的眉批应为后来所加校语。校言:“释南不确,当是字,读为豰,参见《殷墟粹编》考释第1268片。”[16]288而在《殷墟粹编》一书中,郭沫若对第1268片的考释,对的释读,谓:“读为豰,谓郊祀上帝以豰也。旧释为南,于用案为祭牲之事苦难解。……又与犬羊牛同用。又于犬羊牛之外,无与豖豚同用之例。此均当为豰之证。”[17]671672这一更改,似在推翻之前在《甲骨文字研究》和《卜辞通纂》中对甲骨文“”释为“南,当是献于祖庙之物,为钟镈之类”的说辞。如此看来,陆、冯二人的“南字由乐器而成为方向”之立论就值得斟酌了,虽不足证,存疑也很多。但是,这并不代表陆、冯二人的推导是没有价值的。总之,“南字由乐器而成为方向”,这一思路也为“二南独立”,风、雅、颂之为乐器或乐名等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现在尚无有力的证据解决这些问题,仍有待于更多出土材料的发掘。
(二)诗言志辨
“诗言志”这一重要命题由来已久,与儒家说“诗”是紧密相关的。传世文献《尚书·舜典》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8]7879《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又,孔颖达《正义》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是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19]1064后世儒家说“诗”也有不少关于“诗与志”的讨论。如:《毛诗序》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5]610纬书《诗含神雾》云:“诗者,持也,以手维持,则承负之义,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又,“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20]464不管是心之所志,还是手之抱负,抑或“持心”之说,对“诗”的阐述往往紧紧围绕“心志”来发明要义,而且对诗之功能的讨论也难脱政教之用。
出土文献亦有对“诗”与“志”的相关记载。《郭店楚简·语丛一》是一部重要的儒家文献,里面有一段文字是关于“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性质和功用的记载。其中,简38言:“诗,所以会古含(今)之恃(志)也。”[21]181刘钊先生释读为“诗是会集古今之志愿的。”[21]191显而易见,古人在“诗”的认识上,似乎与“志”形成相对固定的关联。《郭店楚简》这部先秦文献的出土,也证明了先秦时期儒家说“诗”的一个特点,对《诗经》性质和功用的认识往往与“志”并提。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且它的表意性表现在形与义的密切联系上。这一特点在小篆以前的古汉字阶段尤为显著。那么,借助相关的甲骨卜辞和金文对“诗言志”内涵问题的深入研究是大有裨益的。朱自清的《诗言志辨》专门讨论了“诗言志”,包括四个部分: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和作诗言志。其中,开篇的“献诗陈志”部分,朱自清先生就征引了杨树达《释诗》和闻一多《歌与诗》关于“诗”与“志”的卜辞释训,来证明“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并借用了闻一多阐释“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的说法,称“但是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指‘怀抱了。”接着,又根据孔颖达《正义》对《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产所言之“六志”的解释,以及《论语·公冶长》孔子让弟子“各言尔志”和《论语·先进》篇子路、曾皙、公西华“各言其志”的说法,称:“这种志,这种怀抱其实是与政教分不开的”[22]1113。他试图要说明的是,“诗言志”,这种怀抱是与政教相关的。也就是说,儒家诗论中所言的“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其实都与政教相关。
借助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成果,20世纪前半期,前辈们在《诗经》名物考释、作品年代的考释、文字、训诂和音韵研究,以及儒家《诗》论研究等方面进行多方尝试,且多有创见,在《诗经》的文本解读和古史研究的道路上可谓迈了一大步。这也启发后来者运用“二重证据法”,借助新材料对《诗经》等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些新出土的文字和图形符号材料,与《诗经》文本并不直接相关,其成果仍可为《诗经》研究所用。可以说,新材料的不断出土极大地开拓了《诗经》研究的空间,也有助于厘清甚至解决很多因文献不足而悬而未决的争议。
[参考文献]
[1]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2]王国维.古史新证[M].王国维全集(第11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3]王国维.观堂集林[C].王国维全集:第8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4]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
[5]王国维.文编[C].王国维全集(第14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6]王国维.东山札记[C].王国维全集(第3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7]郭沫若.十批判书[M].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林义光.诗经通解[M].上海:中西书局,2012.
[10]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傅斯年.傅斯年讲《诗经》[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12]马亮宽,李泉.傅斯年传[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
[13]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3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4]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15][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龚抗云等整理.刘家和等审定.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6]郭沫若.卜辞通纂[M].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
[17]郭沫若.殷墟粹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
[18][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廖明春整理.吕绍刚等审定.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9][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浦卫忠等整理.胡遂等审定.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0][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21]刘钊.郭店楚简校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22]朱自清.诗言志辨[M].诗言志辨 经典长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3]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4]洪湛侯.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5]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6]夏传才.《诗经》出土文献和古籍整理[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6675.
[27]江林昌.甲骨文与《商颂》[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3847.
[29]凌瑜,秦桦林.杨树达先生的《诗经》研究[J].古汉语研究,2011(1):58.
[责任编辑]李献英
"Book of Songs" Research Review In The Study of Oracle And Bronze In The First Half of Twentieth Century
CHEN Feifei,CHEN Liangwu*
(the Faculty of Arts,Minnan Normal University,Zhangzhou,Fujiang 363000,China)
Abstract:"Book of Songs"is our countrys first collection of poetry,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fucian classics, it is alway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and the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 In twentieth Century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rich unearthed material, research of inscriptions on oracle bones and ancient bronze objects advance,"Book of Songs"has entered a new field of study. In the succession of predecessors with wisdom, found in a large number of archaeological, underground excavated material and other documents handed down the double evidence law become complementary."Book of Songs"naming and system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text works in the school release, exege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erms and phonological research both the Confucian school theory of "Book of Songs"is a major step forward.These may offer help to clarify the shortage in suspense controversy, and "Book of Songs"open study on the space.
Key words:The study of"Book of Songs"; Inscriptions on oracle bones;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bronze objects; Textual research and proofreading; The Confucian school theory of"Book of So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