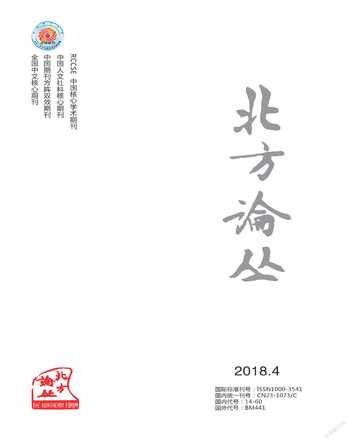当下“自然中心主义”的诗学建构及反思
2018-09-10王学东
王学东
[摘要]黄恩鹏不仅将“自然中心主义”作为他散文诗创作、诗学理论的核心部分,还数十年身体力行地“行走在自然的路上”,在行走中践行了“自然中心主义”理论,这使他成为当下文学“自然中心主义”诗学追求的一个重要代表。他“自然中心主义”的诗学建构,本身就隐含着对现代性批判,特别是对“人类中心”“理性中心”的现代价值的批判。然而,由于现实根基的缺失和“主体性”的消解,“自然中心主义”的文学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就呈现出“宏大感”和“抽象感”,也限制了他们走向更为丰富、复杂的世界。
[关键词]黄恩鹏;自然中心主义;现代性;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4-0045-06
虽然在整个20世纪中我们的“现代”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但是,“现代性危机”也深深地击中了我们的灵魂。面对现代性的“分裂危机”和后现代的“一切都行”恶果,“自然中心主义”使我们试图走出一种“另类现代性”的拯救之路。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中心主义”自然观,使中国传统文学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范式即“意境”。对于“意境”的迷恋,正是当代作家写作的最重要的追求之一。与“自然中心主义”的相遇,是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当下文学众多的“自然中心主义”的诗艺追求中,黄恩鹏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位散文诗作家。他不仅以“自然中心主义”作为他散文诗创作的核心部分,还数十年身体力行地“行走在自然的路上”,在行走中践行了“自然中心主义”理论,这使他成为当下文学“自然中心主义”诗学追求的一个重要代表。本文即从黄恩鹏的散文诗创作出发,探讨他“自然中心主义”追求的主要特征和意义,同时对当下文学“自然中心主义”追求予以省思。
一
“为何一种启悟内心的力量竟会来自山野?”“作为人类群体中的一个,我是否有资格成为自然的果实?”这是黄恩鹏在他散文诗集《过故人庄·自序》中提出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他诗学的一个重要起点。
对于第一个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为什么启悟内心的力量出于自然?”或者“为什么启悟内心的力量源于自然中心主义?”他在《过故人庄·自序》中说:“我始终认为,自然才是真正的王者:风雨。雷霆。雪霜。霞露。花草。树木。江河。山峦。这些自然物象,潜香暗度,以形神之妙,有思无思,返照内心之灵焰。”[1](p.2)在作者看来,自然才是纯净的灵魂,自然才拥有整体。也只有自然,才有起引着我们反照内心,才具有启悟我们内心的力量。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正是黄恩鹏“自然中心主义”追求的正面立论,这构成了他诗学追求的一个重要主题。
第二个问题,“作为人类群体中的一个,我是否有资格成为自然的果实?”则构成了他“自然中心主义”追求的另外一面,即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他在《过故人庄·自序》中做了回答:“科技与生态是永远对立的……传统意义的尊崇自然和敬天法祖已然不存在了。占据人类精神主导的,是蔑视自然万物、欲壑难填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唯人为大奴役自然的思想,让自然生态日渐恶化走向万劫不复”[1](pp.3-4)。也就是说,作为人类群体中的一员,“我”难以有机会成为自然的果实。而从“我”出发,以人类为中心,我不仅不能成为自然的果实,还将使自身处于灭亡的境地。这里他将“城市”与“村庄(自然)”对立,使得他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有了立足点。“‘城市限制了我的想象,‘村庄恰恰能扩展我的想象……我在城市被奴役的现实中似乎找到了一个救赎心灵的办法,那就是有意避开污浊的城市走向纯净朴实的自然乡村”[1](p.5)。所以,在黄恩鹏看来,“人类中心主义”“城市”不仅不具有启悟人内心的力量,还可能会成为毁灭人内心的力量。
既然“启悟内心的力量出于自然”,“启悟内心的力量源于自然中心主义”,那么与大自然结缘,而且不断地投入大自然环抱、融入大自然的“自然之子”,首先就转变成为黄恩鹏的真正梦想和实际行动。他在一次对话访谈中,展现了他追求成为“自然之子”的种种实践,“尤其这10年,我每年利用寒暑假行走中国西部,特别是横断山脉十万大山、三大江流域和少数民族寄居地……作田野调查,写乡村人文,品古老文化,吟草木诗歌。与一些乡亲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还被一个山乡授予‘荣誉公民., [2]。能夠为自然所接纳,能够为一个乡村所认同,能够与乡村、自然融为一体,是需要诗人真正投入的。黄恩鹏就是这样一位投入自然、拥抱自然的诗人,也正是他对于自然的倾心投入,才会被一个山乡授予“荣誉公民”的称号。与此同时,黄恩鹏“在路上”的丰富经历,又反过来进一步滋润了他“自然中心主义”的诗学追求,使得他的“自然中心主义”诗学追求更有了相当丰富的含义。第一,“在路上”首先是一种写作和生活状态。他说:“多年来一直葆有‘在路上的写作状态……行走让一个作家永葆‘活性的状态……我的生活与行走分不开,我的写作与行走分不开。”[2]其实“在路上”这一状态,不仅是对“自然中心主义”追求者有益,对于每一个写作者的身体和生活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当然,对于一个“自然中心主义”追求者来说,行走、生活、写作的三位一体的生存状态也就更为重要。第二,“在路上”是自我灵魂、自我精神的提升的一种方式。在《散文诗创作谈:我爱着这些纯净的灵魂》中,他所谈到的“行走”和“在路上”,有涉足莽原、深山、大地等所指,而且也有在城市、在日常生活中的“路上”等含义。所以,此时的“在路上”探求,就不仅仅是“在名山大川的路上”的追求,而上升为一种“在路上”的精神方式。而他在城市中的“路上”也是对于“自然”的回归,也是在追求走在自然的路上。由此“在路上”生存状态,已完全成为纯净灵魂、澡雪精神的重要途径。第三,“在路上”让诗人体验到更为丰富的诗性精神。他说:“‘在路上”让我找到许多清新的诗性元素。”[2]黄恩鹏的“在路上”之思,是他“自然中心主义”追求的最为重要部分。一个真正的“自然中心主义”,也必然是一位“在自然路上行走”的诗人。没有“在自然路上行走”的“亲在”体验,就不可能有“自然中心主义”追求的直接呈现,更没有“自然中心主义”的完美表达。
黄恩鹏较为直接而且深刻地表现出诗人主体对于“自然中心主义”这一观念的投入。作为一个“自然中心主义”的追求者和实践者,他长时间行走在自然中,直接面对自然,以表达自然、思考自然为创作的主题,可以说他是当下文学“自然中心主义”追求中的一位极具代表性的作家。
二
那么通过“行走在自然路上”的“親在”,黄恩鹏的散文诗又是怎样呈现出他的“自然中心主义”之思呢?
(一)“自然的尺度”
对于“美的规律”,马克思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3](p.97)在“人类中心主义”时代,在“美的规律”中“内在的尺度”得以无限放大,以压倒性的优势出现,以致遮蔽甚至掩盖了“种的尺度”,这是值得深思的。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也正是一个“自然中心主义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张扬“种的尺度”“自然的尺度”,还原“种的尺度”“自然的尺度”,就成为“自然中心主义”者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所谓“自然的尺度”,也就是说只有在“自然的尺度”的观照之下,自然才能获得呈现出自己的独立价值,自然才能呈现自己本身。在“自然中心主义”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视野、方法,都难以释放出“自然的独立价值”,难以进入自然本身的世界,所以必须回到“自然的尺度”。黄恩鹏在《谁能画出鸟鸣》中,展示了他对“内在尺度”的怀疑,同时表明要描述出自然必须以“自然的尺度”。如在《谁能画出鸟鸣1》中,诗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能画出这短促有力、美如露珠滴落的鸟鸣?”诗人明确地回答:“只有鸟儿能够描画出自己的声音。”另外在《谁能画出鸟鸣2》中,诗人认为:“只有鸟儿能够描画出自己的声音”,也就是说只有“鸟儿自身”才能展示出自己。只有以“自然的尺度”,从“自然的尺度”出发,我们才能认识和了解自然本身。
但是,作为“人”,我们又如何能真正地呈现出“自然的尺度”,抵达“自然的尺度”?“内在的尺度”与“自然的尺度”是相悖的,所以,要真正呈现出“自然的尺度”,人就必须把一切都交出来,还原一个最原始的、真实的自然。黄恩鹏在他的诗歌中,喊出“我把什么还给你”(《我把什么还给你》)的呼声。在这个“我把什么还给你”的过程中,诗人认为,就是要一切都还给自然,使自然的一切都回到“原有的位置”,呈现出自然最本真的面目;只有“我把什么还给你”,自然才能“各司其职”,实现出他最原初的价值。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把“内心的尺度”还给“种的尺度”,把“人类的尺度”还给“自然的尺度”,“自然的尺度”才得以显现。尽管作为“自然中心主义”追求的诗人,试图而且也努力把“内在的尺度”还原到“自然的尺度”,但是“人”与“自然”始终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的,于是在《雪的断想》中,诗人更借助于自然本身之力,让大地返回到“自然的尺度”。此时的“雪”就不仅仅是一个只描绘出自己的“雪”,也具有召唤整个大地返回“自身尺度”的力量。
(二)“静值”与“动值”
呈现“自然的尺度”,是“自然中心主义”追求的前提条件。由此在“自然的尺度”的观照之下,由于没有了“人类中心”的等级和权力压制,自然最原始的、最本真的形态得以显露。由此,展示自然自身的“静值”与“动值”,是黄恩鹏散文诗创作中“自然中心主义”追求的第二个追求和特征。
对于自然的一事一物的认知,也必须通过“自然的尺度”,我们才静静地深入到事物的内部,领略到事物本真的形态,感悟到事物最内在的灵魂。在“自然的尺度”视野之下,自然的“静值”,也就表现为静态自然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和意义。黄恩鹏在他的《深入一朵花蕊》中,就呈现了这样一种自然“静值”。一朵花蕊本身就有着“花蕊的尺度”,当我们从“花蕊的尺度”出发,我们方可深入到一朵花蕊。在静态的自然中,进入花蕊本身的世界,才能获得对于事物本身的领悟。同样对于整个自然也是这样,只有在“自然的尺度”之下,才能进入自身的内部,聆听到自然真正的声音。自然的“静值”就是这种真正的自然之声:“来到了王维的鸟鸣涧,俯拾皆是满山满涧闪亮的鸟鸣声。”(《鸟鸣涧》)诗人把自己还给了自然,成为自然间的一缕月光,此时月光、桂花、鸟鸣、幽篁等等自由地舒展开来,并不为任何一种人的价值所笼罩和掩盖,充溢于自然之间。
当把“内在的尺度”还原到“自然的尺度”之时,个人的生命又可以由世界重新赋予新的价值,重新奏响个体生命的乐音。自然的“静值”也直接浇灌着个体的生命,不过在这种生命的灌注过程中,自然的“动值”也就是动态自然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和意义,对于生命来说更有冲击力和启示性。如在《高处的高处》中,古老、雄伟、辽阔的动态自然,比生命更能体现出一种生命的哲学,更能给生命以智慧和力量。面对这种阔大的自然,诗人把他供奉出来。特别是动态自然界所张扬的“动态价值”,更为弱小的生命输人泪泪不息的力量源泉。他的《大河骨魂》,展示了自然的“动值”:“我看见那旺盛的青丝转瞬间变成了枯竭的白发——而只有黄河在不停地奔腾、不停地跳跃,那堤坝如同一只神奇的巨臂,拉满雄劲的大弩,向天狂射!”正是在这种力量的驱动之下,诗人的另外一种生命得以开启:“……那些路途,被一道道闪电的鞭子驱赶。/是时候了,我要策马而奔!越过泥沼,越过大海。/我要邀众鱼加盟,率领众多河流和我的血液一起,冲破重重阻碍。”(《我要策马而奔》)当世俗的生命面对纯粹的动态自然之时,将如被闪电驱赶一样,肉体生命的骨骼和血肉更加强健,生命之力得以勃发,生命之精神得以沸腾。由于本真自然所蕴含的“动值”生命力量,纯粹自然对于生命的洗礼和提升,显得极为强烈与有力。
(三)“自然之子”
在“自然的尺度”之下,“自然”的独特价值得以彰显,也且还以纯粹本真的“静值”和“动值”对世俗生命予以灌注,这让“自然中心主义者”更加痴迷与倾心。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成为自然的一分子,是“自然中心主义”追求的最终完成,也是黄恩鹏散文诗中自我生命与自然的真正融入的诗学表现。
在黄恩鹏的是诗学理论中,成为“自然之子”,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成为自然中的“物”。他曾在《当精神性质成为诗的哲学》中认为,对于“物化”审美的最好解析就是变成“物”。所以对于他自我的“自然中心主义”追求来说,最终完成也是变成“物”。“一种浑然忘记自我的玲珑之美的存在……可说是对‘物化审美最好的解析”。所以,在黄恩鹏的散文诗作品中,处处可见他对于成为自然中的“物”的追求,时时可见他成为自然界中的一“物”,忘情于天地之间。如《身在小屋想着遥远的峡谷》,诗人做了自然中的“一棵草”,由此听见了全天下的风声雨声。在《独坐幽篁》中,诗人又成为自然界中的一竿竹子,化身为自然界中的一“物”的追求处处可见。还有像《种菊南山》,“千年了!何时我也把自己变成一株菊,在南山上,悄然种下”。
其实对于“自然中心主义”者来说,成为“自然之子”与其说是直接成为自然中的“物”,不如说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所以,在《过故人庄》中,诗人动情地说道,“从今天起,我把大地上每一个村庄都叫故乡,把每一个人都认作我的乡亲。/我走到哪里,哪里都会有我熟悉的乡音。”也就是说,尽管人不能真正变成自然的一“物”,但只要向往自然、投入自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扎根在自然中的一“物”,成为一个真正自然之子。
(四)“神性梦想”
让现实生命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中心主义者”一个“真正梦想”。然而,具有“内在的尺度”的我们,始终是与“自然的尺度”有着天然难以逾越的鸿沟,难以实现成为自然之一“物”的梦想。由此,一种高扬宗教信仰的“神性梦想”,成为“自然中心主义”追求的实际落脚点。
对于“神性梦想”这一概念,黄恩鹏在他的《去远方寻觅神性梦想》中阐述:“诗人神性的梦想在大自然的簇拥下永远不会孤独……谁能走进大自然与之默默交流,谁就能体味到一种畅快心灵的神性梦想。有时候,我认为人的精神需要一种依托。而现代人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精神的无根性。”[4]这里他对“神性梦想”的阐释,有以下三层意思:第一,“神性梦想”是人精神的一种依托;第二,“神性梦想”的获取途径只能通过走进大自然,并与之交流获得;第三,自然中的神性梦想,具有宗教精神。由此在黄恩鹏的散文诗作品中,他对自然有着“神性梦想”的寄托,使得他的散文诗充满了神性、宗教、信仰的声音。他不仅从自然界看到世界的大美、纯洁,还看到自然的宗教性、神性。如《去紫竹院看莲》所说:“谁说这个世界已彻底肮脏?/只要你排拒同流合污,只要你心为莲花!”作为象征佛教的“莲花”在他的散文诗中多次出现,这样的纯粹自然就有着一种强烈的宗教气息。而这朵自然界的莲花,不但是黄恩鹏远离喧哗、躁动、邪恶、贪婪、肮脏都市的抵抗力量,而且更是他赢得圆满、纯洁的世界的动力源泉,他试图以这样一种“神性梦想”来拯救大地。在另外一些作品中,黄恩鹏纯粹自然的“神性梦想”,还直接呈现为对于宗教的皈依。此时,自然已经完全化身为“伟大的宗教”,一種浓浓的宗教气息弥撒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魂化为鹰——听布鲁诺·库列斯<喜玛拉雅>》《错温布》等作品中,“自然”与“宗教”融为一体,他对于“自然中心主义”的追求,便直接成为诗人一种宗教信仰的表达。
黄恩鹏在他的文论中多次表述了“神性梦想”,丝毫不掩饰写作中执着的宗教追求。“诗,是在一个干净的圣地说干净的话,是‘在寺之言的心灵宗教,因此就不能亵渎神灵。古诗文中哪一首哪一章不是有着唯美意境的心灵之语?但今天我们却将诗歌异化成如此这般,更逞论要成为诗的‘圣徒了。不能给诗以尊崇,那么他的诗也肯定写不好,更不会写出澡雪心灵之作。把诗作为神性梦想,让浑沌的心灵得以澄澈,一直是我的创作圭泉”[2]。可见,他散文诗中的“自然中心主义”,已纯然是一种“心灵宗教”的表达。诗、自然、心灵、宗教、信仰最终构成了多维一体的“神性梦想”。宗教性、神性的展现,这正是以黄恩鹏为代表的“自然中心主义”者创作的终极指向。
三
黄恩鹏散文诗中的“自然中心主义”追求,在当代诗歌中有着普遍的代表性,体现了当代众多的“自然中心主义”在现代批判和诗学建构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劝诫美学
黄恩鹏“自然中心主义”的诗学表达,本身就隐含着对现代性批判,特别是对“人类中心”“理性中心”的现代价值的批判。他说:“人类在自然面前根本就没有道德和情操可言!还因为人类并未把自然当作‘圣神来崇敬,而是不停掠夺、损毁。”[2]在他看来,正是人类用“科学手段”等现代手段改变了“自然规律”,违背了自然本性,而忽视了自然本身的“神圣”。因此,他的“自然中心主义”追求,正是对于当前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的批判和反思。我们知道,尼采震耳欲聋的一声“上帝死了”,道出了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特征,同时更展示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当我们还未从“现代性危机”中拯救出来之时,“后现代”又在这里隆重地登场、喧哗,占领了我们的舞台。在后现代社会中,而这些根基都缺席了,一切都四散了。没有上帝、没有神、没有终极、没有永恒,甚至没有人、没有世界。后现代社会的“一切都四散了”,照射出人所生存的现实世界的处于沉沦状态,此时的人类丧失了价值、意义、尊严和追求。在黄恩鹏看来,这条走出现代性危机的“另类现代性”的拯救之路,就是走向自然,回归自然。“以梭罗、缪尔、巴勒斯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就是在改变人的主体观念上做着努力,让生命回归自然本态。多年来我一直注重自然对人的影响。自然物象的精神性质照亮了我的抒写。我认为:大自然是最伟大的宗教、最伟大的哲学。它给人带来的是源源不尽的生机,而不似科学给人类带来幻灭”[2]。这样,他的作品中的“自然中心主义”追求,便成为他的“另类现代性”拯救之路。
黄恩鹏的这种“自然中心主义”追求的拯救之路,在他“神性梦想”的基础上,以他所谓的“劝诫美学”来实施、完成。他在《当精神性质成为诗的哲学》中这样定义“劝诫美学”:“面对茫茫人世,芸芸众生以及复杂的社会人性,我们太需要这样闪烁着‘劝诫美学的文字来澡雪内心了。我曾与一些散文诗人等探讨过这种‘劝诫美学。大地万物,人间万象,其实都是相互映照的……我想,一位散文诗人,抒写内心之美和自然之美,是永远的追求。”尽管“自然中心主义”所追求的是“自然的尺度”,但是,“自然尺度”价值的完成是需要“内在尺度”的人来实现。作为大地万物的自然,本身是与人间是相通的,而诗人正是人与大自然的沟通者。把“自然的尺度”“自然之美”传递给读者,在他看来就是诗人的神圣使命。这种在自然与人之间沟通,并把自然之美传递给人,就是他所说的“劝诫美学”的指向。他说:“优秀的作家仍会坚持唯美的生命诗学。他总是关注高贵的精神力量,把内心最美好、最富启示性的作品献给读者。”[2]诗人通过还原大自然的“自然尺度”,呈现出大自然的“神性梦想”。在此过程中,既是对现代社会凌厉的批判和否定,又是把精神、爱、灵魂直接传递给读者,交给读者,以达到他所提倡的“劝诫美学”之旨归。
(二)“文本之美”
诗人要完成“劝诫美学”的使命,除了全身心投入自然,行走在自然中以获得自然的“神性梦想”以外,还需要有一种独特而精确的“诗艺”。对于散文诗“文本之美”的追求,也是黄恩鹏对于散文诗的诗学建构所做出的重要启示。在黄恩鹏的散文诗创作中,就有着他对于“文本之美”的不懈探索和努力的精神。耿林莽曾说:“这是一种‘浪漫主义”是高度的夸张与变形,而又得力于诗人的语言修养之娴熟和鲜活……这些语言来自想象的大胆、奇特,新颖而又准确,不能不令人为之赞叹。”[5]正是在这种精湛的诗艺基础上,黄恩鹏形成他“文本之美”的艺术追求,实践了他的“自然中心主义”追求。同时这一“文本之美”的诗艺追求,展现出黄恩鹏独特的诗意能力,使得他散文诗作品具有丰沛的意境。他在《当精神性质成为诗的哲学》中说:“揆诸诗文本之美的脉息,需要深入语言内部,对其思想进行触及、感受或拥握。那些充盈着曼妙的语言镜像的诗句,让我由衷对神谕的创造产生深深的敬意。事实上,无论哪一位散文诗人的诗作,我都要细读其丰沛意境。”从“文本之美”走向“意境”追求,则是他散文创作的必然趋向。
而当下文学“自然中心主义”追求的“意境”,又继承着中国传统自然观的血脉。黄恩鹏在艺术上的追求中,由于具有先天性的“自然中心主义”之思,所以在审美情趣上就天然地有着“意境”追求。正如他在《物化审美:农事节气意象在内心的敞亮——评成路<大原:意象旗帜>》中所说:“诗画艺术之源,在于对自然造化的生命感和氤氲感。即体现在广远的诗歌境界之中,有着与宇宙相通而‘气象氤氲(皎然《诗式》)的生命感。在孤灯夜影中,诗人内心澄明,聆听笔触对于自然的诉说,在笔墨声声中,提扬古今与未来之精神品格。”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他的散文诗为我们呈现出丰沛的“意境”。
四
当下文学中的“自然中心主义”追求,由于立足于“自然”来批判个体、社会,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也陷入困境。
一方面对于以黄恩鹏为代表自然中心主义者来说,“自然中心”是他的诗学基点,成就了他们诗文创作中的独特艺术魅力。而与此同时,这一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他们走向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世界。“自然中心主义”所具有独特的优势,正是在于这一思想对于“人类中心”或者说“人间烟火”的超越,但真实的人的存在,首先就是“人”的存在,就是在“人間烟火”中存在。忽视“人类中心”,这是“自然中心主义”走向更为丰富、复杂的一个重要瓶颈。在人的存在维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仅是其中的一个维度而已。人的存在还有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其他的维度。毫无疑问,俗界、人间更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真实的存在。诗歌中“自然中心主义”忽视、超越这些维度,恰巧是对于人生命存在的基本现实的遮蔽与忽视。超越“人类中心”,诗歌中“自然中心主义”的致命性问题在于他们对于人“主体性”的抛弃。也正是由于现实根基的缺失和“主体性”的消解,“自然中心主义”的文学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就呈现出“宏大感”和“抽象感”。对于文学来说,我们非常需要这种“宏大感”和“抽象感”,但是,如果这种“宏大感”和“抽象感”没有生活细节,没有个体情绪,其最终的影响力将是极为有限的。其实,黄恩鹏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也不断地反思,并在他的“自然中心主义”的追求中加入“人类中心主义”的多种思考。他在《散文诗思考01散文诗:宁静才能致远》中就说:“早时阅读梭罗,很是感佩他孤寂中强劲的精神崛动腾升的才思火焰,还如此旺盛燃烧至今,吾辈弗如也!”作为“自然中心主义”的杰出代表,梭罗的伟大、不朽与其说是归于自然,不如说是归于人,归于人的伟大人格,这才是梭罗给予自然中心主义追求者最重要的启示。
另一方面,在整个现代诗的发展历程中,“意境力量”对当代诗歌的发展也是需要进一步反思的。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现代工商业文化发展成为主流,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基础已经发生改变,失去了生成古典自然观“意境”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在这样的环境下,在古典“自然观”之下,“意境追求”等美学规范基本失效了。“自然中心主义”及其表达方式与现代生活、现代生存之间有一定的隔阂。当然对“自然”本身的认识是否就已经被穷尽,是否就没有与现代社会、现代人生相契合之处,我们难以否定。然而,在传统自然观缺失、意境消解的基础上,当代诗歌在日常生活中,才能通达对人、生命、时空、宇宙、存在等问题。而这样的探索,才更能为当代诗歌的发展贡献出丰富的价值。
总之,在当下文学中,黄恩鹏以其“在自然路上行走”的“亲在”体验和丰富的散文诗文本,从“自然的尺度”“自然的‘静值和‘动值”,“自然之子”“神性梦想”等四个方面,鲜明地展示出“自然中心主义”追求的诗学特征。他的这种追求不仅隐含着对现代性批判,特别是对“人类中心”“理性中心”的现代价值的批判,还呈现出独特的文本之美和丰沛的意境,在当下文学“自然中心主义”追求中做出相当可贵的探索。尽管这一追求,在当代诗歌走向更为丰富与复杂的精神世界,还需要面对和审视自身的困境。
[参考文献]
[1]黄恩鹏.过故人庄[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2]文榕,黄恩鹏.诗学对话:心灵、大地、精神性质和历史感[J].中国诗人,2012(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黄恩鹏.去远方寻觅神性梦想[J].散文诗,2009(4).
[5]耿林莽.想象力在驰骋——读黄恩鹏散文诗四章[J].散文诗,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