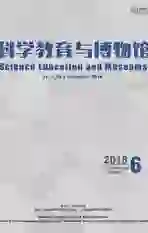震旦博物馆“古器物学研究陈列”教育模式刍议
2018-09-10黎冬瑶
黎冬瑶
摘 要 博物馆是以教育为首要功能的文化机构,而陈列展览则是其发挥教育功能的主要途径。震旦博物馆的“古器物学研究陈列”从文物的“料、工、形、纹”入手进行解读,它以“解构”与“建构”的逻辑关系为教育理念,使用实物、图文、数字媒体、辅助艺术品与纸质媒体、自媒体平台等相结合的集成化教育手段,形成以教育时间为维度贯穿客观物质空间始终的“四维空间”,并突出文物残器在陈列展览中的教育作用。可见,“古器物学研究陈列”教育模式有助于公众自主学习,将最大限度地实现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关键词 古器物学研究陈列 博物馆教育 震旦博物馆
0 引言
博物馆是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1]我国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放在首位,以凸显其重要性。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发挥教育功能的核心手段,近年来各具特色的陈列模式层出不穷,是我国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在位于上海的震旦博物馆中,其常设展览以古器物学研究为主要陈列方式,构成体现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新模式。虽然“古器物学研究陈列”在震旦博物馆的实践中开展许久,但学界对其在博物馆教育方面的理念、策略、特色及作用鲜有论及,这无疑不利于该教育模式的执行与推广。下面,笔者就对此进行解读,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1 震旦博物馆的古器物学研究
古器物学研究是金石学向考古学发展的产物。罗振玉在《古器物学研究议》一文中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即“今定之曰古器物学。盖古器物能包括金石學,金石学固不能包括古器物学也”。[2]近代以来,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古器物学研究已达到相当高的成就。通过研究标的物“料、工、形、纹”四个基础层次,将古器物转化为“器物史料”,并进一步结合考古学、人类学、美术史、文献、科学技术等学科,最终还原古器物所在的时空背景。[3]其中“料、工、形、纹”是古器物学研究的四大要素,既包含器物本身的基本属性,又包含器物演化过程中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更包含器物与人之间通过“制造—使用—影响”所产生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震旦博物馆以历史与艺术并重,集典藏、研究、展览、营运、宣扬为一体,秉持对中国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在“历代玉器”“青花瓷器”“佛教造像”三个常设展览中设立“古器物学研究陈列”单元,置于展厅最后。对古器物进行分项与整合研究,在探究物源的基础上,还原物质文化与社会生活,反映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为博物馆发挥研究、教育、欣赏作用提供理论支撑,为公众自主学习与社会教育提供可靠依据。
“历代玉器”常设展览分为“古代玉器精品”“汉代丧葬用玉”“玉器古器物学研究”三个单元,以不同视角揭示了中国古代玉文化的深厚内涵,在梳理历代玉器艺术风格及发展脉络的同时,具体呈现各个时期迥异的思想潮流、生活方式及美学观点。
“青花瓷器”常设展览分为“中国历代青花”“青花瓷的外销”“青花瓷器古器物学研究”三个单元,精选馆藏元、明、清三代青花瓷器,运用古器物学的研究方法细致剖析,清晰地勾勒了青花瓷器绵亘六百年的轨迹。针对销往海外的贸易瓷器,以典型器物挖掘青花瓷器在世界范围内的流传路径和重要影响,重现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盛况。
“佛教造像”常设展览分为“犍陀罗造像”“本土化造像”“佛教造像古器物学研究”三个单元,旨在全景式展现各造像的材质特征与工艺技术,介绍中国佛像的源起、本土风格的形成及古佛新生的意义,由一个侧面阐释华夏文明所具有的艺术创作力与文化融合力。
2 “古器物学研究陈列”教育模式的构成
2.1 从“解构”到“建构”的教育理念
所谓“解构”与“建构”,源于西方提出的“解构主义”和“建构主义”。古器物学研究用解构思维打破器物的固有结构,用碎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局部现象或构件本身所具有的本质,再建构出一套新的理论体系。
任何一种“物”都可以被解构为两种基本属性,即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自然属性是物质本身的基本属性,包括材质、形态、结构等;文化属性是物与人发生联系之后产生的,如工艺价值、美学意义、实用功能等。比如,“佛教造像”常设展览中的“佛教造像古器物学研究”单元在陈列内容上进行了多层次的解构处理:将“料”解构为“石材辨识”“材质种类”“材质变化”三个部分,其中“石材辨识”又进一步解构为“大理石”“石灰岩”“砂岩”;将“工”解构为“造型工法”“纹饰工法”两个部分,其中“纹饰工法”又进一步解构为“镂空技法”“线刻技法”“浅浮雕法”“高浮雕法”;将“形”解构为“群体造像”“单尊造像”两个部分,其中“单尊造像”又进一步解构为“佛像”“菩萨像”“护法像”“罗汉像”;将“纹”解构为“五官纹饰”“穿戴纹饰”“手足纹饰”三个部分,其中“手足纹饰”又进一步解构为“印式”“坐式”。在每个标题之下继续按照时代或种类进行解构,直至分解为最基本的物质构成。
以古器物为视角的博物馆陈列对包含着复杂信息的文物展品进行碎片化处理,使观众在参观过程中透过解构思维的直观呈现,结合在相关主题中的学习体验以及固有认知,将文物所蕴含的各种要素重新排列组合,搭建起符合个体认知的框架体系。这种“输入—内化—输出”的教育模式,实际上是对文物信息由“解构”到“建构”的认知过程,而认知建构又将为下一次观展所形成的知识迁移提供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震旦博物馆的“古器物学研究陈列”在各常设展览中以独立展区的形式,通过古器物学研究方法,将文物展品的基本信息更加全面地传播给社会公众,促进观众实现由“解构”到“建构”的学习过程,为博物馆创建全新的教育模式奠定了基础。
2.2 “四维空间”中的集成化教育手段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面向社会的主要传播媒介,是面向公众传播文化信息的独特语言,即在一定空间内,以文物藏品为基础,配以适当的辅助展品,按照一定的主题序列,采取适当的艺术形式,进行直观教育和信息传播。[4]震旦博物馆的“古器物学研究陈列”以多种方式、多个渠道展现文物所蕴含的信息,综合运用集成化的手段对社会公众进行教育。下面,以“历代玉器”常设展览中的“玉器古器物学研究”单元为例,列举出如下教育策略:
(1)实物陈列
该展区以实物展品为主,包括古玉器文物标本、玉石原材料和传统制玉工具等。在适当的位置展示某件文物所对应的原材料及生产工具,弥补了传统陈列中“重文物成品而轻生产流程”的不足。当文物本身多层次的信息以有限的方式对外传播时,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势必会产生疑惑,而能否在展览中找到答案,便成为博物馆达成教育目的的关键。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古器物学研究陈列”为观众提供了一个“问题探源”的研究性学习策略,它以实物陈列的方式厘清了文物的原材料构成与生产环节,让观众理解其产生、发展的链条,为后续的自主学习提供了指导性思路。
(2)图文说明
图文说明是展览与观众对话的媒介,是展览的说故事者,直接关系到展览的思想、知识和信息传播以及观众参观展览学习的效益。[5]该展区的展柜上方设有连续性图文版面,形式包括文字解说(中英双语)、实物照片、示意图片等,其内容与展柜中的实物展品对应。系统的图文说明以其延展性的空间布局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有助于提高其在参观过程中的学习效率,而图文结合的展示方式,也为观众带来了生动、形象的学习感受。
(3)数字媒体演示装置
各专题展板旁设有数字媒体演示装置,循环播放视频资料,诸如纪录片《中国古玉之美》等。数字媒体技术的运用,不仅在细节展示上优势明显,而且充分调动视觉、听觉等感官,形成完整的述说式故事情境,能够唤起观众的主动参与意识。
(4)辅助艺术品
该展区放置了一组仿古治玉机器的模型,此类辅助艺术品“是根据客观依据进行的再现、还原和重构”[4],模拟出古玉制作的现实场景。配合清代画家李澄渊的《玉作图说》,依次按照13道工序,营造了关于制玉流程的時空结构。通过身临其境的方式,帮助观众对所学知识作总结与回顾,完成在馆内的学习任务。
(5)纸质媒体与自媒体
出版发行是博物馆实现科学研究与宣传教育职能的重要表现,一般以学术刊物、馆藏图录及研究著作为主要形式。震旦博物馆的博物馆商店中对外售卖《认识古玉新方法》[6]等书,自浅入深,从看玉、读玉、解玉三个阶段循序渐进,用古器物学研究方法论述中国古代玉器在各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让观众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学习,不再受限于场馆空间与开放时间。
步入信息化时代以来,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与自媒体平台的发展改变了公众获取资讯的方式,为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策划与实施提供了新的可能。震旦博物馆在其微博、微信上,每周定时更新“古玉天地”栏目,推送相关科普文章作为陈列展览的内容延伸。诸如《古玉的外来沁染》《古代的制玉工具》《古玉的形制演变》《古玉的纹饰制作》等,从玉料、工法、造型及纹饰的角度进一步探讨,此法“于馆外空间继续与观众保持联动,尤其是为实际观众提供后续的延伸拓展服务”[7],深化了社会公众的学习认识。
上述由“古器物学研究陈列”衍生出的教育策略使得公众便捷、高效地了解到文物知识,以实现“终身学习”的教育目标。这些多层次的互动所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不可估量,因为它们所激发的学习——适合多种方法和目的的学习模式——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无法获得的。[8]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公众认知水平的提高,当代博物馆的陈列设计已经融合了多种教育策略,将文物自身、物与物、物与整体的三维存在状态转变为一个“四维空间”,即以教育时间为维度贯穿客观物质空间的始终。观众在展厅中通过实物、图文、数字媒体、辅助艺术品完成馆内体验式学习,再利用纸质媒体与自媒体平台进行馆外延续性学习。从空间上来说,真正做到了学习环境自博物馆展厅向生活处所的空间位移,以及对多种教育策略的集成化运用。从时间上来说,延长了学习者的受教育时间,使得教育机会更为多样且灵活,满足个性化的需求。
2.3 文物残器中体现的教育模式特色
震旦博物馆的“古器物学研究陈列”多以实物残器为文物标本进行教育展示,如带有沁色的玉器、烧制变形的瓷器、断裂的造像构件等,这已成为该教育模式的一大特色。有些文物或因年代久远损毁严重,或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未能成型,其艺术价值相对较低,但作为记录历史发展与器物演变规律的实物遗存,其历史和科学价值依然弥足珍贵。
相对文物精品而言,文物残器所具有的教育功能更为显著。“青花瓷器”常设展览中的“青花瓷器古器物学研究”单元,引发了观众对钴料种类与青花呈色、绘画技法与纹饰特征、成型方法与装烧痕迹的思考。例如,面对一件因变形而不能将“套烧”器物单件取出的三足炉,观众并不会将目光放在它的缺陷上,而是会揣摩该器物在烧造过程中多层相套的原理。再如,陈列中所展的一件元青花变形大罐,以其变形原因作教育要素之用,使观众直观感受说明牌所言“壁厚不足,高岭土少”而导致青花瓷器在烧制过程中塌陷变形的现象,并与“青花瓷器的胎体是用瓷石加高岭土合成的二元配方胎土”相呼应。
3 余论
博物馆教育中的“自主学习”是指公众通过主动参与而构建个体认知的学习过程,“它会导致新知识的认知同化,对学科态度发生改变或者在实际行动中行为的实质性变化”[9]。公众在博物馆的教育活动是有目的、有选择的自主学习过程,博物馆应当为满足公众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提供机会与平台。震旦博物馆的“古器物学研究陈列”设置于每一常设展览的结尾,观众在参观“文物精品”与“专题展览”之后进入该展区,此时观众通过前两个单元的学习已形成部分意义上的认知构建,而这种构建又往往因缺乏对文物基本信息的了解而显得模糊、笼统。因此,从器物本身出发,通过对“料、工、形、纹”的全面剖析,弥补历时性或专题性陈列对于“物”本身泛泛而谈的不足,观众可以根据前期观展所形成的信息框架,结合自身的认知经验和知识需要进行自主学习,再将得到的信息分类整合到已有的认知体系中,使得整个学习过程发挥更大的自主性作用。
参考文献
[1]博物馆条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2]罗振玉.古器物学研究议[M].天津:贻安堂经籍铺.
[3]蔡庆良.古器物学研究——原生形、次生形、再生形玉器的讨论[M]//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359-379.
[4]单霁翔.浅谈博物馆陈列展览[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5.
[5]陆建松.博物馆展览策划:理念与实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6]吴棠海.认识古玉新方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
[7]郑奕.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8]美国博物馆学会.博物馆教育与学习[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9]Arja Van Veldhuizen.博物馆“主动”参观面面观[M]//郭俊英,王芳.博物馆:以教育为圆心的文化乐园.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