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i奴”缘何不可能:劳动过程的遮盖及非经济报酬的崛起*
2018-08-07杨逐原
■ 杨逐原
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类形塑了一个网络社会,人们纷纷从现实世界进入到网络空间中,生产出大量的信息产品,并尽情地体验着网络空间中五彩斑斓的生活。可以说,网络空间已成为信息产品的主要生产和消费场所,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在网络空间的信息生产和传播中,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同样对作为劳动者的网络用户进行着深层次却极具隐蔽性的剥削,将网络用户变成了网络空间中的“i奴”。然而在获得一定的非经济报酬后,“i奴”也心甘情愿地为网络媒介劳动,呈现出“劳动至死”的大众狂欢状态。
一、作为劳动的传播与作为“i奴”的网络用户
(一)传播是一种生产性的劳动
丹·席勒指出,传播若要在语言、意识形态与意义的展示平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先要让“劳动”与传播产生一种互动关系。唯有从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labor)这个概念,也就是人的自我活动具有兼容并蓄及整合的性质来构成自身的认知出发,传播研究才能开始发展①。可以说,丹·席勒将文化传播与劳动有效地结合起来,较早地把传播安置在了劳动的范畴之中,为传播与劳动的相关研究指明了方向。
其实,关于传播是一种生产性劳动这一问题,我们也可以从马克思有关生产性劳动的论述中找到支撑点。马克思是这样界定生产性劳动的:“生产劳动是给使用劳动的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物化在商品中及物质财富中的劳动”②。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角度来看,生产性劳动无疑是一种雇佣劳动,资本家用工资这一可变资本来交换工人的生产性劳动。交换后,工人在劳动中不仅生产了资本家用于交换的工资资本,还为资本家生产了大量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从单纯的一般劳动过程的观点出发,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更确切地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对我们表现为生产性劳动。③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性劳动并不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只要劳动为资本家创造了高于它的必要成本的剩余价值,它就是生产性的”④。由此可知,所谓的生产性劳动,是存在着雇佣关系,与资本进行交换、对资本的增值起直接作用的劳动。信息传播是具有生产性劳动的特征的,这是因为生产性劳动的范围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范畴的扩张而不断拓展,技术、生产力在生产性劳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在技术和生产力的作用下,资本有能力将工资关系强加在许多以前是非工资关系的社会劳动身上。技术创新,包括信息存储、处理、复制和传播领域的创新,使得众多职业中的生产者与产品以及生产过程相分离。在新传播科技的赋权下,信息传播的经济效益日渐凸显,大量的信息产品被不断生产出来,信息传播者与资本之间产生了泛在化的雇佣关系——资本搭建信息传播平台,信息传播者借助相应的平台实现信息产品的生产和传播,为作为平台提供者的资方创造大量财富,使信息传播和服务突破了自我雇佣的领域,出现了使用平台即被雇佣的情况。而信息的传播能为资方创造大量财富,也就意味着信息传播为资本家创造了巨额剩余价值,因而传播是一种生产性劳动。
(二)网络用户是网络空间中的“i奴”
1.网络用户是网络空间中的劳动者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⑤。而关于劳动力,马克思将其界定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⑥。由此可知,凡是有劳动力的人,都可以成为劳动者。网络用户具有自己的智力和体力,他们在进入网络空间时,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脑力和体力之和)进行劳动,生产出特定的信息产品。因此,从劳动力使用方面来说,网络用户能够进行劳动,是实际意义上的劳动者。
此外,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更换的过程”⑦。同样,在网络空间中,网络用户也以网络中的信息资源为对象进行着信息产品的生产,这一劳动也可视为网络用户与网络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是网络用户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网络各要素之间的信息更换的过程,因而网络用户也在进行着生产资本的劳动,只是在传播科技的赋权下,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没有签定任何劳动合同,靠搭建网络劳动平台来雇佣网络用户而已,这是一种泛化的雇佣。由此可知,在网络中,网络用户以软件、知识、文化、教育艺术等公地为基础,生产出规模极为巨大的信息内容。因此,在网络空间中,网络用户统合脑力和体力,复制、转发、搜索、生产各种各样的信息产品,被嵌入到了网络空间的信息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劳动过程之中,成为了广义上的劳动者。
2.网络用户是网络媒介的“i奴”
网络用户何以成为网络媒介的“i奴”?众所周知,在劳动方面,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与作为劳动者的网络用户之间并没有形成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使得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被忽视了。虽然没有形成法律上的雇佣关系,但网络媒介和网络用户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原因在于这种关系绕开了法律渠道,凭借网络技术而得以存在。不管有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只要在网络媒介经营的平台上进行劳动,网络用户就为网络媒介创造了大量的剩余价值。资本的扩张包含在一切形式的投机之中,能够利用技术手段雇佣劳动者而不承担后果,网络媒介肯定不会放过这种机会。在资本的操纵下,网络用户不计一切报酬地劳动着。在今天的网络中,娱乐消遣已经成为网络用户的头等大事,网络用户不会关心自己的劳动受不受控制、受不受剥削,他们被网络技术驯化了,不分昼夜地投入到网络劳动之中,遭受着更深层的剥削,成为了网络媒介公司的“i奴”。“i”是网络(Internet)的首写字母,“i奴”其实就是互联网中的劳工。在这样的情况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废除“i奴”的呼声此起彼伏。
二、“i奴”日益受关注,废奴之呼声日渐强大
当前,“i奴”遭受着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公司的深度剥削已成为共识。随着“i奴”这一群体被剥削的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i奴”的觉醒,呼吁给予“i奴”合理的报酬以便将其废除。
马克思在谈到资本扩张时曾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⑧。网络技术使网络用户这一新的劳动群体卷入了网络媒介的信息资本体系之中并为之乐此不疲地服务。邱林川、陆地等学者将这种情况称为新的“奴隶主义”。并要求告别、废除“i奴”。在《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一文中,邱林川以17世纪“大西洋三角贸易”的奴隶制世界体系为起点,详细地讨论了当代的数字劳工问题。邱林川强调劳工抵抗是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之必要组成部分,富士康引发的抗争已呈现网络化趋势,这为分析当下网络劳工抵抗提供一定的借鉴。⑨邱林川认为,用户生成内容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增长点,包括用户有意识上传的图片、视频、日志和网络搜索关键词等资料,包括网民的浏览习惯、社交网络及其他信息,特别是个人消费信息,包括信用卡号、有生物体信息(Biometrics),如身体移动让手机里的GPS产生信息⑩。有鉴于此,邱林川呼吁废“i奴”,并认为从富士康的员工引发的,使各阶层人物卷入的利用微博、论坛等抵制、谴责富士康管理体制的运动,已经形成一种WGC,即“工人生成内容”(Worker-generated content),而不是单纯的UGC群体的抵抗运动。北京大学的陆地认为,在网络技术影响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今天,“i奴”对网络技术产生了巨大的依赖性:从行为参考到行为依赖、从精神调济到精神依赖以及从信息使用到信息依赖。陆地呼吁“i奴”及时抬头,不要一味低头做奴隶。在国外,加拿大的莫斯可以及麦克切尔等学者也对信息时代诸如“i奴”在内的媒体劳工进行了研究,也呼吁给予这些媒体劳工恰当的报酬,废除媒体的奴隶。
但事实上,在“i奴”的劳动过程被遮盖,以及非经济报酬强势崛起使得报酬界限日益消弭的情况下,废除“i奴”成了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三、废除“i奴”缘何不可能
(一)“i奴”缘何甘愿被剥削——被网络技术遮盖的劳动过程
1.网络技术赋权下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公司的权力的隐身
在网络技术的赋权下,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公司能够有效地把强制“i奴”劳动的权力隐身起来,以一种柔和的方式(打造“i奴”心甘情愿地为之劳动的信息生产和消费平台)征用“i奴”进行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劳资双方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劳动关系,这给人的印象是资方的强制权力已经消失了。事实上,在网络空间的劳动中,权力并没有消失,它真实地存在并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只不过其通过技术进化、“客观结构的主观化”等一系列隐身术实现了隐身,使人们无法正确意识到它的存在。那么,在网络空间中,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公司是如何实现权力的隐身的呢?
(1)巧妙地利用网络技术所赋予的权力
网络技术为资方权力的隐身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网络技术的赋权存在多面性,在为“i奴”的劳动空间赋权的同时,也为资方赋权。利用网络技术,资方能够将控制手段化为各种各样的“平台”(如各种社交网站、电子商务等等),将劳资关系隐藏于平台之中。由于平台往往以聚集“i奴”进行信息点击、浏览以及发表信息等网站或贴吧的形式存在,已经被符号化为可供“i奴”娱乐的网页,“i奴”凭着惯习很难感觉到平台控制权力的存在。
劳资关系是经济学中的一对重要关系。网络技术在统合了所有媒体技术的同时,还建构了人与人之间即时交互的空间,全面渗透到了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之中。网络是一个泛符号化的世界,因而不管是什么物体和关系,在进入网络后都被符号化了。在网络这个泛符号化的世界中,权力能够对符号的意义进行建构。在“i奴”的劳动中,资方正是通过将劳资关系进行重新建构而实现了权力的隐身的。
(2)将权力在场转化为缺场而实现隐身
网络搭建各种劳动平台,最大限度地吸引“i奴”进行信息生产、传播和消费。“i奴”在进行信息生产、传播和消费等劳动时,往往只感觉到与自己属于同一群体的人的存在,他们把交谈者、围观者和点赞者视为圈内人,被娱乐和社交的天性牵引着与他人发生互动。即使是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的员工带着操控的思想与“i奴”进行互动,也往往被“i奴”看成是一般的交流,或者认为与之交流的员工正致力于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很多时候,在“i奴”仅有的信息交流和娱乐理念的指引下,劳动变成了娱乐和交谈,资方的权力操控被抛之脑后,权力在场无形中变为了缺场。在这种情况下,资方的权力实现了由在场向缺场的转变,权力被隐身了。同时,网络技术使资方在网络空间中构建起一座座“全景敞式监狱”,资方掌控着网络空间中的各种符码。因此,即使资方真的暂时缺场,在对“i奴”的劳动行为进行全方位的监视后,资方也能够将“i奴”劳动的符码进行解码,获取不在场的掌控能力。
2.被网络技术遮盖的劳动过程
在探讨被网络技术遮盖的劳动过程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网络空间中被遮盖的劳动关系进行探讨。“劳动关系是在就业组织中由雇佣行为而产生的关系,它以研究与雇佣行为管理有关的问题为核心内容”。劳动关系的基本含义是劳资双方因利益需求而出现的冲突、合作及权利关系的总和,其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政策法规以及技术的制约。简而言之,劳动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依法确定的劳动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在网络空间中,由于网络媒介(相当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i奴”)之间没有形成明显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因而目前仍鲜有人关注他们之间的劳动关系。也就是说,网络媒介与“i奴”之间的劳动关系被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等因素遮盖着,致使人们长时间忽视了网络空间中作为劳动者的“i奴”与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网络空间中的劳动关系被遮盖了,就意味着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公司与作为劳动者的“i奴”之间没有明确的劳动关系,因而用户在网络空间中的劳动过程也就被遮盖了。
“i奴”在网络空间中的劳动过程为什么会被遮盖呢?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寻找原因:
(1)忽视了“i奴”对信息产品的生产
长期以来,人们集中关注现实社会中的实物产品的生产,较少关注网络空间中信息产品的生产,即使关注网络空间中的产品生产,也往往将之放在网络媒介的范畴下来考量,认为“i奴”只是消费者,而忽视了“i奴”的生产者角色和网络空间中的消费即生产等因素。也就是说,人们从传统消费者的角色出发,对“i奴”进行审视,因而容易忽视“i奴”参与网络空间中的产品生产的事实。这就使得“i奴”的劳动者角色长期受到忽略。事实上,“i奴”的信息生产和消费能生产出数量极为巨大的信息产品,为资本家创造出大量的价值。忽视了“i奴”对信息产品的生产,必然遮盖了“i奴”的劳动过程。
(2)劳资双方没有法律上的雇佣关系
绝大部分“i奴”的劳动都是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来进行的,除少数网络媒介专门雇佣并按时支付报酬的“i奴”外,其他“i奴”与网络媒介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也没有从自身的劳动中获得一分钱的经济报酬,而签订了劳动合同的“i奴”的劳动也往往被置于传统的劳资关系的视野之中进行研究。其实“‘闲暇活动’已成为与工作同样重要的一种社会活动”,这说明“i奴”利用闲暇时间不断地为网络媒介劳动。究其原因,“i奴”正是受到娱乐等动机的驱使而不分白天夜晚地在网络空间中进行着“冲动性的劳动”,给人“劳动致死”的感觉,并由此为网络媒介创造了大量的“闲暇经济”。
麦克切尔等人在描述好莱坞的劳工时曾说:“虽然好莱坞电影的制作需要数以百计乃至千计的媒体劳工的集体努力,但这一事实却往往因为大众媒体始终将其关注焦点集中于为数不多的明星演员和导演身上而被掩盖了”。网络空间中的劳资关系也如此,网络媒介以跟少数网络用户(OGC群体)签订雇佣合同的方式来遮盖与绝大多数网络用户(被剥削最深的“i奴”,主要包括PGC和UGC群体)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情况。因此,在工业生产的存在着劳动合同关系才存在劳资关系的惯性思维的作用下,与网络媒介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网络用户的信息生产和消费的劳动行为也同样被遮盖了。
(3)人们都将“i奴”的劳动界定在寻求娱乐的范畴之内
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i奴”的劳动完全是在娱乐、情感体验、信息利用等动机的驱动下进行的,因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不存在所谓的劳动行为。其实,“i奴”在信息利用、娱乐和情感体验的过程中,也在客观上为网络媒介生产了信息产品,不然“i奴”就不可能那么轻而易举地进入网络空间中进行情感体验等活动了。况且有一些“i奴”是本着完善人类知识的理念加入到百度百科等网络平台的信息劳动之中的。因此,即使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些动机,“i奴”也在客观上进行了劳动,他们与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也存在着劳动关系。更何况网络空间中的消费即为生产,“i奴”的信息点击、搜索等行动本身也为网络媒介生产可供记录的数字商品。网络空间中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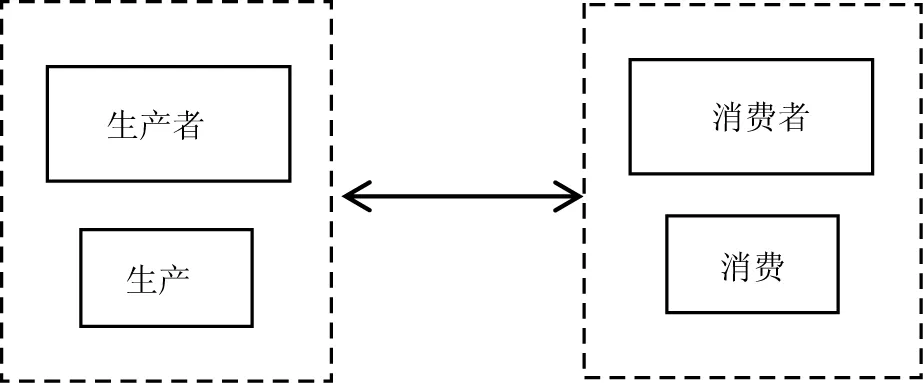
图1 网络空间中的信息生产与消费框架
图1说明,在网络空间中,生产与消费的界限已变得十分模糊,“i奴”在生产中进行着消费,而消费本身也是一种生产。
(4)“i奴”没将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用于交易
“i奴”为网络媒介生产了大量的产品,但他们没有把这些产品拿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易,原因是倘若“i奴”拿着自身生产的信息产品到市场上去交易,很难找到买主,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i奴”生产出来的商品都被网络媒介这个资方拿走了,网络媒介以组织的名义把搜集到的大量商品打包出售,广告商等商家才会感兴趣。这就使得“i奴”生产的产品绕过了生产者,直接在网络媒介和买家之间进行交易。这也是“i奴”劳动中的劳动关系被遮盖的一个重要原因。
(5)“i奴”的劳动往往是在免费的情况下进行的
免费进入网络媒介平台似乎为没有劳动关系的辩护起到一定的佐证作用。但“i奴”的劳动并不是没有成本的。表面上看来,“i奴”进入网络空间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但其劳动的成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商家转移到了其思想/物质信息,特别是商业信息上面。在网络空间中,思想商品和物质商品的混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经济信息与市场营销信息的整合更为彻底,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消费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作为劳动者的“i奴”在信息消费中也必然要付出时间、上网设备的磨损以及隐私被暴露等等一系列成本,很多人还会付出创意成本。因而免费可能变得越来越“贵”。尼葛洛庞帝的一句话道出了众多人的共同心声:“没有人很清楚地知道,在互联网上谁要付钱,为什么而付钱”。所以不应该被表面上可以免费进入网络平台传播和消费信息的现象所蒙蔽,忽视了“i奴”的劳动过程。
(6)网络媒介故意遮盖“i奴”的劳动过程
有个故事,说在古罗马时代,由于奴隶主的剥削、压制和侮辱,很多奴隶不堪忍受而纷纷逃跑。为防止奴隶的逃跑,一些奴隶主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在奴隶的脸上刻上记号,当奴隶逃跑时,可以及时辨认和抓捕。但有的奴隶主及时制止了这种“荒唐之举”,原因在于一旦刻上记号,奴隶们就能随时认清自己的身份,分辨出自己的朋友和敌人,这必将给奴隶主带来灾难。这与网络媒介一直把“i奴”称为“粉丝”,故意隐瞒“i奴”的劳动者身份,遮盖它们与“i奴”之间的劳动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处。网络媒介一旦承认“i奴”的劳动者身份,就要向“i奴”支付相应经济报酬,因而它们极力隐藏网络空间中的劳资关系,以有效地遮盖“i奴”的劳动过程。
(二)非经济报酬的强势崛起使“i奴”身不由己地投入到劳动中,“劳动致死”成为一种潮流
1.技术创新使人类生产和消费目的发生了转变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在这五个需求层次之中,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处于较低层次,属于生存需求;归属和爱、尊重的需求处于中间层次,属于社会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最高层次的需求,在这一层次,人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潜力,成为所期望之人物。需求层次越高,个性化越强,也越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状况。随着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人类的需求逐渐向高层次迈进,其是否进行劳动不再以经济报酬为唯一的依据。
技术对人类的生产和消费目的有着较大的影响。高兹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自动化能通过使人们的时间自由来丰富他们的生活,允许他们的活动和兴趣中心多样化”。随着技术的发展,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必然会越来越多,因为其用于劳动的必要劳动时间会逐渐减少。而随着自由时间的增加,人类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会不断地被激发出来,生产和消费的目的也会不断向高层次迈进。高兹认为科技的发展延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时间,扩展了交往的空间,实现了劳动手段、工具与科技的融合,让人们能自主而有效地利用劳动时间,加速了人类劳动解放的进程。我们知道,当人的劳动得以解放,他们就不再完全以生产某种产品、获取特定的经济报酬为目的而进行劳动,这就使得传统劳动时期的经济决定和支配社会关系的境况发生了变化,劳资双方不是必须形成法律上的劳动关系,不是非要有劳动强迫和经济报酬,而是形成一种“自愿合作”的社会关系,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商品关系的霸权,劳动者是在娱乐和自我需求的目的下进行生产和消费的。可以说,正是网络这一信息技术为人类社会关系的变迁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才使追求自我满足和享受的愿望得以实现。在新技术的赋权下,劳动成了一种享受,成了人们获得更符合人类发展目的的报酬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生产、消费目的发生了转变:由生存性的物质满足转到了享受型、发展型的意义的满足。而这种享受型、发展型的意义的满足就是一种非经济报酬。
技术使人类的劳动目的发生转变,在网络空间的劳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网络等新兴信息技术的作用下,人们不再一味追地求经济报酬,而是把重点放在了符号和意义的生产与消费方面。在互联网空间中,劳动已经成为一种享受,成为一种娱乐手段。当劳动时间更多地与愉悦、满足、激情、兴趣等隶属于目的和意义的活动的扩展相结合时,人类的生产与消费劳动就越来越解放。高兹认为,“让人的愉快体现在生产性劳动之中,劳动的节奏由带着歌舞的节日和庆典给出;劳动工具被漂亮地装饰……”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的生产与消费劳动逐渐摆脱直接强制的异化性,正向着快乐和幸福劳动的目标迈进。在网络技术这一新传播科技的赋权下,人们找到了一种“流行元素”来对劳动和生活进行整合,由此创造出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把文化、生活和劳动交融于一体。人们利用闲暇时间进入到网络空间,凭自己的爱好从事着网络信息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等劳动,这种劳动将人们从追求经济价值的囹圄中解脱出来,生产和消费着作为目的和意义的符号的产品。自此,人类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活动成了目的和意义的社会交换,交换的结果成为社会关系的测量或标志。
互联网和社会网络的充分融合,大大拓展了社会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朝着更为多向和立体的方向前进,由此将人类的社会关系需求及价值创造行为统一起来。人类的生产与消费目的由此发生了转向,由农业社会的吃穿问题、工业社会的住行问题,转向了意义的生产与消费。这是人类需求进入高层次阶段的体现。人们从网络空间中获得的高层次需求的满足与农业、工业社会以及信息时代的现实社会中高层次需求的满足不同,后三者的满足往往是单一的价值判断,如做官、成为富翁等等,这种满足看似层次较高,但往往较低层次的需求都还没有得到解决,如大量富人在财源滚进的同时充满焦虑。网络空间中目的和意义需求的满足是精神层面的满足,它符合人类全面发展的要求。
2.生产和消费目的的转变使“i奴”获得了大量的非经济报酬,“劳动致死”正成为一种潮流
报酬从来就不只是经济上的。在基本的生存和发展得到满足的今天,生产力越解放越体现出游戏、社交、娱乐等天性的重要性,人们正向更自由、更多精神享受的生产和消费目标迈进,满足人们更高层次需求——各种意义建构的非经济报酬成为人类报酬形式的新宠。这样一来,人类意义建构的动机便成为决定人的劳动行为的重大因素,人们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动机,围绕其组织生产,在社会生产中构建起一幅由各种个人动机组成的巨大的动机图景,依据这一图景就能发掘出若干非经济报酬形式,使得具有不同娱乐习惯、信息偏好与社会行为的人们在非经济报酬的巨大调色板上各取所需,创造出巨大价值。
这一理想的非经济报酬形态只有在网络中才能得以实现,因为网络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的信息动机、求知动机、自我发现动机、维持人际关系动机、社会提升动机以及娱乐动机,当这些动机得以满足时,资方也就像劳动者支付了相应的非经济报酬。毫无疑问,这些非经济报酬形式符合人类更高层次的需求,更符合人类全面发展的要求。不过,向人类更高层次的发展目标迈进的道路是极为曲折的,这个人类真正解放的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对之进行塑形。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研究传播的学者以及传播工作者(在中国的新闻界,有关“i奴”劳动和生存状况方面的报道和研究极为匮乏),需要站在这个斗争过程的中心,发挥中坚力量。
“i奴”在网络空间中能获得哪些非经济报酬呢?具体来说主要体现为与社会资本相关的非经济报酬和社会资本以外的非经济报酬。
(1)与社会资本相关的非经济报酬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它们与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认识与认知的持续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通过集体拥有的资本的支持提供给他的每一个成员”。按照这一界定,我们很容易发现一种突出的社会资本——特定的社会关系,它受到能够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的影响。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获取其他行动者所拥有的诸如权力、财富、声望以及人际关系网络等等一系列社会资本。通过在网络媒介提供的网络互动平台上的劳动,“i奴”能够获得各种社会资本,具体如下:
①社会关系维持、扩展与深化。莫斯可指出,传播是一种社会交换过程,交换的产品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标记或者体现。在互联网时代,社交网站将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形成的关系网络投射到网络空间中,并使现实社会中很难形成的“关系层”在网络中不断涌现,这就使得各种社会关系能够在网络空间中得以不断延续、扩展和加深,参与其中的“i奴”的社会关系不断得以维持、扩展与深化。
②社会声望得以提高。网络为“i奴”开启了一条成名之路,一批批草根人物通过网络创作成为知名的网络作家、网络歌手、网络编剧等等,获得社会的认可、受到粉丝的青睐,社会赞誉度、美誉度不断提高。美誉度和赞誉度就能获得社会地位,提升“i奴”的社会声望。
③在信息分享中获取乐趣。可以说,在任何时候,人类都充满分享的欲望。“i奴”往往拥有自己的闲暇时间,有丰富的知识,也有强烈的分享欲望。“i奴”的信息生产不只是个人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如“大笑猫”是“i奴”生成的,也是被“i奴”分享的,创造“大笑猫”是为了分享。“i奴”在分享中彼此获益。“i奴”正是在情感及知识等众多内容的分享中获得乐趣,进而获得非经济报酬的。
④家庭、宗亲关系得以维持和发展。在中国,家庭、宗亲关系被看成是极为重要的东西。这是人们至关重要的亲情的体现和延续,脱离家庭、宗亲关系的人必然会遭到社会的唾弃。网络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将“i奴”的家庭、宗亲关系在不同的时空中进行延展和加深,进而使“i奴”获得亲情这种非经济报酬。
(2)社会资本范畴外的非经济报酬
除了社会资本方面的报酬外,“i奴”还能在劳动中获得娱乐及情感体验、找到参与感和幸福感,以及求知和社交需求的满足等非经济报酬。
①找到参与感与归属感。寻找参与感是“i奴”从事网络劳动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网络媒介为“i奴”提供简洁自由的互动平台,能将“i奴”聚集起来,为“i奴”寻求参与感创造条件。“i奴”参与网络媒介的信息生产、消费和品牌建设等一系列活动,都可以视为互动,在互动中,要让“i奴”充分参与进来,和网络媒介打成一片,实现相互融合,否则就没有真正的参与感。
在劳动中,“i奴”也会追求一种归属感,因而会在网络上形成一个个的圈子,社交网站因为能将有共同爱好和诉求的“i奴”聚集起来,给他们圈子感而吸引着成千上万的“i奴”,给他们归属感。
②求知欲望得以满足。用知识进行补偿,这是很大的非经济报酬。“i奴”在劳动中能免费获得知识,如利用搜索引擎进行搜索可以获得想要的知识,与人互动能够增长见识等等。正如托马斯·杰弗逊的名言:点燃蜡烛照亮他人者,不会给自己带来黑暗;同样,传播思想,无损于思想的传播者。网络与生俱来的自由度使“i奴”在求知时找到了一种低成本甚至是零成本扩张的捷径,“i奴”可以在劳动中以较低的代价获取较多的知识。
③娱乐天性得以满足,情感体验得以进行。“i奴”利用闲暇时间进行娱乐,能够使自己的身心处于愉悦之中。有了娱乐的非经济报酬,“i奴”就会乐此不疲地劳动,而网络媒介也在为“i奴”提供娱乐的过程中获得巨额经济收益。暴雪娱乐的首席执行官麦克·莫汉曾说:“在暴雪,我们确实有一个使命——致力于创造史上最宏大的史诗般的娱乐体验”。娱乐能催生一种彼此共享的方式,这是娱乐最强大的功能,也是网络游戏让人如痴如醉的重要原因。“新信息技术已经对可能为娱乐和消遣活动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将继续产生影响”。使“i奴”欢呼雀跃的投入网络社会化大生产的,正是能为“i奴”带来众多娱乐、体验的网络技术。
总之,在网络技术的赋权下,“i奴”的劳动能获得大量的非经济报酬。在各种非经济报酬的诱惑下,“i奴”身不由己地投入到网络劳动中,这种大众狂欢的方式使“劳动致死”成为一种新的潮流。
需要指出的是,“i奴”获得的非经济报酬与现实社会中获得的经济报酬的界限不是截然分开的,“i奴”与网络媒介之间存在着特定的交易,“i奴”以自身的劳动换取网络媒介的社会资本,进而在必要的时候将这些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如网络游戏获得的虚拟装备可以卖给有需要的人,使玩家获得经济报酬。
四、结论
“i奴”已成为网络空间中的劳动者,他们不分时间、地点地为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公司劳动着。在劳动中,“i奴”很难获得经济报酬,然而他们仍然疯狂地、心甘情愿地劳动着。为了还原“i奴”真实劳动者的身份,一些专家呼吁给予“i奴”相应的经济报酬,并呼吁“i奴”这群劳动者的觉醒,不要再一味的作为网络媒介公司劳动的低头族。可以说废“i奴”之声此起彼伏,但“i奴”这群劳动者依然没有觉醒(或者觉醒了也没有理睬学者们的呼吁),依然兴致勃勃地做“i奴”。就其主要原因来说,首先是在网络技术的赋权之下,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公司能够巧妙地将“i奴”的劳动过程遮盖起来,使社会忽视了“i奴”这群劳动者;其次是“i奴”在劳动中能够获得相应的非经济报酬,有的“i奴”甚至能获得少量的经济报酬,或者能够将非经济报酬转变为经济报酬。正因为如此,废除“i奴”就成了一种呼吁,很难达到真正的目的。
注释:
① [美]丹·席勒:《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王维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②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徐坚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4页。
③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I)》,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页。
④ Maxs.“ResultsoftheImmediat.ProcessofProduction”,p.1048.
⑤⑥⑦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36、42页。
⑧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