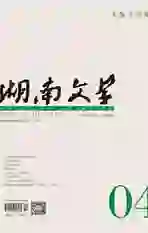打分手
2018-05-31李子胜
李子胜
一
在王小军的记忆里,盐工宿舍的那些大人们上夜班,手电筒是他们必不可少的装备。出发前提溜在手里,显得要多神气有多神气,吧嗒一推,开关开了,通向工区的小路,本来漆黑一团,又漫长难走,手电筒一开,顿时被雪白的光束照亮。光线从手电筒圆圆的柱头里射出来,就像拖着一道长尾巴的大扫把,顺着土路大摇大摆地扫射遍全程。
盐工们上班的工区都靠近海边,远离居住地,就算是顺风骑车,也还得花费一个小时。百里滩被晒盐的大汪子填满了,大汪子类似农田,可是比田亩辽阔得多,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水汪子横七竖八地分布着,堤埝蜿蜒崎岖,行夜路,很容易从堤埝上掉进黏冷的卤水里。有一次,王小军和小伙伴们在暑假里去海边大汪子钓鱼,那天的海鲇鱼出奇地多,不停地咬钩,王小军他们贪图多钓点鱼,回家晚了,装满海鲇鱼的大篮子挎在车把上,骑车时大篮子撞腿,车把就开始晃悠,好不容易走到一半路程时,天就黑透了,一个叫大力的小伙伴将自行车骑进了路边的淤泥里,人栽倒不说,钓的鱼也都甩进了盐沟,掉进盐沟的鱼摸不到几条了,冤得大力趴在地上哇哇大哭。
就在这时,王小军看到支着手电筒骑行在夜路上的盐工们就像一只只巨大的萤火虫,从城市一端蜿蜒飘忽而来,让他觉得那些悠闲骑车的盐工们无比神奇、神气。特别是邻居大红海骑过来时,他的手电筒贼亮贼亮的,刺得王小军眼睛酸疼。
对手电筒,王小军并不陌生,手电筒通常都是可以放四节一号电池的,电池耐久,手电筒的光柱坚硬有力,盐工夜间骑车时,光柱从两腿之间射出,随着路的颠簸抖动着,像一种无法言说的神奇武器。
王小军还发现,大红海骑车的轨迹比其他的盐工要复杂,因为他总是醉醺醺的,包括他的破水管自行车,也总是像个醉得晕头转向的酒鬼,平衡不稳。大红海与王小军家住邻居,他身上永远散发着两种味道,鱼腥味和酒味。他身上总是粘着一些干巴巴的鱼鳞,阳光下能发光,亮闪闪的,好像这些鳞片是镶嵌在他衣服上的饰品,衣兜里总会藏着一瓶白酒,走着走着骑着骑着就会突然掏出来举在太阳光下咕嘟咕嘟喝两大口,好像阳光是随时可以伴着下酒的菜肴。大红海家,到了夏天会听到一种嗡嗡的轰鸣声,那是落在大红海用的各种腥臭的渔网上的大绿豆蝇快乐大合唱的声音。这些声音总是让王小军的注意力离开暑假作业,他的心也嗡嗡地飞起来了。大红海家是王小军心里的神秘之所。
本来王小军家与大红海家不是邻居,前年深秋王小军家的邻居升官了,单位给调换了房子,大红海就成了王小军家的新邻居了,同时住进去的还有那些肥硕的大苍蝇们。從那时起,王小军家总能闻到隔壁院子里冒出来的香喷喷的炖鱼味,还有混杂在鱼香味中的酒味。
王小军的爸爸闻到这些味道后,总会对着高大的院墙仰望长叹,然后独自喝闷酒,喝多了就看家里人谁都不顺眼,指桑骂槐唠叨不停。这样的夜晚让王小军感到痛苦压抑。大红海就一个人住,为什么总把自己家的晚饭搞得那么香,这让王小军很好奇。院墙很高,这是以前的邻居和王小军的爸爸因为一只母鸡的归属吵架后赌气加高的,高得像山一样。王小军没见过山,只看到过盐坨,他和小伙伴们把盐坨叫做盐山,记得小学语文课本里有山这个字,老师也讲过,他琢磨,山不过就是比这堵墙高一点吧。
在一个炎热沉闷让人恹恹欲睡的午后,大红海家锁了门,王小军喊着大力壮着胆子翻过大红海家的院墙,想看看他家究竟有多少只苍蝇。他看到的场景大大出乎意料。一跳进院子,苍蝇毫不眼生地奔袭过来,猛撞他俩的脸,每被撞一下,王小军就一阵恶心。大力沮丧地说,这些苍蝇肯定把他的脸当茅房坑了,它们每撞一下,一定在他脸上解大便了。后来,王小军仔细观察大力的脸,他脸上果然有很多雀斑呢,这些雀斑与王小军家屋顶斑斑点点的苍蝇屎没啥区别的。
适应了苍蝇的围攻,王小军看到黑压压密匝匝的苍蝇落满了挂在墙上的渔网,无论是箔网还是旋网拉网麻虾网,厚厚地落满了一层,苍蝇被惊扰腾身飞起后,王小军才看出那些网边原来是白颜色的。靠屋门的窗台上,摆了一只大海碗,海碗接了半碗雨水,暗黄的水里面也落满了死苍蝇,苍蝇的尸体绿莹莹黑灿灿的,像盛了半碗绿豆和黑豆。这难忘的一幕让王小军干哕了一天。他才明白了他听到的苍蝇的轰鸣声为什么那么巨大。打那以后他再看到大红海时,马上联想到一只巨大的苍蝇的巢穴,好像苍蝇就在大红海身体里藏着,随时要钻出他的鼻孔,想到此,王小军禁不住喉咙里发痒发潮,被一股强烈的恶心感占据。
从那个夜晚见识了盐工们手电筒的神奇魅力后,手电筒也成了王小军与小伙伴们最奢侈的玩具,他们觉得以前迷恋玩泥巴简直就是冒傻气。他们趁大人不在家时,偷出手电筒,在黑魆魆的胡同里互相照对方,跑到飞舞着密密麻麻水蝇子的盐沟边,挥着手电筒的光柱,像挥舞一把砍刀。大人们发现手电筒没装几天的电池竟然很快没电了,王小军他们免不了得挨各自家长的一顿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忍不住把手电筒偷出来玩。王小军还找了一个残留着酒味的玻璃瓶,揣在怀里,模仿大红海喝酒的样子,也咕嘟几口自来水,其他孩子会抢着也喝两口,仿佛自来水装进玻璃瓶子,就变成美味了。
王小军的爸爸就着刚出锅的熬鱼,一边挥手轰赶苍蝇,一边对王小军的妈妈感慨,他说,我算服气了,大红海是不折不扣的鱼鹰子、老鱼王。王小军知道,他爸爸很笨,胆子也小,不会打鱼摸虾,可是嘴还特别馋,最喜欢就着新出锅的鱼喝酒。王小军知道,那些盐工大人们好多都爱喝酒,他们爱打鱼摸虾,就是为家里省点菜钱,为自己多捞点喝酒的理由,鱼虾也是他们眼里最好的酒肴。大力和二锁的爸爸,不也总是满身酒气吗。
爸爸一夸大红海,王小军就知道,家里吃的海鱼八成是大红海送的。王小军的爸爸继续慨叹,这个大红海啊,无论是潮涨潮落的大海沟,还是混养汪子,还是汪子周围的上水沟下水沟还是农田之间的小河沟,海水鱼淡水鱼都逃不过他的渔网。这家伙,嘿,神了。之后,爸爸就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脸上挂着干鼻涕的王小军,好像在打王小军的坏主意。爸爸说,王小军,你咋长得这么慢呢,养你十五年了,你咋刚比水缸高呢。王小军被爸爸的眼神和话语搞得浑身不自在,他哆嗦了一下身子,抗议说,大红海多邋遢啊,看着他我就想哕。
你个小屁孩知道啥,人家大红海会治鱼,吃喝不愁,你和大力二锁他们好好学学人家,别整天瞎淘。你们那破学校上个啥劲儿,老师都是盐工出身。这些话爸爸是撇着嘴说出来的。
王小军也一撇嘴,还击说你是大人,你咋不学?
爸爸突然默不作声了,妈妈在一旁帮腔说,小军,你知道啥,你爸爸一蹚水就犯迷糊,你爸爸一头栽水里淹死咋办?
王小军的爸爸听到淹死这个词,很恼火地把酒杯重重地放在饭桌上,酒杯里的一串酒滴受到惊吓一般蹿到杯沿,险些鱼跃而出。
妈妈得意地冲王小军笑着吐吐舌头,溜到锅台那边去了。
王小军的爸爸只会举着鱼竿在他家附近的一条长满芦苇的水沟里钓几条草腥味的小鲫瓜子。盐工宿舍东面一条水沟芦苇丛生,沟水油绿,鲫鱼很多。但是盐工们一般不喜欢那里的鱼,因为沟的最北端,有个公共厕所,盐工们和盐工家属的大小便就屙在这个厕所里,尽管有掏粪车拉走大粪,但是尿液难免流进沟里。每次闻到大红海家飘来的浓郁的熬海鱼的香味,他爸爸就会丢下筷子,叫王小军给大红海家送点他钓的小鲫鱼,结果呢,大红海不仅不要小鲫鱼,还会让王小军端回来一大盘子大个头的海鱼,这些海鱼香喷喷肉乎乎,都是大鱼切块熬熟的,与骨瘦如柴的甚至被王小军怀疑有淡淡尿臊味的小鲫瓜子真是云泥之别。偶尔几次,大红海不仅让王小军端鱼回来,还让王小军喊他爸爸去他家喝酒。王小军的爸爸一听就跟听到升迁的圣旨一样,兴高采烈,一秒也不耽误地飞出家门。等他喝完酒挺着大肚子回来,满嘴胡话和酒气,让昏睡的王小军觉得发出声响的爸爸简直就是忘了盖盖子的酒缸沿上摆的一个打开的小电匣子。
因为爸爸的这些可耻的行为,王小军在小伙伴中一直抬不起头。
二
王小军对爸爸拽着他去大红海家哀求大红海收自己为徒的事情一直心怀不满。
王小军的爸爸明确告诉王小军必须跟着大红海学习打鱼摸虾后,王小军知道拗不过家长,忍痛与几个铁哥们——王小军十五岁时,他觉得他们不再是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了,他们成了他可以诉说心事的铁哥们——在盐工宿舍东边长满芦苇的小河边话别后,王小军对他爸爸的鄙视如盐碱滩上的碱蓬沐浴了雨水与骄阳,旺盛生长着。
王小军的爸爸拽死狗一样把王小军拽进大红海家。收徒仪式很简单,就是给大红海磕了三个响头,喊了一声师父。
大红海没有儿子,但是他非常喜欢男孩子,他老婆为他生下三个女儿后不久,受不了他又是酒气又是腥气借酒撒疯骂人,带着女儿们跑回河北老家了,从此音讯皆无,大红海喝醉了想起此事,会蹦起来骂老婆是个千人骑万人跨的老骚货,跑了更省心。
本来就喜欢男孩的大红海对突然冒出来的徒弟显然又欢喜又措手不及,他接受了王小军的叩头后,沙沙作响地搓着大手,在堂屋溜达了几个来回,走进卧室,一阵翻找东西的窸窣声后,举出一瓶酒,塞给王小军。王小军定睛一看,酒瓶上竟然有标签,标签上有三个大字:老白干。那个年代,老白干酒虽然不贵,但是盐工们谁也舍不得买。王小军不解师父的意思,王小军的爸爸看王小军愣神,赶紧接过酒,抓牢了,嘴角咧到了腮帮子,脸上笑开了花,连声说,好酒好酒啊,等咱们的小军长大了喝。
拜师仪式后,王小军每天很不情愿地憋着呼吸出入大红海家,时间久了,臭烘烘的气味和撞脸的苍蝇也就习以为常了,再加上大红海隔三岔五塞给他一两块零花钱,他实在抗拒不了用这些零花钱买来五香花生仁与大力二锁分享时,他俩为了多吃几粒花生米争抢着讨好他的快乐。
大红海的家就是个渔具展览会,什么渔具都有,什么箔网拉网旋网粘网棍网罾网泼网提网赶网麻虾网,啥都有,你们信不?王小军对铁哥们吹嘘着,他希望看到哥们眼馋的神情,这种神情很能给他安慰,好在哥儿们每次都不让他失望,他们羡慕的眼神在王小军话语结束后闪现的速度与比按下水缸的葫芦水舀子浮起的速度还快。
拜师一个月后王小军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血网。
大红海把一盆新鲜的猪血兑上水,把一团乱糟糟的棉线泡进去,猪血的殷红在棉线上浸开,浸泡半天后,大红海又让王小军在院子里烧火,把沾了猪血的棉线团放在蒸锅里蒸,热气冒上来时,一股怪味直钻鼻子。蒸了片刻,就把棉线团捞出来,用竹竿挑着,搭在晾衣绳上。
大红海指挥着王小军,把冒着热气的棉线团抻开,王小军就看到了细密的网眼上,像眼睛挂着泪珠一样带着血水。血水滴滴答答砸在地上,苍蝇们兴奋地包围过来,嘤嘤嗡嗡挤满了棉线网。
当天,一股奇臭味道由淡变浓弥漫开来,王小军被熏得晚饭都吃不下了,他对爸爸让他拜师的不满正好借题发挥,趁着恶心赌气少吃一顿饭。
血网晾干了,收拾渔网时大红海很得意地告訴王小军,这种棉线网是专门拉麻虾的,用几次就得用猪血浸一次,这叫血网,其他盐工都不咋会血网。
多年以后从日本进口的聚乙烯网线替代棉网线,血网的味道才从大红海家消失。
第一次和大红海去插箔,王小军还是很兴奋的。
季节已是初冬了,扒盐季节结束了,盐工们开始歇冬三月,王小军上学的盐工子弟学校经常停课搞游行,王小军干脆也不去学校了。
海边一个叫土桥子的渔村派人来请大红海,告诉他去一号混养汪子打分手。大红海找到正和伙伴们玩骑驴游戏的王小军,师徒俩驮着胶皮裤、气搋子、汽车内胎等物什出发了,王小军就坐在大铁筐里,用手死死抓住筐沿。大水管车子很慢,在铺着蛤蜊皮的小路上沙沙前进,钻进鼻孔的风开始变卤变腥。
王小军觉得自己就是一条大鱼,被网获到了鱼筐里,估计是逃不掉了。对这次外出捕鱼,他心里面又抗拒又期待,他不喜欢远离铁哥们,又对陌生的野外捕鱼有很大的好奇。
鱼筐很大,王小军蜷缩着坐在里面不觉得挤得慌。大红海一边奋力蹬着车子一边回头和王小军说话,他用讨好的口气说,小军,咱这个大水管自行车,经过改造过,你看看,后椅架加高了半尺,这样挎上铁筐就可以离地皮儿半尺高,这里面有些窍门儿——打鱼摸虾走的是泥浆浆的黏土堤埝、蛤蜊皮小路。下了雨,泥浆会粘在车圈上,人只能侧身推着自行车,铁筐距离地面矬了,很容易刮地。蛤蜊皮也经常把车胎刮破,瘪了胎的车子,矮了两寸,铁筐底儿也不至于刮地。咱们出来打鱼,就怕车坏了。你看这两个大铁筐上的挂钩,不是焊接在筐沿儿,是焊接在低于筐口半尺处,这样,咱们的铁筐筐身就比别人的长了一尺。别小瞧这多出的一尺筐身,能多装一二百斤鱼获呐。每次去插箔,旋网拉网、大棉猴、黑狗皮褥子啥的就能装半筐。老百姓说,身大力不亏,你看咱的大筐,多有劲。
快到海边了,路两边都是浩渺无边的水光。大红海把车子靠在汪子边一个苇箔苫盖的窝铺上时,王小军两条麻木的腿才伸直了,站在了生长着已经泛红的黄须菜的堤埝上。狂野的海风把苇箔掀起,苇箔又被身上的麻绳拽住趴下,苇箔呼哒呼哒响。四野无人,只有几个窝铺懒洋洋的流浪狗一样卧在遥远的堤埝上。大红海把铁筐里胶皮裤扔在地上,把其他的东西搬到窝铺里,大红海对王小军说,小军你在窝铺里看着东西,我下水插箔。
王小军钻进满是尘土气味的窝铺,风被关在了外面,苇箔的呼哒声却更大了。窝铺里幽暗空荡,只有一个木板床架子,上面有片破凉席,凉席破碎,落满了黄土。太阳光从窝铺透亮处穿刺进来,道道光剑中,尘土如新生的夏虫一样,在欢快地翻飞着。
王小军钻出窝铺,发现大红海已经不在堤埝上,他四处踅摸,看到穿好胶皮裤的大红海已经拖着一卷苇箔下水了。王小军这才注意到,堤埝上有一捆捆卷成圆筒的芦苇箔。
王小军在堤埝上百无聊赖,看着大红海在水里忙活,那些苇箔被他插在水里,插成了一排墙,墙的尽头则插成了喇叭筒。王小军觉得很可笑,鱼虾就这样捕捞吗,它们怎么肯乖乖地钻进去呢。
太阳斜斜地到头顶了,大红海上了大埝,皮叉裤淌着水,走路胡噜胡噜响。大红海面色青紫,嘴唇微微打着哆嗦,看起来被冻坏了。他麻利地脱下叉裤,招呼傻看着自己的王小军钻进窝铺。大红海一屁股坐在床板上,从怀里摸出酒瓶,咕咕嘟嘟喝了几口,哈出一串白气。他把酒瓶递给王小军,王小军接过来,以为是让他把酒瓶放好,王小军低头找放酒瓶的地方时,大红海说,傻小子,让你喝一口。王小军迟疑地举着酒瓶,看着酒瓶透明液体里一些来自大红海口中的食物残渣,有点不敢张口。喝吧,咱们打鱼人,风里浪里的,没有酒可不行。王小军不再迟疑,嘴唇找到瓶口,屏住呼吸,喝了一大口。火辣辣的白酒吞下喉咙,留下了一条烫伤一样的疼痛,直通肠胃。
一口酒喝下去,尽管没什么享受感,王小军却觉得自己像是个大人了。
王小军问,师父,这些苇箔就能把鱼虾治上来吗。大红海说,这么大的汪子,捕鱼捞虾,最好的手段就是插箔,到了深秋和初冬,鱼虾潜在水下不爱动弹,只有插箔才能把它们治干净。天冷了突然赶上搅天,刮大西北风了,很多海边渔村生产队的大汪子里还有上万斤的鱼虾没治上来,大队就派人找我,帮我和工区请假,让我帮忙去插箔。刮西北风,大汪子里的虾钱儿会扎泥,虾钱儿扎了泥,就无法捕捞了,所以得抓紧时间把残余的虾钱儿用箔网治干净。按咱们百里滩的规矩,插箔前三天的鱼获归渔业大队,第四天起,再从箔网里捞的鱼虾,就归咱们插箔人。从箔里捞的鱼虾,都有插箔人的分成,这就叫“打分手”。
王小军问,那第四天要是没有鱼了咋办。大红海笑笑,放心吧,傻小子,第四天你就瞧好吧。
在窝铺里简单吃了干粮,大红海在床板上铺开一张黑狗皮,让王小军打个瞌睡。躺下不久,王小军就听到窝铺外面有了热闹的说话声。钻出窝铺,王小军看到来了几个人,围着大红海嘻嘻哈哈说话呢。这几个人也都穿着胶皮叉裤,举着长柄大捞拎,看来他们马上要下水了;再看堤埝下面,有一条木船停在水边,这些人似乎是划着船过来的。果然,他们开始往堤埝下挪动,大红海走在前面,率先下了水,几个人尾随着,推着船,向第一道箔靠近。汪子里的水浪撞擊着他们,飞溅起来的水花不断开落。王小军跳下堤埝,在水边焦急地走动,恨不能也趟水追随他们,他的鞋很快就被淤泥吸住,他赶紧扭身拔动双脚,立在硬土地上,水边留下了两个深深的脚印,脚印很快被风吹动的水浪浸泡冲刷变了形。远处几个人已经到了苇箔尽头,他们挥舞着捞拎。捞拎轻飘飘插进箔网里,然后捞拎竿再举起时却变弯曲了,奋力之下,捞拎出了水面,捞拎网兜里已经满是白白的鱼鳞闪耀。他们把鱼倒入船舱,继续捞鱼,有几条鱼飞了起来,跳出了箔网,水面上顿时一片水花开放。
等他们捞完了大红海插的三道箔网,把船推向岸边,王小军看到船上鱼已经起了尖,最上面的鱼还在挣扎着弹动身子。
一辆拖拉机把一车鱼拉走时,已经是日头偏西了。大红海再次下水,捞了两个苇箔,鱼就装满了一麻袋。大红海推着水管车子,王小军一手打着手电跟在屁股后头,一手帮大红海推车。两个大铁筐里有百十斤鱼,加上叉裤等物什,已经满满的了,在坑洼不平的大埝上,推起来很费力。手电筒的光束在他们脚下摇晃跳跃着。
大红海和王小军快到家时,都累得精疲力竭。快到盐工宿舍时王小军曾经试着推一会儿车子,谁知他刚抓到车把,水管车子就跟一匹烈马似的站立起身子,王小军拧着车把,车子晃晃悠悠就要立起身子,大红海赶紧帮王小军压住前轮,车子才老实了一些。大红海刚一撒手,车子的前轮就又离开了地面。逗得大红海哈哈大笑。
他们经过盐工宿舍的人们的视野时,歪斜的车子和他们奋力推车的样子还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大水管车子被推进院子后,王小军的爸爸得意洋洋地领着大力二锁的爸爸都尾随进来了。
红海,今天货不少吧。大力的爸爸问。
有港梭鱼吧,河刀海鲙港梭鱼啊。王小军的爸爸说。
大红海笑笑,招呼着大家,说,有货有货,给我徒弟小军分点,还有几十条二丁。王小军也是刚从师父口中知道,梭鱼的大小论“丁”,“一丁”就是一尺长,“二丁”就是二尺长。师父捞的都是一丁二丁的大梭鱼,小的根本不要。
卖吗,卖给我们几条吧。
卖啥,对门间壁的,磕碜我啊,想吃就抓两条回家熬去。
大力二锁的爸爸听了大红海这句话,凑近了铁筐,眼神刀一样地往铁筐里剜。大红海把鱼倒在院子里,他先拨拉出了一半,对王小军说,小军这是你家的,回家取家伙什装鱼。王小军有点迟疑,自己连水都没下,基本没做啥,大红海怎么舍得分一半鱼给自己这个小屁孩呢。他嗫嚅道,我家有两条就够了。
王小军的话还没说完,他爸爸就拉着王小军的手冲出了院子,等王小军和他爸爸举着大木盆兴冲冲跑来,大红海那堆鱼只剩下七八条了。与留给小军家的那堆鱼比,大红海剩下的鱼少得让人心疼。王小军想把属于自家的鱼分一些给大红海,王小军的爸爸拉住王小军的胳臂,高声说,红海,晚上去我家吃吧,咱们馇一缸梭鱼酱,两家伙着吃。这么大的港梭鱼,馇酱最好了,你看我治鱼外行,可馇鱼拿手。大红海很高兴,说,兄弟,那把鱼都弄走吧,明天我和小军接着捞箔,鱼肯定吃不完地吃。
王小军的爸爸把所有的鱼都弄回家,王小军的爸爸妈妈大红海都围着鱼堆,刮鱼鳞,掏鱼肠。大红海说,这种港梭鱼进了箔网后,会惊慌失措往水面上跳,蹦跳一次就会拉泡屎,几泡屎就把肠道清理干净了,百里滩人有句话,港梭鱼——净肠的。港梭鱼的鱼肠去了苦胆,与鱼肉一起炖,油汪汪的比鱼肉还好吃呢。
王小军的爸爸突然想起什么,挑出几条鱼,装在搪瓷盆里,说,小军,去给你班主任送去,以后再耽误课,班主任找上门咋办。
王小军硬着头皮来到了前排,敲开了班主任刘老师的家门,刘老师乐得搔着王小军头发说,没看出你这孩子还挺懂事,我最爱吃港梭鱼,老话说,梭鱼头是香油罐啊。
那个晚上,酒香与鱼香把大力二锁的爸爸都招来了,后来又陆续来了几个住前后排的大人,黑压压围了一桌子。王小军记忆里,这是个美好的夜晚。满院子满胡同浮动的醇厚沉重的鱼香酒气虽然看不到摸不着,却又那么浓烈、清晰、真切,就像某位很少走动却突然一天来访的阔亲戚,给家里带来了值得炫耀的幸福气息。在饭桌边,王小军只要轻轻翕动一下鼻孔,香气就让他满足得陶醉。想到其他几个铁哥们家也都吃了鱼,大家的幸福感觉雷同又实在,王小军觉得打鱼也很有乐趣啊。
到了深夜时分,大红海与爸爸喝成了多年不见的挚友,言语热乎温暖,王小军的妈妈不住地笑,让王小军心情更加激动。
三
捞箔的第四天,王小军格外兴奋,因为从今天开始,捞箔的鱼都归师父和他了,而且师父说,今晚必须住在窝铺里。能在野外过夜,王小军激动无比。 王小军第一个愿望就是多卖鱼,好买一只手电筒,要与师父用的一样大的,插四节电池的。
他们推着一辆木排子车在早晨天不亮时上路了。师父推着车,王小军跟在后面,走得很慢,车上装了好多东西,也不知什么,被一张破棉被盖着。王小军想象着车上装满了鱼的情景,心里却满怀希望,未来几天的经历,又可以对那几个哥们儿吹嘘一番了,以后,自己的腰杆儿会越来越硬。
天光大亮时他们大汗淋漓地来到了窝铺。放好东西站定了,北风嗖嗖地钻进被汗水打湿的衣服里,冰凉冰凉的。大红海喊小军赶紧进窝铺,他则到四下踅摸了一些干草破木板,在窝铺门口点燃了一丛篝火后,喊王小军出来烤火。枯草噼噼啪啪燃烧着,枯木头变得火红,透明的火苗半人多高,随着风势乱舞,像游行队伍里舞动的红绸子一样。不一会儿,王小军觉得身上热烘烘,舒服多了。师父把残火聚拢,把铁筐架在火上,摆上了两个大馒头,几条咸鱼,接着开始把一个汽车内胎搋足气,穿上皮叉裤,举起白蜡杆的捞拎,准备下水。
师父,我也想下水,王小军说。看到师父全副武装的样子,王小军好生羡慕。
你别急,我下去捞一次看看,你先把咱们带的冷馒头烤了,一会儿我上来咱爷俩一起吃。
王小军点点头,看着大红海高大的背影下了堤埝,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温暖,苍蝇群舞的嗡嗡声也在心里远去了,他突然对这位师父有了亲切感。
王小军盯着馒头咸鱼,时不时瞟一眼水里师父的身影。他看到大红海只捞了一个箔就往岸上走了,没有了小船,他推着浮在水面上的轮胎,好像有什么东西隆起在轮胎中央。不多时,师父提着了沉甸甸水淋淋的蛇皮袋子吭哧吭哧走过来,身上的皮叉裤沾了水,摩擦出奇怪的声响,像爸爸总钓鱼的那条河沟里芦苇丛中的老蛤蟆在有气无力地叫唤。
水里肯定冰冷,师父的嘴唇都青紫了,师父丢下袋子,扒下叉裤,从怀里掏出一个扁扁的酒瓶,仰脖子灌了两口,嘴里咕哝着什么。
馒头咸鱼都烤好了,香味招来了更强劲的风,风裹挟了香味跑远了。王小军重新添了一些柴草,让奄奄一息的火苗再次复活,得了后援柴草支持的余烬瞬间活泼起来,师父贴着腾身而起的火苗,烤着前胸后背。
四野空旷,水光接天,破碎的阳光在水面上汹涌着,一个人影也没有。
水凉啊,鱼不咋爱动弹,箔里鱼不多,中午暖和了就好了。好像怕王小军失望,大红海语气里带着安慰。王小军心头一凉,低头看地上湿淋淋的袋子,袋子口露出了几条鱼,鱼中间还冒出几根暗红的虾须子。
这些鱼虾够咱爷俩吃的。大红海说。
王小军疑惑地四下瞅瞅,不知道这些鱼在野地里怎么变熟,难道也在火上烤吗。
吃完馒头,大红海招呼王小军卸车。撩开破棉被,是一口扣放车上的巨大的锈铁锅,一把掘锨,一盘麻绳,两卷破苇席,两个大棉猴,一个装满水的白塑料桶,还有一个装着盆碗油瓶等物的柳条筐。搬下铁锅,铁锅下面藏着的还是那张黑狗皮褥子,褥子打成了卷,手电筒的脑袋瓜伸在外面。最让王小军欣喜的是他看到了一条叉裤。他估摸这是师父给他带的,他没穿过叉裤,很想马上试试。
大红海抓起掘锨,在窝铺的下风头堤埝上开始挖土,不一会儿就挖出一个深坑,大红海把铁锅坐上去,又搬下来,反复几次,铁锅坐稳了。王小军很懂事地提著一把砍刀四下拾柴火,堤埝两侧,有很多干枯的碱蓬和一人多高的鬼柳。
王小军抱着一大抱柴草回来时,大红海已经把铁锅刷干净,铁锅里整齐地挤放着那个袋子里的鱼虾。师父攥了一丛草从刚才的火堆里引着,然后塞进锅底的土坑里,火苗冒起来后,继续添鬼柳枝条,火苗很快添遍了整个锅底。堤埝上散起了好闻的烟火气息。
一个小时后,铁锅热气腾腾,水泡翻滚,鱼虾在水泡推动下颤抖着身子,汤面上飘着一层油,香味诱人。
以前,王小军只是和小伙伴在野地里煮过鸟蛋,烧过蚂蚱、青蛙,从没体验过这种正规的野炊,他兴奋地期待师父发令,好甩开腮帮子品尝鱼虾。
尽情品尝鱼虾,捞箔的鱼获还能卖钱,还没有爸爸的呵斥,王小军突然觉得此刻幸福无比,这种幸福来得太快了,让他很担心自己在做一个随时会被惊醒的美梦。想到此,他忍不住四下观瞧,视野里没有人影,只有风吹得不断摇摆的丛丛枯草。
师徒俩围着铁锅吃饱了午饭,太阳斜斜地到了头顶,大红海把另外一条叉裤提了起来,平铺在地上,让王小军试穿。
叉裤很肥大,王小军钻进去,叉裤到了他脖子的高度,只露出头来,大红海笑着用绳子把叉裤裤腰捆绑了一下,让王小军在堤埝上试着走动,开始,王小军像一只小笨熊一样踉跄,来回走了几圈,脚步就稳当了。
下了水,师父在前面推着滚圆的轮胎,让王小军抓着捞拎木把,牵小狗一样拽着王小军,蹚向第一个箔网头。大汪子的水底坡度很缓很坚实,水一直齐腰深,王小军心不再慌张了。他松了捞拎把,与师父并肩走,帮师父推着飘在水面上的大轮胎。
走到第一个箔网头时,咸水的冰冷已经渗透了叉裤,侵入王小军的骨头,手冻得僵硬粗大,两腿也有点不听话了。站定了,师父用捞拎竿磕打着箔网外沿,然后才举起捞拎插入箔网里,捞拎在水下画了一个圆圈,猛地托出水面,捞拎网兜里竟然满满地都是鳞光闪闪的鱼。
王小军帮师父把鱼装进袋子,把袋子口系紧,放在轮胎中间绳网上,此时的轮胎就是一只小船了。捞完两个箔网,轮胎被鱼压得快沉没了,大红海招呼王小军上岸,此时,师徒俩都冷得嘴唇发青,牙齿打颤。
到了水边,师父背着装鱼的袋子,王小军在下面托着袋子,奋力爬上了堤埝,赶忙脱下冰冷僵硬的叉裤,大红海掏出小酒瓶,自己灌了一大口,又把酒瓶塞给王小军,王小军也学着师父的样子,猛灌了口酒,热辣辣的酒液流过了喉咙,嘴里又热又麻。
下午,师徒俩把其他箔网都捞了一遍,鱼获堆了一排子车,大红海把大虾和几十条大鱼拣出来,放到盆子里说,小军,你看着东西,我去把鱼卖了。你爸爸下午要是来找咱们,就把这些鱼虾给他带回去。王小军乖巧地点点头,看着师父推着排子车高一脚矮一脚在堤埝上远去了。
王小军张望了一下午,他爸爸的影子也没出现,太阳西斜时,师父回来了,排子车上有一捆破木板和一些大盐粒子。大红海塞给王小军十元钱,说,收好了,自己留着花,别让你爸爸知道喽。
傍晚,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由远而近,竟然真是王小军的爸爸。王小军有点高兴,原来爸爸也很惦记他。王小军的爸爸看到了大红海和王小军,用力挥手。到了卧铺跟前,放下自行车,王小军的爸爸很自豪地说,我没绕远,直接就找到你们爷俩了。看,我给你们带来了小虾皮白菜馅的大包子,还温乎呢,赶紧吃了。大红海咧着嘴乐,接过破棉袄包裹的饭盆,钻进了卧铺。王小军的爸爸凑到王小军旁边,耳语道,今天咋样,鱼多吗?有虾吗?
多。王小军自豪地说,师父下午用车推到渔村,都卖了。
你跟去了吗?爸爸急切地问。
没,我看窝铺。
呸!爸爸啐了一口,扭身钻进了窝铺。
爸爸离去时,带走了一大兜子鱼。
寒冷寂静的黑夜来临了。
黑夜让一切都有了陌生感,无论是熟悉的景物还是熟悉的人,在浓厚的夜色里都隐匿,阴暗,半遮半掩,蒙上了一层陌生的漆黑。
大红海说,半夜睡觉听到啥声音也别管,安心睡着。王小军顿觉惊恐,咦了一声,问,半夜三更谁会来这里,闹鬼吗?师父摇头笑笑,不是鬼,是人,来的人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们辛辛苦苦来偷箔,随他们来吧。王小军低头想了想,豁然醒悟,瞪大眼睛喊到,哦,那不就是来偷咱的鱼的吗!师父未置可否说,这大冬天,能吃上几顿新鲜鱼,多美气。谁不想啊。有个胆子大的偷箔的人,喜欢藏在大汪子边的坟圈子里,或者躺在裸露的棺材板上,做出怪声吓唬胆小的看箔人,看箔的被吓跑了,他就大大方方下水捞箔,一晚上几百斤鱼虾,能卖不少钱啊。
那,师父,你被吓跑过吗?王小军后背发凉,颤声问。
大红海乐了,我不管偷箔的,他们就不吓唬我啦,懂这个理儿吗,傻小子。
王小军摇摇头,还是为师父以前丢鱼的损失感到可惜。
夜里,王小军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好像只有风声。
第二天,大红海带着王小军继续捞箔,这天的鱼更多,大红海教王小军把稍微小点的鱼开膛破肚,用大盐揉搓了,晾在破苇席上,说,这些鱼可以到深冬时去农村换粮食。王小军对换粮食当然没兴趣,他关心的是那些新鲜的大鱼可以卖多少钱。
快傍晚,王小军的爸爸又来了,带了几个馒头,带走一兜子鱼。
第三天夜里,喝醉了酒的大红海鼾声雷鸣,王小军怎么也睡不着,他举着手电筒钻出窝铺,起初的新鲜劲已经过去,他有点想家了。也不知道大力二锁他们在干啥。手电筒在堤埝和水里胡乱扫射着,也没啥新发现,一会儿就没意思了,王小军就用手电筒往天上照,照了一会儿弯弯月亮和稀疏的星星。
回到窝铺,钻进破棉被里,把棉猴捂住脑袋,他迷迷糊糊想睡觉,翻来覆去半天,还是睡不着,这时,窝铺外面好像有些异样的聲音。偷箔的人来了?王小军心里一阵惊悚和兴奋,电影里的那些坏人,真来到自己身边了?
他爬起来,把窝铺对着水面的小窗户扒开一点缝隙,用力向外看,真有几个人影在水里。王小军心咚咚狂跳,这时,一只大手把他按回被窝,王小军知道这是师父的手,他乖乖地躺下了,心想,原来师父也没睡啊,他也听到偷箔人蹚水的动静了啊。
从寂静如死亡的窝铺外面隐隐传来的声音,像密码天书一样在王小军心里迅速破译着,他在猜想来人究竟有几个,都是什么人,是不是都青面獠牙面目可憎,他们会不会来窝铺抢东西。半天过去了,也没破译出什么答案。王小军像是身处一场灾难当中,他无力反抗,只能盼着灾难赶紧过去。蹚水声没了,几个人好像上了堤埝,这时,突然传来一个人低声的惊呼,我操,你们捞了这么多啊,咸鱼别动。
这声音让王小军如针刺一般难受,他听出来,发出那个声音的人,很像是他爸爸。
天快亮时,王小军钻出窝铺,他推亮手电筒,手电筒的光柱像刀剑一样在水面劈来砍去,他借助手电筒的亮光,看到距离窝铺不远处,有一条湿漉漉的痕迹,往前走,再看远处的几道箔,都有类似的水印由汪子里通向堤埝。王小军低着头,满怀负罪感,回到窝铺边。放下手电筒,东方微明,他点着了柴火,赎罪一样,把柴火烧得很旺。火光在朝霞中鲜艳动人。他用心烤好了馒头和咸鱼,喊师父来吃。
王小军偷窥师父脸上没有生气的表情,很是诧异。师父很高兴地啃着馒头撕扯着咸鱼。王小军说,师父,今天我来捞箔吧,您老歇着。
大红海哈哈大笑说,我徒弟真懂事,师父哪能让你自己下水呢,咱爷俩下午捞完箔得回去一趟。
尽管这一天捞的鱼少了很多,加上晾晒的咸鱼,也满满地装了一车。天快擦黑,爷俩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里。
快到家时,王小军闻到了盐工宿舍胡同里弥漫的熬鱼的和晒咸鱼的香味腥味。
大红海打开院门,王小军看到院子的地上散落着一些东西,有几个抽屉,还有几个敞着口的破麻袋。他再扭头看门窗,果然有一扇窗户是敞开的。这一切大红海也看到了,他却很镇定,似乎什么都没看到。
心情沉重地帮师父把鱼搬进院子里,他把师父塞给他的几张钞票藏好,王小军低着头提着一袋子鱼回家。
把鱼丢在院子里,王小军就像立了功的大英雄一样,趾高气扬走出家门,找大力二锁他们去了。
家里没有人,王小军就去他们经常玩的地方找,那条臭河沟边,芦苇垛,副食店的东房山,都没找到他俩。天黑了,王小军在两间没人住的破房子里发现了光亮,他悄悄摸过去,从没了窗户的墙洞往里窥视,他看到大力和二锁一人拿了一只锃亮的手电筒,正在照屋顶上的燕子窝。
呔,你们两个蟊贼,往哪里逃!王小军学着评书里的话,高声断喝。他本想吓唬大力和二锁一下,再和他们笑成一团。谁知他俩面色极其慌张,把手电筒往屁股后面藏,抬头看到是王小军,神情才恢复常态,大力颤抖着声音说,小军,你回来了啊。
王小军凑过去,要抢大力的手电筒,口里说,哪里来的手电筒?你爸爸那个没这么大啊。
大力支支吾吾的,我爸爸昨天買的。手电筒没递给王小军,却递给王小军一包吃了一半的江米条。
王小军挥手把江米条打落在地,瞪眼质问,你俩准是偷了我师父的钱了,对不?
大力二锁听了,面面相觑,然后两人蹿起来,猛然推开王小军,钻出门洞,转眼就跑得没影了。
四
夜里起了大风,西北风把王小军家的窗户当成了口哨,嗡嗡地吹了一宿。天亮时,大红海来砸门,王小军吓了一跳,他觉得师父肯定要和他算账,说不定要让他带着派出所的警察去抓大力和二锁。
王小军躲在屋子里,侧耳听大红海和爸爸说话。
大红海说,兄弟,咱们得去大汪子边去捡冻鱼,这一宿大风,汪子里的鱼肯定冻僵了,我先带着小军去,你喊人跟上吧,记着让大伙带着木棍子,砸鱼用。
爸爸给王小军布置了任务,先去通知大力二锁两家去捡冻鱼,再去找师父大红海,要在第一时间赶到汪子边。
顶着力度强劲的北风推着排子车来到汪子边时已经快中午了,王小军觉得自己快被冻成冰坨了,从骨头里冒寒气。脸上像结了层冰壳,摸上去都冰手指。大汪子的水还没结冰,水波冷涩黏稠,泡沫被风吹得蝴蝶一样四处飞舞。再仔细在水岸连接处寻找,真的有一些冻僵的筷子长的梭鱼被水浪推到了岸边,白花花的俯首可拾。王小军和大红海赶紧忙活,有的大梭鱼还能游动,但是已经到了浅水处,用木棍砸下去,被打中的鱼瞬间就翻出水面。在第一批来捡冻鱼的人到来时,他们已经捡了两袋子大梭鱼。条条梭鱼都像白萝卜一样肥得滚圆。
来的这些人里有大力二锁还有他们的爸爸,看到堤埝上那两袋子鱼,他们都急红了脸,默不作声地急匆匆跳下堤埝,在水边紧张地寻觅,手里的木棍时不时地砸向水面,噼噼啪啪,稀里哗啦。他们手里提着的鱼兜子也慢慢变沉重,每个人都掩饰不住地激动兴奋。接着,第二批第三批人也都赶来了,上一批捡冻鱼人的鱼获无疑刺激了新来的人们,他们更加急切地跳下堤埝,大汪子下风头的这个角落,很快乱成一团。不断有鱼从深水处游来,只要它们的身影被发现,几根木棍会抢着砸下去,很多人浑身湿漉,也舍不得离开半步。这些梭鱼像被施了魔法,源源不断涌向浅水处,让人们忘记了一切。
傍晚来了,大红海让王小军在排子车边看着捡上来的鱼获,光线昏暗中,一把把手电筒都亮了,鱼似乎越来越多,狂风把捡冻鱼的人们吹向了汪子的一个东南角。王小军看到他们发了疯一样踩着泥水,手里的木棍狠狠砸向水面。很快,那里有了一个大大的人团儿,人们手里举起的木棍,就像刺猬身上的毛刺。就在这时,王小军听到一声闷重的响,他寻着声音找,王小军看到大红海身体晃了晃,僵直地摔倒在水里。王小军高喊,砸到人啦,谁砸了我师父啦。但是那些人就像木头人,谁也听不见王小军在呼喊;他们又像一群盲人,谁也看不到大红海跌倒在水里。王小军愣了一下神,赶紧跳下堤埝,飞跑过去,从冰冷的水里拽出了大红海,他喊身边人帮忙,才有两个陌生的大人不情愿地各伸出一只手,帮王小军把大红海拖到岸边。大红海猛烈地咳嗽了一阵,嘴里吐出几口呕吐物,身体开始发抖。
王小军在乱哄哄的砸鱼喧嚣中艰难地推着大红海离开了堤埝,他没有央求认识的大人帮忙,因为他知道,大人们此刻脑子里只有多捡冻鱼。把排子车推上通往盐场晒盐工区的那条路上时,天上的星星早就睁开了眼睛,用满眼的寒光冷漠地俯瞰着像雪橇狗一样的王小军。收获满满的人们陆续超过了他们师徒俩,每一辆自行车晃晃悠悠醉汉一样从王小军身边安静地驶过时,全身大汗的王小军就觉得一阵又一阵的寒凉。
五
还是王小军独自一人从师父家找到盐工医疗证,把大红海推进盐工医院,每天给大红海端屎倒尿,送妈妈给做的一日三餐,尽管爸爸不满的声音很刺耳,王小军还是坚持每天去医院。
半个月后,从医院出来,大红海恢复得还好,就是变得有点傻了,他的口水就像屋檐上滴下的雨水一样多,总是稀稀拉拉溜出来,挂在胸前。
王小军发现,师父似乎永远不知道自己口袋里装了几块钱,也不知道钱揣在哪个兜里,有时候他随手掏口袋,掏出一张一块两块的纸币,把自己都惊喜得冒出了鼻涕泡,他会举着钱寻找王小军,把钱塞进王小军的衣兜。
王小军对插箔治鱼的手艺豁然领悟了,他在大海结冰前,从大红海插的箔网里又捞了几次鱼,他给自己鼓劲,把鱼推到周边的乡村卖掉了,给大红海换了很多土豆大白菜还有稻米,连王小军的爸爸在骂王小军吃里扒外时,暗地里和王小军的妈妈耳语说儿子突然懂事长大了。
盐工子弟学校放了寒假,王小军因为总给班主任家送鱼,期末考试也都及格了,这年他上初三,爸爸说,毕业后就提前接班,当一名正式盐工。王小军想,只要不耽误他插箔治鱼卖钱就行,当盐工也可以接受。
快小年了,王小军的爸爸借题发挥,请了大力二锁的爸爸在家喝酒,酒肴是一盘馏咸梭鱼,一盘馇梭鱼冻,一盘花生米,一盘炒鸡蛋,一盘虾油白菜。
大红海不知啥时候走到了王小军家院门口,透过玻璃窗,王小军看到了大红海熟悉的身影,他赶忙跑出屋,把大红海搀扶进屋,大红海傻乎乎地也不推辞,任由王小军摆布。进了屋,大红海站在正在吃喝的三个大人身后,闻到了酒香,大红海的口水就像大雨时屋檐落下的雨滴。几乎连成线了。王小军在一旁很焦急,他期盼着三位大人中谁肯开口说,呀,这不是大红海吗,快来喝两盅。有了这句像台阶一样的话,王小军好给师父搬凳子,摆酒盅碗筷。
可是,王小军和大红海站了很久,三个大人自顾自飲酒谈笑,根本没人搭理口水连连的大红海。王小军在一旁焦急等待着,他觉得大红海肯定变成一团透明的空气了,所以大人们才看不到他。他就走过去,站在大红海身边,希望大人们看到他俩。可是王小军的爸爸回过头瞪了一眼,说,你还不出去找大力玩去?大力肯定想你了,快去。王小军明白,此刻几个大人把大红海当成令人厌烦的乞丐了,他们硬下心不肯施舍。
王小军失魂落魄地把眼睛一直盯着饭桌的大红海拽出屋,拉回家,王小军心里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
回家时,王小军质问醉醺醺爸爸,为什么不请大红海一起喝酒。爸爸看到王小军气愤的神情,也掉了脸子,硬声硬气地说,你个傻子小子,他要是在咱家喝酒时突然犯病死了,你还要给他打幡抱罐啊,真是白养你了。
过年了。王小军从他家鸡窝里掏出大红海受伤之前给他的一百多块钱,拿出一沓,买了一只手电筒两瓶老白干酒一包花生米半斤酱驴肉。他把两瓶酒花生米酱驴肉偷偷送到师父家,塞给师父时,看到师父流着哈喇子傻乎乎微笑的样子,王小军觉得一阵心酸,他眼里含着泪与师父吃完了这顿年夜饭。
他开始疏远大力和二锁他们了。好多夜晚,陪师父吃完饭,伺候师父躺下,再从师父家出来,他会提着手电筒,在盐工宿舍周围照来照去的,像个查夜的巡警,也像只原野里的流浪狗。
盐工们对这个落单的少年王小军指指点点,他们发现他的手电筒近看光亮充足,可是距离远了,就显得微弱无力,因为王小军手电筒发出的那一束光亮,被盐工宿舍各家窗户外泄的灯光以及偶尔驶过的汽车灯光以及路灯光,潮水一样淹没吞噬得干干净净。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