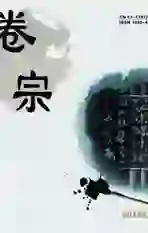解码理论和媒介建构视角下“袁立事件”的看法
2018-05-26周丹
摘 要:在泛娱乐化和人设严重的时代,各大传媒机构对于自身社会效益的坚守似乎懈怠了,更多的是为了经济效益去一味制造“噱头”来迎合受众,博取眼球。这极不利于整个现代传媒生态圈的健康发展,进而导致传媒景观的混乱,混淆受众的视听。基于此,在传者(制造方)与受者(接受反馈与评论方)之间运用编码解码和媒介建构理论来诠释媒介舆情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解码 舆情 建构 媒介素养
一、主导霸权式的蒙蔽
根据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先前受众在传播地位上的被动(跟受众接受信息量多少和媒介素养程度有关),致使对于传播媒介上所传播的一切都全盘接受。传媒机构在制码上是完全占主导地位的,议程设置和把关都由它来掌控,而且这种传播状态是传媒机构非常期望的一种状态,受众毫无反抗能力。比如电视,一档电视节目在最初播出的时候,观众看到的一些发生在电视里的“真实”,就会毫不犹豫的认为那就是真的。于是,传媒机构的基本目的就达到了。观众处于一个被完全蒙蔽的状态(当然对于现在来说,此说法肯定不妥,但这是之前),没有辨识到电视真实与现实真实或者说节目背后的一些操作(技术上和思想意识上的)。但这也仅仅是电视节目制作机构在节目流程设置或者说是节目制作技术上的“障眼法”。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传播情境是需要一定条件的。首先,它需要电视传者和电视观众之间拥有较宽和较深的“信息沟”,双方在信息占有、思想意识的深度方面具有较大差距。这样,观众才没有能力去理解反思电视所传播的意识形态,只能被动接受。其次,它需要电视观众处于一种信息封闭的状态,即他没有能力获得其他信息尤其是相反的信息来提醒他反思甚至对抗电视传播的意识形态。
浙江卫视《演员的诞生》栏目组请袁立来表演节目到后来双方发生纠纷的这一整个过程中,因为节目内部流程或者“规则”被打破了,即在节目编码阶段出了问题(表现为节目组违反了先前和袁立商讨好的节目晋级流程以及后期剪辑严重损坏袁立的公众形象),演员袁立泄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信息。在此之前,这些信息只有节目内部人员才知道,观众几乎毫不知情。节目制作方顾及自身利益,充分行使它的传播霸权,掌控和调动节目内部的种种参与元素(特别是评委及其言论和反应),来制造节目效果和“视觉奇观”。这是一种蒙蔽,节目制作方长期以来处于优势主导地位,由它来迎合或者引导受众的视觉兴趣与口味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利于提高受众的视觉素养,节目制作方之前也一直忽视刻意营造节目效果所带来的弊端,把节目过度的游戏化,不计后果的把规则抛开。因此,袁立事件的爆发无疑也对浙江卫视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而且事件爆发后,有关于袁立表演的关键片段在各大自媒体上就“消失了”;这是一种心虚,也是一种屏蔽受众视听阻止其寻找真相的行为。这种屏蔽,实际上也是对浙江卫视自己的欺骗。
二、协调与对立表征下的舆论交锋
袁立事件爆发后,各大媒体社交软件成了舆论主战场。事件本身的价值似乎不是很重要了,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受众对它的解读,电视机构方主导作用较为明显,受众兴许受电视机构的影响较大;但是在事件不断发酵以及在袁立的不断争论之下,受众似乎对于事件背后的东西逐渐明朗起来,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根据霍尔解码方式之一的协调式符码理论,这是观众一种主观的解读方式,在自己主动理解的基础上解读并加工事件的内涵。用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的话来说,电视节目信息在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可写的文本”,即电视信息(这里我们理解为事件本身)最后传播效果的完成是需要观众予以解读和加工的。在这样的解读情境下,有些观众的解读是内心真实的想法,较为客观公正;但也排除不了“有些人”寻找“舆论契机”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别人观点上(尤其是利用观点比较偏激的对象)来煽动舆情,带偏舆论导向。这样的人,在微博中通常称为“水军”(网络经济时代,利用金钱雇佣水军来形成舆论公关甚至反转舆情不是不可能的事),他们经常会帮着雇佣方进行舆论煽动或者洗白以及舆论公关。但是,对于这次袁立事件,似乎不是很起作用。一方面,受众在信息通道畅通程度较高的今天,所发掘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保真度,而且受众的媒介素养不比以往了,媒介素养大幅度提高(这跟地区经济文化发达程度和受众受教育程度有关),这是一种思想观点上的对抗。这也恰好暗合了霍尔第三种解读方式:对抗式解读方式。个人大胆地把霍尔的对抗式解读引申了一下,因为霍尔对抗式解读是对抗“上”或者说是电视里传播的意识形态,而我這里的对抗是在受众自身范围里的对抗,包括对抗水军(不仅是水军)的一些干扰、误读或者是“有意而为之”。受众之所以会做出“对抗性的解读”,是因为他们自己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这样他们才有能力对抗传媒中意识形态(在这里,我引申为一些误导性的意见)的传播。另一方面,由于袁立不断在微博“发声”,将事件的影响力步步扩大(有影响力的演员也纷纷站出来为袁立发声),才有效弱化 “对立面”对袁立的舆论攻击,不至于舆论形势反转。
三、电视媒介“建构现实”的反思
为了获得更高的收视率,电视媒介会刻意遮蔽现实生活中枯燥、呆板甚至冷酷无情的真实,而将现实生活中娱乐性的元素不断夸张放大,最后形成了让观众开心但是与真实社会生活脱节的电视景观。浙江卫视《演员的诞生》就是这样,一个表演类真人秀节目可能是需要去“建构”一些东西,这跟它节目性质是有关,但是一味追求电视娱乐化功能,而完全忽视和抛弃实际,是有悖于传媒伦理规范的。电视节目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现实生活尤其是现实负面生活的反拨,这是基于主流意识形态对电视的要求。但浙江卫视超过了这个“度”,必然会引起相反的效果。电视媒介用一种逼真的画面营造了一个美好的、理想的电视世界,这个世界用自己的美好遮蔽了现实世界的种种不如意,给人以快乐的幻觉,这种幻觉使人容易沉醉其中,所谓媒介的致幻性;用它来匹配受众的心理结构,匹配程度较高,那么使其忽视媒介所建构的现实真假性的概率越大。现实生活中所有的不快、所有的负面因素在电视中都有可能被化解掉,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消遣的需要。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电视所带来的娱乐性消遣对于受众来说不过是“一时之乐”,表面上看是得利了,其实长期下去,对于电视机构自身的发展是一种“毁灭”。基于培养理论的角度来看,受众会被这种无限的娱乐性给放纵了,电视机构在娱乐上对受众的纵容,会使自己逐渐陷入岌岌可危的地步。
因此,经过这次事件,浙江卫视应该引以为戒,及时反思与调整节目策略和规则。在社会媒介伦理规范之下,使其自身正确发挥娱乐文化功能。打造“阳光下的娱乐”。在今后创作取向上,要增强自己的职业伦理道德建设,要为观众负责,主动担负起“培养”受众的责任(积极的、健康的引导);相关电视管理机构创新管理办法,不能一味采取强制禁令性措施,要防患于未然,控制商业对于电视节目以及电视文化的冲击,多多鼓励和促进公共电视理念的传播。在今后电视传播的接受取向上,观众要建立健全的理解电视信息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尽可能多阅读媒介方面相关的书籍,不断提高媒介素养和媒介免疫力。这样,在舆论里,我们不至于迷失导向,被别人混淆视听;我们应当在理性思考之中,去探求事件真相。
参考文献
[1]《电视文化的观念》祁林著 2006年8月第1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2]《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姚君喜主编 2014年3月第1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作者简介
周丹(1994-),男,汉族,湖南辰溪人,广播电视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方向:影视文化与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