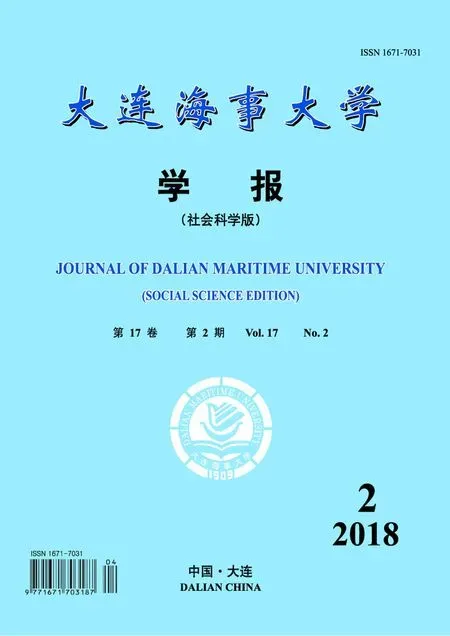日常语言哲学视域下的洞穴奇案
2018-04-12高礼杰陈一萍
高礼杰,陈一萍
(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重庆 401120)
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Lon Fuller)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洞穴探险者案”。纽卡斯国的5名洞穴探险协会成员进入岩洞探险时发生了山崩,继而受困,被困第20天,救援人员通过无线设备与探险者取得联系,不幸的是,营救工作至少需要10天时间,而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再活10天几乎是不可能的。被困的探险员之一威特莫尔向医生发问,吃掉一名成员是否可以维持生命,医生给予了肯定答复。但当他问到是否可以通过抽签决定该吃掉谁时,在场的医疗专家、政府官员和法官选择了沉默,没有人愿意回答。
最终,被困的探险员们听从了威特莫尔的建议,决定以掷骰子的方式选出一人吃掉。但在掷骰子以前,威特莫尔反悔了,表示想要撤回约定,而其他4人仍执意掷骰子,轮到威特莫尔投掷时,一名同伴替他完成,威特莫尔未表示异议。掷骰子的结果是,威特莫尔被同伴吃掉。他们在获救后被控谋杀罪。5名大法官都发表了言之成理的不同意见,结果是有罪判决与无罪判决各半,另有一名法官回避裁判,最终维持有罪判决和量刑。
萨伯在半个世纪后进一步讨论了这个案件,其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与50年前完全相同。萨伯虚拟了9名大法官,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戏剧性地和50年前一样,正反观点相当,维持了有罪判决。50年内前后共14位大法官根据截然不同的理由得出相同的有罪或无罪的结论,这些法官针锋相对的辩论引发读者对诸多法哲学问题的思考。比如“故意”概念的含义,以及如何理解法律适用中的例外情况等。
以下,将在14位大法官观点的基础上,从法官们所提出的“概念的平实含义”出发,对本案的一些疑难之处(即例外和故意)进行梳理。最终,试图澄清这一观点:当法官的解释和大众的直觉或一般经验不一致时,我们更应该尊重概念意义的源头,即大众的一般经验。此外,洞穴奇案这一思想实验着意制造某种两难的困境让我们思考法律条文的适用场景。这种反事实的设定与人们的日常经验有着诸多差异,且这个思想实验所设想的极其特殊的情况并非人们日常生活中自然发生的事情,换言之,这些特殊事实并不对应于语词概念的演变或人们一般经验的变化。因此,这种例子并不足以增进人们对生活道理的理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官的专家意见必然要受到大众一般生活经验的约束。
一、以日常语言哲学作为分析的出发点
论理词总是成对出现,这种现象遍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律领域也自然如此。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各种各样,繁复无比,与之相对应的法律体系也十分复杂。而人们一般谈到法律时,多少会将其与日常生活对比谈论,仿佛法律所构建的那个领域比日常生活复杂无数倍。而法律与日常也就多少构成了两相对照的论理词。
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般遵循各种伦理规范或者道德体系,通常不会刻意地思索自己的言行是否遵守了哪条法律。伦理道德与现代社会的法律体系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洞穴奇案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日常的道德体系、伦理规范不可能与法律完全一样,否则,道德体系本身便是法律条文了。但法律又不可能凭空产生,它必然生长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与特定的政治制度、经济条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法律条文本身无法自证,因此解释必不可少,而所有解释都存在一个终点,可以认为,这个终点就是实践。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规则会有一些漏洞,实践不得不为自身辩护”[1]139。于是,多数法律条文跟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规则一样,当人们追问到最后时,往往就变成了,“人们在生活中就是如此这般行事的”[1]559。也即,规则的基础是实践,实践构成了规则的最后理由。这种实践也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认为,法律条文虽然根植于人们日常的道德直觉,但又在很大程度上与之不同而具有自治性。
在法律与日常生活的对比中,不应忘记的一点是,法律始终应该照应现实生活。就哲学而言,历史上许多哲学家发明了无数超级概念,后来的哲学家也都围绕这些超级概念耗费着自己的才华,仿佛哲学家们的天职就是不断地修补这些哲学体系中的问题。他们忘记了,哲学家创造这些超级概念的出发点正是应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①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事权划分不明,水资源行政管理权分割。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塔管局只能直接管理塔里木河干流,源流的各地州、兵团师实际上既是源流水资源的管理者,又是水资源的使用者,与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没有隶属关系,没有组织管理制度,权利又相对独立,因而各自为政,流域管理举步维艰。
在这个意义上,洞穴奇案作为一个构想出来的奇特案例,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从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得到说明。而当法律“不够用”时,更需要回到日常的生活实践、日常直观来重新审视这种独特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思路并非想让伦理道德和舆论绑架法律、左右判决。相反,我们要做的是,如何让法律条文本身更有道理,而不至于成为令人仰望的空中楼阁。
二、法律条文及其平实含义
特鲁派尼法官出于“尊重法律条文”判决被告有罪,这一法律条文(《纽卡斯联邦法典》第12条A款)的完整表述是,“任何人故意剥夺了他人的生命都必须被判处死刑(whoever shall willfully take the life of another shall be punished by death)”[2]17。在他看来,即使人们可能会出于同情而体谅探险者当时走投无路的悲惨境地,但法律条文绝不允许有任何例外。
基恩法官同样认为忠实适用法律条文是法官的义务,“法官应当根据法律的平实含义(plain meaning)来解释法律”[2]36,不能参考个人的意愿或个人的正义、伦理观念。对于探险者所作所为的对错善恶,他并不加以讨论,因为他认为这无关法官职责,法官宣誓适用法律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观念。所以法官判决时面临的唯一问题是,根据《纽卡斯联邦法典》第12条A款的含义,被告是否的确故意剥夺了威特莫尔的生命。而他进一步认为,假定任何一个毫无偏私的观察者,只要乐于理解这些词的普通含义,将立刻得出结论,被告确实“故意剥夺了威特莫尔的生命”。至于什么是这些词的“普通含义”,尤其什么是“故意”的普通含义,是基恩法官没有解释的,同时也是我们试图梳理的问题。
伯纳姆法官提到,九成的公众希望被告人被宣判无罪。但他认为公众可以仅仅考虑案件的道德处境而宽恕被告,而法官却应当撇开己见,去发现法律的要求是什么,去接受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而不能为了适应公众的观念而修订法律,求诸法律条文之外的一些理论。显然,对于法律条文本身的执着让伯纳姆法官选择忽视法律的目的,从而判决被告有罪。但伯纳姆法官的意见显然与基恩法官的观点有不一致的地方。
以上三位法官均在没有掺杂其他考量的情况下,依据法律条文本身及其所谓的平实含义判决被告有罪。公众并非法律专家,他们对法律条文也有着日常的理解。可以推论说,这些公众十分理解相关法律条文的平实含义。但他们多数人却认为被告人应该判处无罪。那么,法官眼中“故意”的平实含义是否应该反映人们直观的判断?如果法官所理解的“故意”概念与大众所理解的不一致,那么到底应该认为哪种含义更能称得上是平实的?
当人们谈论概念时,总是忍不住对某个语词“下定义”。一个最直白的例子:什么是桌子?有人这样下定义:一种常用家具,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可以用来放东西、吃饭、学习工作等。这样的定义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现,有时候床也可以满足这一定义,或者,找来一个不在此定义之内的棱角分明的箱子也可以当桌子。如此一来,为桌子下定义的活动似乎失败了,也可以说,桌子的定义存在例外,桌子这个语词的含义,不足以确定其外延。然而,谈到桌子,我们确信明白在谈论什么,看到桌子,也能够分辨,至少,桌子这一存在在人们的生活经验中是无须质疑的。出现这样的状况,多半是因为,“一个语词所依的道理纷纷杂杂、不止一端;而且,它们还可能包含没有什么道理的约定或包含难以明述的感性因素”[3]。如此,再来看“故意”,就会发现,无论怎样给故意概念下定义,总是会有不同的理解或者例外,如果致力于从包含着“故意”的法律条文中寻找平实含义,势必要将例外与生活经验考虑其中。
三、作为规则的法律及其例外
大众对本案中“故意”概念的理解与法官不一致。从法官的角度看,大众对“故意”的理解构成了相关条款的例外情况。特鲁派尼法官认为法律不允许有任何例外,但实际上,法律条文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诸多例外。比如,从一个国家的历史承继关系来看,过去的传统律法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例外情况,而就一般而言,法律在现实中往往存在着效力和实效不一致的情形,这种情况往往内在地蕴含了例外情况的发生。
进一步,从一般的人类生活来看,例外也总有其位置。比如,每种语言都有其固定的语法规则,但基本上也都包含了诸多例外规则,比如英文中的动词不规则变化等。而这种现象之基本原因就在于,生活中的规则总是各种可能性的总结,能行和不行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朗。正如人们都追求好生活、幸福的生活,但实现的方式并不完全一致,一个人积累的教训,对另一个人可能恰好是正面经验的积累。
人们对法律的一般理解就包含了各种例外情况,这些例外情况主要源于人们生活经验的演变。具体而言,人们对法律条款中一些具体概念的解释也包含着各种例外情况。维特根斯坦曾说,“要是可以使任何行动和规则相符合,那么也就可以使它和规则相矛盾。于是无所谓符合也无所谓矛盾”[6]201。这意味着,人们对规则并没有唯一的解释。
此外,当某一法律条文被解释时,如何才能确定所谓的“法律的平实含义”?如果说“平实含义”就是字面意思,可正如福斯特法官所说,“我们面对法律条文从来没有依照字面意思加以适用”[2]26,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所谓的“遵循规则悖论”。法令措辞之间本身就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法令的语言表述无法自洽时,就不断创造新的词汇,去契合法律的目的,比如正当防卫等。洞穴奇案看似无解,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把“故意杀人即有罪”看作普遍和无条件的,泯灭了灵活理解的可能性。而拒绝了灵活理解,坚守法律条文概念的完全周延性无疑会将法律推向一个荒谬的境地:法官的工作只是依照固定的法律条文(不掺杂任何其他观念)做判决,与流水线上的工人并无区别,甚至可以发明一台“判决机”,输入案件事实,它就可以立马根据法令文字输出判决结果。显然,现实并非如此,伯纳姆法官执着于接受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可他同时又说,“尽管法律条文只字未提,自我防卫还是被承认为法律条文的例外,其真正原因是在该法起草和通过之时,这是所有的立法者、法官和公民所公认的”[2]67。这表明,他接受没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自我防卫。
可见,明确的法律条文的确不应当是法官判决所依据的唯一标准,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和法律的明文规定之间寻找某种平衡,进而达到概念与相关经验的一致。具体到洞穴奇案,虽然“故意”这个词是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但按照我们所约定的以及大众的一般经验理解,“故意”其实可以在我们希望惩罚的杀人者和我们不希望惩罚的杀人者之间划出一条线。这样,一个杀人行为,的确有可能既是有意的,同时又不是故意的。对于探险者的行为,可以说他们有着清楚的行为意图,却不能认为他们在法律上故意杀了人。
四、“故意”概念的背后——基于情感和常识的判断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人们将故意概念的理解应用到洞穴奇案这种特殊情况中时,会产生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若要进一步理解洞穴奇案,有必要站在立法者或一般法学理论的角度对“故意”这一概念进行深入理解。而这种理解也正好将这一概念拉回到人们的一般生活经验之中,进而能更好地澄清这一概念背后所凝结的一般道理或普遍生活经验。
当立法者制定出“任何人故意剥夺了他人的生命都必须被判处死刑”这条法令时,必定在“故意”中包含了恶意,或者说,他们不仅仅只考虑了道德因素,同时也考虑到社会安定和谐的因素,即如果人们因为私愤或者其他理由去任意杀人,那么没有人可以安心地从事生产和生活,整个社会也将动荡不安。这时,“故意”意味着“错误的谋杀”。比如,如果仅仅从字面意思理解故意的话,执行绞刑的刽子手也可以说是故意杀人,但这显然是荒谬的,依照立法者和正常人的理念,执行绞刑应该可以被归为“正确的谋杀”。可是,立法者立法时怎能想到探险者杀人食人这种情形?当立法者面对这种情况时,会怎样认定探险者食人这一行为的性质,他们会不会将这一行为包含在“故意”之中,还是说他们会创制出另外一个词汇或说法来规制这种行为?从法学理论来看,法学家们对“故意”这个概念的界定也莫衷一是。例如,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都没有在立法中给“故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英国法律委员会曾在1989年的《刑法典草案》中尝试给“故意”下定义,但最终也是因为对于“故意”概念的内涵无法准确表述而宣告失败。
现在不妨假设,在立法者设置法律中的“故意”这一概念之前就出现了探险者案,他们会不会将这种情形置于故意之中。首先,当探险者们决定通过抽签选出一名牺牲者时,就已经注定了这里会有一起谋杀发生,这时他们并非出自通常生活中的故意,而是无奈、不得已,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自己被吃掉的这1/5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们做好了约定,当某一个人被杀死时,他一定得是同意的。而当一名牺牲者被选出来,其他人将他杀死并吃掉时,吃人者也没有出自故意(我们不去探究他们吃人时的心情,是终于得到食物的欣喜,是自己没有被吃掉的庆幸,还是同类相残的不安与恐惧),他们只是对契约的践行。尽管一般而言,执行一项规则、一个命令,也包含了当事人立意去执行的意图,毕竟,人不是机器。但故意之区别于其他行为的关键就在于,故意的行为可能包含了对其他可能的有意忽略;而洞穴奇案中,人们做出食人举动并非这种情况,这个案子中的人们并没有别的选择。
这样看来,很难评价这一谋杀行为的道德性,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契约的实现,进而,探险者仅仅是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践行契约。其次,探险者案很难说会在警告民众不可杀人这一点上有任何作用,因为这一情形无法被模仿,甚至几代人都对这样的事情闻所未闻,并且很难期待一个善良的人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别的选择。也就是说,将探险者案的情形归于故意杀人不会对民众起到引导教育的作用,不会对社会安定有什么帮助。
最后,不得不将这一现实考虑进去:有九成的公众希望被告人被宣判无罪。而立法者来自于公众,当他们不像法官那样被缚于“故意杀人”的成文法令时,还有多少人会认为这是一起故意杀人?这样想来,立法者多半不会将故意的外延扩展到探险者案上。
在洞穴奇案中,人们一般认为,如果没有了其他可能,那么,此时对于行为人的行为就应当最大可能地剥离其意志层面的故意成分,而更多地认为其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行为。若要像法学家那般专业地追究,比如,这些探险者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后果,答案是肯定的。但这却对案件的理解没有什么推进,很明显,这种照章办事的情况就像自然的事情一般必然地发生了,用凯尔森的话说,此处的法律效力与实效等同。而知道和不知道对于事情本身没有明显的影响。这种极端的情形,排除了其他可能的技术性分析。这是人们在面对洞穴奇案时,需要从常识角度进行讨论的理由之一。
如果说法官在面对疑难的个案时会更多地选择尊重法律条文、细致探究法条表述、参考最精妙最前沿的法学理论,那么民众在同样的情况下或许会忽视这些,凭借常识和情感给出自己的判断。洞穴奇案中,九成的公众希望被告人被宣判无罪,甚至,当法官走下审判席时,也会倾向于宽恕被告,因为在面对无线电另一端无助的探险者们提出吃人的想法时,在场的法官选择了沉默。这足以说明,专家意见在面对现实的伦理困境时,并不能给出一个发条般细致清楚的答案,这是基于常识对这个案例进行推理的理由之二。
但所谓“基于常识和情感的判断”绝非忽视法律的规则。只是,如哈特所说的那样,规则会被修正,而修正某种胁迫命令或规则时,最需要的就是将一些新的设想纳入立法之中,立法就是引进或修正社会应普遍遵守的一般行为标准。[7]得以被普遍遵守的行为标准,一定是至少在实然层面经得起考验的,而这就不得不将公众的常识和情感考虑进去。然而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立法机关的原始意图和那些法律条文所使用的词语的一般含义发生冲突,这时就需要像普通民众可能理解的那样去解释法律条文的概念,并根据当时当地的社会大环境来解决疑难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法官根据日常经验来对待法条,而不是被法条本身所束缚。
同样,我们并不否认法律的稳定性与确定性,只是法律的确定性并非确定在法律条文上,尤其当公义、道德、人情、文化等因素纠结在一起时,法律条文必定会稍显单薄。法律无法脱离上述文明社会的种种因素单独存在,所以,法律语言不能与日常语言割裂开使用,也不能局限于自身的学科话语之中,而是应当注意和对比多种相关学科的一致性、差异性,并且注重日常经验的、生活上的、事实上的用语和表达。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其实,只要“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有用处,它们的用处一定像“桌子”、“灯”这些词一样卑微。[6]97当我们在面对“故意”这个概念时,也应该更加尊重其日常用法。
五、结 语
洞穴奇案作为一个思想实验,十分引人入胜。就像有轨电车两难一样,这样的故事总会给人们带来思想上的挑战,并让人们反思法律和道德中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人们对法律条文所规定的“例外”情况的解释,以及对“故意”概念的理解等。
但这样的例子由于过于极端和反事实,并不适合细致的分析。它们更多地像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所谓的直觉泵(intuition pumps),基于直觉的一些思想实验,并没有太多细节,而正如丹尼特对塞尔的中文屋思想实验的评论所指出的,人们只是希望得出自己的观点,对于那些可能挫败自己观点的细节完全不去追究。[8]
因此,这样的案例不适合进行十分专业细致的分析,它们本身也有很多逻辑漏洞。比如,与这种极端情况相匹配,大致也可以设定,探险者们可能有好运气,山体崩塌时砸死了一只野猪等。思想实验本身就由反事实条件句构成,如果再以反事实条件句对之进行分析,就会导致思想的无限后退。这些例子需要人们更多地从日常生活经验汲取反思的资源,并在常识的层面对之进行大致的分析。如果法律与生活经验和常识出入太大,法律本身也就失去了其赖以建立的基础。
[1]WITTGENSTEIN L. On certainty[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2]萨伯.洞穴奇案[M].陈福勇,张世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3]陈嘉映.说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37.
[4]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64-84.
[5]陈嘉映.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J].江苏社会科学,2006(1):8.
[6]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M].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09.
[7]HART H L A. The concept of law[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43.
[8]DENNETT D C. Intuition pumps and other tools for thinking[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3:617-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