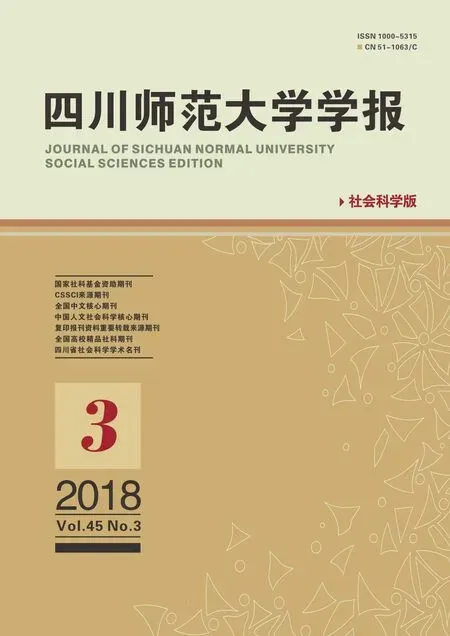钱大昕:大有功于宋史研究的乾嘉巨子
2018-04-03
(1.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2.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 610066)
一 考证《宋史》第一人
当代史家柴德赓称钱大昕为考史“第一个人”①,若将此语改为“考证《宋史》第一人”②,只怕较为确当。在乾嘉考史三大家中,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基本不涉及《宋史》,钱氏《廿二史考异》中考异《宋史》部分多达16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虽然包括《宋史》,但论多于考,《考异》则以考证见长。梁启超说:钱大昕“最有功於原著”[3]292。他考证《宋史》创获颇多,仅以《宰辅表》为例,订正其中的关键性错误就不少,如李曾伯、吴渊、厉文翁等并非执政大臣而误列《表》中,已死者姚希得和已逃者黄镛、陈文龙居然被任命为执政大臣等等。《宰辅表》第一格记载的何年何人官居宰相尤其重要,钱氏发现其中有四个大错:其一,“(秦)桧以(绍兴)二年八月罢相,至八年三月复自枢密使入相。表于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第一格俱有‘秦桧’字,误也”[4]1041;其二,“汤思退于绍兴三十年十二月罢相,而表于三十一年犹书汤思退,误”[4]1041;其三,淳熙九年九月庚午,王淮、梁克家出任左、右丞相,“《表》既失书,又自是年至十三年第一格俱当有‘梁克家’字,亦并失之”[4]1043;其四,“(淳祐四年)十二月,诏许右丞相史嵩之终丧,则起复之诏虽下,仍不果行也。《表》既失书诏终丧一节,而于五年、六年第一格俱有史嵩之字,则误以为嵩之真起复矣”[4]1045。
钱大昕考证《宋史》绝非“毛举细故,无足重轻”[3]272,自有其高明之处,可概括为“两个注重”。
一是注重义例。钱氏发现《宋史·本纪》及《宰辅表》或无明确规矩,或虽有体例而自乱其例。如当书失书。宰相执政任免都是《本纪》与《宰辅表》应当书写的大事,但两者失书均达数十事之多。在《本纪》中,避重就轻,罢免不书之事较多。其例证有:淳化元年,赵普罢相失书而“屡书视疾”[4]949;天禧元年,王旦罢相不书,仅书“对于便殿”[4]950;天禧元年,王曾罢参知政事,仅书“为礼部侍郎”[4]950等等。又如有例破例。《宰辅表》无叙事之例,破例叙事之处甚多。再如体例不一。去世称薨与称卒就很混乱。《太宗本纪》,石守信、陈洪进、潘美同为使相,死时石称薨,陈、潘称卒;《真宗本纪》,张玄德、石保吉、魏咸信都是使相,死时张称薨,石、魏称卒。钱氏说:“均为使相,而书法各异,此义例之可议也。”[4]949《神宗本纪》,官至执政的唐介、欧阳修死时称薨,“陈升之以前宰相而反书卒”[4]951。诸如此类,不胜其举。
二是注重制度。钱大昕考述《宋史》,涉及制度特别是职官制度之处甚多。如《宰辅表》:“(至道)三年六月,钱若水自同知枢密院事以秘书院学士免。”钱氏指出:“秘书省无学士之称,亦无院名。据本传,乃集贤院学士也。”[4]1035《真宗本纪》:大中祥符七年三月,“楚王元佐、相王元偓、舒王元偁、荣王元俨枢密使、同平章事”。钱氏认定“诸王例无授枢密使者”是宋代的一项既定制度,“此文必有讹舛。《长编》亦无此事”[4]949-950。《仁宗本纪》:“庆历四年七月,封宗室十人为郡王、国公。”“然十王之名,《纪》、《传》俱未详列。”“封十王之后”事关宋朝宗室制度,钱氏依据《文献通考》《长编》《玉海》诸书补充十人名讳及封号,并称:“十人者,太祖子二房,太宗子七房,秦王廷美子一房也。”[4]951“潜藩升为节度州”是宋代的一项制度。《徽宗本纪》:“(政和)七年三月,升鼎州为常德军。四月,升温州为应德军。五月,升庆州为庆阳军,渭州为平凉军。”钱氏指出:“此四州皆以潜藩升为节度州,赐军额,当增‘节度’二字。《地理志》温州为应道军,此云应德,似误。”[4]953《宰辅表》:“(德祐二年正月)己卯全允(亦作‘永’)坚加太尉,除参知政事。”钱氏认定宋代外戚一般不参政,他说:“永坚以后族加太尉,不为参政也。《表》又误。”[4]1047钱氏论述宰相制度之处尤多。关于宋初的宰相,他指出:“(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赵)普再入相,除司徒兼侍中。侍中为真宰相,故得入政府视事。司徒三公之官,非宰相也。《(太宗本)纪》书司徒,不书侍中,盖未通于官制矣。宋初,宰相官至侍中,则不复称平章事。端拱元年,赵普三入相,以太保兼侍中,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后虽侍中而不加平章事,祇为使相,非真相矣。”[4]949
二 “三端”说的倡行者
在治学方法上,钱大昕倡行“三端”说。他说:“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1]405又说:“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4]646年代与目录虽不在“三端”之列,但钱氏在这两个方面成就都不小。所著《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是清代具有代表性的年代学著作之一。古文献学家刘乃和有句云:“《考异》《潜研》重史坛,《十驾养新》千古志,《四朝朔闰》拾遗篇。”[5]卷首其价值不亚于《考异》诸书,在当年是很实用的工具书。《潜研堂集》中的《经史子集之名何昉》系目录学名篇。所著《元史·艺文志》为学界所推崇。以宋代目录学研究而论,钱氏对《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现存宋代目录学著作有相当精当的评介,对《文献通考》《长编》《隆平集》等宋代70多种史籍有颇具创见的提要或序跋,对《宋史·艺文志》辨误正讹之处甚多,并探究其颠倒、重复的缘故。
钱大昕说:“氏族之不讲,触处皆成窒碍。”[1]406他将“辨氏族”作为“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之一。他强调:“读古人之书,必知其人而论其世。”[1]446我国古代长期实行宗法制度,家族组织异常牢固,人们家族观念极强,要“知人论世”,离不开“辨氏族”。受史观与史料的双重局限,钱氏将“有名之家”作为“辨氏族”的重点。他说:“予所谓氏族之当明者,但就一代有名之家,辨其支派昭穆,使不相混而已矣。”[1]406在“知人”方面,钱大昕的主要贡献有四。
一是重视辨析名门望族的支派与昭穆,编著《元史·氏族志》。钱氏指出:“作史者不明此义,于是有一人而两传。”[1]406以宋代为例,如程师孟,“一见列传第九十卷,一见《循吏传》,两篇无一字异者”;李熙静,“已见列传第百十六,而第二百十二《忠义附传》又有李熙靖。‘靖’、‘静’同音,实一人也”[6]183等等。“有非其族而强合之”[1]406者,如“范文穆公(成大)世居吴郡,而与文正(仲淹)不同族”[6]203。钱氏十分看重家谱,为若干名门望族家谱作《序》,见于其《文集》;同时又指出:“自宋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而诈冒讹舛,几于不可究诘。”[4]449
二是重视同姓名现象,并加以区分。钱氏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中集中予以指出,其中包括宋代。其《宋人同姓名》[6]329-335列举例证达77条之多。如北宋前期的彭乘系华阳人,而《墨客挥犀》的作者彭乘则是南宋高安人。所著《跋宰辅编年录》除指出作者徐自明非知金华县徐自明而外,又称:“知嘉定县者有钱塘杨万里,非诚斋也。知平江府者有永嘉陈均,非平甫也。知南海县者有晋江王应麟,非厚斋也。”[1]507
三是重视同一官职的传承,编写多种《年表》。相传钱氏著有《唐五代学士年表》二卷、《宋学士年表》一卷,但其《全集》编者尽力搜求而未获,有已失传的可能。《养新录》卷八《四川制置》《沿江制置》《两淮制置》《京湖制置》等条[6]209-218,其实亦可视为《年表》,有助于南宋史特别是制置使制度的研究。所著《宋奉使诸臣年表》[6]1142-1163为后人编著《宋辽交聘考》、《宋辽聘使表考稿》打下了基础。
四是重视历史人物的籍贯、官爵、著作等生平事迹,编撰《年谱》和《疑年录》。钱氏著有《陆放翁先生(游)年谱》《洪文惠公(适)年谱》《洪文敏公(迈)年谱》《王深宁先生(应麟)年谱》,谱主都是他崇敬的人物。为帮助记忆,钱氏自编《疑年录》四卷,书名出自《左传》襄公三十年“有与疑年,使之年”一语,著录历代著名学者300多人的生卒年及年龄,从郑玄到戴震,以生年先后为序。
三 “不谙舆地,犹如瞽史”
“三端”之中,“精舆地”是其重要的一端。钱大昕强调:“读史而不谙舆地,譬犹瞽史之无相也。”[1]405他考证《宋史·地理志》,虽不如聂崇歧后来所著《宋史地理志考异》详尽,但多有独到之处。
其一,动态考述政区演变。钱氏较为具体地探究了宋代路制的前后变化,诸如至道十五路制、咸平十八路制、熙宁二十三路制、元丰回归十八路制以及政和二十四路制等等。《宋史·地理志》称:“天圣析为十八(路)。”钱氏《考异》认为此说不确:“川峡四路之分,在真宗咸平四年,见《通鉴长编》。”[1]974-975其《养新录》卷八,与政治、军事等大势态相结合,考述了四川宣抚司的设立及其治所的前后变迁,诸如由秦州迁阆中、迁河池、迁利州、迁成都、迁兴州、再迁利州、迁兴元府等等。南宋京湖路之设,为《宋史·地理志》所不载,钱氏补充道:“宋初有荆湖南、北路。南渡以后,中原尽失。唯京西之襄阳府、随州、枣阳、光化、信阳军尚唯宋土,故有京湖路之称。盖合京西、湖北为一路也。”[6]208,219钱氏《地名考异》一书《熙宁辟土》、《绍圣三年八月至元符二年冬》等条[7]93考述宋夏边界的变化;同书《宋南渡后与金分界》[7]91-93、《宋末招降中原诸郡》等条[7]82是对宋金、宋蒙边界的动态考察。如《熙宁辟土》条称:“种谔先取绥州,韩绛继取银州,王韶取熙河,李宪取兰州,沈括取葭芦、米脂、浮图、安疆等砦。”[7]93言简意赅,概括性强。
其二,考述有关重要制度。限于篇幅,略举五种。一是守臣兼职。钱氏《考异》称:“予见石刻,知兖州孔道辅结衔云‘提举兖、郓、濮、齐州、清平军兵马衣甲巡检公事’。盖宋时诸州守臣例兼兵职。”[4]975-976随即举出佐证达数十例。钱氏讲到守臣兼职之处还多,如:“太原守臣,例兼并、代、泽、潞、岚、石路都总管,又兼监牧使。”[4]791监牧使不是兵职,可见守臣兼职之广。二是路有数类。《养新录》卷十一《分天下为路》又称:“《(宋史·地理)志》所云路者,以转运使所辖言之。若庆历元年,分陕西沿边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八年,河北置大名、高阳关、真定、定州四路。熙宁五年,陕西又置熙河路。此特为军事而设,每路设安抚使兼马步军都部署。其民事仍领于转运司,故不在十八路、廿三路之数。初陕西只有一转运司,及熙宁收熙河路,乃分转运司为二:一治永兴军,曰永兴军路,鄜延、环庆属焉;一治秦州,曰秦凤路,秦凤、泾原、熙河属焉。《志》于陕西路叙次五路沿革不甚了了,读史者益致茫昧矣。”[6]290-201宋代的路尚不止转运司路、安抚司路两种。同书卷十《帅漕宪仓》:宋“有帅、漕、宪、仓四司”,“帅谓安抚司,漕谓转运司,宪谓提点刑狱司,仓谓提举常平司”[6]277-278,帅、漕、宪、仓四者可互兼。三是州分四等。钱氏《考异》卷六十九称:“宋制,州有四等:曰节度州,曰防御州,曰团练州,曰刺史州。《志》称‘军事’者,即刺史也。州之幕职官,例称‘军事推官’、‘军事判官’,故《志》称‘军事’。《春明退朝录》云:‘节度州为三品’,刺史州为五品。’以此推之,防御、团练州必皆四品矣。”[4]9774宋代州一级另有一种四等制。钱氏指出:“宋时牧守又有府、州、军、监四等。而军、监在州之下,守臣以知军(恐应加‘知监’二字)系衔。如京东之淮阳军、京西之信阳军、淮南之盱眙军、浙西之江阴军。此则唐以前所未有。”[6]242四是军有两种。钱氏《考异》云:“宋时称军者有二等:一为节度军号,以宠大州;一为小郡之称,大约由县升军,由军升州,如北海军后升潍州是也。军名虽同,而品秩大小迥殊。”[4]975因不知军有两种,以致将“升州为军”误会为“改州为军”[6]176。五是州、郡并称。《咸淳毗陵志》云:“唐制,郡刺史带团练守捉使,所置幕曰团练判官、团练推官。国初诸郡,或不置刺史,置权知州事,则曰军事判官、军事推官。毗陵自开宝入版图,守臣曰权知州。初置判官。天圣六年,增置推官。然结衔犹带团练字,盖铨司因旧也。”钱氏引用之后,接着说:“以是推之,苏子瞻除常州团练副使,亦铨司沿唐故事,不考之失也。”[4]979因不知宋代州、郡并称,凡州均保留唐代郡名,以致有升州为郡的误会。《元史·地理志》:“霸州,宋升永清郡。”钱氏案曰:“宋承后周之旧,亦为霸州。政和三年,赐郡名曰永清。盖宋时诸州皆有郡名,以为封爵之号。其郡名皆依唐旧。若五代及辽增置之州,向无郡名,故政和中依例赐之,初非升州为郡。”[4]1228
其三,揭示几种常见现象。一是年号地名。《养新录》称:“吾邑本昆山,宋宁宗嘉定十五年置县,以年号为名。考古以县为名者,唐有宝应、至德、光化,五代有长兴,宋乾德、兴国、淳化、咸平、祥符、崇宁、政和、庆元、宝庆。(赣州之会昌县置于宋,非因年号得名。)又有以年为府名者,则唐之兴元,宋之绍兴、庆元、咸淳是也。(蜀之嘉定府,改名在嘉定纪元之前,非因年而改名。)以年名州者,则宋之太平与兴国是也。”[6]192二是异地同名。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三《州县名同》曰:“国朝之制,州名或同,则增一字以别之。若河北有雄州、恩州,故广东者增南字。蜀有剑州,故福建者亦增南字。以至西和、西安州亦然。若县邑则不问,今河南、静江府、巩州皆有永宁县,饶、卭、衡州皆有安仁县,……”钱氏征引后,补述道:“洪氏所举,尚遗金、绵之石泉,滁、汀之清流,潭、庆、渭之安化,……难免挂漏之讥矣。”[6]307-308钱氏还总结出某些较为特殊的现象,在《地名考异》一书中有《县名互易》《一县两分》《府县同名而异属》《郡县同名不同治》等条。《县名互易》称:“宋大中祥符四年,棣州清河水溢,坏州城,以厌次与阳信互易其地,徙州治厌次。”[7]53三是避讳改名。《养新录》列举历代因避讳而改郡县名,仅宋代部分即达数十例:“宋太祖之祖名敬,改敬州为梅州、石镜县曰石照。父名宏殷,改宏农县曰常农(本曰恒农,史家避真宗讳改)、殷城县曰商城、溵水县曰商水。……”[6]303-304
四 “不通官制,涉笔便误”
钱大昕考证《宋史》,用力最勤、贡献最多者,首推“通官制”。仅以《考异》一书为例,针对《宋史·职官志》的篇幅达1卷半、73条之多,其份量大大超过考述《唐书·百官志》(仅半卷、32条)、《旧唐书·职官志》(仅两条)的总和,足见其对复杂多变的宋代官制何等重视。钱氏有关研究成果,而今大多早已近乎于常识,仅略举数端。
其一,关于差遣制度的形成及改革。钱氏的主要观点有六。一是差遣系宋代独特的一项职官制度。其《答袁简斋(枚)书》系探讨官制之名篇,《书》云:“差遣之名,惟宋时有之。宋时,百官除授有官、有职、有差遣。如东坡以学士知定州。知州事,差遣也。端明殿学士,职也。朝奉郎,则官也。差遣罢而官、职尚存,职落而官如故。”[1]611-613二是差遣渊源于唐天宝以后,但当时尚未成为定制。《旧唐书·职官志》:节度使副等“皆天宝后置,检讨未见品秩”。钱氏《考异》案曰:“节度、采访、观察、防御、团练、经略、招讨诸使,皆无品秩,故常带省台寺监长官衔,以寄官资之崇卑。其僚属或出朝命,或自辟举,亦皆差遣无品秩。如使有迁代,则幕僚亦随而罢,非若刺史、县令之有定员、有定品也。此外,如元帅、都统、盐铁、转运、延资库诸使,无不皆然。即内而翰林学士、弘文、集贤、史馆诸职,亦系差遣无品秩,故常假以它官。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不特此也,宰相之职所云‘平章事’者,亦无品秩,自一二品至三四五品官,皆得与闻国政。故有同居政地,而品秩悬殊者。罢政则复其本班。盖平章事,亦职而非官也。《志》谓节度等检校未见品秩,似未达于官制。”[4]849三是宋代检校官的形成与差遣制度有关,同样起源于中唐。《答袁简斋书》云:“唐初所谓检校者,虽非正授,却办本职事。如检校侍中、检校中书令、检校纳言、检校左相之类,皆列于《宰相表》与真授者无别。而宇文士及检校凉州都督,魏元忠检校并州长史,亦是实履其任。盖内外各官,皆得有检校,若今署事矣。……《宋史》所列检校官一十有九,盖即沿唐末之制矣。公、师之班,首太师,次太尉,次太傅,次太保,次司徒,次司空。王建由检校太师才迁司徒,曹佾以检校太师守司徒,又数年始除守太保,然则检校太师尚在真三公之下也。”四是因官、职、差遣分离而出现“行、守、试”与“判、知、权发遣、权知”之分。《答袁简斋书》解释道:“若夫行、守、试三者,则以官与职之高下而别。《长编》载元丰四年诏:‘自今除授职事官,并以寄禄官品高下为法,高一品者为行,下一品者为守,二品以下为试,品同者不用行、守、试。’”赓即以金石文献为证:“偶检柳公权书《苻璘碑》,其题云‘辅国大将军行左神策军将军’,辅国大将军阶正二品,左神策将军官从三品,此高一品为行之证也。其结衔云‘朝议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朝议大夫阶正五品,侍郎官正四品,此下一品为守之证也。”接着又说:“五代时,李琪为宰相,所私吏当得试官,琪改试为守,遂为同官所纠。此试不如守之证也。”随后讨论:“判与知之分,则宋次道《春明退朝录》所云:‘品同为知,隔品为判’者得之。宋初曹翰以观察使判颍州,盖用隔品为判之例。后来惟辅臣及官仆射以上领州府事称判,其余皆称知,不称判矣。判知之外,又有云权发遣者,则以其资轻而骤进,故于结衔稍示区别。程大昌云‘以知县资序隔二等而作州者,谓之权发遣,以通判资序隔一等而作州者谓之权知’是也。宋制六曹尚书从二品,而权尚书则正三品,侍郎从三品,而权侍郎从四品,则权知与知亦大有别矣。”[1]611-613五是元丰官制改革的要害在于变散官(即阶官)为寄禄官,变寄禄官为职事官,以职事官取代差遣。《潜研堂集》文集卷二十八《又(跋宋史)》云:“宋之官制,前后不同。元丰以前,所云尚书、侍郎、给事、谏议、诸卿监、郎中、员外郎之属,皆有其名而不任其职,谓之寄禄官,以为叙迁之阶而已。元丰以后,尚书、侍郎等皆为职事官,而以旧所置散官为寄禄官。故元丰以后之金紫光禄大夫犹前之吏部尚书也,银青光禄大夫,犹前之五部尚书也。正议大夫犹前之六部侍郎也,太中大夫犹前之谏议大夫也,朝请、朝散、朝奉郎犹前之诸曹员外郎也。”[1]496六是元修《宋史》因不知宋代官制的前后变化所由而导致不少错误。《又(跋宋史)》称:“元人修史者,未审宋时更改之由,其撰诸臣列传也,误以尚书侍郎等为职事官而一概存之,误以大夫、郎为散官而多删去之。不知元丰以前所云散官,不过如勋、封、功臣食邑之类,徒为文具,无足重轻,史家固宜从略。其后改为寄禄,以校官资之崇卑,则亦不轻矣。若谓寄禄不必书,则如尚书、侍郎等在宋初亦是寄禄之阶,又何须一一具载耶?愚意散官不必书,而寄禄官不可不书,当以元丰三年为限断。”[1]496这些观点是否精准,而今或有可商之处,但在当年极具新意。
其二,关于宰相制度及其变迁。其要点有四。一是北宋前期的宰相通常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性质为差遣,最早出现于中唐以后。钱氏《再答袁简斋书》云:“以侍中、中书令为宰相,此二官者皆三品也,然它官亦有三品阶,故入相而官未至侍中、中书令者,必云同中书门下三品,其资望稍轻者则云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历以后,升侍中、中书令为二品。自后入相者,但云平章事,无同三品之名矣。当时除三公者,固不乏人,未尝以三品为限。但三公不必知政事,而居宰相者不皆二品以上官。中叶以降,并有除侍中、中书令而不入政府者矣。”[1]614-615其文集卷十三《答问》称:“唐初三省长官并为宰相。及睿宗以后,但以中书、门下为政府。尚书左右仆射,品秩虽崇,而不加平章事,即不得与政事。”[1]198-199二是对于宰相的“议政之所”和“宰相印”,钱氏有说明。“问:中书、门下长官既均为宰相,又有它官而预平章者,则必有议政之所,将别设一署乎?”钱氏答曰:“此所谓政事堂也。《旧唐书·职官志》云:‘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印也。’《新唐书》亦载其事于《裴炎传》中。”接着便以文物为证:“予家藏后唐升元观牒石,刻有数印,其文曰‘中书门下之印’,盖宰相印也。”[1]199三是宋代宰相的名称前后变化颇多,最重要者为元丰官制改革,不设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三省置侍中、中书令、尚书令而一般虚而不授予人,以左右仆射为宰相,设中书、门下侍郎、尚书左右丞,取代参知政事。《答袁简斋书》以文彦博等人任职为例,略作补充和说明:“元祐元年,文彦博落致仕,加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潞公本以守太师致仕,今复召用,故有落致仕之命。同一落也,落职则为罢免,落致仕则为复用。其云落者,谓结衔内去此字也。元丰三年,彦博落兼侍中,除守太尉,盖其时改官制,以侍中、中书令为宰相,职事官非退闲者所宜授,故落侍中而进太尉以宠之,亦非罢免之谓也。富弼、吕公著之守司空,与蔡京之司空,皆真三公也。而京不云守,则尤贵。”[1]611-613四是南宋时宰相称左、右丞相,但不始于高宗时。《宋史·职官志》载:“南渡后,置左、右丞相省,仆射不置。”《考异》案曰:“南渡初,亦仍左、右仆射之名,至乾道八年乃改为丞相耳。《志》所云未核。”[4]994此后,终南宋之世基本不变。
其三,关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与知制诰。以下三点值得重温。一是这三种官职的关联与区别,钱氏在两条《答问》中讲述得相当详尽。第一问是:“唐宋以翰林学士掌内制,中书舍人掌外制,两制皆清要之职,而内制尤重,顾其叙迁,往往由学士而进舍人,此何说也?”钱氏答曰:“唐自中叶以后,常以它官知制诰,行中书舍人之职,其真除舍人者少矣。宋初专以知制诰掌外制,其除中书舍人者皆不任职,所谓寄禄也。翰林学士虽华选,而初无品秩,常假它官以寄禄,故学士初入或畿县尉,或拾遗、补阙,或诸曹郎中、员外郎。久之,迁中书舍人、给事中,亦有至侍郎以上者,皆食其禄,不任其职。舍人秩五品,为两省清望官,故学士叙迁,必历此阶,非兼掌外制,亦非由内制改外制也。凡两制官,结衔云翰林学士知制诰者,内制也。其但称知制诰者,外制也。其云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者,以舍人为寄禄官,仍内制也。其但称中书舍人者,外制也。唐末赵光逢以中书舍人为翰林学士,其弟光裔亦由膳部郎中知制诰,对掌内外命书,士歆羡之。后晋时,陶谷以虞部员外郎知制诰,会晋祖废翰林学士,遂兼掌内外制。周广顺中,窦俨以主客员外郎知制诰,其兄仪自阁下入翰林,兄弟同日拜命,分居两制,时人荣之。又扈蒙以右拾遗知制诰,从弟载时为翰林学士,兄弟并掌内外制,时称‘二扈’。盖知制诰与翰林学士对掌两制,唐五代及宋元丰以前,皆然矣。元丰改官制,始正中书舍人之名,与学士对掌两制。资浅者则称直学士院、直舍人院,亦有称权直者。嗣后无单除知制诰者矣。”第二问是:“翰林学士带知制诰,唐五代及宋皆然,又有翰林学士而结衔无知制诰者何也?”钱氏再答曰:“学士不带知制诰有二例,洪遵《翰苑遗事》云:‘唐以来至国朝熙宁,官至中书舍人则不带三字’,元微之《承旨学士院记》题衔称‘中大夫行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续翰林志》题衔称‘翰林学士承旨、朝请大夫、中书舍人’,皆以官至舍人,故不带知制诰。此一例也。徐度《却埽编》云:‘翰林学士,祖宗时多有别领它官,如开封府、三司使之类,则不复归院供视草之职,故衔内必带知制诰则掌诏命者也。’盖宋初学士六员,故有以学士而别领它职者,其结衔亦不带知制诰,此又一例也。元丰以后,中书舍人不为寄禄官,则无以学士带舍人者矣。南渡以后,直学士院者不过二三人,即学士之名亦不轻授,则亦无以学士领它职者矣。”[1]199-200二是对于宋代翰林学士制度,钱氏有重要的补充和说明。其《跋中兴学士院题名》云:“唐时翰林为掌制之地,选工于文学者,以它官入直,无不除学士者。其久次则为承旨学士,职要而无品秩,当时但以为差遣,非正官也。宋初亦沿唐制,太祖、太宗朝,间有以它官直学士院者,然不常设。元丰改官制以后,学士之名渐重。于是有直学士院、权直学士院、翰林院权直之称。南渡以后,真除学士者益鲜矣。”以上或可称为学士地位变迁简史。随后论及学士员额的前后变化:“《新唐书》云学士无定员,然白居易诗已有‘同时六学士’之句;《五代会要》载开运元年勅,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旧分为两制,各置六员,是唐五代皆以六员为额也。宋初学士亦六员。至和初,……学士遂有七人。南渡,学士不轻授,多以它官直院。然在院不过二员或三员。其员额不审何时裁省,史家失于讨论,亦疏漏也。后读洪文安《翰苑遗事》,称元祐元年七月,诏从承旨邓温伯之请,学士如独员,每两日免一宿,候有双员,即依故事则,其时学士之员已不多矣。”[1]509-510三是翰林学士与馆职、殿阁学士迥然不同,但又易于混淆。钱氏认为,“苏门四学士”之称,就容易造成误会。他说:“黄鲁直、秦少游、张文潜、晁无咎称‘苏门四学士’。宋沿唐故事,馆职皆得称学士。鲁直官著作郎、秘书丞,少游官秘书省正字,文潜官著作郎,无咎官著作郎,皆馆职,(元丰改官制,以秘书省官为馆职。)故有学士之称,不特非翰林学士,亦非殿阁诸学士也。唯学士为馆阁通称,故翰林学士特称内翰以别之。”[6]203-204《宋史·职官志》载:“翰林资政保和殿大学士。”即是将翰林学士与殿阁大学士混同之一例。钱氏《考异》指出:“翰林无大学士之称,此‘翰林’二字衍文。”[4]1005《养新录》又称:“宋初,昭文馆、集贤殿大学士皆宰相领之,盖沿唐五代之旧。其后置观文殿、资政殿大学士,虽不任事,亦以前宰执充,余官不得与焉。”[6]269-270并在《跋麟台故事》中不烦其详地申说道:“宋时翰林与馆职各有司存。钱文僖之《金坡遗事》、李昌武之《翰林杂记》、洪文安之《翰苑群书》、何同叔之《中兴学士院题名》,此翰林故事也。宋匪躬之《馆阁录》、罗畸之《蓬山志》、程俱之《麟台故事》、陈骙之《中兴馆阁录》,此馆职故事也。馆职亦呼学士,乃侪辈相尊之称。如武臣例称太尉耳,非真学士也。翰林掌制诰,馆职典图籍,班秩不同,职事亦异。然馆职之名亦再变。宋初沿唐旧,以昭文、国史、集贤为三馆。昭文有学士,有直馆;集贤有学士,有直院,有校理;史馆有修撰,有直馆,有校勘。学士不常置,自直馆以下皆馆职也。太宗时又建秘阁,设直阁、校理、校勘,与三馆并列,故有馆阁之称。元丰改官制,罢三馆职事,归之于秘书省。其官曰监,曰少监,曰丞,曰秘书郎,曰著作郎,曰著作佐郎,曰校书郎,曰正字,自丞郎以下皆为馆职矣。若元丰以前,校书、正字、著作但为虚衔,其秩甚卑,州郡幕僚与知县皆得带之,非若后来之清要也。前后官称既改,后之言官制者漫不能辩,因读此书为略叙之。唐时尝改秘书为麟台,故北山以名其书。”[1]508-509
其四,关于官府、官员的名称、合称、简称与俗称。名称,如升朝官、京官。《养新录》先引《宋史·选举志》:“前代朝官自一品以下皆曰常参官,其未常参者曰未常参官。”然后补充道:“宋目常参者曰朝官,秘书郎以下未常参者曰京官。”再引《老学庵笔记》:“国初,以常参官预朝谒,故谓之朝官,而未预者曰京官。元丰官制行,以通直郎以上朝预宴坐,仍谓之升朝官。而按唐制去京官之名,凡条制及吏牍,止谓之承务郎以上,然俗犹谓之京官。”钱氏案曰:“元丰以前,秘书省著作佐郎、大理寺丞、光禄寺丞、卫尉寺丞、将作监丞、大理评事太常寺太祝、奉礼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皆京官也。元丰改制以宣教、(本宣德,政和改)宣义、承事、承奉、承务郎为京官。京官之下则为选人,有七资四等之差。(崇宁中,改选人七阶为承直、儒林、文材、从事、通仕、登仕、将仕郎。政和以从政、修职、迪功易通仕、登仕、将仕三阶。其通仕、登仕、将仕三阶系奏补未岀身人)。”[6]272又如前行、中行、后行和头司、子司。《养新录》称:“唐宋制,六部有前行、中行、后行三等,而廿四司有头司、子司之称。”并引《唐会要》等书较为具体地予以说明。《唐会要》:“故事以兵、吏及左右司为前行,刑、户为中行,工、礼为后行。每行各管四司,而以本行名为头司,余为子司。(如吏部为头司,司勋、司封、考功为子司。)五部皆仿此。显庆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户部尚书为度支尚书,侍郎亦准此,遂以度支为头司,户部为子司。至龙朔二年二月四日复旧次第。”《海录碎事》:“唐制郎官前行为要,后行为闲。”《南部新书》:“先天中,王上客为御史,自以才望清华当入省台,望前行,忽除膳部员外郎,微有惋怅。吏部郎中张敬忠咏曰:‘有意嫌兵部,专心望考功。谁知脚蹭蹬,却落省墙东。’盖膳部在省最东北隅也。(膳部为后行,又在礼部四司之末)。”[6]272-273合称,如吏部七司。《养新录》称:“唐制,六部各置四司。宋元丰改官制以后,分尚书左右选、侍郎左右选,各置郎官。南渡后,遂有尚左、尚右、侍左、侍右之称,皆吏部一司所分也。并司勋、司封、考功。是为七司。”[6]273又如四总领。《养新录》称:“绍兴十一年,收诸帅兵以为御前军,屯驻之所皆置总领一人,以朝臣为之,叙位在转运副使之上。镇江诸军钱粮,淮东总领掌之;建康池州诸军钱粮,淮西总领掌之;鄂州荆南江州诸军钱粮,湖广总领掌之;兴元兴州钱粮,四川总领掌之。(四川总领初称总领四川宣抚司钱粮,绍兴十八年改四川总领。)总领财赋所,或谓之总所,亦称饷所,又谓之饷司。(《鹤山集》中往往有此名目)。”[6]278再如十都统。《养新录》称:“绍兴十一年,张俊、韩世忠、岳飞除枢密使副入觐。俊首纳所部兵,乃分命三大帅副校各统所部,自为一军,更其衔曰统制御前军马。镇江大军即韩世忠旧部,建康大军即张俊旧部,鄂州大军即岳飞旧部也,并荆南府、江州、池州皆有御前军,凡六统制。十九年,又改汉沔两大将为御前诸军。吴璘称利州西路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在兴州),杨政称利州东路都统制(在兴元),金州但以知州兼节制。所谓利路三大屯也,而兴州之事权特重。及吴曦叛后,改兴州为沔州,又分兴州十军为沔利二军,移沔州副都统司于利州。沔州除都统制不除副,利州除副都统制不除正。天下有十都统矣。”[6]279简称如尚左、尚右、侍左、侍右。《养新录》引《文献通考》:“宋朝典选之制,自分为四:文选二,曰审官东院,曰流内铨;武选二,曰审官西院,曰三班院。元丰定制,以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流内铨为侍郎左选,三班院为侍郎右选。旧制,吏部除侍郎二员,分典左右选,总称史部侍郎,间命官兼摄,惟称左选侍郎或右选而已。绍熙三年,谢深甫、张叔椿兼摄,始有侍左侍郎、侍右侍郎之称。既而林大中、沈揆擢贰尚书,则侍左、侍右径入除目,相承不改矣。……”[6]273-274俗称,如抚干、运干等等。《养新录》称:“宋人文集、小说称人官名往往割取两字,盖流俗相称之词。如云‘抚干’者,安抚司干办公事也;‘运干’者,转运司干办公事也;‘提干’者,提刑司干办公事也;‘总干’者,总领所干办公事也;‘制机’者,制置司主管机宜文字也;‘帅机’者,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也;‘帅准’者,安抚司准备差遣也。”[6]281又如阁老、堂老。钱氏《恒言录》云:“中书舍人以久次者一人为阁老,判本省杂事”,“宰相相呼为堂老,两省相呼为阁老”[8]108。又如老爷、爷爷。《恒言录》云:“今百姓称官府曰老爷。爷者呼父之称,以是称者尊之也。《宋史·宗泽传》:北方闻其名,常尊惮之,对南人言,必曰‘宗爷爷’。《岳飞传》:金所籍兵相谓曰‘此岳爷爷军’,争来降附。《孟宗政传》:金人呼为‘孟爷爷’。”[8]110-111钱氏上述阐释文字大多简明易懂。
五 若干领域的开路人
对于钱大昕的学问,我辈或许知之不详,甚至有所“冷遇”。然而老一辈则大不相同,钱氏在他们心目中威望高,其学问对他们影响极大。如陈垣“早年治学,服膺钱氏”[5]卷首,称他为“清朝唯一的史学家”[9]237;陈寅恪将钱氏盛赞为“清代史学家第一人”[10]26。陈垣强调:钱大昕文集“不可不一看,此近代学术之泉源也”[11]6。其名著《史讳举例》是为纪念钱氏诞生二百周年而作,他认为:“前人可称做避讳学专家的”,“应推钱竹汀先生”;并称,《史讳举例》“资料大半是采自钱先生所著的书”[9]237-238。
如上文所述,钱大昕考证《宋史》堪称“第一人”,其后继者为数甚多。钱氏对《宋史·艺文志》很是不满,不仅“重复讹舛,较前史为甚”,而且脱漏甚多,“宋人撰述不见于《志》者,又复不胜枚举”[6]186-188。陈乐素继钱氏之后,倾其大半生之心血,著《宋史艺文志考证》;其高足徐规力图将考证范围拓展到《宋史》全书,80年代曾主持浙江省“七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宋史》补正”,其主要成果包括何忠礼著《宋史选举志补正》、梁太济与包伟民著《宋史食货志补正》、龚延明著《宋史职官志补正》等等。龚延明说:“钱氏之《考异》实已为后人草创了体例、规模”,“其启迪后人之功,未可泯灭”[12]11。在众多考证《宋史》的著述中,以邓广铭40年代所著《〈宋史·职官志〉考正》最负盛名,但因邓氏未曾言及与钱氏有无关联,不便臆测。
陈垣将钱大昕的学问视为“近代学术之泉源”。仅以宋史为例,钱氏便是不少领域的先行者。如晚宋史研究,学界一般将张荫麟视为首倡者,其实张氏《南宋亡国史补》[13]105-122开篇便引证钱氏的有关论述,如“《宋史》于南渡季年臣僚褒贬多不可信”等,以示钱氏是其晚宋史研究的指路人。又如《金史》有《交聘表》而《辽史》无,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序例》明言,首先着手解决问题的是钱氏《宋奉使诸臣年表》;聂崇歧《宋辽交聘考》同样是以钱氏《年表》为基础。人们或许以为南宋末年四川抗蒙山城研究的开创者是姚从吾,其实钱大昕对此已有研究。钱氏《考异》称:“宋末,川蜀诸州多依险为治。如遂宁府权治蓬溪砦,顺庆府徙治青居山,叙州徙治登高山,合州徙治钓鱼山,渠州徙治礼义山,广安军徙治大良平,富顺监徙治虎头山。阆州徙治大获山,政州徙治雍村,涪州移治三台山,皆载于《志》。而潼川府之治长宁山,隆庆府之治苦竹隘,蓬州之治运山,《志》独遗之。”[4]980-981其涉及面较广,已不限于合州钓鱼城。《地名考异·宋末州郡徙治》有所补充,如:“施州徙治倚子山,开庆初,城东十五里。”“泸州,嘉熙三年筑合江之榕山,在县南五里。再筑江安之三江碛,在江安县城西,或云即绵水口也。四年又筑合江之安乐山为城,在县西五里。淳祐三年又城神臂厓以守,在州东八十里。”[7]97-99《养新录》又称:虎啸城与大良平“为宋元交争之地,其筑城始末历历可考”;宝祐七年,“遣便宜都总帅汪惟正戍青居,与大获、运山、大良平称四帅府”[6]296-297。姚从吾对这项研究有所推进,将《养新录》卷八《四川制置》所列南宋四川制置使补足即是一例[14]152-153。
不必讳言,《疑年录》系钱大昕的不成功之作。因其性质为自编以备自用,生前未定稿,死后由其弟子刊出,以致内容粗糙,错误不少。余嘉锡著《疑年录稽疑》为其纠错正误。然而,钱氏此书开创了一种新体裁③。此后,吴修《续疑年录》、钱椒《补疑年录》、陆心源《三续疑年录》、朱昌燕《四续疑年录》等书以及陈垣《释氏疑年录》、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相继问世。贾贵荣、殷梦霞辑《疑年录集成》,收录同类著作达17种之多[15]。
六 “重修不如考订”
金毓黻说:“清代诸贤多有志于改修《宋史》。”[16]166钱大昕自当名列其中,他对元朝官修《宋史》深表不满。钱氏认为“繁芜”是《宋史》的一大缺陷:“复重列之,连篇累牍,皆可省也。”[4]1006更为严重的是“缺略”:“世人读《宋史》者,多病其繁芜,予独病其缺略,缺略之患甚于繁芜。”[1]518此言可谓深中肯綮,《宋史》缺传问题很突出,尤以南宋为甚。王德毅有统计:“《循吏传》1卷,载12人,南宋无一人。《儒林传》8卷,北宋31人,南宋46人;《文苑传》7卷,北宋85人,南宋仅载陈与义、汪藻等11人;二者合计北宋116人,南宋57人,为二比一。至于一般臣僚,北宋109卷,1155人,南宋68卷,466人,南宋为北宋的四分之一。”[17]282前面已经说到,钱氏对元朝官修《宋史》最不满意的篇章是《艺文志》,最不满意的时段是南宋特别是宁宗以后。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钱大昕对《宋史》最不满的观点是:片面尊崇程朱理学,并以此作为标准评价宋代人物。其主要表现可归纳为“三个反对”。
其一,反对立《道学传》。《宋史》的做法是:“创为《道学传》,列于《儒林》之前,以尊周、二程、张、邵、朱六子,而程、朱之门人附见焉。”钱氏不解之处甚多,如:“夫刘彦冲、胡原仲、刘致中,朱子之师也,而不与;吕东莱、陆子静,朱子之友也,而不与。其意以为非亲受业于程、朱者,皆旁支也,不得以干正统也,而独进张南轩(栻)一人。南轩非受业于程氏者也,南轩与东莱俱为朱子同志,进南轩而屏东莱。”概而言之:“彼修宋史者,徒知尊道学而未知其所以尊也。”他的主张是:“周、程、张、朱五子宜合为一传,而于论赞中著其直接圣贤之宗旨,不必别之曰‘道学’也。自五子而外,则入之《儒林》可矣。”[1]494-496
其二,反对美化张浚。钱氏一再指出《宋史》因张栻系道学中坚而为其父张浚隐恶扬善:“史家以其子为道学宗,因于浚多溢美之词”[1]1091,“至以诸葛武侯相况”;钱氏则反其道而行之,力图将张浚塑造为“生平用兵,有败无胜”的常败指挥官,历数其富平之败、淮西之败、符离之败等劣绩,谴责他“竭生民之膏脂,糜生民之血肉,有损于邦国,无益于君亲”[1]35-36,并指斥其人品低下,“党于黄汪,力攻李忠定(纲),几欲置之死地”[6]200-201。钱氏对张浚的总体评论是:“志广而才疏,多大言而少成事。”[1]35平心而论,大体属实,但对其“志广”一面似应给予更多一点肯定。
其三,反对将韩侂胄置于《奸臣传》。《宋史·史弥远传》称:“台谏给舍交章论驳,侂胄乃就诛。”钱氏《考异》案曰:“史家欲宽弥远擅杀之罪,故为此语。”又云:“弥远之奸倍于侂胄,而独不预奸臣之列,《传》于谋废济王事并讳而不书,尚得云直笔乎?推原其故,则以侂胄禁伪学,而弥远弛其禁也。弥远得政,祇欲反侂胄之局,虽秦桧之奸慝众著,尚且为之昭雪,岂能崇尚道学者?使朱元晦尚存,未必不排而去之。史臣徒以门户之见,上下其手,可谓无识矣。”[4]1108言犹未尽其意,在《养新录》中仍愤愤不平:“史弥远握权卅余年,威焰甚于京、桧,且有废立大罪,而不预奸臣之列。”[6]183且有诗云:“十年富贵老平原,一着残棋一局翻。毕竟未忘青盖辱,九京不愧魏公孙。……成败论人亦可嗤,谁持秦镜照须眉。如何一卷《奸臣传》,却漏吞舟史太师。”[1]1164
钱大昕评论历史人物,虽非毫无见识,但从总体上看,算不上高明。如对王安石的评论就相当偏颇,他指斥王安石“平生好为大言欺当世”,其《王安石论》全面恶评王安石,无非是为范纯仁所言“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1]32-33作注释而已。他断言:“宋之亡始于安石之新法,终于朱勔之进奉”[1]286,“安石非独得罪于宋朝,实得罪于名教”[6]195;并做诗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两朝定策数安阳,晚节黄花独自香。何事裕陵亲政日,翻将国事付貛郎。”[1]1164但钱氏不赞成将王安石视为奸臣:“王安石之立新法,引佥人,虽兆宋祸,而本无奸邪之心。”“以奸臣目之,未免太甚矣。”[1]497-498
钱大昕不仅对元朝官修《宋史》不满,而且认为此后各种重修《宋史》均有重大缺失,如薛应旂《宋元通鉴》“未能寻其要领”,柯维骐《宋史新编》“见闻未广,有史才而无史学”[1]497,陈黄中《宋史稿》“前后义例不能划一,《纪》《传》无论赞,《志》无总序”[1]498等。于是,他有意亲自动手重修宋史,只因忙于重修《元史》而无瑕顾及。在他启示下,邵晋涵著《南都事略》,钱氏及章学诚均参与其事。邵氏采纳钱氏不少主张,如改修宋史当“自南渡始”,不立《道学传》,乃至仿效王偁《东都事略》之例,书名不称“南宋史”或“南宋书”而称《南都事略》。此书或未竟其业,或已失传,仅存“《儒学》《文艺》《隐逸》三传目录”[6]584-585。梁启超称:“不得不为学术界痛惜也。”[3]281而本人则对《南都事略》无太多期待。对于当今大多数宋史研究者来说,明清学者重修的各种宋史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仅是史料而已。重修宋史的致命通病在于不具有史料所应有的原始性,因而参考价值不大,绝无取代元朝官修《宋史》的可能。在同类书籍中,陆心源《宋史翼》价值较大,原因在于抓住《宋史》缺传这一要害,“补《宋史》缺传949人”④,“利用百数十种史子集部的典籍”[17],具有史料汇编的性质,原始性较强。明清重修的《宋史》大多渐渐被人遗忘,而考订《宋史》的钱大昕著述历300余年之久,至今仍熠熠生辉,可见其成就与影响之大。
(附言:本文由2017年10月25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讲稿修订压缩而成,感谢北大文研院提供的支持!学友成荫、陈鹤对本文有所贡献!)
注释:
①柴德赓《王西庄与钱竹汀》一文指出:“以治经的方法治史,又专治史而不专治一经的,应该说竹汀是第一个人。”参见:柴德赓《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第262页。
②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序论》认为:“考诸前人之作,致力于考校《宋史》全书者,有之。但今所能及见者,无多。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之‘宋史’部分。”(参见: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页)考证《宋史》并非前无他人,如方以智《通雅》讨论宋代制度之处便不少,但就系统性而言,与钱大昕差距较大。此事承蒙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胡斌同学告知。
③卞孝萱在《陈垣与〈释氏疑年录〉》一文中说:“疑年录是清人钱大昕所开创的一种新史书,专门记载名人的生年、卒年和岁数。”参见:《卞孝萱文集》第5卷,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38-154页。
④罗炳良在《〈宋史〉研究·前言》中说:陆心源《宋史翼》“采集宋人文集、杂著、年谱、族谱、方志等史料,增补列传845人,以补《宋史》之缺”(罗炳良主编《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第八卷《〈宋史〉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12页),其统计数字与王德毅稍有出入。
参考文献:
[1]钱大昕.潜研堂集[M].吕友仁,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王瑞明.钱大昕考订《宋史》的卓越成绩[C]//顾吉辰.钱大昕研究.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书店,1985.
[4]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刘乃和.题词[C]//顾吉辰.钱大昕研究.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6]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G]//陈文和.嘉定钱大昕全集:第7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7]钱大昕.地名考异[G]//陈文和.嘉定钱大昕全集:第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8]钱大昕.恒言录[G]//陈文和.嘉定钱大昕全集:第8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9]陈垣.史讳举例[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0]陈寅恪.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C]//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1]陈垣.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2]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13]张荫麟.南宋亡国史补[C]//台北宋史座谈会.宋史研究集:第2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4.
[14]姚从吾.余玠评传[C]//台北宋史座谈会.宋史研究集:第4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9.
[15]贾贵荣,殷梦霞.疑年录集成[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16]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7]王德毅.补宋史周麟之传——兼论宋史中的缺传问题[C]//台北宋史座谈会.宋史研究集:第14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