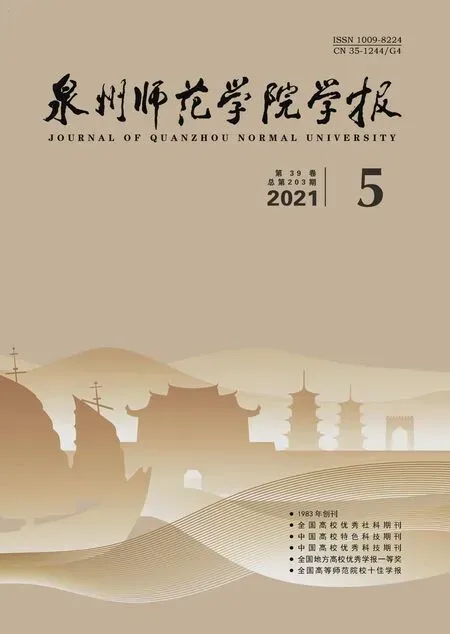论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中的导向问题
2021-01-03黄志军
黄志军
(泉州师范学院 应用科技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文革结束后,1980年《围城》重印,钱锺书及其文学创作成为社会的一个关注热点,众多读者和研究者急切地想要认识钱锺书,虽然钱氏诚恳地劝告“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1]168,但是这样的应对显然不够,“钱迷”们并不买账。实际上此前有关钱氏生平的传述材料和《围城》创作的背景资料的确缺乏,而这与钱氏向来拒绝自传和他传直接相关。1979年钱锺书在致黄裳的信中曾说:“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也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2]417这真是一个智者的见道之语,因为任何事一经他人叙述甚至转述都免不了变形走样,所以他对写自传一事颇为反感。1981年钱氏在《答某记者问》中说:“去年有人叫我写《自传》……我敬谢不敏。回忆,是最靠不住的”[2]581。钱氏拒绝传述自我。在此情况下,彼时中国社科院的领导胡乔木同志建议杨绛写一篇《钱锺书与〈围城〉》,于是1982年7月杨绛写了传述钱氏的重要文章《记钱锺书与〈围城〉》,以“供《围城》的偏爱者参考之用”[1]168。有趣的是,1982年8月钱氏重复道:“我们在……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2]586不过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的开篇即说:“我只据事纪实;锺书读后也承认没有失真。”[1]168实际上自此以后,显然乐于代笔的杨绛后来又写了大量有关钱氏的传述文章。
于慈江在《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一书中写道:“自传(或日记之类),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如何维护自己身后形象的内在冲动的驱使、左右或制约。”[3]288杨绛出于爱惜自己的羽毛、保护钱氏声名以及其他原因而在个别传述内容上尽力持有某种明确的“先在”导向,所以不难理解2013年百余岁的杨绛老人全力阻止拍卖他人手中的钱氏书信手稿。2009年杨绛欣慰地写道:“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锺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有风趣的钱锺书。他的痴气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钱锺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我对全世界所有喜读他作品的人,功莫大焉!”[4]289所以从某一角度来说,杨绛的传述材料帮助杨绛全力维护了钱氏形象,并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钱杨在作品中所寄寓和秉持的某些理念,并成功引导了读者的理解与认同方向。
学术界对钱氏的文学创作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杨绛对钱氏的传述材料基础上的,其中《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对《围城》研究影响重大。然而几十年来,在这篇传述材料中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特别是杨绛在该文中对读者所进行的“先在”导向问题,还有杨绛在其中提示和暗示的一些重要内容等,至今未引起学界的注意,更未获得应有的重视。
一、“痴气”与“忧世伤生”的问题
《记钱锺书与〈围城〉》是一篇逾1.5万字的长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钱锺书写《围城》”,第二部分“写《围城》的钱锺书”。杨绛在全文的结束部分总结道:
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 的 锺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1]192
杨绛这段文字及其表述方式似乎否定了钱氏的著作——除《槐聚诗存》外——具有他写作期间“忧世伤生”的精神烙印,但明确了《围城》是钱氏“痴气”性情的产物与载体。可是钱氏在《围城》序言中明确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5],还在写于同时期的《谈艺录》序中明确该书“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6]即便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杨绛也明确说“《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1]172。显然《围城》的作者同《槐聚诗存》的作者以及《谈艺录》的作者一样都是“‘忧世伤生’的锺书”,况且在那个国难连年的时代书生报国救国的方式之一就是读书著书,钱氏更不例外。然而杨绛却执意要说《围城》是钱氏“痴气”的产物,并为此不惜占用全文一半的篇幅来“论证”这一观点,引导读者也持如是观,显然别有用意。其中一个例证颇为特别:
锺书小时最喜欢玩“石屋里的和尚”……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就是“石屋里的和尚”。……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小孩自言自语,其实是出声的想象。我问他是否编造故事自娱,他却记不得了。这大概也算是“痴气”吧[1]186。
杨绛写儿时锺书玩“石屋里的和尚”游戏,既为了例证她所谓“《围城》是钱氏‘痴气’的产物”这一观点,也为了引导读者认同该观点。其逻辑是:钱氏自幼就会编故事自娱,长大后当然就会编《围城》自娱了,《围城》是钱氏“自娱自乐”的载体,是他思维游戏和文艺游戏的呈现,是他“痴气”的表现,也是他“痴气”作用下的结果。并暗示说钱氏未否定她的看法。
当然这实际上只是杨绛的一家之言,她甚至对这个特定语境里的“痴气”的具体内涵也界定得不够明确。其实杨绛之所以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大费笔墨来铺排钱氏的“痴气”表现,其用心一方面是出于为读者塑造“风趣”的钱氏,让读者喜欢钱氏的“痴气”,另一方面还是希望读者如此看待钱氏及其《围城》创作——“痴气”是钱氏的性情实际并因之而产生了《围城》!
假如杨绛的“痴气”说符合钱氏性情实际,那也只是钱氏内在的与创作灵感和创作冲动有关的创作激情,但并不可以说在此“痴气”的创作激情下《围城》就是“大孩子”认真玩的思维游戏或文艺游戏的产物。杨绛之所以强行将《围城》的创作与“忧世伤生”脱钩而仅与“痴气”捆绑,显然是别有考量。因为在“文革”刚结束不久且政治风气尚不够开化的1980年代初,解放后三十多年来一贯谨慎有加、始终“明哲保身”的杨绛出于继续保护钱氏免遭政治运动的波及,因而不想让《围城》及钱氏的创作行为被读者和研究者挖掘出太多的政治负荷或社会责任意识。所以杨绛在1982年写成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中有意否定《围城》“忧世伤生”的性质,却长篇累牍劝说读者视《围城》为“痴气”满满的钱氏的“痴气”作为,同时以“《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来大力引导读者将《槐聚诗存》视为“‘忧世伤生’的锺书”的创作产物,而颇具宋诗风格的《槐聚诗存》中的诗作大多富含典故艰涩难懂,一般人颇难解读索引!经杨绛这一“作为”,似乎钱氏就“安全”了!并且也“全”了钱氏“忧世伤生”的实际,两全其美。其实写成于文革后期的《管锥编》之所以采用文言和繁体字,其由一也。
实际上抗战期间钱氏沦陷沪上,“围城”心境顿生,“忧世伤生”,困苦不堪。为求排解,遂创作《围城》并完成《谈艺录》,此举正是他所谓“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6]这是钱氏创作《围城》期间的处境与创作心态,杨绛虽然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努力避而不谈,却又担心因此而被读者“坐实”说钱氏对世事漠不关心只是“痴玩”,她也只好在该文结束部分写道:“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令人回肠荡气。”[1]192
因此,《围城》的创作当然既与作家与生俱来的精神特质有关,但就《围城》的创作背景、主旨及内容来看,更与作家当时“忧世伤生”的精神世界有关。换言之,创作《围城》的钱氏或许的确是个“痴气”旺盛的钱氏,但更是个“忧世伤生”的钱氏。
二、《围城》与《西游记》的互文性问题
《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述及儿时锺书“家里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锺书在家里已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其实钱氏自幼及老,一生酷爱《西游记》,痴迷程度非常人可比,然而杨绛在此对其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或许是不好意思多说。诚如钱氏的学生、复旦学者王水照所说,一般人年幼时会被《西游记》所吸引,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则对《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更感兴趣,大都不会在小说名著中对《西游记》打高分,然而钱锺书对《西游记》的强烈兴趣却至老不减,反复阅读。据统计,《管锥编》中引及《西游记》达50多处”[7]49,《钱锺书手稿集》以及公开的钱氏与人往来书信中都屡见称述。而且年逾古稀的钱氏仍旧爱看儿童动画片和电视连续剧《西游记》[8]34-35,仍像孙悟空一样充满率真与童趣,真是“痴气”不减。他曾对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同事刘世德说:“我不喜欢《红楼梦》。我也不喜欢《三国演义》。我喜欢《西游记》,喜欢《儒林外史》。”[9]210-211显然,《西游记》滑稽玩世戏谑的美学风格吻合了钱氏的审美取向,与钱氏的“痴气”相投,与其诗意的性情相合,钱氏的性情与“痴气”也因之而深受激荡。
由此来看杨绛述及儿时锺书最爱玩“石屋里的和尚”游戏,这段传述材料已经足够引起研究者注意《围城》与《西游记》之间的互文关系——将对《围城》的互文性研究引向钱氏一生最爱的《西游记》。杨绛描述的游戏情状令人联想及《西游记》开篇仙石孕育石猴仙胎以及仙胎打坐禅定吸取日精月华的情状,“被单”则被儿时锺书拟想作袈裟了,这是儿童本真的体现!杨绛虽点到为止而不说破,只将钱氏此行为“认真”归结为“痴气”作罢,并且钱杨都不曾说破此一互文关联,但《围城》在创作灵感、思想意蕴、情节结构、象征意象、叙事方式等诸方面都受到了《西游记》的影响。其实杨绛所论钱氏之“痴气”可与孙悟空之“猴气”相关联起来解读,《围城》对人类心性的艺术探索与《西游记》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多心经》之间的关联也极富奥妙……不过作为作家,毕竟谁也不愿自己的作品被读者认为受此前古今中外某作家作品的影响从而降低自己作品的独创性和可崇拜性,所以一般都不愿主动言及或承认。所以此前虽有评论认为《围城》受英国某些作家作品的影响,但钱杨对此从来不应一词,更何况一向自视甚高的钱氏怎可认同他的创作乃为前人作品影响的产物呢?
客观地说,钱氏学贯中西,其小说创作及作品主旨也体现了其“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6]之理念,比如《围城》主旨灵感来源于英国和法国两个古谚“鸟笼”和“围城”意象,而在笔者看来《围城》主旨的灵感同样来源于东方宋明理学,特别是心学——钱氏以文学创作来注解心学,表达他的心学观,探讨人的心性问题。又比如早有研究者注意到《围城》在创作上与西方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诸如菲尔丁《汤姆·琼斯》)的互文关系[10],也就是说研究者早已注意到西方文学与《围城》创作的关系,但至杨绛写作《记钱锺书与〈围城〉》时仍旧未有研究者注意到《围城》与中国古代重要文学典籍(诸如《西游记》)之间的互文语境关系,事实上直到今天也乏少有人领会和注意。
所以杨绛述及儿时锺书最爱玩“石屋里的和尚”游戏,目的(至少表面上)虽然在于论述钱氏的“痴气”表现,但客观上提示了研究者注意《围城》与钱氏最喜欢的《西游记》之间的互文性问题,注意钱氏自由自适的“痴气”精神同《西游记》中孙悟空那被重点规驯的“心猿意马”的自由精神意志之间的互文关系。
三、钱氏的自由天性被扼阻的问题
《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还谈了一个意思,就是钱氏的“痴气”——自由自适的自由天性——遭到人为扼阻,致其小说《百合心》被迫停笔作废,《围城》遂成绝响。
杨绛不吝笔墨长篇细述钱氏表现出来的“旺盛”的“痴气”——这一与生俱来的、原初的、随性的、具有创造力的且未曾受到人为扼阻的特质,或许也是人的一种本性,它在一定条件下自由呈现。这让人联想及《西游记》中孙悟空身上表现出来的“野性”——小说着重书写的孙悟空身上(被天庭、如来、观音及唐僧等势力阶层所努力规驯)的“心猿意马”。不过按《西游记》故事的内在逻辑,这一自由自适的自由天性最终受到了规束,因而作为修行者的孙悟空得成“正果”。然而按杨绛述来,自由天性受到扼阻的钱氏,至少在小说创作上再无“正果”面世。
按杨绛所写,钱氏与生俱来之“痴气”,解放前即便是在严父的管控和传统人文环境的拘囿下也未被扼阻,“他淘气、天真,……他的痴气……钱锺书的父亲认为这个儿子的大毛病,是孩子气,没正经”[4]289,但杨绛颇为欣慰自豪地说是她“保住了钱锺书的天真、淘气和痴气”。不过,杨绛所谓的钱氏的“痴气”应该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基于不同的人生内容而有不同的体现,比如也体现在他自青少年时代开始并持之一生的狷介、好藏否人物以及他的诗文小说创作等才情意兴的释放上。1949年钱杨选择北上京城,加入新中国领导下的清华大学执教,稍后转入中国科学院,继而钱氏被借调参与毛选和毛诗的英译工作。《记钱锺书与〈围城〉》中杨绛写道:
锺书写完了《围城》,“痴气”依然旺盛,但是没有体现为第二部小说。一九五七年春,“大鸣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诗选注》刚脱稿……写了《赴鄂道中》五首绝句……“碧海掣鲸闲此手,祗教疏凿别清浑。”“弈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后两首寄寓他对当时情形的感受,前一首专指《宋诗选注》而说……据我了解,他自信还有写作之才,却只能从事研究或评论工作,从此不但口“噤”而且不兴此念了[1]192。
“闲此手”“事多端”“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驻车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可见,钱氏的“痴气”显然是被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吓阻和扼阻了。
实际上1980年2月钱氏在《围城》重印前记中写道:“我写完《围城》……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我把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兴致大扫……我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11]智者如钱杨二人,对彼时社会政治形势何等敏感,因之而应对沉着。而《百合心》的停笔作废,可谓壮士断腕。
所以说,有如孙悟空接受了如来佛主的安排皈依了佛门并承担护送唐僧取西经的任务后,孙悟空与生俱来的“野性”开始接受被驯服,亦即“心猿意马”开始被驯服,自由自适之精神备受限制,显然,钱氏的“痴气”在当时形势下至少是受到了较大的扼阻,这特别是在其于该时期所著之《宋诗选注》中呈现得尤为明显,以至于钱氏在《宋诗选注》序中说:“这部选注是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已故郑振铎先生要我干的……由于种种原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不过,一切这类选本都带些迁就和妥协……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12]295钱氏如此计较得失,显然这是他的一部颇为特别的学术成果!然而杨绛说《管锥编》和《谈艺录》代表钱氏好学深思的一面,《槐聚诗存》代表钱氏“忧世伤生”的一面,《围城》代表钱氏“痴气”的一面,却唯独不提《宋诗选注》,令人何等讶然!要知道,钱氏自1949年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呆了几十年,唯有《宋诗选注》是其明确接受上级指示并独自完成的一项“重要学术任务!”杨绛在此却只字不提,显然是钱氏对《宋诗选注》颇不满意。
由此可见,杨绛所写《记钱锺书与〈围城〉》中特别是第二部分——“写《围城》的钱锺书”——杨绛絮絮叨叨不厌其烦地讲述钱氏自小到大(“大”至解放后50年代初钱氏在清华期间常持长竹竿帮自家的猫同林徽因家的猫打架)的那些但凡能反映钱氏之“痴气”情状的琐碎事情和细节是何等重要!这要求研究者能从一个整体来看待杨绛长篇细述钱氏的“痴气”所要表现的目的和意义,注意《记钱锺书与〈围城〉》的内在逻辑的转折处和叙事结束时间都是在解放后的1957年——即“痴气”旺盛依旧的钱氏未再进行小说创作。如此转折和结束,杨绛的行文安排显然自有用心,那就是:在进入1950年代的社会政治环境后,钱氏的“痴气”,也就是其自由自适的“痴气”秉性即自由天性被扼阻,因此尽管“‘痴气’依然旺盛,但是没有体现为第二部小说”。
其实,许多研究者忽略了《记钱锺书与〈围城〉》中所包含的两个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前者(“钱锺书写《围城》”)其实谈的是钱锺书与其笔下《围城》世界及其中人物的内在关系,后者(“写《围城》的钱锺书”)谈的是写《围城》的钱锺书的内在特质——杨绛即谓这一内在特质促成了《围城》的写就并织就了《围城》的风格。这两个部分,就前一部分来说,杨绛在字里行间暗示出钱氏在《围城》中集中体现了他对身陷“围城”困境中的人对自由自适的精神的肯定与渴求,而就后一部分来看,杨绛是说钱氏的身心及其人生的点点滴滴都饱含着自由自适的精神品质。换句话说,杨绛通过这篇文章所呼吁的,恰是她夫妻俩向来特别看重的——自由精神!而《记钱锺书与〈围城〉》虽是在胡乔木的建议下写成于1982年7月,但杨绛却并未立即将之公诸于世,或许是她觉得时机未到罢,束之高阁三年多后才又在胡乔木的“过问”即促导下于1986年拿出来面世(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168。那时已是八十年代中期,彼时社会各阶层(文艺界也不例外)慷慨激昂,欢呼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革除旧习,以民主、自由、平等来引领时代。这也许也是推动杨绛如此写作此文并选择在此时出版此文的一个内在动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