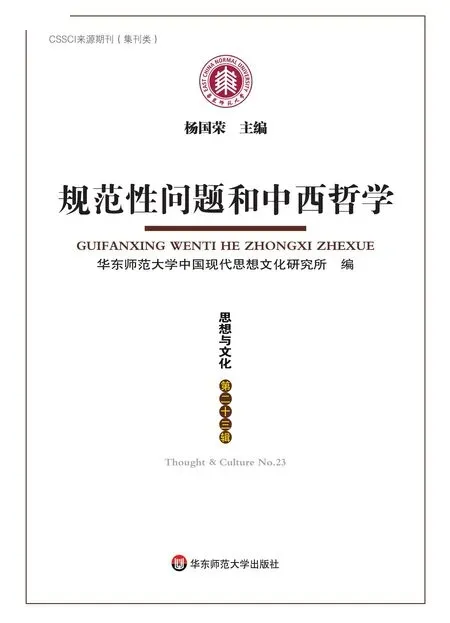“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当代修辞理论建设*
2018-04-01
●
引言
20世纪下半叶,修辞学在西方迅猛发展,在学术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西学术交流和话语互动日益频繁的今天,借鉴当代西方修辞学的理论建设经验对我们大有裨益。国内学者在介绍西方修辞学发展史时,倾向于将修辞的历史分为“古典主义修辞学、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学和新修辞学”三个阶段[注]常昌富: 《导论: 20世纪修辞学概述》,载肯尼斯·博克等: 《当代西方修辞学: 演讲与话语批评》,常昌富、顾宝桐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谭学纯等: 《接受修辞学》,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刘建华: 《修辞在网络社会中的传播价值——评〈中外名家各类比喻赏析辞典〉》,《传媒》,2016年第14期。;倾向于将20世纪欧美修辞学的发展描述为西方古典修辞的复兴,并在这一复兴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基础的当代修辞学科和修辞理论。一些学者认为,“修辞学自本世纪初复兴以来基本上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唱独角戏”[注]常昌富: 《导论: 20世纪修辞学概述》,载肯尼斯·博克等: 《当代西方修辞学: 演讲与话语批评》,第3页。;认为劳埃·比彻(Lloyd Bitzer)、韦恩·布斯(Wayne Booth)、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或凯姆·帕尔曼(Chaim Perelman)等当代主流修辞理论家都可以归入“新亚里士多德学派”[注]李建军: 《论小说修辞的理论基源及定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温科学: 《20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6年,第150页。从莱庭、徐鲁亚: 《西方修辞学》,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7页。柴改英、郦青: 《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研究》,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189—191页。详细讨论参见: 赖玉英: 《国内外亚里士多德修辞思想研究综述——兼评国内关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误解》,《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2期。。这种将“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看成当代修辞学基础的做法看似顺理成章,实则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把“古典修辞的复兴”等同于亚里士多德修辞理论在当代的复兴内化了一个预设,即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古典修辞的代表,其《修辞学》是古典修辞发展的最高峰。“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是当代修辞学的基础”或“伯克等当代修辞学家的理论都可以归入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理论体系”等表述则内化了另一个基本设定,即亚里士多德在古典时期提出的主要概念、范畴和基本理论范式是高度抽象化了的修辞原理和法则,对描述当代社会的语言现象和以往的任何社会时期一样都有普遍适用性,当代主要的修辞理论都是亚里士多德修辞理论的拓展和延伸。本文将从亚氏修辞理论的当代意义、亚氏在古典修辞中的历史地位以及当代修辞学界对“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评价三个方面入手,考察“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当代西方修辞理论形态的关系。
一、 亚里士多德修辞理论在当代的“再语境化”
在当代修辞研究中,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和思想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其《修辞学》众多文本和译本的广泛流通。20世纪末美国著名修辞史学家George Kennedy在广泛参考先前各译本和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他自己的版本,并将之命名为《修辞学: 一种公民话语理论》(OnRhetoric:ATheoryofCivicDiscourse, 1991/2007)。因其行文简练、注解丰富、评论深刻,并广泛引用了亚里士多德修辞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该译本自面世以来就被认定为亚氏修辞学的标准译本。
Kennedy的《修辞学》译本引起了很大反响,加上20世纪下半叶语言转向和修辞转向的大背景,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一股研究亚里士多德修辞理论的高潮,四本影响颇大的亚氏修辞思想研究论文集相继面世,即《亚里士多德之〈修辞学〉: 哲学论文集》(Furley & Nehamas, 1994)、《亚里士多德之后的逍遥派修辞学》(Fortenbaugh & Mirhady, 1994)、《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论文集》(Rorty, 1996)、《重读亚里士多德〈修辞学〉》(Gross & Walzer, 2000)。其中,《亚里士多德之〈修辞学〉: 哲学论文集》(1994)是第十二届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研讨会的成果,收录了11篇文章,涉及修辞推论,修辞与辩证、寓意语言、诗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的关系,常言(endoxa)的运用等话题,“反映了亚氏修辞思想研究的最高水平”[注]David C. Mirhady, “Review: Aristotle’s ‘Rhetoric’: Philosophical Essays by David J. Furley and Alexander Nehamas,”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Vol.29 No.4 (1996): 441.。它表明哲学家开始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看作其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大多数哲学家(至少那些分析学派哲学家)认为修辞和交际研究不如形而上学、认识论乃至逻辑研究高贵,因而打消了更全身心地投入修辞研究(或亚氏《修辞学》研究)的念头”,因此可以说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注]John T. Kirby, “Review: Aristotle’s ‘Rhetoric’: Philosophical Essays by David J. Furley & Alexander Nehamas,” Rhetorica, Vol.15 No.2 (1997): 214.。这种将修辞学研究作为新领域纳入哲学研究的做法还体现在哲学家A.O. Rorty编著的《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论文集》之中。然而,这些哲学研究者都试图将发展势头强劲的修辞学纳入哲学体系,让《修辞学》成为“在哲学意义上令人尊敬的”[注]A.O. Rorty, Essays on Aristotle’s “Rhetor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47.著作;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从古典修辞中汲取理论资源,使哲学继续发挥统摄整个人文领域的作用。于是,修辞在当代哲学体系中的合法性便成了首要问题。因此,在修辞学家John Kirby看来,《亚里士多德之〈修辞学〉: 哲学论文集》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而其中收录的Jürgen Sprute的《亚里士多德与修辞的合法性》一文甚至可以作为整个论文集的“副标题”。[注]John T. Kirby, “Review: Aristotle’s ‘Rhetoric’: Philosophical Essays,” Rhetorica, Vol.15 No.2(1997): 213-215.在该文中,Sprute从当代读者的困惑出发: 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不是应该远离修辞这种肤浅的东西吗?怎么会正视修辞学,讲授修辞理论并专门撰写了有关修辞的“艺术”?亚氏在《修辞学》开篇提出言说者不应该诉诸情感等“外在于主题”的手段,为什么在第二章又将诉诸情感、诉诸人格和诉诸道理并列为三大人工说服手段并加以详细论述?对此,Sprute的解释是: 亚氏在《修辞学》开篇提出言说者不应该诉诸情感等“外在于主题”的手段,这是一种“理想修辞”;但在具体的修辞实践中,若“局限于理想形式的修辞”,便几乎等同于放弃诉诸情感、人格等手段所能取得的所有社会功效,因此应该“以务实的态度看待修辞的煽动性潜力”[注]J. Sprute, “Aristotle and the Legitimacy of Rhetoric,” in Aristotle’s “Rhetoric”: Philosophical Essays, D.J. Furley and A. Nehamas (ed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27.。如此一来,修辞与亚氏的整体哲学思想相统一,修辞的“合法性”得到确立。虽然两本文集中收录的许多论文和Sprute这篇文章一样反映了早期哲学家对修辞的“偏见”[注]Lawrence D. Green, “Review: Essays on Aristotle’s ‘Rhetoric’ Edited by Amélie Oksenberg Rorty,”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Vol.83 No.4 (1997): 494.,但不可否认地,这些哲学家对《修辞学》的热烈讨论为亚氏修辞理论在当代的传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收录于以上这两套文集的文章中,修辞学界给出较高评价的当属Myles Burnyeat的《修辞推论: 亚里士多德论说服的逻辑》一文(该文收录于1994年Furley和Nehamas主编的《亚里士多德之〈修辞学〉: 哲学论文集》中,两年后它经过部分修改又以《修辞推论: 亚里士多德论修辞的合理性》为题收入Rorty主编的《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论文集》中)。Burnyeat通过“修辞推论”的研究得出结论: 修辞推论既不是省略三段论(abbreviated syllogism)也不是基于或然性或征象的三段论,而是从“理性”和“论辩”的角度来解读,认为应该将“修辞推论”看作在缺乏“确定性论据”(conclusive argument)的情况下基于人类特有的理性(reasonableness)的一系列“考量”(considerations)或“反思”(reflections)。[注]Myles F. Burnyeat, “Enthymeme: Aristotle on the Logic of Persuasion,” in Aristotle’s “Rhetoric”: Philosophical Essays, D.J. Furley and A. Nehamas (eds.), pp.3-55. David C. Mirhady, “Review: Aristotle’s ‘Rhetoric’: Philosophical Essays by David J. Furley and Alexander Nehamas,”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Vol.29 No.4 (1996): 441.显然,Myles Burnyeat的解读有明显的当代特征,为解释“修辞推论”这一亚氏修辞理论研究中的“老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另外两本文集由修辞学家主编,其中《亚里士多德之后的逍遥派修辞学》(1994)收录的19篇文章勾勒出亚氏和整个逍遥派修辞思想在23个世纪中的发展概况。该文集虽然题为“亚里士多德之后的逍遥派修辞学”,但除了少数几篇研究亚氏之后的逍遥派传统外,该文集主要还是关注亚氏本人,这说明亚氏修辞学至今仍有吸引力,同时也说明关于亚氏修辞学,学界仍有较大的争议。[注]John T. Kirby, “Review: Peripatetic Rhetoric after Aristotle by William W. Fortenbaugh and David C Mirhady,”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Vol.31 No.2 (1998): 161.《重读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是2000年由著名修辞学家Alan Gross和Arthur E. Walzer编著的论文集,收录了10篇亚氏修辞学研究论文,其作者主要是出身于言语交际系和英文系的学者,该论文集可以被看作修辞学界对哲学家日益增长的亚氏修辞理论研究热情的回应,对于“不太熟悉修辞研究领域的哲学家”[注]Carol Poster, “Review: Rereading Aristotle’s ‘Rhetoric’ Edited by Alan G. Gross and Arthur E Walzer,” Ancient Philosophy, Vol.21 No.2 (2001): 507.来说很有价值和意义。两位编者在前言中有意夸大亚氏及其《修辞学》的学术地位,将亚里士多德之于修辞学等同于柏拉图之于哲学的基础性地位,称“(除了修辞学外)没有其它任何一门学科会宣称某一本古典作品如此有效地启发了人们对当代相关的实践和理论的思考”(No other discipline would claim that a single ancient text so usefully informs current deliberations on practice and theory),这一看法实际上得不到历史文献的支持。从事修辞研究几十年的美国密苏里大学英文系教授Carol Poster指出,在过去两千年中,西塞罗在修辞学历史上远比亚里士多德更有影响力;在19世纪中叶之前,《修辞学》不管在修辞学科内部还是亚氏全部作品中都算不上特别重要的著作。[注]Carol Poster, “Review: Rereading Aristotle’s ‘Rhetoric’ Edited by Alan G. Gross and Arthur E Walzer,” Ancient Philosophy, Vol.21 No.2 (2001): 503.
二、 历史学家对亚里士多德在古典修辞中地位的重新评价
古典修辞理论是当代西方修辞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关于这一点并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这个古典修辞传统应该以亚里士多德还是以西塞罗的理论思想为中心却是当代修辞史学家争议的焦点之一。长期以来,美国修辞教育界的不少人倾向于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辞传统及其认可的原理、目标和准则奉为正统。[注]Carol Lipson & Roberta A. Binkley (eds.), Rhetoric Before and Beyond the Greek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p.1.例如,美国学者Edward Corbett认为经典修辞理论家在古典时期提出的言说技巧和修辞原则依然适用于现代写作教学,其1965年出版的著名写作教科书《古典修辞学今用》几乎照搬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发明、谋篇、风格、三种说服方式、一般话题和具体话题等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范式,因而具有“浓重的亚里士多德色彩”(heavily Aristotelian)[注]Lynee Lewis Gaillet & Winifred Bryan Horner (eds.), The Present State of Scholarship in the History of Rhetoric: A Twenty-First Century Guide, 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10, p.188.。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Thomas Conley为代表的修辞历史学家对亚里士多德在古典修辞的中心地位提出了严肃的挑战。
在其极具影响的代表作《欧洲传统中的修辞》(1990)一书中,Conley对欧美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进行了全程回顾,对西方修辞传统进行了整理和再表述。根据他对修辞发展史的梳理,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高度发达的言说实践引发了古代思想家对说服性话语的本质和功能的深刻思考,催生了高尔吉亚、普罗塔哥拉-伊索克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四个‘版本’的修辞学理论模式”[注]Thomas M. Conley, “Review: Response to Bizzell,”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Vol.22 No.3 (1992): 62.,他们在随后的整个修辞历史中此消彼长,共同构成了西方修辞思想的基础。Conley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既不同于高尔吉亚和普罗塔哥拉的哲辨思想(sophistic conception of rhetoric),也不同于他的老师柏拉图对修辞持有的批判视角,在修辞历史中的确有其重要性,但他同时明确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尽管充满了智慧和天才,它在其作者身后的许多世纪内却谈不上有什么影响……事实上,可以说一直到了19世纪它才被看成对修辞学发展真正作出重大贡献的经典。在此之前虽然它也曾被许多作者提及,却大多只是一语带过而已”[注]Thomas M. Conley, Rhetoric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 New York: Longman, 1990, p.17.刘亚猛: 《西方修辞学史》,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64页。。如果以对当时及后世修辞理论发展所施加的“实际影响力”为衡量标准,则公元前4世纪最重要的修辞思想家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伊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对他所处时代[的修辞话语]没有明显的影响,对在他之后的[古典]修辞思想家也几乎没有,或者根本就没有影响。”[注]Thomas M. Conley, Rhetoric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 p.viii.根据Conley的考证,绝大部分现存的16世纪以前的修辞文献显然尊西塞罗为权威,并保留了体现于其作品的理论框架,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西塞罗——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才是西方修辞传统中真正“有影响力的”的人。[注]Thomas M. Conley, “Review: Response to Bizzell,”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Vol.22 No.3 (1992): 62.
在Conley的《欧洲传统中的修辞》的影响下,学者们就修辞的历史编撰(historiography)展开了持久而广泛的公开辩论。当代西方最富盛名的修辞理论期刊之一、1968年由“美洲修辞学会”创办、标志着美国修辞学最新进展的《修辞学会季刊》邀请了著名的Patricia Bizzell教授为该书撰写书评。Bizzell肯定了Conley在撼动“一个单一的、相当传统的‘修辞传统’”中做出的贡献,但她认为修辞的历史编撰应该把“与当代的相关性”而不是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因此应该“以更加灵活的态度对待被一般接受了的修辞传统”,只要符合当代的写作教学和政治需要,不管是“传统的传统”(traditional tradition),还是未被接纳的女性修辞、有色人种修辞等其他修辞传统(alternative rhetorics)都应纳入修辞的历史叙事之中。[注]Patricia Bizzell, “Review: Rhetoric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Vol.22 No.3 (1992): 61.不管Conley和Bizzell在具体的编史过程中的立场有多大的差异,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即不再相信存在一个唯一的、正统的亚里士多德修辞传统。
与此同时,以Richard Rorty和Stanley Fish为代表的当代反基础主义思想家跟古代哲辨师一样,对现代以来人们深信不疑但实则禁锢思想、限制话语可能性的各种观念和预设进行了解构,对构成现代主义话语秩序基础的“真理”、“本质”、“理性”、“客观”等概念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西方文化将“科学”、“理性”、“客观”和“真理”等概念捆绑在一起,科学被认定为是对世界的一种“理性”、“客观”的探索,为人类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真理,真理本身则是与“现实”契合或“正确反映”了“现实”的表述,这些观念造成的客观主义、“唯实主义”在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构成了现代主义的观念基础。Rorty等人指出,人们只要认真审视导致我们接受唯实主义观念的那个思维过程,就不难看出,其关键环节并非是基于“事实”与“逻辑”的严密推理和论证,而是通过某种“信仰的跃升”实现的,跟人们用以“支撑自己深信不疑的宗教观”的那种不通过推理的“顿悟”并无二致。在Rorty看来,话语的发展史不是客观、理性地反映现实并揭示真理的历史,而是人类玩不同的“语言游戏”,应用不同词汇对事物进行各种“描述”和“再描述”以达到各种不同目的的历史。他提出,“我们可以通过重新描述使事物看起来或好或坏,或重要或无足轻重,或用处很大或一无所用”;他还指出,话语的演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运用各种新方法,对许许多多的东西进行再描述,直至一个新的语言行为格局被创造出来,使正在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动心并加以采纳”。Rorty在宏观层面上对修辞无与伦比的功用和力量做出了具有震撼性的再表述,他的这些观点表明,当代哲辨思想家和古希腊哲辨师一样对话语无穷无尽的力量表现出“醉心”,并继承了古典修辞的“言说是一位大权在握的王公,它能够通过最为细微精致的手段产生最为神妙的效果”的著名观点。在他们的启发下,Edward Schiappa等当代修辞学家公然为古代哲辨师平反,推翻了从柏拉图到洛克等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加在他们头上的诸如“诡辩”、亵渎神明、颠覆真理、蛊惑民众等恶名。[注]刘亚猛: 《西方修辞学史》,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296—299页。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7-9.
以Rorty、Fish为代表的哲辨思想的兴起以及Conley对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传统修辞历史观的质疑进一步激发了西方学者对修辞历史的研究兴趣。早在1988年,“大学作文与交流协会”(CCCC)专门就以“修辞历史编撰背后的政治”(politics of historiography)为主题邀请了8位卓有成就的修辞历史学家围绕着修辞历史研究的方法、内容和目的展开深入讨论,史称“八人小组”讨论会(Octalog),他们的主题发言和在场听众的主要反馈一并刊发在著名的国际修辞理论期刊《修辞评论》(RhetoricReview)上。因为该讨论产生了巨大反响,《修辞评论》又相继推出了Octalog II (1997)和Octalog III (2010)。与Octalog I相对保守和宽泛的讨论主题相比,Octalog II明确提出将修辞历史“引向局部的、有争议的、被边缘化了的历史和修辞实践并鼓励人们倾听被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解释所遗忘的声音”[注]Octalog III, “The Politics of Historiography in 2010,” Rhetoric Review, Vol.30 No.2(2011): 109.,如Jasper Neel, Edward Schiappa, Kathleen Welch等主题发言人提出对古典哲辩修辞的重新评价。而Octalog III邀请了包括毛履鸣(LuMing Mao)在内的非西方学者担任小组发言人,将修辞历史研究的兴趣延伸至西方之外的修辞传统,更加关注“权力机制和身份建构问题”[注]Ibid., p.110.(dynamics of power and issues of identity formation)对历史编撰的影响。总之,当代修辞理论家就什么是修辞的历史、修辞历史研究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对古典哲辨修辞应该如何重新评价、女性修辞在修辞历史中起了什么作用、非西方修辞传统是否应该纳入修辞的历史、修辞在当代有什么地位和作用等重大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所有的与会者都主张并致力于开拓修辞的历史,使它超越Graff和Leff所总结的“欧洲男性白人民主”[注]Ibid., p.110.的修辞传统。可见,当代西方修辞史学家普遍对“正统的修辞传统”产生质疑,这一传统的基石,即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思想,不再被当代修辞研究主流当作是古典修辞的合法代表。
三、 “修辞转向”中的古典修辞及西方修辞学界对“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质疑和否定
理顺修辞历史的发展脉络并从古典修辞理论中汲取理论资源一向被当代修辞学家中的大多数认定是修辞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曾经有一段时间,这种“古为今用”的情结突出地表现于一种被著名美国修辞学家Edwin Black称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Neo-Aristotelianism)的理论建设和实践之中。这里的所谓“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指的是某种以“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修辞学为基础的当代修辞理论或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征包括: 强调修辞话语的类型(庭辩性、审议性和表现性)、论据的分类(诉诸逻辑、诉诸情感和诉诸人格)和修辞的五大任务(发明、谋篇、风格、记忆、发表);此外,它还关注如何说服特定的受众。[注]Edith Babin & Kimberly Harrison, Contemporary Composition Studies: A Guide to Theorists & Terms,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9, p.204.从表面上看,该理论范式为当代修辞研究提供了古典修辞理论的主要概念资源,似乎是对古典修辞合理合法的运用,因而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几乎支配了修辞批评领域的半壁江山。然而,自那以后,尤其是对于当代修辞学的理论建设而言,“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不管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作为一个实践范式,却谈不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一个明显的证据是西方迄今为止出版过的两大著名的修辞学百科全书——Theresa Enos主编的《修辞与作文大百科全书: 古典时期至信息时代的交流》(1996)和Thomas Sloane主编的《修辞学大百科全书》(2006)都没有把“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收为一个词条,而只是在评价Edwin Black的贡献时一语带过而已。正如Black在其经典论著《修辞批评: 方法研究》一书中指出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一词只被用于“圈出”(circumscribe)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等古代文本提及的常用范畴和主题,并未指明如何应用原文所体现的修辞原理,因此,充其量不过是亚里士多德修辞观念穿越两千多年在当代产生的“回音”(echo of sound),必定造成原有理论洞见的改变及扭曲(alter and transform)。[注]Edwin Black, Rhetorical Criticism: A Study of Method, 2nd e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p.92.况且这些回波的“原音”——即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本身就是一个带有缺陷的概念工具。亚里士多德把修辞看成“在判断过程中实现修辞目的的能力”,这一认识不管是对当代修辞实践还是对修辞话语的评价都显得过于局限、过于理性主义,以至于将某些话语、受众类型及某种思维状态排除在外。[注]Edwin Black, Rhetorical Criticism: A Study of Method, 2nd ed., p.131.正因如此,Black在该书的前言部分就提出了对“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严厉批判,认为它“方法上缺乏多样性、可资批评家选择(的程序)不够多”,作为一个“修辞批评模式”是“极度错误的”。[注]Ibid., pp.xvii-xviii.这一权威论断不啻是宣告了“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破产”的一纸“讣告”(obituary)[注]Dilip Parameshwar Gaonkar, “The Idea of Rhetoric in the Rhetoric of Science,”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Vol. 58 No.4 (1993): 262.。Black对“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批判引起了当代修辞批评界的广泛共鸣,已经完全渗入其学科意识之中。当代美国修辞理论家迪利普·加翁卡(D. Gaonkar)甚至认为Black的批判表面上局限于对亚里士多德修辞原则和概念的质疑,实际上却是在拷问整个古典修辞及其法则和术语在当代修辞批评中的用处。[注]Ibid., p.262.
在Gaonkar[注]Dilip Parameshwar Gaonkar, “Rhetoric and Its Double: Reflections on the Rhetorical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The Rhetorical Turn, Herbert W. Simons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p.341-366. Dilip Parameshwar Gaonkar, “The Idea of Rhetoric in the Rhetoric of Science,”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Vol. 58 No.4 (1993): 258-295.本段有关加翁卡的引述主要综合了以上两篇文章的观点。看来,当代修辞在理论建设上存在两大问题。首先,对古典修辞过度依赖。与古典修辞相比,当代修辞实践呈现出两大显著差异: 其一,修辞的范围已经大大超越了古典修辞界定的说服性话语。就算是比较保守的修辞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尽管西方修辞传统有一定的连续性”,古典时期所界定的基本范畴,如修辞目的、受众、创作过程、论辩、组织谋篇和文采风格等,依然是各个历史时期修辞理论的基本关注,“但在这漫长的修辞历史中,修辞已经极大地扩展并改变了(rhetoric has grown and changed)”[注]Patricia Bizzell & Bruce Herzberg(eds.), The Rhetorical Tradition: Reading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 Boston: Bedford Books, 1990, p.7.。当代的修辞话语已经包括了从微观的科学论文到广告宣传、公关、新闻传媒、公共外交等更加宏观的修辞实践形式,这是古典修辞不可企及的。其二,当代修辞学家颠覆了经典理论家更多地把修辞看作“实践/生产的活动而不是批评/解读的活动”(rhetoric as a practical/productive activity over rhetoric as a critical/interpretive activity)的传统,而更偏向于把修辞当成一种阐释工具。Gaonkar将当代修辞研究的这一倾向称为“阐释性转向”(interpretive turn),并认为当代修辞研究本质上是一种“阐释性的超级话语”(hermeneutic discourse)。这种“阐释性转向”起初正是以“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面目出现的。与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把修辞界定为“一门生产性艺术”相比,“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修辞实践形式即修辞批评,显然展示的是修辞“解读性的一面”(interpretive axis)。也就是说,“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其实已经完全跟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初心”不相干。然而,无论是有名无实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还是在它之后出现的多元理论模式,如现象学、结构主义、戏剧主义,都或多或少地依赖古典修辞提供的“词汇”,而后者的目标在于提高话语生产的能力而不是促进对修辞话语的理解。再者,“古典修辞所提供的那些概念、范畴、法则等在理论上过于‘单薄’,难以使修辞批评家在进行表述和分析时达到应有的深度、强度、精度和信度”[注]刘亚猛: 《当代西方修辞学科建设: 迷惘与希望》,《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如果说“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提法的短暂流通折射出某种在古典修辞话语的基础上重构当代修辞理论的愿景和规划,则这一规划执行起来一直步履蹒跚,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勃然兴起的“修辞转向”形成明显的对照。由于这一“转向”,修辞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说服艺术”,而早已被广泛接受为一门“关于基本建构的艺术”(an architectonic art)。Gaonkar认为该“转向”有显性和隐形两重表现。代表了“显性修辞转向”的作者通常直接运用修辞学词汇作为一种解读和批评方法(如Wayne Booth, Paul de Man, Ernesto Grassi),或者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明确阐明修辞与当代思想的相关性(如Chaim Perelman, Kenneth Burke, Richard McKeon, I.A. Richards)。代表了“隐性修辞转向”的作者和作品通常并未使用修辞学术语,但其理论却充满了修辞精神,如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Steven Toulmin的《论证的使用》、Gadamer的《真理与方法》、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Habermas的《合法化危机》等当代伟大的理论著作。由这两条“显性”和“隐性”线索共同构成的“修辞转向”对当代修辞的理论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迫使其一次次调整对自我的认知。[注]Dilip Parameshwar Gaonkar, “Rhetoric and Its Double: Reflections on the Rhetorical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in The Rhetorical Turn, Herbert W. Simons (ed.), pp.341-366.可见,“当代修辞思想发展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可以被称为‘修辞意识’的认知形态对人文科学各个领域的放射、湮散和渗透,以及隶属于其他学科的学者对丰富和发展这一意识作出的贡献”[注]刘亚猛: 《修辞与当代西方史学论争》,《修辞学习》,2007年第4期。。然而,这也提醒我们,在修辞学科体制内,专门从事修辞研究的学者在促成这场声势浩大的“修辞转向”中只不过扮演了一个有限的角色[注]Dilip Parameshwar Gaonkar, “Rhetoric and Its Double: Reflections on the Rhetorical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in The Rhetorical Turn, Herbert W. Simons (ed.), p.362.;化学、逻辑学、人类学等非修辞学科的著作为当代修辞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概念资源。但如果不坚持修辞的主体性,而总是试图将其它强势理论的概念、范畴、设定、观点、策略的应用范围扩展到整个修辞领域,则修辞必将沦为强势学科的附骥和补充。这正是当代修辞理论建设的另一大问题。
既然当代修辞理论建设既不能过度依赖于古典修辞,又不能附骥于其它强势学科的理论,那当代修辞学如何才能在群雄辈出的学术界立稳脚跟呢?Schiappa认为:“学术进步并不是通过在更高理论层次上吵嘴……而是通过创作出起示范作用的学术作品而实现的。当隶属于不同范式的实践者发生冲突时,胜利总是属于能够就面临的问题提出有示范意义的解决办法,从而为其他学者和研究生提供了一个研究模式的那些人。”[注]转引自刘亚猛: 《修辞与当代西方史学论争》,《修辞学习》,2007年第4期。也就是说,修辞研究必须扎根于当代广阔的话语实践,建构适用于分析当代修辞实践的具有代表性的修辞理论。在西方,“当之无愧的当代大修辞学家”要数Chaim Perelman和Kenneth Burke,他们根据“对当代修辞实践的细致观察与深入思考,分别围绕着‘动机’和‘论辩’这两个中心课题构筑起自己的原创理论体系”[注]刘亚猛: 《西方修辞学史》,第317页。。其中,Perelman的“新修辞”横跨了法学、哲学、政治学以及论辩学等领域,而Burke的思想“不管被称为‘文学批评’还是‘修辞理论’,都是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新闻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研究成果的融会和综合”[注]刘亚猛: 《西方修辞学史》,第321页。。正因为如此,Gaonkar在谈到伯克时才会这样评论道:“尽管我们都知道伯克本人曾承认自己受益于亚里士多德,但(如果据此就)认为伯克的修辞理论基本上属于亚里士多德主义学派,这是站不住脚的。”[注]Dilip Parameshwar Gaonkar, “The Idea of Rhetoric in the Rhetoric of Science,”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Vol.58 No.4 (1993): 258-295.
结语
虽然当代西方学术界对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这种兴趣更多地聚焦于对亚里士多德修辞理论的“再语境化”和“再改造”,使其与当代思维和认知方式相符合,而不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式的简单套用古典修辞。然而,即便是“改造”后的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也因为其概念母体过于抽象和“单薄”而无法有效推动当代修辞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修辞意识”对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渗透和“修辞转向”的出现表明,当代西方修辞实践与古典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典修辞理论提供的基本概念、范畴和范式已经不足以用来描述和分析当代波澜壮阔的修辞实践。另外,哲学、法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种非修辞学科在“隐性修辞转向”中的广泛参与也提醒我们,修辞学的理论建设不应局限于本学科内部的理论资源,而应将目光投至更广阔的学术领域。这一点对于中国修辞学人建设自己的修辞学理论体系不无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