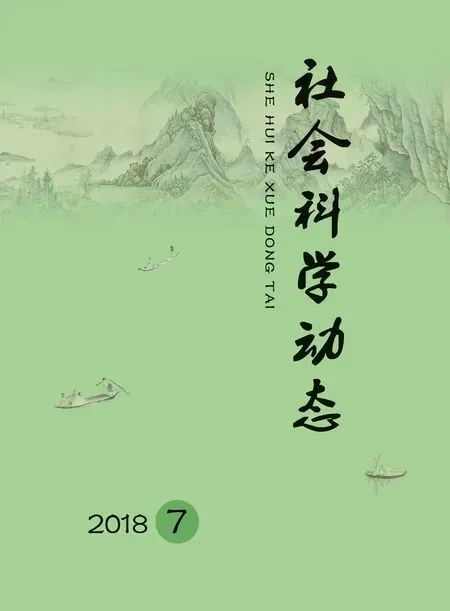慈父舒芜二三事
2018-04-01方非
方 非
2018年1月初,得吴永平先生赠予《舒芜胡风关系史证》①。捧读之际,感慨万端。
我的父亲舒芜一生的经历就是一部大书,他的前半生基本是在与胡风的恩怨纠缠中度过,后半生则在历史的谬误中焚膏继晷、吟啸徐行。他是个真正的读书人,也就是胡风等鄙视的“书生”或“五四遗老、遗少”那一类人。他读了一辈子书,也写了一辈子书。书斋之内父亲纵横诗文,挥洒自如;走出书斋便力不从心,运交华盖。
《舒芜胡风关系史证》中记载了我父亲早年的一段经历,引起了我的很多回忆和共鸣。
1945年6月,23岁的舒芜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困境,思想、工作、感情三重危机同时爆发。这年5月,舒芜读到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思想上受到很大冲击,感觉有一个“真的主观在运行”,“自己赖以立论的理论资源似乎一下子被掏空了,于是便产生了自我怀疑”。恰值此时,舒芜任教的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因教授间的互相倾轧导致舒芜可能失去工作,“饭碗”将不保。而不幸的是他的失恋又在此时发生。
作为子女,直到父亲晚年我们才知道他曾经有过的这次失恋。有一天我们几个儿女都在,父亲从他房间里拿出一封信,郑重地交给我们。抽出信,是几页旧时日记。原来,父亲初恋的那位阿姨去世后,她的女儿从母亲日记中看到母亲生前特别作了标记的几页,明白母亲心思的女儿便把这几页日记寄给了我父亲。直到此时,我们才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并且也才知道了前几年来看望父亲的几位他当年的学生中就有那位阿姨。之后的某一天,父亲又特地向我指出,他诗集中哪几首诗是为记念这夭折的初恋而作。我问及父亲当年分手的原因,父亲说:“她觉得我更坚强,应该比另一位追求者更能忍受痛苦吧。”我问:“是这样吗?”父亲说:“哪里,当然还是痛苦。”
我相信,即便在当时,即便面对自己,父亲都不知怎样倾诉,不知怎样把这种痛苦化成平实的语言或文字表达出来,而是任由它们慢慢凝结成几首含蓄隽雅的小诗。
父亲晚年,我每周休息日去看望他。父亲一生手不释卷,古籍书刊、笔记杂谈、报章杂志无所不看。我儿子教会他用电脑后,父亲更是海阔天空地在网上随意浏览。儿子还给外公配备了一台多功能一体机,父亲看到书中有喜欢的图片就扫描下来存入电脑。每次我一到,父亲便立即将一周阅读的感想心得、印象体会,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地讲给我听。父亲记忆力极好,讲述之中诗词章句、典故民谣随口吟出以助谈资。
我工作中无意间得罪了领导而不自知(多年后才知原因),从此被多方刁难,一连三次阻挡我评级,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内心很愁苦。有一天我去看望父亲,在与他聊天时忍不住提及此事,本意是想说几句诉诉委屈,没想到他马上用一种见怪不怪、超然事外的口气说:“哦,这种事我以前听过很多,某某人工资没评上,某某人职称没评上等等,但过了几年再看,也都评上了。”随后口气一转,“你听这句:满山红叶女郎樵,多美!你想想,秋天,满山红叶,一个打柴的女孩子。如果拍成电影,这个特写镜头该多美!”我问是谁的诗,父亲说是苏曼殊,然后随口吟道:
柳荫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退潮。茅店冰旗直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
父亲又从电脑中调出一个文件夹,打开一张图片让我看,正是丰子恺先生根据“满山红叶女郎樵”所作,父亲知道我非常喜欢丰子恺先生的画。
父亲不善于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伤痛与烦恼,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但他一定待之以真情,虽然有些不知所措,方法也很笨拙,却是一颗真诚的心。
1945年6月,23岁的舒芜敞开心怀,以对胡风毫无保留的信任、毫不设防的亲密感,以及自己特有的不知所措的、笨拙的方式,向当时引以为师友的胡风倾诉自己思想上的怀疑、彷徨以及内心的孤独苦闷。舒芜一连写了三封信,信中大谈苏俄作家屠格涅夫的《春潮》 《罗亭》,又提到法捷耶夫《毁灭》中的主人公。对于“饭碗”将不保这件直接威胁到自己生存的事情却没有明说,只是用有些愤世嫉俗的语言含糊地提及学院内的人事倾轧,就是“怕我们已成了中国的罗亭”及“特别窒息,窒息”这样的字眼。接着以一首律诗抒发内心的压抑与苦闷,还有“中国更是走到歧路口上”“花旗帝国的情形,亦颇可怕”这样的语言,对于“饭碗”将丢的现实却仍然没有明说,只隐约地提了一句要另谋职业,要到“坛”上去看看。
胡风最初不太明白,以为舒芜只是恋爱婚姻上出了一点问题,大略劝了劝后仍催舒芜赶快将《论主观》的答复文章写出,说《希望》第4期等着刊发。对于舒芜一再表露的苦闷彷徨,他有些不明就里,有些漠然,更有些不耐烦。及至看到舒芜信中另谋职业云云,胡风认为这表明舒芜是要到《希望》编辑部来工作,要像另外两人一样立意与自己“分一杯羹”,不禁大为反感,觉得“可怕得很”,并立即措辞严厉地给了回绝。
舒芜这种把国事家事天下事,小说人物旧诗词搅在一起的倾诉方法,令人摸不着头脑、不耐烦甚至产生误会,这在真正熟识他的人看来都很正常。但产生什么样的误会、误会到哪一步,则因人而异了。胡风竟然以为舒芜要去与他“分一杯羹”,相较于那时舒芜对胡风的坦诚相待,胡风对舒芜的这种怀疑某种程度上表明他对舒芜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在后来的书信往来中,感受到这点的舒芜除了解释外,还以颇不驯顺的态度给胡风以反诘。吴永平先生指出,“这种状况在路翎与胡风交往中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但在舒芜与其交往中却不鲜见”。
“分一杯羹”是胡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这不仅仅表现在具体的“饭碗”问题上,更不仅仅限于朋友之间,如以后胡风全副精力奋争于仕途,也曾以非我莫属之气概定要在权力的角逐中“分一杯羹”。
舒芜则挚爱文学事业,而绝意于仕途。李辉先生曾说解放初舒芜远远留在南宁的一所中学里,处境不好,非常羡慕其他朋友,一心往上爬。但史实并非如此。吴永平先生指出:首先那些“朋友们”的位置并不理想;另外,更重要的,舒芜当时可算是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重用,他曾同时担任南宁高中校长、南宁市人民政府委员、省文联筹委会委员及研究部长等七八种社会职务,是南宁有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如果不是舒芜自己坚辞,他很快就将被任命为南宁市文教局局长。然而舒芜无意于此,宁愿选择了到北京来当一名普通的文学编辑。
这一点便是舒芜与胡风的区别所在。
说来也巧,几乎就在我拿到吴永平先生的《舒芜胡风关系史证》的同时,又看到一篇小文,屠岸先生的《舒芜其人其事》②,其文称:“《致路翎的公开信》是卖友求荣的铁证,必将收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收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那是一定的;“卖友求荣”,实则不然。
关于路翎,我最早的印象就是“文革”后,父亲在家里一堆劫后余生的破烂中发现了一本草纸印刷的陈旧的《财主的儿女们》时那种惊喜的神情。父亲一遍遍地给我们讲当年他怎样介绍路翎到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工作,两人住在一间屋里,工作之余或者各自写文章,或者促膝长谈,两人的一些谈话内容后来就成了路翎正在写的《财主的儿女们》的素材。父亲一再让我看看这本书,我没坚持看下去。过一段时间,父亲又会提起,建议我看。这情景我永远不会忘。
还有一件关于路翎的事,是我们后来在徐绍羽整理的《保存在舒芜信中的路翎情书》③中读到的。在此之前,作为舒芜的子女,我们从不知有这封舒芜致胡风的信件存在。事情是这样的:1944年3月,与舒芜同住一室的路翎陷入了失恋的痛苦之中,舒芜百般劝慰无效,担心朋友会就此“毁灭”,便乘着路翎醉酒熟睡之际连夜给胡风写信求助,并把路翎刚写成还未寄出的表述“生和死”的数千言的“情书”也抄录在信中。舒芜信中流露出的对路翎感同身受的体贴,以及对胡风倾心相托的信赖之情真挚恳切,令人动容:
晚饭后,陪宁兄下街喝酒,我什么也不能说,无能为力……
现在,他好像是睡着了。我写这信,告诉你,向你求助!你曾经拯救过他,现在,也只有你的话是重要的。设法吧,来信吧,如果可能,如果必需,就来一趟吧!
我不知道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但我觉得危急,我也在惶惧之中,只有求助于你!
舒芜对朋友就是这样的真诚,过去如此,一直都是如此。他希望朋友们都能过得好,都能进步,都能跟上时代大潮。也许他不懂权宜机变,也许他不会选择最好的方式,但他总在尽力地帮助朋友。我想,无论是《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是《致路翎的公开信》,舒芜的写作动机都是这样的。
舒芜这一生,热忱地追寻过,忘我地投入过;虔诚地信仰过,痛苦地思索过;坚强地面对过,高傲地蔑视过;严肃地反思过,丰饶地收获过。为人为文,坦荡真诚。
舒芜去世后,挚友朱正先生赠挽联一幅:“二十文章惊海内,一片婆心哀妇人。”从年青时的《论主观》,到晚年文集《哀妇人》,既概括了舒芜的文学生涯,也描摹出了舒芜的心路历程。
一位历史学家曾说过:“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的材料面前,没有人能说假话。”诚然如此,吴永平先生这部《舒芜胡风关系史证》在此,一切撒谎造谣者都将被打回原形。
注释:
① 吴永平:《舒芜胡风关系史证》,台湾花木兰出版公司2017版。
② 屠岸:《舒芜其人其事》,《开卷》2017年第10期。
③ 徐绍羽:《保存在舒芜信中的路翎情书》,《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