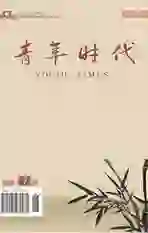“灰姑娘”故事:从“鞋子”意象看女性命运
2018-03-31朱仁美
朱仁美
摘 要:鞋子作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中西方的“鞋文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经历着从无到有、从简到繁的过程,“鞋子”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反映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中国版本的灰姑娘故事《叶限》与德国版本的《灰姑娘》均出现了相同的意象——“鞋子”,此处的“鞋子”不再仅仅起防寒保暖的作用,而是成为等级身份的外衣和反应女性命运的重要媒介。
关键词:鞋子;《灰姑娘》;《叶限》;中西文化;女性主义
“灰姑娘”的故事家喻户晓,有民俗学家进行考证,世界上凡是有人类居住的大洲便有灰姑娘故事原型。美国著名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指出:“也许全部民间故事中最著名的要算《灰姑娘》了。”[1]西方关于“灰姑娘”的最早文字记载出现于意大利作家乔姆巴迪斯塔·巴西尔的《故事集》(1632)中,后被格林兄弟收入《格林童话集》,成为世界上流传最广的版本。而灰姑娘故事的最早文本记载出现于中国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续集《支诺口》上篇,其中《叶限》篇女主人公叶限是最早的“灰姑娘”(860年左右)。
在这个广泛流传的故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象,而“鞋子”几乎出现于各个版本中。“鞋子”究竟有何象征意义,其折射了怎样的文化内涵,为何“鞋子”与女性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文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中获得启发,拟以“鞋子”作为出发点来窥探中西方文化下“鞋子”与女性命运的关联。
《灰姑娘》讲述了在继母虐待下的女孩通过神力相助找到幸福归宿的故事。我们可以把故事简化为五个部分:生母去世、继母虐待、神力相助、相会丢鞋、以鞋验婚。如果我们把研究的视角聚焦于灰姑娘故事中的意象可以发现,“鞋子”是各个版本中都会出现的中心意象,一双小小的鞋子不仅反映了中西文化中的等级制度,也是女性命运转折的关键点。
一、“鞋子”——等级身份的外衣
鞋子的产生对于人类有深远的意义,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用藤条编制和用兽皮缝制的最原始的鞋,那时鞋子仅起防止受伤和防寒保暖的作用。在封建社会,鞋子同外衣一样,是一个人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现在人们已经慢慢从关注鞋子的内在使用性质到关注鞋子外在的表征意义。
在中国,自古以来对鞋服的颜色就非常讲究。《叶限》中,陀汗王拿到一只“金鞋”,“金”代表尊贵,可想而知“金鞋”的女主人一定不是泛泛之辈。德国版的《灰姑娘》中,王子对“水晶鞋”的女主人苦苦追寻,亦是因为他相信,这样一只珍贵的鞋子必出于美丽不凡的女子。陀汗王和王子作为权力的顶层,他们对择偶的要求必然体现着等级制度的不可谮越。正所谓“灰姑娘”并不是与生俱来就遭受苦难,叶限的父亲是一位洞主,而辛德瑞拉的父亲是一位贵族。“灰姑娘”只是暂时受困于家庭矛盾而已,父亲的地位是她们将来择偶的有利的条件。
那为何东西方的“灰姑娘”都有一双美丽的鞋子,而不是漂亮的帽子或手套之类的呢?又为何中意于“相会丢鞋”这样的情节呢?曾有人类学家指出,“足”是男性的象征,与“足”紧密相关的是“鞋”,在中国民间亦有未婚女性制作一双精美的“鞋子”作为定情之物赠与男性的风俗,“鞋”与“谐”谐音,女性赠与男性一双精美的鞋子有求“和谐美满”之意。在灰姑娘故事中,“集会丢鞋”成为女性命运的转折点,“以鞋验婚”成为女性找到幸福归宿的唯一途径。
灰姑娘们的幸福与不幸福皆源于男性。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父权制不仅在物质上压迫了女儿的成长,也在精神上牢牢束缚了女性的发展。中国要求女性“三从四德”,西方要求女性“做客厅中的天使”,女性基本上被视为男性和家庭的私有财产。父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男性不屑于处理家庭矛盾,因此“灰姑娘”故事中的两位父亲不会对女儿起到实质性的保护作用。叶限与辛德瑞拉面对继母的虐待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因为她们从未被教授过反抗,反抗意味着失去男性的庇护,如果她们反抗便不会因此得到国王和王子的拯救。西蒙·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曾一阵见血地指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被社会和男性规定的。”[2]
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女性自身无论是在精神,还是肉体上,已被男权世界牢牢掌控。作为两个“天使”形象,要想改变命运,除了借助神力,别无他法,而一直被男性世界定义的“鞋子”成为解救女性的一个重要媒介。
二、“鞋子”——反应女性命运的媒介
在《叶限》中,“国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减一寸……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叶限,令履之而信。叶限衣翠纺衣,蹑足而进,色若天人也……载鱼骨与叶限俱还国,以叶限为上妇。”[3]从中国版本的“灰姑娘故事”中,陀汗王手中得到的是小巧美丽的金鞋,强调“足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审美观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古代形容女性之美有“三寸金莲”之说,“莲船盈尺”则被视为奇丑无比,更有“貌不甚佳丽者,只要双莲纤小,绣履光艳,自可动人”,南唐后主李煜更是在女人脚上大作文章。清人余怀在《妇人鞋袜考》中记载:“考之缠足,起于南唐李后主……以帛缠足,屈上作新月状……回旋有凌云姿态,由是人多效之。”[4]虽然关于妇女“缠足”的起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这个祸害中国妇女达千年之久的传统,正是封建社会中女性沦为男性“玩物”的一大罪证。缠足是为了让女性的脚停止发育,一方面是为了限制女性的活动,另一方面因为“足”是女性的性象征之一,那么“足小”便意味着女性的性感与妩媚,再者女性缠足的后果是导致女性的羸弱,而娇小、柔弱一直是中国男性对女性之美的定义之一。叶限那一双小巧美丽、轻如羽毛、履地无声的金鞋自然也就成了陀汗王费尽周折也要找到其女主人的原因了。
再看一下辛德瑞拉的“水晶鞋”,也在强调其“小”,但我们此时不能牵强附会,一定认为西方男性也以女性“双莲纤小”为美。学者考证,德国版《灰姑娘》之所以也有对“鞋”小巧的強调是因为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强调鞋“小”目的以找到鞋的主人为主,至于其他未必重要[5]。但正如中国男性强调“三寸金莲”之于女性美的重要性,西方的高跟鞋对女性的束缚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直到现代社会,高跟鞋仍与女性的性感、妩媚、自信相挂钩。所有搬上荧屏的辛德瑞拉都是脚踩着一双高跟鞋于午夜十二点仓皇离开。高跟鞋的出现与西方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有很大的关联,西方男性似乎更喜欢高挑、优雅和具有独特魅力的女性。
这其实反映了中西不同的文化内涵,中国妇女受儒家“三纲五常”的道德约束,女子须“从父,从夫,从子”,因而“娇小、柔弱”便是美;而西方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重视人的个性之美,尤其强调女性的轮廓之美与健美,只不过这种美也是局限于身体之上。
三、相关反思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及其原型理论的支撑点来源于对神话、民间传说的研究,在相隔近千年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内部,居然产生了如此相似的民间故事,不得不说是人类相似的生活境遇与相通的精神机制的原因。从“鞋子”意象出发,我们可以探寻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似性,而其所折射出的不同的文化内涵亦可以说明民族文化的复杂性与多元性。我们不仅应该看到“鞋子”背后所折射出的这些文化异同性之中的交集所在,如“鞋子”背后的女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相似或不同的地位,也应该看到跨文化交流沟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童话故事是一场残忍和绝望的拯救,或许也只有儿童能读出其中“灰姑娘”的美好归宿。世界上只有一个叶限得到了鱼骨的神力,也只有一个辛德瑞拉得到了仙女的帮助,除此之外千千万万女性只能沦落在男权社会的压制之下而无反抗之路。女性不该再抱有所谓的“灰姑娘情结”,这是一种对改变现实女性处境完全无用的“情结”。在这些传统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必须是“天使”或者“仙女”才可能获得好的“归宿”,而那些反抗注定要被消灭。如果女性把追求幸福的筹码放到男性身上,企图通过向男权社会低头来求得所谓的“幸福美满”结局,那么女性便无望改变自身被压抑的处境。
因此,笔者有理由相信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所极力畅扬的“女性写作”的使命:“女性必须书写自己,就像努力把自己嵌进世界和历史一样。女性不可能从男性邪恶变形的笔底生产的‘真理中寻到自己的本质。”[6]现在已有女性主义作家在努力改写童话,那么《灰姑娘》如何改写?或许可以从对童话做出新的理解开始,如帮助灰姑娘的并不是什么神力,而正是灰姑娘自己;面对父亲的漠视,继母姐妹的虐待,灰姑娘们要想找到幸福必定要痛定思痛,坚强克己。“集会丢鞋”又怎么可能是仓皇鲁莽之举,如果灰姑娘不留下任何信物,试问国王王子们如何寻得佳人?灰姑娘靠智慧和勇气积攢逃离苦难的资本,试问这样的灰姑娘哪还需要等待被拯救呢?
参考文献:
[1]王青.灰姑娘故事的传输地——兼论中欧民间故事传播中的海上通道[J].民族文学研究,2006(1):P16.
[2]西蒙·德·波伏瓦.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3]段成式.酉阳杂俎[M].金桑选,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4]龚维英.从性心理视角探析“鞋恋”的秘密[J].东南文化,1991(2):299.
[5]格林兄弟.格林童话[M].魏以新,张威廉,译.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
[6]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